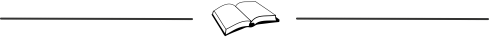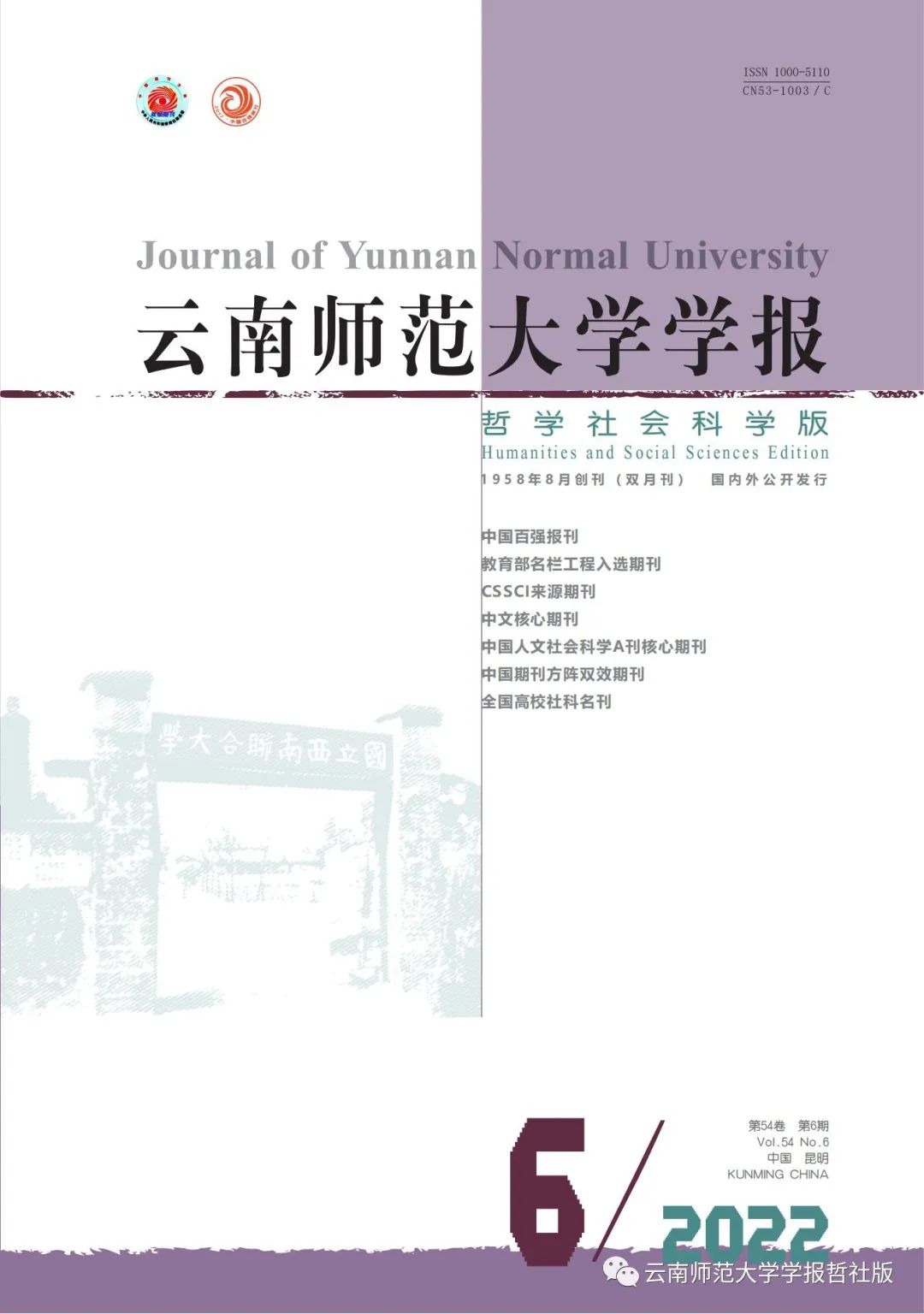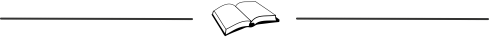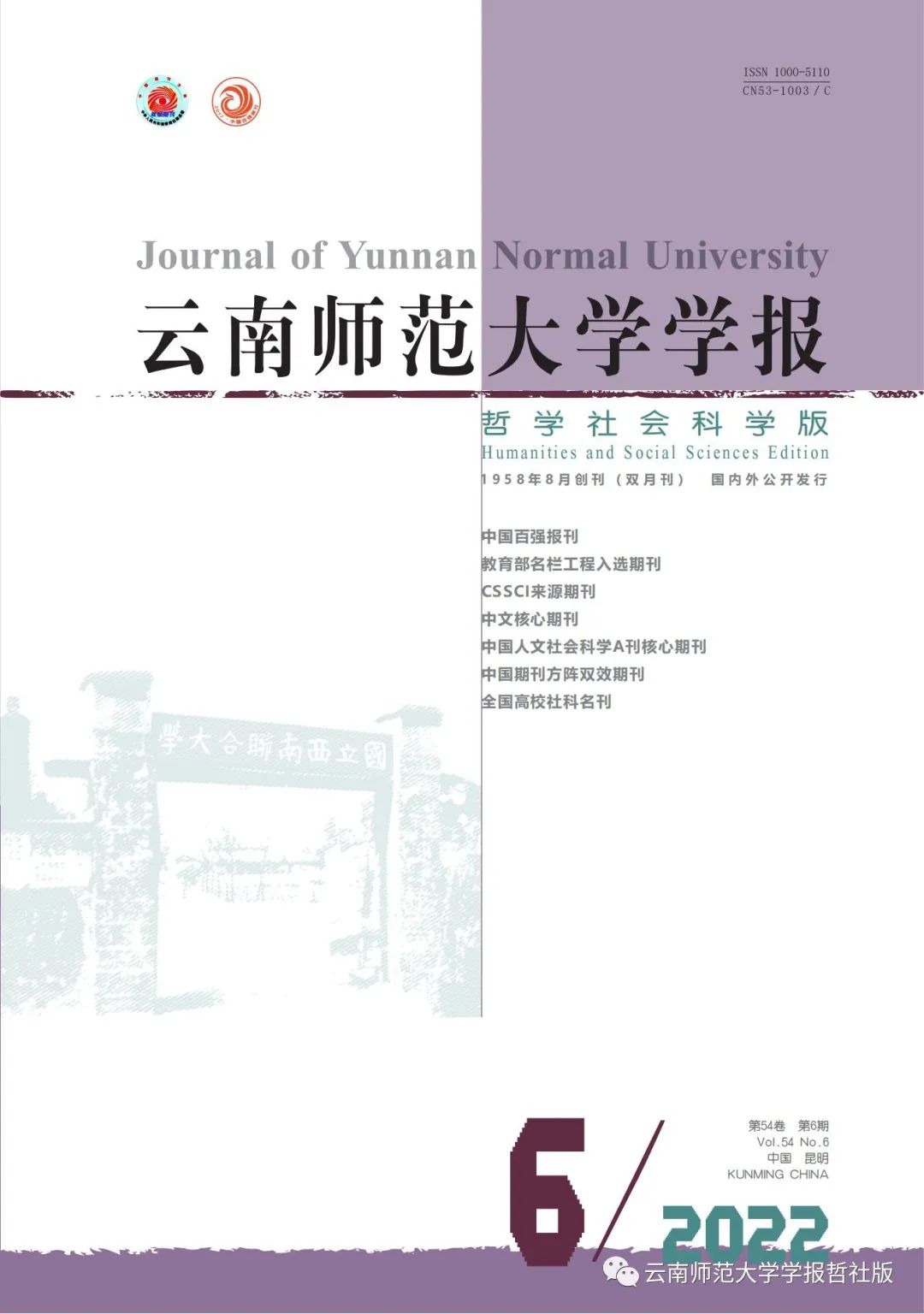宋可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江南区域史,海疆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历史地理研究》《浙江学刊》《安徽史学》《古代文明》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项。
宋可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江南区域史,海疆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历史地理研究》《浙江学刊》《安徽史学》《古代文明》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项。
政区边界与幅员、形状、区域和位置一齐构成了政区的基本要素,这中间,边界这一要素又显得颇为重要。针对政区边界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地理研究的基础工作。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陆权国家,中国历来重视对陆地边界的管理,而对于海域边界的勘定和划分则相对滞后。至明代,随着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王朝权力逐渐向海洋拓展,强化了对近海海域的管控。清代继承了前明制度,将近海海域属沿海政区管辖。不过,由于海洋疆土观念淡薄,加上海洋地理环境的复杂性,致使沿海政区之间海域边界混淆不清的状况长期存在,极不利于清王朝对海疆的治理和控制。由此,对沿海政区进行海域勘界,以明确并规范彼此的管辖范围,便有了很强的现实性和必要性。迄今为止,清代海域勘界问题仍未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关研究相对薄弱,甚至有论著认为清代从未开展过海域勘界工作。相关成果中,杨国桢先生《中国古代的海界与海洋历史权利》曾提及清代若干沿海政区海域边界的划分情况,不过未对此作深入论述。刘正刚先生从军事防御视角出发,在揭示清前期王朝努力构建海防体系的同时,敏锐观察到这一时段省际海域边界的变化。王宏斌先生《清代前期浙江划分内洋与外洋的准则和界限》及《清代前期江苏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研究》重点讨论了清前期浙江、江苏两省海域内外洋的划分情况,并对康熙二十九年(1690)两省海域边界的勘定作了简要还原,极具启发意义。总体来看,前贤研究主要是将海域勘界作为讨论清代海防建设、海域管理等相关问题的背景事件来描述,对于海域勘界这一重要历史活动本身仍缺乏系统性关照,因此难以展现这一时期沿海政区海域边界勘定、形成的动态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如何对海疆实现清晰化治理与有效控制。除此以外,在绘制清时期沿海政区的海域边界时,既有成果亦未能充分反映清代海域勘界后的划界结果。要更加深入地认识清代的海疆治理体系,辨析清代政区在中国古代政区形态中是否具有变革意义,其中一大关键是细致梳理清代的海域勘界活动,并将其与清人疆界观的演变联系起来作一整体性的考察。
中国古代很早就对近海海域行使管辖权,从史料记载来看,至迟在宋代,已经产生了朴素的海界意识。如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知明州象山县俞光凝言:“本县管海洋阔远,接连温、台州界,其间常有贼船结集。”宝庆《四明志》叙昌国县县境四至云:“东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西南至州驿三百五里,旧志云然。然海面际天,本不可以里计也……南五潮至隆屿,与象山县分界。西一潮至交门山,与定海县分界。北五潮至大碛山,与平江府分界。东南三潮至韮山,与象山县分界。西南二潮至三山,与定海县分界。东北五潮至神前、壁下,与海州分界。西北三潮至滩山,与秀州分界”。明代关于沿海政区分辖近海海域的记载颇多。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东南沿海倭患肆虐,明廷开始严厉整饬海防,建立起一套巡洋会哨制度,“分汛分洋,以为之备”。以地居抗倭前线的南直、浙江两省为例,嘉靖三十七年(1558),右通政唐顺之在《条陈海防经略事疏》中建议:“春汛紧急时月,苏松兵备暂驻崇明,宁绍兵备或海道内推择一人,暂驻舟山,总兵、副总兵常居海中。严督各总,分定海面,南北会哨,昼夜扬帆,环转不绝。”获准。次年,在应天巡抚翁大立主持下,正式划定两省水师汛地,南直水师,“南会哨于洋山,北会哨于莺游山”;浙江水师,“其南哨也,至镇下门、南麂、玉环、乌沙门等山,交于闽海而止。其北哨也,至洋山、马迹、滩浒、衢山等处,交于直海而止。陈钱为浙、直分舟宗之处,则交相会哨,远探穷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南直、浙江等沿海省份对所辖海域作了大致划分,但这并不代表沿海各省之间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海域边界。正如时人俞大猷在《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中指出的:“如陈前、马迹、韭山、衢山、岱山、长涂、羊山、马暮、沈家门、石牛港,此海中数港,为(浙江)宁波、直隶公共之岛。”不难看到,在未进行正式的海域勘界活动前,南直、浙江等沿海政区之间的海界划分并不明晰。清初,清军窘于海战弱势,无力与明朝残余势力在海面上展开争夺。为切断沿海民众与郑成功等海上抗清集团的联系,朝廷在沿海省份施行禁海迁界措施。顺治十八年(1661),苏纳海奏请将“山东、江、浙、闽、广海滨居民尽迁于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该议得到朝廷批准,并派遣苏纳海等“赴江南、浙江、福建会勘疆界”。显而易见,在这一时期,清廷难以控御近海海域,遑论进行海域勘界活动。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攻占台湾,郑氏集团降清。随着海疆日趋稳固,沿海省份展界问题被提上日程。同年十月,康熙帝遣“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往勘福建、广东海界。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雅思哈,往勘江南、浙江海界”。次年,康熙帝又下诏:“今海外平定,台湾、澎湖设立官兵驻扎,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至此,清初的禁海迁界政策遂告废除,这为不久以后沿海地方海域勘界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现实基础。康熙二十九年(1690),江苏、浙江对两省海域边界作了第一次勘定,这是清代首例有明确记载的海域勘界活动。关于这次海域勘界的起因,乾隆《江南通志》记称:“康熙二十八年,因江、浙洋面盗艘窜入商舶,总镇梁鼐奉谕旨,与浙省分汛洋面。”从中可以看到,于时江、浙海域的海盗活动颇为猖獗,严重干扰了商民船只在这一海域的航行。面对这一形势,朝廷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制定了严格的水师巡哨条例,“议准水师总兵官不亲身出洋、督率官兵巡哨者,照规避例革职”,希冀确保海疆稳定。与此同时,中央和江、浙地方政府也希望尽快勘定两省的海域边界,以明确彼此的海域管辖范围与管理权限。从这次海域勘界的人员构成来看,江苏方由两江总督傅拉塔委任苏松镇左、奇两营游击丁际昌、郭龙,浙江方由闽浙总督兴永朝委任定海镇左、右两营游击叶纪、原尔怀,四位水师将领联合主持勘定江、浙两省海域边界。海域勘界,很大程度上就是确定彼此分管海域范围的过程,而这又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尤其是水师营弁的职责及奖惩。因此,与后世相比,这一时期海域勘界活动的突出特征是:勘界关涉方皆希望尽可能多地将争议海域划给对方,以减轻自身肩负的行政、司法、军事责任。这与近现代以来海域勘界关涉方积极争取争议海域归属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果不其然,在这次海域勘界活动中,江、浙双方围绕两省海界应划在小洋山至马迹山沿线抑或是划在大洋山处产生了不小的争议。江苏方提出,应以“羊山、马迹两山南面之诸山及海面总属浙江,北面者总属江南,是以两山之南北分界,非以两山之东西为界限”。对于这一划界提议,浙江方极为不满,定海镇游击叶纪援引成例,辩称小洋山、马迹山自明中后期以来一直属江苏省(明代为南直隶)管辖,故不应以这两座本属江苏的山岛为“江、浙两界之山”;不仅如此,从地理位置来看,定海镇水师官兵从定海山出发巡哨至马迹山,“水程千有余里”,而苏松镇水师员弁出海巡哨,自“吴淞关出高家嘴,即是小羊山。出瞭角嘴,即是马迹山”,两者“相距远近,不啻天渊。”故叶纪等浙江勘界人员要求“照历来江、浙官兵会哨之处,以大羊山为止,南属浙省,北属江省”,即以大洋山作为江、浙两省海域的分界点,“其先到者,于大羊山太子岙插立木牌,而转建碑勒石,以垂永久。”值得关注的是,何以江、浙双方对两省海域边界的具体走向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通过对争议海域人文环境的考察,我们可以窥探出一些端倪。原来,大小洋山之间的这片海域,乃“黄鱼之渊薮”。每年黄鱼汛期一至,江、浙沿海民众“各驾滑稍、沙弹等船,千百成群”,捕捞黄鱼,俗称“打洋山”。他们“于官兵巡缉不到之地,以苦海为闹市,遂至海寇垂涎”。因此,该海域实为海盗活动的重灾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江、浙地方官弁在勘界过程中对于海域分界点是划在小洋山至马迹山沿线抑或是在大洋山处发生了激烈争辩。两省的划界主张上呈后,朝廷作出了裁决:以大洋山、马迹山两座山岛为江、浙两省海域的分界点,自西向东海岛、海域的归属,皆以此二山为准。并在小洋山处勒石建碑,永为定例。在江、浙海域边界的划分上,双方整体维持了一个较为平衡的格局。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勘界裁决虽未明言大洋山、马迹山两座山岛的具体归属,不过从勘界以后的文献记载来看,大洋山应属浙江海域。乾隆十年(1745),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自崇明出高、廖二嘴,即为外洋。大羊山屹峙于中,其北则小羊山,(两山)为江、浙两省分辖之处。”语中明显以小洋山和大洋山分隶江、浙两省。至于马迹山,则属江苏海域,如康熙五十年(1711),两江总督噶礼疏请江苏省每年派遣官兵“驻扎马迹山等处,巡逻海洋贼盗”。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江、浙海域勘界,奠定了江、浙两省海域边界的基本走向,并为之后海域勘界活动的陆续开展树立了典范。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朝廷复准盛京、山东两省海界:金州之铁山、旧旅顺、新旅顺、海帽坨、蛇山岛、并头双岛、虎坪岛、筒子沟、天桥厂、菊花岛等处,皆系盛京所属,令该将军委拨官兵巡哨;北隍城岛、南隍城岛、钦岛、砣矶岛、黑山岛、庙岛、长山岛、小竹岛、大竹岛……皆系山东所属,令登州总兵官委拨官兵巡哨。至铁山与隍城岛中间相隔一百八十余里,其中并无泊船之所,自铁山起九十里之内,盛京官兵巡哨。自隍城岛起九十里之内,山东官兵巡哨。如遇失事,各照地界题参。对于承担海域管理责任的沿海地方文武来说,海域边界的勘定,彼此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制度层面的明确。雍正四年(1726),闽浙总督高其倬奏称:“闽、浙之例,本处巡哨之兵,只在本处洋面巡哨。即总巡、分巡之员,亦只福建者巡福建,浙江者巡浙江。”可见在对海域边界进行初步勘定后,沿海省份可以依据相对明确的海界对所辖海域进行管理,这对减少省际海域管理纠纷,维护海洋社会秩序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海域勘界活动的持续推进与清中后期海域管理清晰化
乾隆以降,王朝海洋经济蓬勃发展,海上非法活动也随之增多,所谓“海洋盗匪,最为地方之害”。频繁的海盗活动,增大了商民船只在近海海域的失事概率。乾隆元年(1736),朝廷议准“内洋失事,文、武并参;外洋失事,专责官兵,文职免其参处”。这条律例的制定,不仅在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沿海地方文武官员的海域管理权限,同时也推动中央和地方对沿海政区的海域边界作进一步勘定,使彼此的海域管辖范围愈加清晰化。同年七月,浙江按察使胡瀛上《奏为沿海内外洋盗案州县承缉文官驳诘推诿请饬部勘明内外洋省县界限等事》一疏,疏中申明了全面勘定沿海政区海域边界的必要性:内洋形势,实与内地迥别。虽有山坳、岛屿名色,在州县原未经由,每于失事之日,虑及四参不获,即干降调。故为驳诘,推诿外洋,兼卸邻邑。辗转移查,经年不结。并有关提船户、事主前往失事处所指认内外洋面及某省某县界址者,以至事主拖累无穷。臣愚以为,海洋界址,自可预为分别。仰恳皇上敕部行文沿海督抚,除向有定界者毋庸复查外,其有内外洋并两三县及两省相邻界限不清之处,传饬沿海州县会同营员,带领谙练舟师勘明在内在外洋面、山岙、岛屿名色、某省某县界址,逐一绘图造册,详报督抚,汇齐送部存案。遇有盗案发觉,州县官会同营员即日照图讯明的实处所,按供通报,则文武各官自无耽延、推诿之弊矣。胡瀛在奏疏中指出,当前朝廷关于海洋失事案件的查勘规定存在很大漏洞,沿海地方往往利用所辖海域无界可循的现状,互相推诿追缉洋盗的责任。因此他建议沿海地方文武对内外洋界限及沿海政区之间(包括省际、县际)的海域边界作清晰勘定,逐一绘图造册,送部存案,以为凭证。关于胡瀛奏疏的处置,笔者没有找到清廷明确的旨意。不过从乾隆时期海域勘界活动广泛开展的情况来看,朝廷显然认可了他的主张。现有材料显示,乾隆初年,广东沿海县级政区之间已积极展开了海域勘界工作。据道光《阳江县志》记载,乾隆九年(1744)六月,勘定阳江海界,“先是,新宁县大澳地方屡岁失事,互诿不决。时知县庄大中奉檄,会同新会、新兴三县及广海寨、春江协各营员,勘定广、肇海面,以葛洲山中分为界,东属新宁,西属阳江,咨部立案。”道光《肇庆府志》的记录同此。新宁、阳江两县勘定海界的动机显然是为了明确大澳海域海洋失事案件的查勘职责,减少彼此之间的推诿扯皮现象。有意思的是,这次海域勘界活动的参与人员,由阳江县知县庄大中领衔,包括了阳江、新宁、新会三县知县以及广海寨、春江协水师官兵。与康熙二十九年(1690)江、浙海域勘界时单纯派遣水师营弁勘定两省海界相比,此时地方文官已经充分参与到海域勘界事务中来,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同时也是对此前胡瀛疏中“其有内外洋并两三县及两省相邻界限不清之处,传饬沿海州县会同营员,带领谙练舟师勘明在内在外洋面、山岙、岛屿名色、某省某县界址,逐一绘图造册”建议的积极回应。勘界的结果,则是以争议海域的标志性山岛——葛洲山作为新宁、阳江两县海域分界所在。类似这种县际之间的海域勘界活动,在当时文献记载中并不鲜见。乾隆《鄞县志》即收录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发生的一例颇为典型的“会勘海洋分界案”:本年二月二十八日,蒙宁波府正堂陈批卑县,具详奉化县事主夏士华呈报在黄牛礁洋面被窃钱文一案,移明各营、县订期会勘另详等情由,奉批查此案。先据镇海县讯供通详,当经批饬会同该县及象山县勘明失事洋面,绘图另详在案,仰即会同勘明黄牛礁失事处所,实系何营、县管辖,照例办理。一面绘图注说,先行通详察夺,毋得推诿迟延,致干严谴,仍候抚、臬二宪批示缴,等因。蒙此该卑职遵即订期于二月二十九日,会同镇邑汪令、象邑袁令并前营、左营、定中营各汛员带同事主夏士华等前赴该地,勘得黄牛礁一座,系悬海石礁,头东尾西,与北岸穿鼻山直对。穿鼻山脚,立有界石,载明西系鄞邑前营管辖,东系镇邑左营管辖。界石下有南北土塘一道,直至海边,塘西系鄞邑田亩,塘东系镇邑田亩。询之土人,穿鼻山即因直对黄牛礁头而名,盖鄞、镇所指以划界者也。当令汛兵捕役等,带同事主驶舟亲至失事处所,举炮为号,其地系过礁迤东,离礁约有三里。卑职等均于界石前指认,并非鄞邑界内。据定中营汛员认明,系属该营旗头汛所辖。至县境,系属镇海所辖。象邑虽属连界,但所辖洋面,系在礁之迤南,距失事处尚隔数里。除俟镇邑通详,照例严缉办理外,所有业经会同勘明,并非卑邑地界情形,合行绘图,详报宪台察核,为此备由,另册具申,伏乞照详施行。奉本府转详各宪,批准立案。这是一起十分生动的海域勘界案例。奉化县人夏士华在黄牛礁洋面遇窃报案,在宁波府知府饬令下,鄞、镇海、象山三县知县遂会同定海镇前、左、中三营水师官兵对这一争议海域的归属进行勘定。从勘界过程来看,勘界人员声称与黄牛礁直对的穿鼻山山脚,“立有界石,载明西系鄞邑前营管辖,东系镇邑左营管辖”,这说明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前,鄞、镇海已对两县的海域边界作了初步勘定和划分。经实地查勘后,勘界人员探明事主失事地点位于黄牛礁以东三里,对照之前的勘界定案,系镇海县所辖海域,与鄞、象山两县无涉。同时,将勘界结果绘图造册,由宁波府知府转呈浙江抚、臬,咨部立案。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乾隆以降,县际之间的海域勘界已逐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备的勘界程序和勘界制度。与县际之间海域勘界的高效相比,省际海域勘界直接牵涉到地方高层,勘界过程更为复杂,往往旷日持久。以江、浙两省为例,虽然经康熙二十九年(1690)勘界后,两省的海域边界得到了一定明确,但彼此之间的海界纠纷和矛盾依然存在。这主要缘于之前的海域勘界对大小洋山、马迹山以东海域的归属并未作清晰规定,只是简单制定了“自西至东,山岛洋面,俱以(大洋山、马迹山)二山为准”的判定标准,但这条标准实际上颇为模糊。因此,中央和江、浙地方亟待对两省海域边界作进一步的勘定。乾隆四十八年(1783),因马迹山东南的黄龙、梅子二山“未定专属,间有商船遭风浪,或亡失财物者,无所告诉”,江、浙两省遂对这一海域展开勘界活动,勘定以“黄龙、梅子专责浙省管辖,并令马迹山以南诸海岛,皆归浙省”。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年的江、浙海域勘界,只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海域划界方案。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通过又一次海域勘界,“分江、浙管辖界限”,最终确定以黄龙、梅子二山,“全系浙江管辖”。经过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五十五年(1790)两次海域勘界,江、浙两省的海域边界变得愈加清晰。乾隆五十八年(1793),“因蔡云山在尽山洋面被劫,两省未定参缉”,江、浙开展了入清以来第四次海域勘界活动。这次勘界,江苏方委派苏松太道通恩、苏松镇候补副将陈安邦会同浙江金衢严道邢屿、定海镇副将袁永清赴马迹山勘定两省海域边界,双方在“马迹(山)中峰最高处立准”,勘得“马迹东北数十里曰花鸟,直东偏北百余里外小山曰陈钱,陈钱南数里大山曰尽山”,于是议定“以陈钱山脚为界,南归浙江,北归江南(江苏)”。至此,江、浙两省的海域勘界工作基本完成。江、浙海域勘界是清代省际海域勘界活动的典型成功案例,与之相对,同时期江苏、山东两省海域边界的勘定过程却颇多波折。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间,据江苏、山东两省地方官呈称,元和县船户杨恒发、赣榆县船户杨长泰、通州船户高隆茂、崇明县船户范王顺、海门厅船户林灿先等五家船户先后在两省交界的黑水洋海域遭遇海盗抢劫。传统上,山东省海域以莺游山为界,江苏省海域以牛车山为界,而“牛车山距莺游门,中间尚隔一百二十里,从前未经立定界址”。不仅如此,在两省水师绘制的洋面图上,亦“无黑水洋字样”,这就使得山东、江苏两省每“遇有盗劫之案”,辄“互相推诿”,以至五起盗案案悬累年,“犯未弋获”,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乾隆帝命江苏狼山镇总兵会同山东登州镇总兵带领水师将弁亲往黑水洋处查勘,“究明何省管界”,并将此前办理勘界事务不力的江苏常镇道道台梁群英、山东登莱青道道台曹芝田革职,“以为监司规避玩误者戒”。在朝廷严令下,江苏、山东两省迅速展开黑水洋勘界工作。是年六月二十九日,江苏狼山镇总兵蔡攀龙、山东登州镇总兵恩特赫默带领水师将弁登舟出洋,勘得“(自)牛车山放洋直出,正属两省交界之区”,“就此山(指牛车山)推之,江南(江苏)、山东两省各有黑水洋”。既然江苏、山东皆辖有黑水洋海域,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黑水洋的归属作具体勘定。不过,和以往海域勘界案例不同的是,黑水洋海域“浩瀚绵长”,自此洋“遥望东去,不知何所止极。四面绝无岛屿,无所画界”,也就是说,该海域缺乏具有标志意义的海岛、礁石作为划界的依据。面对这一技术难题,蔡攀龙、恩特黑默等遂在“牛车山安定罗经针盘,先定子午,而后线分卯酉东西。卯酉之上,为北,属(山)东;卯酉之下,为南,属江(苏)。各认界管,永远遵守”。即在牛车山顶将罗盘针定准,两省海域边界以牛车山为起始,平行于罗盘针卯酉方向(即东西向)向海延伸,凡处卯酉方向以上的海域皆属山东省,卯酉方向以下的海域则属江苏省。这与此前的海域勘界活动相比,在勘界的技术水平、理念上无疑有了一定进步。这一划界方案上呈后,乾隆帝表示认可:“今据该总兵等亲往勘明,即以牛车山分界,立定缉盗责成,亦只可如此办理。所有奏请划定界址,及巡哨捕盗事宜,俱着照所请行。”至此,江苏、山东两省海域勘界大致告一段落。乾隆朝以后,沿海政区之间仍时常开展海域勘界工作。如嘉庆八年(1803)十月,“以江、浙洋面分界未定,两省互争”,苏松太道道台李廷敬奉两江总督陈大文檄令,会同浙江文武官泛海“至大羊山勘定江、浙分界”,这是对乾隆末年形成的江、浙海界格局的进一步细化。总之,清中叶以降,在中央和地方共同组织下,对沿海省、县的海域边界展开了颇为全面的勘界工作,这对于明晰地方政府之间的海域管理范围和权限,维护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边界的划分向来被视为至关重要之事,《周礼》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孟子》言:“夫仁政必自经界始。”雍正帝更强调:“疆界所关,诚为至重。”纵观清代的海域勘界活动,尽管每次勘界的起因不尽相同,但根本上还是出于明确海域管理责任、维护海洋秩序稳定的需要。尤其在清代海洋经济蓬勃发展和人口急速增长的时代背景下,大量人口涌向海洋,海洋案件频繁发生,这给王朝如何有效管理近海海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一形势,对沿海地区的海域边界进行全面勘定,使地方政府能够依据相对清晰的界线来处置海洋事务,实际上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正如乾隆时期两江总督高晋所说的:“洋面未经勘定,则承缉之责,尚无所归。辗转迁延,必至盗逸赃消,难于捕获。”自地方督抚看来,对沿海政区海域边界的勘定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当然,在讨论清代海域勘界活动时,以下3个问题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一是清代政府勘定的海域边界,究竟是不是一般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边界?二是地方文武官员是依据什么原则对勘界后的海域、海岛施行有效管辖?三是海域勘界活动的广泛开展,对清人的疆界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前两个问题,在嘉庆间一例海域、海岛改隶案中有着集中体现。嘉庆十二年(1807),闽浙总督阿林保、浙江巡抚清安泰奏请将一部分原属温州府乐清县的海域、海岛改隶玉环厅管辖,该折称:窃照海中岛屿繁多,皆有农渔寄居,舟航碇泊,须与驻扎之地方官道里相近,庶耳目所及,查察易周。兹查有温州府属外洋山岛曰东臼、曰口筐、曰扎不断、曰鲳鱼岙、曰山坪、曰鹿西,共毗连六处,向隶该府,属乐清县版图。山外洋面,则归温州镇标中营管辖,由来久矣。奴才清安泰,因巡察口岸,抽查保甲,亲诣温台一带,往返数次。查得东臼等六山,距温州府属乐清县城,计水程一百七十里。距温州镇标中营衙门,计水程二百四十里。该文武官于平时稽查搭寮种地居民及冬末春初约束闽省钓带船只,实均有鞭长莫及之势。惟查温州府玉环厅同知、参将驻扎城垣,止离东臼等山六十余里,且与该厅所属之黄门、坎门洋面相连,比较距隔温州营、乐清县之里数,远近迥殊。推求从前,何以舍近就远,不归玉环,而归温州乐清(县)、营管辖之故,则缘划界定制在未设玉环厅以前,雍正五年创设玉环厅时,因仍旧规、未及更改所致。今既查如远近情形,自应即为改正。奴才当即询问道、府、厅、县、营员,登答无异。一面札商奴才阿林保,意见相同。随行距藩司崇禄、臬司朱理会同覆加查议,具详请奏前来,应请将东臼等六山改隶玉环厅版图,其洋面改归玉环营管辖。俾就近巡缉、稽查,期于海洋有裨。如蒙俞允,所有该六山烟户嗣后改归该厅编查造报。其洋面界限,应饬巡道陈昌齐会同营员亲勘划分,咨部立案,永为遵守。在雍正五年(1727)创设玉环厅之前,温州地方文武已通过海域勘界的方式,“划界定制”,将东臼等六座外洋海岛属温州府乐清县管辖,同时以海岛附近的海域属温州镇标中营管辖。至嘉庆十二年(1807),闽浙总督阿林保、浙江巡抚清安泰等经实地查勘,发现这样的区划措置并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遂疏请将东臼等六座海岛改隶玉环厅,对岛民造册编甲;海岛附近的海域则改属玉环营。并饬令道台和水师将弁对改隶以后的海域边界作进一步的勘定,“绘图贴说,敬呈御览”。由于海岛是清代沿海政区控御海域并对其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关键支点,因此在嘉庆十二年(1807)的海域勘界后,东臼等海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行政隶属关系,实际上已经由乐清县迁转至玉环厅。换句话说,此时浙江地方文武官员勘定的这条海域边界,不仅是温州镇标中营与玉环营之间的汛地界线,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乐清县与玉环厅之间的海上分界。通过这起案例,我们可以对前两个问题作如下回应:首先,海域勘界后形成的海域边界与陆地边界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皆是政区边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海域勘界以后,地方文武基本以海岛属州县、洋面属水师的原则进行管理。至于第三个问题,从清代文献记载来看,海域勘界前后,清人尤其是地方士大夫对传统行政区划的理解有着明显变化。以浙江为例,江、浙海域勘界前,康熙《浙江通志》在书写浙江省疆域时描述道:“(浙江)东至大海莲花洋界”,仅仅把靠近宁波府海岸的莲花洋纳入浙江省管辖范围,莲花洋以外的“陈钱、马迹、羊山、大衢诸山”及其附近海域则不被包括在内。到了雍正时期,地方士人的观念已颇有不同,雍正《浙江通志》认为浙江所辖“洋面辽阔,与海外诸岛四通八达”。与之相应,雍正《宁波府志》记定海县辖域称:“(定海)北洋四百余里,至定镇左营营汛内之大衢山、右营汛内之大羊山,而与崇明镇接界。”该《志》将大洋山以南的广阔海域纳入定海县辖境,明显是对康熙二十九年(1690)江、浙第一次海域勘界结果的积极回应。乾隆以降,随着省际、县际海域勘界活动的广泛开展,沿海地方在修纂方志时,有意识地将海域、海岛看作地方疆土的一部分。对此,嘉庆太仓知州于鳌图有着深刻的体会,其在嘉庆《太仓直隶州志》中写道:旧志不列洋面,予以崇为州属邑,崇境皆州境也。洋面距邑远者,至七八百里,去州且千里,其中海岛纷峙,吾州属之行货于海道者,咸往来出入于其间,而司牧者或慢不加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因于行县时,亲至海口访之识海道者,尽得其曲折以归旋。取营汛所绘之图,目营手画,辨其方位,论其讹误。又参崇邑详案之有涉于洋面者,互相考核,而洋面始有确然可据之界,因附识于此。得益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间4次海域勘界活动,江苏太仓州崇明县与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之间的海域边界变得愈加清晰和明确。不难推断,正是在上述海域勘界活动影响下,于鳌图等沿海地方官已经把相关海域、海岛纳入地方政府的管辖范畴,并将海域勘界后形成的海域边界视同于地方行政区划的边界。无独有偶,嘉庆《澄海县志》的撰志人认为“疆域为邻邑分界,陆地宜详,而海外尤不可略”,其依据嘉庆以来澄海与南澳、饶平、潮阳、揭阳等相邻厅、县之间海域勘界的结果,详细绘制了该县海域分界图,“东南海面,与南澳厅属之五屿、凤屿(即侍郎屿),以屿之中流分界;东北与饶平县属之三屿外西南线路分界;西南与潮阳县属之浔洄山、三屿、泥屿、角屿、草屿、龟屿外东北线路分界;西北与揭阳县属之青屿炮台外东南线路,依岸上小坑汛分界”,使“守土者按图考说,了如指掌”。同一时期,在修纂嘉庆《新安县志》时,当地士人也明确将海洋视为新安县辖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安形势与他处海疆不同,盖他处以抵海而止,而新安则海外岛屿甚多,其下皆有村落,固不能不合计海面,而遗居民于幅员之外也。且以四至定县治,不能以县治定四至,故须统计海洋,开方画界。《旧志》但即县治陆地而论,此四至八到皆不足凭。即以正南言之,《旧志》谓抵佛堂门,而佛堂外如蒲台、长洲、大屿山、担杆山各处居民,竟不得隶于新安版图乎?《府志》亦谓新安南抵海四十里,而新安县城外即海,则至海四十里之说亦误。今就现在形势,合计海陆,酌定里数,而海面则以极尽处之山为止。通过对清代地方精英阶层疆界观的考察,可以发现传统上被视为政区版图以外的海洋疆土,至清中后期已逐渐成为沿海省、州、县的固有辖域。与此同时,海域勘界后形成的海域边界,亦和陆地边界一齐被看作政区边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照康雍时人蓝鼎元“海洋相通,无此疆彼界之殊”的认知,不难看出清中后期行政区划的边界形态和时人的疆界观念已经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清代持续推进的海域勘界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现实层面来看,海域勘界以后,国家权力在勘界涉及的海域、海岛确实得到了强化。以地处江、浙海域分界点的海岛为例,光绪时,朱正元在《浙江省沿海图说》中叙述大洋山情状称:“定海营派练军五十名驻(大洋山)西北大澳,自此(指大洋山)以北,尽属江苏。”除大洋山外,如花鸟、陈钱等海岛亦有兵弁驻守。“花鸟山,定海营派练军二十名驻南澳,是岛因居民皆浙人,故权由浙营管辖”“陈钱亦名嵊山,岛民患盗,由定海营派练军三十名驻澳内天后宫防守。自此以北诸岛属江苏省,因居之者皆浙人,故权由浙营管辖。”这些材料,进一步证明海域勘界在强化国家权力对海洋疆土的控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对沿海政区进行海域勘界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近海海域的控制,其核心是厘清争议海域、海岛的行政归属,明晰地方政府之间海域管理范围和权限,以更好地应对清代海洋社会环境急剧变动给王朝统治带来的挑战。从这一意义来看,海域勘界显然是清代国家对海洋疆土实现清晰化治理的有效手段。海域边界的勘定与划分关系文武官弁的职权与奖惩,不可能以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其模糊的地理认知为基础,必定有一套具体和缜密的勘界程序和勘界技术。梳理清代的海域勘界活动,不难发现清前期的海域勘界主要由水师营弁主持,同时以标志性的岛、礁作为相邻海域的分界点;清中期以后,海域勘界活动多由地方文官和水师官兵联合开展,罗盘针在海域勘界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初步具备了后世海域勘界适用的“纬度分割法”的雏形。这是清代海域管理清晰化走向深入在制度与技术层面的有力体现。某种程度上来说,清代海疆正是随着沿海政区海域边界的勘定而逐步形成和巩固的。在清代海域勘界活动持续开展过程中,精英阶层对行政区划的认识得到深化,其传统疆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清中期以后,海域、海岛作为王朝疆域版图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意识得到广泛普及,并在沿海政区地方志的编纂中深刻体现出来。这种疆界观的变化,反映了清代海疆不断演变的历史进程。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审稿费、版面费;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唯一投稿途径为云南师范大学官网
学报编辑部:
https://xbbjb.ynnu.edu.cn/zsb/CN/1000-5110/home.shtml。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