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七期请到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蔡骏治(Philip Thai)教授共同讨论他的新著《中国缉私之战:法律、经济生活及现代国家的形成(1842–1965)》(China’s War On Smuggling: Law, Economic Lif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tate 1842–1965)。本文为蔡教授对本期书评的回应,刊于《广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本期书评请见:
沈佳颖 | 缉私史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评《中国缉私之战:法律,经济生活及现代国家的形成,1842-1965》
陈佳奇 | “国家-社会”视域下近代中国“缉私”与“走私”的利益博弈:评《中国缉私之战》
现代中国缉私史书写的历程、问题与可能
对两篇书评的回应
蔡骏治
王雨/译
首先,我想感谢CCSA组织的这期书评活动。《中国的缉私之战》是一部司法史和经济史著作,它关注的是晚清至共和国初期中国沿海地区走私活动以及国家对走私活动的压制。从研究到写作,这本书花费了我十年的时间,也给了我一个和其他学者以及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珍贵机会。在这篇回应里,我会回顾一下这本书的写作历程,书评人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并对将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可能的路径。
《中国的缉私之战》脱胎于我的博士论文[1]。选择走私这个题目也是机缘巧合。2009年夏天,刚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我飞到中国进行田野考察。那时只是模糊地想做一个关于东南沿海贸易史的课题。初来乍到,我整天在档案馆里翻阅卷宗,时常看到一些材料谈及“走私”或者“缉私”。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些和我的研究看起来没有任何明显关联的大量材料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了一些厌恶:“我不想看走私,我只想看贸易!” 直到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走私就是贸易,只不过是不合法的贸易罢了。从那时起,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走私。走私不能被简单认定为法律执行不力所产生的小麻烦(nuisance)。实际上,走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意味着众多重要的东西: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种实践,公众视野中令人担心的议题,国家财政的持续威胁,以及对国家权威的顽固挑战。最重要的是,它与近代中国史上的许多关键议题都有勾连,包括国家威权的扩张以及经济生活的转变。我被许多致力于中国及其他地区走私史的研究所吸引,最终决定把他们的研究再往前推进一步[2]。于是,我开始认为,走私或许只存在于法律的边缘,但对重要历史变迁的作用绝不是微乎其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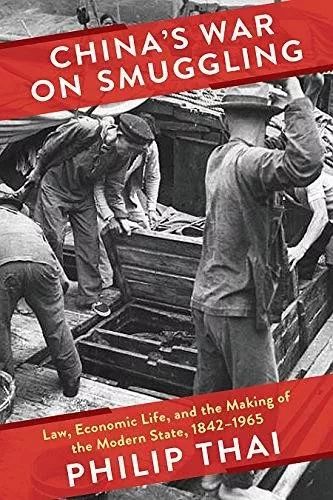
书写走私史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资料的可用性(availability)。记录这些非法行为的历史资料基本上都呈现碎片状且令人沮丧地含糊不清(elusive)。对诸如走私之类的行为的记录尤其如此,因为走私者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去避免暴力,因而也就极少被暴露到公众视野当中。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有关走私的案例,从而重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视角,我必须仔细审阅众多形式不一的材料。我的研究所依赖的核心材料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 (1854–195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1949至今) 的报告,通信及统计数据,因为这二者直接监管中国的对外贸易。这些材料由身处走私稽查最前线的人员书写,清晰地记录了不同政权下走私的实践以及政府应对方式的变化。同时,为了使材料的视角多样化,我还参考了外交档案,报纸,杂志,商业记录,甚至文学作品。司法案件尤其吸引我,因为它们揭露了法律和制度如何实施,以及普通人如何与国家权力进行实际的互动。阅读这些材料,使我看到“走私”的法律定义远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变化。同时,它还使我看到民众对走私的不同理解方式,以及为何走私对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是一种非法行为,一种牟利机遇,甚至还可以是一种存活策略。
把博士论文改写成一本书实在是个挑战。除了要应付助理教授任期内的各种事务——教课,履行行政责任,以及适应新城市的生活——我还要绞尽脑汁思考从哪里开始我的修改历程以及如何修改。我给这本书立下两个目标:拉长它的时间段以及打磨明晰它的学术贡献。针对前者,我做了额外的研究,增加了新的章节讨论晚清和共和国初期的走私活动。针对后者,我广泛阅读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司法史和经济史方面。所有的这些都帮助我在讨论现代中国的政权建设时集中于那些被已有研究忽视但又异常重要的方面,比如说查缉走私如何帮助扩张国家能力,集中司法权力, 以及转变经济生活。它还帮助我突出帝制、民国以及社会主义三个不同政权下那些不断变化以及延续的议题。
我想特别感谢两位书评人以及她们深思熟虑写出的书评。对于她们在阅读我的作品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我充满感激。尽管存在一些观点和解释上的分歧,两位书评人都对鄙著的主要观点和贡献给与了认可。以下是我对她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的回应。
陈佳奇认为“‘国家-社会’互动模式理论最明显的问题依然是采用一种二分法来考察中国历史的结构性变迁,而忽略了区别于国家、社会两大范畴的第三空间存在的可能。”我完全同意这一论断。尽管我在著作中并没有直接使用“第三领域”这个概念,但我有意识地避免了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的做法。例如,在第四章,鄙著探讨了诸多行业商人对走私的不一态度。有些商人确实与走私者“同流合污”。然而,另一些商人则组织起来,去反对走私或者向官员表达他们的忧虑。这些商人既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公会与商会,也包括影响力巨大的工业巨子刘鸿生,美孚洋行,甚至日本财阀三菱洋行[3] 。这些例子表明,所谓“社会”对走私和禁运的反应是多种多样,远非整齐划一的。

刘鸿生
陈佳奇的另一个批评是“现代国家的形塑不仅是权力的建构、强化与扩展,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文化心理层面的动员与千千万万民众的合力。”这一点我也十分认同。但语言的不同或许让人觉得我的作品忽视了现代国家形塑的这些特征。在英语中,“state”与“nation”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指涉政府,后者则强调民众。但在中文里,这两个词都被“国家”这一个词汇表达。我的作品在讨论“state-building”时,更多的是强调律法、规章的扩张与实施。相比之下,它对“nation-building”探讨较少,而这个概念更多强调促成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的民族特征。
虽是如此,我的著作讨论了民国尤其是共产党政权针对走私给大众的宣传教育。它描述了几种劝导中国消费者不去购买走私品的方式,以及使用宣传与动员来强调走私如何伤害了中国的经济与民众[4]。书中的这些案例虽然较少强调官方提升公民意识的举措, 但他们确实展示了state-building与nation-building之间的一些关联。
关于第七章论及的共和国早期的走私,沈佳颖提问:“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走私贸易,是否有根本性的差别呢?”我的答案是既有也没有。回答没有,因为任何对贸易的限制和赋税都会刺激走私。实际上,只要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只要有约束,规章和赋税,就会有走私。但也可以回答有,这是因为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持续的物质匮乏。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注意到,世界范围内的计划经济同时催生了非官方的平行经济,而后者恰恰鼓励走私和其它黑市行为[5]。既然催生走私的条件是计划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走私在计划经济中就更显得比在市场经济中更加流行。
在谈及女性走私者时,沈佳颖提出了一个非常棒的观点:“除了女走私者之外,女缉私其实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我非常同意这个建议,而且我非常感激她能够指出一处非常有用的网络文献。我的著作探究了哪些关于女性柔弱的偏见如何为女走私者带来便利以及给反走私行为带来严峻挑战[6]。在做研究期间,我遇到中国有趣的案例与故事,但无法一一将其囊括到书中。如果能往这个方面挖掘,那么无疑是可以加强我们对走私的性别维度的认知的。
沈佳颖还有一些关于本书的理论框架的问题,特别是指出没有引用诸如米歇尔·福柯以及米歇尔·徳塞都等学者的观点。这个观察有一定的道理,尽管我的书对剖析国家政策所引发的不同反应更感兴趣,而不是个人的主体性。新闻报道,政府沟通以及本书参考的一些其他材料已经清楚地记录了走私者,商人,消费者如何钻商业约束和赋税的漏洞。走私背后的统计以及隐藏域对禁运的反感背后的感受也变得清楚起来。应用福柯以及徳塞都的观点固然会给讨论“抵抗”背后的动机增加一些微妙,但他们的观点——依我之见——并不能改变本书的解释以及总的论点。
最后,沈佳颖提问能否就现代中国的国家形塑的特殊性展开谈一谈。鄙著的一个总的目标是打破平衡。一方面,我想突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国家形塑方面的相似性。比如,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初期都严重依赖关税来为国内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和保障。因此,与走私做斗争对于保障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非常重要的。至于结果,许多国家发动了他们自己的具有扩张性的,暴力的,反走私运动,而这些运动反过来又刺激了大规模的抵抗行为[7]。因此,走私,反走私,以及国家形塑在近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做法有诸多相似之处。
同时,我也想指出现代中国的经验确实有其独特之处。中国的国家塑形毫无疑问地受到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以及恢复关税自主等强大呼声的影响。中国的政权——从晚清到共和国初期 ——都一直在强调国家主权在反击走私和应对外国挑战时的重要性。这与其他国家的历史有所不同,比如18世纪的英法或者19世纪的美国,这些国家并没有把反走私的运动当做恢复国家主权的手段。
在准备和写作《中国的缉私之战》这本书时,我有幸阅读了一系列涉及中国史,世界史,司法史以及经济史等方面的著作。我开始敬佩并感激这些令人惊喜的研究,并从中发掘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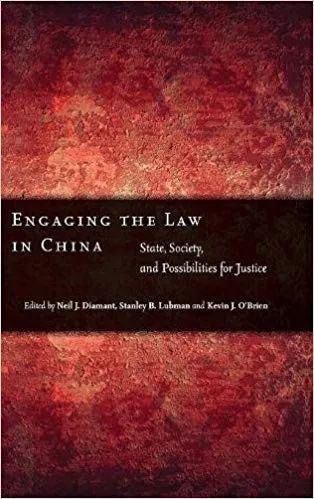
一个令人期待的领域是现代中国司法史。八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法律的研究呈现爆发式的发展。司法史与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学者探究了后毛时期政府引入新的司法制度的巨大努力以及寻常百姓运用新法的种种方式[8]。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则钻入新开放的档案之中,试图更好地理解帝国晚期以及民国时期司法表达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差异[9]。他们展示出一般民众如何频繁地,毫无保留地使用法律,法庭以及其它各种司法专业手段来解决争端或者寻求保护。所有这些研究都在展示法律,司法机构以及法律意识是如何被编织到日常生活的网络中来的,这也就修改了学界对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知。与这种繁荣相比,针对毛时代的律法的研究则显得逊色很多。最近的研究多建立在六七十年代的司法史学者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之上,但共和国早期的司法史则明显地尚待开发。《中国的缉私之战》略微探讨了共和国早期的司法状况以及这一时期有关民国司法的传说(legacies),但我真心认为更多的相关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开展起来。
另一个值得倾注更多研究力量的领域是现代中国经济史。这个领域近年来经历了重要的转型(metamorphosis)。八十年代以前,学者们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多集中于寻找中国“失败”的原因——中国失败于工业化,失败于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失败于创新,等等。但随着改革后经济的兴盛——如果不是繁荣的话——这一旧的强调失败的研究方案则日益显得落后。现在,学者们处理的议题更加广泛,包括中国商业机构与实践的突出特征,公司与企业在并不友好的环境中的适应性,以及后49中国存在的对前49中国的传说[10]。《中国的缉私之战》以多种方式触及以上三个议题,但更多的相关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经济的运行方式(dynamism)以及探索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
最后,中国海洋史这一领域需要更多的研究出现。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沿海防卫,海上贸易,海上旅行并由此对中国总是重视内陆多于沿海这一观点提出挑战[11]。但这部分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集中在明清时期而忽视了相关方面在二十世纪的延续与发展。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民国与共和国政府延续了之前对海洋边界进行定义的努力以及更好地规范化海洋经济[12]。研究走私与缉私是讨论该主题的一种方式,但相关的讨论方式无疑是多样和丰富的。
最后,我想再次表达我对CCSA以及两位书评人的感激。书评人的评论很有见解且富有建设性。我非常希望我的作品能回应她们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和建议。我也希望这次的交流不仅能够使其它读者对我的作品产生阅读兴趣,而且还能激发显得更令人兴奋的研究与对话。谢谢!
(向下滑动查看)
[1] Philip Thai, “Smuggling, State-Build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Coastal China, 1927–1949”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13): http://purl.stanford.edu/fn325kj8897
[2] 关于近代走私活动的外文研究包括:Felix Boecking, No Great Wall: Trade, Tariffs,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7); Emily M. Hill, Smokeless Sugar: The Death of a Provincial Bureaucra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0); Eric Tagliacozzo.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Smuggling and States Along a Southeast Asian Frontier, 1865–191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ans Van de Ven, Breaking with the Past: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关于近代中国走私活动的中文研究请参见:连心豪:《近代中国的走私与海关缉私》,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齐春风:《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 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孙准植:《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 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国史馆1997年版;孙宝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林美丽:《抗战时期的走私活动与走私市镇》,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硏讨会》第2卷,1998年。
[3] Philip Thai, China’s War on Smuggling: Law, Economic Lif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tate, 1842–196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129–137.
[4] 同上: 250–253.
[5] 涉及计划经济的物资匮乏和黑色市场请参见:Paulina Bren and Mary Neuburger, eds. Communism Unwrapped: Consumption in Cold War East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ita Chan and Jonathan Unger, “Grey and Black: The Hidden Economy of Rural China,” Pacific Affairs 55, no. 3 (1982): 452–71; 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ria Łoś, ed., The Second Economy in Marxist Stat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Lynn T. White, “Low Power: Small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1949–6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1978): 45–76; 冯筱才:《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中共利伯维尔场政策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 年第2 期。
[6] Thai 2018: 115–117, 152–155.
[7] 涉及近现代欧美国家的走私和缉私问题请参见:Peter Andreas, Smuggler Nation: How Illicit Trade Made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drew W. Cohen, Contraband: Smuggling and the Birth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Alan L. Karras, Smuggling: Contraband and Corruption in World Histo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Michael Kwass, Contraband: Louis Mandrin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Undergrou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8] For an overview of Western scholarship on Chinese law in the reform era, see: Neil J. Diamant, Stanley B. Lubman, and Kevin J. O’Brien, eds., Engaging the Law in China: State, Society, and Possibilities for Jus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 请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10] Recent works include: Morris L. Bian, 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Elisabeth Köll,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Brett Sheehan, Industrial Eden: A Chinese Capitalist Vi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Madeleine Zelin,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inese-language research on the pre-1949 history of commerce, finance,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s especially rich. For examples see: 陈海忠:《近代商会与地方金融 : 以汕头为中心的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李培德編:《近代中国的商会网络及社会功能》,香港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吴景平主编、朱荫贵, 戴鞍钢副主编:《近代中国 : 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 This research is very extensive. Two excellent works recently published are: Xing Hang,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1620–17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Ronald C. Po,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2] Notable exceptions include: Micah S. Muscolino, 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Chris P. C. Chung, “Drawing the U-Shaped Line: China’s Clai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946–1974,” Modern China vol. 42, no. 1: 38–72.

CCSA致力于促进中国学和比较研究领域中的年轻学者、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ccsasso@gmail.com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ssociation
本公号所刊一切文章版权均归作者所有,接洽发表或转载请在后台留言或发邮件联系,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CCSA所有内容均由编辑部同仁利用业余时间组稿、编发,欢迎诸位学友打赏支持我们的工作,打赏金额将用于为购买书评所需样书、组织工作坊等。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CCSA学术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