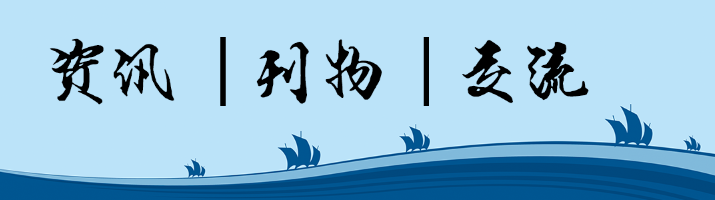

疫病与日本古代的对外交流
摘要
Abstract /
古代日本的疫病分布存在三个相对显著的区域,分别是近畿、西海道与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并且,从疫病的传播情况来看,还存在着疫病由沿海向内陆,即由西海道及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向近畿传播的倾向性。这样的传播路线,与来自唐、新罗、渤海等国的人、物在日本国内流通的路径基本一致。以天平九年(737)的疫病为代表的诸多事例也佐证了疫病由他国传入日本并由沿海地区向内陆传播的可能性。在经历数次外来疫病的侵袭后,在古代日本人尤其是贵族的观念中,“异国”“藩客”俨然成为了疫病的重要源头。这样的疫病认识在相当程度上阻断了外来疫病在贵族社会中传播的途径,但也间接影响了古代贵族排外、封闭的对外意识。
关键词:日本古代 疫病 祭祀 对外意识
进入21世纪以来,非典、新冠等传染性疾病在全球的大规模爆发,让人们再次体验并认识了传染性疾病的威力。得益于科学、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方式、手段有了很大进步,但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心理造成的冲击,以及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却有着无关时代、地域的相似。在东亚地区,日本作为与大陆地区隔海相望的岛国,具有地理上的隔离性特点。这样的特点在古代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日本人免受大陆疫病的侵袭,但恰是这种地理位置上的隔离性,同时导致了日本人的免疫能力难以建立。结果,尽管日本人免于受到频发传染病的威胁,但只要传染病从外国传入,便会迅速肆虐开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疫病尤其是外来疫病对古代日本社会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目前学界对日本古代疫病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医学史或医疗史领域,大抵以复原疫病发展史、解析病名、探究疫病的应对措施,以及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但是,疫病尤其是外来疫病与日本古代对外交流的关系,在迄今的研究中却未受到充分重视。为此,本文拟对日本古代疫病的分布及传播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疫病由外部传入日本的可能性,探讨疫病对日本古代对外意识及对外交流产生的影响。
疫病,在古代日本亦称“疫疾”“疫气”“时疫”“疫疠”“瘟疫”等,虽然不像水寒灾害一样会对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产生非常直观的危害,但由于疫病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群的大规模感染,因此疫病的发生动辄就会造成“死者溢路”“骸骨塞巷”,甚至“民有死亡者大半”的惨况,而且疫病所造成的人口损失还会间接地影响农业生产,并导致饥荒等二次灾害的出现。因此,对于古代国家而言,疫病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国之“急速大事”,需“遣使驰驿申上”,上报朝廷。正是因此,作为日本古代国家正史的“六国史”中收录了众多的疫病记录。虽然这些疫病记录通常只是只言片语地记录了“某国疫”,鲜有关于病症、危害等相关内容的记述,但仍然不失为反映古代日本疫病基本情况的重要依据。
依据“六国史”所收的疫病记录,可以大致了解古代(11世纪以前)日本发生疫病的基本情况(参看表1)。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疫病在古代日本的空间分布,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日本古代疫病的地域分布存在明显的东、西之别。具体来说,近畿以西,即畿内、中国地方(山阳、山阴两道)、九州地方是“六国史”中疫病发生的核心区域,而近畿以东,包括关东、东北地方则鲜有疫病发生的记录。
表1 日本古代疫病的空间分布情况 | ||
地域 | 次数 | 国名 |
畿内 | 15 | 大和、和泉 |
东海道 | 12 | 骏河、常陆、伊豆、尾张、安房、甲斐、三河、远江、伊势、伊贺、志摩 |
山阴道 | 10 | 石见、伯耆、出云、因幡、隐岐、但马、丹波 |
山阳道 | 7 | 长门、周防、安艺、备后、备中、备前、美作、播磨 |
西海道 | 8 | 大隅、筑前、筑后、肥前、丰后 |
南海道 | 5 | 讃岐、伊予、阿波、纪伊、淡路 |
北陆道 | 5 | 若狭、加贺、能登、越后 |
东山道 | 3 | 美浓、信浓、陆奥、出羽、近江 |
其次,就近畿以西的地域而言,存在以畿内为中心,以近畿地区为外延的疫病分布圈。从疫病发生的次数统计来看,畿内的发生次数最多,其次分别为东海道、山阴道。东海道与山阴道在古代国家的行政区划中,虽然只是地方七道之一,但从地理位置来看,东海道的伊势、志摩、伊贺以及山阴道的但马、丹波都属于近畿的地域范围。可见,近畿是古代日本疫病分布核心中的核心。
再次,在近畿以西的地域中,还存在以大宰府所在地筑紫为中心,以西海道为外延的疫病分布圈。并且,相对其他的诸道、诸国而言,疫病在西海道诸国的发生往往具有地域上的整体性与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西海道某国一旦发生疫病,很快就会在整个“大宰府”“镇西”发生蔓延,但却未必与其他诸道的疫病存在直接关联。
最后,日本古代疫病的地域分布存在南、北之别。与靠近太平洋的地方诸国相比,靠近日本海一侧的诸国具有相对更高的疫病发生率。尤其是石见、出云、伯耆、因幡、但马、若狭、加贺等位处山阴道、北陆道的沿海诸国,不仅疫病发生的频次相对较高,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均分布于日本海一侧。
由此可见,从“六国史”的记录来看,日本古代疫病的空间分布存在三个相对显著的区域,分别是近畿、西海道与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并且,从疫病的传播情况来看,还存在着疫病由边缘向核心部,即由西海道及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向近畿传播的倾向性。具体来说,即在西海道、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与近畿地区之间,存在着两条常见的疫病传播路径:一是所谓“自筑紫入京师”,即由西海道传播至京城的路径。在天平九年(737)、正历五年(994)、长保二年(1000)以及宽仁四年(1020)发生的疫病记录中,所谓“初自筑紫来”“起自镇西及京师”的表述都说明筑紫、镇西也就是西海道被视为了疫病发生的源头以及向京师传播的起点。二是所谓“自敦贺津入京邑”,即由北陆道若狭国敦贺津传播至京城的路径。圣武天皇年间的疫病、贞观十四年(872)平安京的“咳逆病”即被认为由敦贺津传播而来。
在上述事例中,天平九年(737)的“痘疮”可以说是再现疫病起于筑紫、后在五畿七道广泛传播的典型案例。根据《续日本纪》的记录,天平九年(737)三月时疫情最初出现在大宰府管内诸国,六月,平城京内也出现病例,以至“百官官人患疫”“废朝”。时至七月,疫情进一步扩大,大和、伊豆、若狭、伊贺、骏河等地也相继出现疫情。并且,依据天平九年(737)地方诸国正税帐中的减免记录推断,和泉、河内、淡路、周防、出云、备中、但马等国也都有疫病发生。可见,天平九年(737)所谓“初自筑紫来”的疫病不仅在大宰府与平城京造成了“死者过半”“路头死人伏体连连”的严重疫情,而且还传播至西海道、近畿、山阴道、山阳道等广大地域。史无前例的疫情直接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公卿以下天下百姓,相继没死不可胜计”“天下百姓死亡实多,百官人等阙卒不少”,从四月开始包括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藤原麻吕所谓“藤原四子”在内的众多公卿贵族先后病死,而因此丧命的庶民百姓更是无法计数,所谓“近代以来未之有也”。具体的死亡人数虽然无从可考,但根据当时各地的赋税减免比例推断,天平九年(737)的疫病大概造成了当时日本全国25-30%的人口死亡。
总而言之,近畿、西海道与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是日本古代疫病分布的主要区域。位处内陆核心地带的近畿作为平城京、平安京的所在地,不仅是古代日本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人口密集且流动性高。因此,无论是出于稳定政治统治的需要,还是基于客观的地域特点,近畿都必然是疫病高发且备受古代朝廷关注的重点地域。而位处边缘地带的西海道与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尽管不具备近畿一般的政治或经济地位,但西海道的筑紫与北陆道的敦贺津在古代日本却是唐、新罗、渤海等大陆国家来航日本的重要口岸,是唐、新罗、渤海等国人与物向畿内流通的起点。从对外往来的角度来看,西海道、北陆道疫病的发生以及向畿内的传播,或与外来人、物的流入与流通密切相关。
那么疫病究竟从何而来,其源头何在呢?以天平九年(737)的痘疮为例,关于此次疫病何以在筑紫爆发并蔓延诸国,历史上存在多种说法,如“痘疮初发,起自圣武天皇御宇,钓者遇藩人,继此病”“从藩船,疱痘到天下,自是患其难者多”等,认为此疾由“藩人”“藩船”即他国传入。在此基础上,还有观点认为此疾“自新罗国起,筑紫渔人船至彼国,传于其人”“此病自新罗国来,其始自筑紫渔人,船遇难风,着彼国,移于其人,病而来”,直接将新罗视为此疾的病源地。简而言之,在古代日本人看来,天平九年(737)的疫病是由他国,确切地说是由新罗传入的外来疫病。所谓“痘疮”“疱疮”,从“肢体肿胀”“大热如烧”等症状表现以及极高的致死率来看,基本上被断定为现代医学中的天花。天花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4世纪前半,据《肘后备急方》记载,东晋元帝时期天花由南洋传入中国。时至8世纪,朝鲜半岛也对这种传染病有了一定了解。而8世纪初的天平九年(737)时天花是否由朝鲜半岛的新罗传入了日本,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确有筑紫渔人曾行船至新罗,即是否存在疫病由新罗传入日本的可能性。
关于天平九年(737)是否有筑紫渔人曾船至新罗,自然是无从考证,但天平八年(736)日本朝廷确曾向新罗派出以阿倍继麻吕为大使、大伴三中为副使、壬生宇太麻吕为大判官、大藏麻吕为少判官的使节团。换言之,在天平八年(736)至同九年之间,日本与新罗间曾经进行官方层面的往来。那么使团的出使与疫病的传入与传播是否存在关联呢?《续日本纪》天平九年(737)正月二十七日条记载,遣新罗使大判官壬生宇太麻吕、少判官大藏麻吕等入京。依据《延喜式》中平安京至大宰府“海路三十日”、大宰府至对马岛“海路行程四日”的表述推算,遣新罗使团大概在天平八年(736)末或同九年(737)初返回日本。另外,同日记录还记述了“大使从五位下阿倍朝臣继麻吕泊津岛卒。副使从六位下大伴宿祢三中染病不得入京”,即大使阿倍继麻吕死于对马岛,副使大伴三中染病的内容。不过,关于两位遣新罗使于何时何地患疾,《续日本纪》中并没有记载。依据《万叶集》(第15卷)所收遣新罗使一行人所作的和歌(第3578—3722首)可知,在使团去程中行至对马岛竹敷浦时,大使阿倍继麻吕还曾在宴席上创作和歌。也就是说,大使阿倍继麻吕在天平八年(736)九月底、十月初时,在渡海远赴新罗之前仍然健在,但在滞留新罗或返回日本的途中患病,并在返抵对马岛后病死。副使大伴三中大概在同时期染病,但幸运的是并没有因此丧命。天平九年(737)三月二十八日,“遣新罗使副使正六位上大伴宿祢三中等四十人拜朝”,副使大伴三中携同使节团40人入京拜朝。相较正月时入京的大判官与少判官,副使一行的入京时间整整推迟了约三个月的时间。换言之,以副使大伴三中为首的四十余遣新罗使团成员在返回日本后,并没有直接入京,而是在筑紫停留了约三个月之久。结合大使病死、副使染病的情况来看,可以想见罹患此病的或不仅限于大使与副使,而是更多的使团成员,很有可能是某种传染性疾病在使团成员间的传播导致了使团的长时间滞留。另一方面,按照三月二十八日的入京时间推算,副使一行大概于二月底、三月初离开筑紫,而天平九年(737)的疫病恰是从三月开始在大宰府管内诸国流行。同样,在副使一行人入京后,从四月开始平城京便出现了贵族突然病逝的情况。从传播的时间脉络与路径来看,显然疫病在筑紫与平城京的爆发与遣新罗副使一行的行动轨迹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存在遣新罗使团将疫病从新罗带入日本的可能性。并且,也不能排除疫病随着遣新罗使团一行人的停留与移动在筑紫至畿内沿途广泛传播的可能。
总而言之,天平九年(737)在日本列岛上肆虐的疫病说明,8世纪时已经出现了疫病跨越海洋、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间传播的情况。并且,除天平九年(737)的疫病外,天平宝字七年(763)、延历九年(790)以及弘仁五年(814)起于九州后遍及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的疫病,也都被认为是由大陆地区传入。显然,随着人、物的交流与流通,疫病已然成为与对外交流内容无关、却又无法规避的副产品。关于疫病进入日本的途径,除官方的外交使者外,自然还存在其他的多种可能性,如在日本海海域上频繁往返的来自东亚各国的民间商人与渔人,这些人无疑也是疫病在东亚各国与日本列岛间传播的潜在载体。这也解释了为何位处边缘地带的西海道与靠近日本海一侧的山阴道、北陆道地区成为了疫病分布的主要地域。而那些行迹遍布濑户内海沿岸的外交使节团,无论是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遣新罗使团,还是唐、新罗出使日本的使团,都必然在疫病传播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由于疫病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在古代日本十分重视对疫病的应对,不仅效仿唐令构建制度性的医疗体系,在中央建立了典药寮等专门的医疗机构,并且通过积极学习、借鉴大陆地区的医疗技术,普遍推行了药疗、食疗等医疗手段。不过,古代医学及科学知识、技术水平的局限必然无法全面、有效地对疫病进行应对,而填补医学与科学在疫病应对方面不足的,正是各种形式的宗教祭祀,如道飨祭、疫神祭、傩祭等。
所谓道飨祭,按照《令义解》的解释,“谓卜部等于京城四隅道上而祭之。言欲令鬼魅自外来者,不敢入京师。故预迎于道而飨遏也。”简单来说,即在京城四角的道路上,用酒食款待的方式阻止“鬼魅”从外部进入宫中或者京城,避免疫病的发生。所谓疫神祭,按照《延喜式》的规定可以分为“宫城四隅疫神祭”与“畿内堺十处疫神祭”。二者的祭祀方法基本相同,即向疫神供奉酒、米、鱼等各种祭品,但祭祀举行的地点不同,前者在皇宫、都城的四角,后者在畿内五国间以及畿内各国与毗邻畿外各国间的十个交界处,如山城与近江的交界处、大和与纪伊的交界处等。所谓傩祭,由《延喜式》的规定可知,是由阴阳师在皇宫内举行的祭祀活动。其祭祀方法与道飨祭、疫神祭大同小异,也是向疫神供奉各种祭品,但不同的是,阴阳师同时念诵所谓“秽恶疫鬼,藏匿村村所所。千里之外,四方之界。东方陆奥,西方远值嘉,南方土佐,北方佐渡。此外远境,汝等疫鬼当居之所”的祭文。
简而言之,尽管道飨祭、疫神祭与傩祭在祭祀的方法、内容上略有差异,但其中体现的疫病认识却十分相似。首先,疫病的发生源于“鬼魅”“疫鬼”或“疫神”的存在。因此,在针对疫病的祭祀中,既有固定在六月、十二月晦日举行的道飨祭与十二月晦日举行的傩祭,也有随时因需举行的各种疫神祭。其次,疫病的传播源于“鬼魅”“疫鬼”或“疫神”的移动。并且,“鬼魅”“疫鬼”或“疫神”的移动往往是由外而内,具体来说,即由日本四方之外至畿内十界,再至京城、皇宫之内。再次,疫病的预防在于将“鬼魅”“疫鬼”或“疫神”隔断或放逐于特定的地域范围之外,而驱逐“鬼魅”“疫鬼”或“疫神”的最佳地点则位于区分皇宫、京城、畿内乃至日本内、外的“四隅”“四方”。换言之,皇宫、京城、畿内以及日本之内是“鬼魅”“疫鬼”或“疫神”不可进入的清净之地,而之外则是“鬼魅”“疫鬼”或“疫神”的可居之地、污秽之地。
归根结底,在古代日本人的观念中,疫病被视为外来的污秽之物。在这样的疫病认识中,不仅疫病是可惧的,而且疫病的由来之地也是污秽的。这样的疫病认识不仅体现着对疫病发生、传播等方面的认知,而且还关联着对日本以外的空间、国度的认识。贞观十四年(872)正月,“京邑咳逆病发,死亡者众”,平安京流行咳病,众多平民因此丧命,连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也未能免于此疾。由于此次的流行病以咳嗽为主要病症,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所谓“咳逆病”即现代医学中具有传染性的流感或肺炎。《三代实录》同日的记录中记述了当时坊间的传言,所谓“渤海客来,异土毒气之令然焉”,即将咳病的流行归咎为渤海使的到来。根据《三代实录》的记录可知,渤海使团于贞观十三年(871)十二月十一日在加贺国登陆日本;翌贞观十四年(872)正月六日,朝廷开始任命负责接待渤海使的相关使节。换言之,渤海使登陆的消息在贞观十四年(872)正月六日前被送入平安京,但渤海使一行此时尚未入京。当然,不能排除渤海使中有携带病毒者,且病毒随信使被传入平安京的可能性,但矛盾的是,在此之后直至渤海使一行入京的五月,无论是渤海使登陆的加贺国,还是渤海使入京途中经过的诸国,都没有发生类似的咳病。也就是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贞观十四年(872)的咳病与渤海使的到来存在直接联系,所谓“渤海客来,异土毒气之令然焉”不过是坊间的无端猜测而已。尽管这种主观猜测看似毫无依据,但却与疫病祭祀中体现出来的疫病认识完全相符,即疫病是异土藩客带来的毒气所致。其中不仅表现出了对疫病的恐惧心理,更影射出了对外国以及外国人的嫌恶、抵触情绪。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古代的疫病认识也是一种对外认识。
事实上,10世纪以后古代日本人尤其是贵族们的对外意识愈发地走向封闭。9-10世纪期间,在日本先后断绝了与唐、新罗以及渤海的正式国交后,以天皇为核心的贵族社会中逐步形成了外藩之人不可面见天皇、不可进入皇宫的定制。如9世纪末宇多天皇制定遗训,规定“外藩之人,必召见者,在簾中见之,不可直面”,明确禁止外藩之人直接面见天皇;公卿九条兼实在其日记《玉叶》中批判后白河法皇接见宋人的举动时,称“我朝延喜以来未曾有事也,天魔之所为欤”;公卿讨论是否应在宫中接见负责铸造东大寺大佛的宋人陈和卿时,中山忠亲直接提出“异朝俗殊,辄不可入禁里”的意见。可见,在断绝与周边国家往来的同时,古代贵族们的对外意识也愈加走向消极、封闭。当然,东亚地区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才是实际上左右日本对外政策的客观决定性因素,但在这些外部的环境因素之外,对疫病的惧怕以及对异国的排斥心理必然也在无形中加剧了贵族们消极的对外意识,甚至成为了古代日本朝廷对外交流的意识屏障。
总而言之,日本的地理环境是阻断疫病传播的天然屏障,但从疫病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古代对外往来的展开,这样的天然屏障显然失去了隔断疫病的功能,西海道的筑紫与北陆道的敦贺津,作为对外通交的开放口岸成为了外来疫病向日本传播的中转站。这对生存环境相对封闭的古代日本人所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外来疫病的传播动辄就会造成民众的大规模染病甚至死亡。结果,在经历数次由沿海地区向本州内陆传播的外来疫病后,在古代日本人尤其是贵族的观念中,“异国”“藩客”俨然就成为了疫病的重要源头。尽管这样的观念认识在现实世界中并不能阻挡海上商人与渔人的往来,亦不构成左右日本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但这样的疫病认识却在相当程度上阻断了外来疫病在以天皇为核心的贵族社会中传播的主观以及客观的可能性,也间接加剧了古代贵族排外、封闭的对外意识。从日本古代对外交往的情况来看,自9-10世纪期间日本断绝了与周边国家的往来后,日本朝廷便始终固持消极的外交姿态,尽管允许海外的民间商船来航进行贸易,但却始终拒绝与周边国家建立政府层面的外交关系。这样的政策选择一方面取决于古代东亚地区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也与古代贵族们排外、封闭的对外意识密切相关。而外来疫病无疑是影响古代贵族对外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者简介】
作者王玉玲: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研究员
原载《海交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凡在本刊发表论文,除非另有约定,视为作者同意本刊拥有文章的网络首发权。
转载敬请注明出处。
推荐阅读
2022年第3期编校人员
陈丽华、陈少丰、李静蓉、林仪
王丽明、肖彩雅、薛彦乔、张恩强
图文编辑:王绮蓉
审核:陈少丰
终审:林 瀚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海交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