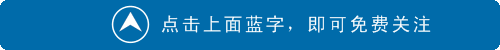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中,文化典籍作为载体的交流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是用有形的文字来沟通和交流彼此文明的,因此其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
中日两国文献典籍的交流,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东传扶桑,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规模大、领域广,这在全球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亦是极为罕见的。
中日两国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文献典籍的交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两国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差异,使其传布的渠道、媒介、和方式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日本自应神天皇(日本的第十五代天皇)之后,就不断有汉籍文献传到扶桑,直到明治维新前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到了近现代,日本出版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又大量西渐,传布到大陆,这种微妙的变化,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日两国间先进与落后的转化,先生与学生的演变过程。
在文献典籍传布的媒介和方式上也由最初人员的自然交流,进而命专人抄写、请求馈赠、寻访或赏赐、彼此交换,到现金采购,翻刻和翻译等。沿着这条文献典籍的传布轨迹,进行探索和研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是意味深长的。
一、 清代以前中日文献典籍的交流
中日两国文献典籍的交流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当时是伴随着人种交流进行的。传说早在秦代时,方士徐福(市)就曾率领三千童男童女以及百工等东渡日本列岛并带去了不少典籍。对此,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曾作了如下描述:“传闻其岛居大国,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提手边加个为)童老。……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正大典藏夷陌,苍波浩荡无通津。……”(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五,《日本刀歌》)这首诗可以说是中国文献典籍早期传入日本的记录和历史的回顾。可是这只是一种传闻,并不见于正史记载。
在徐福之后,据传在公元284年(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百济使者阿直岐到达日本,由于他的推荐,百济博士王仁于次年到达日本,为皇子菟道稚郎子之师,并“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从这一记载中可以得知,在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典籍已传入了日本。到了公元7世纪初(即隋未唐初之际),有更多的中国文献典籍东传到了日本。这可从公元604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十 七条宪法》中的许多遣词造句,直接引用中国经典,得到证明。其次,日本奈良时期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律令中也经常引用中国典籍的内容。例如在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制定的《养老律》和《养老令》中,除大量引用中国典籍外,亦按中国唐代国子监、太学一样,有把儒家经典分为“正经”和“旁经”的规定,将其分为“大经”(《礼》、《左氏春秋》)、“中经”(《诗经》、《周礼》和《仪礼》)和“小经”(《易》、《尚书》)三类。此外当时日本学者都兼学《论辩》和《孝经》等中国经典。这充分说明在日本飞鸟、奈良时代,中国文献典籍已在东瀛广为流传。
与此同时在日本政府中还专门成立了汉籍的抄录、誊写机构—“写经所”。在这里由“写经生”专门抄写汉籍,以便于其广为流传,至今有的抄本还完好地保存着。
日本平安时代,由贵族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遣唐使、遣唐僧和留学生团体,开始了中日文化的直接交流。他们中许多人曾经在中国长期居留,回国时便把他们在华搜集的大量典籍、文献带回了日本。据藤原佐世编纂的《本朝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有中国典籍四十类,共计1568种、16725卷,约占当时中国文献典籍的一半左右。
在日本镰仓、室町和安土桃山时期(1184—1600年),即所谓“五山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南宋至元明时期,文献典籍的传布主要靠禅宗僧侣、知识分子往来,用儒释互补,彼此融汇、沟通的方式进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长年战乱不已,将军擅权,故寺庙成了保存文化和传播文化的最好避风港。当时日本禅宗大兴,僧侣们认为学习和掌握中国的文献典籍,特别是研究儒学典籍是候选者本身素质高低的一种体现,亦是一种美德。因此非常用心,并竭力搜求更多的中国典籍,因此他们是当时日本最有学问的人,操纵着一切学术活动。例如僧人荣西1168年(日本仁安三年)首次入华求法时,就带去天台宗的新章疏三十多部,共计60卷。其后僧人俊仍于1211年(日本建历元年)回国时带的典籍更多,总计2013卷,其中有律宗大小部文327卷、天台教规文字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儒家著作256卷(内含朱熹的《四书集》初刊本、杂书463卷,法贴、御笔、堂贴等碑文76卷等。他的弟子闻阳湛海1244年从华返日时也随身带回佛经数千卷。此外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圆尔辩圆(即圣一国师)于1241年(日本仁治二年)自宋带回国的汉籍也达数千卷之多。这些书籍除一小部分是用钱买或以物交换的外,大多数都是由宋朝当权者者或朋友赠送的。这些从中国带回来的宋版典籍促进了日本出版事业的发展,很快在京都和镰仓等地出现了以“宋、元刻本作版样而仿刻的版,或者仿效这些版样而刻印的版。”这就是所谓的“唐式版”。其后入元僧镰仓净妙寺的太平妙准和他的弟子安禅等人从中国带回了《大藏经》。此外还从元朝引进了除佛经以外的各种书籍,如《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周礼》、《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老子》、《列子》、《庄子》、《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荀子》、《墨子》、《淮南子》、《文中子》、《东臬子》、《吴子》、《孙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山海经》、《尔雅》、《神仙传》、《孝子传》、《先贤传》、《烈女传》、《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群书治要》、《玉篇》、《广韵》、《传灯录》、《五灯会元》、《宗镜录》、李善注《文选》、《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亨释书》、《新刊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春伙经传集解》和《佛祖统记》等书。入明以后,中日两国除僧侣往来外,彼此间还互通使节。日本当政者借此机会公然向明政府索要称有已知和铜钱。例如足利义政将军曾向明朝上书说:“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教乘法教》全部、《三宝感录》全部、《教乘法数》全部、《法苑珠林》全部、《宾退录》全部、《兔园策》全部、《遁斋闲览》全部、《类说》全部、《百川学海》全部、《北堂书钞》全部、《石湖集》全部、《老学庵笔记》。经过访明使了竺清茂代奏,终于得到明朝颁赐,并得到铜钱五万文。
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总是双向传递的,彼此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通有无。日本人撰著的典籍文献也同样通过僧、使节、留学生和商贾等传入中国大陆。例如圣德太子所撰《三经义疏》就是通过遣唐僧诫明和居士德清带入中土的。五代十国吴越王钱淑(947—988年)读《永嘉集》时屡遇难点,便向天台僧义寂请教,得知许多佛教和汉籍散佚在海外特别是东邻日本。于是为了寻求汉籍,钱淑便派遣使臣赴日,以重金购买佚书。
公元983年(宋太平兴国八年),日本奈良东大寺高僧大周(原字上大下周,无法打出)然搭乘吴越商人陈仁爽、徐仁满的商船来华。次年到达开封,觐见宋太宗并献呈日本汉籍和中国佚书,其中包括《职员令》和《王年代记》各一卷;《孝经》(郑氏注)一卷;《孝经新义》第十五(即《表启》)一卷等。其次,公元1072年(宋熙宁五年),日本大云寺僧人成寻携弟子七人,乘宋人商船来华,带来了“天台真经书”600余卷。又,在宋代时,日僧源信还托宋商朱仁聪和宋僧齐隐将其所著《往生要集》等五部书带到中国大陆。此外天台高僧知礼、源清和遵式等人还多次托求日僧抄录阙经,因此宋代天台宗的复兴,就多方面得助于佚经回归甚多。
二、 清代中日文献典籍的交流
(1) 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的主要手段是贸易。
从明代后期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间海上贸易有了长足发展。表现在出海经商的人数、船只均成倍增长,海商贸易活动范围也比前代更加扩大。东起日本、朝鲜,中经菲律宾、中印半岛,南至南洋群岛,西达印度洋的许多国家的港口均有中国商船出没。当时航行在东亚和南亚洋面上的贸易商船,尽管国籍有所不同,但他们真正的船主却大部分是华人或华裔中国人。有时一艘商船从中国出航后,先达某国进行贸易,然后又驶往另一国家,同时船籍也相应地做了改变。
自从公元894(唐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始,日本废止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后,中日两国的民间关系却一直维系着,从未间断,有清一代更不绝如缕。此时尽管中日两国均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特别是日本方面严禁本国人和船只擅自出国,并只允许中国与荷兰等国的商船在长崎一地进行限量贸易,但是中国商船却在沟通两国经济的互补、物产的有无,乃至文化交流上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于民间贸易的发达、文化的兴盛,更使中日两国书籍贸易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的景象,特别是中国书籍东传日本的数量和种类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中日两国的贸易品除丝绸、铜、金银、砂糖、海产品和药材外,大宗的商品就要数书籍和“文房四宝”了。(当然书籍和文房四宝的贸易是以中国向日本输出为主。)
当时中国赴日商船比前代增加,贸易额扩大。特别是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回归大陆后,次年康熙帝颁布了“展海令”,决定民间商船可以自由出海贸易,于是大量商船涌向了日本。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扩大海上贸易,又开设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今连云港)等四处榷关,开始与外国互市贸易(见郑燮《中西记事》三,互市档案)。
“展海令”颁布后,中国对日贸易迅速发展,仅从赴日商船的成倍增加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统计,在1662年(清康熙元年)赴日中国商船为42艘;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驶日中国商船为73艘;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赴日中国商船为115艘,另有载回船22艘;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竟有中国商船199艘到达长崎港进行贸易。此后几十年间由于日本施行信牌制度限制贸易量,以解决严重的入超问题,规定每年限定驶至长崎的中国商船数为70至80艘。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至1790(清乾隆五十五年)间,日本规定只允许30艘中国商船进入长崎港进行贸易;1790年至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又进一步限制每年赴日中国商船为10艘。1840年以后,赴日中国船逐渐减少,大约每年只有五、六艘中国商船驶至长崎。而同一时期荷兰驶往长崎的商船每年在四、五艘左右。由此可见中国商船在船数和贸易量上,在日本对外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正如前文所述,当时中国向日本的出口品主要是丝、绸缎、砂糖和药物外,便是文献典籍、文房四宝和绘画等。几乎每艘赴日中国商船都载有书籍、绘画和文房用具等。仅居日本学者永积洋子所著《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一书,自1637—1833年间,仅从乍浦港运往日本的各种绘画就有62586幅、各种毛笔235198支、墨5792箱(另有435块、2530斤)、纸张202988连(另有11980张,60525册)、书籍742箱(另有15129册,若干组)。
(2)中国书籍输往日本及日本的藏书家。
日本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大量进口中国书籍,是与德川幕府的创建者德川家康及其继承者重视文治有关。德川家康(1542—1616)是与一般武人不同的将军,他崇尚风雅之道,重视各方面的修养。他掌握政权之后除了重视武功之外,更重视文治,尊重文人,使日本文化日趋发达、兴盛。早在他受封征夷大将军之前,他就在江户(今东京)富士见亭建立了枫山文库(又名红叶山文库)。他特别注重搜集历代的文献典籍,尤其是注重从中国购进各种书籍。他以后的几代幕府将军也非常喜欢买书和藏书,继续向中国商人订购中国书籍。
德川时代由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町人(以商人为主的城市居民)势力崛起,因此文化也更加繁荣、兴盛,特别是日本儒学进入了隆盛时期。此时寺庙文化走向衰落,开始向世俗化文化(主要是代表武士阶层和町人)过渡,其主要表现是此时以商业贸易为主要通道的汉籍传布形式开始形成;另外除经史子集书籍继续进口外,各种笔记、小说等市民文学书籍进口也占有重要地位。
德川时代以前,严格的讲日本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儒学,它主要做为寺庙文化的附属物,由僧侣掌握着。到了德川时代,儒学地位得到了提高,其领导权掌握在代表武士阶层利益的人手中,变成了“官学”。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德川氏家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十分崇尚儒学,尤其是对朱子学尊崇至深。当时日本汉学的奠基人藤原惺窝和他的弟子林道春(号罗山)等人原来都是僧侣,后来才还俗,他们本人不但精通佛学,而且私人藏有大量汉籍。特别是林道春对德川时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有着重要影响,他曾历仕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德川家光和德川家纲四代将军执政时期。在德川幕府“创业之时大被宠任,起朝仪、定律令,大府所颁文书无不经其手者”。(原哲公道:《先哲丛谈》卷一,《林罗山传》)他还在江户上野忍冈地方专门办了林家私人书库,创设了学校,培养儒学者。其子林恕(号鹅峰)亦掌握幕府的文化教育事务曾经编著了《本朝通鉴》和《华夷变态》等书。其孙林凤冈被任命为高级儒官(即学官)—“大学头”。他曾经把林家私塾迁移到昌平坂,扩大成为幕府的学问所。后来林氏的后代也一直担任幕府的学官,并掌握江户汤岛“圣堂”(即今东京神田町附近的孔庙)的事务。此外这一时期城镇市民(以商人为主)文化崛起,“町人”跻身于学术文化领域,购书、藏书和印书,进而兴办学校、图书馆等。如当时日本最大的商业城市大坂,“町人文化”表现的非常突出。正如日本学者天囚西村时彦所说:“大坂诸儒,崛起市井,称雄海内,鸣盛当时。”(天囚西村时彦《怀德堂考》上卷)享保九年(1724年),由三宅石庵、中井(秋字下面加个瓦字)庵等人创办了大坂第一所私立学校—“怀德堂”。
当时从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差不多均载有汉籍。其中有的是为了贩卖,有的则是为了自己阅读。中国商船有时一艘就运载上百种汉籍,数量达几百部之多,其中除经史子集外,还有小说、碑贴等。据大庭修先生统计,从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至1855年(清咸丰五年),经长崎输往日本的汉籍达6118种,总计57240多册。其中有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理性全书》以及程、朱、陆、王的大量著述外,还有《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各省地方志和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此外还有顺治帝的《六谕》、康熙帝的训谕《十六条》、《性理精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有大量的实用书籍(如科技、医药、兽医和音乐书等)、“警世书籍”和文艺小说等输往日本,其中主要有:《算学》、《齐民要术》、《天工开物》、《论衡》、《医宗金鉴》、《唐马乘闻书》、《唐马乘方补遗》、《马书》、《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两汉通俗演义》、《染武帝西来演义》、《唐国志传》、《列国前编十二朝》、《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金瓶梅》、《西游记》、《西游后记》、《红楼梦》、《痴婆子传》、《珍珠舶》、《列国志》、《一片情》、《绣榻野史》、《欢喜冤家》、《五代史演义》、《封神演义》、《凤箫媒》、《照世杯》、《杜骗新书》、《醉菩提》、《拍案惊奇》、《五色石》、《云仙笑》、《百家公案》、《有夏志传》、《古今言》、《包孝肃公传》、《开辟演义》、《云合奇纵》、《点玉音》、《归莲梦》、《苏秦演义》、《禅真逸史》、《寒肠冷》、《禅真后史》、《水晶灯》、《艳史》、《炎凉岸》、《梧桐影》、《玉楼春》、《白猿传》、《锦带文》、《英烈传》、《笑谈》、《清律》、《玉金鱼传》、《后水浒传》、《定情人》、《灯月缘》、《龙图公案》、《春灯闹》、《笑府》、《俗呼小录》、《妍国夫人传》、《韩湘子》、《觉世名言》、《隋史遗文》、《琵琶记》、《今古奇观》、《孙庞演义》等(因原文目录过长,在此恕不一一录入。有兴趣的朋友可去看看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
从以上所列汉籍书目中不难看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小说、传奇等文艺作品,反映出德川时代在引进中国文献典籍方面具有鲜明的庶民文化的特点。这也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商人为首的町人势力逐渐强大,教育和印刷业亦有长足的发展,因此在日本主要的商业城市(如大坂、长崎),反映市民文化的“町人文学”、人形净琉璃、歌舞伎和风俗画等都十分盛行。为了适应这种形式,满足广大町人的爱好和需求,势必要大量进口小说、传奇等通俗文学作品。
为了满足日本各界对中国文献典籍的需求,当时中国出版的书籍十分之七、八骑士上都传到了日本。有时中国一本新书刚刚问世,往往不出几年,甚至几个月就会被运到日本,并且很快会被日人用训点、翻刻、摘抄等方式使其广为流传。这一点可以用中国得泰号商船财副朱柳桥与日本儒官野田希一(号笛浦)的对话得到认证。野田曰:“贵邦载籍之多,使人有望洋之叹,是以余可读者读之,不可读者不敢读,故不免夏虫之见者多矣。”朱柳桥曰:“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跺邦人以国字译之七、八,贵邦人以国字译之不患不能尽通也。况兄之聪慧勤学者乎!如兄鸿才即在我邦亦可出人头地,取素紫如拾芥耳。”(见《得泰船笔语》载于田中谦二、松浦章编著《文政九年远州漂着得泰船资料》,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86年出版)当时中国每有新书问世,很快就会被商船运往日本,特别是在嘉庆、道光年间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学津讨原》中国于1806年(嘉庆十一年)出版,次年即被运至日本长崎;《平易法》1804(嘉庆九年)出版,1811年(嘉庆十六年)被运到日本;《钦定中枢政考》1808年(喜庆十三年)出版,1811年亦被运至长崎;《圣武记》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出版,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就被运至日本,1850年(道光三十年)日本便出版了和刻本;〈武备辑要〉1832年(道光十二年)出版,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运至长崎;《乍浦集咏》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出版),当年就运至日本,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就出版了和刻本;《春草堂丛书》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出版,次年便运到了长崎;《乡党正义》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被运到日本;《临正经验方》1847(道光二十七年)出版,当年便被运至日本;《瘟病条辩》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出版,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被运至日本;《金石碑版考例》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被至日本;《韵宗集字》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被运至日本;《海国图志》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出版,1851年《咸丰元年》被运至长崎,1854年(咸丰四年)就出版了和刻本。
为了管理好进口汉籍事宜,德川幕府特在长崎专门设立了负责检查中国书籍的官员,名叫“书物改役”和“书物目利”,以防有关天主教的书籍入境。每当中国商船入港,书籍检察官都要上船查验,严访“违禁书籍”在日本入口和流传,因此至今还保存着不少有关中国书籍进口的帐簿。其中详细地记载着汉籍至日的时间、书名、编号、船主姓名以及数量、价格等,有时还记载着该书被何人买走。此外书物目利还要将每本汉籍作内容提要,即所谓“大意书”供幕府将军首先认购,其次是幕府大老、老中等中央官员选购,再其次为地方大名等各级官员选购,最后才能由民间人士选购。
当时书籍贸易的手续很复杂、繁琐,因此也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录。一般说来,中国商人在国内看到什么书,特别是新出版的书,只要官府允许就装船贩运,有时也有日本将军、各级官员或商人指名预订的。上前在日本还保存着不少进口汉籍的目录,有关藏书的记录以及各种帐簿等文献。其中包括舶载书籍的书目、书籍内容提要(即“大意书”)、书籍的原始帐簿、分开帐簿、见帐(即长崎商人对书籍所作的备忘录和记录投标结果的帐簿)和中标帐簿等。在这些帐簿中记录了汉籍的书名、销售地点、起运地点以及售价等。
如上所述,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是一位文武兼治的将军。他好学嗜书,专门在江户创立了图书馆收藏典籍,尤其是中国书籍。他重视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在他干预下儒学逐渐从佛寺中独立出来,并成为官方哲学。他死后,曾把他的藏书分赠给幕府的御文库(即红叶山文库)和“御三家”(即尾张、纪伊、水户德川家)收藏。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和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执政时期也十分热衷于招集和采购中国书籍,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汉籍收入到御文库中。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对学术尤其重视,嗜书如命。他原为纪州藩主,在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去世后继承了将军之位。他平时热心学习儒学著述,注意掌握各种知识,故其修养和素质较高。他还用自己的方对御文库的图书进行整理并编纂了新的目录。在他执政期间还放宽了对“禁书”进口的限制,允许少数由西方传教士写的有关天文、历法和受西方技术影响的特殊书籍进口。他本人对明清时代的法律书籍和中国各地言志十分感兴趣,故特意向中国船商预订了《大清会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十五省方志等。在德川吉宗在位期间,御文库的书有了成倍的增加。
其次各地大名、学者及至富商也都竞相采购中国书籍,每当中国商船驶入长崎港,他们便派人打听有没有新书问世,或指名道姓地询问鲍廷博编的《知不足斋丛书》出版到那一辑了?袁枚、赵翼、王鸣盛等人又有什么新作?(参见《得泰船笔语》)德川时代著名藏书家、加贺地方大名前田纲纪,他从长崎采购了不少汉籍,尤其是有关法律和方志方面的书籍最多。他的藏书成为今天“尊经阁文库”藏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平户地方大名松浦清也是有名的藏书家,他也性喜采购中国书籍,他家的藏书在当时的日本是很有名的,至今平户还设有松浦博物馆。其次丰后(今大分县)佐伯地方大名毛利高标、因幡(今鸟取县)鸟取大名池田定常、近江(今滋贺县)仁正寺大名市桥长昭和幕府大学头林述斋,以及大阪经营造酒和木材的商人木村巽斋(号兼葭堂)、土佐地方学者谷时中(名素有)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大藏书家。其中谷时中藏书的经历非常生动,兹作简要介绍。他家乡在土佐州(今四国高知县),本来家境富裕、“饶资富财”,在当地颇具声名。但他平生喜书爱书,崇尚程朱理学。为了“访求经典”,他特意跑到长崎等地搜求中国书籍,结果“ 以购买书籍之故,饶资富财为之荡尽”。(琴台东条:《先哲丛谈后编》卷一,《谷时中传》。)为了搜求中国书籍,他不惜万贯家财,“唱朱学于土(佐州当时称之为南学,从游者甚众”(琴台东条:《先哲丛谈后编》卷一,《谷时中传》。)
(3)日本书籍输入中国及中国的藏书家。
中国书籍输往日本,在中日文献典籍交流中无疑是占主导地方的,但同样也有不少日本书籍运到中国,深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
进口日本书籍最主要的港口仍然是对日贸易基地以及宁波船的起锚地—乍浦。此地交通便利、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且风景优美,故清代不少文人雅士来此游览驻足,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访书、探奇。如朱彝尊、杭世骏、高士奇、吴骞、石韫玉、张问陶、翁广平、阮元和鲍延博等人。他们在乍浦都留下了诗篇,故有据可查,其他来过的人想必更多。在清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中国知识界对日本书籍的需求和向往。兹举几例如下:
浙江平乍浦人林大椿曾为同乡赴日商人杨西亭(即杨嗣雄)画的《东海归风图》配诗,其中反映了中国人喜欢日本书籍的心情,原诗为:“海外长留五载余,风回雪浪慰离居。相逢漫问归装物,可有新来日本书。”(沈筠:《乍浦集咏》卷八)又,顺德人何太青的《乍浦集咏》也记载了有关书籍贸易的事宜:“海不扬波俗不浇,迎龙桥接凤凰桥。东洋雕漆罗番市,南浦明珠烛绛宵。异域在书通日本,暇方琛赆驾秋潮。鲛绡莫向潜渊织,已见珍奇列圣朝。”(沈筠:《乍浦集咏》卷七)作为中日书籍交流媒介的清代商人不但把中国书籍运往日本,同时还把日本人编著、翻刻乃至保存的中国早已失传的书籍运回中国。
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记载,在日本德川时期,大约编著了说经之书四百余种,其他方面的论著和翻刻、训点的书籍就更多了。在那些日本人编著的著述中不乏学术佳作。如山井鼎所著的《七经孟子考文》一书。开日本考据、校雠学之先河,启中日古籍沟通之机运。此书由清商伊浮九运至中国,对清代学术影响颇大,深受中国学者的称赞和青睐,并被著录在《四库全书》之中,流传于中国。乾嘉学术大师王鸣盛晚年寓居苏州,经常能看到清商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书籍。故他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曾赞扬日本文学兴盛,学术空气浓,价值亦高。清代学者卢文绍受《七经孟子考文》的影响和启示,也从事校勘经典的工作。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阮元也深受山井鼎的影响,他最早在扬州江氏随月楼看到《七经孟子考文》,阅后深为其内容精细、结构科学、严谨所感动,对山井鼎十分欣佩。1797年(嘉庆二年)在他主持下翻刻了此书。此外藏书家汪启淑也经常从赴日商人手中购买日本书,他也收藏了《七经孟子考文》一书。
清代著名学者、刻书家和藏书家鲍延博原籍安徽歙县,后来寓居杭州。他与赴日本贸易的清商关系十分密切。他通过商人汪鹏、伊浮九等人购入了不少日本书籍,其中有《古文孝经孔氏传》、《论语义疏》、《七经孟子考文》等。后来鲍延博将《古文孝经孔氏传》收录在他编著的《知不足斋丛书》第一辑中,清商贩运到日本,亦颇有影响。这套丛书很受日本人欢迎,他们对此书的出版情况很关心,经常询问到长崎的中国商人。(参见《德泰船笔语》)
著名学者、藏书家朱彝尊(字竹咤)亦十分重视日本书籍的搜藏。如1664年(康熙三年)他曾在杭州高氏稽古堂看到日本史书《吾妻镜》(又名《东鉴》),视为海外奇书,甚是喜爱。后来几经波折才把此书弄到手。为此他专门撰写一篇《吾妻镜跋》记述此书内容和收藏经过。朱去世后,此书又转到其好友,藏书家曹寅的手中,曹亦对此书爱不释手,他编写戏曲《太平乐事》时曾参考过此书。当时曹寅的忘年交老友、著名学者尤侗看到此书也颇喜欢,便借曹家藏本抄录了全书,后来江苏吴县的一位学者翁广平(号海村)撰写《吾妻镜补》时,更是详读了此书。翁广平所看到的《吾妻镜》就是从尤侗处借阅的。
嘉庆年间,日本学者、藏书家林述斋所刻的《佚存丛书》十七种,一百一十卷传入我国,在道光年间由阮元重刻,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注意。此外,日本人撰刻的,专门介绍清代时中国知识,尤其是北京和京畿一带风貌的大型图书《唐土名胜图会》,此时也被贩入中土;日本学者安积觉等人用汉文撰著的《大日本史》(《大日本史》是用汉文,按中国正史体例、文风编著的一部大型日本历史。安积觉后又由多位儒臣赓续,直至明治三十九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才最后完成。前后共经过二百五十年。(此书共计397卷)和另一位学者赖山阳用汉文撰写的《日本外史》,几乎与中国人撰写的书籍一模一样,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就被清商贩入国内,后来又被翻刻,颇有影响,乃至编写《清史稿。艺文志》时人们竟把它误认为中国人的著作而收入其中。
(4)从事书籍贸易的清代商人。
如上所述,清代时中日贸易的大宗货物是丝与铜。因为当时清朝政府急需日本的“洋铜”铸造钱币,故特别把乍浦港作为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乍浦港还是日本海外漂流民的集中地和遣送地。)在这里设立了众多的商业会馆和从事中日贸易的批发商、牙行等。乍浦港不但云集了江浙一带的商人,而且也聚集了不少福建、广东等省的商人。其中最主要的是为朝廷服务的皇商和“十二家额商”,他们垄断了大部分贸易品和贸易额。他们有的人亲自出海,而更多的人是另觅代理人作为船主到日本长崎进行贸易。
在赴日贸易的众多商人中,有的是当年往返;有的是常驻长崎,并在那儿娶妻生子,一住多年;有的人学问不多但精于贸易的单纯商贾,有的人则出身官宦,有一定的知识,后来才经商的。这些人一般素养较高,知晓学术界的情况,甚至本人能诗擅画,以至著书撰文。这些人是从事贸易的骨干,他们不但承担着中日书籍交流的媒介,而且本人也读书、撰文、吟诗作画,甚至还能著书、演唱戏曲。现举几位代表人物如下:
汪鹏,字翼沧,号竹里山人,生卒年月不详,大概生活在乾隆年间,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他平日“慷慨好施,予朋好中孤寒者助膏火以成其名,亲串有婚嫁不克者成全之。”(光绪《杭州府志》卷143“义行传”)。他“以善画客游日本,垂二十年,岁一往返,未尝或缀。喜购古本书籍,归呈四库馆,或付鲍渌饮(即鲍延博)或阮芸台(即阮元)传刻行世,有《袖海编》(李浚之:《清画家诗史》)。由此可知他是一位很重情谊、乐于助人,并且能诗擅画、多才多艺的人。他“尝泛海往来浪华岛,市易日本(光绪《杭州府志》卷143“义行传”),故是一位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海商。他与江浙一带的知识界有广泛的联系,常受学者所托在日本寻访书籍。“购古本《孝经》、皇侃《论语》、《七经孟子考文》。流传中土。”(光绪《杭州府志》卷143“义行传”)。此外他还在长崎购得日人松井元泰所著《墨谱》一书运回中国,为中日制墨墨技术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汪鹏撰著了《袖海集》一书,此书又名为《日本碎语》,为笔记体,一卷,除小序共五十条,总计五千余字。书中主要叙述了他在长崎的所见所闻、以及日本的风情、长崎唐馆、中国商船入港后进行交易等各种情况,内容详细、具体。如有关书籍贸易,他写到“唐山书籍历年带来颇夥,东人好事者不惜重价购买,什袭而至,每至汗牛充栋。”(汪鹏:《袖海集》)“书卖字于货口之上,盖以图记,则交易之事粗毕,专待出货。”(汪鹏:《袖海集》)为了防止清商携带有关天主教方面的“邪书”,“唐山船至,例有读告未、踏铜板二事,告未中大略叙天主教邪说之非,煸人之巧,恐船中或夹带而来,丁宁至再。铜板以铜铸天主像、践履之以示摈也”(汪鹏:《袖海集》)。这些史料是汪鹏所见所为的第一手资料,故弥足珍贵。
与汪鹏同时代的清商伊孚九也是一位喜爱书籍又擅长山水画的画家。他原籍江苏吴县,名海有、号也堂。他曾经到日本做马匹生意,同时还教给日本人绘画技法。(《长崎记事》、《画乘要略》)《七经孟子考文》就是他从长崎得手后转让给鲍延博的。
又,乍浦商人杨嗣雄,号西亭。他常驻长崎经商,本人亦能吟诗作画,留有《长崎旅馆怀韩桐上(维镛)、倪苍溪(永弼)》等诗文和《东海归风图》的绘画(沈筠:《乍浦集咏》)。
又,浙江平湖商人朱柳桥,自称为朱熹后人、其父名潜发,号慕亭。曾任“山西、福建邑令,升州牧”(《得泰船笔语》)。朱柳桥“弃官行贾”往来于乍浦与长崎之间。他也能诗擅画,知道中国士人的情况,经常贩运书籍,沟通两国文人的感情交流。他还会演戏唱曲,曾为日本人唱《彩云开》、《九连环》和《烧香曲》等(《得泰船笔语》)。此外,同船商人江芸阁、刘圣孚和杨启堂等也都不得是多才多艺、素养较高、知识面广的商人。他们曾为日人代购《缙绅全书》等书籍,并在船中也经常手捧《聊斋志异》、《今古奇观》等小说阅读。告别是得泰船船主刘景筠长期滞留在长崎,他曾在嘉庆八年(1803年)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三十四年间,作为船主多次往来于中国和日本间,并以在长崎搜集已佚汉籍而出名。(松浦章:《中国商人与长崎贸易—以嘉庆道光时期中心》,载《史泉》第54号,1980年3月)
又,乍浦商人杨懋功,他知书达理,能诗擅文。这从他所作的《癸卯(1843年)仲冬将之琼花岛(亦称浪花岛,皆系指日本长崎)月夕乘潮东渡回望观山感而赋此》的诗文中就可以得到反映:“人生值盛世,怀才终显名。我朝重文治,读书愧未精。维时有苗格,无劳请长缨(一说时海氛初熄)。四民各安业,我艺将何成。曾闻海外琼花岛,重洋远隔三六更(海行六十里曰一更)。赤铜药物互通市(岛产赤铜,官商往采以供鼓铸),百余年来货殖腾。楼船万斛驾沧海,聊复破浪乘风行。冯夸潜伏烛龙卧,冰轮皎洁悬天庭。此时心胸顿开拓,昂首长吟向世轻。回头瞬息家山远,烟际隐约灯光明(观山悬灯远引海船,故一名灯光山)。涛声猛涌百愁动,帆影遥悬双涕零。上念高堂疏视问,下累深闺忘寝兴。少小未尝远离别,勿忽分袂若为情。寻思此行殊自惜,十年书剑劳长征。(沈筠:《乍浦集咏》卷十三)
三、 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的几个特点
中国清代和日本的德川时代,在两国历史上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商船往来频繁,民间经济、文化交流不绝如缕。在文化交流中文献典籍的交流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书籍作为商品采取有偿销售的方式进行交流。
每部书都有标价,双方可以讨价还价,最后拍板定交。有的书还可以预先订购,事先提出书名、数量,委托清商进行采购。详细情况前文已经述及,故此不再赘言。
(2) 由于日本当时实行锁国政策,严禁有关天主教的书籍入境,故在书籍交易中实行检查制度,日本政府设立专门已知检查官员,对进口和第一部已知都进行严格的查验、登录,然后上报幕府,只有经幕府批准者方可投入市场。
(3) 书籍交流的规模、数量大大超过前代。
有关中国书籍东传日本的数量、种类的问题,在前文中已有提及,故此处不想多言。在此仅举一例加以说明,据日本长崎书物改役向井富的统计,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至1803年(嘉庆八年)间,中国四十三艘商船,共运至长崎汉籍4781种(向井富:《商舶载来书目》)这个数量和规模已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至于日本向中国输出的已知目前还没有详细统计。据杭州大学王宝平先生对国内六十多家图书馆的初步调查,约有日本版古籍书3400余种。当然这些书不一定都是清代流入中土的,但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西传的。尤其是清未民初时期,不少中国人至日搜寻、探访得来。如黎庶昌、杨守敬、孙楷第、董康、傅增湘、俞樾和李盛铎等人。
(4) 书籍传播速度超过前代。
以往书籍传播,往往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之久。然而到了清代,由于书籍交流是通过贸易渠道进行,故大大加快了速度。许多汉籍迅速东传的事例已在前文述及,故不再赘言。至于日本书籍西渐,也往往是几年或十几年之内就传入中国的,如《七经孟子考文》、《大日本史》、《日本外史》等都是如此。
(5) 这一时期中日双方贸易的书籍除儒学、佛学、医学和书画外,还有法律、地理、地方志、数理科技和工农业方面的实用书籍。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如《圣武记》、《海国图志》、《武备辑要》和《乍浦集咏》等一批所谓“警世之书。”日本人士认为这批书籍对加强该国海防,提高全民抵御外患的意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海国图志》在中国问世后不久就东传到日本,仅在数年之间就在扶桑出版了二十多种翻刻或翻译的选本,不论在速度或数量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乃至世界出版史上都是少见的。许多日本人士认为这部书是维新的启蒙读物,并将其视为“无以伦比”的“有用之书”(尾佐竹猛:《近世日本的国际观念之发达》第53页中引广濑旭《九桂草堂随笔》中的话),还推崇它是一部“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也。当博施以为国家之用”(南洋悌谦:《海国图志》、《筹海篇》译解序)。
总之,这批“警世之书”影响到幕府一代知识界,特别是对那些强烈要求抵制外国列强,革新内政的维新志士们以启迪和鼓舞,从而推动了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展开。由此可以得知清代,特别是晚清,文献典籍的交流已从学术理论为主流,步入为以实用、为现实服务的已知为主流的轨迹。
四、 结语
清代时,中日两国文献典籍交流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中国“闭关”,日本“锁国”的形式下进行的。尤其是日本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于1633年(日本明正十年)下令对全境实行封锁,严禁一切日本人出境,也严禁一切外国人入境。使日本孤立于世界之外。直至1636年(日本明正十三年)才又作了补充规定,开长崎一港作为与中国和荷兰两国进行贸易的窗口。于是中国商船每年来往于两国之间,运载着双方急需的物资,同时也运载着各种文献典籍。中国与日本商人就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从事书籍交易。当时中国的乍浦港和日本的长崎港便成了主要的书籍集散地。当时两国学子不能直接交往,只好到这两个港口游学、访书,隔着大海,翘首对望。尽管如此,中日文化交流的巨浪势不可挡。书籍作为商品不管其交易的规模、流传的速度还是种类的繁多,涉及面的广度和现实的作用都大超过了前代。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