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葛兆光,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引子:江南女子季文兰的题诗
康熙二十二年(1683),来自关外的满人打败明王朝建立大清帝国,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不仅原来中国的汉族人已经渐渐习惯了异族新政权,就连一直相当固执地认定满洲人是蛮夷的朝鲜人,尽管心底里始终还怀念大明王朝,但对这个日渐稳定的新帝国也无可奈何,只好承认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把原来对大明帝国的朝贡,原封不动地转输给了新朝。这一年初冬,朝鲜使者金锡胄(1634—1684)奉命出使清国,经过多日跋涉后,进了山海关,有一天,使团一行到了丰润县附近的榛子店,在中午歇息时,金锡胄无意中看到,在姓高的一户人家墙上有一首旧日的题诗:
椎髻空怜昔日妆,
红裙换着越罗裳。
爷娘生死知何处,
痛杀春风上沈阳。
诗下还有小序,记载着这个题诗者的经历和悲哀:“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掳,今为王章京所买,戊午正月二十一日,洒泪拂壁书此,唯望天下有心人见而怜之。”尾题“季文兰书” 。
原来,这个题诗的江南女子叫做季文兰,丈夫被清人杀害之后,被王章京买得并带去沈阳,不仅是生离死别,远赴殊方,而且被掳入天寒地冻的北方蛮夷之地,比起远嫁匈奴的王昭君和蔡文姬,仿佛更加多一重被迫为奴的痛苦。在始终对清王朝怀有偏见的朝鲜使者看来,季文兰的题诗,当然象征的是汉族江南人对北方入侵蛮族的痛诉。越罗裳换了蛮衣衫,江南繁华换了关外荒凉,爷娘亲人换了陌生人,所以,同样心里深藏着对满人鄙夷的朝鲜使者,便不断想象着这个弱女子的痛苦、无奈、屈辱和哀伤。当时,金锡胄就写下了两首和诗,一首是:“绰约云鬟罢旧妆,胡笳几拍泪盈裳。谁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阳。”另一首则是:“已改尖靴女直妆,谁将莲袜掩罗裳。唯应夜月鸣环珮,魂梦依依到吉阳。”(下注:吉阳即古袁州,今江南地也)他在诗里感慨,在中国,再也没有人能像当年曹操从匈奴那里赎回蔡文姬一样,把季文兰解救出来了。他想象,这个苦命的女子也许可以在梦中魂回故乡,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为这个弱女子一洒同情之泪。
明清易代,对于一直怀念和感恩于大明帝国特别是对自己国家有“再造之恩”的万历皇帝的朝鲜人来说,简直是天崩地陷,“万代衣冠终泯灭,百年流俗尽蒙尘”,他们很难想象这个一直被当作文明中心的“天朝”,怎么竟然会在数年之间,就一下子变成了“蛮夷”。在一直坚持奉皇明正朔、书崇祯年号的朝鲜人心里,充满了对于历史的想象。在这个想象世界中,季文兰就是明清易代的落难者,在季文兰身上演出的就是明清之际的悲剧。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抒发朝代兴衰、华夷变态的感慨。在现存的几百种朝鲜使者出使清朝的日记、笔记和诗集中,留下了好多对此事发感慨的诗文。金锡胄路过之后两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作为到清国贺岁兼谢恩副使的崔锡鼎(1646—1715)路过此地,也写了一首和诗:“纤眉宝髻为谁妆,染泪潇湘六幅裳。却羡春鸿归塞远,秋来犹得更随阳。” 此后,“榛子店”就成了一个象征,朝鲜人只要路过,就会想起这个弱女子来 。偏偏这里又是清帝国规定的朝鲜朝贡使必经之路,于是,一首又一首追忆季文兰的诗歌就不断出现。他们想象季文兰的题诗,仿佛是献给前明凄哀的挽歌。乾隆年间,李(1737—1795)路过榛子店,就遥想当年说:“此店原有江南女子季文兰壁上所题诗,即悼念皇明,有慷慨语云,而今已泯灭无迹,欲寻不得,只诵天下有心人见此之句,而为之兴感。” 嘉庆年间,徐有闻(1762—?)想起季文兰的故事,也说是“大明末年江南女子□文兰被虏向沈阳时所作也” ,而另一个姜浚钦(1768—?)更是清清楚楚地说,作者是“明季江南女子季文兰”。
在朝鲜人的想象中,季文兰被当成一种历史回忆,她就是明清易代时的悲剧主角,她的诗中透露的,就是前明江南汉族人在战乱中的悲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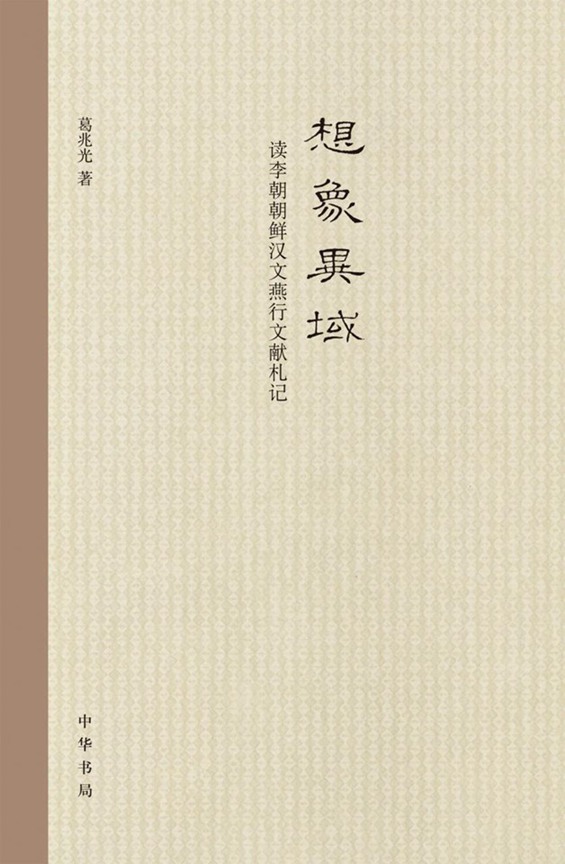
一、想象中总是以夷乱华的离散悲剧
国破与家亡总是连在一起,兵荒马乱的时代常常上演家庭离散的悲剧,这些悲剧总是引出对战争的悲情,传为元代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和施惠的南戏《幽闺怨佳人拜月记》写的是同一个故事,记载那个改朝换代的战争里面人们的凄惶:“风雨催人辞故国,行一步,一叹息。两行愁泪脸边垂,一点雨间一行恓惶泪,一阵风对一声长吁气。” 这个故事后来在《六十种曲》里面改名作《幽闺记》,唱词里也说:“怎忍见夫掣其妻,兄携其弟,母抱其儿。城市中喧喧嚷嚷,村野间哭哭啼啼。可惜车驾奔驰,生民涂炭,宗庙丘墟。” 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深思,这出悲剧原来写的是蒙古兵入侵大金朝,蒙古固然是北狄,可金朝女真在汉族中国人看来也是蛮人,但是,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的战乱离散,好像只是属于汉族人的,只有以夷乱华才会演出如此凄惨的故事,所以在记忆中,战乱仿佛总是被置于“蛮族入侵”和“文明遭劫”的背景下,像《幽闺记》里面,就好像忘了金朝原来也是“番邦”,倒把骑马入侵劫掠的人叫做“蠢尔番兵”,把虎狼扰乱大金朝的情势叫做“势压中华”,说是“胡儿胡女惯能骑战马,因贪财宝到中华” 。所以,这悲情又常常糊里糊涂就被引向华夷之分背景下的民族仇恨,像《醒世恒言》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里被虏的白玉娘,后来被改成《生死恨》京剧中的韩玉娘,有一段唱就是:“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山河万里几多愁。金酋铁骑豺狼寇,他那里饮马黄河血染流。尝胆卧薪权忍受,从来强项不低头。思悠悠来恨悠悠,故国月明在哪一州。”
历史中国曾经有太多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里又有不少不止是皇帝改易了姓氏而且是皇帝换了民族,像元朝代替了大宋,“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就让汉族中国人平添了好多“遗民” ,而清朝替代了大明,薙发易服,也让汉族人着实悲伤了很久。不过,时间似乎总是很好的疗伤剂,时间一长,伤口就渐渐平复,历史也就被当作遥远的记忆,放进了博物馆,除了还记得沧桑的人看到会唏嘘一番之外,大多数人都会把这种惨痛淡忘到脑后。在大多数汉族中国人都渐渐心情平静的时代,倒是固执的朝鲜人,却总是在心底里替汉族中国人保留着一份回忆。当他们的使者来到中国的时候,就非常敏感地寻找民族悲情。看到季文兰的题诗,就会想到:“海内丧乱,生民罹毒,闺中兰蕙之质,亦未免沦没异域,千古怨恨,不独蔡文姬一人而已。”在他们的心里,最不能释怀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忘记了明清易代的惨痛历史。
季文兰的那首题诗,就是这样被朝鲜使者一次又一次地从历史召回现实。
二、季文兰题诗故事:成为典故与象征
其实,并没有多少朝鲜使者亲眼看到过这首诗。最早听说这首诗的申晸本人,并没有亲眼看到它,而当年金锡胄看到题诗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字漶漫不清,仅仅七年后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随冬至使团入燕京的徐文重(1634—1709)路过此地,已经说季文兰题诗“今漫患无存” 。到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崔锡鼎路过榛子店的时候,更只是藉着当年的回忆,在想象中感慨“素壁题诗字半昏”。二十多年后(1720),在李宜显(1669—1745)不那么清楚的记载中也已经说,季文兰诗由于人家“改墁其壁,乃至泯灭云” 。泯灭归泯灭,泯灭的只是在壁上的题诗,但在朝鲜使者的历史记忆里面,它却始终留存。
康熙过了是雍正,雍正以后到乾隆。每一年,朝鲜使者要到大清国来贺岁谢恩,奉命前来的使者,大都事先看过很多前辈的诗文。《燕行录》里很多记载中国当年风景文物世俗的文字,并不见得都来自亲眼目睹,很多有关中国的风物、很多故事甚至很多感慨,很可能都来自文学和历史的典故代代沿袭。不管看没看见真的季文兰题诗,朝鲜使者一到这个地方就要对想象中的这个女子吟一吟诗,雍正十年(1732),韩德厚经过榛子店,就凭了阅读金锡胄的想象和记忆,说“清初江右女子季文兰,士族也,颜貌绝丽,又能歌诗,为胡人所掳过此店,题怨诗于壁上……,清城金相公奉使时,适见壁诗。文兰则莫究所终焉” 。到了乾隆年间的李路过榛子店,虽然一面说季文兰壁上所题诗,“而今已泯灭无迹,欲寻不得”,但是一面又好像亲眼所见似的,照样悲悲切切地想象着当年的悲情。乾隆四十七年(1782)作为冬至谢恩副使的洪良浩(1724—1802)路过榛子店,也写道:
偶过榛子店,遥忆季文兰。
古驿春重到,辽城鹤未还。
空留题壁字,何处望夫山。
蔡女无人赎,遥瞻汉月弯。
尽管那个时候,榛子店的墙壁上早就没有季文兰的题诗了,就连当地人,也已经记不得有这回事了,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这里早已经是“数株垂杨,摇曳春风。欲觅壁上题字,了不可得,且举其事问诸店人,漠然无知者” 。
“举目山河异昔时,风光纵好不吟诗。胸中多少伤心事,尽入征人半蹙眉。”“兹行归自黍离墟,痛哭山河属丑渠。况复箕都逢壬岁,小邦悲慕更何如。” 对于满族入主中国,成了新的统治者,朝鲜人似乎比汉族人还要介意,他们出使北京的路上,只要一有感触,就会写诗;只要一看到可以联想的题诗,就会感慨万端,像乾隆五十一年(1786),曾经中过状元的沈乐洙(1739—1799),出山海关过王家台,看见墙壁上题有一诗:“长脚奸臣长舌妻,苦将忠孝受凌迟。乾坤默默终无报,地府冥冥果有私。黄桔主谋千载恨,青衣酌酒两宫悲。胡铨若教阎罗做,拿住奸臣万剥皮。”虽然明明知道它的水平不高,而且有欠格律,但是,他就要想象这是汉族人指桑骂槐,有激而发,说:“于此亦可知海内人心可悲也。” 所以,季文兰的那首已经随着坏壁消失了的题诗,就成了他们唤回历史记忆的契机,只要经过榛子店,它就会从心底里搅起他们的浮想涟漪。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谢恩副使李在学(1745—1806)经过此处时写道:
痴儿金货买残妆,
尚忆征车泪染裳。
壁上芳诗无觅处,
一尊惆怅酹斜阳。
道光八年(1828),上距季文兰被掳已经整整一百五十年,离开明朝覆亡也已经近两百年,朴思浩经过此地,仍然写得悲悲切切:
塞天漠漠晓啼妆,
尚忆阿娘作嫁裳。
梦里江南春草绿,
芳心应羡雁随阳。
三、凭想象改塑历史
可是蹊跷的是,大多数朝鲜使者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把季文兰的故事想象成了明清易代时候的历史断片,时间越久,这种想象仿佛就成了历史。可是,这里却有一个破绽在,所有的资料都证明,当年金锡胄看到的这首诗,明明写于“戊午年正月二十一日”,然而,这个戊午如果不是后金国天命三年或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那么,就应当是大清康熙十七年(1678)。可是,万历四十六年的时候,明帝国控制着关内,满人不可能从这里把江南女子掳到沈阳,而康熙十七年,明朝已经覆亡,清人却已经不需要与明朝人在北京附近打仗了。那么,把季文兰想象成明清易代时的落难人,把这首诗解读成明清之际的悲剧记录,不免就有些落空。
文学家常常在前台看戏,随着戏中人泪水涟涟,可是历史家却总是到后台窥戏,看到卸装以后种种“煞风景”的情态。从想象中稍稍清醒一下,朝鲜人也会看到这里的历史裂缝,于是不免匆匆去修补一下。乾隆五十八年(1793),李在学路过这个地方,在一个姓张的人家歇脚,想起这段往事,便写道:“天启中东使过此,招问此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用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又说:“今距天启已近二百年,店舍亦墟,不可复寻。” 有意无意中,他把题诗的时间一下子从康熙年间,提前到了明代天启年间,也许他意识到了康熙十七年的季文兰并不是明清落难人?
可是,换了“天启”并不管用。因为天启年间并没有一个戊午,事实上,只剩下了康熙十七年(1678)这一个可能。然而,康熙十七年并不是清兵入关征服中原的时代,倒是吴三桂叛乱反清(康熙十二年,1673)之后,清兵与叛军大战的第五年 ,这个时候被掳为奴,恐怕并不是明清易代时遭遇世变的江南女子,即使她有故国之思,似乎怀念的也不一定就是朝鲜使者想象中的“皇明”。
其实,事情一直很清楚。康熙二十二年(1683)金锡胄路过榛子店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让他的副使柳氏招呼这座房舍的女主人询问过,而“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以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五六年前,恰恰就是康熙十七八年前后,这时被掳的季文兰,恐怕就是属于吴三桂一部的家属,所以,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徐文重(1634—1709)在《燕行日录》中说的季氏,就是“顷年吴三桂平后,南中士女为沈阳王章京者掠去” 。康熙三十五年(1696)洪万朝在《嘲季文兰》中就说“季文兰,秀才虞尚卿之妻也。或云居在苏州,盖南土人也,年十六当庚申(康熙十九年即1680年)吴三桂之乱,为沈阳王章京所掠” 。五年后(1701)姜到榛子店,也清楚地记载说:“此乃吴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为北兵所掳,怆感伤悼,而有此作也。” 只是在稍稍时间流逝以后,固执的朝鲜人就是要把江南女子季文兰当成大明秀才的妻子,就是要把满洲王章京以七十两白金买她上沈阳,就是要把它想象成明清之际蛮夷乱华的一出悲剧。
朝鲜人很不喜欢吴三桂。一开始,他们还期待他作三国蜀汉假降邓艾却试图复兴汉室的姜维,“我东闻中原人,皆以为三桂必复立皇明子孙以图复兴云” 。但是,在康熙年间吴三桂再度反清,却并不用大明旗号之后,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吴三桂所有的同情和期待,一致把他看成是断送大明锦绣河山的罪人。像康熙十六年(1677)的孙万雄,就说吴三桂“手握重兵,外召戎狄,一片神州,终为羯胡之窟” 。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崔德中,也痛斥吴三桂“自坏长城,请入外胡,使神州陆沉,可胜痛惜”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朝鲜使者借题发挥的兴致。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再次路过榛子店,又为季文兰题诗一首:“江南女子洗红妆,远向燕云泪满裳。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怜征雁每随阳。” 这以后,榛子店和季文兰就成了一个典故、一个记忆 ,不管这个墙壁和这首诗还在不在,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借季文兰题诗想象中国的悲情,用种种和诗表达自己对满洲人蛮夷的鄙视:
王嫱出塞犹平世,蔡女沦身尚得归。琵琶弦弱胡笳短,难写崇祯万事非。
临水无心洗汉妆,胡儿夺掷旧衣裳。苍黄死别三生恨,不向江南向沈阳。
千行哀泪洗残妆,一叠清词惜旧裳。堪恨当时无义侠,教他流落海山阳。
名花一朵堕胡尘,度尽榆关不见春。秉笔兰台谁作传,千秋寄与有心人。
悲容想见靓明妆,尘壁题诗泪渍裳。天下有心东海子,芳魂独吊立斜阳。
四、悲剧如何演成正剧?
在朝鲜人的记载中,季文兰不仅身世凄楚,而且也容貌动人,而容貌动人,本身就更增添了身世凄楚。当年,金锡胄不仅听说季氏“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而且听说弱不胜衣,“垂泪书此,右手稍倦,则以左手执笔疾书”,在想象中已经平添了许多同情和怜爱。而后来的传说里,更在同情和怜爱中加上了更多想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林翰洙(1817—1886)的笔下,季文兰是“姿貌针茧笔画书琴俱极绝美” ,而且在申锡愚(1805—1865)咸丰十年(1860)写的《榛子店记》一文中,还想象出了季文兰到达沈阳之后的故事,说她不仅被章京掳到沈阳,而且被“河东狮子,日吼数声”,“鞭笞严下,辱等奴婢”,只好在夜半三更时到后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其中最后一首说道:“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当然,这是故事外编故事,传说中加传说了 。
这些朝鲜使者有关季文兰的诗歌里面,最早的是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这一首:
壁上新诗掩泪题,
天涯归梦楚云西。
春风无限伤心事,
欲奏琵琶响转凄。
而最被推崇的是说不清作者的这一首:
江南江北鹧鸪啼,
风雨惊飞失旧栖。
日暮天涯归不得,
沈阳城外草萋萋。
据说,正是因为这首诗被乾隆皇帝读到后,便下诏在离开榛子店二十里的地方,特意为季文兰立了一块碑 。可是,如果季文兰始终被视为明清之际汉族悲情的象征,乾隆不会赞同立碑;如果季文兰已经被知晓是吴三桂孽党家属,乾隆也不会赞同为她立碑。所以,皇帝为其立碑是什么意思,是迎合朝鲜使者的心情?还是附庸风雅?现在不得而知。
不过,这块碑也很早就已不存。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路过此地的时候,就已经感慨:“榛子店荒凉愁绝,有古陂,天旱水干,往往有芍药丛生。金清城《息庵集》有江右妇人为满洲章京过所掠过榛子店题七绝于壁,词甚哀怨,使臣所过者,皆有诗,后来磨灭不辨,今不知其为何家也。” 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也说到:“榛子店有古城,城周可七八里,今尽颓夷。……肃宗癸亥,息庵文忠公奉使过此………其后金稼斋到此……自此遂成故事,我人到此者,多次其韵,闻其后使行过此,见有短碑在路旁,曰:‘季文兰所过处’,必因我国人闻之而为此,其好事者有如此,而今不见。”
让人注意的是,渐渐地,倒是另外一些诗歌开始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