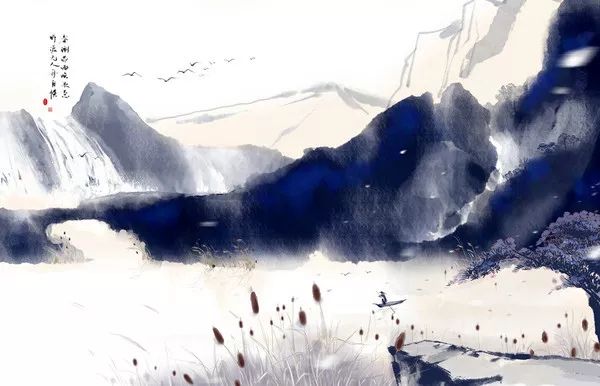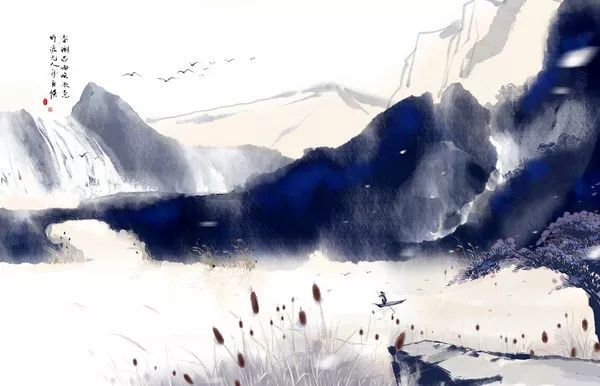
2017—2018年元史研究述评
◇
马晓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
2017—2018年,元史研究欣欣向荣,新的著作、论文层出不穷。中国元史研究会这两年分别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发表元史论文较为集中的期刊和论文集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下文简称《集刊》)第32—34辑,《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7、8辑,《清华元史》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以及余蔚、平田茂树、温海清主编《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史的新可能性——首届中日青年学者辽宋西夏金元史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8年)。这两年的研究成果,在21世纪元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问题取向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取得的成果与隐藏的问题都值得深思。本文主要评述国内的学术成果,兼及一些外文著作。
一、专题研究
元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一向以实证见长。近年随着杉山正明、冈田英弘、梅天穆(Timothy May)、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约翰·曼(John Man)等外国学者的概论性著作出版汉译本,历史叙事、历史阐释这样的宏观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沈卫荣《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3期)回顾和反思了东西方学术传统,再度提出当今学者参与历史叙事、历史书写的重要性。
自现代学术建立以来,中国元史研究在实证方面取得的成果极为丰硕,足以改写以往对宏观历史很多方面的认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元史研究常常被打上冷僻的标签,很多重要成果不为学术界以外人士所知。将元史研究成果向更广的学术界乃至大众推广,实为必要。尤其在当今,全球史观已经是不可回避的课题。利用实证史学的研究成果,建立更宽广的历史叙事视野,这是当今学者面临的一个挑战。
元史学界耆宿也在近两年出版了带有学术总结性质的著作和文集。如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时隔60多年修订出版;杨讷结集出版四种著作《丘处机“一言止杀”考》《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元代白莲教研究》《刘基事迹考》(以上四种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7年);刘迎胜将31篇论文结集为《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生代学者陈广恩《西夏元史研究论稿》、屈文军《元史研究:方法与专题》(以上两种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是约20年成果的汇集。这些著作不仅是对具体问题的探讨,更从整体上反映出元史研究自20世纪后期以来在史料、方法、视野等方面的发展动向。
元朝的二元制度,是元史研究的核心领域。中原汉制一直是深耕细作的领域,而草原制度、游牧民族文化相对而言研究较薄弱。近年中国史学界整体上有提倡内亚研究的风气,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学术热点。近两年学者进一步探研元朝制度中的蒙古旧俗。李治安《元朝诸帝“飞放”围猎与昔宝赤、贵赤新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考证元朝两都附近的春猎秋狝及怯薛执事,有助于深入理解作为元朝的核心政治状态的两都巡幸、四时捺钵。在职官中,必阇赤(蒙古语,意为书记官)在蒙古兴起和早期统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屈文军《元代翰林机构的成立——兼论元初中枢体制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指出,元代翰林机构不仅吸收中原制度,而且保留了原先必阇赤体系的大致形态。在元朝政治制度中,汉式名称表象下所掩盖的草原本质,仍是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重要政治人物研究中,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有助于重新理解元朝政治。党宝海2013年在越南史料中发现元世祖时期的诸王昔里吉谋反失败归降后被派遣征伐安南(《昔里吉大王与元越战争》,《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4期)。而毛海明《元初诸王昔里吉的最终结局》(《集刊》第34辑)利用高丽史料探明了昔里吉出征安南后最终被流放到了高丽的一座海岛。这不仅印证了波斯语《史集》的记载,也提醒我们思考元朝对待反叛的黄金家族成员的态度,以及蒙古帝国的内部关系问题。
元朝的政治脉络,通过人物研究可以得到改写。元朝权臣桑哥,在政治斗争中被杀,列入《元史·奸臣传》,被贴上“敛财”的标签,看似与汉人格格不入。毛海明《桑哥汉姓考——元代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侧面》(《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钩沉索隐,揭示出权臣桑哥曾使用汉姓“王”,并论述了元初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状况。因此,像以往那样简单地将元初政治定义为汉人与非汉人(色目、回回)的族群文化对立,显然是不妥当的。元武宗以往常被看作来自草原的皇帝,其施政常常被视为草原旧制。谢辉《元儒保八生平与著述新考》(《版本目录学研究》第9辑,2018年)揭示出武宗朝尚书右丞康里人保八的易学修养。陈新元《脱虎脱丞相史事探微——兼论元武宗朝尚书省之用人》(《文史》2018年第3辑)考证出蒙古人脱虎脱的生平,指出武宗朝施政的尚书省官员皆为熟悉汉文化、行政经验丰富的大臣。因此,我们不宜再将武宗及其尚书省机械地划为草原集团。上述文章考稽史实,将不同文献中的人物进行勘同,从而纠正了以往对元朝政治脉络的理解偏差,对未来的研究有启发意义。
女性史在西方学术界很受重视,两年间出版了两部著作:英国学者布鲁诺·德·尼古拉《蒙古时期伊朗的女性:哈敦》(Bruno de Nicola, Women in Mongol Iran: The Khatuns, 1206-1335,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美国学者安·布罗德布里奇《女性与蒙古帝国的形成》(Anne F. Broadbridge, Wome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ngol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这两位作者不通汉语,其著作主要侧重的是大蒙古国前四汗时期和伊利汗国,充分展示出波斯语、阿拉伯语史料在这一领域的可行性。中国学者的长处是利用丰富的汉文史料研究元朝女性。从不同语言史料中构建的历史场景实际上有一定差异,未来很有必要将东西方学术融会贯通。
军事史一直是元史研究的重点。但军事镇戍问题因为变动复杂,材料零散,难度很大,进展较为缓慢。刘晓《镇戍八闽:元福建地区军府研究》(《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温海清《元代江南三行省“万户路”问题析考——江南镇戍制度的另一个侧面》(《文史》2018年第1辑)在军事镇戍研究方面有所推进,尤其是对方志资料的大量利用。
元代历史地理、行政地理研究,较其他断代仍显薄弱。在2017年修订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元代卷”(李治安、薛磊著)是最薄的一册。元代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史料零散,为研究带来了难度。李大海《金元之际京兆、安西诸府路沿革发微——兼论金元时期的路制演变》(《文史》2017年第3辑)、王素强《元代襄阳、归州监察归属辨析——兼订〈元史〉等史籍记载之误》(《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可以说是具体考证的范例。这一领域从点到面的推进,尚有很大空间。
地方社会与家族研究,在中国史研究中是重要的课题。刘晓《元代家族发展略论——以族谱、族田与祠堂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梳理元代家族的发展情况,指出了南北方家族组织发展差异及其原因。在华南研究的启发下,学者从长时段、历史人类学角度关注华北地方社会。碑刻、家谱等地方文献成为研究的主要依据。代表性的专著是王锦萍《1200—1600年华北社会新秩序的形成》(Jinping Wang, In the Wake of the Mongols: The Making of a New Social Order in North China, 1200-16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该书从科举、宗教、家族、水利等方面深入探究华北地方社会的变动与延续。朝代更替过程中家族如何延续,是学者最关注的问题。这需要以资料相对丰富的家族作为典型案例。于磊《金元交替华北地方家族及其在元代的发展——以河南巩县张氏家族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8卷,2017年)考述了从元初“军功家族”至元代中后期转型为“仕宦家族”的典型案例。饭山知保《〈西隐文稿〉所见元明交替与北人官僚》(《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史的新可能性——首届中日青年学者辽宋西夏金元史研讨会论文集》)关注的是元代士人宋讷在王朝兴替中维系家族地位的案例。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在断代史之中研究地方社会与家族,容易出现雷同的成果,难有突破,而长时段是必备的视野。
元代政治文化中的多元因素冲突与融合,涉及问题众多。美国学者田浩和苏费翔著《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中庸〉与道统问题》(肖永明译,中华书局,2018年)从学术与政治思想角度作出了有益探讨。刘浦江遗著《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中收录多篇与元史相关的论文,例如《历史是怎样写成的?——郝经雁帛书故事真相发覆》考辨雁帛书故事之伪,并揭示此故事流传与元仁宗延祐儒治的关联。洪丽珠《义随世变——元人的“胜国”运用》(《文史》2018年第2辑)指出元人使用“胜国”专称宋朝,体现了元人的正统观。翟墨《蒙元时代的杜甫记忆——以至元三年追谥杜甫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考证了请谥人也速达儿的身世,认为追谥杜甫与顺帝朝罢免伯颜这一极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关。刘海威《谶谣中所见之“达达”、“回回”和“汉儿”——〈元典章〉“乱言平民作歹”条解读》(《清华元史》第4辑)对钟焓《中古时期蒙古的另一种祖先蒙难叙事——“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逃者”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的观点提出商榷,认为此条谶谣是汉人的传说,不能确定是否吸收了蒙古祖先传说;并指出真定栾城作为元中期白莲教在北方的传播中心,是谶谣的源头。刘海威《元朝灭亡文化因素的思考》(《集刊》第34辑)认为元朝皇帝作为“普遍性君主”,与汉文化较为疏离,在文化上不能有效应对元末的起事者,是导致元朝灭亡的因素之一。
我们在当前的研究中,越来越能看到政治史、思想史、观念史、文学史的交汇,用实证方法梳理思想观念,有一定的深度。
文化交流、民族互动研究,需要学者有广阔的视野和多领域的知识。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结合敦煌文献和考古、谱牒等材料,将元代镇守西北的诸王与裕固族联系起来。马娟研究元代穆斯林移民,发表《元代杭州的穆斯林移民》(《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元代泉州穆斯林移民探析》(《集刊》第33辑)等。日本学者宫纪子《蒙古时代的“知”的东西》(《モンゴル时代の“知”の东西》,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8年)分为上、下册,上册关注的主要是汉文史料,下册关注的是非汉文史料,同时发掘多语言文献、美术品、出土文物等新资料,史料范围广,考证细。
从专题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元史学界将史料学置于首要位置。对史料的充分占有,是研究得以进步的阶梯。下文依次评述元史学界在几种主要类型史料方面的成果。
二、史料整理与研究
(一)基本史料。
《元史》是元史研究的首要文献。南京大学“《元史》汇注”项目以全面吸收前人成果和史料为目的,推进研究,近两年发表的比较集中的成果如刘迎胜《〈元史〉卷三〈宪宗纪〉笺证三》(《欧亚学刊》新6辑,2017年)、毛海明《〈元史·成宗纪一〉至元三十一年史事笺证》(《集刊》第32辑)。同时,很多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通过考证史事,对点校本《元史》作出了不少勘误。例如毛海明《〈元史〉标点正误一则》(《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等。学术界的《元史》勘误工作较为零散,还有很多系论文中兼及者,数量较多,亟须全面搜集和总结。而勘误工作不应止步于表面,更深入地探讨致误原因以及相关史源问题,才是真正实质性的推进。
《元典章》作为元代法律、政治、社会史的一手材料,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校勘释读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得到了新探索,如毛海明《读〈元史〉校〈元典章〉两则》(《中国四库学》第1辑,2018年)。高桥文治等《〈元典章〉所说之事:元代法令集的诸相》(《〈元典章〉が语ること:元代法令集の诸相》,大阪大学出版会,2017年)选取其中几个典型案例,对元代法律、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美国学者柏清韵《忽必烈时代的婚姻与法律:来自〈元典章〉的案例》(Bettine Birge, Marriage and the Law in the Age of Khubilai Khan: Cases from the Yuan dianzha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将《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婚姻》全卷译为英文,并广泛吸收了中、日学术界的成果,逐条详细解读。这是西方学术界首次将《元典章》中的一卷完整译出。
元大都研究方面,日本学者渡边健哉《元大都形成史研究:首都北京的原型》(《元大都形成史の研究:首都北京の原型》,东北大学出版会,2017年)是日本学界首部关于元大都的专著。陈高华点校的《辽金元宫词》(北京出版社,2018年)出版,是元大都城市史、宫阙制度的重要史料。史料价值更高的是元末成书的元大都方志《析津志》,其书已佚,《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辗转抄撮,问题很多。2017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了半个世纪前徐苹芳整理的《辑本析津志》手稿(“徐苹芳北京文献整理系列”四种),对于辑佚而言有参考价值。邱靖嘉找到了《析津志辑佚》最主要的一种底本徐氏铸学斋抄本(《天津图书馆藏抄本〈析津志〉的四库学考察》,《文献》2017年第4期),有追根溯源之功。近二三十年间,学者对《析津志辑佚》做出了很多勘误,又找到了一些散见的《析津志》佚文,因此未来应该有必要整理一部新的《析津志辑佚》。
其他一些重要文献,也有新的探索。例如南宋人所记载的蒙古早期史料,王国维已有论述,赵宇《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集刊》第32辑)对王国维的观点作出修正,论证金熙宗朝金蒙大战为真,但《征蒙记》《行程录》两书确系伪书,应出自书坊商贾。李寒箫《再论〈行程录〉的真伪问题》(《历史教学》2019年第3期)认为《征蒙记》《行程录》不同,后者并非伪书。金亡后元人纂修《金史》,既是金史问题,也是元史问题。邱靖嘉《〈金史〉纂修考》(中华书局,2017年)全面考证元人修《金史》的过程及《金史》的史源。《蒙古秘史》是最重要的蒙古语史料,其成书年代在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何启龙《考证征伐女真、高丽的札剌亦儿台与也速迭儿——兼论〈蒙古秘史〉1252年成书之说》(《集刊》第34辑)通过史事考证,支持1252年成书说。
在日本藏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陈广恩贡献最多,他发表了《日本宗家文库所藏〈事林广记〉的版本问题》(《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7辑)、《静嘉堂所藏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的文献价值》(《暨南学报》2018年第10期)。目前陈广恩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静嘉堂所藏宋元珍本文集整理与研究”,将整理刊布一批国内难得一见的宋元文集。
(二)石刻史料。
元代石刻史料研究起步不可谓不早,但一直缺乏较完善的工具书和资料集。洪金富主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元代石刻拓本目录》(2017年)收录元代石刻拓本800余幅,图文并茂,著录品名、年代、高广、出土地、撰文书丹等人名氏、钤印及题跋、著录和研究等,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
在各类碑刻中,传记类碑刻最便于直接利用,史料价值较高。陈高华《元代墓碑简论》(《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7辑)对行状、墓志铭、神道碑、非汉文墓碑的生成、性质、特点等问题作了高屋建瓴式的论述,对研究石刻者乃至研究元史者而言都是一篇必读文章。
买地券的研究价值在民间层面,其内容大同小异,单个承载的历史信息较少。只有积攒了足够的数量,才能做出研究成果。李春圆《元代买地券校录及类型学的初步研究》(《清华元史》第4辑)是对元代买地券的较全面归纳和分类。
近年来,很多学者在不同的省区着力搜集整理石刻史料,发掘其史料价值。朱建路搜集河北碑刻,补证元代史事,发表了《读元代碑刻札记四则》(《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元代真定路的几个畏兀儿家族》(《西北民族论丛》第15辑,2017年)。杨洁《元〈邠州淳化县重修华岳庙并创建乐楼题名记〉碑调查及相关问题考述》(《文博》2017年第5期)通过碑刻与文物调查,考察元代关中地方社会。
石刻史料是元代道教史研究得以进步的主要根基。刘晓《元代全真道被遗漏的掌教关德昌——〈井公道行碑〉读后记》(《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2期)指出元末完颜德明曾两度担任掌教,而在他两度任职之间担任掌教的是关德昌。马晓林《碑刻所见蒙元时期全真掌教印章及相关史事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4期)揭出了碑刻所存的汉文、八思巴文玄门演道大宗师印,认为是全真掌教的正式印章。赵建勇《金元大道教史新考》(《道教学刊》2018年第2期)发掘石刻史料,解决了大道教史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对该领域研究有所推进。
目前学界对传记类、公文类石刻最为重视。未来的拓展方向,一方面是多种类型石刻的综合利用,另一方面是深入考察石刻的生成机制及其在具体场景中的功能性。
(三)文书。
文书,是元史研究中的“新史料”。新史料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修正和补充以往的学术问题,更在于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目前的研究在这方面较有收获。
黑水城出土文书,经多年深耕细作而产出了新的研究成果。杜立晖对公文行政运作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代表性的文章有杜立晖《黑水城元代公文结尾类型与公文运作》(《文史》2017年第3辑)、《黑水城文献所见元代亦集乃路的机构建制与运作机制》(《敦煌研究》2017年第2期),杜立晖与付春梅《元代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分司的设置与运作——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朱建路《黑水城所出元代议札文书探研》(《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丰富了学者对圆议联署制度的认识。党宝海《黑城元代蒙古文、汉文文书拾零》(《西部蒙古论坛》2018年第4期)刊布了以往学者未注意到的额济纳旗博物馆收藏的三件文书,考释确定这三件文书分别是回鹘体蒙古文雇工文书、蒙汉合璧税粮簿文书、汉文儒学学正到任文书。
公文纸印本或曰纸背文书,是近年备受瞩目的新领域。其中资料篇幅最大的是上海图书馆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的湖州路户籍文书,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的江浙地区公文。郑旭东《元代户籍文书系统再检讨——以新发现元湖州路户籍文书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在纸背文书资料基础上,重新整理出元代户籍文书系统。张国旺、杜立晖《国图藏〈魏书〉纸背文书所见元代县级官员俸额考论》(《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研究辨明这件文书的性质是元代建德路牒呈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分司,说明本路官员俸禄情况的公文。孙继民《公文纸印本〈论衡〉纸背元代文书的整理与介绍》(刘进宝、张涌泉主编《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揭出南京博物院藏宋刻元递修本《论衡》一册(卷一四至一七)有72叶纸背文书,录文并研究认为这批文书是元代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司刷卷文书中的“卷宗事目”。张重艳《新出元代浙江工本钞文书探析——以上海图书馆藏〈论衡〉纸背文献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揭出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元递修本《论衡》二册(卷二六至三〇)有64叶纸背文书,研究认为是元代延祐年间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档 案。
石刻上、家谱中保存的公文书,也得到了关注。党宝海《巨野金山寺元代榜文八思巴字蒙古文考释——兼论元朝榜文的双语形式》(《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11辑,2018年)以新发现的石刻为中心,释读蒙古文,讨论了元朝蒙汉双语榜文的特点与变化。于磊《新见元代徽州儒户帖文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安徽史学》2018年第5期)发掘并解读了徽州家谱中所收公文。
元代文书学,颇多新创获。但是文书具有碎片化的特点。将文书合理地拼入历史的拼图,需要对传统史料有丰富积累和深刻认识。这是目前的元代文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另外,将元代文书与其他时代文书相互勾连,相互启迪,是引人瞩目的趋势。
(四)非汉文史料。
元史研究不同于中国史其他断代的最大特点,是多语言史料。自近代以来,元史学界就极为重视非汉文史料。多语言史料的整理,至今远未完成。
元代有大体量回鹘体蒙古文碑刻,但存世者屈指可数。嘎日迪等《元代〈全宁张氏先德碑铭〉蒙古文考释》(《北方文物》2017年第2期)刊布了翁牛特旗新发现的蒙汉合璧碑的拓片、录文、转写与考释。这通新发现的碑刻,为元代历史、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藏学与汉藏对勘研究在沈卫荣的引领下成果不少。清宫旧藏《大乘要道密集》作为一种密教修法文本,以往一般不受历史学界重视。沈卫荣从中发掘出珍贵的历史信息(《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清宫旧藏的《宫廷瑜伽》《演揲儿法残卷三种》,也显示出从西夏到元、明、清宫廷的密教修法传承。沈卫荣、安海燕《清〈宫廷瑜伽〉、西夏“道果机轮”及元代“演揲儿法”》(《文史》2017年第1辑)以缜密的语文学研究,揭开了数百年来被污名化的“演揲儿法”的真实面貌。2017年青海出版社出版的藏籍译典丛书中的《汉藏史集》《贤者喜宴》《布顿佛教史》《安多政教史》,都有元史史料。藏文史料中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元史信息。谢光典《“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考释》(《中国藏学》2017年第4期)从藏文史料《红史》《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雅隆教法史》中勘定出“统领释教大元国师”的藏文音译,认为西藏现存两方玉印的主人不一定是八思巴或其弟亦邻真,而更可能是元代后期的若贝多吉、贡嘎仁钦或曲吉坚赞。
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内容丰富,构成了 国际蒙元史研究的柱石。英国学者彼得·杰克逊《蒙古与伊斯兰世界:从征服到皈依》(Peter Jackson, The Mongols and the Islamic World: From Conquest to Convers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讨论蒙古在中亚、中东的征服和统治。英国学者兰天德出版了波斯语史料《蒙古消息》的英文译注(George Lane, The Mongols in Iran: Qutb Al-Din Shirazi’s Akhbar-i-Moghulan, Routledge, 2018)。日本学者大塚修《普遍史的变貌:在波斯语文化圈中的形成与展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年)以《列王纪》《选史》《史集》《历史集成》等史书为主线,梳理波斯文化圈对亚洲的历史认知和“普遍史”(即当时所知的世界的历史)的史学编纂思想的变迁,对当前热门的全球史、区域研究尤有启发意义。曾出版日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六卷本,平凡社,1999—2002年)的家岛彦一,2017年出版了《伊本·白图泰与前往境域之旅——〈大旅行记〉新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这是他20余年成果的结晶。邱轶皓《〈完者都史〉“七〇四年纪事”译注》(《暨南史学》第17辑,2018年)将波斯语史书《完者都史》1304—1305年史事译为汉文并做了详赡的注释。邱轶皓《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与边界观念——基于乌马里〈公文术语指南〉记述的一则考察》(《中古中国研究》第2卷,中西书局,2018年)广泛利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史料研究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疆界冲突。魏曙光《域外文献与蒙古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主要基于波斯语史料讨论蒙元前期历史。陈春晓《伊利汗国成立前后伊朗与汉地关系史新考——记1258—1265年间的三次遣使事件》(《清华元史》第4辑)重点利用了两种伊利汗国时期波斯语史料《世系汇编》和《武功纪》。
欧洲史料主要是欧洲人旅行记。1245年出使蒙古的西蒙·圣宽庭(Simon St Quentin)著有《鞑靼史》,是关于蒙古帝国的一手史料。此书以往罕为国内学者所知,张晓慧据让·里夏尔法语译注本汉译发表(《鞑靼史》,《西域文史》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便于学者利用。北京大学荣新江、党宝海主持的“马可·波罗研究”项目在《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17期开设专栏,发表与元代中外关系史相关的论文和学术信息。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中西书局,2018年)引介欧洲抄本文献学最新成果,利用《马可·波罗行纪》的各种抄本,研究元朝礼俗、宗教等方面问题。
多语言史料的难度之一,在于不同文化的差异和隔阂。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叙事逻辑。必须深刻谙熟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才能充分理解文本中承载的历史信息。国内学界正培养越来越多具备各种语言能力的研究者,投入到元史研究中去。
三、考古与文物
日本、蒙古国联合考古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克鲁伦河上游成吉思汗大斡鲁朵奥鲁遗址的发掘最引人注目。白石典之《蒙古帝国诞生:发掘成吉思汗之都》(讲谈社,2017年)总结了近年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新进展,从自然环境、铁冶、交通路线、游牧生活等方面探讨成吉思汗的崛起和蒙古帝国的诞生。
国内的考古学者也在继续刊布新的材料。2009年西安发现的刘黑马家族墓12座,墓群规模大、排列有序,形制基本完整,出土文物数量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元代刘黑马家族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提供了包括5方墓志在内的详细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蒙元世相:陕西出土蒙元陶俑集成》(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甄选刊布了60余年来出土的198件(143组)代表性陶俑,对于元代历史与艺术都有参考价值。汪世显家族是元代另一支显赫的世侯,俄军主编《汪世显家族墓出土文物研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刊布了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220件文物。元代高规格墓葬发现不多,刘黑马、汪世显家族这样显赫的家族墓,是珍贵的资料。
元大都遗迹的考古调查,有了新的发现。故宫内考古发现了元代遗迹,很可能是元宫城大明殿周围的周庑基址(《故宫隆宗门西元明清时期建筑遗址2015—2016年考古发掘简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5期)。林梅村则通过新的考古调查和文物研究,发表《元大都南镇国寺考》(《中国文化》2018年秋季号)、《元大都西太乙宫考——北京西城区后英房和后桃园元代遗址出土文物研究》(《博物院》2018年第6期)重新厘定元代重要寺庙的布局,多有新见。
陶瓷、官印、牌符研究也有新材料和新创获。林梅村《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兼论浮梁磁局创烧元青花之年代》(《文物》2018年第12期)利用考古出土材料,将青花创烧年代上推到13世纪末。薛磊《元代河泊所与河泊课考述——从“金山台池印”谈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利用官印材料,考察了河泊课这一重要税收,以及元代河泊所对捕鱼船只和捕鱼人的管理。党宝海《伊利汗国蒙古文牌符考释》(《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释读出伊朗现藏的一件牌符上的蒙古文,揭示出元代急递铺制度对伊利汗国的影响。
在艺术史方面,湖南省博物馆编《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商务印书馆,2018年)收录多篇论文讨论蒙元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陈晓伟《图像、文献与文化史:游牧政治的映像》(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以刘贯道的名画《元世祖出猎图》为中心,讨论元代游牧制度。
元朝征日本在学术界一直是热点问题。图文并茂的传世文献《蒙古袭来绘词》、九州以北鹰岛海域的元军沉船遗迹、海岸线上的元寇防垒遗存,聚合了考古学界、艺术史与日本中世史学界的共同关注点。九州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中世史专家服部英雄《蒙古袭来与神风:中世对外战争的真相》(中央公论新社,2017年)是其专著《蒙古袭来》(山川出版社,2014年)的概说版,其内容涵盖了作为元日战争背景的日宋贸易,文永之役、弘安之役的详细过程,《蒙古袭来绘词》的史料批判与解读,战争之后的元日关系,以及相关考古遗迹。近年水下考古技术的发展,使鹰岛元军沉船的面貌日益清晰。琉球大学考古学教授池田荣史《长眠海底的蒙古袭来:水中考古学的挑战》(吉川弘文馆,2018年)收录了丰富的照片、线绘图,详细介绍了近年鹰岛海底遗迹的地形学、水下考古学调查方法与过程,以及鹰岛一号、二号沉船的考古研究收获。
考古实物材料对于元史研究颇多促进。如今,蒙古帝国时期考古赢得了国际范围的关注。德国学者的蒙古高原考古,意大利学者的海洋考古,俄罗斯学者的欧亚内陆考古,历时长久,至今还在刊布新材料。可惜以往信息沟通不畅。未来,考古与历史紧密结合的交叉研究是大势所趋。
四、总结与展望
2017—2018年,元史学界成果极为丰硕,本文只举了笔者所见的部分著述,难免挂一漏万。目前各类科研项目中涉及元史研究的不少。下面仅举几个比较重要的史料方面的项目。北京大学张帆主持的《元史》新点校本已经提上议程。《元典章》校释项目即将完成。北京大学王一丹主持的波斯语史料《五族谱》译注已经初步完成。南开大学李治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已整理完成北方现存元代碑刻资料集。《经世大典》《圣武亲征录》即将出版整理本。这些史料整理工作,将为未来的学者带来极大便利。
10余年来,从事元史研究者日益增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门相对冷僻的断代史,在有足够后备力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展壮大,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而新加入的研究者不断砥砺自身,增强史料学功底和语言素养,研究才能有实质性进步。一方面不断开拓新史料,另一方面深度开发史料中蕴藏的价值。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不少领域有所突破。在此基础上,才能回应全球史视野影响下的宏观历史叙事问题。
元史研究与国际上所谓蒙古帝国研究有很大的重合。最突出的特点是跨越现代国界,涉及地域广阔,语言众多。近年西方学界提出历史研究的帝国转向,就是应对这种情况的学术角度。不同国别的学者使用不同的工作语言,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各有专攻,不同的领域又有不同的学术传统,这势必造成很多人为的障碍和隔膜。令人欣喜的是,近年的研究已经初步显现出多重视野交相辉映的态势。一方面是冲破断代史界限,尝试真正长时段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横向的学术扩展。语言、文献、历史、考古、艺术等领域不同国别的学者,汇聚于元史研究中,通力合作,冲破学科界限,相互启迪,必能产生有深度的贯通性研究。
欢迎关注

分享史学研究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