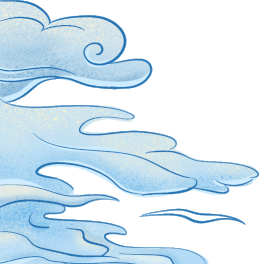宋代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相比,更多地被描述成一个军事上积弱不振、外交上蒙羞连连的时代,但它同时也拥有丰富卓越的文化成果、叹为观止的思想成就、不断创新的制度体系、充满活力的 经济以及生机勃勃的都市文化。
本文旨在揭示宋代中国在10至13世纪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历史学家们已经普遍注意到海外贸易对于宋朝具有特殊意义。笔者则在此试图强调此重要性的背景,认为在此时期内,东亚的国际环境集中体现为各国彼此竞争以及相互间繁荣的海运贸易。这样一个政治上分立的东亚世界导致海外贸易成为宋代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进一步认为此多国体系其实 是相当稳定的,最后是蒙古的崛起和入侵这样一个历史上的突发事件才终止了这样的国际秩序。
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宋史研究中的三种诠释架构。其一是“唐宋变革论”,对于理解这一时期社会 经济变迁而言,这是一个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学说;再一个值得重视的是9世纪后期到13世纪之间的 东亚多国体系模式;最后则是此时期中覆盖了整个亚洲海域的跨国海洋贸易系统。在下文中,笔者将逐一介绍此三种研究架构,并且讨论当今学者对于它们的应用,它们之间的彼此联系,以及我们如何从宏观角度来审视它们的作用和重要性。
史乐民(Paul Smith)在他关于宋代四川I茶业及茶马贸易一书的导言中谈到:自从二十世纪初期內藤虎次郎(湖南)以来,历史学家开始认为晚唐到宋代是一个关系到中国近世形成的关键变迁时期。特别是九世纪以来,木版印刷术的普及为我们保存了相对丰富且详尽的史料。从此,一代代的宋史学家利用这些资料发现这一中世纪变革对于中华帝国的社会、思想和经济生活的种种深刻影响。笔者在此处引述史乐民的原话,并非因其表达出新的观点,而是因为它把中古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合宜地表达出来。大家普遍认为此唐宋变革期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变迁有着重要意义。而此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萌生于8世纪“安史之乱”之后的动荡时局。当然,史学家们对“唐宋变革论”具有共识并不代表没有争论存在。特别是关于两宋期间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学者们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不过,笔者这里强调的是“唐宋变革论”的经济层面,这也是最没有争议的部分。受日本学者特别是斯波义信的影响,史学家们大都认为唐代后期两税法的实行导致土地私有化,随后南方农业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限制逐渐减少,各地都市的兴起带来商业繁荣,一些学者认为这已经是“商业革命”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验证了此模型中的一些元素,比如从北宋到南宋精英社会的变迁,又如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这一模式。
我们随后会重新讨论唐宋变革论及其相关的许多影响。不过,在此之前,笔者先介绍另外两种研 究架构。对于中国和日本学者而言,从多国并存的角 度来研究10到13世纪的东亚历史并非新论,而西 方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则截然不同。起初,几位欧洲 史学家对于征服王朝进行开创性研究,例如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的《征服者与统治者》(Conquerors and Rulers),魏复古(Karl Wittfogel)和冯家昇合著的 《中国社会史:辽代》,以及傅海波(Herbert Franke)的 一系列文章。近年来,莫里斯.罗萨比(Moryis Rossabi)编辑的《势均力敌下的中国》(China Among Equals)、 牟复礼(F.W.Mote)的权威之作《帝制中国》(Imperial China)以及孔华润(Warren I.Cohen)的《以东亚为中 心》(East Asia at the Center)都显示出一个引人注目的东亚世界、一个不被中国(或者汉人)统治的东亚 世界。在这个多国秩序体系中著名的政权有契丹人的辽国(907年建立)、党项人的西夏(1032年建立) 以及女真人的金国(1115年建立)。不过,我们也不要忽略越南的丁朝(968),中国西南部的南诏国,甚 至936年在朝鲜半岛建立的高丽王朝。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史学家一直责备宋代军事积弱、重文轻武的政策。但是以前的汉朝和唐朝都没有在周围面对过这样一些发展成熟强大的政权。宋朝对朝贡系统的原则和象征性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妥协政策。这样虽蒙受羞辱,但在此前所未有的国际形势下,它也是一种成功求生的战略手段。
很久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就认识到从8、9世 纪到14世纪的亚洲海洋贸易具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后来,世界史的学者认识到它在世界史中的重要地位。珍妮·阿布一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在她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就主张13世纪的欧亚世界包含着一个巨大的贸易系统。当然,它是分区域的,一共包括了七个地区性的子系统,比如海运连接的东亚、东南亚、 西南亚等等,可是它们之间发达的远距离贸易使得整个地区可以被称为“世界体系”。再者,她认为这个经济体系中最主要的发动机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既是陶瓷等大宗热销商品的出口者,也是东南亚和南亚生产的燃香、香料的主要消费者。与此同时,占城、三佛齐、古里、巴格达和开罗也都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并且为这个经济体系增添活力。
以下笔者将探讨这三个理论架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笔者相信这些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从时间上回顾一下相关历史事件。唐宋变革中,如果不是大部分,至少也有许多的变化是发生在晚唐五代时期的。这一时期中,政治上的分立逐渐演化为后来宋代的多国秩序结构。9世纪后期,安禄山以及之后的各地节度使势力不断扩大,导致唐朝的势力从内部瓦解,帝国分裂为南方的多个小国和北方若干短命王朝,进贡的属国则各行其是。所以我们看到阿保机(872—926)治下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崛起以及966年越南与南汉的分离(后来证明这是一个与中华帝国永久的分离)。在更遥远的朝鲜,中国的朝廷无力去影响内战(889—935年间的后三国时期)进程,也导致后来高丽统一整个朝鲜半岛。虽然自960年开始,宋朝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重新统一各地,开始有效地重建帝国,但它却没有能力征服邻国。这些邻国在10世纪中成功实现了它们的建国努力。粗看之下,海运贸易体系的诞生跟以上所述之晚唐五代变迁并不相关,因为至少从8世纪前期开始,唐朝在广州就已经同中东地区建立了繁荣的商贸往来,直到879年黄巢叛乱洗劫广州为止。据阿拉伯史家记载,这次洗劫共有十二万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袄教徒丧生,这也打断了唐代末期的海外贸易活动。同时期,中东的政治局势在9世纪后期也进入不稳定的状态。从这以后,五代时期南方各政权以及宋代所进行的海外贸易跟唐代颇不相同。政府开始采取鼓励贸易的政策,贸易的规模也大得多,交易的商品种类更丰富,参与者更多,就连船舶的工艺也有很大的提高。南汉和闽国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地以靠海外贸易来获取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后来的宋代所效仿。因此,笔者认为,仅就中国来说,阿布一卢格霍德所描述的海运贸易体系是专指10到13世纪的新图像。
在9到10世纪时期,多国秩序体系和海运贸易的同时产生在笔者看来并不是巧合。某种程度上,这两者可以被看作是唐宋变革在国际范围上的一种体现。笔者强调“某种程度”是因为这两者也同时受其他外在重要因素影响,并且也都具有一些与中国发展无关的基本特征。下文认为,宋代经济、多国体系、海运贸易系统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十分深入,它们共同决定了东亚世界的格局。
与宋代经济变革和海运贸易之间明显的联系相比,经济变革和多国秩序体系之间的关系相对间接但仍然很重要。人们已经发现宋朝与其北方南方邻居的关系差异很大。占城、越南和南诏同宋朝的关系显示出中国无法被挑战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以及其他亚洲海域地区的朝贡行为在宋初的海运贸易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可是在北方,1005年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战争,此盟约要求宋朝每年向辽国进贡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白银,继而在1042年,进贡额增加到了三十万匹绢和二十万两白银。两年后,宋朝同意每年给西夏十三万匹绢、五万两白银和两万斤茶叶。一个世纪之后的1141年,与金朝缔结和平的代价是每年向其进贡二十五万匹绢和二十五万两白银,宋朝皇帝并且向金朝皇帝表示了臣服姿态。尽管受到羞辱,这些外交条件似乎并没有给宋朝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斯波义信在讨论到宋给辽的岁贡时说:宋代的出口额通常远超过它的进口额。平均来看,宋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得八十万贯顺差。这其中,政府的官方贸易往来占到了四 十万到五十万贯。
此顺差使宋朝实际上重新赚回了对辽国的岁贡。换言之,宋朝贸易规模超过它的岁贡支出。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宋朝的岁贡反而增加了辽国对宋朝货物的消费需求,金国和西夏也是这样,这些其实对宋朝的生产者有很大好处。这种和辽、西夏以及后来金国的多国秩序体系可以说至少从三方面影响了宋朝经济和商业。首先是地缘政治因素。在对10世纪后期到11世纪东亚各地普遍政治动荡进行一番概览之后,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这样写道:正是在中亚、北亚、东亚以及最后中国自己的政治动荡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贸易路线逐步的从传统的陆路交通转变为海路交通。在很大程度上,各地统治者和宋朝政府在十世纪的时候积极推动海洋贸易的发展也是根植于 这样的背景之中。换句话说,宋朝没有能力去控制通往中亚和欧洲的陆路,它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积极地推进海洋贸易政策。第二方面的影响是四川和陕西大规模的茶马贸易。这个方面的出色研究者是史乐民。由于宋朝无法控制任何一个中亚和东北亚盛产马匹的地区,几乎所有的战马都被迫仰赖进口。茶马贸易每年涉及四五百万斤(2600到3000吨)茶叶出口和大约一万匹战马的购买。这种贸易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四川以及帝国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吐蕃成为宋朝更中意的贸易伙伴,因为自830年吐蕃各部分裂以来,政治上的分立导致他们比西夏和辽国对宋朝更不具威胁。当然,大规模的茶马贸易对中亚的影响范围其实远远超越了吐蕃的边境。第三,北方各国持续不断的威胁迫使宋朝维持一个规模上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根据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收集的数据,1073年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国防开支就占了34%,1172年则是48%。这并不只是一个维持庞大陆海军的问题,开销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做武器军品的生产和新式军事科技的研发。这其实是一个军备竞赛,因为契丹、女真以及其后的蒙古人都很擅长获取并利用宋朝的科技优势,不过这仍是宋人军事战略中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此外,正如北宋开封附近钢铁业的发展所显示,军费开支被证实是促进工商业增长的一个有利因素。
由上文关于宋代经济在海运贸易体系中的角色的讨论来看,两者的关系是直接的、有活力的。尽管开罗的法蒂玛王朝、印度东南部的注辇国以及苏门答腊的三佛齐在印度洋海域有效地构成了一个贸易系统,但是“世界贸易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无疑是宋代中国。除了中国商品扮演中心角色,中国市场对于其他地区的产品十分重要以外,到11世纪的时候,绝大多数贸易所使用的航船是中国式的舢舨,中国的海商也是首次扩展到国外,并开始了一场传统的海洋式散居移民,直至今日。与以前不同,宋朝政府发展了一套海运贸易的政策模式。在征服南汉的一年后(971年),政府在广州建立市舶司来管理所有从南海来的船。两年后,一个禁止华商出洋贸易的命令则显示出政府试图控制贸易的意向。然后在987年,太宗皇帝(976—997年在位)派遣八位宦官组成四个使节团前往南海去邀请商人们来中国做生意。两年后,在杭州设置了第二个市舶司,992年在明州设立了第三个。在这最初的年份里面,唐代的先例还是很重要。大部分贸易仍然在朝贡之名下进行,即使有市舶司管理交易的进行,朝廷仍然保有对贵重香药的垄断购买权。
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朝廷集中控制的尝试让步给一个分散管理的体制。这个体制由一系列的市舶司或者市舶提举司组成,一段时间中共有十个港口设置了这些机构。
基本上,朝廷张开双臂来欢迎海外商人,不遗余力地接纳他们,并且也鼓励中国商人去海外冒险,朝廷在经济上更多地依赖关税而不是贡品。值得注意的是1087年在福建泉州设置了市舶提举司,到了北宋末年,泉州已经超越广州成为南海贸易最重要的集散地。与此同时,明州(今宁波)则是与琉球、日本和朝鲜贸易的重要港口。
这一全新监督海外贸易的体制被证明是获利极丰的。在11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政府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的财政收入每年增长五十万贯,到了12世纪早期,增长额超过一百万贯,而到1159年的时候,增长额度已经达到大约两百万贯。此时,政府的财政总收入是六千万贯。
历史记载宋高宗(1127—1167在位)曾谈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 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 可以少宽民力尔。
海运贸易本身涵盖的商品范围很广。在宋初时,从西亚来的奢侈品还占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到了12世纪,从日本、朝鲜、琉球和东南亚来的大宗多样商品成为主流。
宋朝出口的商品最主要的就是陶瓷。在亚洲沿海各地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对于宋代陶瓷的普遍性需求,这些陶瓷往往也是驶往国外货船的压舱物。因为这种出口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大型陶窑生产中心出现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等地,并且扩展到内陆的江西一带。
除了陶瓷以外,宋朝出口也包括丝绸、粮食(通常装在大的陶罐里)、制成品(如书籍)以及大量的铜和锡(特别在13世纪)。这种对铜币的需求导致政府反复试图禁止它们的出口,但从来都是无能为力。
至于进口品,宋代都市消费者对于“香药”有极大的爱好。“香药”通常被翻译为香料,包括燃香、香木、香水以及药品,但是它也包括珍珠、象牙、犀角、棉织物、乌木、苏木等商品。
海外商业贸易对于中国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除上文提到的以出口为导向的陶瓷生产以外,由于受益于浮动船坞和干船坞(位于地平线以下)等先进技术的引入,以及使用模型和蓝图来标准化官船的制造,造船业也成为宋代的一个主要工业。
大部分船舶制造是为了满足水军和国内商贸的需要,但是宋代对于海船的需求也很高。特别从11世纪开始,中国式舢舨开始取代长期在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域跨洋航行的阿拉伯独桅帆船。
虽然造船机构在包括山东在内的帝国各地都被发现,东南沿海仍是最精于造海船的地区。吕颐浩(1071—1139)曾经提到南方的木材特别能抵抗盐水的腐蚀,他并且认为福建所造之船为最佳,其次是广东广西,再次是明州和温州,这些地方均是东南地区。
最能体现繁荣的宋代海运贸易就是东南沿海各港口城市的迅速发展,例如广州、福州、温州、明州,以及杭州(临安)。杭州是南宋时期帝国最大的城市,扮演南宋首都的角色。当然,既然它是首都,又位于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边上,到底它的繁华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海外贸易是很难判断的。
在福建南部的泉州就不同了,它从10世纪相对默默无闻的一个地方发展成为中国南海贸易的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泉州并没有重要的内陆地区可依靠,它成功地成为贸易转运中心,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陶瓷工业基地,并且拥有蓬勃发展的都市文化。
在这里,中国商人和阿拉伯人、三佛齐人、泰米尔人、注辇人、朝鲜人、琉球人以及日本人相混而居。
最后,商业成功带来了东南地区在政治卜前所未有的成功。有宋一代,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路科举出身的进士占了全部人数的27%,而在南宋时期,这个数字达到了52%。
我们无法断定这样的成绩与参与海运贸易到底有多少关系,因为中国的传记作者一向不喜介绍家庭的经济背景。官员们自己是不可以参与贸易的,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有官员因为卷入这种活动而被控告或者定罪的记载。
对于南宋时期宗室在海运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就了解得比较清楚。当朝廷失去了北方领土之后,泉州成为帝国里面宗室成员最大的定居地,受南外宗政司管理。宗室成员中共产生了122位进士(泉州府共有582位进士),在87位南宋市舶使中有9人或者10人是宗室成员,有一些宗室还因利用贸易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而被定罪。
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1973年在泉州发现的一艘1277年的大型海船,上面运送的各种货物标有“南家”的宗室标志,清晰地表明有主要宗室的一支参与到这样的远行中,他们甚至可能是这艘船的所有人。


五、东亚和东南亚的海运贸易
行文至此,笔者主要着重于宋代中国的分析,但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海运相关的亚洲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在10到13世纪中,繁荣的海运贸易给整个地区都带来了深刻的冲击与影响。桃木至朗和莲田隆志认为11世纪到14世纪期间“东北亚第一次被深入的整合到国际贸易网络中去”。
山内晋次称这段时期为“日宋贸易时代”,因为“在与亚洲大陆频繁的海运贸易中人员、商品和信息被活跃的交换着”。夏洛特·佛舒尔(Charloue yon Vershuer)也用类似的话语来描述日本与中国、朝鲜之间的自由贸易时代。
同样地,韦杰夫(Geoff Wade)认为东南亚在900到1300年间是一个“商业时代”,肯尼思。霍尔(Kenneth Hall)把1000—1400年看作是这一地区在贸易和国家发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段时间。
在朝鲜,大约一个世纪内,高丽统治者接受他们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派出使节先是前往五代时的各朝廷,然后前往宋朝,直到1020年为止。当然,辽国的存在使关系复杂化了,共同对抗辽国似乎是此时期宋丽关系得以加强的一个因素。不过,1005年辽国成功和宋朝达成了对前者有利的澶渊之盟,随后契丹入侵朝鲜。在1020年通过和约使高丽成为辽国的进贡国。迈克·罗杰斯(Michael Rogers)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种新的想法开始浮现出来,人们认为这个半岛国家不再是一个卫星国,它有自己的发展路径,是有自己权利的一个‘小中华’”。
尽管缺少朝贡关系,在北宋和南宋时期,宋丽贸易还是十分繁荣。我们有高丽商人在中国一一特别是在明州(宁波)一定居的记载,高丽史料也显示11世纪时几十艘中国货船的造访。
这段时期也是高丽和日本贸易的高峰期,两者有频繁的使节来往。此外,高丽史书中关于阿拉伯使节和商队访问朝鲜的记载很丰富,特别是在1024年从阿拉伯来的一位大食使节和一百多人的到访证明了朝鲜在海运贸易世界的参与程度。
日本的情况就更突出了。从836年起,曾经跟唐朝维持活跃朝贡关系的平安朝廷中断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达两世纪之久。这期间日本跟位于长江河谷的吴越王国还有少许官方往来,但直到1070年代才派遣第一个使节前往宋朝,同时间,日本也开始向高丽派遣使节。
日本和大陆之间的关系由私商(主要是中国人)主导,管理他们的是位于博多的大宰府。贸易量极其可观,佛舒尔估计大概在平安时代每年都有一艘中国商船抵达日本。
贸易总额在12世纪后期急剧增加,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内政治不稳定(源平之战及镰仓幕府的建立),对东亚海运贸易增长的回应也是原因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僧侣对中国的访问以及日本佛寺来中国进行的商业活动。
日本人不但从中国和南海进口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也进口大量的宋代钱币,造成了通货膨胀(一些人称“钱病了”)。这也引起日本当局的警惕,他们无数次地试图限制钱币的进口,但也是毫无效果。
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难题反而把日本和海运贸易世界的其他地区连在了一起。同时南宋成为一个大规模铜钱(和未铸成钱的铜)的流出地,流出路线从中国一直远到非洲海岸,这也强烈地刺激宋朝政府,他们也徒劳无功地试图禁止这些铜钱的出口。
海运贸易对东南亚的影响更加显著和强烈。肯尼思.霍尔认为宋朝的重商政策导致贸易额猛增,这也给东南亚局势带来不安的影响,因为斯里兰卡人、缅甸人和马来人开始挑战三佛齐长期以来在东南亚海运贸易的优势地位。霍尔并且确认了在14世纪早期形成的五个独立贸易商业区。
桃木至朗对10到15世纪大越(越南)的研究更具体地显示出这个国家是东南亚和中国之间转运地,并且它的贵重出口商品产业也不断成长,这些都给大越带来了欣欣向荣的发展。他也认为虽然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时候,宋朝对南海贸易加以限制,但是总的来说,大越和宋朝之间的非朝贡贸易额超过了记载更详细的朝贡贸易额。
王添顺关于宋元时期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研究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人手,对贸易的影响程度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他不但充分地记述了上文提到过的从奢侈品到大规模普通商品贸易的转变,也发现了货物商品化的变革。
从11世纪后期开始,这样的贸易的特点表现为“大规模的商品运输,中国商人对于运输的直接参与,以及拥有商品分级化的知识”。最后一点很重要,因为根据史料,东南亚对中国的出口如香料与从中国进口商品如丝绸或者瓷器都展现出逐渐分级化的倾向(分为高质量、低质量以及介于两者中间的若干级别)。这表明随着商业网络越来越复杂,人们的商业知识也不断增加,因为这种分级化行为只有在对于市场不同的需求有确信的时候才合乎商业常识。
最后,韦杰夫的近期一篇文章认为900到1300年这段时间标志着东南亚第一个伟大商业时代,是一项由宋代“商业革命”引起的发展。因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复述韦杰夫的十二项结论,不过他列举各样贸易的影响包括新港口的诞生、管理中心向沿海地区的迁移、人口增长、东南亚商业化农业和陶瓷业纺织业的发展、新兴消费模式以及新式商人组织。
原刊《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注释从略。
海交史研究资讯公众号
微信号:hjsyjzx
联系邮箱 : hjsyjbjb@163.com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海交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