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之所在
1970年,西嶋定生以册封体制为中心,提出了东亚世界的概念。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年时间,这期间,关于中国、东亚诸国或是北亚游牧地区的研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展着。笔者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前往中国北部实地考察或旅行,但仅仅是通读从《汉书》《后汉书》到《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外国传记,笔者也知道统一的中国王朝与北亚诸国(换言之即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为了守住北方边境,修建绵延数千公里的长城是有必要的,但是在被山川、河流分割成相对狭小区域的中国南方,则没有修建长城的必要。

金子修一先生
因此以中国为中心进行研究时,前近代的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与北亚之间的关系。对西嶋提出的东亚世界设定有所质疑的研究者不在少数,但东亚世界的设定是否是没有意义的呢?笔者并不那样认为。由于北朝的存在,南朝无法与北方民族时常往来,其交往对象便被限制为东亚诸国及东南亚诸国。要找出南朝与东亚诸国和与东南亚诸国交往中的差异绝非难事,二者间的差异可以通过有无册封得到体现。西嶋定生以极具逻辑性的方式提出了册封体制和东亚世界的概念,这在1970年是很具划时代意义的,从结构性视角去捕捉古代国际关系也是非常新颖的。虽然在那之后,关于国际关系的各论研究也在着实进行着,但却很少有人试着去追溯到册封体制论及东亚世界论的理论立足点进行探讨。所幸,随着井真成墓志的发现,包括中国史研究者在内,学界讨论遣唐使相关内容的机会增多了。2007年正值小野妹子(他是607年的遣隋使)至华第1400年,这一年召开了数个关于东亚世界的研讨会,它们与笔者也有些联系。关于西嶋以来的册封体制论及东亚世界论(包括笔者在那些研讨会上阐述的观点),以现今的角度来看应该继承哪些观点?要对哪些观点进行进一步探讨?笔者想针对上述问题,发表一些私人看法。某些部分与笔者参加的研讨会的会议记录有重复的内容,请大家谅解。
二 古代东亚世界论成立之前提
首先,笔者想回顾一下西嶋定生提出册封体制论及东亚世界论的成立过程。
战后第一次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962~1964年),23卷中的4卷都收录了考察日本与中国、朝鲜关系的专论。可以说该书收录这些专论的目的在于,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审视日本——这个被海洋与他国隔绝开来的国家——的历史发展,而不是将眼光限于日本国内。此书中刊登的有:藤间生大《四、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第一卷《原始及古代一》,1962年)、西嶋定生《六~八世纪的东亚》(第二卷《古代二》,同年)、旗田巍《十~十二世纪的东亚与日本》(第四卷《古代四》,同年)、中村荣孝《十三、四世纪的东亚形势及蒙古袭来》(第六卷《中世二》,1963年)各文。其中,西嶋在他的文章中详细论述了到唐代为止的东亚诸国的交往,并将这一国际关系的特点命名为册封体制。他没有将国际关系视为临时的交涉,而是尝试着从国际结构的观点来把握汉唐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这对东亚诸国国际关系的考察及之后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一来便开创了一种新视角——在研究尚未与他国产生直接往来时期的日本历史发展时,将海外动向纳入视野。将大化改新(乙巳之变)和壬申之乱的发生与中国、朝鲜的动向结合起来理解的各研究就可以说是这一视角的产物。

西嶋定生先生
此后,西嶋在1970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四卷的《总说》中,以册封体制的存在作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东亚世界”的存在。他在此强调了从东亚世界的角度来理解日本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还提出构成东亚世界的共同指标是汉字、律令制、儒教以及中国化了的佛教(汉译佛教)。然后,在历史产生变动的前提下,他将东亚世界的范围设定为河西走廊以东的中国、朝鲜、日本以及越南北部。关于西嶋的东亚世界论,本文将不进行更加具体的叙述。前面所提到的李成市《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对此有着详细的介绍,并指出了西嶋设想的出发点,作者还进一步从汉字文化圈扩大的角度提出了对西嶋东亚世界范围的质疑。西嶋的《六~八世纪的东亚》与《总说》均被收录于李成市编著的《古代东亚世界与日本》(岩波现代文库,2000年)中,后者被改为第一章“序说——东亚世界的形成”,前者则被改为第二章“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六~八世纪的东亚”。这两篇文章在收入西嶋《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时改名,前者中的“六~八世纪的东亚”成了副标题,且加上了初次发表时没有的“东亚世界”之语作为主题。这一变更,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西嶋的设想从册封体制扩大到东亚世界的过程。
此外,“册封体制”及“东亚世界”这两个词是从何时起被日本学界使用的,笔者并无确切把握。笔者认为“东亚世界”之语最初被使用是在筑摩书房版《世界历史》第六卷(1961年)的副标题——“东亚世界的改变”之中。关于这一点,笔者希望诸位不吝赐教。同书收有松本新八郎的《东亚史上的日本与朝鲜》一文,这是一篇较早从东亚世界角度来理解古代末期日本历史发展的论文。文中有这样一节:
这虽然是关于古代末期叛乱的内容,但已经列举出了影响国际的因素——与外交、贸易并列的“册封关系”。松本的论文可以被视作是最早着眼于国际性因素中的册封关系存在的一篇论文。

向达先生
但“册封”一语是明清时期针对琉球等国使用的,唐代以前,即使是正史也几乎不使用这一词语。向达在他著名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一书中,将唐对南诏王异牟寻的册立表述为册封(《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前书第143页,该文初次发表于1951年)。涉及此事的原文在《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蛮传》的《南诏传》中,仅有“册”一字:
明年(贞元十年,794年)夏六月,册异牟寻为南诏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节领使(中略),赐黄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
恐怕向达是将明清频繁使用的“册封”一词转用到唐代了。南诏的异牟寻由臣服吐蕃转为归属唐朝,并接受了前述王号。但在前一年的贞元九年,他曾向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送去了一份控诉吐蕃无道的帛书。其中称“讷舌(吐蕃的神川都督论讷舌)等皆册封王,小国奏请,不令上达”,将吐蕃内部授予王号记载为“册封王”(同书同传)。但这是四字句的表达,实际上,应该将这四个字从中间断开,读作“皆册,封王”。此外,在同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中的《室利佛逝传》中有如下记载:
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中略)。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
可能也需要将其分为四字句,读作“宰相会册,封宾义王”。
依笔者浅见,唐以前的正史中“册封”的使用仅此二例。我们很难通过它们断定,唐代已经确立了“册封”一词的使用。论者们无法基于用例对“册封”的含义进行归纳性定义,可能是学界对唐代以前的册封体制存在不同解释的一个理由。
三 东亚世界论、册封体制论的扩大
两个以东京为据点的、具有代表性的学会,即历史学研究会和史学会在西嶋提出册封体制论的次年与后年举办了学会和研讨会,对东亚世界进行探讨。1963年5月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编成了名为《东亚历史像探讨》的总会报告,堀敏一以《从前近代史角度来看》为题做了报告。堀的《东亚历史像是如何构成的——以前近代的角度》(《历史学研究》第276号,同年)是面向大会的报告,《近代以前的东亚世界》(同杂志第281号,同年)是大会结束后的报告。即便是看这个题目我们也能知道,“东亚世界”一词在1963年就已经被使用的。堀敏一生前最后的著作是《东亚世界的形成——中国与周边诸国》(汲古书院,2006年),他是终生持续关注着东亚世界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史研究者中的一位。该书的第一章“关于匈奴与前汉国家关系的考察”是《金启孮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东亚历史研究会,2005年)中收录的论文(但“前汉”一词在原题目中作“西汉”)。第二章“汉代异民族支配中的郡县与册封”是《汉代少数民族地区的郡县与册封——以朝鲜、东北、西南夷为例》(收录于《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一文的日语版。正如笔者将在后文中所讲到的那样,秦汉以后的中国统一时期,从中国王朝的立场来看,国际秩序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是考察东亚世界基础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堀敏一在最后两篇论文中提到了汉代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同样是对问题有所关注的表现。
如前述论著题目所示,堀敏一与西嶋定生同样使用了“册封”“东亚世界”之语。但可以认为,堀使西嶋提出的内容更加相对化了。他认为册封是构成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要素,其他要素有朝贡、和蕃公主等。汉代以来,中国王朝使用“羁縻”一词规范国际关系。“羁”是马的笼头,“縻”是牛辔或牛缰。其原意是要像控制住牛马一样笼络、控制异民族。堀认为,册封、羁縻州、和蕃公主、单纯的朝贡-回赐关系都是羁縻的一种形态。虽然这一点是堀的解释,同样的内容并没有在史料中得到体现,但他一般会将“羁縻”当作描述汉代与异民族间关系的词语使用,从这一情况来看,他大概认为“羁縻”是最具包括性的词语。他还在研讨会上反复提出要注意羁縻与羁縻州之间的差异。羁縻州的出现恐怕是在唐代,并不是之前有了“羁縻”一词,“羁縻州”的概念也就存在了。关于汉代羁縻的用例笔者将放在后文中叙述。

堀敏一先生
接下来,笔者将说明与西嶋定生相比,堀敏一东亚世界论的一大特征——东亚世界范围的扩大。堀认为,北亚诸国与中国王朝的交往是东亚诸国与中国王朝交往的重要历史前提,因此可以将其放入东亚世界之中进行思考。如前所述,这一点在从中国立场出发来研究与周边诸国的关系之时是可以肯定的。他更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中说道:
西嶋所说的中亚属于内亚世界,东南亚属于南亚世界而不属于东亚世界,事实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但关于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的归属则产生了问题。与西嶋的说法不同的是,笔者认为它们不能被排除在东亚世界之外。不用说,蒙古高原属于北亚世界(内亚世界),但将东亚世界视作历史性世界时,如果离开中国和蒙古高原上兴亡民族的对抗与交往,就无法讲述东亚的历史。虽然是否将西藏高原视为北亚世界的一部分可能有所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与中国有着紧密联系。而且尽管西嶋仅将他所讲的西北回廊地带的东部纳入东亚世界,但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将这一地带的西部——即今天的新疆、历史上的西域——与中国有紧密联系的地区也包含在东亚世界之内。(同书4~5页——引者著)
如此,堀敏一将与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有历史性密切关系的所有地区都包含在“东亚世界”之中了。一方面,他没有像西嶋那样,为东亚世界树立共同的标志,也未言及西嶋所说的那四个标志。西嶋有着始终将日本历史的发展置于东亚世界中进行理解的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在他的著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不用说,堀敏一也关注着日本,他一边从日本、朝鲜、中国这些东亚诸国的关系出发,一边坚持从中国与周边诸国的总体关系中试着理解东亚世界的特点。西嶋定生与堀敏一都是从战后最初阶段起活跃于学术界的中国史研究者,他们研究了许多共同的课题(如关于均田制的实施问题等)。虽然两人都使用了“东亚世界”这一术语,但他们设想的世界未必是相同的。接下来,笔者将通过阐述两人对册封的理解来稍稍展现出两人想法的差异。
四 关于“册封”的定义及范围
如前所述,“册封”一词在唐代之前的正史中几乎没有出现。因此我们无法从史料实例对唐以前的“册封”含义进行归纳性定义,只能在理论上将其设定为理解当时国际关系的一种手段。在此,通过阅读最初提出“册封体制”一词的《六~八世纪的东亚》,我们可以看出西嶋所着眼的是以下事实。
高句丽在313年吞并乐浪郡后,受到了西方慕容氏前燕的压制。342年,高句丽国都丸都城陷落,王母(指高句丽故国原王之母——译者注)等人被前燕所俘。高句丽于343年与355年遣使前燕,在355年王母被准许归国的同时,故国原王接受了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高句丽王、乐浪公的称号。即高句丽向中国王朝(此处指前燕——作者注)称臣、接受册封,成了前燕的藩属国。这一事件体现了失去乐浪郡后的中国王朝与朝鲜半岛之间产生了一种与郡县关系不同的新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在370年前燕灭亡后消失了,但416年,高句丽长寿王向东晋遣使朝贡,被封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高句丽王、乐浪公,前燕与高句丽间产生的关系被东晋继承。西嶋关于高句丽王从前燕与东晋处接受乐浪公称号一事做出了如下解释:汉以来的中国王朝的郡名转化成爵名,这从中国王朝的角度来看只不过是将郡县转化为封国,它仍然会被视为中国王朝秩序体制内的一部分。相反,如果从高句丽的角度来看,它占领乐浪郡、消灭了中国的郡县,但随着其国王受封乐浪公,它又参与到了中国王朝的秩序体制之内。也就是说,因为这次册封,高句丽与中国王朝之间形成了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政治体制。
西嶋的慧眼在于他注意到了高句丽被授予的两种爵号中的乐浪公这一称号,并由此发现了新的国际政治体制的产生。但这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南齐书·卷五八·蛮传·东夷传》中的加罗国条记载:
建元元年(479年),国王荷知使来献。诏曰:“量广始登,远夷洽化。加罗王荷知款关海外,奉贽东遐。可授辅国将军、本国王。”
当时就已经存在着本国王的说法,这里的“本国王”指的是诏书中的加罗王。在高句丽的例子中,西嶋在“本国王”一类之内并没有找出册封的特点。但他在《六~八世纪的东亚》的结语中称,册封体制是周代封建制的基本理念,在秦汉时期,它相当于与国内爵制秩序整顿一同出现的外臣制度。西嶋对于“外臣”的解释,是以后述栗原朋信在1960年发表的观点为依据的。此外,他还将“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的例子作为册封体制存在的佐证。并且在此论文的正文部分中,他详细叙述了隋唐时期东亚诸国的国际关系。总的来说,在西嶋眼中,册封体制是规定从汉到唐的古代东亚世界秩序的一个一贯原理。
但这样看来,西嶋所说的册封体制的本质是:是否授予本国王或乐浪公等中国王朝曾经领有土地的地名。恐怕对西嶋来说,它们都是显示册封体制存在的事例。像高句丽被封为乐浪公这样的例子应该是展现册封体制意义扩大的事例吧。实际上,他在《六~八世纪的东亚》的结语中还指出,虽然册封体制自身是传统的,但它实现的途径则受到各个时代的特殊条件的限制。它一旦形成,该体制自身的规则就会制约国际政局。换言之,如果册封体制的规则是唯一的,它的实现方式却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产生变化。那么,承认他的观点时,要将被授予何种称号的国家(异民族)视作册封对象呢?设置且回答这样的问题并非易事。与西嶋的东亚世界相比,堀的东亚世界的范围更大,这一点笔者刚才已经确认过了。被堀纳入东亚世界范围的北亚诸国中,突厥和回纥都从唐王朝处得到了可汗的称号。西域小国从唐王朝处得到国王称号的例子很多,西藏的吐蕃则从唐那里得到了赞普的称号。因此,授予突厥、回纥、吐蕃等君主的称号(可汗、赞普)是否应该包含在册封范围之内,也关系着东亚世界范围的设定。
除所引《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的例子外,我们还能列举出很多中国王朝以王号之外的其他称号册立、册命异民族的例子。堀敏一认为,中国王朝赠予异民族掺杂着汉语的可汗称号也是册封。但西嶋从高句丽被封为乐浪公一事注意到,中国王朝的郡名向爵名转化。他认为册封体制是周代封建制度的基本理念,是与秦汉时期爵制秩序的调整一同出现的外臣制度。并且,册封体制是作为国内秩序的外延部分出现的,它内在的规则与国内君臣秩序的规则基本相同。他还强调,因为作为国内君臣秩序延伸的册封体制秩序成为了历史契机,因此中国文物制度的影响(对于外国而言)或中国王朝的出师讨伐便由此发展(《六~八世纪的东亚》结语)。这样,西嶋的册封体制论被认为是中国国内君臣关系向国外的投影。因此,关于册封的例子也是以王、郡王、公等中国爵号为中心进行考察的。也就是说,西嶋与堀所说的东亚世界范围的差异是同“授予何种称号才是册封”这一点有关的。西嶋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二十等爵制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和《古坟与大和政权》(《冈山史学》第10号)都是在《六~八世纪的东亚》的前一年(1961年)发表的。其中,后者是将前者分析爵制秩序的方法运用在了日本古坟的研究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西嶋的册封体制论中反映了他对爵制秩序问题的高度关注。
虽然已经整理了以上诸多内容,但笔者在此还是想谈谈栗原朋信的内臣、外臣论。如果要利用某颗传世印来探讨“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真伪的话,那么辨别该传世印的真伪本来就是必要的。因此栗原特意不使用传世印,仅以文献作为依据探讨了秦汉的公印制度,并以这种验证方法发表了《文献所见秦汉玺印的研究》(收录于栗原朋信《秦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0年)。虽然他没能从文献上来鉴别“汉委奴国王”印的真伪,但他却在论证过程中,阐明了国外臣子的外臣印与国内臣子的内臣印相比,降低了一个等级的事实。栗原由此指出,春秋时代以降的华夷思想发展中,秦汉的印章将华夷思想刻印其上。如前所述,西嶋采用了栗原的结论,判断出册封体制是秦汉以后(准确来说是汉代以后)的产物。虽然栗原强调汉代内臣与外臣间的差别,但这并不是说他直接认为国内内臣的规则适用于国外的外臣。笔者认为,没有经过证实就直接将西嶋的册封体制论同栗原的内臣、外臣论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并且,栗原的看法也被指出没有考虑到汉代印制变化的问题。现如今,有关传世印的信息与1960年代相比有了飞跃性的增长,以蛇钮印为中心的新著作也在不断发表,栗原的内臣、外臣论也迎来了需要进行探讨的新阶段。
堀敏一立足于前述栗原结论的基础指出,随着五胡的进入,内臣、外臣的区别消失了。但如《新唐书·卷二二○·东夷传》中的《百济传》所述,在唐朝也可以找出外臣的例子:
(贞观)十五年(641年),璋(扶余璋)死,使者素服奉表曰:“君外臣百济王扶余璋卒。”帝为举哀玄武门,赠光禄大夫,赙赐甚厚。
因此,虽然对于堀敏一的意见应该慎重考虑,但笔者亦不认为唐代存在着显示内臣与外臣差别的制度。如果堀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将唐代册封体制的存在和汉代内臣、外臣制度联系起来,也无法证明汉代之后册封体制的存在。堀认为册封体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成效(《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而西嶋则是将此问题放在唐代重点讲述,这是二者的不同。这样看来,要把握从汉到唐册封体制的特点,必须要考虑各种问题。
曾在安史之乱中出兵助唐的回纥,其可汗在广德元年(763年)被唐王朝册立为登里颉咄登密施含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同时,唐将其臣下左杀封雄朔王,右杀封宁朔王,胡禄都督封金河王,拔揽将军封静漠王,都督十一人均封国公(《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亦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三)。由此可见,可汗号与王号可同时授予。这种情况下,异民族的固有称号——可汗号是比王号等级更高的称号,且左杀以下诸人得到的王号并非前述的本国王。雄朔王可能是朔方豪杰之意,而宁朔王是安定朔方之意,两个均是赞扬他们的称号。金河王的“金河”源于地名,这与册封非常接近,但这个称号似乎并未被继承下来。拔览将军所封的静漠王有安定北方沙漠之意,与雄朔王、宁朔王称号类似。从他的上级武官胡禄都督获得了源于地名的王号来看,“静漠”可能也有别的解释——这也是一个地名。关于这一点希望能够作为今后的课题。
如同前述,中国王朝授予的王号名称有多种由来。笔者在拙稿《唐代册封制一斑》中,逐一列出了唐代异民族首领被授予的王号。这些王号除本国王之外,还有因归附唐朝而受到嘉奖、被冠以形容词性修饰语王号的“循义王”等德化王(“德化王”由笔者命名)。本国王可以被继承,但德化王仅被封一次,不能被继承,这是它们的特点。并且,笔者在拙稿《唐代异民族的郡王号——以契丹、奚为中心》(收录于《古代东亚世界史论考》,该文初次发表于1986年)及《从唐朝方面看渤海的名分位置》(同书所收,该文初次发表于1998年)中也提到,异民族郡王号是唐朝在该民族或该民族出身的个人归属唐王朝时授予的,并且渤海在对外交涉中也积极使用“渤海郡王”这一具有如此性质的称号。此外,也有异民族首领的儿子(王子)等人被授予王或郡王称号的例子。笔者在拙稿《关于〈宋书·夷蛮传〉的觉书》中也提到:南朝时期的东南亚诸国中,不存在像日本、高句丽、百济那样被授予本国王或继承本国王的情况。
这样,即使只将中国王朝授予王号的例子列举出来,我们也能发现它们并不都是相同的,将汉唐间的册封体制一概而论是非常困难的。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册封体制和东亚世界的讨论就在持续着。从中国王朝授予王号的特性这一点来看,学界也并未在对具体事例进行深入探讨过后展开讨论。本文以西嶋和堀的论点为中心,论述了唐代以前东亚世界论的特点。同时,笔者希望立足于现状来弄清楚这一问题,并以此为目的写下了本文。笔者在展示以上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想要提出、总结出今后的课题。但在此之前,因为笔者看到了一篇从正史中搜集出汉代羁縻用例的论文,因此笔者想要参照此文的结论,对汉代羁縻相关的问题作一简单叙述。
五 汉代羁縻的用例
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最早的羁縻用例是在《史记·律书》中的:
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藩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
也就是说,即使汉王朝领有天下,但最初不仅其周边诸国不服,连诸侯王都不尽臣节,高祖为此对战争十分苦恼。萧何、张良欲节制战争,用羁縻之道而对他们不加防备。这一羁縻的用法不仅用于“三边”,可能也会用于国内的“大国之王”。但“羁縻”是对没有直接囊括入郡县体制下的对象使用的,并且这一方法展现出了汉王朝消极的姿态。这两点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在《史记》的《司马相如传》(《汉书》同传几乎与此相同)中,有司马相如所写的阐述经略西南的意义的文章,这是他被武帝任命为前往训诫西南夷的使者而返回长安后所写下的。其文首有“汉兴七十有八载”,因此推断该文写于元朔五年(前124年):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
虽然没有引用前后文,但这一部分是作者(司马相如)在阐述蜀地长老及有权势之人反对与西南夷扩大交往:为了打通前往夜郎的道路,汉王朝加重了自身的负担,疲敝不堪。汉朝在与西南夷交往时,值得使自己背上如此沉重的负担么?实际上,这里的羁縻之语是以西南夷为对象使用的,并且不是汉王朝的官方发言,它是一个以不增加中国人民负担的说法展现出汉王朝消极外交的例子。
众所周知,汉武帝推行了积极的对外策略,以下《史记》的《大宛列传》及《汉书》的《张骞传》叙述了将江都王刘建之女下嫁乌孙王(昆莫)之时西域的情况。从前后文推测,这应该是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的事情:
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史记·大宛列传》)
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张骞传》)
即汉朝对那些远离汉朝且骄恣的大宛以西诸国,无法用礼使他们屈服,于是便使用了羁縻的手段。这里的羁縻可以说是笼络异民族的一种消极方法。
《史记·封禅书》、武帝纪末尾之文(二者几乎相同)和《汉书·郊祀志下》中的以下文字,是武帝时期的羁縻用例,颇有意思,并且它也是汉代羁縻用例中的一个特殊事例:
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史记·封禅书》)
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莱者终无验,公孙卿犹以大人之迹为解。天子犹羁縻不绝,几遇其真。(《汉书·郊祀志下》)
大家都知道,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迷信方士,但即使武帝怀疑方士们的言行,却依旧羁縻他们,期待他们说的能够成真。此处的“羁縻”有不断绝关系,不让他们离开的意思。虽然方士是与一般臣民不同的方外之人,但方士与异民族一样被用以“羁縻”之语是耐人寻味的。反过来说,汉王朝对国内的一般臣子和庶民是不会使用“羁縻”一词的。
接下来,《汉书·匈奴传上》(后文的引用会省略《汉书》的标记)中的以下文字描述的是昭帝时期之事的:
卫律在时,常言和亲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后,兵数困,国益贫。单于弟左谷蠡王思卫律言,欲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
卫律是亡命匈奴的汉人,关于他的情况在此不加赘述。以上这段文字说明,在前汉后半期,势力衰微的匈奴向汉请求和亲,于是汉王朝便羁縻之。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指出这是元凤二年(前79年)之事。虽然在迄今为止见到的羁縻用例中(包括上述方士的用例)并没有积极的用法。但此处的“羁縻”是应对匈奴动向的产物,可以认为它是汉王朝积极态度的反映。
到了宣帝时期,郅支单于与呼韩邪单于对立,战败的东匈奴呼韩邪单于同日逐王一起入汉朝觐。关于此事,《匈奴传下》中记载有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黄门郎扬雄的上书,其中有:
逮至元康(前65~前62年)、神爵(前61~前58年)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专制。
《萧望之传》亦有:
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
当时(宣帝甘露年间)对呼韩邪单于“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的待遇有种种议论,本文将予以省略。关于“羁縻”的用法,上述两则史料中,前者说明了日逐王与呼韩邪单于归化后,汉王朝并未施行“专制”,只是在羁縻。后者叙述了即使外夷称藩,中国也让而不臣,此乃羁縻之谊(义)。从前述羁縻方士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汉王朝对一般的臣子和庶民(栗原朋信说的“内臣”)不使用“羁縻”一词,上述二例无疑可以证明这一点。即使外夷表明了作为臣下的立场,中国王朝也只是采取“羁縻”的方式,来保留他们外夷的身份。从这点来说,这里的“羁縻”可以被认为是汉王朝积极态度的体现。
一方面,在《傅常郑甘陈段传》的《陈汤传》中,关于西匈奴的郅支单于有以下记载:
初元四年(前45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以为……今郅支单于乡化未淳,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
即郅支单于请求送回在汉廷入侍十年的质子,贡禹、匡衡认为最好将质子送至边境,而被选为使者的谷吉则主张尽礼数,将质子送至单于处。此处的“羁縻不绝”,应该取“中国笼络夷狄”这一基本意思。既然也有使者本人的发言,那么将此视为汉王朝维持与异民族关系的积极用法也是可以的。然而,送归质子的谷吉却被郅支单于所杀。此后,郅支单于虽然在西域扩张了势力,但最终却被陈汤逼入绝境,在其逃亡地康居被杀。
这样,汉与西域之间的道路便得到了确保,很多西域国家向汉王朝派遣使节。在《西域传上》的康居国条中有:
至成帝(前33~前7年在位)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慢,不肯与诸国相望……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
康居因离汉路途遥远,故与那些离汉更近的国家不同,它自尊大,但汉为了维持新的交通要道,仍对其施行羁縻未绝的政策。此处的“羁縻未绝”与前引谷吉所说的“羁縻不绝”一样,指与异民族的一般关系及维持这一关系,其中体现了汉朝比较积极的态度。
笔者还想举出前汉的最后阶段——王莽的新朝时期唯一的一个羁縻用例。
它并不是在《汉书》中,而是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的《乌桓传》中:
及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
王莽不承认异民族是平等的存在,他露骨地推行将异民族(在名义上)置于中国之下的政策,于是很多异民族便叛离了。据《汉书·匈奴传》,此事发生在始建国三年(11年)。作为征伐匈奴的准备工作,王莽将乌桓、丁令(丁零)士兵驻扎在与匈奴对峙的代郡,同时将他们的妻子置于郡县中作为人质。乌桓水土不服,担心久驻,于是请求回归故土,但王莽并未准许。于是乌桓士兵便开始逃亡,并反过来侵入了中国边境。诸郡县由此尽杀人质,乌桓因此怨恨王莽。匈奴趁机诱其有权势之人为官,一般的庶民则羁縻之且置于自己治下。因此,这里的“羁縻”是在匈奴与乌桓间使用的。除笼络外,还有将其置于己方统治之下的意思。
前汉的“羁縻”之语被用于描述与异民族的联系。最初,没有展现出汉王朝主体影响的消极用法较多。但后半期,在以汉王朝为主体构成的国际关系中,也能见到汉将对方置于羁縻之下的一种有其意志的积极用法。且仅有的对方士使用的羁縻之例显示出,“羁縻”原本是对一般臣下和庶民以外之人使用的词语。那么,后汉的羁縻用例又显示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呢?请看下文。
到了后汉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的日逐王比与其祖父一样称呼韩邪单于,并入朝汉廷。一方面,北匈奴也在建武二十八年(52年)向后汉请求和亲。下文是当时的司徒掾班彪上奏中羁縻的用例(《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接下来的部分将省略《后汉书》的表述):
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巿,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
也就是说,南匈奴臣属汉之后,北匈奴向汉请求和亲的行为都显示出了北匈奴的衰落。但是在未能完全援助南匈奴的时候,不应与北匈奴断绝关系。“羁縻之义”与后面的“礼无不答”相对应,这两句话表示:在对方前来请求和亲的时候不应拒绝。因此,这里的“羁縻”可以认为是在叙述与异民族的一般交往。
班彪之子班固是本文频繁引用的《汉书》的作者,他在《汉书·西域传》末尾的赞中,针对光武帝的外交叙述道:
(前略)故自建武(25~55年)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
也就是说,到后汉时期,西域诸国希望内附中国。匈奴近邻的小国鄯善、车师虽然还受匈奴的压制,但莎车、于阗这样的大国则希望受到西域都护的保护。但光武帝因时之宜,仅仅羁縻他们,并未准许他们的请求。因此,此处的“羁縻不绝”并未体现出汉朝积极的姿态。
章帝建初四年(79年)前后,讨论如何应对请求和亲的北匈奴单于时,班固有如下看法:
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遣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班彪传附班固传下》)
班固称乌桓、康居、月氏现均来朝,匈奴分裂,中国三方(即东、北、西)的异民族来降,汉应向异民族派出使者,以继宣帝五凤(前57~前54年)、甘露(前53~前49年)年间呼韩邪单于来朝时期的盛世,且不失光武帝与明帝的羁縻方针。
如前所述,虽然实际上建武、永平(明帝的年号,为58~75年)时期的羁縻并不怎么有积极意义,但班固在此将它们与前汉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的来朝进行对比,使“羁縻”一词有了更加积极的意义。
和帝章和二年(88年),鲜卑击破北匈奴。南匈奴将此视为良机,请求后汉出兵。于是汉廷以窦太后之兄侍中窦宪为车骑将军,欲远征匈奴。反对此事的侍御史鲁恭上奏:
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卓鲁魏刘列传·鲁恭传》)
他对异民族持否定的态度,这里的“羁縻不绝”是一种消极做法。当时的尚书宋意也上谏窦太后,他称:
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第五钟离宋寒列传·宋意传》)
“羁縻蓄养”在此处被当作是对异民族的消极对策,且被作为光武帝的功绩进行评价。尽管鲁恭和宋意反对,窦宪仍被派出征战。次年,北匈奴被消灭。
之后,《汉书》的作者班固被卷入和帝扫灭外戚窦氏的事件,他作为窦宪的亲信受到株连,死于狱中。如前所述,《班固传》中有着他关于羁縻的看法,《汉书·匈奴传》赞的末尾也有以下之语:
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这是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的一般论,因此在论述前汉的相关问题时不能强行引用。但这里的“羁靡”应与“羁縻”意思相同。班固的看法是:蛮夷慕义而贡献,朝廷以礼让待之,羁縻不绝,使曲(非)在彼,这是圣王的常道。因此,这里的“羁靡”(羁縻)也是一个不怎么有积极意义的用法。
安帝时,国内羌族叛乱,后汉的西域经营因而受挫。元初六年(119年),受到北匈奴攻击的鄯善求援,汉敦煌太守曹宗欲往援,但邓太后不许。关于此事,《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如下:
邓太后不许,但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羁縻而已。其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
此外,《班梁列传》的《班勇传》中也有记载:
于是从勇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简而言之,汉廷虽然恢复了羌族大叛乱后衰颓的西域经营,复置护西域副校尉,但最终也只不过是驻扎敦煌,而未能进行积极的西域经营。因此两则史料中的“羁縻而已”“羁縻西域”可以说是代表着“来者不拒”的一种消极外交。
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上书建议增加被汉人同化的西南夷的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只虞诩一人反对:
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羇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南蛮西南夷列传》)
此“羇縻”和前引的“羁靡”一样,应视作与“羁縻”同义。这是《后汉书》中羁縻的最后一个用例。虞诩批评说,圣王不臣异俗是因为知道蛮夷兽心贪婪,难以以礼率之,故增税只能招致其怨恨而已。他对异民族的评价非常低,因此这里的“羇縻”也是具有消极性质的外交手段。但后汉朝廷并未采纳虞诩的意见,而是进行了增税,结果招来了武陵蛮的背叛。
以上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所有的羁縻(羁靡、羇縻)用例。其中前汉时期有对方士的用例,后汉时期有对国内蛮族使用的用例,可以概括为:“羁縻”一词是对一般臣僚、庶民以外之人使用的。虽然这些大部分是对异民族使用的,但也有对国内使用的例子,可以说都是依据“笼络控制”这一原意而使用的。一方面,前汉初期与后汉的大部分时期,“羁縻”一语都被用在对异民族展现出消极态度的场合中,但另一方面,前汉宣帝时期的例子和后汉明帝永平八年班固的说法都显示出汉王朝有其意志的政策——不将异民族强行编入内臣之列,仅羁縻之;或是向就阙、来降的异民族派出使者,进行羁縻。可以说这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用例。概言之,对异民族采取消极态度时,“羁縻”就有着消极含义;而采取积极态度时,“羁縻”就有着积极含义。这样一来,就能像堀敏一那样,将“羁縻”作为中国与异民族缔结某种外交关系时的一种概括性用例来理解,也能够将朝贡及和蕃公主囊括其中进行思考。但如果要将和蕃公主纳入羁縻之中,那么这种解释并不是能直接从史料之中得出的,这一点大家有必要知道。
六 今后的课题
如前所述,对统一了南北的中国王朝来说,与北亚诸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硬要设定一个东亚世界的话,那这个设定就必须展示出它是对历史的有效分析。西嶋主张不只将日本历史作为一国史去独立理解,还要用包含东亚诸国的更宽广的视野去看待它。并且,他还提出了东亚世界的存在。当日本人从日本人的视角去考察中国、朝鲜的历史时,应该充分重视这一意见。但北京大学的王小甫认为,只要以中国传统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就很难将中国与东北亚的关系视为册封体制、朝贡体制、羁縻体制等“体制”的经营。虽然没有必要立刻赞同这一见解,但我们有必要知道,东亚世界论、册封体制论在现阶段尚未被中国、韩国的研究者们当作一个不需证明的理论去接受。为了尽可能地活用由西嶋提出、诸人继承的东亚世界论和册封体制,使它们成为中国、韩国研究者们也能认同的理论,我们有必要从各种角度加深对它们的验证。目前需要进行探讨的和笔者思考的问题有以下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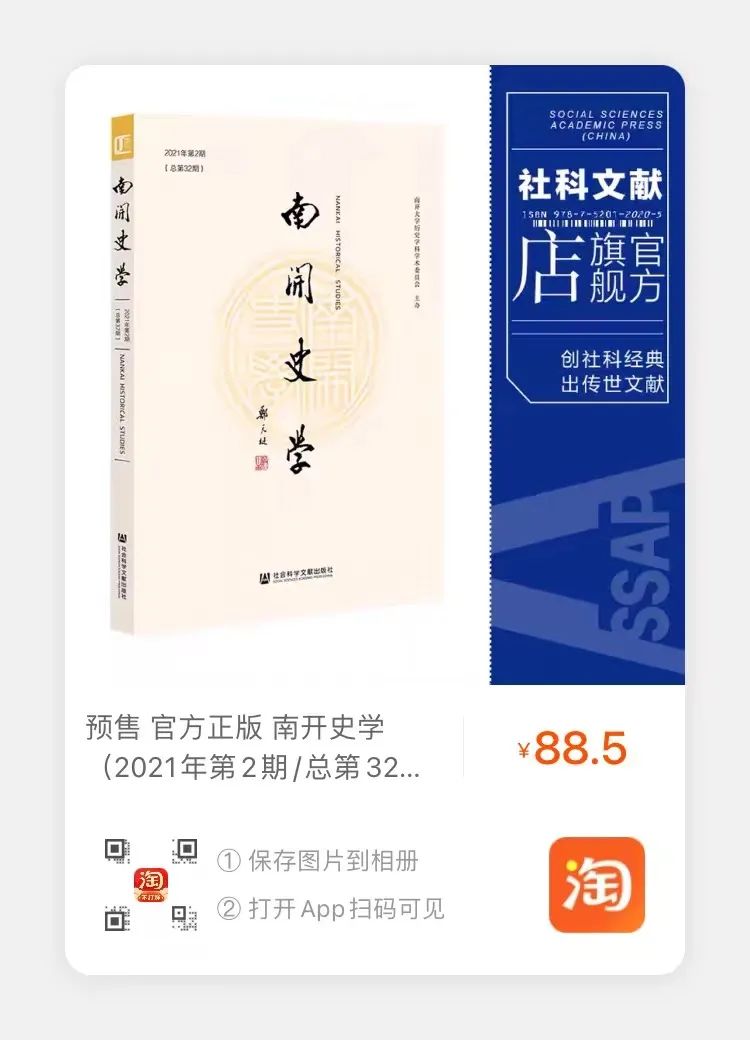
要像西嶋那样,以册封体制来规定秦汉以来中国和周边诸国关系,以及要用册封体制将国内君臣关系扩大到国外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弄清,伴随着秦汉帝国国内秩序的形成,秦汉帝国与周边地区国际秩序的调整过程。遗憾的是,由于史料不足,秦到前汉的国际秩序是如何形成、调整的,这一问题并不十分清晰明了。工藤元男在《以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属邦律》(《东洋史研究》第43卷第1号,1984年)中,利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属邦律探讨了秦代异民族支配体系。渡边英幸的《秦律的夏与臣邦》(《东洋史研究》第66卷第2号,2007年)对此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堀敏一的《关于匈奴与前汉国家关系的考察》和《汉代异民族支配郡县与册封》业已前述。熊谷滋三的《前汉属国制的形成——以“五属国”问题为中心》(《史观》第134册,1996年)与《前汉的“蛮夷降者”与“归义蛮夷”》(《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34册,1997年)也是与前汉异民族内属有关的研究,他的《前汉的典客、大行令、大鸿胪》(《东洋史研究》第59卷第4号,2001年)则研究了前汉的异民族统御官。笔者希望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秦汉的国际秩序问题及内外臣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熊谷的《关于后汉异民族统治的官爵授予》(《东方学》第80辑,1990年)列举了后汉授予异民族的官爵号(包括印谱的例子),其中能看到许多武官系统的官号。小林聪的《关于后汉的少数民族统御官的考察》(《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17号,1989年)一文指出,作为武官的度辽将军担任了北方各民族统御官的职务。佐藤加代子《关于南朝校尉的考察》(山梨大学教育学部毕业论文,2001年1月提交)探究了南朝对周边诸国授予校尉号的实际状况,非常有趣。同样研究武官中异民族统御官的专论还有三崎良章的《后汉的破鲜卑中郎将》(初次发表于1992年)、《东夷校尉》(初次发表于2000年,均被收录于作者的《五胡十六国基础研究》,汲古书院,2006年)。西嶋的册封体制论是以爵号授予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并不只限于倭五王被授予的将军号,我们还要弄清楚武官系统称号授予的总体情况及其意义。
笔者指出了西嶋使用的“册封”一词并不是依据到唐代为止的实例归纳出来的,但本文也提及了汉代的羁縻用例。在国家制度尚未完全确立的汉代,“羁縻”一词并不是像唐代“羁縻州”那样一个指特定体制的词语。因此,论述汉唐的国际秩序特性时,不仅是册封,关于羁縻我们也有必要明了其含义。那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暂时将实例归纳法与理论方法区别开来,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是否能下一个综合性的定义。现在距离“东亚世界”和“册封体制”被提出已经经过了近五十年,它们如今也在慢慢被日本学者以外的海外研究者使用。笔者希望这些术语不会脱离实际情况独自发展,而是在研究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时,为我们提供多彩且有益的视角。
2020年1月28日追记:拙著《隋唐的国际秩序与东亚》早已绝版,因此笔者编集了《古代东亚世界史论考——改订增补隋唐的国际秩序与东亚》一书。虽然书中再度收录了《隋唐的国际秩序与东亚》中的许多论文,但也有部分拙论未予刊载,《漢代蛇鈕印に関する覚書》即是其中之一。同时,本文后半部分笔者关于前汉、后汉羁縻用法的论述亦被收录于《古代东亚世界史论考》第一部分第二章“东亚世界论摭遗”中。
本文出自《南开史学》(2021年第2期/总第32期),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作者金子修一,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
整理 石石 审核 李丽丽 宋荣欣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