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所谓的社会科学中国化,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即运用西方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然后是要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在大量的实证观察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从中国社会抽象出来的概念、法则和理论体系,发展起一种对中国社会更具有穿透力的研究范式,从而使中国研究(这里主要指中国学者对本土社会的研究)不仅可以在相当广泛的领域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而且更可以对世界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本文试图以中国家族研究为例,就社会科学中国化的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家族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一环。中国学者从开始学习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眼光检视中国社会,就已经敏锐地体察到,家族主义,或家族本位,是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基本差异所在,研究传统家族制度,对于破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外学者在研究传统中国社会时,把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家族制度上,努力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剖析传统家族制度。如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关于“家族及宗法”的讨论,虽主要是阐述传统文献中的宗法理论和根据传统宗法观念记录下来的事实,但他的阐述,已经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眼光来解释传统文献的记录,他着重分析的是,家族组织的构成法则,权利义务关系和社会功能等由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经验引出的问题,这就在认识的角度和深度上,表现出和传统宗法理论的根本差别。在三四十年代国内出版的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研究的著作,如吕思勉的《中国宗法制度小史》、高达观的《中国家族社会的演变》、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等,都表现出类似的旨趣。尤其是潘光旦先生在30年代写成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在运用近代社会科学方法整理和利用家谱资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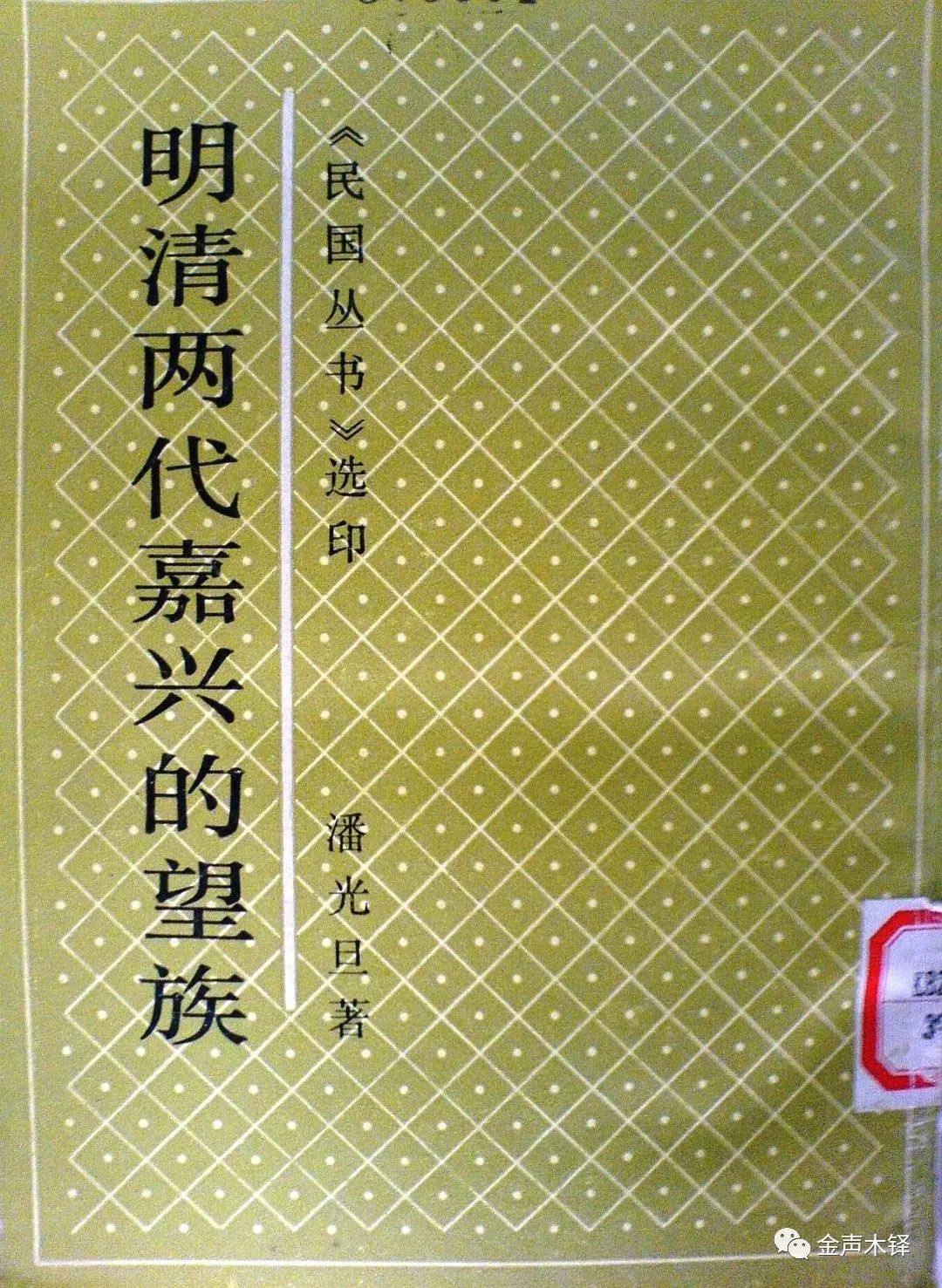
与此同时,一些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中国学者,如费孝通、李安宅、陈翰笙、杨懋春、林耀华等人,更彻底地脱离了中国学术的传统,突破了传统诠释文献资料和宗法理论的局限,用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学到的方法,开展实地调查和处理文献资料,走出了一条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本土社会的道路。传统家族制同样是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或者把家族私有制度作为他们进行社区研究的重要一环,或者对家族制度的一些侧面进行专题的研究。他们着重考察的大多是由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经验中引出的基本问题,如亲属称谓、血统继承原则、乱伦禁忌、家族财产关系、家族组织的结构和社会功能等等。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从一起步就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5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研究风格更为多元化。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曾一度中断,但一些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在研究传统家族制度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和专制统治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趋势方面,已取得一定的进展。而在台湾,则有一批人类学家,着重以台湾社会为研究对象,作了大量的人类学调查和研究。一批西方人类学家也在香港新界和台湾地区,对传统中国家族制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起一套关于中国家族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另外,日本的学者则从历史学的角度,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着重从村落共同体、家族法、族产制度等方面,考察传统中国家族制度。
中外学者这些研究,尽管角度不同,方法多样,风格各异,良莠不齐,但大多是根据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经验,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传统所建立的概念体系、理论法则和研究技术,直接移植于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研究的科学化,有着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剖析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改变和深化了人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认识(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家族制度本来只是我们直接参与其中的一种生活体验)。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形成了一套在世界上堪称发达和完备的宗法理论,但这套理论是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伦理观和思维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是一种凭直觉和睿智建立起来的政治伦理学说,与西方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有根本的差异。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家族制度,使国人得以走出伦理观念和心理情感的圈子,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认识本土社会。无论是从家族制度中寻找中国社会停滞和落后的原因,还是把宗法制度解释为封建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带有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缺陷,但这些认识都曾经在近代中国革命中引起了对传统家族制度的强大冲击,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显示出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社会研究置于社会科学的一般框架之中的可能性,证明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般法则来解释。如主要由西方人类学家根据研究部落社会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功能主义理论和功能分析方法,就曾成功地广泛应用于中国家族制度研究。特别是英国人类学家Maurice Freedman的华南宗族研究,更是把功能学派的单系继嗣群体理论成功运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一个范例。
总之,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研究的进展,改变了中国人对本土社会的认知结构,显示了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随着研究的深化,进一步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实践中,发展出一套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必要性,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二
在中国社会研究逐步深化的进程中,研究者们越是努力把中国社会和文化套入西方社会科学的框架之中,就越能发现,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在相当深刻的层面上有着根本的差异。从由西方文化中产生出来的问题意识出发,把一些由研究西方社会所获得的经验性法则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假设,以至直接套在中国的历史事实上进行解释,往往会力不从心,甚至会使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淹没在一堆西方式的概念术语和逻辑法则之中。本来一些通过比较不难体察到的差异,也可能会由于采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及分析方法来研究,而变得模糊难辩,或似是而非。因此,重新检讨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对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适用限度,就成为深化对中国社会文化研究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在家族制度的研究中,西方的社会科学早已发展起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这些理论和方法,或是从西方社会和历史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或由西方人对各种部落社会的实地观察与亲身体验中归纳出来的。那么,由西方社会和部落社会归纳出来的理论、法则,如果直接套在中国的史实之上,可能会产生多大的偏差呢?是否足以解释中国家族制度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呢?我们在承认这些理论、法则在相当程度上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同时,似乎还应该对可能存在的局限有充分地了解。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无论在外观上,还是在深层结构上,都与西方社会和部落社会有一系列重大的差异。从文化价值系统到思维方式,从文明的起源到后来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文化传统都有其相当明显的独特性。显然,从西方社会和部落社会的研究经验归纳出来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要直接套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必然会出现种种不相适应的问题。
譬如,关于家族制度的演变法则及其历史地位,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建立起来的理论,一般认为,血缘关系本是人类最早的现成的社会关系。随着国家的形成,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血缘关系就由地缘关系撕裂并取代。宗法关系必然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解体。大家族的解体与家族规模的小型化,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韦伯甚至断言,中国的宗族制度,绝对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些观念,长期以来已形成为一种“成见”。这种“成见”,虽然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及其演变历史的复杂性,有许多现象和问题,并不是这些“成见”所能解释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就没有以撕裂血缘关系为前提来确立地缘关系,而是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国家系统和宗法系统高度统一起来,整个地缘性群体往往表现为血缘性的纽带。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家族关系和家族组织的外观形式曾有过很大的变化,但其文化内涵却一脉相承地存续下来。尤其是16世纪以后,虽然商品经济有长足地成长,货币经济关系广泛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也没有导致宗法关系的解体。甚至越是经济发达,商人资本越雄厚的地区,地域性社会组织越是表现出家族化的倾向,血缘关系恰恰由于商品货币的力量而更为强固起来。但另一方面,在宗法关系交织渗透于一切社会关系,大家族组织广泛存在的同时,那种一般认为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占统治地位的小家庭,又在两千多年前已成为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家庭形式。而近年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乡村小家庭的经济基础更为稳固的时候,宗族组织却又死灰复燃,联宗活动异常活跃。这些事实,如果根据西方社会科学的经验,看起来是颇为矛盾和难以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一种更适合于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解释模式,形成对中国社会更具穿透力的研究技术,归纳出一些社会科学的新法则,这就不但可以大大深化人们对中国家族制度的认识,更可以修正以至丰富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为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特性,就是中国的传统家族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并且作为一种文化系统,包含了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家族宗法理论和伦理观念。这一套理论,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正统的社会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又深深影响和制约着基层社会的家族结构与亲属行为;既外化为一种由国家权力提倡的社会理想规范,又内化为一般社会成员普遍的心理体验和内心自觉。于是,在这种政治伦理学说长期影响下所形成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和符号系统,就不仅构成为大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更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向基层社会渗透,融为地方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制度,除了要区分理想规范与实际社会关系,区分大传统与小传统外,更有必要发展起一种从历史过程与文化过程的互动中把握家族制度的社会特质与文化性格的分析方法,建立一种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如何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渗透的理论解释模式。
要做到这一点,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研究方法尤其显得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研究的要求。根据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主要是以西方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以及以非西方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实地调查和亲自参与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的方法,通过对调查问卷等资料的分析,从研究者观察和体验到的事实中,抽象出一系列分析性的概念,再通过理性的思考形成理论。除了像马克思、韦伯这样的思想大师外,社会科学家很少重视历史的方法,很少注意历史因素的作用,对历史资料的意义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没有理论假设,不重视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体验。特别是中国的正统史学传统,把文人的记录等同于社会的现实,把理想的规范当作实际的社会关系。这两种倾向都妨碍了对传统中国社会研究的深化。就中国传统家族制度而言,文字记录下来的事实,与传统社会的实态之间是有相当大距离的。但文字记录的文化传统,又对现实中的家族制度有相当深刻和复杂的影响。因此,在具体地考察家族组织的构造及其与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现实联系时,如果没有对早已形成为一种理想规范的观念,对文字记录下来的传统有深入的了解,也就很难真正认识到家族制度的全部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的意义。于是,如何把历史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把对历史文献的阐释同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结合起来,从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揭示出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真相,需要发展起一套更为有效的研究技术和方法。
我们似乎无须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运用于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研究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一一举出,以上的一般性例子显然已表明,在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实践中,建立起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理念和研究范式,已成为当今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研究者们不可回避的责任。

三
如何建立起中国社会的科学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又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在大量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的研究,不管研究者是否自觉,已经开始走出了一条新路,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现在要从大量研究实践中总结出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范式的一般原则,也许为时尚早,亦非笔者学力所能胜任。这里只打算谈一点笔者从前人的研究实践中得到启发而形成的想法。
由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定范畴出发,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实际中,抽象出一套适合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概念体系,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项基本要求。传统的中国学术缺乏逻辑的分析的方法,很少通过抽象的概念来分析社会事实,也就不需要建立起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概念体系。所以,在西方社会科学被引入于研究中国社会时,很自然地首先是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的概念套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事实之上进行分析。例如在家族制度的研究中,最常见是把诸如:nuclear family, stem family ,joint family,extended family这一类在西方家庭研究中形成的分类概念,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组织之上,作为分析中国传统家族形态的基本前提。这种把按西方社会之“足”定制出来的“履”,套在中国社会之“足”上的做法,虽然简单易行(中国传统社会中复杂异常的家族组织,因为套上了这些概念,也就很容易被分类和分析了),但正如把按人脚外形制造的鞋子套在猩猩之足上一样,开头或者会产生一种新鲜感,但新鲜感过后,因不合“脚型”而产生的不适就会越来越令人感到别扭。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的许多基本范畴,都有着与西方社会根本不同的特殊内涵,即使在个人,群体、社会这样最基本的范畴上,其文化内涵也与西方有本质的差异。把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直接搬过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总难免出现移橘为枳的结果。在家族制度的研究中,甚至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也难逃此“厄运”。以family,lineage,clan这三个概念为例,这三个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其一般之意分别是家、宗族和氏族。但实际上,西方社会中的family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有着很不相同的内涵。由西方人类学研究中界定出的Lineage和Clan两个概念的含义,也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和“氏族”有许多重要的差异。西方人类学者开始时就曾为应把中国传统的宗族组织译为lineage还是clan感到困扰。这本身说明中国的宗族与lineage和clan都有差异。后来Freedman 等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各种类型的继嗣群体的基础上,或根据功能性因素,或根据系谱关系,界分了Lineage和Clan两个概念的区别,力图使之更贴近中国社会的实际。但实际上,“宗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定的文化范畴,它的意义是很难与Lineage或Clan直接等同起来的。作为一套文化符号的集合,中国传统的宗族,并没有人类学家界定Lineage和Clan时所指出的区别;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实体,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两个概念又不能涵盖中国传统家族组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值得玩味的是,西方人类学研究者一般把有更明确的系谱关系和更强的文化功能的继嗣群体定义为Lineage,反之则为Clan。但近年来中国出版的许多译著,却常常将Linage译为“世系”、“族系”,反将Clan多译为“宗族”。虽然这主要是由于译者对西方人类学家关于中国宗族制度的研究不熟悉之故,但即使将Lineage译成“宗族”,Clan译为“氏族”,是否就与这两个中文词语的本意一致呢?这一简单的事实,反映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中的一些基本的理念,是很难准确地互译,而不发生“误读”与“变形”的。这种由于文化的差异而导致对“话语”的会意“颠倒”,在跨文化研究中是普遍存在的。正因如此,由另一文化母体中产生出来的概念体系不能直接搬来套用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诚然,社会科学研究本来就是通过一系列由社会事实抽象出来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现象的,抽象的概念当然不必直接等同于社会事实本身。因此,我们无意否认西方社会科学既有的概念体系对于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能够起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无论研究者是否承认,当他们把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移用于分析中国社会时,总是要重新界定或调整这些概念的定义。当西方人类学家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血缘群体界分为Lineage和Clan的同时,亦就赋予这两个词语以新的含义了。既然如此,我们建立一种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理念和研究范式时,不是更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范畴出发,从中国的史实中抽象出一些新的概念吗?这些由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产生出来的概念,并不是与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原有的概念系统相冲突的,恰恰相反,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形成的概念系统,必将丰富和完善社会科学的整体理论架构,使之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因而对深化人类对自身社会的认识具有更强的穿透力。
建构关于中国研究的概念体系,并不只意味着发明一些新的术语,界定一些新的概念,而是要由此形成一套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理念。因此,困难在于要从中国社会的事实出发,根据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来形成概念。当我们只是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传统中国社会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学习用西方人的眼光,用西方文化的逻辑来观察本土社会。但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的逻辑与中国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西方的文化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文化,西方的学术传统是建立在原子论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文化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科学也就必然是从个人出发,说明个人组成群体、组成社会的种种法则。在家族研究中使用的群体(group)、组织(organization)和法人(corporation)等概念,以及像功能主义这样的分析方法,都是在一种从个体到整体的逻辑基础上形成的分析理念。而中国传统社会从来就不是由个人本位构成的,社会组织在本质上并不是由个体组合成的界限分明的团体,4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别,对于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分析理念是一大贡献。用“差序格局”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意味着形成一套与西方社会科学既有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系统,它要求从思维方式到研究方法都必须更多地根据传统中国文化的逻辑来调整。
关于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分析理念,应该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一系列独特的范畴进行现代诠释来形成。黑格尔说过:“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哲学史讲演录》三联书店,1956)故此,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范畴,是建立一种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基本途径。在传统家族制度的研究中,诸如礼、气、孝、义、宗、家、房、伦之类范畴,对于我们理解传统家族制度,都是一些关键性的范畴。怎样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闸明这些范畴的意义,建立起一系列分析性的概念,可能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基本范畴的意义往往十分歧混,很难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抽象思维方式和概念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去把握和规范其概念。形成这些范畴的中国文化母体本来就缺乏逻辑思维与抽象思维的传统,对这类范畴只需要凭直觉与悟性去体验,或者从具体化的形象来理解。于是,要用在科学主义时代形成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来解释和定义这类纯中国式的文化范畴,并企图从中抽象出形式化的概念系统,似乎存在着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又牵涉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还包括了在认识论的层面更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内容。
认识论的问题应留给科学哲学家去讨论。这里只想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与思维方式,是一种强调矛盾和谐的整体连续性的表意思维,与西方的原子论宇宙观和分析性逻辑思维方式有着根本的差异。是否能形成一种既建立在近代科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又能为传统思维方式留有一席之地的认识论,并在这种认识论的支持下,形成更适合于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这也是建立中国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一个关键。令人乐观的是,20世纪科学认识论的新发展,与中国传统的整体观与表意思维方式有相通的一面。这就意味着,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有可能得到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支持,并与国际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趋势相一致。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基本范畴,尽管用逻辑的抽象分析方法难以驾御,但可以用现代的文化阐释方法,将这些范畴的逻辑规定性悬搁起来,返回其具体性与表意性上,以隐喻思维的方法,形成分析性研究的概念。这样,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就不必回到中国学术传统的直觉和内心体验上去,而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现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要建立的关于传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绝不可误解为向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回归。如果说,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趋势是要把概念从逻辑法则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则首先应从内省直觉中走出来,在实证性和分析性研究的基础上,开辟通向世界学术潮流的道路。
本文原刊于王宾、[法]阿让·热·比松主编:《狮在华夏——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2—183页。转载自“金声木铎”公众号。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历史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