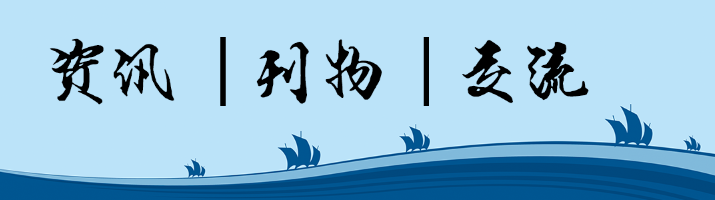

瘟疫、饥馑与施饿鬼仪式——朝鲜“己亥东征”背景下日本的饥疫对策
康昊
//摘 要
///
ABSTRACT
日本室町时代的应永期(1394-1428)是相对安定和平的时期。但自1419年朝鲜对日本发动“己亥东征”之后,日本列岛接连被饥馑和瘟疫打击,室町幕府遭遇了空前的政治危机。在这样的局面下,作为执政者的足利义持实施了一系列饥疫对策及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对五山禅宗制度进行的改革与为超度战争、饥馑、瘟疫死难者亡魂而举行的大施饿鬼法会仪式,二者是室町幕府所实行的饥疫对策中最重要的环节。
引言
日本室町时代(1336-1357)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1386-1428)执政期间,是被称作“应永和平”的安定时期。但自应永二十六年(1419)以后的两年之间,却先后发生了“应永外寇”(即朝鲜发动的“己亥东征”)、日本与明朝断交(朝贡中止)、应永饥疫等接连动摇室町政权统治的事件。尤其是1420-1421年爆发的大规模饥馑、瘟疫,造成大量死亡,引发社会动荡,并因其与“己亥东征”这一对外危机事件的联系,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应永饥馑是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馑之一。关于应永饥馑、瘟疫爆发的原因,伊藤俊一从气候的视角指出,应永(1394-1428)至宽正(1461-1466)期间是日本列岛气候由寒冷期转向温暖期的重要时期,急剧的气候变动引发了洪水和旱灾。1417年以后,持续三年的旱灾与秋季的连绵降雨使得1420-1421年之间爆发了全国性大饥馑。清水克行从经济角度入手,认为市场经济、物流业活跃使得京都成为粮食囤积的消费都市,饥馑发生时饥民大量涌入京都造成二次饥馑是应永饥馑扩大的主要原因,并指出饥馑发生——难民流入京都——瘟疫爆发是室町时代饥馑、瘟疫的基本模式。
有关室町幕府在应永饥疫之际采取的应对措施,清水克行和早岛大祐做出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清水克行对瘟疫之后足利义持于1422年发起的“德政”改革做出了深入分析,认为1422年的德政以七月足利义持发布的《御成败条条》为契机,对土地制度、诉讼制度做出了自南北朝战乱(1336-1392)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足利义持推行了厉行佛事神事、保护寺院神社领地、改革诉讼、债务破弃等“德政”政策,并以禅宗式禁欲主义大力推行佛神事祭祀活动。早岛大祐则关注了足利义持以对外关系的紧张为背景复兴神祇祭祀仪礼的举动。
可以说,“己亥东征”及紧随其后的1420-1421年饥疫期间足利义持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对室町社会及室町幕府的政治走向有着极大的影响。但目前为止,对室町幕府对策的研究仍有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足利义持的宗教政策与应永饥疫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尚不充分。因此,本文从1420-1421年饥疫期间足利义持发动的禅宗改革,及举办的五山禅僧大施饿鬼法会仪式(死难者追荐仪式)入手,关注施饿鬼这一宗教仪式对幕府重建灾后秩序所起到的作用,并考察灾害危机中室町幕府的对策。
1420-1421饥疫期间幕府举办的大施饿鬼法会也引起了先行研究的一定关注。原田正俊认为施饿鬼是五山禅宗的主要法会,是五山禅宗参与到国家祈祷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显密诸宗异质的“大陆风”(即宋元风)法会。西尾和美则具体从1422年的大施饿鬼入手,认为该法会是室町幕府采取的主要饥疫对策之一,幕府对饥民的施食失败之后就将对策重心转移到了施饿鬼这一追荐仪式上。本文在二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作为饥疫对策的大施饿鬼仪式的全貌,并试图分析其与足利义持禅宗改革以及“己亥东征”这一东亚背景的联系。应永饥疫期间的大施饿鬼是幕府最重要的饥疫对策之一,对这一系列仪式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室町社会及室町幕府灾害对策机制的认识。
一、1420-1421年的饥疫与禅宗改革
如前所述,应永二十八年(1421)瘟疫的发生是前一年爆发的饥馑所导致的结果。在瘟疫、饥馑发生前的1419年,因为朝鲜对日本发动“己亥东征”、日本与明朝断交等事件,室町幕府遭遇了南北朝合一以来的最大危机。关于“己亥东征”即日本所谓的“应永外寇”事件的过程,目前已有充分的研究。在此依据佐伯弘次的论述对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事件发生的背景是14世纪后半叶以来日益威胁朝鲜半岛的倭寇问题。1419年5月14日朝鲜太宗(1367-1422)决定攻击倭寇巢穴对马岛,23日“大唐国、南蛮、高丽等”进攻日本的消息传到京都,6月20日战斗正式开始,8月7日少贰满贞向室町幕府报告战况,7月至8月朝廷和幕府要求醍醐寺、石清水八幡宫等进行“异国降伏祈祷”。在整个事件前后,日本除了与朝鲜的武力冲突之外正经历着对明朝朝贡贸易的断绝、对琉球船只的拘留,以及东南亚“南蛮船”来航等状况。另外,朝鲜发动袭击的导火索是5月5日对马倭寇集团袭击朝鲜半岛,其原因则与对马守护宗贞茂死去,对马岛内部局势不稳有关。
从1419年的“己亥东征”事件到1421年的瘟疫之间,日本各地神社出现了众多的怪异事件。这是神国思想影响下不安定的国内局势的反映。譬如说,1419年6月25日京都流传着山阴地区最重要神社出云大社“震动流血”的传言,同时摄津广田社也发生震动,传闻有一位“女骑之武者”率军兵数十骑向东而去。另外,前一日将军足利义持参拜八幡宫时鸟居突然倒塌。此后京都流传记载前方战况的“探题持范注进状”(伪文书)当中,也记载了一名女性武者出现,大败“异国军兵”的逸事。西山克认为,广田社是祭祀天照大神荒魂的神社,京都流传的女武者怪异是对天照大神或神功皇后灵威的宣传。除此之外,直到1421年饥馑、瘟疫爆发期间,北野社、伏见御香宫、热田社等多地陆陆续续都发生了怪异现象。面对外敌侵入之下诸神社怪异的现象,足利义持仿效“文永、弘安之役”(即忽必烈征日战争)的先例命令神社寺院实施祈祷,当时明朝使节吕渊正在日本,吉田贤司认为足利义持驱逐明使、对明朝断交的动机之一就是出于对诸神社怪异频发的恐惧。即通过神社祭祀,让守卫日本列岛的神灵将外敌、饥馑和瘟疫阻挡在“神国”日本之外。
然而,在“己亥东征”事件之后的第二年,日本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饥馑。由于大量流民饿死未及收尸,次年开春以后瘟疫开始在京都蔓延开来,“疫病兴盛,万人死去”。而后公家贵族之中也陆续出现死者,内大臣大炊御门宗氏、大纳言北畠俊泰、中山满亲、左大臣今出川公行等纷纷病死,令贞成亲王惊呼“天下病事恐怖无极”。从2月开始,5-6月疫情到达顶峰,到7月以后逐渐平复下来。然而就在7月11日,京都传来的伊势神宫的“神讬”(神官或巫女被神明附体,代传神旨的行为)。神讬内容将这年的瘟疫与两年前的“己亥东征”事件联系在一起,将导致瘟疫的原因解释为“蒙古袭来”(即己亥东征——当时谣言袭击对马岛的是“高丽”与“蒙古”联军)之际被日本的神明杀死的“异贼”(实为朝鲜军)化作怨灵作祟所致,并说瘟疫将导致万人死亡。
濑田胜哉认为,伊势神讬的出现唤醒了民众对己亥东征事件的记忆,伊势神宫成功地将伊势的神明塑造为击退异国的守护神和驱散瘟疫的治病神二者的结合体。西山克则指出神讬意在表明“异贼”怨灵作祟、“外寇”持续作乱,变为疫鬼继续威胁日本的王都。在伊势神讬的影响之下,室町幕府果然增进对伊势神宫的崇信。山田雄司发现足利义持是室町时代参拜伊势神宫最多的将军(共20次),其中仅瘟疫爆发的1421年就参拜了四次。早岛大祐则指出足利义持同时下令恢复中断数十年的祈年谷奉币仪式,这一仪式实质上就是伊势神宫的祭祀仪式。事实上,足利义持的祈祷并非局限于伊势神宫一家,在对外战争和瘟疫面前宣扬本寺本社灵验的也绝非仅有一个伊势神讬而已。本文特别关注的,是瘟疫期间足利义持对五山禅宗寺院采取的措施及其与“己亥东征”后饥疫的关系。
在瘟疫横行的1421年5月28日,贞成亲王在日记中记载了此期间后小松上皇(1377-1433)做的一个关于禅宗寺院的异梦。以下是日记内容的译文:
这段时间,仙洞(后小松上皇)做了个异梦。梦中相国寺门前聚集了一千头牛,意图闯入门内。寺院的住持将牛驱赶出去,进前喝道:此处乃坐禅之所,你们不得进入。于是一千头牛退出相国寺,乱入京都街市。梦中有人说道,这牛就是疫病之神。而后,后小松上皇清醒过来,在将军足利义持参见上皇时将异梦内容告诉义持,义持离开上皇居所之后就去了相国寺,命令寺僧认真坐禅,寺院僧侣随“依座勤行”。
中世日本人对异梦极为重视,认为是神佛的示警,对梦的解释往往带有宗教含义。早在镰仓时代,贵族社会已倾向于认为由宋元中国传入的新兴宗派禅宗具有镇伏怨灵、妖怪、天狗的能力,将禅宗寺院结制安居、二时粥饭、四时坐禅视为对付妖怪的手段。清水克行认为,后小松上皇梦中的牛是对疫病之神牛头天王的联想,而梦境的含义是瘟疫之际唯有兴盛禅宗,督促禅僧坐禅,才是消除国难的唯一“德政”。在中世社会的普遍认识中,厉行佛事神事、保护寺院神社领地是“德政”的基本内容。清水克行指出瘟疫结束之后的1422年足利义持实施了其执政期间第二次“德政”改革,其中就包含了禅宗式的禁欲主义政策。因此,后小松上皇这段关于瘟疫和相国寺、坐禅的异梦,可以说是对足利义持“德政”中整肃禅宗寺院政策的反映。
原田正俊认为,足利义持执政时期是幕府的五山禅宗寺院管理制度的重要形成时期。五山禅宗内部创制了详细的管理细则,在将军的认可之下得以实施。其内容主要是整肃佛事,防止佛事法会的形式化,禁止僧侣奢侈行为,严控住持推选流程等等。但原田并未对足利义持禅宗政策的背景做出考察。
事实上,足利义持对五山禅宗亲自发布的法令,主要是在1419年的“己亥东征”到1421年的瘟疫之际实施的。譬如1419年足利义持曾对五山建仁寺发布《建仁寺法》,当年10月9日又制定针对五山禅宗全体的,涵盖饮酒、佛事、僧职、服装规定等的《山门条条法式》。当月相国寺僧不遵法令饮酒,当即遭到了幕府的严惩。1421年瘟疫期间,足利义持又发布《住持规式》,整顿禅宗五山十刹诸山寺院住持及寺官选任、任职年限等问题。可以说,足利义持在1419-1421年期间发布的针对五山禅宗寺院的管控及改革措施,是在“己亥东征”及其后发生的饥馑、瘟疫的背景下做出的,是对其父足利义满发布的《禅院法则条条》(1372)与《诸山条条法式》(1381)的改革和发展。足利义持禅宗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整顿禅宗寺院秩序,严格寺规寺法,来确保禅僧祈祷、坐禅的灵验效力。因此,足利义持的禅宗改革政策是饥馑、瘟疫肆虐之下厉行神事佛事“德政”的一环。而后小松上皇的异梦及此后足利义持要求相国寺僧认真坐禅的举动,正是其禅宗“德政”的反映。
二、作为饥疫对策的禅宗大施饿鬼
五山禅宗寺院参与到1420-1421年的室町幕府饥疫救济对策当中,主要形式是举行施饿鬼法会。施饿鬼即施饿鬼食,是中国佛教及日本中世禅宗主要佛事法会之一,在中世禅宗语境之下与中国佛教极为常见的“水陆会”同义,并且,施饿鬼或水陆会进入统治者的镇魂、战争及灾害死难者超度追悼仪式的契机,是文和三年(1354)由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举办的战死者追悼水陆会,这是南北朝动乱期间最重要的“战争终结仪式”。此后,施饿鬼法会逐渐出现在室町时代历次的战争、饥馑与瘟疫后的镇魂仪式之中。根据《看闻日记》《师乡记》等的记载,1420-1422年这三年间,一共有至少七次施饿鬼法会能够得到确认:
第一次:应永二十七年(1420)4月16日在相国寺举办的足利义满十三回忌佛事大施饿鬼(《师乡记》)。
第二次:应永二十七年(1420)5月4日同在相国寺举办的足利义满十三回忌佛事大施饿鬼(《看闻日记》)。
第三次:应永二十七年(1420)7月15日盂兰盆节在大德寺、相国寺等京都禅宗寺院各处举行的定例施饿鬼法会。此次施饿鬼法会期间发生了相国寺喝食(禅寺当中的少年修行者)互掷飞石的斗殴事件,正在法会现场的将军足利义持的乌帽子也被击落,十分狼狈。同时大德寺举行的施饿鬼法会当中,大德寺住持暴死,传为盗贼所害。
第四次:应永二十八年(1421)6月15日在大光明寺及五山以下各寺举行的为瘟疫、饥馑死者追悼的大施饿鬼法会(《看闻日记》)。
第五次:应永二十八年(1421)7月15日在大光明寺等寺院举行的定例施饿鬼(《看闻日记》)。
第六次:应永二十九年(1422)7月15日在大光明寺等寺院举行的定例施饿鬼(《看闻日记》)。
第七次:应永二十九年(1422)9月7日在鸭川河原举行的大施饿鬼法会,后变革为在五山寺院举行(《看闻日记》)。
这七次当中,明确与应永饥馑、瘟疫有关的施饿鬼法会为第四次(1421)、第七次(1422),两次法会均为规模较大的“大施饿鬼”。接下来我们就来结合具体史料及先行研究来对这次法会仪式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在室町幕府举办施饿鬼仪式之前的1421年2月,室町幕府试图对涌进京都的饥民进行救济。饥馑频发的室町京都堪称“饥饿之都”。《看闻日记》记载道(以下为译文):
去年(1420)干旱饥馑之时……公方(将军足利义持)命令各大名在五条河原设立临时建筑,向饥民施行救济。领导施与的食物仍然“醉死”的人据说多达千万。到今年开春,疫病更是猛烈。据说死者达万人。天龙寺、相国寺施行救济,贫困的灾民聚集于此。
显而易见,室町幕府实行的救济措施并未收到成效。吉田贤司认为幕府应对已晚,致使死者增加,进而引发瘟疫。西尾和美则指出,本次救济由将军主持,而后由于死者迅速增多,救灾已经无效,幕府的救济遂转向施饿鬼这一超度佛事。这两次大施饿鬼实施的状况均记载于《看闻日记》。其中1421年的大施饿鬼仅记载“今夕大光明寺有施饿鬼,是人民死亡为追善,五山以下寺寺有施饿鬼云云,仍俄执行,地上地下劝进云云”一句,1422年的大施饿鬼则记载较为详细,以下为《看闻日记》当年9月6-7日条,这两段记载为汉文,故直接引用于下:
9月6日:抑闻,于〈五条〉河原今日大施饿鬼依风雨延引云云。此事去年饥馑病恼万人死亡之间,为追善,有劝进僧。〈往来啰斋僧相集〉。以死骸之骨造地蔵六体,又立大石塔为供养。可有施饿鬼云云。此间有读经,万人鼓操打栈敷。室町殿可有御见物云云。五山僧可行施饿鬼云云。
9月7日:抑河原施饿鬼事,劝进野僧为张行,五山僧众可执行事不可然之由,自山门支申。室町殿御见物事更不被仰出云云。又劝进僧河原物喧哗出来,僧一両人被突杀了。施饿鬼供具等散散取失,河原物取之。余过分之间天魔为障害,大风大雨散散无正体罢成云云。劝进施物如山出来被入五山,于寺寺可行施饿鬼之由自公方被仰云云。并天狗障害不思仪事也。
以上两段史料记载了9月7日在京都鸭川五条河原(河岸)举行的大施饿鬼法会的状况。史料当中记载了“河原物”与“劝进僧”的冲突,导致施饿鬼供物被抢,劝进僧一二人被杀,加之大风大雨,使得现场一片狼藉的状况。其中“河原物”即“河原者”,是居住在鸭川沿岸的底层民众(贱民)。根据下坂守的研究,四条河原的“河原者”居住在鸭川以西、四条以南的河岸,其聚落与一般民众被区别,受到一般民众的歧视、贱视。“劝进僧”则是为法会、寺院修建等募资的专业僧侣集团,中之堂一信认为室町时代的劝进僧往往采用各种演艺形式丰富劝进活动的内容,吸引广泛社会阶层的人们捐资。劝进僧在饥馑、瘟疫发生之时也非常活跃,譬如室町时代中期著名的劝进僧愿阿弥就曾在饥馑之际受将军资助造临时建筑两百间,并向饥民施粥和菜羹。受到幕府支持的愿阿弥率领麾下的劝进僧集团,在灾害发生时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救济。
但对于以上两段史料,尤其是鸭川河原施饿鬼的执行者及执行状况,“河原者”、劝进僧与五山禅僧各自扮演了何种角色,先行研究的理解略有不同。因为“劝进僧”集团相较于五山禅僧更带有民间的色彩(《看闻日记》称其为“野僧”),故厘清此次法会仪式参与者的角色,对于了解仪式的性质很有必要。西尾和美认为鸭川河原施饿鬼的执行者是劝进僧,即河原施饿鬼的执行者是劝进僧,在劝进僧举行施饿鬼之后,幕府才吸收劝进僧所举办的施饿鬼仪式,让五山禅宗再次举办。而清水克行则认为本次河原施饿鬼是由五山禅僧在鸭川河原举行的。
笔者赞同清水克行的意见,认为西尾和美对这两段史料的理解有误。由1421年施饿鬼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1421年的施饿鬼是由五山僧“执行”,而法会所需要的资金及法具调度等则通过“劝进”的方式实现。1422年的施饿鬼应当也是这种形式。1422年9月7日的记载也说山门(延历寺)僧反对“劝进野僧为张行,五山僧众可执行事”,“张行”即“举办”之意,“执行”则为实行法会之意,因此五山禅僧是实际参与法会的僧侣,而劝进僧则是法会的募资者及运营者。6日条也明确记述“五山僧可行施饿鬼”。也正因为如此,当“河原者”和劝进僧为争夺法会的供物大打出手,法会无法正常进行之后,足利义持命将施物全部收入五山寺院,令五山僧重新在各自的寺院举行施饿鬼佛事。施饿鬼是室町时代五山禅宗的代表性法会,由五山禅僧来实行,是符合常理的。
另外,本文下一节将讨论,室町时代中后期以后的饥馑、瘟疫、战争超度大施饿鬼都是由五山禅僧在四条、五条河原举行的。1422年的大施饿鬼与室町幕府在之后举行的大施饿鬼在形式和地点上是基本一致的。再者,四十年后的宽正二年(1462)饥馑大施饿鬼时, “就河原施食之事被申先规,于渡月桥施食之事,天龙寺子庭和尚,以状被申”,即天龙寺就大施饿鬼举行的地点选定依据“先规”请求将军的意见。此处的“先规”只能是1422的鸭川河原大施饿鬼。因此,认为1422年的大施饿鬼与1462年的大施饿鬼一样,是由劝进僧操办、五山禅僧在鸭川河原执行,是符合逻辑的。1422年室町幕府为超度饥馑、瘟疫死者举行的大施饿鬼法会,是由五山禅宗执行的法会。五山禅宗是室町政权控制下的“官寺”,其仪式法会带有室町政权的意志。很显然,1422年的河原施饿鬼是在室町政权意志下实施的。足利义持对五山禅宗的改革政策也好,命五山禅僧举行的大施饿鬼也好,都是其饥疫对策的一部分,禅宗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1422年的鸭川河原大施饿鬼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如拙文所述,大施饿鬼或水陆会成为室町幕府的重要法会仪式,其契机是14世纪的南北朝战乱。这是因为施饿鬼仪式具有敌我双方战死者超度这一“怨亲平等”的意义。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屡次实施的“蒋山法会”也具有类似的含义。如前文所述,1420-1421年饥馑、瘟疫爆发之前曾发生朝鲜侵入对马岛的“己亥东征”事件,瘟疫之中出现的伊势神讬也认为瘟疫爆发是战死的朝鲜军化作怨灵作祟的结果。濑田胜哉指出伊势神讬唤醒了人们对两年前外敌入侵的记忆。西山克则认为怨灵的出现使得当时人们相信“外寇”未止,瘟疫是战争的延续。因此,除了亲赴伊势神宫祭祀神明,请求神明驱逐疫病之外,我们可以认为,足利义持积极利用五山禅宗,实施禅宗政策改革,确保禅宗佛事、坐禅的灵验效力,并令五山禅僧实行施饿鬼,就是要通过施饿鬼这一“敌我双方超度仪式”,对“己亥东征”之役中死难的日本军及朝鲜军进行荐亡,以防止其继续作为怨灵作祟。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作为镇魂仪式的大施饿鬼,是室町幕府面对“己亥东征”以来的危机,试图平复饥馑、瘟疫,重建灾后秩序而采取的重要政治措施。
三、幽冥入口:大施饿鬼的仪式空间
上一节提到,1421年的大施饿鬼是在禅宗五山各寺院分别举行的,而1422年的施饿鬼则转移到了京都鸭川五条河原(河岸)举行。此后室町幕府为饥馑、战争举行超度,举办大施饿鬼法会之时,也往往选择鸭川河原为会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场所转移呢,鸭川河原这一“场域”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比如说,宽正二年(1462)著名的“宽正饥馑”爆发,当年前两个月据说已有八万两千人死亡。禅僧横川景三则记载“天下大饥,枕骸遍野,不知其几千万人”。3月到4月,幕府命令五山禅宗举行大施饿鬼:
3月29日:相公命建仁寺之一众,开施食会于第五桥上,以荐饥疫死亡之灵〈且书牌曰,尽法界没亡灵〉。
4月10日:以源相公(足利义政)命,相国寺一众率其派等持寺・等持院・真如寺之众,于四条坊桥上开施食会,以荐饥疫死亡之灵。
4月12日:本寺东福之众,就四条坊桥上开水陆会,赴其会者三百余员也。以前亡没后各各幽灵之八字书灵牌。相国建仁以三界万灵十方至圣为牌字也。
4月17日:万寿寺一众于第五桥上开水陆会,书牌以河沙饿鬼各各幽灵之字。
4月20日:南禅之众于四条坊桥上开水陆会,以它界此界一切亡灵书牌。
引文中的“施食会”“水陆会”均是同一法会,即施饿鬼。可以看到,1462年幕府举办的大施饿鬼由五山禅僧分别在四条大桥、五条大桥即四条河原、五条河原举行。与之类似的还有大永七年(1527)川胜寺口之战(室町幕府军与堺公方军的冲突)之后,五山禅宗为战死者举行的大施饿鬼会。根据《东福寺清规》的记载,当时东福寺在四条桥设水陆会,以“前亡没后各各幽灵”为施食牌;南禅寺也在四条桥开水陆会,书“它界此界一切亡灵”为牌;相国寺同在四条桥,以“三界万灵十方至圣”为牌;建仁寺在五条桥施食,以“尽法界没亡幽灵”为牌;万寿寺亦在五条桥施食,书“河沙饿鬼各各幽灵”为牌。可见,1462年的大施饿鬼与1527年的大施饿鬼在地点安排、五山各寺院施食牌的书写方式上是一致的。
1422、1462、1527年的大施饿鬼均选择鸭川河原举行,前者仅在五条河原举行,后者则扩展到四条、五条河原。之所以选择五条河原为施饿鬼场所,与中世人对京都空间的认识有关。在1422年大施饿鬼实行之际,京都鸭川上仅有四条大桥和五条大桥两座桥,五条大桥是由民间出资建造,竣工于应永十六年(1409),1427、1441年因洪水冲毁,后由愿阿弥募资重建。四条大桥建于1374年,1383、1441年两次被洪水冲毁。四条、五条大桥及河原在京都空间中具有特别的宗教意义。下坂守指出,四条大桥属于祇园社,西侧鸟居为祇园社结界处,结界以东属于“神圣空间”。五条大桥则是通往观音信仰的中心区域清水寺的起点,中世人认为走过五条桥,登上清水坂之后就进入观音净土世界,而五条桥在“六道十字路”(现京都六道珍皇寺一带)处向东南方行进则是古代中世以来的丧葬场所鸟边野。五条大桥、五条中岛一带具有“冥界入口”的宗教意味。清水克行则发现,作为中世京都南段界限的五条、六条一带是处死囚犯、枭首的主要场所,70%的处刑、枭首在六条河原进行。因此,五条河原一带是中世京都都市的界限处,同时也是京都通往关东等地的起点,又是作为丧葬之地、被视为轮回起点、冥界入口的生死交替之处。这使得五条河原(及四条河原)在中世京都人的认识中具有象征生死轮回、由此岸到彼岸的宗教意义。这就是室町幕府选择在四条、五条河原举行超度战争、饥馑、瘟疫产生的无主死难者的场所的原因。
再者,在五条河原附近,五条大路以南还有祇园社的下属神社五条天神社。1648年刊印的俳书《山之井》中写道:
到了节分日,京都的习俗要参拜五条天神,将白术年糕买回来,与家里人一同庆祝节分日。到了晚上,说着“‘mokuri’(蒙古)和‘kokuri’(高丽)”来了”,把入口和门窗加固。
这段江户时代的记述描述的是京都人在节分日驱魔除鬼的一种仪式。值得注意的是,白术是祛除疫病的药材,而被驱逐的疫鬼则是“蒙古”与“高丽”。这可以说是中世“蒙古袭来”与“己亥东征”的残留记忆。濑田胜哉指出,五条天神被视作疫病之神,被视为授予药品白术,使得蒙古、高丽(带来的瘟疫)退散的神社。在1421年的瘟疫期间朝廷还曾颁布旨意“流放”五条天神,即对神明实施惩戒,将神舆逐出京都四境,以祈愿瘟疫消退的宗教仪式。因此,1421年大施饿鬼以五条河原为法会场所,显然是意识到了五条天神作为驱逐“蒙古”“高丽”带来瘟疫的疫病之神的效力,祈愿疫病之神在瘟疫死者超度佛事之中发挥效验。
本节我们对1421年及此后的1462、1527年大施饿鬼的仪式空间做了一个简单的考察。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1421年的大施饿鬼法会时,室町幕府选择以中世京都南段的界限的五条河原为场所,是因为五条河原在中世京都人的精神世界当中具有独特的宗教意义,被视作生死轮回、连接此岸与彼岸的“神圣空间”。另外,幕府同时还期望位于五条河原附近的疫病之神五条天神社在瘟疫死者的超度法会当中发挥灵验效力,将“蒙古”“高丽”即己亥东征带来的瘟疫驱逐出去。在此以后,室町幕府的大施饿鬼法会多此以鸭川四条、五条河原为场所,延续了1421年大施饿鬼时的宗教考量。
结语
本文以1419年的“己亥东征”之后日本爆发的饥馑、瘟疫之后室町幕府采取的对策为考察对象,从室町幕府在此期间发动的禅宗寺院改革及举行的大施饿鬼仪式入手,探讨了室町幕府的宗教政策及宗教救济仪式对平复饥馑、瘟疫,重建灾后秩序起到的作用,并对大施饿鬼的仪式空间做了分析。
1420-1421年的饥疫之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持命令五山禅宗举办的大施饿鬼法会仪式,是其饥疫对策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相较于其失败的饥民救济对策,足利义持在战争、饥馑、瘟疫死难者亡魂的追悼方面更为着力。同时,之所以选择大施饿鬼法会,应该也是因为施饿鬼仪式所具有的敌我双方死者超度的宗教意义,足利义持通过实行施饿鬼,来对被视作造成瘟疫元凶的“己亥东征”朝鲜军死者的怨灵进行宗教救济。
在施饿鬼的场所选择方面,足利义持在第二次大施饿鬼法会中选择了在京都都市空间中具有独特“冥界入口”宗教含义的五条河原,并试图借助疫病神五条天神社将“蒙古”“高丽”即己亥东征所“带来”的瘟疫驱逐出去。另外,在这场精心准备的饥疫救济施饿鬼举行的同时,足利义持还发动了对禅宗寺院的改革,对禅寺制度、佛事法会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力图通过禅宗改革来增强禅僧抵御饥疫的祈祷效验。因而,足利义持的禅宗改革与施饿鬼法会是其饥馑、瘟疫对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室町政权统治者对“己亥东征”及天变地异认识的突出体现。但我们同时也看到,1422年鸭川河原大施饿鬼仪式之时发生了打架斗殴、哄抢供物的状况,令足利义持精心安排的荐亡仪式潦草收场。这反映出了室町幕府宗教救济对策的局限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ZDA235)、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古代中日佛教外交研究”(19ASS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康昊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
原载《海交史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
转载敬请注明出处。
推荐阅读
2021年第2期编校人员
陈丽华、陈少丰、李静蓉、林仪
王丽明、肖彩雅、薛彦乔、张恩强
图文编辑:ZEQ
审核:陈少丰
终审:林 瀚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海交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