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术社
学术传播 × 知识共享


作者桑兵,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文科资深教授
//
还是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笔者与当时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骆宝善老师合写过一篇义和团研究的论文。此后虽然再无直接的论著,不过相关的联系却不少。我的老家河北威县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建有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义和团纪念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周锡瑞教授研究义和团,还一道谈起河北、山东南部交界一带农村的秘密结社与义和团起源的关系。更早时日本的久保田文次教授参与小林一美教授组织的重回满铁调查,便中查访义和团,也到过威县,曾当面讲述过刻骨铭心的相关经历。就个人涉及的晚清史与辛亥革命研究范围而言,义和团是绕不过去的大问题。20世纪初国内学界风潮以及新式社团发起的拒法拒俄和抵制美货运动极度强调文明排外,就是鉴于义和团民气可用而不能泛滥的教训。至于庚子勤王,更是与义和团同时并起的大事,关系尤为紧密。进一步放宽视野,义和团不仅影响了清季最后十年的走向,对于民国以后的历史发展以及历史认识也影响深远。近年来重写大历史,笔者原拟从庚子系列开端,无奈计划较多,精力有限,加之亲历者的日记等资料不足,很难从关键年代小历史的视角充实映证,权衡再三,才不得不忍痛割爱。
一
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并称为三大革命高潮,进一步分别,则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主体都是农民,辛亥革命则是士农工商共同参与,但先驱和领导者已经不是或不仅是士绅。改革开放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研究短暂热闹了一阵,很快陷入沉寂。辛亥革命热度维持的时间相对较长,近一二十年也沉寂下来,其中一部分转为晚清史研究。也就是说,虽然告别革命之说引发不小的争议,在原来以五四运动为下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革命不再成为当然的中心主体,却是不争的事实。
曾几何时,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研究盛极一时。记得1981年参加两广太平天国研讨会的学者超过150人,会议从广州开幕,仅研讨就持续了四天,随即相继辗转桂平、桂林等地,共历时15天,除去水陆交通,实际研讨时间不少于12天,包括途中在西江航船上,仍然进行大会与分组讨论。其时提倡思想解放,压抑已久的学术激情喷薄而出,群贤毕至的与会代表热情高涨,畅所欲言,仿佛有一肚子的话,不吐不快。经过充分的讨论和争论,最后到桂林闭幕时,连发言最为积极的几位学者也感到无话可说了。会议之前,太平天国的议题热闹非凡,关于农民政权的性质问题,意见不同的两造连续撰文不断再论,相持不下。会上这样的争论依然延续,只是形式由单纯打笔仗变成面对面地直言不讳。由于航船上条件所限,无论吃住行,与会的前辈大家如胡绳等和大家一视同仁,充分体现了学术平等的精神。也许因为会期很长,意见都充分表达完了,自此以后,相关讨论渐渐偃旗息鼓,留在人们脑海的,只有会上各路高明侃侃而谈的余音绕梁了。后来本人所关注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各种类型属性的会议,一般而言,长会的效果往往更好,总结与开启,相向而行。至于日程密集紧凑的会议,则大都不过走过场的表态而已。难怪钱钟书眼中的学术会议如此不堪。
二
谈到义和团研究的理念与取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如何认识义和团,二是如何研究义和团。
首先,谈谈对义和团的认识。以往对义和团的看法,大致是从革命以及对外态度两个视角考察。国共两党原来都有革命史,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虽然具体而论分歧不少,大体上看法都比较正面和积极。唯有义和团,观念大异旨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首先就从义和团开始,这与国民党的近代史观清楚分界大有关系。不过,尽管后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基本否定义和团的行为,在官方认可的历史书写以及教科书中,对义和团的看法多为负面。可是在其革命时期,对义和团的动机却加以肯定。1901年留日学生所办《开智录》发表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是正面肯定义和团反对外国侵略的最早文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宣传下,原来受日本影响以正面评价为主导的帝国主义观,迅速为列宁式的帝国主义论所取代,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支持的军阀,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压倒性主张,于是国民革命高揭反帝旗帜。随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高涨,国民革命对义和团进一步表示赞誉。共产党方面,1924年《共进半月刊》第67期刊登的《“反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认为义和团发起的动机,是千对万对的,虽然方法错了,但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排外运动,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件该大书特书的事。国民党方面,1927年有陶百川发表于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办的《向前进》第10期的文章,题为《反帝国主义的先驱———义和团》。文中作者痛斥骂义和团为拳匪的贤士大夫是不识好人心的狗,呼吁用历史家的眼光为被帝国主义走狗污蔑的义和团平反。该文认为义和团是带有革命性的原始民族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先驱,其精神可佩,其手段不足取。陶百川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反帝,不要盲目排外,要用三民主义领导民众踏上革命的正轨。
义和团是否具有反帝的性质,从主观自觉和客观事实看,不能全同。历史巧合,义和团蜂起的1900年,帝国主义概念刚好进入中国,只是并非负面,甚至主要不是负面,而是具有民族主义积极进取的趋向。作为主观认识,直到1920年代,受苏俄革命和列宁式帝国主义论的影响,中国终于正式提出反帝的概念,并据以鼓荡国民运动。所以,五四运动也没有正式提出反帝口号,国民革命才是反帝的正声。而作为客观事件,义和团甚至近代中国史上更早的各种反侵略行动,是否具有反帝的性质,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义和团事件影响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具有分水岭的地位。抗日战争临近胜利之时,中共中央概括总结中国近代史上对外态度的变化,指出:“近百年的中国外交史,中国人在民族立场上曾有过两种错误观念。在义和团事变前,排外的观念占上风,其后惧外的观念占上风。‘五四’到大革命,惧外观念虽曾一度被民族高潮冲淡,但国民党当政二十年,即在抗战时期,上层人士的惧外观念仍很浓厚,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故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这样的论断,符合历史的大势,具体则有不少可以进一步解读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义的双刃剑问题。
所谓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与帝国主义问题联系紧密。列强争霸,引发战争,原因之一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帝国主义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极端发达的形式,作为落后国家图强振兴的可行之道,予以肯定。后来苏俄列宁式的帝国主义论,则认为帝国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大生产过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发动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解放运动在内的世界革命,以打破资本帝国的全球垄断。为了模糊共同属性,有的西方政客以民族主义进行划分,并重新组合,典型的事例就是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划等号,从而使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失去理直气壮的合理性。诚然,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民族主义,也会产生向心和离心的倾向相互作用的情况,从这一角度谈论双刃剑,确有一定道理。若是面向列强,尽管排外不可取,反抗却是正义之举。部分欧美人士主张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全球化,而其国内掌握权力者,很多是不同种族的代言人。无论如何,相较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更应该批判。由此可见,双刃剑之说,相当程度上是欧洲中心至上的变形,用意之一就是试图瓦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反抗强权的正当性,从而剥夺其行动权。
强权与公理,是近代中国知识人遭遇的第一个双标困惑。经过晚清以来一系列对外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知识人普遍意识到西方先进,文明程度更高,并且开始相信其所主张的统统都是公理。可是当他们努力寻求和掌握公理之后用以争取平等时,却又总是遭遇强权。这让他们感到相当失落和沮丧。于是,一部分人转而奋起反抗强权,坚决抵抗外来侵略,一部分人则不得不委曲求全,习惯成自然,逐渐觉得不得不然就是天经地义。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分合。所谓上层人士惧外,不仅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层,也包括相当部分的知识精英,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多少都有惧外的表现,希望尽可能延迟与日本正面冲突的时间。只不过诸如此类的言行一度被冠以理性的名义。他们总结近代以来国人反抗侵略的经验教训,认为“战”虽然获得舆情支持,却毫无成功把握,因而每战必败,结果还是割地赔款。而“和”看似忍辱负重,却能以局部牺牲换取整体安定,哪怕只是暂时苟安,也好过战祸降临,国破家亡,玉石俱焚。毋庸讳言,对抗强权不能盲动,应对高度工业化、军事化的日本的步步紧逼,审时度势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只是一味退让,过度消极,不但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使之得寸进尺,也严重危及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并与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抗热情产生严重分歧和对立。
近代中国历史上,知识精英与民众的显著疏离已经不是第一次。四民社会的中国,虽然士为四民之首,但历史上士人与民众的关系常常若即若离。近代依然如是。戊戌变法与义和团,就是各自分立的典型事件。庚子保皇党的勤王运动,方向与义和团仍不相凿枘。义和团之后,在梁启超等人的宣传下,四民社会开始转化为国民国家,相继发生的拒法拒俄运动,知识人与民众有合为一体之势,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双方正式合流。结合起来的好处立竿见影,既减少了盲目排外,又增强了群体力量,相得益彰。但是义和团式的民众大规模运动,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是知识人心中的噩梦,因此他们对群众运动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五四运动之时,部分知识精英与民众脱节,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对于转向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置身事外。只有陈独秀、李大钊与少年中国学会的部分成员大力支持,由此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另有部分人加入改造后的国民党,逐渐取代知识精英,成为民众运动的领导者,使得二十世纪成为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尤其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摸索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所依靠的力量,正是20多年前义和团的主体。依靠并且掌握农民,是中国革命能够独树一帜并且取得成功的关键。
三
在正确认识义和团历史地位的基础上,需要认真检讨义和团研究的成败得失。革命高潮作为研究取向的退隐,除了本身耕耘较多、超越不易等因素之外,研究视野、态度和方法有所局限,无疑也是影响其难以有效推进的重要原因。以往的义和团研究主要有两方面局限:一是和太平天国研究类似,受历史研究整体环境的影响,过于集中在性质评价方面;二是由于农民的历史没有凭借,需要白手起家建构,因而着重于义和团自身的历史,而比较忽视相关方面的研究。
农民问题毕竟是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农民和农村的研究如何深入,值得高度关注。近代的农民问题更起到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作用。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一样,此前义和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也仅仅是拓荒,远远谈不上穷尽。而且和古代农民起义、农民政权的研究类似,研究近代农民革命的历史普遍存在认识偏差和取径过窄的问题,加上研究者资质不足,训练有限,总体上非但未能借助材料的大幅度增加而超越古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甚至尚未达到平均水准之上。几年前笔者曾写过民国史研究应该深耕细作的文章,今年又谈过辛亥革命应该精细化,其实整个近现代史都存在精细不够乃至不知如何精细化的问题。三大革命高潮虽然用力较多,相比于历史研究应有的细密严谨,仍然显得较为粗疏,尤其是受时代的影响,观念和视野难免偏窄,许多可以且应当研究的问题,或浅尝辄止,或熟视无睹。尽管如此,前人披荆斩棘、千辛万苦开拓出来的园地,已经令不少新进感觉难以下手。这说明近现代史的研究整体上仍处于刀耕火种的拓荒时代,研究方式相当粗放,尚未普遍进入深耕细作的阶段。
研究历史当然不能没有认识,但是正确的历史认识必须建立在弄清楚全部事实的基础之上。事实尚不清楚,微言大义难免主观臆断,再头头是道,也经不起材料和时间的检验。实际的情况往往是,正因为没有办法弄清楚各种事实及其联系,只能看到简单的表象,才不得不借助外力大谈所谓认识。由于材料繁多,史事复杂,如果只是简单地抽出一些论据,形成论点,视角不同的人各执一词,翻来覆去地争论,不仅无助于深入本题或接近真理,反而容易陷入意气用事,导致两极化,说好就夸上天,说坏就妖魔化,无法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而诸如此类的认识,大都是舶来的陈货或别科的常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与近代史学受西学影响转变之初,混淆社会发展史和一般历史大有关联。所谓弄清楚历史事实,就是通过比较不同的材料,一面努力近真,一面求得联系。在此过程中,恰如其分的历史认识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治近代史者,往往误以为弄清楚事实可以轻而易举,其实大谬不然。这里说的并非枝蔓细节,就近代史而言,许多重大问题连基本事实也有待进一步澄清。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历史教学、人员资质和训练、以及研究历史的目的等方面的混乱,不少专业人士并不具备弄清事实的能力。从一般通史或教科书获取的知识,与事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以此为据,研究问题,作出判断,自然难得一当。
具体而论,中国历来农民众多,可是农民从来不是史学研究的主体。研究农民,并非史学的老题目,而是新课题。英国史学家曾说,有人认为,要想写成农民的历史,除非伪造材料。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如今农民的确已经成为特定时期历史叙述的主体。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一度被冠以农民革命的名目,这一指称是否恰当,历来争议不少。不过,虽然革命退隐是世界性的趋向,与国内的沉寂相反,有的海外学人逆势而上,不仅继续研究,而且取得不俗的成效。如美国学者柯文、周锡瑞的义和团研究,就颇为学界所看重。太平天国的研究,海外学界从土客问题入手,深入发生之地的乡村社会,也有不俗的进展,至少展现了可取的方向。诸如此类的旧题新做,不仅有具体研究的贡献,更能锻炼、检验和展示研究的功力,值得继起者认真揣摩。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少数特定时期,革命是变态而非常态,目光仅仅聚焦于革命时期,要想普遍认识农民的常态化显然难以深入。在基层和乡村社会的研究渐入主流之前,历史研究中常态的研究对象实事上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非农民,真正以农民为主体的历史,主要就是农民战争史。农民战争史虽然问题不少,毕竟是前无古人以农民为历史的主体,其偏蔽在于,一是没有研究一般农民的历史,仅仅将非常时期、非常状态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二是由于第一点局限,作为重点研究的农民领袖,不是以一般农民为衡量,而是与其他群体的历史人物作比较。按照常理,应该首先研究不同地域的一般农民的日常,才有可能研究异常状态下一般农民的非常或反常,这样也能更好地理解群体性的农民。海内外学术界的进展,一方面建立在非常时期农民成为历史研究主体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等辅助学科,使得日常状态下农民的群体性部分得以展现。
农民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他方面。以往的研究在凸显农民形象的同时,对于其他方面的关注明显不足,许多争议即由于各取所需地采用史料史事而衍生出来。因此,纵横两面都要放宽视野:纵向时间要上溯下延,不能只看事件发生时的一小段;横向范围要旁及方方面面,不能就事论事。受原来农民无法入史的条件制约,以往的研究必须首先集中于义和团本身的活动,而对于清廷及各级官府、列强及其在华势力,以及同时期没有义和团的其他地区包括农民在内的一般民众,乃至义和团活动地区的非义和拳民众的历史,研究明显受限。与义和团相关的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西幸”时期的西安行在,涉及勤王、谈判、新政、回銮等多项事情,只知大而化之的概略;辛丑条约如何杀人诛心,引发士人对朝廷官府的不满,同样语焉不详;“八国联军”之称如何生成,结构怎样,京津之外如何分布,如何控制占领地区,也是悬而未决之事。
中国幅员辽阔,且分合不定,即使都是农村,东西南北仍有很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义和团发端的乡村地区,主要是北方的华北一带,平时散漫的农民能够聚众起事,发挥组织作用的一是源于萨满的教门,二是众多的民间结社。北方的教门与南方的会党,结构不同,系统各异,南北各地的民间结社,也各有分殊,义和团活动的区域性分布,与此紧密关联。当然,各地官府的应对存在差别,也会产生连带作用。清中叶白莲教被剿灭后,教门虽然分散,但并未消失,随时可能死灰复燃。义和团研究中,仅仅关注到连庄会之类的自卫习武组织,对于教门的研究因为有封建迷信等先入为主的成见,认识远远不够。
义和团与反洋教关系密切,以往对于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播的历史研究相当表浅,最近的二十多年,传教史的研究进展较为显著,可是传教史在宗教研究中处于边缘,而宗教研究又建立在欧洲中心的基础上。基督教的一元意识极为强烈。在所有文化系统中,基督教文化的排他性最强且最彻底。传教史研究或多或少受了文明等后设外衣的迷惑,对于基督教的本质及其传教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缺乏洞见,民教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以及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威胁,认识反而不及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美国的陈寅恪来得深刻。
在华北地区,天主教传播的时间相当长,早期即以河北等地为主要传教区域。尽管康熙、雍正时严厉禁止耶稣会传教,但是民间信教者依然暗地传布,许多教徒举家信仰,世代相传,绵延数百年。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对华北鞭长莫及,其暗中关注的社会势力,除西北军外,对知识界和天主教民,尤为重视。义和团研究虽然注意到“拳民”与“二毛子”的冲突,可是人数众多的一般教民如何自处,却少有涉及。
义和团的大规模事件牵动朝野中外,后来对涉事的农村有何深远影响,似乎只有个别事例。许多地方抗战时期就是根据地范围,但是根据地研究似乎很少联系到义和团。其实就时间而言还不到40年,一些当事人依然健在。相比于淮北红枪会的研究牵涉数百上千年,旁及社会各方面,义和团的研究显然太过拘泥。况且,如前引全面抗战期间中共中央的论断,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远不止华北和乡村,实际上制约了中国社会各界几代人对外关系的态度,而这方面的历史很少得到实证性的展现。
传统中国是四民社会,农民占多数,士绅居其首。用后来外在的观念认识士绅,产生不少误读错解。例如受日本的影响,依据所谓在地性分为城绅、乡绅。实则一般而言,除了社会地位不高、影响力不强的土地主外,多数士绅在乡村有土地,在城里有产业,居处也因人而异,很难一概而论定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以地主与农民的划分为准,双方严重对立,所以国民革命时国共两党在南方各省都要打倒土豪劣绅。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北方反而提出开明士绅。实际上普遍而言,北方的地主属性明显强于南方。
传统乡村社会中,士绅与农民的关系在宗族等血缘、地缘、姻缘纽带的作用下,形成利益共同体,存在鲜明的共生性。同时,士绅与官府的联系又十分紧密。在南北各地的各种反洋教事件中,士绅承上启下,起到重要的联接作用。而义和团的研究里,士绅似乎湮没于拳民汹汹涌动的浪潮之中,不见踪影。这样非同寻常的隐身怪象,究竟是士绅有心置身事外,还是研究者无意间视而不见,应该认真检讨。缺少士绅的角色作用,这一场席卷广大乡村都市乃至震惊世界的大动荡似乎变成官民直接联动,多少令人觉得有些异常。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义和团的研究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如果随手可以找出上百本专书的拓展空间,至少不能说是已经圆满充实,无从下手。如果看不到问题所在,理应反躬自省,千万不可一叶障目。后来者不要一味寻找前人未曾论及之处,以凿空蹈隙为创新超越,这样很容易将前人的唾余当成宝藏,非但无法超越,而且势必等而下之。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必须加强基本训练,掌握更多的辅助工具,在放眼读书的基础上重新研读基本材料,在整体关怀之下检讨基本问题,只要切实提高读书和研究的能力,放眼望去,有待研究的问题俯拾皆是,所谓学界共识或许不过是集体误判,老生常谈有时实为普遍迷失。按照历史和逻辑的顺序,梳理材料与问题前后左右地普遍联系,探究史事的发生及其衍化,则历史的本相和前人的本意都会自然呈现,整体改观也未必是天方夜谭。那时的义和团研究,或许有望渐入佳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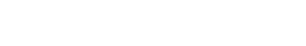
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23年第10期,注释从略;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