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资料是每一个年份都有的长时间序列资料,可帮助研究者较精确地了解较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变迁。美国哈佛大学所藏中国旧海关史料的公布与及时利用,相信会带来协助了解世界与近代中国关系的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近代中国旧海关资料之汇编,肇因于外国人接掌中国海关,之前并没有经常性汇编、出版的海关资料。外国人之所以接掌中国海关,起因是1853年小刀会之乱骚扰、破坏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上海的海关,使得该海关无法照常课税。满清政府方面,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急需此项关税以应军需。英、美、法方面,自从1842年中西贸易推展以来,碍于语言、文化方面的隔阂,外商感到诸多不便,也希望有所改革。又因《南京条约》曾规定英国可以派遣海关税务司监督中国海关以确保关税之征课,中外双方遂同意改由外国税务司监督中国海关税收。此项安排在1858年《中英、中美、中法通商章程》第十条之中纳入规章。次年起,即有海关出版品发行。出版文字以英文为主, 中文为辅。
近代旧海关资料有逐年的贸易统计、报告,1882至1931年间每十年又推出十年报告。每期报告以各关为单位,综述各关在十年之内司法、军事、贸易、财政、金融、交通、农业、矿业、工业、教育、文化、移民、饥荒、病灾等之一般情形。1864至1927年间有针对鸦片、 丝、大豆、中药、乐器、田赋、中国若干地区的发展等特别报告。1868至1947年间有关于灯塔、关税税则、度量衡等的杂项报告。1875至1948年间出版有海关通令。1876至1896年间的公署报告除人事资料之外,又有银两、常关税、厘金等资料,1861至1948年间出版有职员录,1880至 1940年间出版有税务司报告、电报密码、海关处理国际借款等资料。1974年至今,笔者个人研究利用较多的是历年与每十年的贸易统计与报告、鸦片方面的特别报告及海关医报。

1873年通帆船的沿海港口,来自淡水1873年年报。
1974年起利用旧海关资料
1974 年笔者开始利用旧海关资料,是为了撰写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的硕士论文。此前一年,笔者准备撰写清代台湾士绅功能分析的硕士论文。受张仲礼的《19世纪中国绅士研究》与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影响,笔者准备由中国大陆移到台湾做类似的研究。当时运用的资料以地方志和官书、族谱、文集为主,科考中举者为关注焦点。但因台湾样本太小,统计结果解释力不大,题目需再加更动,所以拟缩小题目,只写台湾中部的雾峰林家。在研究雾峰林家历史的过程中,笔者留意到樟脑业在台湾历史中的重要性。为追寻台湾樟脑贸易的资料,笔者于“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发现若干年份台湾海关报告的日译本。继而联想到刘翠溶教授某一次演讲中提及海关报告,她使用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资料。在试图找寻更完整的海关资料原本时,由刘处得知近史所藏有海关资料微卷。这些微卷是余秉权主持的中国资料中心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制作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主要是由海关美籍税务司马士(H. B. Morse)捐赠。读过海关资料微卷之后,发现这批资料对笔者的论文帮助极大。因为海关资料是每一个年份都有的长时间序列资料,可帮助研究者较精确地了解较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变迁。
又因为海关资料是以依据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为单元编排,此时笔者联想起Ramon H. Myers与Evelyn S. Rawski的论著,前者讨论晚清开港对于河北、山东的冲击,后者讨论晚清开港对两湖地区特别是湖南的影响。笔者硕士论文的主题因而调整为晚清淡水、打狗开港对台湾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论文题目最后具化为《茶、糖、樟脑业与清末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茶、糖、樟脑业是台湾开港后最大的三项出口产业。
这项研究在利用海关资料时,结合了若干经济理论,如市场结构分析、技术创新分析;在社会变迁方面触及自然环境、区域、族群与阶层等人类学关怀。由于海关资料直接涉及国际贸易,这使笔者在何炳棣、张仲礼以传统科举为基础的社会流动外,还观察到因为国际贸易牵动的更大的社会秩序的变化。1887年以前,台湾的行政中心一直在台南,之后则一直在台北,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一转折?笔者1978年初版、1997年由联经增订出版的《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一书中,由1860年台湾依《天津条约》规定对全球开放贸易开始,论述此一转折的经济背景:相对南台湾蔗糖出口的疲软,北台湾茶、樟脑业的兴起及大量出口是重要原因。因为茶、樟脑贸易所得的利润,就近支持了将台湾行政中心北移的刘铭传的建设。台湾开展对外贸易以后,大陆资本及外国资本还造成本土资本的兴起,产茶与樟脑的山区城镇崛兴,靠山居住的客家人与漳州人相对靠海居住的泉州人改善了其经济条件。这个研究成果是笔者得以在“中研院”取得研究专职的重要基础。及后另有以海关资料为基础探讨与全球史与中国史有关联的几项研究。
其他以中国旧海关资料为基础的研究
相对于台湾经济重心在清末的北移,中国大陆的经济重心在唐宋以后南移,富庶的沿江及沿海地区在《南京条约》之后纷纷开放国际贸易,其与贫困的内陆地区的关系,是更加融合还是更加分离?2005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的《日本、中国以及亚洲的国际经济增长,1850-1949 》(Japan, 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49 )收入笔者“China’s ‘Dual Econom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1842-1949”一文,分五个阶段描述两区的经济关系。文中强调: 穷区生产富区所需的高价商品,极有助于两区的整合。今年8月这篇文章将会在南开大学出版的《吴承明先生纪念集》中刊出。这篇文章有两项重要基础,其一为笔者个人以海关资料为重要史料来源的晚清土产鸦片研究,其二为在《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一书出版后,台湾出现了10余个以海关资料为重要史料,分别针对近代中国10余个条约港的口岸贸易与腹地变迁的研究。
海关资料记录了不同等级的鸦片价格及流通路线。2006年笔者在台湾、日本出版的《晚清土产鸦片的运销市场》中提到不同等级的本国鸦片跨越区间边界,流通到不同的所得者手中。这是针对商品的一种社会史分析: 商品流通,不单只依循经济逻辑,如交通成本;也会照顾社会逻辑,如传统中国社会阶层区分并没有像传统欧洲或日本一般严明,低所得者仿效高所得者消费行为的情况更加显著。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商业资讯仍可穿透区域疆界,达到全国性串连的效果。
2014 年我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上发表了论文《晚清对土产鸦片的观念》(“Late Qing Perceptions of Native Opium”),其中指出禁烟名臣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前6年的1833年,曾主张对土产鸦片弛禁,以减少白银外流。之后直至1906年,中国开始实施十年的渐禁鸦片政策期间,清朝有关土产鸦片的讨论中,经济因素(包括国际收支的平衡、税收的掌握)一直凌驾于国民健康之上(无论鸦片是药还是毒),居于优先考量地位。鸦片由医药转为毒物的观念在西方于1870年代逐渐兴起,一直到19、20世纪之交,方才深入人心。1874至1906年间,“鸦片是毒品”多于 “鸦片是药物”的观念虽然增强,但因为经济方面对鸦片有非常大的依赖,又有本国持有鸦片才能自主禁绝这样的理由,导致了本国供应更多鸦片。
有关清末中国对鸦片在财经方面之依赖,笔者1979年在台湾出版、2016年8月经修订将由上海的《国家航海》出版的《晚清的鸦片税,1858-1906》论文,主要利用海关资料重建 1858至1906年间的鸦片税制。此文指出其课征沿革、种类、性质及与各级政府间的关系,也指出鸦片税在晚清全国与各地财政中的地位,以及其在平衡区间财政盈亏中所发挥的作用。文中也利用进口鸦片需求的价格弹性,指出因为鸦片上税而导致的价格上涨,对鸦片消费总额的影响不大。在对鸦片吸食人口与鸦片消费额作出估算之后,文中指出: 清政府的鸦片税征课政策虽增加了岁入,以此协助政权的维系,并且由于本国、外国鸦片税率的差距,也有助于本国鸦片逐渐取代外国鸦片,从而减少中国的漏卮,但整体而言,这项政策还是延缓了中国的经济成长。
2011年笔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银线》一书, 焦点放在19世纪前期的“银贵钱贱”现象及其与全球银供应的关联。中国对银的需求量大,而本身产量不足,主要仰赖海外输入,外国以银与中国换取商品,再输往其他地区获利。由于西方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高于中国对洋货的需求,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是银流入区,而非外流地。但此情况到19世纪前期发生转变,世界主要银产区拉丁美洲在1820至1830年代进入独立战争时期,各地纷纷脱离殖民母国建立独立政权,政治纷扰影响到银输出,使得世界市场对银的需求高于供给量,产生了银荒现象。全球性银荒,刺激了鸦片向中国进口数量的提高,以此吸取中国的白银,同时弱化英美等国对中国茶丝等出口品的购买力,故此时不但没有大量的银流汇入,反而是中国的银大量向世界外流,造成“银贵钱贱”问题。相对于作为政府收支及大规模远程交易媒介的白银主要由民间商人在国际贸易中换取,作为小规模及近程交易媒介的铜钱虽主要由政府铸造,但采铜、运铜、铸造铜钱都需要用银,在白银外流的情况下,使得铸造铜钱的成本提高。在白银减少导致白银相对铜钱价格节节上升的情况下,铜钱需求亦减少——铜钱不是如以往学者所说供应增加,反而是减少了。在银钱供应双双减少的情况下,货币供不满足社会所需,社会便发生萧条与失业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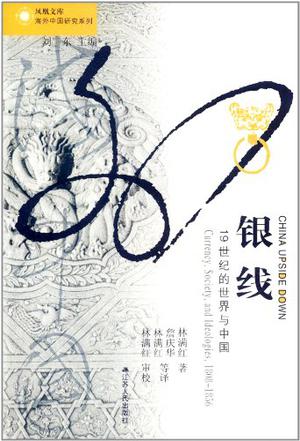
朝廷税收以银两为主,在银缺乏的状况下,清政府财税收入短少,导致国家机器更难运转,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之后三年,朝廷已发不出官吏与军队的薪饷。帝国面临的灭亡危机因1856年(清咸丰六年)后墨西哥“鹰洋”大量输入而扭转。世界金银供应大增,中国的出口贸易转为顺畅,虽然鸦片也同时增加进口,但顺差扩大,白银反而回流,导致商业税收增加,弥补了朝廷的财政缺口。清廷财政状况好转后,可以应付大量的军事开销,接连平定太平军、捻军及西北的回变,从而使帝国的危机得以暂缓。清廷规定1000个铜钱兑换一两白银,但市面上则是约2000铜钱换一两银,这一现实对支持“绝对君权”的思想是一大挑战,对支援“有限君权”的思想,则提供了一大发展空间。主张“有限君权”的今文学派经过1600年的沉寂之后,于19世纪上半叶显著昂扬。
在知识精英的议论转为朝廷政策论辩的过程中,清朝有关货币政策的形成过程绝非中央集权。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来,“中国皇权自宋元以后日趋专制,到清朝时登峰造极”的论点广为学界接受,而历史教科书也是如此书写,成为一般大众对中国帝制时代,特别是明清时代的既定印象。将这种印象套在清廷应付“银贵钱贱”问题的决策过程,会使人以为这事是由负责经济的户部主导,经皇帝批准下令后正式成为国政,但事实并非如此。清廷在处理此项议题时,不单只是户部,地方及中央二品以上官员,甚至礼部、刑部、监察御史等官员皆可加入讨论。
另一方面,依赖拉丁美洲白银的中国在咸同年间忙于平定内乱,不用依赖拉丁美洲白银的日本则走向明治维新,欧美各国因为没有类似中国的银钱两币制,且有现代银行体系作支持,比中国更早获得拉丁美洲恢复生产的白银,再次说明了中国在经过19世纪上半叶货币危机后国际地位的滑落。以往讨论清代中国的由盛转衰,论者十分强调清王朝本身的腐败或者是中国相对西方军事力量的薄弱。《银线》一书描绘了清朝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紧缩及银贵钱贱危机对它由盛转衰产生的重要影响,也讨论中国有关国家与市场乃至社会关系的思潮起伏。此书论证的关键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收支变化,如果没有海关资料在手,则无从刻画箇中情形。
1979 年在台湾出版,2014年经修订收录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中的地方”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的《银价贬值与清末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1874-1911)》一文,指出清末本国货币对外汇率的长期下跌趋势下,中国曾在1874至1887年间促进若干出口及进口替代,但并没有办法扭转这一期间贸易收支恶化的现象。造成国际贸易收支剩余减少继而恶化的,是进出口量对进出口价的价格需求弹性小。原因之一是清末使用银铜复币制,银两或银元虽然是国际贸易的交易媒介,但进出口的零售、零买则以铜钱为交易媒介。所以银两(元)对金币贬值对进出口量的影响尚需透过银两与铜钱的关系而运作。而在1874至1911年间,铜对金贬值的影响幅度较银对金贬值的影响幅度小,对外汇率下跌之后,以铜表示的进出口价波动幅度较以银表示的小,导致进出口量随银贬值而变化的幅度减少。原因之二是进口货占国民消费总值的比率低,故进口货价格虽变动,国民消费总值变动的幅度不大,因此随着进口商品价格涨跌而减增的这些进口商品的消费的数量亦小。原因之三则为出口货在生产以前即有先行贷款的期货买卖行为,致使出口现货失去价格弹性。
就 1874至1887年的贸易收支顺差而言,1887年以前虽然出口量增长率小于进口量增长率,但出口价增长率却大于进口价增长率,贸易对手国物价低迷与所得增加是为要因。造成1887至1911年中国贸易收支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出口量增长率仍大于进口量增长率,但以银计算的进口货价格的增幅大于出口货价格的增幅,而且前者相对增幅较大,在这一过程中,汇率下降与贸易条件的恶化固然有所关联,但国外货品进口价格的显著上涨,则是相对1887年以前的不同变化。这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发展迈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工资及其他产销成本由持平转为上涨。出口货价格因国内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略微发展、粮食的出口、粮食因经济作物栽植而减产及大量代用货币的发行等而上扬。但因1895年以后,出口货的国际市场更趋竞争激烈,其以金表示的价格增长率远低于进口品价格增长率,导致了贸易收支恶化。国际汇率的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可能影响,仍是当前国际金融的重要课题,以旧海关资料为基础而进行的历史回顾,仍可提供当前借鉴。
学术基础工程与学术研究
在没有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海关资料微卷以前,笔者撰写的硕士论文,因为只凭地方志、族谱、清代官吏的文集、口述资料及一些日文资料,看来不够扎实,曾一度想放弃完成学位。硕士论文写成之后,受到学界的肯定,最大因素就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海关资料微卷。
根据张存武教授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发表的《中国海关出版品简介(1859-1949)》,张教授是在接受福特基金补助前往哈佛研究期间,留意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海关材料。其接受福特基金事,由“中研院”近史所1985年出版的该所《大事纪要》第46页可知是发生在1964年。根据张存武教授前引文,这些微卷是在王树槐教授代理近史所所务期间由福特基金会赞助购置。根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第9页,王树槐系于 1970至1971年间代理所务。与海关报告一样亦是每一年都有的资料,在笔者的研究中也运用甚多的是《英国领事商务报告》(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ommercial Reports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这是由近史所黄嘉谟教授所征集,根据同上《大事纪要》第67页,黄嘉谟教授于1969年接受福特基金补助前往英国,而近史所图书馆清楚纪录该书是于1973年3月购入的。笔者开始利用近史所这些资料是1974年的事,没有近史所在笔者利用资料前夕的学术垫底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笔者往后的学术生命,而这批资料也深刻地影响笔者往后从世界角度去研究近代中国的学术视角。
1974 年笔者去请教刘翠溶教授有关海关资料的事时,刘教授告诉笔者近史所藏有海关资料微卷,但因为微卷阅读机设备老旧,用起来既不方便,又伤眼力,她劝笔者最好不去使用。1974年在我的研究一再触礁时刚巧碰到海关资料,即便当时阅读的是不能影印的微卷,加之微卷阅读机的屏幕影像极为模糊,但这都改变了我的一生。目前有纸本可资利用,与这套资料可以并用的资料库、计算与制图软件都很精进。美国哈佛大学所藏中国旧海关史料的公布与及时利用,相信会带来协助了解世界与近代中国关系的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而在世界与中国关系日趋密切的今天,亦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载于7月22日的《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