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清朝与朝鲜的咨文往来与交涉
丁晨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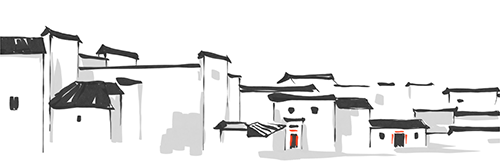
摘 要:皇太极提出的“毋违明国旧例”原则贯穿了17世纪清朝与朝鲜咨文往来与交涉的全过程。但清初并没有全盘照搬明制,并非由礼部而是由户部主导对朝咨文交涉。顺治帝亲政后,对朝咨文处理模式开始转换为明朝时旧例——由礼部主导。这说明清朝对明制的接受与继承过程是曲折的,是经过改造的。清朝展示出符合宗主国身份的姿态,在涉朝事务上采用“明国旧例”,而朝鲜亦在同样的原则下进行回应,这也是清鲜封贡关系得以稳定运行二百余年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清鲜关系;朝鲜王朝;咨文往来;明国旧例;盛京礼部
“丙子之役”结束后的崇德二年(1637)春,清朝正式将朝鲜纳入自身为中心的封贡体制,从此清朝与朝鲜开始在君臣关系的框架内展开双边交涉。按皇太极最初的构想,朝鲜的一应文移均应奉大清国为正朔,公文与礼仪往来亦需“毋违明国旧例”。但新建立的清鲜封贡关系并不是对明鲜封贡关系的简单继承。有学者指出:“清朝使用的通常被称为‘明模式’的制度在形式与功能上并不是一种照搬的制度,而是在建立国家的努力中借鉴类似的工具来满足不同的需要。”虽然皇太极强调“毋违明国旧例”,并认为这是处理对朝交涉的有效方式,但此时清朝所处的文化、政治、军事环境与明朝不同,与朝鲜新建立的封贡关系也需要一定时间加以磨合。换言之,将该原则落实到双边交涉中并非一件简单易行之事。
在当时的东亚世界,国与国间的交涉主要通过外交文书来进行,通过外交文书来了解对方意图,再借助文书表达处理意见是最主要的往来方式。清朝与朝鲜亦大致遵循这一方式。朝鲜向清朝递交的外交文书有表文、奏文、咨文、申文、方物单子等多种,其中在处理具体事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文书是咨文。在清鲜封贡关系框架内,清朝六部等官衙与朝鲜国王之间多以咨文来交换信息,从而处理两国间的具体事务。咨文往来正是双边交涉实情的写照。探究双方咨文往来情况的变化,可以有效追踪“毋违明国旧例”的原则如何贯彻到实际交涉中。
针对清朝与朝鲜间的咨文往来问题,既有研究分析了咨文格式;注意到了崇德年间户部、礼部并行处理朝鲜事务,户部有权介入甚至主导涉朝咨文的格局;讨论了18世纪上半叶,盛京礼部开始介入与朝鲜交涉,并逐步发挥作用的历史过程;整理了18世纪晚期双边往返的咨文;探讨了有清一代,朝鲜以咨文形式报告的日本情势,即所谓“倭情咨文”的内容。亦有学者探讨了清朝入关前,朝鲜国王上呈清朝的表、笺等礼仪文书中的用词、抬格体例等,并认为这些“都沿袭自对明朝皇帝的规范,直接在文书体系方面促进了清方宗藩政治话语的成熟”。但咨文与礼仪文书不同,咨文因涉及具体事务,在处理时可能涉及多个衙门,并不像礼仪文书一样多由礼部接收处理,其处理流程也远较礼仪文书复杂。本文将参考既有研究,爬梳域内与域外史料,论述清鲜双方咨文往来模式成立并逐步规范化的17世纪情况,同时聚焦经办咨文的衙门、人物的关联与互动,从而勾勒出不同时期的双边关系的发展特点,并从咨文往来的历史变迁来理解双边关系的演变。
一、清朝入关前与朝鲜的
咨文往来与交涉
所谓咨文,即“二品以上官,行同品衙门之文”。明朝继承了元朝以中书省名义使用咨文就具体事务知会高丽国王的惯例,也曾在明初时以中书省名义移咨高丽恭愍王。朝鲜王朝建立后,朝鲜国王的等级大体相当于明朝的正二品,与明朝礼部等六部级别一致。明朝与朝鲜咨文往来的旧例如下:首先,礼部是负责发送咨文给朝鲜国王的主要中央机构,嘉靖元年(1522)因朝鲜谢恩使姜澂的奏请,明廷同意若有庆事,辽东都司(正二品)可移咨朝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礼部报辽东、辽东报朝鲜国王的惯例。其次,15世纪至16世纪前期,朝鲜使臣并非通过礼部,而是将咨文等文书递交鸿胪寺,再由鸿胪寺进呈御前。因礼部尚书夏言的奏请,从嘉靖十三年开始,朝鲜的咨文等文书必须递交礼部,再由礼部转奏皇帝。也就是说明朝与朝鲜之间存在发送方与接收方均为正二品衙门,即“礼部—朝鲜国王”与“礼部—辽东都司—朝鲜国王”这两条咨文往来途径。
该咨文往来模式一直延续至16世纪末壬辰战争时期。由于战争这一特殊历史背景,该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万历二十四年(1596)出现了所谓“朝鲜国王书奉天朝石太师门下”的伪书传播事件,朝鲜国王宣祖移咨礼部解释此事,对双边咨文往来模式有如下描述:
当职为照小邦凡有事情,或报或请,须用文书,其在封疆之上,则只得于辽东都司;其有使价前赴京师,则只得于贵部有移咨之例。虽事系他衙门者,必关由转行。惟自军兴以来,缘事机迫切于兵部及行部等衙门,不得必须转报转请然,且依式样修咨而已。今乃不因使价之行,直发一走,遥奉书帖于本兵大臣,则揆之事体事理,宁有是乎?当职实不敢知何等诈妄人,撰出一件文字,暗投兵部,至于流播……右咨礼部。万历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按上文所言,第一,朝鲜与辽东都司存在咨文往来事例;第二,朝鲜遣使赴北京时,只向礼部递交咨文,若事情涉及其他衙门,由礼部转为行文;第三,战争爆发以来,朝鲜无需礼部转报,开始与兵部等衙门直接咨文往来,且咨文格式与递交礼部的咨文一致;第四,朝鲜国王不可能不经由使团而直接与明朝兵部尚书书信往来。以上模式在壬辰战争结束后继续维持,朝鲜依然可以就军情事务直接移咨兵部。要言之,在明朝末年,朝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直接移咨辽东都司、兵部,但礼部在与朝鲜的咨文往来中仍发挥主导作用。
然而在清鲜封贡关系建立后的崇德年间,清朝与朝鲜的双边咨文往来并未按明末的模式进行。当时清朝负责与朝鲜交涉的并非全是礼部官员,户部承政英俄尔岱与马福塔也长期介入其中。此二人曾多次出使过朝鲜,分别被朝鲜人称为龙骨大或龙胡、马夫达或马胡。此外英俄尔岱的心腹、崇德年间任内国史院副理事官的郑命寿(古尔马浑)也在与朝鲜交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一结构下,形成了朝鲜就礼仪等事务咨礼部,逃人与向化人刷还、双边互市等事咨户部,倭寇、军情等事咨兵部,而由越境采参衍生的犯罪问题咨刑部的咨文往来模式。但在朝鲜看来,英俄尔岱等人负责的户部才是其中最重要的衙门,世子侍讲院的官员们在发回本国的状启中明确提到:“各项等事,大则移咨于该部(即户部),小则令备局移文于臣等,以为酬答之地。”原因在于,“两将自初往来定约之人,世子教来此之后,大小之事,专主周旋”。而且“龙、马两将,盖皇帝信任之人,而诸臣亦无出其右者矣”。即户部并非因为六部的职权划分,而是依靠英俄尔岱等人的对朝交涉经验与皇帝的信任而得以成为主导衙门。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移咨清朝时,自然无法按明朝时旧例进行,只能做出相应调整
但户部的崛起亦可能触犯其他衙门的利益,尤其是本应主导处理朝鲜事务的礼部。崇德三年礼部承政满达尔汉(满月介)曾私下派人向世子侍讲院右副宾客朴嶇带话如下:
满月介使清译河士男密通于臣曰:我自初往来朝鲜,情意甚亲……今职在礼部,事系朝鲜,则亦竭力周旋,世子所请,力虽不及而无不曲从为乎矣。朝鲜只知有龙、马两人,而独于吾一不记问,使人大惭,朴侍郎亦不知之耶?今番药材觅来人出送事段,龙将塞之,而吾力图出送,可于此知之……前日龙、马处果物入送事乙,满也必知之,而于渠处,则我国曾无一番表情之事,宜乎有此言也。
满达尔汉对朝鲜只知有户部承政英俄尔岱与马福塔,并加意馈送此二人的行为非常不满。究其原因,是户部职能的扩张影响了礼部的职能履行与官员个利益。又如同年发生的清朝停止供给沈馆,要求昭显世子及其随从自行解决饮食供给问题的事例,尽管满达尔汉欲为通融,但最终执行的是英俄尔岱等人提出的停止供给的主张。可见当时礼部在对朝交涉中的影响力仍难以与户部抗衡,而朝鲜也很清楚户部与礼部的影响力差距。
崇德时期清朝对朝鲜咨文处理还具有以下若干特征。首先,在咨文的传递流程中,户部凌驾于礼部、兵部等部之上。从朝鲜因不同事务而移咨不同衙门的模式来看,咨文本应由相关衙门递交内秘书院拟定回咨,但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多次出现由户部转递内秘书院的情况。如崇德三年,朝鲜国王因派兵迟误而向清朝兵部移咨辩解,却是户部派人将原咨送至内秘书院。又如崇德四年,朝鲜因边境居民杀害厚罗岛人而移咨礼部,该咨文亦由英俄尔岱派人送至内秘书院。内秘书院撰写完回咨后,亦由户部转发朝鲜。如崇德四年内秘书院替兵部撰写要求朝鲜国王派兵攻打加哈禅(即庆河昌)等人的回咨,加盖兵部印章,再由内秘书院派人送至户部英俄尔岱处转发朝鲜。由此可见,户部在清朝各衙门间的咨文传递流程中扮演了中枢角色。可以推知,户部可以因这样的角色而及时获见朝鲜咨文的内容,从而在与礼部等部的竞争中占据信息优势地位。
其次,虽然户部主导对朝交涉,但在撰写涉朝咨文与拟定处理意见时,在内秘书院之外仍需多个衙门配合。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由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组成,其中内秘书院掌“撰与外国往来书札”。从咨文处理流程上来看,朝鲜递交的咨文到达户部等衙门后,首先需递交内秘书院译为满文,原咨与译文再发回原衙门处理。而朝鲜咨文并非仅原接收衙门与内秘书院的官员可见,在上奏皇太极之前,相关衙门的官员会对内容进行筛选。如崇德三年,清朝要求朝鲜出兵助力征明,但朝鲜不愿派兵,因而在递交礼部的咨文中多有推脱。于是“范文程,龙,马两将,皮波博士、加利博士、卢时博士、虎皮博士、甫大及不知名并十人,以皇帝命来到世子前,仍招使臣及内官使之参听为白谴。出示我国陈奏咨文及敕书草一本,曰:此咨文甚为不似,不敢奏达,只以言语陈之矣”。此处出现的清朝官员,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龙马两将为户部承政与参政,皮波博士即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加利博士即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卢时博士即内国史院学士罗硕,虎皮博士即内弘文院学士胡丘,甫大即户部启心郎布丹扁俄。即尽管该咨文的接收方是礼部,但在处理过程中,英俄尔岱等户部官员与内三院的大学士等多位学士均有介入,并由他们决定是否上奏皇太极。同样地,如果内三院的大学士们判断咨文内容应该上奏,亦会通过口奏的形式以获得皇太极的意见再拟定文稿。由此可见,并非所有咨文都会奏报皇太极,户部等部与内三院在处理朝鲜事务时拥有一定的决策操作空间。此外在崇德初期,内秘书院撰写完“与外国往来书札”后,大学士并无权力定稿,还需经由皇太极审阅。但到崇德后期,皇太极信任倚重范文程,不再审阅文书草稿。要言之,户部在处理涉朝咨文时需要内三院进行配合,其中并非仅需与负责撰写涉外文书的内秘书院,而是与整个内三院合作。
最后,崇德初期的清朝并不十分清楚咨文的使用等级与范围,文书使用上曾出现混用情形。按明朝时旧例,清朝六部与朝鲜国王才是平级,而咨文是清朝“高级衙门之间相互行文时使用的平行文种”,也就是说咨文应该用于六部与朝鲜国王之间。但在崇德二年,清朝兵部直接移咨朝鲜义州,要求义州将攻打椵岛所得的兵器与火药等物转运凤凰城。义州的最高长官——义州府尹仅是朝鲜的从二品官员,显然不应是兵部移咨的对象。然而到了次年,内秘书院再代兵部就明朝兵船出没事件撰写文书时,移咨的对象就变成了朝鲜国王,至于朝鲜的地方官——义州兵使、安州兵使、平安道观察使等人,则以下行文书牌文发送。由此可见清朝对咨文等文书的认识与使用也存在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而清朝衙门以牌文发送朝鲜地方官之举,亦可被视为对“明国旧例”的继承。壬辰战争爆发后明朝将官常以牌文与朝鲜官员沟通,在16世纪晚期业已形成惯例。
需要补充的是,部分清朝官员在明面流程之外发挥的个人作用亦不容小觑。首先是英俄尔岱。朝鲜需要告知或求请的内容能否顺利奏达皇太极,英俄尔岱是极为关键一环。朝鲜右议政申景禛认为:“与皇帝相面,则容或有通情之路,龙将操弄于中间,欲以为自己之功,故其意所好则通之,所恶则不得通矣。”再次是郑命寿。他活跃在崇德年间清鲜双方几乎所有的交涉事务中,从朝鲜的立场来看,他虽然贪婪,但亦“周旋之力居多”。最后是希福。希福娶有朝鲜宗室怀恩君之女,常私下与昭显世子侍讲院的官员们往来,并透露消息。他曾提醒朝鲜在奏请世子册封时“只陈册封之意而已,切不可并及请还世子之语”,而他“主管内事,亦当从中致力矣”。郑雷卿案爆发时,他亦私下嘱咐朝鲜在撰写咨文时“若或有一语营救之端,则定无可生之道”。这些人物或消极或积极影响了清朝与朝鲜的交涉。
总之,在入关之前,清朝与朝鲜的咨文往来与交涉并未严格按照“毋违明国旧例”的原则进行。由于英俄尔岱等人处理朝鲜事务的经验与皇太极的倚重,户部在与朝鲜的咨文往来与交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与明朝礼部发挥主导作用的模式形成鲜明对照。
二、清朝入关后与朝鲜
咨文往来模式的变化
顺治元年(1644),清朝下令提高礼部在对朝文书交涉中的地位,“议准朝鲜一应事宜,不许越奏御前。叙功等事申吏部;地亩、仓库、钱粮等事申户部;朝贺、贡献、婚娶等事申礼部;军务、逃盗等事申兵部;辞讼、告首等事申刑部;修理城池、边关等事申工部;其应申各部之文均礼部转发”。按此规定,清朝礼部被赋予了明朝礼部类似的职能,在咨文传递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但该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按韩国学者金昌洙的研究,顺治帝即位后虽下令与朝鲜交涉均由北京礼部单一负责,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清朝中央各部仍然按入关前惯例直接向朝鲜发送咨文等外交文书。实际上在顺治初年,颇受摄政王多尔衮宠信的英俄尔岱仍活跃在对朝交涉中,其负责的户部依然在对朝咨文往来与交涉中扮演主导角色,这应是上述规定无法落实的重要原因。顺治五年英俄尔岱死亡,此后多尔衮与英俄尔岱的属人郑命寿的关系迅速接近,郑命寿继英俄尔岱之后,秉承多尔衮之意积极介入朝鲜事务。换言之,该时期清朝负责处理对朝交涉的官员依然是崇德年间的旧人,尽管成文规定发生变更,但在实际交涉中仍然遵循崇德年间的旧例。
关于清朝入关后,与朝鲜咨文往来模式发生转折的具体时间点问题,朝鲜后期学者丁若镛(1762—1836)曾有论述,按他的说法,郑命寿正式失势发生在顺治十年,从次年即顺治十一年起,朝鲜“一应事务皆咨于礼部,其有应申各衙门者,皆由礼部转发”。因而在他看来,“有事而报于礼部,冀其转达曰咨”。从朝鲜的角度来看,情况的确如此。从顺治十一年起,朝鲜开始遵循有事移咨礼部的模式,即恢复壬辰战争前的明朝旧例。如顺治十二年,朝鲜不再像之前一样将“倭情咨文”移咨兵部,而是移咨礼部,礼部再将此咨文转发其他衙门。但从清朝的角度来看,变化早在数年前就已发生。顺治七年底多尔衮去世,其亲信郑命寿的权势顿减。在顺治帝亲政体制下,户部主导对朝咨文往来与交涉的格局随即发生转变。参考顺治七年的事例,多尔衮令“例贸桦皮,着令永止”,于是朝鲜按惯例“咨谢户部”。又该年多尔衮同意朝鲜的请求,允许将贡布折算成大米或小米进贡,此事由户部移咨朝鲜,而朝鲜亦回咨户部。但到了多尔衮死后的顺治九年,朝鲜因原本准备进贡的柚柑烂坏较多,只得以生梨替代,因而将缘由咨报户部。然而并非户部而是礼部奉“以后免进”的旨意回咨朝鲜。可见礼部逐步取代户部,在对朝交涉中的地位得到提高。这一变化与清朝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紧密相关。顺治八、九年间,顺治帝完成了八旗的改组,并结束了诸王贝勒掌管部院的情况,皇权对八旗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下,多尔衮的亲信属人不再可能通过把持户部从而主导对朝交涉,这样一来,清朝对朝咨文往来才有可能延续明朝时由礼部主导的惯例。另外,顺治朝的内三院并不受理部院题奏,由六部直接呈奏皇帝领旨。奏事完毕后,携带本章回部拟旨,再送至内三院。在这样的公文处理流程框架下,对朝咨文的拟定亦受到影响。与入关前由内秘书院等内三院参与拟定户部、礼部等衙门的对朝回咨不同,该时期不再由内三院代撰户部、礼部等衙门的对朝回咨。
在17世纪中后期,刑部与兵部仍会就分管事务移咨朝鲜,尽管频度极低。如顺治十四年,朝鲜收到义州府尹上送的清朝刑部咨文,内容是减免朝鲜焰焇犯禁人员的处罚,朝鲜因而打算派遣译官将回咨送去北京。数日后,朝鲜又收到回还使臣带回的针对同一事件的礼部咨文,领议政郑太和因而建议根据礼部咨文来撰写谢恩表文。再如康熙七年(1668),朝鲜收到兵部咨文,文中要求朝鲜将清朝漂流船上的两门火炮送至清朝。但这些仅是个案,进入18世纪后,罕见兵部与刑部直接移咨朝鲜的事例,即礼部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导对朝咨文往来的衙门。顺治帝亲政后,清朝诸衙门处理涉朝事务并移咨朝鲜的具体流程,可见顺治十八年四月十二日的《礼部发回越境投充人咨》,咨文内容如下:
礼部为公务事。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开,镇守盛京总管吴库礼等据凤凰城住章京阿尔珠称朝鲜国人一名投充到凤凰城,及问缘由,口称我属义州人,因我叔不疼养,不爱惜,闻上国养育得善,因此投来等因。到部,凡朝鲜国事务皆隶礼部,并原文移送。到部,该臣等议得移文盛京总管,将投充之人送义州地方官收管,仍咨朝鲜国王可也等因。顺治十八年四月初八日题,本日奉旨是,钦此。到部送司,奉此,相应知会。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合咨贵国,烦为查照本部题奉旨内事理钦遵施行云云。顺治十八年四月十二日。
上述事件的起因是清朝凤凰城城守尉(正三品)发现一名朝鲜义州人投充到凤凰城,于是上报镇守盛京总管,盛京总管(正二品)再将此事报给兵部。涉及犯越国境问题,兵部本有权介入,但因“凡朝鲜国事务皆隶礼部”之由,而将此事并原文移送礼部。礼部拟出处理意见后,题请皇帝,得到批准后,再移咨朝鲜国王。综合以上流程来看,尽管犯越事件发生在盛京总管与凤凰城城守尉所管区域,但他们均无权与朝鲜移咨往来,拥有对朝事务拟议权与移咨资格的为礼部。礼部在顺治末年处理涉朝事务中的权限扩张由此可见一斑,这与崇德年间户部掌握对朝交涉主导权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咨文的传递方式在清朝入关后也发生了改变。入关之前,清朝或采取使臣顺付的方式,即让朝鲜使臣将咨文带回;若有急事,清朝会通知沈馆派遣善于骑马之人领走文书飞驰朝鲜。至于专门负责传递咨文的所谓朝鲜“赍咨行”使臣人选,此时清朝并没有同意朝鲜按明朝旧例派遣译官为赍咨使,而是提出了特殊要求。按《沈阳状启》的记载,内官朴之荣“赍来咨文段,朝廷分付内臣等处传给,使之呈纳是如为白乎矣……所以必定内官者,清人等以为外廷之臣不从国王之命,且不直辞以告,内官则必无此患云云为白卧乎所。其言虽是无礼无伦,清国不信我国之心,则类如此为白齐”。即清朝不信任朝鲜外廷的文官,要求派遣内廷的宦官充当赍咨使,而这一要求在入关后不复执行。正如上文所述,顺治十四年朝鲜收到刑部咨文后,计划派遣译官赍回咨赴北京。18世纪初期刊行的记录朝鲜司译院沿革的《通文馆志》曾如此定义:“赍咨行,凡有事奏禀而关系不重,不必备正副品使者,择才堪专对院官咨行礼部。”此处所谓的“院官”即朝鲜司译院的官员,也就是通事。换言之,派遣宦官为赍咨使的惯行在17世纪中晚期已不复存在,赍咨行已按照明朝旧例选用通事出使。
此外,清朝凤凰城与朝鲜义州、平安道等边境地区在咨文传送上发挥的作用逐步提升。正如上所述顺治十四年的事例,在使臣顺付的方式之外,清朝在入关后也会利用本国内部公文传递网络,将咨文送至边境地区,再转交义州府尹,由义州府尹负责把咨文送至朝鲜朝廷。同样地,朝鲜也可利用这条途径,由义州府尹将咨文转交凤凰城城守尉。如康熙八年,针对会宁开市事务,朝鲜备边司启禀国王,令承文院撰出回咨,“下送义州府,传给凤凰城将处,以为转送北京之地”,得到国王的许可。需要留意的是,同样与清朝接壤的咸镜道地区并不像义州等地一样可以介入咨文传递流程,该地区发生的与清朝相关事务亦经义州、平安道等地而通知清朝。如康熙九年,咸镜道会宁府捉住走回人吴守立,此人即由咸镜道直接押送平安道安州,准备由此转送凤凰城,又派出义州地方青水万户金后立担任押送差员。而相关咨文亦由朝鲜朝廷发送平安监司,从而移咨清朝。其实义州等地早在明初就已介入双边咨文传送事宜。如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去世后,礼部咨文即由明朝使臣陈纲等人在鸭绿江沿岸附近交付义州万户李龟铁,随后由李龟铁送至朝鲜朝廷。换言之,清朝利用与义州相邻的凤凰城传送对朝咨文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明国旧例”的继承。
总之,清朝入关后,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发送对朝咨文大致遵循崇德时期由户部主导的模式。但从顺治七年底多尔衮去世,顺治帝建立亲政模式开始,对朝文书事务逐渐收归礼部统一办理,对朝咨文往来亦从此逐渐由礼部主导,展现出“毋违明国旧例”的样貌。有学者称:“定鼎中原使清政权得以全面接收明朝的体制,直接进入了更大层面的建设进程。”但就对朝咨文往来来看,这一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清朝内部的政权建设而最终成立。
三、盛京诸衙门的登场及其作用
由于清朝的机构设置与明朝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毋违明国旧例”的原则在实践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清朝机构设置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其中最受影响的当属盛京诸衙门与朝鲜的咨文往来与交涉。清朝入关后,以内大臣留守盛京,朝鲜使臣赴华的最终目的地随之由盛京转为北京。顺治年间,朝鲜使臣并不直赴盛京,而是经由牛家庄,在此获取通行所需票文后,再转赴北京。康熙十六年,朝鲜使臣不再经由牛家庄,而是从盛京转赴北京。由于清朝政治中心的转移,朝鲜在顺治年间与盛京的咨文往来次数显著减少。不过在此期间,朝鲜仍曾移咨盛京留守大臣。按《通文馆志》的记载,顺治三年朝鲜发生了权大用、柳濯等人密谋叛乱的事件,于是将平定内乱的情况咨报清朝礼部。朝鲜方面担心赍咨官的马匹中途生病,耽误咨文传递,便移咨盛京留守大臣,望其提供清朝的马匹以供替代。然而此时盛京留守大臣并无支应朝鲜使团所需之物的义务,朝鲜备边司也认为“彼之肯许替传,亦难可必”,因而建议国王令平安监司准备丰厚的雇马资金以备不时之需。
17世纪晚期,清朝先后设置盛京礼部、户部、兵部、工部、刑部等衙门,并设有正二品的侍郎,完善盛京地区的治理体制,这也为盛京诸衙门与朝鲜直接往来交涉奠定了制度基础。按金昌洙的考证,《同文汇考》中收录的首次以盛京礼部名义发送朝鲜的咨文是康熙五十年四月通知穆克登将赴朝鲜勘界事宜的文件。但盛京礼部并未将此咨文发送朝鲜国王,而是“右咨义州府”。该咨文后由义州府转送朝鲜朝廷。盛京礼部之所以以咨文通知义州府,或与该时期双边边境衙门文书往来规范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况相关。此前康熙三十二年初,发生了清人犯越进入朝鲜境内的事件,朝鲜决定将此清人押送凤凰城,并知会凤凰城城守尉。左议政睦来善建议先行移咨凤凰城城守尉,具体做法是“其凤城清将处了咨,则自义州府专人入送于城将处事,分付何如?”此处“了”是吏文标记,可以理解为汉语的“致”,即咨文的接收方明确是凤凰城城守尉。随后备边司提出了补充意见,即“自义州移咨,亦不如朝廷之直为移咨”,建议“自朝廷先咨于凤凰城将宜当”。肃宗接受了这一建议。从朝鲜的立场来看,由义州府尹移咨凤凰城城守尉也是可行的路径。18世纪初,凤凰城与义州府之间的文书往来模式逐渐规范化,彼此均采用名为“驰通”的文书来传递消息。所谓“驰通”,在朝鲜国内是“衙门官吏间紧急传递消息时使用的文书”。换言之,驰通的使用范围已突破朝鲜国内,在朝鲜与凤凰城城守尉的信息交换中扮演了外交文书的角色。而在17世纪晚期,双边间咨文使用范围尚未规范化,加上义州府尹在双边文书往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盛京礼部或以为直接移咨义州府尹亦无妨。
早在康熙五十年之前,朝鲜就曾以国王的名义移咨盛京礼部。康熙三十年底,北京礼部移咨朝鲜,称为纂修《大清一统志》即将派遣五位使臣调查宁古塔、乌喇等地方的地理情况,因与朝鲜邻近,令朝鲜派熟悉道路之人指路并预备驿站等事宜。左议政睦来善认为,如果五使确实出来,由于涉及朝鲜西北地区的接待准备问题,那就应该派出“解事译官持文书前往凤城或沈阳,一一详问,定夺回报后,凡干应行之事,可以详知举行”。于是朝鲜决定派出译官卞尔璹携带“沈阳礼部了咨文”赶赴沈阳。该咨文内容如下:
朝鲜国王为咨报事。先该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承准礼部咨。节该散秩大臣宗室查山等,恭请训谕,会议得纂修《一统志》所载城池山河舛错之处,详阅定夺,令其即回。自义州江至土门江南岸一带,俱系朝鲜国人接壤居住,令将熟识道路之人及驿站俱行预备,俟往看时指引详阅等因。奉此,除将所经道路形势先已差人报知外,驿站支待等事,有不可不变通者,必须预先定夺,方可料理。专差行副司直卞尔璹前往于使行所到处,停当以回,以为及时定待之地。为此,合行移咨,烦为查照咨内事意,俾无阻碍迟滞之弊,允为便益,仰照验施行云云。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移盛京礼部。
从上述咨文来看,朝鲜收到北京礼部的咨文后,决定派人指路并准备驿站接待事务,但仍有变通之事需与清朝提前约定,所以派出卞尔璹赴使行所到处。卞尔璹所行道路是盛京所辖之处,朝鲜担心出现“阻碍迟滞之弊”,因而移咨盛京礼部。从朝鲜角度来看,在事发突然,不知道五使是否出发乃至是否已经抵达边境的情况下,移咨与朝鲜相邻的盛京方面的衙门实为实用之举。至于移咨的对象是盛京礼部,这应与朝鲜一直以来与北京礼部移咨往来有关。在朝鲜的认识里,北京礼部是处理本国事务的主导衙门,很有可能将此认知移用在盛京方面,而盛京礼部亦是二品衙门,使用咨文亦未为不可,因而选择盛京礼部为移咨对象。但该咨文发出未久,朝鲜就接到了燕行使臣发回的先来状启,称五使不会出来。此事随即告终,朝鲜也未收到盛京礼部的回咨。
总体来看,17世纪时盛京方面与朝鲜间直接咨文往来的次数较少,盛京诸衙门若有事务需要通知朝鲜,比起直接移咨朝鲜,更可能的是采取通过北京礼部移咨朝鲜的方式。如康熙十二年,由北京礼部移咨朝鲜免去进贡祭祀关外陵寝所需的果物,而祭祀本是盛京礼部所管事务。又如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年的中江开市事件,这本是盛京户部的提议,但盛京户部并未直接移咨朝鲜,而是移咨北京户部,再由北京户部移咨北京礼部,最后由北京礼部移咨朝鲜国王。但正如前文所述,该时期盛京方面虽未直接移咨朝鲜,而朝鲜已曾移咨盛京礼部。换言之,在17世纪晚期的盛京方面与朝鲜之间,业已出现直接咨文往来的可能。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进入18世纪后,盛京礼部开始直接移咨朝鲜国王。康熙末年,发生了垄断经营运输朝鲜贡物与货物的承包人——揽头胡嘉佩勒索朝鲜使团事件。事发之地乃盛京所管地区,为处理该事件,盛京礼部于雍正元年(1723)在“奉旨”的名义下移咨朝鲜国王,令其将遭受勒索的朝鲜人送至凤凰城对质。雍正帝的圣旨开启了盛京礼部直接移咨朝鲜国王之例,这一先例也被朝鲜接受。到了雍正五年,盛京礼部与朝鲜国王之间咨文往来的模式正式确立。即盛京方面发送咨文的主体被定为盛京礼部。换言之,在“北京礼部—朝鲜国王”之外,双边间又形成了“北京礼部—盛京礼部—朝鲜国王”这条咨文往来途径,并一直使用至19世纪。正如嘉庆十七年(1812)朝鲜使臣李鼎受所言,该年朝鲜爆发“洪景来之乱”,相关文书正是沿着“凤城报沈,沈报燕”,即以盛京礼部为枢纽的这条路线传至北京。这条线路,恰与明朝时以辽东都司为枢纽的“礼部—辽东都司—朝鲜国王”传输路线一脉相承。有学者认为明朝时的辽东与朝鲜平安道地区,作为彼此之间文书传递与情报交流的“前沿”与“枢纽”,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明代辽东都司也曾作为枢纽传递明朝皇帝及各部院衙门同朝鲜之间的外交文书,亦与朝鲜直接交换咨文。例如它曾作为辽东各地方衙门的代表移咨朝鲜,要求国王管制其边地军民的越境采捕行为。明清易代后,辽东地区在双边文书交换、边务处理等方面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清朝盛京诸衙门所管辖的辽东等地区依然与朝鲜接壤,犯越、贸易等事件仍多发生于该地区。考虑到减少文书传送所需时间、提高文书传递效率的实际需要,盛京礼部作为盛京各衙门的代表向朝鲜发送咨文,并承担一部分北京与朝鲜之间的咨文中转工作,这既是行政与外交实践上的合理选择,也可以说是对“明国旧例”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四、结语
纵览17世纪清朝与朝鲜咨文往来模式变化的历史,可见“毋违明国旧例”这一原则一直贯穿其中。囿于现实条件,崇德年间并未按照明朝时旧例,而是由英俄尔岱等人负责的户部主导对朝咨文交涉,但在清朝定鼎中原及顺治帝亲政后,对朝咨文处理模式开始转换为明朝时旧例——由礼部主导。17世纪晚期,盛京治理体制逐渐完善,出现了朝鲜直接移咨盛京礼部的事例,并在18世纪前期确立了盛京礼部与朝鲜国王直接移咨往来的新模式。这实际上反映出17世纪清朝对朝交涉的渠道与体制经历了一个由个别人物所在的衙门主导到入关后两国关系走向安定后由相关职能衙门负责的变化。
虽然皇太极明确指出“毋违明国旧例”,但双边的咨文往来证明清朝在崇德时期与顺治前中期的与朝鲜交涉中并没有全盘照搬明制,甚至是在知晓明国旧例的情况下另起炉灶,由强势的个人,如英俄尔岱、多尔衮等便宜行事。双边的咨文往来问题也给“清承明制”这种广泛接受的说法提供了一个深度思考的机会,即至少在与朝鲜的咨文交涉中,清朝对明制的接受与继承过程是曲折的,是经过改造的。
“毋违明国旧例”不只是清朝对朝鲜的要求,其实也暗示了清朝对自己在与朝鲜关系中的定位。即清朝作为明朝的继承者,全方位继承了明朝在与朝鲜关系中的地位、礼仪、典章等等,这也要求清朝在与朝鲜交涉中需展现不亚于明朝的、符合宗主国身份要求的姿态。换言之,皇太极提出的这一构想不是限于单方面的,而是清鲜双方都应遵循的原则。清朝沿袭明朝时处理对朝事务旧制的努力收到了朝鲜的正面回应。乾隆三年(1738),曾出使北京的朝鲜领议政李光佐提到:“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清朝展示出符合宗主国身份的姿态,在涉朝事务上采用“明国旧例”,而朝鲜亦在同样的原则下进行反馈,这亦是清鲜封贡关系得以稳定运行二百余年的原因之一。

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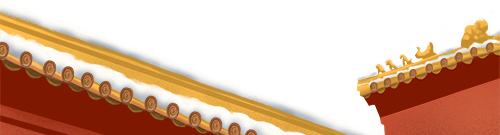
编辑:桃
责任编辑:熊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山大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