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丽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上海20043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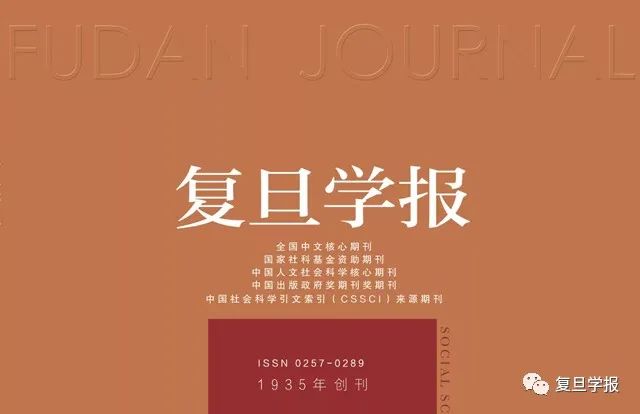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2期
【摘要】朝贡礼仪既是明朝与其朝贡国之间关系的呈现方式之一,也是明朝用来规范朝贡国行为的手段之一,其在现实中的施行受到明朝内政以及宗藩关系的影响。聚焦于紫禁城这一朝贡礼仪发生的核心空间,通过将日本使节、朝鲜使节的朝贡记录与明朝文献相对照,一方面可以复原出外国贡使在明朝期间所履行的广义的朝贡礼仪的全貌;另一方面可梳理出在明朝的不同阶段,朝贡礼仪实际的举行空间、施行频率和具体内容所发生的变化。借助中外文献互证这一重要方法,不唯能够揭示出礼仪的实际展开与文本上的制度规定之间的差异,亦可窥见中朝、中日间的外交互动对于礼仪运行情况的影响,进而揭示出朝贡礼仪在现实中的运行曲线与明朝的内政外交之间的紧密关系。
【关键词】朝贡礼仪 紫禁城 朝鲜朝天使 日本遣明使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国家礼仪最重要的实施空间,将封贡作为处理对外关系基本模式的明王朝,通过在紫禁城举行的一系列庄严且声势浩大的朝贡礼仪,将明朝的威势传达给外部世界。礼仪的展示不仅是为了昭示在朝贡体系中作为天下共主的中国皇权之威严,同时也有着使域外诸国的代表感受明朝礼教庄严,使之对明朝抱持敬畏之心的教化功能。外国使节要在正式朝贡的三日前在鸿胪寺官员带领下学习礼仪,以配合皇帝进行这场盛大演出。除去进表、进方物这一朝贡礼仪的核心环节,尚有见朝、受赏、谢恩、辞朝等一系列与朝贡相关的礼仪活动。笔者认为,以上活动共同构成了使节们在京期间礼仪活动的内容,即广义上的朝贡礼仪,而非局限于“受蕃国来附遣使进贡仪”“受蕃使每岁常朝仪”等狭义的朝贡礼仪。上述使节们履行的礼仪,在《大明会典》中被分散记载于诸司职掌下,并和中国官员的礼仪活动混同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讲,《大明会典》中的记载缺乏对朝贡礼仪的整体呈现。此外,虽然朝贡礼仪全部是在紫禁城即明代宫城的范围内进行,但在明朝的不同时期同一礼仪的举行场所并非完全相同,这一点同样难以仅通过明朝的史料去究明。因此,引入域外使节出使记录,对于还原朝贡礼仪在现实中执行的样貌十分重要。这亦是通过人的活动去“活化”制度史、客观呈现历史上朝贡制度运行情况的重要途径。


一、明初朝贡礼仪的确立及文本规定的变迁

明太祖立国之初便着手制定礼仪规范,“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 ,洪武元年成《存心录》,洪武三年成《明集礼》。在《明集礼》这一明代早期的礼制书籍中,外国的朝贡活动被分为“蕃王朝贡”和“蕃使朝贡”两种情况,“蕃使朝贡”又划分为“蕃国初附”和“每岁常朝”。其中,“蕃国初附”指外国归附后的首次朝贡;“每岁常朝”指首次朝贡之后的常例朝贡,即正贡,不包括因谢恩、进香、吊唁、陈奏等特殊事项的来朝。蕃王朝贡的例子极其罕见,有明一代仅有郑和下西洋期间少数东南亚国家的君主来朝,但这些国家并未留存有朝贡情况的文字记载。留有详细记录的日、朝两国,均只涉及蕃使朝贡。鉴于这一文献状况,本文所探讨的朝贡礼仪主要针对蕃使朝贡。从《明集礼》中“蕃使朝贡”之“蕃国初附”和“每岁常朝”的礼仪规定来看,明初针对“蕃国初附”的礼仪规定较为隆重,仪仗陈设参照“蕃王朝贡”的规格;而蕃使的“每岁常朝”只随班行礼,不再另设仪仗。两者的另一区别是:“蕃国初附”的场合,使臣在皇帝面前进献表笺和方物状,并在奉天殿前陈设方物;“每岁常朝”的场合,进表和进献方物的环节在中书省进行,由丞相接纳表笺和方物。
《明集礼》中的规定繁琐复杂,反映了极其重视“华夷之辨”的明太祖在立国伊始对朝贡礼仪的极致追求。但正如岩井茂树所指出,明太祖制定的朝贡礼仪“并非在具体来往的过程中拟定对外关系的方针和态势,而是在往来以前便事先订好严谨的礼仪制度。制定如此细密礼仪制度的目的,是要对‘允许其成为中华天子的臣从’这种唯一关系进行具体的呈现”。也就是说,明朝初年制定的礼仪虽然是“广征耆儒,分曹究讨”的结果,但其在现实中实施的效果尚需证实。遗憾的是,洪武初年相继来朝的占城、安南、高丽、爪哇等国均未留下礼仪相关的记录,《明实录》亦语焉未详,故而难以证实明初所制定的“蕃国初附”的礼仪在现实中是否曾得到相应实施。明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朱元璋借清除丞相胡惟庸之机,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这就决定了原本与中书省相挂钩的“蕃使常朝”的礼仪将发生改变。据《大明会典》,洪武十八年明朝对“蕃国初附”及“蕃使常朝”的礼仪进行了改定:

洪武十八年定:蕃国初附……其日锦衣卫陈设仪仗,和声郎陈大乐于丹陛,如常仪。仪礼司设表案于奉天殿东门外丹陛上,方物案于丹陛中道之左右……蕃使服其服,捧表及方物状至丹墀,跪授礼部官,受之,诣丹墀置于案,执事者各陈方物于案毕,典仪,内赞,外赞,宣表、展表官,宣方物状官,各具朝服,其余文武官常服就位。仪礼司官奏请陞殿,皇帝常服出,乐作,陞座,乐止。呜鞭讫,文武官入班叩头,礼毕,分东西侍立。引礼引蕃使就丹墀拜位,赞四拜,典仪唱进表,序班举表案由东门入,至于殿中,内赞赞宣表,外赞令蕃使跪。宣表、宣方物状讫,蕃使俯伏,兴,四拜,礼毕。驾兴,乐作,还宫,乐止。百官及蕃使以次出。其蕃国常朝及为国事谢恩遣使进表、贡方物,皆如前仪,唯不宣表。
将上述在《大明会典》中归于“蕃国礼”(礼部十六)下的 “蕃使朝贡”与《明集礼》中的相对应条目“宾礼二·蕃使朝贡”相对照,可以发现以下两点变化:其一,“蕃国初附”的场合,其仪仗不再参照蕃王朝贡的规格,而是“陈设如常仪”;其二,“蕃国常朝”及“为国事谢恩遣使进表贡方物”的场合,其礼仪与蕃国初附基本相同,“唯不宣表”。
据此可知,一方面,随着中书省的废除,原本在中书省进行的“蕃国常朝”的进表进方物环节改在奉天殿(明初皇帝常朝的地点之一)进行,从礼仪举行的空间到礼数均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原本便在奉天殿前举行的“蕃国初附”的仪仗陈设,较之《明集礼》所载洪武初年的规格有所简化。《明集礼》现存最早刊本是嘉靖九年的内府刻本,前有落款为嘉靖九年六月望日的明世宗御制序文。先行研究大多认为《明集礼》在洪武三年制定后并未刊行,直到嘉靖初年明世宗出于礼制改革的需要才付梓刊行,目的是以复太祖初制为标榜,“减少因祭礼改制而触动历代遵用的定制时可能遇到的阻力”。但在此之前,《明集礼》中的规定是否曾被行用,对后世影响几何,均是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学者指出:“《集礼》虽然在嘉靖以前秘而不刊,但并非没有行用……实际上是藏之有司,仍然与其他颁降礼书一样发挥备查、备考功能,并不时被后人参稽相关内容单独行用,或与其他颁降礼书相关内容合并行用而形成新的礼制规范。”笔者认为,至少就朝贡礼仪的情况而言,这一论断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大明会典》中以“洪武二年定、三年定”起始的诸多礼仪规定,很可能便是承袭自《明集礼》,可作为佐证的是两部典籍中“蕃王朝贡”的仪注几乎完全相同。《明集礼》是按照吉嘉宾军凶五礼对礼仪进行归类,而正德、万历两部《大明会典》是以六部职掌划分。尽管修纂体例不同,但就具体规定而言,《大明会典》不乏对《明集礼》中的礼仪进行沿用或损益的情况。笔者认为,朝贡礼仪的雏形在明初已经确立,正德《大明会典》及此后的万历《大明会典》与其说是制礼作乐,毋宁说是对曾经存在的朝贡礼仪的梳理总结以及对现有制度礼仪的明文化。
然而,朝贡礼仪在现实中施行的情况,比从制度文本中所能看到的规定要复杂多变。比如从各国“常朝”的频率来看,现实中各国常朝的时间并不一定是“每岁”。以东亚的朝贡国为例,朝鲜是一岁数朝,琉球起初朝贡不时,成化年间改为二岁一朝,正德二年(1507年)起改为每岁一朝,而日本则是数岁一朝。其次,朝鲜的常例朝贡的时间与明朝的重大朝会相重合,即于正旦(嘉靖十年改为冬至)、皇帝生日的万寿圣节以及皇太子生日的千秋节来朝。在众多的朝贡国中只有朝鲜的常例朝贡是一年三次,显示出朝鲜在明的朝贡体系中的特殊性。


二、明前中期的朝贡礼仪——以景泰朝日本遣明使在紫禁城的活动为例

有明一代,同属明朝藩属国的朝鲜和日本均留有一定数量的出使记录。“朝贡络绎,殆不胜书”的朝鲜除了上述每年三次的“常例朝贡”外,还有以谢恩、陈慰、进香、告哀、请兵、陈奏、辩诬等各种事由来朝的使节,有时一年来朝可达十数次之多。而作为明朝两大忧患“南倭北虏”之一的日本,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贡期被限制为十年一贡。与朝鲜使节赴明名目极其多样化不同,明宣德以后来到中国的日本使节全部为常例朝贡。虽然来明频率的不同导致朝鲜使节的出使记录在数量上相较于日本拥有绝对优势,但在针对明朝的观察方面两者各有千秋。
针对礼仪活动的记载方面,日方记录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存的朝鲜使节《朝天录》中对使行活动详细的记载始于嘉靖十二年,之前的或是针对南京,或是行文简略,或是寄情诗文,能够详细反映使节在明朝礼仪活动的文献基本空白。而日本史料《笑云入明记》作为唯一一部详细记载了嘉靖朝之前外国使节礼仪活动的资料,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第二,朝鲜使节来朝频繁,大概基于这个缘故,朝鲜使节对明朝的事物也生出了“习以为常”的意识,故而许多《朝天录》针对礼仪活动的记载十分简略。与此相对,十年一贡的贡期使得日本人接触明朝的机会较少,且与朝鲜使节均系儒家知识分子不同,日本使节由禅僧担任,虽然他们具备儒学知识,但对于中国的礼仪制度所知有限,以上原因使其对明的礼仪更加留心。当然,朝鲜使节对于明朝礼仪的熟悉使他们的记载中较少出现错误,针对官名、礼仪的记载更准确,这是朝鲜方的记录相较于日方记录的优势。
景泰年间日本遣明使团成员笑云瑞的出使日记《笑云入明记》是目前所发现的东亚使行文献中唯一对嘉靖朝之前的朝贡礼仪有着详细记载的,对于我们了解明代前中期朝贡礼仪实施的情况十分重要。为了更为直观地呈现景泰年间遣明使在紫禁城的礼仪活动,笔者将《笑云入明记》中的相关记录以表格的形式做一展示:
表:景泰四、五年日本遣明使在紫禁城参与的礼仪活动

据上表可知,日使在抵达京城第三天的九月二十八日首次在奉天门觐见了明代宗;十月二日进表文;十一月八日,日本的贡物陈设于奉天门,“鞑靼、回回诸蕃观之”。《诸司职掌》(洪武二十六年作成)和《大明会典》中所记载的方物陈设地点包括“奉天门、奉天殿丹陛、华盖殿、文华殿”,均系明初皇帝常朝的场所。明代的常朝仪分常朝御殿仪和常朝御门仪,御殿听政曾在华盖殿、奉天殿、武英殿、文华殿举行,御门听政则在奉天门。永乐十九年(1420)四月,刚建成的北京宫城三大殿因火灾被毁,常朝遂改在奉天门进行,并成为定例。由《笑云入明记》可知,景泰四年遣明使的进表、进方物均在皇帝常朝的奉天门。既然有贡,就势必有赐。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二月六日,使节分别受领了明朝所赐的服饰和彩段。除此之外,使节在紫禁城还履行了见朝、谢恩、辞朝等礼仪。
这些礼仪均有出典。万历《大明会典》中所列洪武年间所规定的应向皇帝谢恩、见、辞的人员中,“见”之项下有“外国进贡人员”,“辞”之项下有“外国进贡人员回还”。其具体的流程是:“凡谢恩、见、辞官员人等,先于本寺(鸿胪寺)报名,该面见辞及领敕缴敕,或赐酒饭者,预先具白本题知。次日早,俱于午门外行五拜三叩头礼。俟常朝官叩头毕,本寺官具名数帖宣念,行礼毕,其该面谢、见、辞者,仍引赴御前。谢恩者居先,次见,次辞。”外国使节谢恩的名目包括谢赐宴(下马宴、上马宴),谢正赏(服饰、布帛等的赏赐),谢钦赏(皇帝钦赐的下程)。除了这些与朝贡本身相关的礼仪活动,景泰时期的遣明使在紫禁城参加的礼仪活动还有贺冬至、贺正旦、朔望朝以及授历。
景泰年间日本遣明使的经历,较完整地呈现出明代前中期朝贡礼仪执行的情况。从中可知,使节朝贡活动的主要空间是皇帝常朝的奉天门。进表、陈设方物以及见、辞等仪式均在此进行。而受赏与谢恩的场所则未明记。据《大明会典》中的相关规定,笔者推测,受赏的情况,如皇帝视朝,那么便如《大明会典》“鸿胪寺”条所记,“凡赏赐外夷人员衣服彩段等件,本寺官举案,引至御前。俟礼部官奏过,赞叩头毕,仍举案引出给散”。即先赴御前(奉天门)领旨,而后出午门在阙左门由礼部官员颁赏;若免朝,则在午门外行礼,而后在阙左门领赏。日、朝两国使节关于嘉靖、万历年间皇帝免朝时均在阙左门受赏的记载可以辅证笔者的这一推论。谢恩的情况,如皇帝视朝,则在午门外行礼后引至御前,免朝则止在午门外行礼。贡使参与的贺冬至、贺正旦及颁历的仪式,则系于奉天殿随班行礼。


三、明中后期的朝贡礼仪——嘉靖至崇祯朝

日本、朝鲜使节的礼仪实践景泰之后,日本方面虽然有成化四年(1468)天与清启一行、成化十三年(1477)竺芳妙茂一行、成化二十年(1484)子璞周璋一行、弘治八年(1495)尧夫寿蓂一行、正德七年(1512)了庵桂悟一行先后来明朝贡,但关于使节在京活动的记载出现了空白。同样,朝鲜方面虽有成伣《辛丑朝天诗》(1458)、申从濩《丙辰观光录》(1481)、洪贵达《燕行诗》(1481)、申从濩《辛丑观光行录》(1496)、 李荇《朝天录》(1507)等燕行文献,但因为一律采取诗文体,亦无法凭借其还原使节们在京的具体活动。直到嘉靖年间日本才再次出现了详细记录使节在京活动的资料,这便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和二十六(1547)年两次来明朝贡的策彦周良的出使日记《初渡集》和《再渡集》。相较于景泰年间的遣明使,嘉靖十九年时遣明使在京城停留时间较短,未参与冬至、正旦等朝贺,也未履行御前的进表环节,表文由礼部向贡使索取,方物由礼部乞收于内府,未陈设。虽然履行了见朝、受赏、谢恩和辞朝的仪式,但行礼的场所全部在午门外。至于蕃使应该参与的朔望朝仪,则因为明世宗的免朝而未举行。嘉靖二十八年策彦周良再次来京朝贡时,同样在午门外履行了除受敕之外的所有仪式,之后日本便因把持勘合贸易的大内氏覆亡而终止了向明朝朝贡。因此,我们无从通过日本的记录得知嘉靖朝之后明朝朝贡礼仪施行的情况。庆幸的是,此后朝鲜使节的记录弥补了这一空白。
有学者指出,明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在嘉靖朝呈现更加紧密之势。在笔者看来,这一变化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朝鲜使节出使记录数量的增加和记载详细度的提高上。前文述及,朝鲜使节对于在明活动的详细记载始于嘉靖年间,具体而言是始于嘉靖十二年(1533)为进贺皇太子诞生前来的苏世让一行。因此正好与日本使节的记录形成前后相续的关系,两者针对嘉靖年间礼仪实施情况的记载可资对比。
嘉靖年间的日记体《朝天录》,目前笔者所见的有苏世让《阳谷赴京日记》、苏巡《葆真堂燕行日记》、丁焕《朝天录》、权橃《朝天录》、任权《燕行日记》、柳中郢《燕京行录》等。其中属于正贡的是贺冬至使任权一行。以上记录中,除嘉靖十二年的皇太子诞生进贺使苏世让一行曾在谢上马宴和受赏时因世宗早朝亲见世宗外,其他几次的朝鲜使节也同日本使节一样,止于午门外行礼。丁焕《朝天录》记载:“皇帝免朝而三门不启,十二健卒双牵六象而出,军威之陈于庭者亦皆散去。唯大小官之辞朝、见朝者仅七八十人留于门外。序班李氶华、李时贞、孙壁等引余等齿于外郎之后,遂升御路,五拜三叩头。”据此可知,若遇免朝,文武百官与陈设俱散去,只留辞朝、见朝者在午门外行礼。一并结合日本使节与朝鲜使节的其他记载以及前引《大明会典》中的规定可以推知,留下来的除了见、辞的人员,还包括谢恩者。
从上述嘉靖朝朝鲜使节的出使记录来看,尽管明世宗基本处于不视朝的状态,使节们依然要履行相关礼仪,只不过行礼的场所从皇帝日常视朝的奉天门换到了午门。若三大朝时皇帝缺位于奉天殿,明朝百官则诣奉天门行礼:“(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丁酉朔……是日,上不御殿,文武百官朝服诣奉天门行五拜三叩头礼,各具表贺”;“(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辛酉,行冬至庆贺礼,上不御殿,百官朝服诣奉天门行五拜三叩头礼,仍上表称贺”。至于这种情况下外国使节所处的礼仪空间是否与百官相同,笔者会在下文分析。
世宗驾崩后穆宗即位,皇帝恢复视朝。隆庆年间朝鲜使节留下的记录不多,目前为止仅见隆庆三年(1569)贺冬至使朴承任的《啸皋观光录》和隆庆六年(1572)来朝的许震童的《朝天录》。但前者系诗文体,后者来明时穆宗已殁,觐见的是明神宗,均无法反映出隆庆朝的礼仪状况。不过,《朝鲜王朝实录》里记载的一则朴承任的归国报告,帮助我们了解到其在明朝的朝贡过程:
今者卑职等赍擎冬至贺表,进至天阍。不期,鸿胪寺将卑职一行人等退班于无职生员及亵衣人之后。又朔望朝见,不许入皇极门内,只令于门外行礼。较诸久远,见行事例,尊卑悬绝,远人惶惑,罔知厥由。即欲呈禀于该部,以未行见朝之礼,不敢径进干冒,姑循新令,隐忍迁就,觍面汗背,无地容措。始令通事仰达微恳于执事,且禀呈文辨白之意,则执事不以烦诉为罪,特赐温慰。又教以不须呈文,只可口禀于该司郞中。郞中大人亦讶其变易之轻率,即禀议于尚书阁下。于进贺之日别遣下史,曲谕序班,使之依旧随班,得厕冠佩之后。失而有复,喜幸良深。某等拜受执事之赐,以谓自是尽遵旧规而无忧矣。日昨望日朝见,鸿胪寺犹执变礼,止之戟门之外,与左袵羶丑分庭比级,闷默而退,无以自解。
隆庆三年的贺冬至使一行,冬至朝贺时的班位被安排在无职生员之后,朔望朝时又未获许进入皇极门(此处疑为午门之误)。朝鲜使节通过通事向执事者委婉申诉了如此安排不合旧规,而执事者即会同馆主事建议朝鲜使节口头禀报于主客清吏司郎中。郎中亦对这一变例感到惊讶,上报礼部尚书。讨论的结果是在进贺之日遣人告知鸿胪寺序班,让朝鲜使节随班于百官之后行礼。朝鲜使节以为就此恢复旧规,心生欢喜。岂知接下来的望日朝见时,依然被安排在戟门(应指代午门)之外,一行“闷默而退,无以自解”。
这段朴承任回国后的陈述主要针对贺冬至使一行在紫禁城“朔望朝”及“贺冬至”时在班位上受到的不合前规的安排,但有一处应系表述有误,即“朔望朝见,不许入皇极门内,只令于门外行礼”一句。虽然《大明会典》载洪武年间定“朔望朝”于奉天殿举行,但在永乐年间“朔望朝”已随着常朝地点的改变而迁移到奉天门(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改称皇极门),皇帝御皇极门而非皇极殿,朝见的百官和外国使节自然不会进入皇极门内。笔者怀疑此句中的皇极门系午门之误,这也对应了后文“望日朝见”时“鸿胪寺犹执变礼,止之戟门(午门)之外”的记载。对此,朴承任议论道:

今朝廷于小邦,遣使颁诏,特抡近侍之臣。而况且郊后庆成之宴,则陪臣之坐亦赐于殿内。以此观之,陪臣朝贺班列似当有级,而朝见之际则序于流品之次,生员杂类之前。贱价后生虽未知此仪肇于何时,而自先朝以来未尝移易,则亦后世不可率尔更变之成规也。司朝仪者固当率由旧章,坚如金石。设或流弊防政,在所损益,则亦当申奏,委诸该部,详议定夺,取裁圣断,昭布知会,使无疑讶。如是,则处事得体,远人无辞矣。今者朝廷不与知,该部不经议, 无半行文字,无片言端绪,迫令序班舌掉臂挥,破开先朝已定之旧规,易置一时无弊之成法。某等反复思惟,窃所未喻。必以为偏荒贱价,蔑无知识,呼来斥去,谁敢违逆,所以随意指使而然也。窃谓朝廷接待外国,其一号一令,实体统所关;一进一退,乃等威所系。一朝无故贬降班品,区隔内外,岂不妨于体统而缺于慕望之心乎?
针对明朝令朝鲜使臣“退班于无职生员及亵衣人之后”的安排,朴承任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不满及其缘由:朝鲜使节在朝见之际序于品流之次,生员杂类之前,是先朝以来的规定。而此次被序于无职生员之后,于前规不符。对此朝廷不知,礼部不议, 既无文字规定,亦无言语告知,只授意序班指挥,轻易破先朝已定之旧规,如此“无故贬降班品,区隔内外”,实“妨于体统而缺于慕望之心”。自诩为“小中华”的朝鲜对礼仪的敏感,反映了明朝在未有明文规定,甚至在礼部与鸿胪寺未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随意变更外国使节朝见班位的做法在域外引起的非议。可以想见,这只是诸多变例中被记载下来的一处。在接下来的时代,礼仪在实施过程中“因时”“因事”“因地”做出调整的情况也接连发生。
隆庆朝之后朝鲜使节的境遇,根据现存万历年间的《朝天录》可知,万历二年(1574)的贺圣节使一行曾在八月十七日的万寿圣节到达皇极殿前行礼,且在八月初九日和九月初三日皇帝视朝时在皇极门见朝和受赏,其余的诸如谢恩和辞朝等活动均在午门外进行。万历五年的谢恩兼宗系辩诬使金诚一(副使,写有《朝天日记》)一行则未有亲见皇帝的机会,因为此次使节的见朝、谢恩、受赏、辞朝等一系列活动均非在皇帝常朝的日子进行。
以上万历年间朝鲜使节的礼仪活动反映出的信息是,皇帝改为三六九视朝后,如遇皇帝视朝,使节则往皇极门朝见皇帝,如遇三六九之外皇帝不视朝的日子,则在午门外望阙行礼。万历十五年谢恩使裵三益一行曾因受赏在皇极门见到了万历皇帝,由此可知在万历十五年七月的时候万历皇帝依然视朝。而之后留有朝天日记的万历二十年请兵陈奏使郑崑寿一行、万历二十一年谢恩使郑澈一行、万历二十六年陈奏使李恒福一行、万历二十七年陈奏兼贺冬至使赵翊一行、万历三十六年贺冬至使崔晛一行、万历三十七年贺冬至使郑经世一行、万历三十八年贺千秋使黄士祐一行、万历四十二年贺千秋兼谢恩使金中清一行,均因神宗不视朝,所有的礼仪止于在午门外。
明熹宗即位后恢复视朝。天启三年(1623)奏请册封李倧(仁祖)为朝鲜国王的奏请使李民宬与贺冬至、圣节兼谢恩使赵濈的《朝天录》中,均记载了明熹宗在冬至贺仪时出御皇极门。“小顷,皇上自内乘轿舆到皇极门内,乃二层高阁也。皇极殿万历间因火而灾,故此后例于皇极门行礼云。”皇极殿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遭火后尚未复建完成,故原本应在皇极殿举行的冬至贺仪改在了皇极门。但上述两批朝鲜使节均未能进入午门参加贺冬至仪,而是在“午门外,三虹门洞开,瞻望皇极门”,赵濈更是因此发出了“只恨生于小邦,待之以夷”的感概。天启四年十月,奏闻使李德泂一行来到北京,其肩负着为李倧请得诰命冕服的任务。据反映其此次入明经历的《朝天录》(系后人根据李德泂遗稿作成)记载,天启四年的贺冬至、贺圣节以及天启五年的贺正旦等重大朝会,在明熹宗出御皇极门的情况下,李德泂等于五凤楼即午门行礼。天启五年以贺圣节的使命而来,并在北京经历了万寿圣节、冬至、正旦三大节日的全湜,对其在紫禁城的活动,每次均以“诣阙行礼”“诣阙参班”一笔带过,可知其亦未能进入午门。
三大殿在万历年间烧毁后,经历了漫长的修复工作,直至天启六年九月才完工。在皇极殿修复完成之前,明的重大朝会改在了皇极门进行,这一点不唯反映在朝鲜使节的《朝天录》中,亦可以从《明实录》中得到确认。《明实录》中记载了天启二年、三年以及五年贺正旦时皇帝御皇极门内受百官四夷朝贺,但是并未记载明的百官和四夷所处的礼仪空间是否相同。假如我们按照以往在皇极殿前大朝的情形类推,很容易会导出明的百官和四夷均是在皇极门前行礼的结论。然而从天启年间朝鲜《朝天录》的记载来看,朝鲜使节在参加明朝的贺冬至、贺正旦以及贺圣节等重大朝会时,行礼的地点均在午门外,而明朝百官是在午门内、皇极门前的丹墀。也就是说,明的百官和朝鲜使节被午门区隔于两个空间,这是不同于三大朝在皇极殿举行时的情形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向被明朝“视同内服”的朝鲜的使节无法进入午门与明的百官同处一个礼仪空间呢?这种现象是否可以关联到明朝和朝鲜宗藩关系的某些变动呢?
以笔者所见,虽然从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后金因素在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影响,造成了明朝对朝鲜的一些疑虑比如“监护朝鲜论”的出台,但后金的存在对于明、朝关系的影响并不全是负面的。实际上,从万历萨尔浒之战前后直到天启朝,明朝一直寄希望于朝鲜能够牵制后金,与明朝形成相倚之势,为解决明朝的辽东危机出力。因此朝廷中对朝鲜进行拉拢的呼声要高于对其进行戒备。在两种意见中,明神宗和明熹宗也倾向于对朝鲜进行“怀柔”而非加以军事控制。因此,在重大朝会时朝鲜使节无法进入午门,应该不是明朝故意对其疏离的结果,一个更合理的推论是皇极门前的丹墀并不像皇极殿前那般广阔,大朝时京官、地方朝觐官、四夷贡使齐聚,较之参加朔望朝的人员数量更为庞大,皇极门前无法同时容纳如此多的人员,故而将包括朝鲜使节在内的外国使节的班位安置于午门之外。而这一做法在皇极殿修复后也被延续下来,崇祯朝的《朝天录》反映出三大朝时朝鲜使节的行礼场所依然在午门外。由于《崇祯长编》的特殊性,其中关于礼仪的记载非常少,同时以笔者管见,《朝鲜王朝实录》和反映崇祯朝朝贡情况的《朝天录》中也并未针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因此目前对于这一问题尚无法给出明确的结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终明一代,无论是朝鲜使节还是日本使节,他们在紫禁城履行朝贡礼仪的场所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发生改变。记载在明的典制类书籍中的“制度层面的礼仪”和通过域外使节的出使记录所反映出来的“现实中的礼仪”之间的参差是十分明显的。


四、结论

外国使节在紫禁城的礼仪活动,即本文所探讨的广义的朝贡礼仪,包括进表、进方物、受赏、见朝、谢恩和辞朝等环节。除了常例朝贡本便系于正旦(嘉靖十年改为冬至)、万寿圣节和千秋节的朝鲜外,其他国家的使节在京朝贡期间,若逢三大朝会(正旦、冬至、万寿圣节)必参加,朔望朝则随同明朝百官一起行礼。在景泰年间遣明使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使节参与这些礼仪的情况。而嘉靖朝以后,不管是日本使节还是朝鲜使节的记录,均反映出礼仪逐渐崩坏的倾向。
第一,嘉、万两朝均存在皇帝长期不视朝的阶段,在皇帝不视朝的情况下,虽然外国使节依然履行见朝、谢恩、受赏、辞朝等礼节,并且有参与三大朝和朔望朝的义务,但在皇帝缺席的情况下,行礼的场合从皇帝常朝的奉天门变为在午门外望阙行礼。这反映出,相对于文本层面的规定,现实中皇帝的个人因素往往对礼仪的施行有着决定性影响,制度对皇帝的约束力是有限的。皇帝对制度的调整或者改变,有的进入了国家根本制度的层面,被写入《大明会典》;有的则仅仅以“权宜”的方式在某一阶段执行。终明一代,除了我们在典制书籍里所能捕捉到的变迁外,制度在实际施行中还有着更为复杂的面相。
第二,涉及天启和崇祯朝的《朝天录》中,均出现了在三大朝时皇帝出御皇极殿或皇极门、百官亦入午门的情况下,朝鲜使节止于午门外遥拜行礼的记载。起初这只是在皇极殿无法使用、三大朝的礼仪空间移至皇极门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措施,然而经过长期的实行后却相沿成为了“固定”的制度。正如前人所指出,制度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制度可以指导实践,实践亦可以改变制度。所谓“制度”并不限于呈现于文本之中的规定,当一种做法在现实中被反复施行,并且被践行者所接受的时候,其实这种“做法”便已经成为“实际”的制度。朝贡礼仪作为一种用来确定明朝及其藩属国之间关系的制度,从明初到明末其施行情况的日渐弛缓,与现实中明朝对藩属国控制力的减弱是相对应的,反映出明朝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变化。
第三,在朝贡礼仪乃至整个制度史层面,相较于明代官方文本上所呈现的“不变”,也许在日常中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反复发生的“变”才是历史的常态。侯旭东指出,“古人心目中,因应于天道之外的‘制度’不过是小康时代王朝行事所设置、所依托的例行性安排,有常有变有权,皇帝诏令或臣僚奏章常因时因势围绕制度产生议论与损益,内涵丰富,并没有今人以为的那么单一性的强烈规范意义,仿佛具有超越时空的本体色彩”。这一论断提醒我们反思“实际存在”的制度是什么。王朝初期的制礼作乐为了凸显皇权之威严往往极尽繁琐之能事,实际的可操作性反在其次。或者像岩井茂树所指出:“将以皇帝为顶点的天下统治秩序具体展演,呈现出主客双方各自都应置身其中的礼制世界,才是这套对外关系仪制的企图。”但制度一经确立,必然面临着实际中如何贯彻施行的检验。制度落脚于现实,便会成为“事务”。在日常反复进行的事务中,相较于高高在上的规定,身处事务链条上的个人往往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在考察明的朝贡礼仪时,除了关注国家层面的因素比如关系的变动和制度的调整外,亦应注意到具体的司事者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不断发生的日常,实际中反复进行的事务,构成了“实在”的制度。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日朝三国文献的综合研究,一来可见礼仪在文本规定层面与实施层面存在何种差异,二来可见同一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沿袭或变革,并且也能看到“宗藩关系”中关系的变动对制度的影响。正如邓小南所指出,“正是各类关系与制度本身之间形成的‘张力’,决定着制度运行的实际曲线”。反过来讲,朝贡礼仪这一联系着明朝和朝贡国的制度在实施中的变例,很多时候亦反映出处在跷跷板的两端的二者之间的博弈。
The Tribute Etiquette of the Ming Dynasty in Foreign Literature: Centered on the Etiquette Space in the Forbidden City
Zhu Lil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tribute etiquette by Korean and Japanese envoys at the Ning court wa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al policie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Dywasty and its vassal state. Focused o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core space where tribute rites took place, this paper will compare the tribute records of Japanese envoys and Korean Envoys with the sources of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the study of related texts will reveal the actual transformation of etiquette in comparsion with originol system reg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see the impact of diplomatic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Korea and Japan on the operation of tribute etiquette.
Keywords: tribute etiquette; Forbidden City; Korean envoys to Ming court; Japanese envoys to Ming court

主办:复旦大学
主编:汪涌豪
编辑出版:《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邮编:200433
电话:021-65642669
传真:021-65642669
电子邮箱:fdwkxb@fudan.edu.cn
印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年3月25日
发行范围:公开
国内总发行:上海市邮局报刊发行处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复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