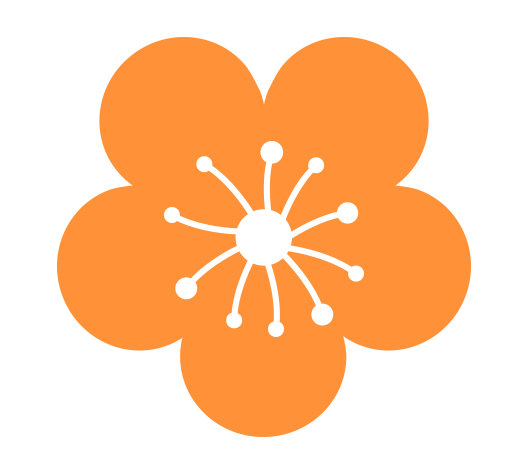


马光,历史学博士,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兼职齐鲁青年学者。
近代广东既是外国鸦片进口的最前沿地带,又是川滇黔土产鸦片消费的远距离市场,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土洋鸦片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盘根错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往学者认为,近代广东鸦片进口替代率较低,从而以寥寥数笔将之带过。事实上,约自1880年代开始,土产鸦片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不断提高的品质,成为外国鸦片的有力竞争对手,逐渐赢得了广东的消费市场。面对残缺数据,通过采用新的推算方式可知,高峰时期,广东每年消费的土产鸦片可达2万多担,而非只有数百担,进口替代率可能高达66.61%,远非以往学者所认为的并“不显著”。通过对广东这一特殊区域鸦片进口替代问题的研究,可一窥近代鸦片中“国货”与“洋货”互相竞争的复杂过程。
近代中国;广东;土产鸦片;鸦片走私;罂粟种植;进口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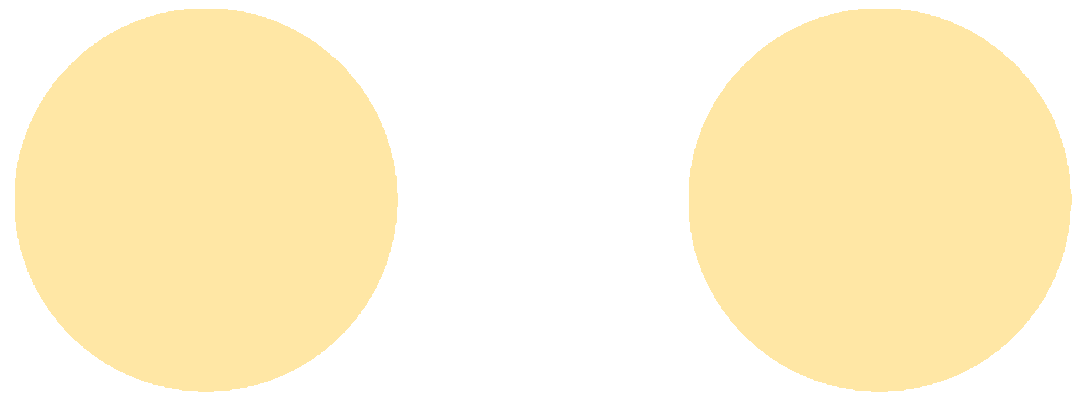
鸦片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19世纪初,外国鸦片大量涌入中国,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至迟在1830年前后,各省开始普遍种植罂粟。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拾两”,表明鸦片贸易已属“合法”【1】。随着清政府对鸦片贸易的弛禁,土产鸦片不断增多,逐渐替代外国鸦片,成为消费的主要来源。
目前,学术界对早期鸦片问题研究较多,但对鸦片战争之后的鸦片问题关注不够,在有限的成果中,又多偏重外国鸦片贸易、吸食和禁烟运动等内容,而对土产鸦片的研究则多显不足,尤其是对广东土产鸦片问题的研究更是鲜见,且多有误解。广东土产鸦片产量有多少?又有多少外省鸦片输入到了广东?土产鸦片是否无法与外国鸦片抗衡,进口替代是否真的并“不显著”?学术界通常认为,即使是在全国鸦片自给率高达91%的情况下,广东是个异类,其鸦片进口替代却并“不显著”,从而以寥寥数笔将之带过【2】。窃以为,以往学者并未就丰富却又十分零散的资料加以发掘利用,致使其对广东的鸦片产量、外省鸦片输入量和消费量等问题上做出了不当统计,进而导致对进口替代这一问题的认知出现偏差。
近代广东土产鸦片问题的学术价值,并不因学者的忽视而降低。事实上,广东个案具有典型意义:一方面,因毗邻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外国鸦片进入中国的大本营,广东成为外国鸦片进口的最前沿地带;另一方面,广东及其周边地区的气候并不适宜罂粟生长,所以不得不从遥远的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输入土产鸦片,广东属于土产鸦片消费的远距离市场。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土洋鸦片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盘根错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对这一典型区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近代鸦片土货与洋货竞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海关档案、英国议会文书、宫中档、调查报告等,重新审视近代广东罂粟种植、鸦片产量、外省鸦片的输入和消费、土产与外国鸦片的竞争等问题,意在突破原始数据残缺的局限,创建鸦片进口替代率新的估算方式。该计算方式,对于其他地区鸦片进口替代率的推算,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罂粟属温带、亚热带地区植物,对自然环境有特殊要求:雨水少但土地要湿润,日照长但不干燥,喜欢光照充足和通风良好的地方,耐寒,不耐湿热。由于广东的气候过于湿热,台风又多,所以并不太适合罂粟的生长。比起四川、云南和贵州等鸦片大省而言,广东的罂粟种植面积微不足道。粤海关在其报告中就曾多次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天气或土壤,都不适合种植罂粟【3】。因此人们判断广东“本省所产之土,乃系创始田亩间,亦不常见,终年所收,大约共有五十担之谱,即将来此等土药,亦必不能丰盛。细观风土情形,于种莺粟花不甚相宜”【4】。
尽管气候不太适合罂粟生长,但至迟从元代开始,广东就已开始种植罂粟。大德《南海志》香药门类下有“莺粟子”,花门类下有“莺粟”的记载【5】。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相关文献。之后,在明清方志中均有提及罂粟(别称莺粟、御米、米囊花等)的种植,且多作为观赏花卉,偶可食用【6】。由此可见,元明清时期,广东的罂粟种植并未中断,且分布广泛,但并未用作生产鸦片。
 大德《南海志》所载鸎(莺)粟
大德《南海志》所载鸎(莺)粟
19世纪初,以生产鸦片为目的的罂粟种植开始在内地出现。1820年包世臣称:“自嘉庆十年(1804年)后,浙江台州、云南土司亦有种罂粟取膏者,然必转贩至澳门,加以药材,方可吸食,是内土亦待成于洋药,仍不能谓为内物。”【7】这表明内地已开始试图生产鸦片,但仍不得其法,需要到澳门进一步加工才能吸食。《清宣宗实录》记载:1823年云南“迆东、迆西一带,复有种莺粟花,采其英以作鸦片烟者”【8】。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有关内地直接生产鸦片的较早记录。1831年李鸿宾奏称“粤东省惟潮州府属间有种植莺粟花之处”【9】。1836年许乃济也奏称:“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10】记载表明在此之前,这些地区就已种植罂粟并能生产鸦片,后虽屡经当地政府拔除禁遏,并未停止。1863年海关调查报告称,香山、顺德、东莞、罗定、鹤山、新安、肇庆、新宁和高要等地是广东种植鸦片较早的地区,当年广东地区的鸦片产量大约有100担【11】。1869年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报告称,广州已有罂粟种植并生产鸦片【12】。1887年海关报告称惠州、潮州和嘉应等地区也有种植【13】,尤其是潮州府全境都有种植,但所产鸦片一般只供本地消费,并不供给汕头等地消费【14】。
1893年前后,有福建人携带罂粟种子到香山县淇澳司的金星门一带,教当地人栽培、收浆的方法,并约定收获之后由福建人收购,每斤给洋银3元。当地人在利益的诱惑下种植了数千亩的罂粟,海关方面估计每亩可收浆4~13斤,每斤浆价值洋银2.5~4.5元。土产鸦片收获后用罐子装起来,多在石崎一埠出售【15】。1895年广东种植罂粟的地区又增加了东莞、增城、番禺三县,并且据说这三县所产的鸦片,尤其是番禺的,甚至比云土还要好【16】。
如果单看以上报告,会误以为香山一带的罂粟种植会大有发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气候和土质问题,罂粟种植并没有全面推广开来。香山县属的那洲、屏南、乌石等乡当时都曾试种罂粟,但是几年后就因“土性不宜,烟质甚劣,失利颇多”而停止种植【17】。1897年海关对当地调查后,做出了悲观结论。报告指出,澳门附近所产土药“甚属寥寥”,香山县属种植的罂粟大约只有200亩,亩产鸦片3~10斤不等,每年总共也就6~20担而已。香山等地所产的鸦片多就地销用,并未远运别处销售【18】。1898、1899年报告进一步显示,土产鸦片在附近地区吸食者较少,即使有一些偷运过来,也只是用来掺和洋药使用,而且数量不多,所以可知罂粟种植在广东并未得到大的发展【19】。广东其它地方同样有一些零星的种植,鸦片产量也不多。1895年潮海关估计海阳、饶平、澄海、大埔等地每年出产土药约300~400担,甚至可能高达600担【20】。次年,鸦片商估计潮州府境内所产鸦片为700~800担【21】。
据估计,1863年广东全境的鸦片产量为100担【22】。粤海关指出,1895年广东土产鸦片产量共约50担【23】。上述估值差异较大,这也从侧面说明获取真实产量的难度之高。1905年、1906年、1907年,广东土产鸦片产量分别为89担、77担、66担【24】,1909年为83担【25】。但是,据国际鸦片调查委员会(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和马士等人的统计,1905—1907年广东土产鸦片年均产量为500担【26】。广东土产鸦片产量较少,通常只占全国土产鸦片产量的0.1%【27】。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Native Opium(1887年版)图书封面

中国各省鸦片产量(Opium production in China, 1908)
有关广东土产鸦片加工生产的具体情况,目前所见到的史料极少。潮海关报告称,1896年一家中国公司计划在潮州采用印度技术加工土产鸦片,仿制公班土的制法,以使口味更佳。为此,该公司甚至雇佣了三个印度人前来指导,但不久即以失败而告终【28】。
1906年鉴于鸦片的危害和国内外禁烟的大形势,光绪帝发布谕令决定禁烟【29】。谕令不但禁止吸食鸦片,而且也禁止国内种植罂粟,规定罂粟须按现有种植面积逐年减少1/10。受此影响,多地开始减种。因牵涉多方利益,官民之间冲突不断。1913年潮州等地开始严格禁止种植罂粟,派遣稽查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铲除罂粟。因稽查极为严格,引起民众愤怒,甚至导致当地政府不得不用武力镇压反抗者【30】。

1909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大会现场

万国禁烟大会遗址(今上海和平饭店)
广东自身所产的鸦片非常有限,远不能满足其巨大的鸦片消费市场需求。因是之故,除进口外国鸦片外,它还需要从国内其他省份如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处大量进口土产鸦片。最终出现“粤东行销土药,以云贵所产为大宗,川省次之”【31】,“两广行销土药,以来自川、云、贵三省为数甚巨”【32】。

曾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1861—1933)
晚清时期,中国大多省份都生产鸦片,尤其是四川、云南和贵州出产最多【33】。三省不但是全国最大的土产鸦片产地,同时也是最大的鸦片输出区,所产鸦片多销往外省,以获得巨额利润。农民将鸦片运到市场后会将鸦片卖给当地商人,这些商人可能要付市场捐等许多费用,但运到广州或其他口岸后,鸦片的转手价就会涨到12元/100两(即每担约200元)左右,所以这些运输商依然可以获取很高的利润。在广州,支付各项费用后,鸦片成本会上升至每担约260元,然而其零售价格可能高达460元,远高于其成本价,所以商人们获得的利润足以支付一切运费而最终能牟取暴利【34】。一方面是土产鸦片的剩余,一方面是巨大利益的驱使,由此,土产鸦片跨出省界,运往别处销售就再自然不过了。

民国时期某地种植的罂粟
土产鸦片进入广东的渠道错综复杂,“土药产自他方,所有来粤销售者,行走之道途繁多,兼之颇为机密,故其数目多寡,本关无由知悉”【35】。广东巡抚张人骏等人在奏折中也提及,“土药来路不一,且有由云南出越南而进广州湾者,亦有绕越南而航北海者,更有夹杂洋货自香港、澳门输入者”,足见问题的复杂性【36】。川滇黔鸦片到达广东的主要路径是运往华东、华南的水路联运:先运输到湖北、湖南、江西各省,再经由这些省份转运广西、广东。四川鸦片运到广东连州,通常需时36天,运费每担约11.8两【37】。1890年北海关区的土产鸦片主要来自云南和贵州。这些鸦片先被运到广西南宁府,在此地重新打包,每个重10斤,然后再运到广东。仅从这条线路输入到廉州和钦州的土产鸦片,每年大约有300~400担。此外,广西百色、宾州、芦墟等地也是沿途重要的集散地【38】。1906年7.6担云土经越南东京(今河内),由轮船运到北海关报关进口,前所未闻。次年,又有14担依此路线进口【39】。龙州关1882—1891年十年报告称,每年都有大量的云南和贵州鸦片流向广西百色,其中一小部分通过陆路流向广西西南部,其余约有18 000担鸦片则从郁江到南宁府,然后再顺西江而下,通过陆路到广东的廉州和钦州,再沿左江而上到太平府、龙州等地【40】。1892年潮海关指出,挑夫先把鸦片从四川运到湖南、江西赣州,到广东兴宁后,再水运到潮州等地【41】。1901年九龙关区的土产鸦片主要来自川滇黔,其中销量最大的是川土。川土之前主要通过廉州、南雄等陆路输入,但后来因沿途多有厘金卡,故放弃这些线路,转而通过梧州输入,途径佛山到达广州后,再用瓦罐分装,转运到九龙及沿海各埠【42】。
因为海关常关并不像新关那样公开和透明,常对它们的税收情况保密,所以要想得知土产鸦片从原产地经过沿途省份需缴纳多少税厘比较困难。尽管如此,粤海新关经过细心调查,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土产鸦片经过沿途省份和进入广州时所缴纳税厘的大致情况。1876年前后,土产鸦片从收获地到运出本省境之前,沿途每担需缴14~15两银,到达广东省边境时,每100两鸦片又要交9钱银(即每担14.4两银),另加厘金税每100两交350铜钱(即每担4两银),到达广州城时,还得再向广州府交另一种入市税每100两鸦片交4钱银(即每担6两银)。这样一来,每担土产鸦片在广东要交税计约24两银。最终,在广州出售的土产鸦片总共需交内地税约每担40两银左右。如果采用海运的话,不论是通过粤海新关还是常关,都要按新关税率每担纳税30两银。相比缴纳的税厘而言,鸦片的运输费就显得微不足道了【43】。1887年粤海关调查报告称,土产鸦片进入广州途中,遇到第一个厘金关卡时,每担会被征收厘金12两银,之后便不再征收【44】。而到了1901年时,凡是由民船进口的土产鸦片,征税开始增加30%,计每担共征银26两。如果由轮船载运,新关也会征收同样的税。尽管如此,土产鸦片大多数还是仍旧由民船载运,而由轮船者寥寥无几【45】。
1892年潮海关调查指出,每担四川鸦片原值约200两,在原产地需缴纳落地税银4两8钱,在野三关再缴纳3两。这两项税,鸦片贩子基本无法逃脱,至于沿途其他关税,能逃则逃。从四川到广东,每担鸦片的盘费即运输费约20两。在广东市场上,每担川土通常可售价250~280两,除去成本,鸦片贩子可从中获利40~50两。从四川到广东,路途遥远,整个路程大约需时3个月,且沿途多有劫匪,鸦片贩子一旦被抢劫,损失惨重,所以他们尽量贩卖那些价值相对较低的次等鸦片。如此一来,即便是被打劫,也能将损失降到最低。当地烟民,大都不能分辨出川土的等级,故鸦片贩子多以次充好,虚开售价,与从宜昌、上海等地轮船运来的上等货价格相差无几。还有一些川土,经由海运输入。海运方便快捷,又无被抢之虞,但其纳税和运费成本却很高。海运来的川土,每担需纳税64两8钱,运输费约7两,其费用比陆运要高约44两,因此多受阻碍【46】。1901年进入广东的云土和贵土,每担需缴纳税银约14海关两,此外,在出产地也需缴差不多等同的费用,所以,总共需缴税约30两【47】。
为节省成本,很多土产鸦片商不愿意多交这些鸦片税,这就导致鸦片走私盛行。实际上,许多土产鸦片都是通过逃避税厘的办法走私运进广东,“加之地面辽阔,水陆纷歧,土商绕越走私,零星洒费,以致厘税终难起色”【48】,“入广东之土药,多偷漏厘金”【49】,“查土药……大半俱由内地土船及陆路走私漏税耳”【50】。走私的土产鸦片经常藏在伪装好的民船的油埕、柴堆等地方,“自梧州沿途零星发卖,至江门而止”【51】。走私者通常10~30人组成一队,用担挑鸦片,随身携带马枪等武器。这些武器,名义上是为了防止盗匪抢劫,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向海关缉私人员示威。过关时,面对这些走私者,海关通常只能征收很低的税,然后放行。过关之后,走私队伍再分散成5~6人的小团伙,以避免太招摇过市,引起民众的围观。也有一些走私者,宁愿多用几天的时间,绕道走远路,以逃避海关征税【52】。1895年琼海关指出,只有一小部分的土产鸦片曾在常关完税,其余大部分土产鸦片都是绕过海关,走私进入该关区【53】。大量走私而来的土产鸦片对外国鸦片的进口和海关税收、厘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54】。为此,海关当局采取了多种缉私措施,但收效甚微【55】。
每年进入广东的土产鸦片到底有多少?这个问题颇难回答。其实,就连当时的海关对这个问题也感到极为棘手,无奈之情跃然纸上。粤海关报告称,“土药进口,报关只有39担,其由内地陆路运来省城者,实数多少,无可稽查”【56】;“土药之由内地来省城者,实数多少,无可稽查”【57】;“土药一项,欲查明本省销数,实难尽悉”【58】。九龙关称,虽然土产鸦片消费量相当大,但是因其在广东各地到处都有走私,根本无法获知准确的输入量【59】。

粤海关大楼遗址
1892—1901年间,每年通过粤海关报关的土产鸦片最多时有100担,最少时只有1担,波动非常大【60】。通过拱北关的土产鸦片也较少,1897年只有8斤【61】,1898、1899年无,1900年缉获136斤,1901年缉获6斤,1902年无,1903年有报关出口8担34斤,1904年出口9担16斤,此后,1905—1917年长达12年内,均无土产鸦片报关的记录【62】。1891年潮州府和嘉应州等地每年输入的川土和云土不超过400担【63】。1897—1907年间,每年在常关报关后进入琼州的土产鸦片分别为683、499、592、531、371、190、130、389、205、369、511担【64】。1902—1910年间,每年在海关报关后进入北海关区的土产鸦片分别为38、70、49、41、9、14、95、14、0担【65】。

拱北关工作人员
如果单纯看报关统计的话,可能会误以为数量不多。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上述一个事实:通过报关合法进入广东的土产鸦片,仅仅只占实际输入量的一小部分。据粤海关估计,1863年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土产鸦片输入广东的数量分别是800担、400担和200担,共1400担【66】。之后,数量不断增长。据华商估计,1877年(农历年)广东土产鸦片总进口量可能达1300担。一位广州官员估计,每年至少有1100担土产鸦片通过税卡,而粤海关税务司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则认为实际的土产鸦片输入量应该超过上述数值。1877年10月起,因海关又降低了土产鸦片税,故输入量仍持续增长【67】。琼海关称,1891年左右,每年大约有12担的云南鸦片输入当地【68】,1891年经过潮海关的土产鸦片只有1.27担,然而当地实际消费却有600~700担,亦即约99.8%的土产鸦片都未报关纳税【69】。1892年北海关估计当地消费土产鸦片约550担,但只有50担报关,走私率约为91%【70】。同年,从陆路私运到潮州一带的四川鸦片有500多担【71】,到1896年已增至2000多担【72】。琼海关称,自1897年每年约有638担的土产鸦片经过常关,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土产鸦片走私进入琼州【7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海关通常认为,即使是算上各种走私,每年输入广东的土产鸦片可能只有2000多担。然而,1896年的粤海关报告却认为,进入广东的土产鸦片每担需纳银14两,而广东每年此项收入约为5万~8万两,所以据此推测,每年进入广东的土产鸦片约为6000担【74】。1897年梧州关报告称,经过该关的土产鸦片“大约一年有二万箱之谱,每箱重三十五斤,共计七千担”,而这些鸦片主要都流入到了广东【75】。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载,1906年广东出产鸦片83担,但土产鸦片消费额却有8075担,缺口多达7992担【76】。据此推测,每年输入到广东的土产鸦片应该约有8000担。1909年在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会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珍贵的第一手调查资料。该报告称,1908年前三个季度,通过粤海关输入的土产鸦片为2150担,其中80%产自四川,15%产自云南,5%产自甘肃;从上海运到潮海关的土产鸦片为2100担,其中1892担产自四川,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从江西和湖南陆路运来的土产鸦片。江门关称每年约有30担的贵州和云南所产的鸦片经由该关进入广东。琼海关称1908年前11个月共有1085担土产鸦片报关,其中901担产自四川,143担产自云南,41担产自江苏【77】。据此推算,每年进入广东的土产鸦片大致应有6881担。此数与1896年粤海关报告、《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估值相差不多。
约6000~8000担的估值,貌似较高,但实际上,广东每年输入的土产鸦片数量应远超此数。英国领事报告指出,1896年广东土产鸦片税收为25万两【78】,1903年《支那经济全书》提及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有关各省土药厘金的报告,缺失广东省数据,却言“其他书中记载为廿五万两”,估计应该是根据英国领事报告而来【79】。若按每担土产鸦片约14两的税厘计算,则有17 857担。粤海关称,广东消费的川滇黔鸦片,1899年分别为8000、6000、1000担,共约15 000担;1900年分别为8000、6500、1500担,共约16 000担【80】。统税大臣柯逢时奏称,两广未实行统税前,因走私严重,广东每年征收的土产鸦片厘金只有7万两左右。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两广开始实行土产鸦片统税,至次年正月,短短三个月内广东就已征收统捐银50.1万两;至三十二年十月底,两年内共征收154.14万两。较之统税前,年均增长达十倍之多。刚开始实行统税时,可能因执行严格,所以税收较多。若按照前三个月的收税趋势,每年可收税约200万两。按每担征收约100两的粗略统计,则每年数量约为20 000担【81】。由此可见,广东每年输入的土产鸦片,高峰时期,至少应有2万担。

China. Report on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Chinese Empire (1897)-封面

1879年海关年度报告封面
输入到广东的土产鸦片,除一部分再出口外,大部分都被用于本地消费。广州无疑是鸦片消费的重要城市,其销售的土产鸦片主要来自四川、贵州和云南,偶尔也会有少量陕西、河南、甘肃等地所产的鸦片。1877年粤海关报告称,广州每年的土产鸦片消费量约160担,主要是用于掺和洋鸦片【82】。广州出售的鸦片通常称为“云南白土”,就像白皮土一样结实。广州的云南白土虽然外观不如白皮土整齐,颜色稍深,加工工艺也明显粗糙一些,但是其质量却明显优于浙江地区的“状如蜜糖的粘稠液体”。在广州,约80%的鸦片店铺都出售土产鸦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表面上经营各种不同商品的商店,却在私下偷偷摸摸地出售土产鸦片,而不出售外国鸦片,这也表明了土产鸦片的受欢迎程度。虽然如此,它的流行度似乎不如进口鸦片,因为广州城内几乎没有一个鸦片商店专门营销土烟而不卖洋药的,但是却有20%的鸦片商店只销售洋药而不卖土烟【83】。1892年粤海关十年报告称,广州店铺每年销售的土产鸦片约为700担【84】。20世纪初,广州吸食鸦片的成年男性约占33%【85】。
另外一个消费土产鸦片较多的地方就是比较贫穷的肇庆府。肇庆背枕北岭,面临西江,上控苍梧,下制南海,这使得运往肇庆的鸦片能够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渠道前往其它鸦片消费区。鸦片商从西南各省将土产鸦片小批量地带到肇庆出售,为避免三水以下各种税卡的苛索与前往省城沿途的困扰,他们宁愿在这里低价抛售鸦片,然后换取洋货和广州的工业产品带回去【86】。
此外,佛山、新安、潮州、海口等地也多有吸食土产鸦片的情况【87】。1883年惠州、潮州和嘉应等地吸食的土产鸦片约1320担【88】。潮州府吸食的土产鸦片,主要是质量较高的川土和云土。1889年该地至少消费了300担土产鸦片,主要用来掺和洋药吸食【89】。1896年一些江苏产的鸦片开始流入潮州,但并未流行开来【90】。进入海口的土产鸦片,或由外出的本地人返乡后带入,或由内地士兵带来,或由内陆旅客乘船携带,每年输入量不超过5担,海关很难发现这些鸦片,所以基本上没有任何征税。土产鸦片通常用来和外国鸦片混合吸食,而且基本上都是在店里秘密进行【91】。19世纪末,高州、雷州、廉州三府,每年约消费4000~5000担土产鸦片,其中7/10来自四川,3/10来自贵州【92】。据1909年国际禁烟会报告,汕头城内,有25~30%的人吸食鸦片,农村则有5%的人吸食鸦片【93】。
土产鸦片进入广东后,除供当地消费外,还有一部分再转口到香港、澳门、台湾、天津、广西等地,主要用来和外国鸦片混合制成熟烟膏销售。有称“土药进口,沿海运来只有四川土五担,由北省用轮船运来;另有云南土二百六十六斤,由西江来省,转运出口,前往香港、天津等处”【94】。又称“出口土药,本年仅有四川土三十七担运赴台湾”【95】。1897年327箱土产鸦片在九龙关报关后,又全部转销至台湾【96】。在潮州,一些鸦片商将土产鸦片和波斯湾鸦片混合,然后再运到台湾【97】。还有一些鸦片商把土产鸦片与麻洼鸦片混合后,当作外国鸦片,再销往到广西梧州、桂林等地,大获其利【98】。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土产鸦片出口到国外,如东南亚、美国等地。有称“有私运华土出口,赴新嘉坡、安南等处,与印度洋药掺杂,贩卖价值较贱”【99】。有称“进口土药货质甚佳,现粤省有以之掺和洋药,自粤之西海,运赴南洋各岛销售”【100】。一些广州商人将土洋鸦片以6∶4的比例混合制成低品级的烟膏,以每两2~2.5钱的价格偷偷走私转销至安南、新加坡和美国旧金山等地,这些混合烟膏数量为数不少【101】。1907年有50箱云土输入香港,其中41箱用以和外国鸦片掺和,之后再出口到安南、南洋等地【102】。
土产鸦片进入澳门的情况尤其值得重点关注。澳门主要实行鸦片专营制度,既有大量的外国鸦片,同时也消费不少的土产鸦片【103】。进入澳门的土产鸦片主要是从云南、四川等地运来。云土每块大约重0.11担,每担大概价值200~240两【104】。云土出云南进入广西境内遇到第一个关卡时,广西厘务总局会贴上印封,然后再运到广州,再由广州通过汽轮运到澳门,最后卖给湾仔的各个烟膏店,用来熬制成熟鸦片膏,也有少量土药是用帆船,或从石岐陆路运输。湾仔熬制的鸦片主要提供给澳门港的渔民使用【105】。澳门烟膏公司生产熬制鸦片时,有时也会掺和土产鸦片【106】。广西厘务总局的印封上标有年月号数,这就给海关提供了估算依据。据海关估计,每年少则750担,多则千担的云土进入澳门,按照每担价值银220两计算,则每年总值银约165 000~220 000两【107】。被调查时,鸦片店铺商人通常会否认当地人吸食土产鸦片,也拒绝承认会用土药掺和洋药。但是,海关多次缉获的走私土产鸦片却一一揭穿了商人的谎言【108】。

广州烟馆的鸦片吸食者(约1907年)

澳门洋药公栈(鸦片屋)
近代以来,中外竞争与冲突不但体现在政治、军事与文化上,同样也表现在经济方面,土产鸦片替代进口外国鸦片就是其典型代表之一。据统计,1879年中国鸦片的自给率已高达80.12%,至1880年代末期,很多地区土产鸦片市场占有率都已超过90%【109】,1906—1908年,自给率分别约为91.5%、85.8%、88.4%【110】。从全国范围来讲,鸦片已成为进口替代最为成功的商品。然而,中国地域辽阔,各地之间风土人情差异很大,在鸦片进口替代方面,势必同样存在着不少差异。例如,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盛产鸦片且又距离沿海较远的地区,土产鸦片有着天然的竞争优势,进口替代率必然较高。但是,对于那些自身鸦片产量较少,且又远离土产鸦片主产区的广东,情况又会如何?囿于篇幅,以往学者对广东境内的土洋鸦片竞争问题并未展开论述,故笔者在此对之做进一步的探究。
土产鸦片和外国鸦片在广东的竞争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初,土产鸦片因口味欠佳,所以很少有人单独吸食,通常都是和外国鸦片混合吸食。在广州,烟民通常以1:4的比例,将土产鸦片和麻洼鸦片混合吸食。1863年前后,土产鸦片尚未对外国鸦片造成多大的影响,故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在一次调查中,各港海关税务人员均认为土产鸦片对外国鸦片的进口没有妨碍,本国鸦片也没有取代外国鸦片的可能。虽然土产鸦片不断在增长,但吸食鸦片者也在逐渐增多,市场需求量增长更多,所以对外国鸦片影响并不大【111】。
然而,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864年潮州等地尚无土产鸦片种植,但十多年之后,惠州、潮州和嘉应等地已多有种植罂粟并生产鸦片,供当地消费【112】。此时,潮州等地方政府对土产鸦片并不征税【113】。1870年英国驻广州领事馆报告称,自1854年以来,印度鸦片进口量逐年减少,价格也在下降。与此同时,土产鸦片却在增多,且价格只是外国鸦片的40%,极具竞争力【114】。1876年粤海关指出,土产鸦片在种植和销售数量方面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逐渐成为外国鸦片的主要竞争者,是导致外国鸦片在粤海关进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115】。1889年北海关称土产鸦片基本和外国鸦片持平,而在广东东部,土产鸦片更多一些,正在蚕食外国鸦片市场【116】。
1892年土产鸦片代替外国鸦片的趋势更为明显。是年,北海关和九龙关均称,土产鸦片的竞争导致外国鸦片减少【117】。1895年粤海关称“洋药所来者虽少,而土药所来者有长,是洋药短销之数,已被土药侵占”【118】。因为云南鸦片的品质和口味已有很大提升,雷州和琼州等地的烟民,甚至只愿意吸食云土,而不愿意再用印度鸦片掺和吸食【119】。这种情形,和早期只愿意吸食纯印度鸦片的情况完全相反,足见土产鸦片的盛行。1896年粤海关对外国鸦片贸易甚至做出了更为悲观的判断,“洋药进口年见减少,土药则年盛一年。缘近来土药味美价廉,食者日众,洋药生意自然滞销,从此想难有起色矣”【120】。1903年粤海关报告指出,土产鸦片和外国鸦片掺和之后的鸦片烟,“其味比土药尤佳,其价比洋药更廉”,故深受烟民欢迎【121】。
相比而言,土产鸦片在潮州地区占据优势的时间稍晚。1885年有少量土产鸦片输入潮州。1888年潮海关称土产鸦片并未对外国鸦片造成多大影响。1889年土产鸦片增至300担,开始引起海关重视【122】,但直到1891年,潮海关还坚称土产鸦片的影响无关紧要,并不能对外国鸦片构成任何威胁【123】。然而,现实很快就证明潮海关的误判。次年,外国鸦片就降为7145担,减少了9.5%。潮海关认为,这无疑是土产鸦片竞争所造成的后果【124】。之后,外国鸦片继续呈下降态势,与之相反,土产鸦片则持续增多。1882—1891年外国鸦片报关量年均约7500担,但1892—1901年间年均只有5213担,减少了约30.5%。1891年报关的土产鸦片只有1担多(152斤)【125】,但到了1901年,总量已飙升至1459担【126】。一些原先只吸食外国鸦片的地方也开始吸食土产鸦片,且渐成风气【127】。
1904年底,八省开办土膏统捐给土产鸦片运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128】。土产鸦片在湖北宜昌缴纳每担关平银52两的税捐以后,运往全国各地时,沿途各地税关厘卡一律照章放行,不会再行收费。如果用轮船载运,还可以购买保险,不必担心被抢劫。这就大大便利了土产鸦片的运输,导致从北方用轮船运到广东的土产鸦片在粤海关报关数量的增加。1903年经粤海关报关的土产鸦片只有39.55担,但是开办八省统捐后的第二年,即1905年却猛增到了860担【129】。
土产鸦片之所以能够不断取代外国鸦片,扩大自己的消费市场,归根结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价格低廉——“人们需求哪种鸦片,主要取决于鸦片价格的高低”,价格是其决定性因素【130】。相比外国鸦片而言,土产鸦片的生产成本低、赋税轻、运费低,尤其是1893年之后,印度的币制改革给土产鸦片带来了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它所出售的价格也比外国鸦片要低很多【131】。

图1 1892~1901年潮海关土产鸦片报关量趋势图
数据来源:《1892—1901年潮海关报告》,《1892—1901年十年各埠海关报告》第2册,第157页。
下面我们就以土洋鸦片的具体行情来做对比分析。1863年土产鸦片在广东的平均价格为380~460墨西哥圆,而公班土为570墨西哥圆,白皮土则更高达670墨西哥圆。1877年外国鸦片熟膏在烟馆的售价每两约4钱5分至5钱8分银,土产鸦片熟膏每两约3钱6分银——比洋鸦片便宜1/3【132】。1880年前后,外国鸦片熟膏每钱价格可能高达5分4厘,土产鸦片熟膏则只值3分9厘【133】。1887年潮州鸦片每担值230海关两,即使是质量较高的四川生鸦片,在潮州每担也只值294海关两【134】。而在广州,每担生土产鸦片价格约为300两,价格稍高。根据品质和重量,每担生鸦片加工成的熟膏,可分为三个等级:60斤,值384两;70斤,值358两;80斤,值332.8两。烟民所吸食的土产烟膏,80%都属于质量较差的第三等级【135】。1889年北海、南宁、玉林等地,每担外国鸦片价格约461~475两,而土产鸦片价格只有约225~275两【136】。粤海关1882—1891年十年报告称,在广州,上等土产鸦片税后价格每担约为250海关两,而外国鸦片则要高很多:每担印度喇庄土400海关两,公班土410海关两,白皮土480海关两【137】。正因为土产鸦片价格比外国鸦片价格低,所以土产鸦片的消费者主要是较贫穷阶层,而那些有购买能力的人还是多选择吸食外国鸦片(主要是印度鸦片)【138】。
鸦片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烟民的吸食偏好。1894年印度鸦片大量减产,受此影响,香港市场上的公班土均价从上一年的每担567元上涨至684元,最高价甚至达847元;白皮土则从每担574元上涨至664元,最高价甚至达730元。过高的价格迫使很多烟民转而改吸土产鸦片,而当价格下降时,一些烟民又改吸外国鸦片【139】。英国驻广州领事馆认为,外国鸦片价格上涨,竞争力下降,从而导致土产鸦片增多【140】。北海关称,每担外国鸦片由485两暴涨至660两,导致吸食量和进口量减少【141】。在潮州,每担公班土暴涨了200两,导致外国鸦片减少,土产鸦片趁机取而代之【142】。1895年潮海关的外国鸦片报关量比1891年减少了3773担,由此引起的缺额则由土产鸦片弥补【143】。1896年因外国鸦片过高,导致潮州六家鸦片公司关闭【144】。甚至,外国鸦片内部也存在价格竞争。1906年当公班土价格上升而剌班土价格下降时,前者进口减少,而后者进口增多【145】。
1901年潮海关称,因为大众普遍转向吸食廉价的土产鸦片,故外国鸦片不断减少【146】。1904年外国鸦片价格骤涨,每箱白皮土涨至1240~1580元,公班土和剌班土鸦片从1320涨至1560元,创历史新高。受此影响,该年外国鸦片进口从1903年的5892担骤减至4865担,减少了1027担,即17.4%。在这样的情况下,土产鸦片乘势而入。1904年增至1473担,是1903年603担的2.44倍【147】。1905年土产鸦片增至2990担,再次倍增,1906年又增至3172担,占鸦片进口总量的42%【148】。1901年北海关报告称,因为土产鸦片产量很多,价格便宜,且口味也有所改进,所以在当地市场有很强的竞争力,导致外国鸦片所剩无几——它们的存在只是用来与土药掺和吸食。外国鸦片进口有时会有短暂的增长,但从大趋势来看,前景极其黯淡【149】。

图2 1895—1901年琼州每担外国鸦片和土产鸦片价格对比图
说明:1895—1898年外国鸦片价格为Malwa、Patna、Benares三种鸦片的均价,1899—1901年为Patna、Benares两种鸦片的均价;土产鸦片来自云南和贵州,琼海关报告中未对其价格作具体分类。数据来源:《1892—1901 年琼海关报告》,《1892—1901年各埠十年海关报告》第2册,第385页。
土产鸦片能够扩大其市场份额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品质不断提高,口味也逐渐迎合吸食者需要。1877年粤海关报告指出,土产鸦片的质量逐渐有所改善,种植者在实践中已改善耕作和收割的方法,熬制的土产鸦片也成功地辟除了混合印度鸦片特有的不受人们喜欢的味道【150】。1895年北海关报告称,土产鸦片的增多,导致外国鸦片以每年10~20%的比例减少。之前土产鸦片只是用于掺和外国鸦片,但是随着品质的提高,一些烟民,尤其是年轻人,改为吸食纯土产鸦片,不再掺合洋药【151】。
潮州海阳县的一家中国鸦片公司,为了提升质量,甚至专门雇佣了三个印度人,采用印度的加工技术,以制造出和公班土类似口味的土产鸦片【152】。汕头西北的沙连村,建有一家鸦片加工厂。该厂司理人曾在香港某洋行充当过管事,后又到槟榔屿习得制鸦片法。该工厂用特殊方法熬制土产鸦片,并和以药物杂质,所以味浓气烈,口味足以媲美印度鸦片【153】。1901年前后,“吸鸦片烟者已逐渐适应吸用国产鸦片。国产鸦片的质量不断改善,而且由于其价格便宜,可与洋烟混合使用,因而深受欢迎”【154】。经过不断改善,云土的质量极高,甚至足以与土耳其及印度烟膏相匹敌【155】。
土产鸦片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不断改善的口味,迅速占领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整体上成功实现了进口替代。根据前述内容,可知广东大体上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但具体进口替代率则不详。为此,我们需要详细考察广东土洋鸦片具体数量。北海关1892—1901年十年报告称,19世纪末,广东总人口约为1914万至2500万之间,其中7/10为妇女和儿童,3/10为成年男子(约570万)。据保守估计,成年男子中约有3/10的鸦片吸食者(约171万)。普通烟民每天平均需吸食1~2钱烟膏,烟瘾大者可能需7~8钱,甚至多达1两。即使按照每人每天1钱烟膏吸食量计算,广东烟民每天也需要消费100担烟膏,每年需36 500担。即使按照最低的1500万的人口量计算,广东每年也需消费20 000担烟膏。通常情况下,1.6担生鸦片能加工成1担熟膏。此外,还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生鸦片通常还会掺杂高达30%的其它杂物,即使是没有杂物的生鸦片,也只含90%的纯鸦片。因此,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广东每年需要至少输入35 500担生鸦片【156】。
其他海关对土产鸦片的估算,通常基于报关量,但无法统计走私部分的数据,故其数值精确性大打折扣。北海关直接从宏观方面进行测算,有效排除了走私等因素的干扰,不失为一种合理的估算方式。北海关声称,这是“最保守的统计”,事实的确如此。据清末宣统年间官方调查数据,广东省约有2800万人口,而该估值按1500万计算,只是实际人口量的53.6%【157】。北海关对于人均吸食量、吸食人口比例的估计,也是基于保守考量。
尽管如此保守,如此巨量的估值还是难免让人怀疑其可靠性。其实,这个估值并不夸张。1888—1891年间,通过广东各海关报关的外国鸦片分别为26 845、25 583、24 991、25 339担【158】,这些统计尚不包含走私鸦片。上述已经论及,进入广东的土产鸦片,每年可能多达2万担以上。外国鸦片加土产鸦片,极有可能达4万~5万担。若再加上走私鸦片,相信总量会更多。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35 500担应该是比较保守的合理估值。鸦片是成瘾性消费,在人口没有较大变动的情况下,吸食总量通常也不会有大的波动,所以我们可以将35 500担设为参考定值。土产鸦片具体数值难以估算,但可以通过总吸食量减去外国鸦片报关量的方式获得,最终可得土产鸦片比重,即进口替代率。
表1 1892—1901年广东中外鸦片数量及其比重(单位:担)


数据来源:《1892—1901 年北海关报告》,《1892—1901年海关十年报告》第2册,第411~412页;《1892—1901年各港口鸦片净进口量》(“Opium: Net Importation into Each Port, 1892 to 1901”),《1901年海关年度报告》第1册,第17页。
由此可见,1892—1901年间,广东土产鸦片消费量在14 275~23 645担之间。上述计算方式,囿于客观原因,未能考虑走私等因素,可能并不太精确,但从中可以看出大体趋势。1892—1901年十年间,广东鸦片市场上,土产鸦片平均约占56%,1896年达到最高峰值66.61%。琼州关报告称,1896年琼州吸食的鸦片中,土产鸦片占70%。次年,约消费1400担鸦片,其中土洋鸦片分别为855担、545担,土产鸦片占61%【159】。琼州的比例和广东全省的情况基本一致。
林满红称,“福建、广东已为川滇黔鸦片运销网之尾闾,所使用之鸦片主要来自国外进口”,“东南地区本国鸦片对外国鸦片的取代,除一八九〇年以后的福州、开港以后的温州以外,均不显著”【160】。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广东——外国鸦片进口的最前沿地带和川滇黔鸦片的远距离市场,鸦片进口替代并非“不显著”,相反,土产鸦片同样据重要地位,其进口替代现象也是相当明显。

图3 1863—1915年在广东与全国新关报关的外国鸦片数量
数据来源:《1869年海关年度报告》(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1869)第1册,第13页;《1870年海关年度报告》(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for the Year1870)第1册,第13页;《1878年海关年度报告》(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for the Year1878)第1册,第13页;《1886年海关年度报告》(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and Trade Reports,for the Year1886)第1册,第13页;《1891年海关年度报告》第1册,第13页;《1901年海关年度报告》第1册,第17页;《1911年海关年度报告》(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1911)第1册,第34页;《1917年海关年度报告》(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1917)第1册,第72页。
尽管土产鸦片不断增多,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土产鸦片并没有完全取代外国鸦片。受产地减产或沿途动乱的影响,土产鸦片价格也不断上升【161】。1898年潮州市场上的土产鸦片价格就比上一年上涨了25%【162】。而且,土产鸦片的煮出熟膏率不如外国鸦片高,当二者的价格相差不多时,前者的竞争力会逐渐削弱【163】。事实上,直到1908年,经粤海关进口的外国鸦片依然高达10 060担之多【164】,1909年经广东全境海关输入的外国鸦片有18 532担【165】。之后,受全国禁烟大形势的影响,进口鸦片数量才开始递减,直至1917年才基本消失。同样,全国各地开始削减罂粟种植面积,广东的土产鸦片输入量也随之大为减少。以广州为例,1902年从川滇黔运到该地的土产鸦片为4000担,1910年从川滇来的土产鸦片降为1390担,而到1911年则骤减为180担【166】。
至迟从1836年开始,广东就已开始生产鸦片,后虽屡经当地政府拔除禁遏,但并未停止。香山、顺德、东莞、罗定、鹤山、新安、肇庆、新宁和高要等地是较早生产鸦片的地区。1880年代,广东大部分地方都有零星生产鸦片,但是因气候和土质问题,罂粟种植并没有全面推广开来,其产量也比较有限,最初可能只有百担,高峰时期约有1000多担,至20世纪初期约有500担,占全国土产鸦片产量的0.1%。
广东自身所产的鸦片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其巨大的消费市场需求。除了进口外国鸦片外,它还需要从四川、云南、贵州大量输入土产鸦片,偶尔也从甘肃、江苏、陕西、河南等地输入。鸦片从川滇黔运输到广东,不但要经过长途跋涉,更要沿途缴税厘,每担约30~40两。由于沿途缴费成本较高,导致走私盛行。通过报关合法进入广东的土产鸦片,往往只占实际输入量的一小部分。关于外省鸦片的输入量,海关通常认为,即使是算上各种走私,每年可能只有2000多担。然而,1909年万国禁烟会报告、《清朝续文献通考》等资料显示,每年进入广东的土产鸦片约为6000~7000担,是通常估值的数倍之多。尽管如此,综合考察各种史料后,笔者认为,此估值依然较低,土产鸦片实际最高值可能高达20 000多担。
土产鸦片进入广东的渠道错综复杂。川滇黔鸦片到达广东的几条重要路径是运往华东、华南的水路联运:先运到湖北、湖南、江西各省,再经由这些省份转运到广西、广东、福建。四川涪州是川滇黔鸦片的重要中转基地,土产鸦片多在此地汇集,然后再经过湖南、广西等地进入广东。而在广东境内,西江和北江则为主要通道。土产鸦片进入广东后,主要供当地消费。广州无疑是鸦片消费的重要城市,肇庆、佛山、新安、潮州、琼州等地也多有吸食土产鸦片。除供当地消费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再转销到香港、澳门、台湾、天津、广西,主要用来和外国鸦片混合制成熟烟膏销售。另外,还有一些出口到国外,如东南亚、美国等地。
土产鸦片和外国鸦片的竞争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初,土产鸦片因其口味欠佳,所以很少有人单独吸食,通常都是和外国鸦片混合吸食。但是,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不断改善的品质,土产鸦片迅速占领广东市场。1876年土产鸦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逐渐成为外国鸦片的有力竞争者,是导致外国鸦片在粤海关进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之后,土产鸦片不断增多,至1890年代,进口替代的趋势更为明显。土产鸦片走私数量等关键数据的缺失,导致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推算出具体进口替代率。根据新的计算方式,笔者认为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1892—1901年十年间,土产鸦片平均约占56%,1896年进口替代率达到最高峰值66.61%,而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比值更高。由此可知,即便是在广东,鸦片进口替代并非“不显著”,相反,土产鸦片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其进口替代现象也是相当明显。
由上观之,以往学者多是以全国为研究对象,从宏观视角考察鸦片进口替代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大而化之,无法做到对各地具体情况的精细量化研究,以致于对部分地区的替代情况做出了不当判断。通过对广东这一典型地区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到,之前被忽略的土产鸦片,在历史时期曾经扮演过关键角色,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也得以彰显。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学术界或可进一步挖掘近代海关史料、外国驻华领事档案、清宫档、调查报告等各类相关史料,重新逐一考察全国各地鸦片进口替代问题的异同,避免粗线条的笼统概括,如此,方能有助于掌握各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重新理解近代国货土烟与洋货鸦片相互竞争的复杂过程。
(说明:本文所用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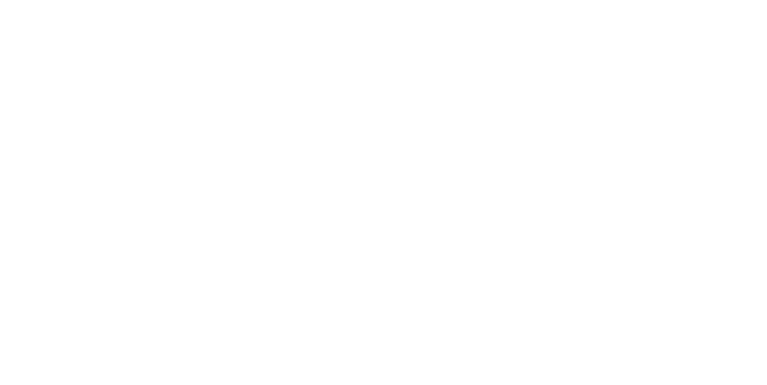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