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自由”观念并非完全由美国人“原创”,而是有着深刻的欧洲理论源头和国家实践印记。在革命年代,美国开国先辈在设计国家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基于中立国国家角色定位,“舶来”了欧洲的“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原则,主要体现在“1776年条约计划”中。而在争取加入1780年“武装中立”联盟,以及与欧洲国家的谈判中,富兰克林、亚当斯等人借鉴并阐发了源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海上私人财产免于捕获”理念,将其确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之一,并落实在1785年与普鲁士签订的双边条约之中。作为具有美国特色的海洋自由观念,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属性,反映了美国建国之初海军力量弱小的现实,其式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美国外交政策;海洋自由观;海上私人财产豁免;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
近年来,随着美国海军在中国南海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持续升级,在美国立国之始便被确立为国家外交政策原则之一,却久已淡出史家视野的“海洋自由”(freedom of the seas)原则,再次频频出现在美国的现实政治和学术话语中,并被加以美化乃至神圣化。美国国防部网站公布的《航行自由计划简报》称:“自建国时代起,美国就一直主张维护海洋自由这一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历史表明,美国对海洋自由的维护,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空间上具有全球性。”[1]该简报刻画了美国自诩世界海洋自由捍卫者的高大形象。当代美国外交史学家阿明·拉帕波特(Armin Rappaport)和威廉·E.威克斯(William Earl Weeks),则更进一步提出了海洋自由为美国“原创性”外交政策的观点,称该原则“代表了一种把美国的国际法观念和普世人权观念扩展至世界所有海洋的努力”。[2]他们明确地把海洋自由与人权观念联系在一起,在美国学术史上实属罕见。
其实,拉帕波特和威克斯的“原创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传统观点:20世纪20年代,英国学者J.M.肯沃斯(J.M.Kenworthy)的“海洋自由是美国独立以来美国人的守护神”一说,[3]20世纪30年代美国第一代专业外交史学家塞缪尔·F.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的海洋自由是美国“与生俱来的古老权利”说,[4]以及马克斯·萨维尔(Max Savelle)把美国海洋自由观念的源头追溯到17世纪四五十年代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的做法,[5]所透露的都是这种认识倾向。可见,强调美国对于海洋自由观念和政策的“原创性”贡献,具有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是美国外交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宏大叙事”。[6]
本文将挑战上述历史叙事,通过回顾美国殖民地时代和革命时代的历史,考察彼时美国人,特别是美国诸位“开国元勋”海洋自由观念的来龙去脉和具体内涵,以及他们将其确立为国家外交政策原则的动机和思考,以探幽索微、正本清源,重新认识当时美国的“海洋自由”原则及其实践。
鉴于海洋自由概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必要先对本文的核心概念“海洋自由”做一简要界定。从国家外交政策原则的视角出发,美国政治家一般把“海洋自由”定义为所有人拥有的不受干扰地在国际海域游弋的权利,不论战时还是平时皆然。[7]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时人口中的“海洋自由”有着更加具体和明确的内涵所指。历史地看,美国的海洋自由政策可概括为“两个政策原则”和“三大发展阶段”:“两个政策原则”即“海上私人财产豁免(缉拿)原则”(The Doctrine of Immunity of Private Property at Sea)和“航行自由原则”(The Doctrin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三大发展阶段”,即从美国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是以“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为主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50年前后,是从“豁免原则”到“航行自由”原则转折的阶段;1950年之后,是以“航行自由”为主要利益诉求的阶段。本文所考察的“海洋自由”概念,显然是指上述第一历史阶段的“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具体时段始于1643年约翰·温斯洛普阐发朴素的海洋自由观,终于1785年美国与普鲁士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探求“海洋自由”观念的源头所在为本文的核心任务。通过对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美国“海洋自由”观念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国家实践层面,抑或思想理论层面,美国海洋自由观念的源头都指向欧洲,而美国人的贡献无非是把“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引入现实国际政治之中,将其转化为一种外交政策原则。
马克斯·萨维尔认为,美国海洋自由观殖民地起源说的主要依据,是一则发生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轶事,概括如下:17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殖民地阿卡迪亚内部发生了查尔斯·拉·托尔(Charles La Tour)与查尔斯·德奥内(Charles d’Aulnay)之间围绕殖民地控制权的纷争,拉·托尔依靠此前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商人在毛皮贸易方面的良好关系,于1643年6月亲赴波士顿,谋求与后者结盟并共同对抗德奥内。当时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立法机构正处于休会期间,在商人群体的鼓动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自行决定,允许拉·托尔雇用那些愿意追随他的人员和船只。德奥内则对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与拉·托尔的贸易关系提出抗议,并威胁要掳获波士顿人的船只。对此,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地方法官给出了一个“言辞犀利的答复”,声称英国殖民者拥有海上自由航行并与一切“投契者”进行贸易的权利。温斯洛普在写给地方法官的信件中,不仅完全同意地方法官的观点,而且“借题发挥”,进一步阐述了上述原则:“船舶主人和船长可合法受雇于拉·托尔,这是他们的职业使命所在……若我们船只的合法业务遭到反对(而不加捍卫),他们事业的正义性就可能因此丧失殆尽。譬如,某人携其货物雇乘一辆马车在英格兰旅行,其债主登上马车,以暴力手段抢夺其货物。在此情形下,尽管目前其雇主正遭到不遵守债务约定的指控,但马车夫依然可以保护该旅客及其货物,因为马车夫业务的正义性是基于不同的(法理)依据。”[8]萨维尔对温斯洛普所阐述的原则做出解读:温斯洛普在这里区分了两种行为:一是为拉·托尔提供援助。温斯洛普主张,马萨诸塞人有权将自己和船只租给任何愿意承担他们所开价格的人,该主张的本质是自由贸易;二是运载拉·托尔本人及其货物。温斯洛普强调中立承运人在不受客户的敌人骚扰的情况下运载客户及其货物的权利,主张中立承运人行为的正当性源于其并非纠纷中的任何一方,因此不应被纠纷中的任何一方所攻击。萨维尔指出,温斯洛普为中立承运人权利所进行的辩护,虽然是特定形势下对于特定政策的表达,但是却道出了日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海洋自由原则。美国海洋自由原则的思想源头,或可追溯于此。[9]萨氏关于海洋自由原则思想根源的这番讨论,仅仅基于殖民地时期的单一事件,立论未免单薄和仓促,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
众所周知,近代海洋自由概念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于1609年在《海洋自由论》(The Free Sea)中提出的。同时代的英国人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则是第一个把格氏著作译成英文的人,不过其译稿长期处于手稿状态,直到2004年,方由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教授编辑并撰写“导论”加以出版。[10]换言之,在17世纪早期,尽管上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之轶事发生在格氏提出海洋自由论三十余年之后,但当时格氏《海洋自由论》的流传范围较为有限,温斯洛普阅读此著作并受其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也许可以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之轶事表明,北美殖民地独立于欧洲产生了自己的海洋自由意识,但不宜夸大这一轶事在此后美国海洋自由观念发展中的作用,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轶事对当时其他英属殖民地产生的影响,其对美国开国元勋产生的影响也无从稽考。再者,温斯洛普所表达的充其量只是一种朴素的海洋自由观,不仅提出的时间相对更晚,在论证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上,与格劳秀斯的论述也无法相提并论。
宏观地看,在近代早期,主导海洋自由的国际法理演进及世界海洋自由实践进程的,始终是欧洲大国的法学家、政治家及国家实践。作为“化外之地”,北美殖民地精英人士是以大英帝国“子民”的身份参与到世界海洋秩序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并在其中逐步形成对海洋自由观念的认知。这是由北美殖民地对母国的政治经济从属关系所决定的。换言之,对美国海洋自由原则起源问题的探讨,固然需要着眼殖民地本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总体发展状况,但从国际关系的大背景出发,考察当时欧洲大国的海洋自由观念与实践同样不可或缺,甚至尤为重要。
从当时北美殖民地社会文化发展的状况来看,务实主义正在这块大陆上生根发芽,成为殖民地人民判断事务价值、处理内外关系的根本指南。正如王晓德教授所指出的:美国人以讲究实际而著称于世,这是早期移民在征服莽莽荒野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传统;美国人无暇也不愿意在深奥的理论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那样做太费周折,还不见实际效益;抽象思辨的研究在美国几乎没有市场。[11]这种判断显然适用于殖民地人民对于海洋自由问题的思考。对于海洋自由的法理论证和相关国际法原则的创立,当时的北美殖民地显然没有做出突出贡献。一直到革命年代,美国开国先辈表达的海洋自由观念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欧洲法学家那里学习借鉴而来的。当然,他们根据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对海洋自由观念灵活运用并有所发展,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就在北美殖民地的海洋自由观念停留在朴素状态之时,欧洲法学家却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法理论战”,对于海洋自由的法理认识不断提升。首先,17世纪中期,经过格劳秀斯与威廉·威尔伍德(William Welwod)、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等人关于海洋法律地位的论战,领海主权、公海自由的海洋法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其次,进入18世纪后,3海里的领海宽度得到确认。1703年,荷兰法学家宾刻舒克(Cornelius van Bynkershoek)发表《海上主权论》(De Dominio Maris),提出了领海宽度以“大炮射程”为限的原则;1782年,意大利人费迪南德·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发表《中立国君主对交战国君主的义务》(The Duties of Neutral Princes Towards Belligerent Princes),进一步把“大炮射程”具体化为3海里,并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12]最后,贯穿17—18世纪始终的,是“海洋自由”问题被逐渐纳入一般性的国际法著作中,并得到更为客观和超然的讨论。在这些著作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德国人普芬道夫(Pufendorf)的8卷本《论自然法和万民法》(Law of Nature and of Nations,1672)和瑞士人埃默·瓦特尔(Eme de Vattel)的简明《国际法》手册(Droit des Gens,1758)。[13]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际法通论性著作均以自然法为理论底色,虽以拉丁文、德文和法文书写,却在17—18世纪纷纷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发行,有的甚至被多次再版发行,风靡欧洲。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论》(War and Peace)于1654年、1682年和1738年再版发行;普芬道夫的《论自然法和万民法》于1710年、1716年、1729年和1749年再版发行;宾刻舒克的著作于1759年翻译出版;瓦特尔的著作在1760年之前也开始在伦敦流传。此外,根据从国际法角度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名家杰西·S.里夫斯(Jesse S. Reeves)的研究,到18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的律师们已或多或少地了解这些著作中的法律观点。[14]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欧洲法学家的著作是北美殖民地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海洋法理论知识的源头所在。
但是,对于北美殖民地人而言,他们在海洋事务实践中主要遵循的并非上述基于自然法的“格劳秀斯主义”,而是宗主国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所订立的商业条约,以及英国为保护自身商业利益而提出的一些海上行为规则。在海洋政策问题上,北美殖民地只能对母国亦步亦趋,“蜷缩”在大英帝国强大海权的羽翼之下,“享受”作为“英国人的权利”的“海洋自由”。[15]而海洋大国的本性决定了扩大交战权利与抑制中立权利成为这一时期英国海洋政策观念的主导倾向。在连绵不断的海洋争霸战争中,英国的如下实践和规则,深刻影响了独立后美国人的海洋政策观念和国家实践。
第一,武装私掠(privateering)。所谓“武装私掠”,即战争时期由政府颁发“私掠许可证”(letter of marque),授权私人武装民船,在公海针对敌国船只进行拦截、袭击并抢夺其货物。一般认为,英国的第一份正式“私掠许可证”颁发于1295年,标志着英国武装私掠政策正式推行。不过,大规模的武装私掠行动开始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1651年《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s)的颁布,进一步刺激了武装私掠行为。[16]1708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一个新的掳获法,以刺激日渐降温的私掠活动。[17]总之,在17—18世纪,武装私掠是英国“一以贯之”的国家实践,它与皇家海军的不断发展壮大相呼应,共同铸就了近代英国的海洋霸权。
北美殖民地曾是英国武装私掠的重要参与者和实施者。每有战事发生,国王向高级海军上将下达命令,授权适当的官员(如殖民地总督)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条件下颁发特许状或私掠委任令,这在当时已成为惯例。而在北美殖民地,武装私掠政策也形成了一套堪称健全的组织架构和成熟流程,在劫掠船装备、政府与私掠船主获益分成、捕获法庭(prize court)的组成及规约制定、私掠船指挥官与船员间民事关系界定等方面,皆有章可循、“有法可援”。[18]其结果是,武装私掠不但成为殖民地战时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而且被殖民地人民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权利,就如同他们在陆地上拥有不被侵犯的持枪权一样。这是美国独立后,费城制宪会议将宣战及“对民用船只颁发捕押敌船及采取报复行动的特许证,制定在陆地和海面掳获战利品的规则”的权力赋予国会,并将其郑重写入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的历史根源。[19]不过,美国独立后奉行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作为交战权利的武装私掠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因此,美国虽未正式宣布废止武装私掠的宪法权利,但在美国内战、美西战争等战事中并未诉诸武装私掠。[20]
第二,“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原则(free ships,free goods)。17—18世纪,英国海上实力不断增强,但尚未取得绝对的海洋霸主地位。因此,在与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的海上争霸战争中,英国不可能同时与各国为敌,而是需要“合纵连横”,各个击破。同时,英国也希望在其他国家进行战争之时,以中立国身份与交战国进行贸易,大发战争横财。由此便产生了适当照顾中立国权利、收缩交战国权利的需要。1654年,英国与葡萄牙的双边条约明确了“敌船所载货物属于敌货”(enemy ships,enemy goods)、“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双轨并行的原则。1667年,英国与西班牙签署《马德里条约》(Treaty of Peace and Commerc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Spain,concluded at Madrid),含蓄地表达了“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原则。不过,更具意义的是英国与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于1667年签订双边条约,写入上述两项原则,并在1668年的双边条约中再次对其加以确认。这标志着有利于中立国的“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原则,得到了欧洲两大海洋国家的确认,成为它们共同遵守的海上行为准则。[21]在1672—1678年法、荷战争期间,英荷两国于1674年签订《海洋条约》(Marine Treaty),对“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原则、战争违禁品等事项进一步做出详细规定。[22]1713年3月,英法两国签订了《英法航海通商条约》,即《乌特勒支条约》(The Treaty of Utrecht),采纳了“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原则,并对战争违禁品和公海中立权利做出了界定。[23] “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的国际法普遍原则进一步得到巩固。
上述国际条约及其“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条款同样适用于北美殖民地,为殖民地从事中立贸易、获得丰厚财富提供了必要的外交和法律保护,也使殖民地人民对中立地位的裨益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正因如此,《乌特勒支条约》成为此后美国革命中开国精英制定新国家对外关系原则的重要参考。
第三,“1756年规则”(The Rule of 1756)。在海洋争霸的过程中,英国始终没有停止对实施“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原则之利弊得失的反思,并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允许中立国家接手并从事英国敌对国的海运贸易,特别是与美洲的海运贸易,那么英国控制海洋的意义就不能有效发挥,甚至荡然无存。在英国海军实力实现了对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的逐一超越后,英国人的这种感受愈发强烈,于是开始调整对中立国的政策。在1756年“七年战争”打响后,为了禁止荷兰和其他中立国与法属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英国提出了被后世称为“1756年规则”的中立国政策。该规则宣布:中立国不能在战争期间从事和平时期对其关闭的贸易以获取利益;从事非法航行的中立国船只将被定罪,非法贸易所涉货物将被没收。[24]美国独立后,英国仍未废止该规则,并适用于美国,从而引发了与美国的中立权利纠纷。
综上所述,就海上权利、海上行为规则的国际法和国家实践演进而言,殖民地时代留给美国的显然是一笔错综复杂的遗产,其中既有基于自然法的理想主义成分,倾向于自由贸易、保护中立权利,也不乏基于条约法的现实主义,倾向于重商主义,主张以具体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为依据,在交战国立场和中立权利之间进行灵活选择。这是美国革命爆发时,国父一代在思考新政权对外关系时所面临的基本国际法背景和国家实践现实。在他们关于海洋问题的思考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贸易与重商主义思想取向交织并存、相互影响,共同服务于美国的现实利益。正如倡导以全球史视角考察美国历史的著名史学家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所言,欧洲帝国为争夺海洋贸易、增强海军力量而展开的各种竞争,正是美国革命及随后作为一种世界强权而出现的合众国的(历史)语境。[25]
在与宗主国的政治冲突发生后,基于英国依赖北美市场的基本判断,大陆会议以商业为武器,开始采取一些影响海上贸易的政策:1774年9月,大陆会议通过了不进口、不出口和不消费的决议,并从该年12月1日起开始执行,希望以此迫使英国议会取消针对殖民地的一系列“不可容忍”的法令;1775年11月25日,通过“关于捕获船只及其货物的决议”,开始实施针对英国的武装私掠。这是一种通过关闭北美殖民地市场迫使英国就范的政策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殖民地时期海洋政策思想的影响。
不过,随着与英国人的矛盾不断加深,在革命来临之际,殖民地人民关于与宗主国关系的思考和论辩策略发生了转变,从诉诸“作为英国人的权利”,转而诉诸“人”的自然权利。在论辩策略的转变过程中,自然法的效用得以凸显,逐渐成为殖民地上层人士的主流话语。[26]美国早期文化史家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发现,在美国开国元勋的著作中,“关于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及瓦特尔的引用比比皆是”。[27]自然法还进入大学课堂中,国王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于1773年设立了自然法讲席。为此,约翰·亚当斯于1774年开列了一个国际法参考书目,涵盖了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巴贝拉克、洛克及哈灵顿等学者的经典著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推荐了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28]不过在那个时代,标准的国际法准则指南是瓦特尔的简明《国际法》手册。1775年12月,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为大陆会议找来了瓦特尔著作的最新版本。他致函该书编辑称:“在国家崛起之时,有必要经常参考国际法,(瓦特尔著作)的到来恰逢其时……已然成为大陆会议代表们手中的必备书籍。”[29]在瓦特尔的国际法理论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对美国革命领导人尤具吸引力,并为他们拿来所用:其一是对国家自由、独立及相互平等、依赖关系的强调,并以此作为国家存在及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前提条件。这一论述为殖民地的政治独立提供了哲学依据。其二是关于掳获、中立权利、战时禁运品等问题的论述,为规定外交政策与外交事务的具体操作提供了法律技术层面的基本参照。
1776年6月12日,大陆会议通过决议,任命了一个包括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在内的五人委员会,起草面向欧洲大国(首先是法国)的“条约计划”(Treaty Plan of 1776),亚当斯被指定担任这一重要文件的起草者。[30]1776年9月17日,大陆会议批准了“条约计划”。“条约计划”的最后文本共包括30项条款,前13条主要涉及拟定中的美法关系的具体问题。第14条至第30条则涉及自由贸易的一般性原则,尤其是航行自由和中立权利问题,体现在第26条和第27条当中。第26条规定,当两国中的一方处于战争中,而另一方为中立国时,中立国国民应该享有与交战国双方进行贸易的权利,不仅包括敌方港口与中立国港口之间的贸易。也包括敌方港口到另一敌方港口之间的贸易。在同一情形下,应赋予自由船只运载货物的自由,战时禁运品除外。这是对源自欧洲的“自由船只所载货物自由”原则的承认和接纳。第27条把战时禁运品严格限制为武器、弹药和马匹,并明确食品和海军用品不应被列为战时禁运品,表达了尽可能严格限制战时禁运品范围的主张。[31]以上条款显现了当时美国人心目中的“海洋自由”权利。
那么,“条约计划”所表达的海洋自由观,是亚当斯等人的原创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为一名成功的执业律师,亚当斯本人对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瓦特尔等自然法权威的理论十分熟悉,[32]但起草国际条约却非其所长——这项工作显然不能光靠自然法抽象理论,还必须参照体现在国际条约中的国家实践。当亚当斯开始起草条约计划时,在欧洲有着丰富人脉资源的富兰克林把一卷“刊印条约”放到其案头,并在一些条款边侧用铅笔做了标记,提醒亚当斯重点参考。亚当斯发现,“这些做了标记的条款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挑选出来的”,因此采纳了它们,并把另外一些他本人认为重要的条款一同纳入草稿。[33]
据美国外交史学者格雷格·林特(Gregg L. Lint)考证,亚当斯在起草“条约计划”的前13个条款时,还参考了两类材料:1705—1707年间出版的威廉三世统治时期的国际条约与1709年出版的海洋法条约。在起草第14条至第30条条款时,亚当斯主要参考了1760年出版的由亨利·埃德蒙兹(Henry Edmunds)和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编辑的与海洋事务相关的条约全集。“条约计划”的绝大部分条款,照搬了其中1655年英法和约、1686年美洲和约及1713年《乌特勒支条约》。[34]因此,基本可以断定,1776年“条约计划”中关于海上中立权利的规定,本质上并无特别之处,更谈不上是亚当斯的原创。
杰西·里夫斯在具体分析“条约计划”各项规定后指出,除了关于进口关税需在签约国之间统一设定的规定外,条约计划其他条款均未超出欧洲国家通行的商业惯例。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任何意义上讲,草案似乎都不应被视为完全根据条约所宣称的自然法理论拟订的”,而是与当时流行的以瓦特尔为代表的自然法规定有所出入,在某些方面宽松一些,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严格一些。[35]其实,进一步分析后不难发现,宽严驰紧的取舍标准无非在于使美国中立权利最大化。例如,在对战时禁运品的界定上,条约计划的清单是宽松的,仅包括武器、弹药和马匹,而瓦特尔的清单则更严格些,还包括海军装备和物资;在登临检查权利问题上,瓦特尔认为拒绝搜查的船只及所载货物仅从诉讼程序就可被判为合法战利品,条约计划虽承认登临和检查权,但把检查内容仅限于船只的文件。以上区别说明,亚当斯在制定条约计划时是十分务实的。
其实,亚当斯本人对于未来美国的国际角色及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性质有着长远思考和清晰规划,而“条约计划”得到大陆会议批准,则说明其思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所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将与所有欧洲国家维持永久和平,在它们未来发生的所有战争中保持完全中立。[36]基于中立主义国家的角色定位,他认为新国家与法国的“联盟”应该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无任何政治联系,不屈从于她的任何权力,不接受她派来的任何官员;二是无任何军事联系,不接受她派来的任何部队;三是只有商业联系,即缔结条约接受法国的船只进入我们的港口,让法国保证允许殖民地的船只进入其港口,为殖民地提供武器、大炮、硝石、火药、帆布和钢铁等。”[37]由此可见,在亚当斯的心目中,美国与“外国的联盟”是一种商业联盟,而非政治联盟,更非军事联盟。关于这一点,亚当斯本人解释道:“我不想向法国乞求任何政治联盟、军事援助或海军援助,我心中只有商业,只想同它缔结一项海运条约。”[38]对美国开国元勋一代而言,商业和外交政策是同义词,经济是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寻求与所有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是他们所认为的国家长远利益所在,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他们,在战争时期,只有保持中立,经济增长和繁荣才能得到最好保障。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认为,美国的中立可以作为与欧洲大国进行谈判并打开由后者控制的市场的潜在工具。基于对17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与英国在北美连年争战的解读,杰斐逊相信:美国拥有对欧洲而言堪称无价的、不可放弃的资源,战争时期更是如此。他尤其看好美国市场对于伦敦和巴黎的价值和吸引力,并由此得出一个观点:精心筹划并运用得当的中立政策,可以鼓励欧洲人“公正地对待”美国人。[39]
总之,尚处在革命中的美国国父们已经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预先确定了“中立国”的世界角色,尽管当时美国实际上处于交战国地位,但他们却念念不忘从中立国的角色出发,思考和定位未来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以追求中立权利的最大化。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美国外交史学家杰拉尔德·克拉菲尔德(Gerard Clarfield)断言,与“独立宣言”相比,“条约计划”的知名度要小得多,但在事实上“奠定了美国早期外交的基调”,[40]即捍卫中立国贸易自由和航行自由的权益。
从全球范围看,在维护中立国海上自由通商航行权利方面,当时作为交战一方的新生美利坚国并没有什么发言权。海洋自由观念体系的发展主要源于欧洲,美国革命前的年代如此,美国革命年代亦复如此。就世界海洋自由进程而言,在美国革命时期影响力更大的事件,当属1780年2月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倡导俄国、丹麦、瑞典等国发布的“武装中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Empress of Russia Regarding the Principles of Armed Neutrality)。该宣言就战时中立国海上商业保护提出了五项原则:第一,中立国船只可以在交战国各口岸之间和交战国沿海自由航行;第二,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第三,战时禁运品仅限于武器和战需品,不包括海军用品和造船木材;第四,只有进攻方国家在某一港口附近驻扎了足够多的舰只,并对开进去的船只构成明显危险时,封锁才有效;第五,在决定捕获品是否合法的问题上,上述原则将作为提出诉讼和作出判决的准则。[41]在这五项原则中,前两项已经包含在了美国与法国的友好通商条约中;第四项在当时还不足为虑;第五条只是对宣言效果的一种声明;唯有第三条关于战时禁运品的界定,引起了美国革命领导人的极大兴趣。因为相对于美法条约的规定,该条款关于战时禁运品的界定对中立国更有利。“武装中立宣言”因此激起了美国国父们推动中立权利向更为自由化方向发展的热情。
亚当斯相信,“武装中立宣言”提供了一个增进美国利益的难得机会。[42]基于这种理解,1780年4月14日,亚当斯致函大陆会议主席,提出了实现美国海洋观念国际化和自由化的建议,认为“全部废除战时禁运品规则将有利于人类的和平与幸福”。他指出:“随着人类理性的进步,以及人们对和平福祉的认识越发清晰、对追求战争荣耀的热情降低,所有中立国应被允许使用自己的船只运载物品,只要这些物品事实上不以交战国为目的地,即应获得普遍同意。”[43]这种观点不无国际法创新意义,若被普遍采纳,将意味着禁运品与其他货物、宗主国与其殖民地之间区别待遇的终结,从而把绝对的贸易自由建立在普世性国际法的强制基础之上,而非依赖于约定性条约。因此,后世美国政界人士称亚当斯这一主张为“美国人对中立贸易自由权利的第一项原创性贡献”,[44]将其视为美国外交政策原则之一的海上私人财产豁免主张的萌芽。
“海上私人财产免于捕获”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在国家间发生战争的状况下,交战国及中立国国民的普通贸易和非禁运品不应受到骚扰,享有不受国家军舰和武装私船阻断或缉拿的权利。该原则与格劳秀斯基于自然法的海洋自由观一脉相承,并与美国强调保护私有财产、重视公民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相联系,为美国历届政府屡屡重申、竭力追求,给美国的海洋自由观增添了自由主义的色彩,从而被称为“美国的原则”。[45]但是,这一原则的思想源头仍在欧洲,尤其可以追溯至法国启蒙思想家。
早在1748年,法国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利(Abbé de Mably)发表了《根据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至今的各项条约建立的欧洲国际法》,其中便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陆地上的私有财产在法律层面一般受到保护,以此类推,只有允许海上的私有财产享有类似的豁免权才是合理的。他写道:对于一支向平民发动战争并掠夺平民财物的军队,我们应该深恶痛绝,这是对公共权利和人类法律的侵犯。那么,我要质问的是,陆地上可耻的事情,怎么可能到了海上就变得正当或至少是被允许的呢?这就是所谓的“马布利类比”。这一类比尽管在事实经验和逻辑推导上均有瑕疵,但却风靡一时,推动了欧美国家关于海洋自由问题的思考。[46]
比马布利年少却更负盛名的卢梭在1762年发表了《社会契约论》,在前者的法理推论之外,为海上私人财产免于捕获的观念增添了一种政治哲学的支撑维度。他在谈及战争的理性基础和文明准则时写道:“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之中,个人与个人绝不是以人的资格,甚至也不是以公民的资格,而只是以士兵的资格,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他们绝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只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最后,只要我们在性质不同的事物之间不可能确定任何真正关系的话,一个国家就只能以别的国家为敌,而不能以人为敌。”[47]卢梭这一论述对战争中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界定的准确性似可商榷,但被后人称为“对海上私有财产掳获权发起舆论攻击的起点”。[48]
此外,美国革命领导人倡导海上私人财产豁免时,往往基于人道主义考量,但最早把人道主义及其组织贵格教会带到美国的著名人物,乃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创建者、来自英国的威廉·宾(William Penn)。[49]人道主义在美国革命时期,被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等人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他们海洋自由观念的思想资源之一。
在美国革命年代,一个被当今学者称为“跨大西洋文人共和国”(Transatlantic Republic of Letters)的作家、思想家和“爱国者”交流网络已经形成,为海洋自由观念的洲际流转提供了可能。该网络以法国—荷兰—美国为轴心,当时在欧洲执行外交使命的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斐逊自视为这一“共和国”的公民,并在其中扮演着十分活跃的角色。[50]其中,亚当斯出使法国期间曾与马布利有所交往,在返回北美后仍与马布利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51]如此一来,欧洲思想家的一些观点,如“海上私人财产免于捕获”等观念为美国开国元勋所熟悉并对他们产生影响,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不过,在推动该原则的发展与实践上,美国人并非毫无贡献——正是他们把这一观念带出了启蒙思想家的书斋,运用到国际关系现实之中,并最终转化为美国的国家外交政策原则。
1782年1月至1786年5月,美国与荷兰、瑞典、英国、葡萄牙、丹麦和普鲁士等国展开双边谈判,以期缔结保护中立权利的双边条约。在这些谈判中,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斐逊等人始终坚持“自由船所载货物自由”的原则底线,并以进一步限制战时禁运品范围为突破点,阐发源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海上私人财产免于捕获”观念,最终将其确立为国家外交政策原则,并落实在双边条约之中。这一历史进程较为复杂,本文仅选取其中三个重要节点加以阐述,以展示该时期美国海洋自由观念逐步发展与升华的进程。
第一个节点是美国与英国的和平谈判,标志着美国开始正式提出关于战时海上贸易政策的独特主张。1783年1月14日,富兰克林致信英国谈判代表,指出在公海抢劫商人的做法是古代海盗之遗毒,无论对施害者还是受害者,均贻祸无穷——前者会因挥霍非法所得而丧失勤劳习惯,增加社会犯罪的概率,最终自我毁灭;后者则意味着众多诚实商人及其家庭的无辜毁灭,给人类的共同利益带来浩劫。[52]显然,富兰克林对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的呼吁,是基于其一贯的人道主义观点。1783年6月1日,美国谈判代表向英方提出了八条“最终确定条款”,其中第四条和第五条分别阐述了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关于海上中立权利的观点:第四条指出,在缔约双方发生战争时,“所有商户和交易者都可以使用他们的非武装船只从事商业活动、交换不同产地的商品,允许他们不受干扰地自由通行”;任何缔约国不得授权武装私掠船夺取或摧毁此类贸易船只或中断此类商业活动。第五条规定,在缔约方之一与任何第三国发生战争时,“缔约一方驶往另一方的敌国的船只及所载物资,即便携带了武器、弹药和军事用品,也不得被视为禁运品予以没收或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但运输此类物品的船只可以被扣留,所载军事物资可被捕获者以全价购买。[53]显然,这两点主张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和人道主义考虑,带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二者结合在一起,其实质就是“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
但是,英国谈判方案中的互惠自由贸易主张与美国的海上自由贸易主张,在目的和宗旨上是根本对立的——前者旨在恢复战前美国附属其中的帝国体制,后者则以巩固新国家的中立为目的,这一矛盾决定了英美谈判失败的必然结局。美国追求“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的国际实践遭遇首次失利。
第二个节点是“1784年条约计划”(The Treaty Plan of 1784)出台,标志着“海上私人财产豁免”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原则地位的确立。1784年5月7日,邦联议会做出决议,要求美国驻巴黎公使继续推进与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丹麦、萨克森、汉堡、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热那亚、托斯卡纳、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撒丁岛和奥斯曼帝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并对计划中的条约提出了须认真遵循的九点规定,此即“1784年条约计划”。在海上自由贸易和中立权利事务上,该计划不仅全盘采纳了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的主张,而且进一步补充发展,提出了更为激进和自由化的海上中立权利主张,集中体现在条约计划的第四点、第五点和第六点规定中。
第四点规定涉及交战国的商人和贸易保护问题,提出在缔约双方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采取保护对方国家的商人、生产者的生命、财产和生产活动安全等诸多措施;强调商业活动不受干扰、自由进行的权利,规定“缔约的任何一方都不能雇佣私掠船去夺取或摧毁中立商船,或阻断其贸易活动”。第五点涉及对于禁运品的界定,规定在缔约方之一与任何第三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缔约一方驶往另一方的敌国的船只及所载物资,即便携带了武器、弹药和军事用品等物资,也不得被视为禁运品予以没收或造成个人财产损失”;船只可以被合法扣留,但需予以补偿。第六点涉及封锁的法律界定,规定港口封锁的标准是攻击国“使任何企图驶进或驶出该港口的船舶暴露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这是美国对封锁事项的首次表达。[54]总体而言,相较于“1776年条约计划”,“1784年条约计划”对中立权利的规定更加丰富和详细,更加强调对于海上私人财产的保护。
第三个节点是1785年9月,美国与普鲁士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标志着“海上私人财产豁免”的外交政策终于落地。该条约第12条规定,如果缔约一方与任何第三方发生战争,保持中立的缔约方臣民或国民与交战国的自由交往和商贸活动不应受到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应一如和平常态,中立方船只可以自由航行于交战国港口和海岸,自由船只所载货物自由,中立国所拥有的任何船只所运载的货物均为自由货物,即便这些货物可能属于另一缔约方的敌国。同样的自由原则应当延及至自由船只上的人员,即便他们可能是另一缔约方的敌人(除非其属于敌国现役军人)。第13条规定,如果缔约一方与任何第三方发生战争,缔约方可以依法拦截船只进行禁运品检查,但需要对这种拦截滞留所造成的损失给予合理赔偿;对于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不得没收,但可以依据目的地当前价格对这些物资进行全额购买;应同意船只自愿抛弃禁运品,此后该船只不应被带至任何港口,应允许其继续航行。第23条则基本全盘接受了“1784年条约计划”的第四点规定,强调了在缔约双方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对普通商业和商人的保护,强调所有从事商品交换的商船和贸易船只的自由通行不应受到阻碍,不得从事武装私掠活动,重申海上私人财产的豁免权。[55]
在缔约谈判前夕,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曾共同致信普鲁士外交代表,从推动国际法进步的角度,阐述两国应该支持条约中新原则的理由:“根据原始国际法,对施害者的惩罚方式是战争与灭绝;随着国际法的逐渐人性化,把施害者贬为奴隶而非处以极刑的做法得到承认;更进一步的步骤,则是建立交换战犯的制度;而另一种进步,则是尊重被征服(国家)的私人财产,并满足于获得统治权。为什么不对国际法加以持续改进……把这样的原则上升为未来的法律呢?——在以后的任何战争中,下列人等(耕种者、渔民、商人和交易员、工匠、机械师及医护人员)不应受到干扰,相反,他们应得到双方的保护,允许其从容地从事自己的工作。”[56]从这一论述中不难看出,美国与普鲁士友好通商条约中的新原则的实质,便是“海上私人财产豁免”。美国人如愿以偿,首次把该原则纳入国际条约当中。比米斯因此声称,1785年美国与普鲁士签订的条约是18世纪“最先进的条约”,就扩大中立权利而言,此前任何条约都难以望其项背。[57] “海上私人财产豁免”的美国海洋自由原则由此得以落实。与普鲁士的友好通商条约是首个依照“1784年条约计划”成功签署的双边条约,对后来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从学术上把“海洋自由”上升为美国外交政策原则地位,可能始于1905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约翰·B.摩尔(John Bassett Moore)出版的《美国外交的精神及成就》一书。在该书前言中,摩尔自陈撰书目的在于揭示美国堪称具有“世界大国”风格的外交政策的根源,表达一种旗帜鲜明的“爱国主义自豪感”。他认为,美国外交的精神实质是“自由”,对“海洋自由”的追求即是自由精神的展现;海洋自由原则,连同中立贸易权、门罗主义等原则一起,不仅支持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事业,而且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法制化和民主化,极大提升了美国外交的品格,使之与“自由和正义的事业携手并进”,成为美国的大国力量之源,是“始终如一、完完全全和最高意义上的‘世界大国’”的精神保障。[58]摩尔对“海洋自由”的美国外交政策原则言之凿凿的界定,对美国坚持“海洋自由”原则之世界意义的肯定,顺应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希望扮演更重要国际角色的民族主义心理,一经提出便风靡美国社会,确立了其独特地位,深刻影响了美国外交史学的叙事结构。显然,比米斯、萨维尔、拉帕波特等人从摩尔那里所接受的不仅是其外交政策研究的方法,而且包括其热情洋溢的民族主义笔法,“海洋自由”在美国外交政策原则中的地位因而被进一步神圣化。
本文对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美国开国先辈制定海上政策、推动国际条约签订的历史考察,挑战了这一民族主义叙事,揭示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思想根源而言,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原则的“海洋自由”并非美国革命一代人的原创,而是他们从欧洲“舶来”的——不仅“自由船只所载货物自由”原则早就载入了欧洲国际条约,甚至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也有着清晰可辨的欧洲思想根源。美国人的贡献,无非是把后者引入现实国际政治之中,并将其转化为国家外交政策原则。
不可否认,“自由船只所载货物自由”及“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尤其是后者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反映了启蒙理性、古典自由主义对美国国父一代人的影响。这是带有美国特色的海洋自由政策观念产生的思想基础。美国独立建立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美国国父一代成长于启蒙时代,深受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古典自由主义包含两项基本原则——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涵盖了天赋人权及政府必须保障个人自由等内容,而经济自由则要求政府保障个人的财产权,以及自由贸易和自由创办企业等经济发展的权利。[59]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是约翰·洛克与亚当·斯密。洛克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倡个人自由,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追求自由、平等和财产的权利,个人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在个人与政府间的关系上,洛克认为个人是第一位的,是本源与目的,社会和政府则是第二位的,是派生物与手段。洛克的著作提供了支撑美国建国元勋道德观的三大重要支柱,即自然或自然神明、财产权或对幸福的追求,以及作为理性人的个人的尊严。[60]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他在《国富论》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将增加国家财富。斯密还提倡个人自由和自由竞争,并且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活动。美国早期众多领导人与亚当·斯密处在同一个时代,对后者的理论并不陌生,认为“他的推理无可挑剔,合乎需要,符合我们的天性和愿望”。[61]《国富论》与美国《独立宣言》都发表于1776年,它们所宣称的理论观点被称为“1776年精神”,成为之后美国社会发展的信条,产生了持久的历史影响。《独立宣言》把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宣布为平等的个人之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言而喻的真理,这种观点显然受到了洛克和斯密的深刻影响。而战时海上私有财产豁免原则,正是《独立宣言》精神和自由贸易理论顺理成章、契合逻辑的衍生物。
同时必须看到,“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又是现实主义的产物。首先,它根植于美国浓厚的商业精神,反映了美国的商业利益诉求。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就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精神根深蒂固。杨生茂先生指出:“美国的商业精神直接影响和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使之以维护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为最终目标,以争取海上自由、发展中立贸易为主要内容。”[62]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商业资本发展至工业资本、信息资本,海上自由——包括为了实现和平贸易,美国公民、商品和船只可以自由地旅行至世界任何地方;所有海域、大洋和海峡,都不应该对美国船只封锁;必须压制海盗行为,在战时对待中立船只方面,外国必须遵循国际法——始终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主流。[63]此外,“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基于中立国的国家角色定位,反映了美国初创之际海军力量弱小的现实。基于对欧洲传统外交方式的反感和创造国际新秩序的革命理想,美国国父一代在革命时期就为新国家设定了中立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并把扩大商业以促进经济繁荣确定为国家利益的主流追求。美国立国之初,海军力量几乎不存在,商船群体也处在成长过程中,与英国、荷兰、法国等老牌海洋强国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为了保证本国海上贸易的自由进行,保持中立并提倡战时海上私人财产豁免权,实为当时作为海军小国的美国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一种精明的选择,有利于中立国在交战国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地大发战争之财。
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开国一代为了把他们关于国家间关系和中立权利的理想付诸实践,借鉴历史上欧洲国家订立双边条约的做法,开辟了把美国关于中立权利、海洋自由的理想和原则国际化的实践路径。格雷格·林特指出,美国国家实力的孱弱、对欧洲传统外交方式的疏离、扩大商业以促进经济繁荣的需要,以及对法律本身的有限认识,使得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成为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唯有此种政策能够实现利益与原则的统一,并形成国内共识。[64]的确,这一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表现在美国与法国、荷兰、瑞典和普鲁士等国达成了一批包含美国主张的双边友好通商条约,其结果便是“海上私人财产豁免”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原则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但是,“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说到底仍是一种海军弱国的政策,是基于中立国国家角色定位的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政策主张。及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军事实力急剧增强,马汉的“海权论”横空问世,强大海军建设稳步推进,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已经不能适应美国利益全球化的新形势,以及逐渐清晰的“世界领袖”的国际角色定位,其式微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经过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两任总统的艰难重塑,“航行自由”逐渐取代“海上私人财产豁免”,成为美国海洋自由诉求的政策口号,美国海洋自由政策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65]
作者简介:曲升,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史与世界海洋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与现代太平洋世界关系研究(1500—1900)”(LSYZD21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列强南海政策与中国海洋权益维护研究(1840—1949)”(2022&ZD232)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与世界海洋自由历史进程研究”(15BSS019)的阶段性成果。
[1] U. S.Department of Defense, “Freedom of Navigation (FON) Program, ” February 28, 2017, https://policy.defense.gov/Portals/11/DoD%20FON%20Program%20Summary%2016.pdf?ver=2017-03-03-141350-380, 2019-10-09.
[2] Armin Rappaport and William Earl Weeks, “Freedom of the Seas, ” in Alexander DeConde et al.ed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2,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2, pp.111, 121.
[3] J. M.Kenworthy and George Young,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London: Hutchinson & CO.Publishers LTD., 1928, p.15.
[4] Samuel Flagg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4th ed., New York: Henry Holt, 1955, p.875.
[5] Max Savelle, “Colonial Origins of American Diplomatic Principles,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3, No.3 (September 1934),pp.343-344.
[6]美国外交史学界对美国海洋自由观念起源问题的研究较为分散,除萨维尔的“殖民地起源”说外,格雷格·林特考察了约翰·亚当斯与1776年“条约计划”的起草问题,指出亚当斯对当时欧洲国家条约加以借鉴,参见Gregg L. Lintt,“John Adams on the Drafting of the Treaty Plan of 1776,” Diplomatic History,Vol.2,No.3(Summer 1978),pp.313-320.国内的美国外交史学界尚无专门探讨美国海洋自由观念根源的成果。在与该问题有一定相关性的研究中,王晓德教授的论文《一七七六年“条约计划”及其对美国早期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对1776年“条约计划”的思想意识根源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开国元勋的“美国例外论”和“不卷入欧洲政治纷争”思想的反映,但该文没有涉及“条约计划”所包含的海洋自由观念的根源问题;李文雯的博士论文《美国海洋航行自由原则的演变及其对美国海军力量发展的影响(美国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博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5年)第二章探讨了美国海洋航行自由原则的确立,但亦未深入考察该原则的根源所在。
[7]参见“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to the Senate, ” January 22, 191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7, Supplement1, The World War, Washington DC.: U. 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1, p.28;John D. Negroponte, “Who Will Protect Freedom of The Seas?”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6, No.2115 (October 1986), p.41.
[8] Joel Munsell, ed., The Hutchinson Papers, Vol.1, Albany: The Prince Society, 1865, p.143.
[9] Max Savelle, “Colonial Origins of American Diplomatic Principles, ” pp.343-344.
[10]参见Hugo Grotius, The Free Sea, translated by Richard Hakluyt with William Welwod’s critique and Grotius’s reply,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Armitage, Indianapolis, Indiana: Liberty Fund, Inc., 2004.
[11]王晓德:《试论务实传统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17、119页。
[12]刘泽荣:《领海法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8页。
[13]参见Pitman Potter,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in History, Law and Politic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4, pp.94-95.
[14] Jesse S. Reeves, “The Influence of the Law of Nature upo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 No.3 (July 1909), pp.550-551.
[15]当时有许多殖民地的章程都授予美洲人以“英国人的权利”,参见[美]托马斯·帕特森著,顾肃、吕建高译:《美国政治文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16] Douglas Owen, “Capture at Sea: Modern Conditions and the Ancient Prize Laws, ”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Vol.49, No.2(July 1905), p.1236.
[17] Francis R. Stark,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ering and the Declaration of Paris, ” 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Vol.8, No.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897, p.69.
[18] John Franklin Jameson, ed.,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 Illustrative Document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3, p.xi.
[19]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ticle I, Section Ⅷ, https://constitution.congress.gov/constitution/, 2019-07-18.
[20]参见Nicholas Parrillo, “The DePrivatization of American Warfare: How the U. S.Government Used, Regulated, and Ultimately Abandoned Privateer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Yale Journal of Law & the Humanities, Vol.19, No.1 (Winter 2007), pp.74-95.
[21] Philip C. Jessup and Francis Deák,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Law of Neutral Rights,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46, No.4 (December 1931), pp.497-499.
[22] “Marine Treaty in 1674, ” in Extracts, from the Several Treaties Subsisting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Other Kingdoms and States: of Such Articles and Clauses, as Relate to the Duty and Conduct of the Commanders of His Majesty's Ships of War, the Third Edition, London, 1758, pp.132-141.
[23] “Treaty of Navigation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Crowns of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Concluded at Utrecht, March 31, 1713, ” in Extracts, from the Several Treaties Subsisting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Other Kingdoms and States: of Such Articles and Clauses, as Relate to the Duty and Conduct of the Commanders of His Majesty's Ships of War, pp.43-59.
[24] O.H.Mootham, “The Doctrine of Continuous Voyage, 1756-1815, ”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 (1927), p.65.
[25] [美]托马斯·本德著,孙琇译:《万邦一国: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1页。
[26] Jesse S. Reeves, “The Influence of the Law of Nature upo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 p. 551.
[27] Perry Miller, 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n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5, pp.109, 145-146.
[28] Mark Weston Janis, America and the Law of Nations, 1776-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4-25.
[29] [美]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25页;Mark Weston Janis, America and the Law of Nations, 1776-1939, p.25.
[30] John Adams, “Autobiography, ” in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Seco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Vol.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51, p.52.
[31] Worthington C. Ford, ed.,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1774-1789, Vol.5, Washington: U. 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 pp.768-779.
[32]例如在1773年1月26日和3月2日代表马萨诸塞州众议院写给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书面答复中,亚当斯多次提到并引用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瓦特尔的言论,以论证其议会对殖民地权力有限论。参见Robert J. Taylor, et al., eds.,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320-321, 327, 330, 331, 335, 344-345.
[33]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The Works of John Adams, Vol.2,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50, p.516.
[34] Gregg L. Lint, “John Adams on the Drafting of the Treaty Plan of 1776, ” pp.313-320.
[35] Jesse S. Reeves, “The Influence of the Law of Nature upo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 p. 558.
[36]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The Works of John Adams, Vol.1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56, p.269.
[37]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The Works of John Adams, Vol.2, pp.488-489.
[38] “John Adams to John Winthrop, ” Philadelphia, June 23, 1776, in Edmund Burnett, ed., Letters of Member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Vol.1, Washington, DC.: The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21, p.502.
[39] James R. Sofka, “The Jeffersonian Idea of National Security: Commerce, the Atlantic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Barbary War, 1785-1805, ” Diplomatic History, Vol.21, No.4 (Fall 1997), pp.520-524;James R. Sofka, “American Neutral Rights Reappraised: Identity or Interest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Early Republic?”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6, No.4 (October 2000), p.608.
[40] Gerard Clarfield, “John Adams: The Marketpla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52, No.3 (September 1979), p.348.
[41] “John Adams to the President of Congress, ” April 10, 1780, in Francis Wharton, ed.,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9, pp.606-608.
[42] “John Adams to Digges, ” May 13, 1780;“John Adams to the President of Congress, ” May 20, 1780, in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3, pp.676-677, 693-696.
[43] “The Peace Commissioner (J.Adams)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Huntington), ” Paris, April 14, 1780, in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pp.612-614.
[44] Carlton Savag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Maritime Commerce in War, Vol.Ⅰ, 1776-1914,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4, p.4.
[45] Edwards S. Corwin,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209, No.758 (1919), p.34;John H. Latané,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84 (July 1919), p.163.
[46]参见William ArnoldFoster, The New Freedom of the Seas, London: Methuen & Co.Ltd., 1942, p.33.
[47]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页。
[48] William Arnold-Foster, The New Freedom of the Seas, p.34.
[49]参见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6页。
[50] Carine Lounissi, “French Writer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1780s: A Republican Moment?” in Maria O’Malley, et al, eds., Beyond 1776: Globalizing the Cultur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8, pp.78-85.
[51] A.Owen Aldridge, “John Adams Meets the Abbé Mably, ” Dalhousie French Studies, Vol.52 (Fall 2000), pp.88-99.
[52] “Franklin to Oswald, ” Passy, January 14, 1783, in Francis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6,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9, p.210.
[53] “Propositions Made by Commissioners to David Hartley for the Definitive Treaty, ” June 1, 1783, in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6, pp.470-471.
[54] “Treaty Plan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May 7, 1784, ” in Gaillard Hunt, ed.,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1774-1789, Vol.26,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8, pp.357-362.
[55] “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ussia, September 10, 1785, ” in Hunter Miller, ed.,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2,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1, pp.162-183.
[56] “Reasons in Support of the New Proposed Articles in the Treaties of Commerce, ” November 10, 1784, in Th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3-1789, Vol.1, pp.532-533.
[57] Samuel Flagg Bemis,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Knop, 1949, p.43.
[58] John Bassett Moore, American Diplomacy: Its Spirit and Achievemen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05, pp.63, 251-252, 266.
[59]钱满素:《前沿》,《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页。
[60]参见Thomas L. Pangle, The Spirit of Modern Republicanism: The Moral Vision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ock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2;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4页。
[61]参见Alfred E. Eckes, Jr., Opening America's Market: U. S.Foreign Trade Policy Since 17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p.4;王晓德:《美国开国先辈们的自由贸易思想探析》,《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第25页。
[62]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63]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13页。
[64] Gregg L. Lin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Law of Nations, 1776-1789, ” Diplomatic History, Vol.1, No.1 (Winter 1977), p.33.
[65]相关内容可参见曲升:《从海洋自由到海洋霸权:威尔逊海洋政策构想的转变》,《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曲升:《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对美国海洋自由观的重塑及其历史影响》,《世界历史》,2022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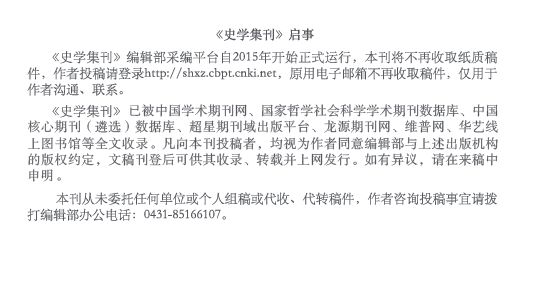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史学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