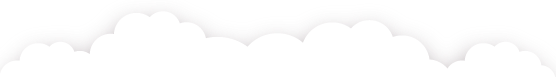
近代民间禁毒组织的国际参与:
以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际联盟的交流为中心
黄运
摘要:作为近代重要的民间禁毒组织,中华国民拒毒会在国内发动禁毒运动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禁毒事业,主要表现为与国联的持续交流。大体而论,二者的交流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前后。中华国民拒毒会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召开而成立,与国联在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期间有所交流,但是中华国民拒毒会因为对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失望而在会后对国联有所疏离。第二次在北京政府末期的1927年。是年,国联承认中华国民拒毒会为可与其沟通禁毒事务的中国民间组织,且双方曾多次交换出版物。第三次在1929年,国联副秘书长约瑟夫 · 爱文诺访华和国联派出远东鸦片问题调查团。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的交流,受到其与民国政府和国联三者动态关系的影响。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国联禁毒主张的差异,导致它与国联在交流的同时存在持续张力,也注定其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压而走向解散,与国联的交流也因之结束。
关键词:中华国民拒毒会 国际联盟 鸦片咨询委员会 南京国民政府 国际禁毒
19世纪中后期,反对鸦片吸食的禁毒话语在中国酝酿,民间禁毒组织也陆续成立。由清末至民初,民间禁毒组织的发展大致呈现两种趋势:一是逐渐由区域性转向全国性;二是逐渐去殖民化,外国人在这些组织中的影响日益式微。中华国民拒毒会于1924年成立,便是这一趋势的体现。该会成立后,不仅动员民众发起禁毒运动,呼吁政府勠力禁毒,而且积极参与国际禁毒事业。学界对中华国民拒毒会已有所研究,但是对其参与国际禁毒之事鲜有分析,例如其与国联的交往。学界注意到中华国民拒毒会因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召开而成立,但是对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之后,该会与国际联盟的交往未做探讨。中华国民拒毒会存在于1924至1937年,其与国际联盟的交往需要置于更长的时段内考察,方能更为趋近实相地呈现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国联的交流,展现近代中国民间禁毒组织参与国际禁毒的复杂面相,从而丰富中国近代禁毒史研究和国际禁毒史研究。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国联档案、民国政府《外交公报》和《外交部公报》、《拒毒月刊》和《拒毒季刊》(Opium: A World Problem)等资料,分析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国联的交流,双方之间互动又充满张力的变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背后的原因。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国联的交流,是管窥近代中国禁毒史和国际禁毒史的新视角。从民间组织而非政府层面参与国际禁毒的维度来探究20世纪国际禁毒体系的创构问题,有利于重思这一过程中的非政府因素和复线的国际禁毒史,并借由禁毒问题探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近年,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禁毒体系,越来越多地受到非政府组织(NGO)的影响。重审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的交往,有助于我们思考非政府组织和当前处于变革中的国际禁毒体系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政府和非政府力量,来更有效地治理国际毒品问题。
一、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前后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的交流
国联成立后,对禁毒问题颇有关注,并成立专门机构来应对。1921年2月,国联决定成立鸦片咨询委员会,该会于1921年5月召开第一届会议,并逐渐发展为国联重要的禁毒机构。1923年5—6月,鸦片咨询委员会召开第五届会议,提议国联行政院邀请相关国家召开国际会议,期望就实施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达成协议。随后,国联大会和行政院批准了这一提议。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召开,成为继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和1911—1914年海牙国际鸦片会议之后,20世纪国际禁毒史上的重要事件。
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对于彼时国内热心禁毒的民众多有鼓舞。在此氛围影响下,总部位于上海的30余个社会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华国民拒毒会。该会在成立之初,即定下注重国际联络的工作目标,首要对象就是国联。1924年8月 23日,该会第一届董事会会议议决,派蔡元培、伍连德和顾子仁三人参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9月6日,在第一届董干事联席会上,该会议决,由许建屏等五人组成小组,起草说帖,以提交给将于年底召开的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9月19日,董干事联席会第三次会议,议决拟向国联提交的说帖。9月26日,董干事联席会第四次会议,议决“修正向日内瓦大会暨北洋政府请愿文”。10月3日,董干事联席会第五次会议,议决“推派钟可托起草致日内瓦国联鸦片股股长函”。10月17日,董干事联会第七次会议,又议决推派罗运炎等人为起草委员会,“拟电国际禁烟大会表示国人拒毒诚意”。由此可见,中华国民拒毒会在其成立之初,将准备参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和联络国联作为重要工作之一。
致力于联络国际社会以推进中国禁毒运动的中华国民拒毒会,起初并未受到其他民间禁毒组织的广泛认可。例如,万国拒土会在允诺合作的同时,极力与其划清各自的领地。1924年8月23日,该会第一届董事会曾议决,函请万国拒土会等组织与其合作。10月15日,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霍德进(H. T. Hodgkin)赴京公干,中华国民拒毒会托其与万国拒土会商讨两个组织将来合作的事宜。万国拒土会就双方的合作提出议案七项。主要内容是,其愿与中华国民拒毒会工作,且愿意将其地方分会并入中华国民拒毒会。万国拒毒会的出版物,中华国民拒毒会可出资购买。与中外政府的联络,由双方共同协商开展。10月31日,中华国民拒毒会董干事联席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万国拒土会的提议。虽然讨论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从事后双方的活动来看,此次讨论的合作议案并未落实。双方意在单独行动,无意于受对方的牵制。此时中华国民拒毒会刚成立不久,尚难以做到无视已运作数年的万国拒土会。11月28日,该会董干事联席会第十三次会议就曾议决,“函请万国拒土会相机协助本会提交北洋政府之请愿书”。
前述中华国民拒毒会在第一次董干事联席会上提出的拟具说帖致国联,虽然说帖迅即拟定,但是未能很快送达国联。中华国民拒毒会希望能由参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中国官方代表将说帖转交给国联,但北京政府内务部回复称,因为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会期迫近,为参加该会准备的各项文件,内务部已交中国代表核阅,中华国民拒毒会的说帖已来不及交给即将参会的中国代表。虽然不能帮中华国民拒毒会转递说帖,内务部希望该会所派民间 代表,能够与官方代表“就近接洽,以收内外相济之效”。
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前后,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的交流主要由顾子仁实现,有时是直接联络,有时是以中国官方代表为中介进行沟通。这一阶段交流的主要目的,除了向国际社会显示中国民间禁毒努力,充当中国官方参会代表的后援外,也包括利用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召开之机,进行自我宣传,以期得到北京政府和国联的认可,从而实现自身发展。前文述及,该会拟派三位代表—蔡元培、伍连德和顾子仁。事实上,主要工作由顾子仁开展。这或许是因为顾子仁在国际工作方面经验丰富,且在三人中资历最浅。该会选蔡元培为国民代表参加会议,或因其社会威望,尤其是他“国联同志会理事”的身份,且其人在欧陆,方便就近办事。然而蔡元培1923年春不满教育总长彭允麟而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于同年秋季赴欧洲,目的是从事研究和著述。虽然伍连德也被选为代表,但他似乎并未参会。因为顾子仁与国联鸦片股股长瑞秋 · 克劳迪(Rachel Crowdy)第一次通信时,顾氏称中华国民拒毒会派出的代表是蔡元培和他自己,而未提伍连德。

顾子仁
在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召开之前,顾子仁已与国联开始了联络。1924年10月14日,已在日内瓦的顾子仁电告中华国民拒毒会,请后者提供“本会大纲、暨经过情形及国民代表之任务”,以准备提交给日内瓦鸦片会议的报告。11月6日,由芬兰返回日内瓦途中的顾子仁致函克劳迪,告知他将于12日抵达日内瓦,问后者能否与自己面谈半个小时。同时,他希望克劳迪询问会议主席,希望允许自己参加大会并发言。顾子仁在信函中简单介绍了中华国民拒毒会,并强调了国际合作禁毒的重要性。11月8日,克劳迪回复顾子仁,同意就其参会并发言一事询问大会主席,并且告知顾子仁可以在13日下午两点半与其面谈半小时。11月14日,顾子仁又致函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二次会议秘书处,表明自己是中华国民拒毒会所派代表,要求参加两次大会并在第二次大会发言。当日,秘书处克劳迪即复函顾子仁,称其会将信函转交大会主席,一有消息即回复。
最终,顾子仁如愿以偿。1924年11月,他在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发表了演说,介绍了中华国民拒毒会概况,以及该会重点关注的四个问题:罂粟种植;鸦片吸食和使用吗啡及可卡因等物质;麻醉品非法贸易;海外华人吸食鸦片。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1月3日开始,原计划于11月17日结束,随后召开第二次会议。但由于会议期间争论颇多,国联只好在11月17日第一次会议尚未结束时即开始第二次会议。12月11日,顾子仁致函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二次会议主席赫卢夫 · 扎赫勒(Herluf Zahle),表达了他对第一次会议协议草案的失望,因为它并没有以清晰的措辞规定各国该如何落实1912年《海牙国际鸦片公约》第二章的内容。次日,扎赫勒复函告知顾子仁,这是第一次大会要处理的事情,而自己是第二次大会的主席,他会把顾的信件转交给第一次大会的主席。
在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期间,顾子仁一方面直接与国联,尤其是其下属机构鸦片股联络,同时还以中国官方代表为中介加强与国联的联系。在中华国民拒毒会不为国联熟知之时,这一渠道显得尤为重要,北京政府的背书有利于刚成立不久的中华国民拒毒会取得国联的认可。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召开期间,顾子仁曾多次致函中国官方参会代表施肇基。1924年11月12日,顾子仁致函施肇基,告知后者中华国民拒毒会的活动已经扩展到24个省份,600个城市的30万人已经保证为铲除鸦片贡献力量。此处顾氏或有言过其实之处,他意在向官方代表说明,有民间禁毒组织愿为后援。11月15日,顾子仁再函施肇基,并请其将函件于大会上公开。该函主要内容,是呼吁列强尽快停止在亚洲属地上准许鸦片吸食的政策,并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在大会发言。当日,施肇基在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一届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宣读了顾子仁的信函,主要内容是中华国民拒毒会开展的民众拒毒运动。
作为中华国民拒毒会的国民代表,顾子仁理应待会议结束后再离会。然而不知何故,1924年12月19日,顾子仁致函克劳迪,告知后者他无法继续参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二次会议,将由梁敬錞接替。此外,顾子仁还请克劳迪将会议相关材料寄送至梁敬錞处,并请其令国联分发部将国联鸦片股印刷品尤其是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二次会议的报告邮寄至中华国民拒毒会位于上海的总部。12月30日,克劳迪告知顾子仁,很遗憾他无法继续参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并已将梁敬錞备注为中华国民拒毒会的代表。顾子仁提前离开会议,或与他不满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协议草案有关。此外,参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并非顾子仁前往欧陆的首要目的。其本职工作是全国青年会副总干事,也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干事。他1924年6月出发前往欧陆的首要目的是考察欧美诸国的教育问题。过于繁杂的参会劳务或许也是他离会的一个原因,一再延长的会期已经占据其太多时间。不过,辞去代表身份的顾子仁依然与中华国民拒毒会保持联络。
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前后,位于上海的中华国民拒毒会总部也一直有所活动。它时而联络该会在日内瓦的代表,时而经由中国官方代表和国联联系,与其所派代表和中国官方与会代表互为策应。前述顾子仁告知施肇基中华国民拒毒会的发展情况,就来自该会上海总部发至日内瓦的电报。1924年11月17日,中华国民拒毒会总干事钟可托曾致电顾子仁和施肇基,在电文中概述了三件事:1300个组织代表两百万民众签署了请愿书;和平会议纳入了禁烟问题;内政部正在安排会议,与拒毒会全面合作。电文意在说明当时中国国内民众热心禁毒,政府也大为支持。北京政府派往日内瓦的代表团,除了首席代表施肇基,另有朱兆莘、王广圻和外籍顾问韦罗璧(W. W. Willoughby)。为了声援中国参会,中华国民拒毒会总部曾邮寄该会出版物给朱兆莘和王广圻,受到二人的赞许和鼓励。

朱兆莘
在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英美两国难以就熟鸦片管制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导致中美两国代表提前退会以示抗议,中华国民拒毒会也因此对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深为不满。会上,英国同意美国代表提出的国际社会要逐渐抑制熟鸦片使用的提议,但是要等到中国抑制了国内鸦片的非法生产和贸易之后。倘若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英国同意在15年的期限内逐渐抑制熟鸦片的使用。美国同意将原先提议的10年改为15年,但是要求立即执行,而不是等中国解决其国内鸦片非法生产和贸易的问题之后。双方因此争执不下。美国代表于2月6日退出会议,中国代表随后也愤而离会。中美两国代表的提前离会,是英法等殖民大国操纵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国际禁毒政治化的表征。如张勇安所论,“‘弱国联’和‘强国家’的国际格局,注定大国才是左右国际公约议定的主要力量”。顾子仁会后评述:“因禁烟有无效果,非但中国应负其责。即他国亦难辞其咎。何以独将中国提出作为鸦片之罪魁。”
虽然对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颇为失望,也在报刊对国联多有指责,但领导国内民间禁毒和参与国际禁毒毕竟是中华国民拒毒会的既定目标,所以在疏远国联之时,该会依然注意维护与北京政府外交人员的联络。而且该会总部设在彼时的通商大埠上海,是众多政商名流出入境必经之地,有利于其开展社交。1925年4月6日,中华国民拒毒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议决:“我国出席禁烟大会代表施公使闻将于五月间回国,本会应筹备欢迎,并请以一个月功夫,前赴各省宣传拒毒事业。”后来,中华国民拒毒会还邀请施肇基担任名誉副会长。1926年5月,中华国民拒毒会出版首期《拒毒月刊》,又邀请顾维钧题刊头“拒毒”二字。尔后,朱兆莘等人也曾为其刊物题字。凡此种种活动,为中华国民拒毒会恢复和国联的直接交流做了铺垫。
二、北京政府末期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的交流
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后,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国联的联络短期沉寂,后又逐渐恢复,并在1927年迎来重要发展。是年,国联正式承认中华国民拒毒会为可与其沟通禁毒事务的中国组织,之后双方多次联络并交换出版物。1927年3月22日,克劳迪请国联分发部沙雷尔先生(M. Charrere)将鸦片问题相关的出版物免费邮寄给十个组织,其中便有中华国民拒毒会。1927年4月12日,钟可托致函告知克劳迪,他从中国驻国联代表朱兆莘处得知,国联已正式承认中华国民拒毒会为可与之沟通禁毒事务的中国组织。钟可托还问克劳迪,可否给中华国民拒毒会邮寄1925年以来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的年会记录和国联大会第五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及鸦片咨询委员会的出版物和油印件清单。5月6日,克劳迪称其收到钟可托的函件,并已安排分发部邮寄他所请求的出版物;但钟可托所咨询的会议记录尚未完成,所以暂时无法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对中华国民拒毒会的承认,让后者备受鼓舞,其出版英文刊物的计划也快速推进。1926年10月20—22日,中华国民拒毒会第二届年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为中华国民拒毒会成员的中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提议:“筹划数种外国文字(至少须有英文一种)之出版物,将吾国人民铲除烟毒之决心与夫外籍奸商输运毒品之黑幕,剀切宣传,以明真相,引起国际间之了解与同情。”受到国联承认后,中华国民拒毒会认为,自此“对于国外宣传之责任,更为重大”。1927年7月,该会开始出版英文《拒毒季刊》,名为Opium: A World Problem。其中文刊物《拒毒月刊》的英文名为Opium: A National Issue。“Problem”和“Issue”之别,折射出该会认为中国的鸦片问题起于外因的心境。《拒毒季刊》的编辑是钟可托、戴秉衡和黄嘉惠。三人也是该刊作者,其中尤以戴秉衡撰文最多。关于出版《拒毒季刊》的宗旨,该会曾刊文指出:“鸦片不但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的问题,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将毒物不住的输入中国,一方面又在痛骂中国烟禁的废弛,强词夺理,到处做不利于中国的反宣传”。

《拒毒月刊》,创刊于1926年
《拒毒季刊》的内容体现了这一宗旨。该刊每期52页,各期版式有相同之处,每期内封皆刊登该会工作目标、主要领导者及组成该会的30余个团体,随后是目录,目录页之后是“林则徐公拒毒遗训”和林则徐全身像,或者是孙中山拒毒遗训及其头像。每期封底登载该会章程和该会中文出版物清单。其余内容各期有别,主要内容是中华国民拒毒会上一季度的活动、国内毒情、国内禁毒运动及其社会反响、国际禁毒新闻。中华国民拒毒会中文刊物《拒毒月刊》也曾刊文向读者推荐介绍《拒毒季刊》。《拒毒季刊》上也有对《拒毒月刊》的介绍。如此,以收中英文出版物互相宣传之效。
《拒毒季刊》的出版,无疑有利于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国联的交流,因为国联的官方语言是英法两语。国联承认中华国民拒毒会后,不仅乐于接收其《拒毒季刊》,而且希望该会能再派代表前往日内瓦。1927年8月2日,克劳迪在致中华国民拒毒会的信函中,告知鸦片咨询委员会下一届年会将于9月28日召开,希望中华国民拒毒会派员参加。8月25日,戴秉衡复函鸦片顾问委员会,称该会已经收到其寄送的国联出版物,并寄出中华国民拒毒会出版的首期《拒毒季刊》三份。此外,克劳迪还希望中华国民拒毒会能够就9月28日将要召开的鸦片顾问委员会年会发表一些看法。后该会总干事钟可托回复克劳迪,确认已收到鸦片咨询委员会将于9月28日召开会议的消息,并告知后者,因时间紧迫,路途遥远,无法派员参会。钟可托随函附上克劳迪询问的首期《拒毒季刊》20份。9月27日,克劳迪回复钟可托,称其已经收到三份,待20份收齐后,她将分发给鸦片咨询委员会成员。
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的交流之所以在1927年得以推进,部分因为该会经过三年的发展已明显壮大。至1926年,它已在全国成立了两百多个分会,而且在组织上进行了改革。1926年,该会第二届年会决议组织七组委员会,其中之一为“国际组”,为后续的国际交流奠定了组织基础。除此之外,1927年的中国处于政权鼎革之际,国联和中国官方的沟通因局势动荡而受阻。表现之一是,从1925年2月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结束至1927年底,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召开的四届会议,中国官方代表只参加了两届(第八、九届),而且四届之中有三届会议中国政府都未提交报告。表现之二是,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顾问莱尔(L. A. Lyall)曾建议该委员会联络南京国民政府,以取得中国鸦片生产相关数据。虽然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因有所顾虑而未表态,但此事表明,对国联而言,当时作为民间组织的中华国民拒毒会所能提供的中国烟毒情况有一定价值,这也是双方交流得以推动的基础。北京政府外交人员对中华国民拒毒会的支持,是该会能够得到国联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前文述及,该会虽然因不满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结果而对国联有所疏离,但依然注意与北京政府外交人员保持联络。中华国民拒毒会注重及时向中国驻国联外交人员汇报该会的活动。1927年1月,朱兆莘在给中华国民拒毒会的函中告知,他将在下一届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中华国民拒毒会第二届年会议决的“四年进行计划”,“并建议国联承认中华国民拒毒会为中华民族唯一之拒毒团体,与国联禁烟委员会互通消息,以利拒毒事功之进行”。是月20日,中国代表向鸦片顾问委员会转交了中华国民拒毒会的工作计划,鸦片顾问委员会将其分发给该委员会其他成员国代表和顾问,为中华国民拒毒会做了宣传。中华国民拒毒会在此工作计划“民众外交”部分中指出,该会将“为下一届国际鸦片会议的召开做准备,并与其他国家类似的禁烟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同年,美国国民外交大会代表梅海白周游列国途经上海时,中华国民拒毒会曾设宴欢迎并与之交流禁毒工作。1927年10月,中华国民拒毒会第三届拒毒运动周开展之后,曾向朱兆莘汇报。朱兆莘向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介绍了拒毒周的情况。
不过,虽然该会在1927年初得到国联的承认,但是二者的毒品管制理念有很大差异。中华国民拒毒会视鸦片等毒品为洪水猛兽,主张严厉禁绝。而国联主张专卖与缓禁的政策。除此之外,该会以中国民间禁毒代表自居,对于国联指责中国烟毒情况,多有反对。在这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下,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虽然有持续交流,但是二者之间也一直存在张力。这一实相,在1928—1929年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事件中表现得愈加明显。
三、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与中华国民拒毒会的因应
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的交流,受到其与国民政府变动关系的影响。该会对国民政府一度抱有深切希望。1927年,国民政府迁汉口,再迁南京,中华国民拒毒会在这一过程中曾屡次拜谒国民政府官员请求禁毒。不过,国民政府对此做出较为积极的反应,是在奠都南京之后,在此之前的国民政府,如中华国民拒毒会所言,“戎马倥偬,谈不到此种内政”。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该会曾拜访国府要人伍朝枢等人,请求国民政府禁毒。并呈请国民政府设立“中央禁烟委员会”,以推行中华国民拒毒会所提各项禁毒建议。
在中华国民拒毒会等民间团体发起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5次政治会议议决,限期三年,分年分区肃清国内鸦片。并在财政部设禁烟处,各县分设禁烟局及戒烟药品专卖处,由财政部颁布《禁烟章程》13条。自1928年起,限三年内鸦片烟完全禁绝。鉴于国民政府有此三年禁绝计划,中华国民拒毒会认为“民众拒毒团体应有所表示”,于1927年8月17日在沪召开“各团体代表联席禁烟会议”,国民政府财政部禁烟处处长李基鸿受邀赴会,报告了禁烟处的八项禁烟计划。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应中华国民拒毒会的请愿,设立中央禁烟委员会,并于11月召开第一届全国禁烟会议。中华国民拒毒会主席李登辉和总干事钟可托也在全国禁烟会议中担任职务。尚处执政初期的南京国民政府,需要取得更多社会支持,这是其愿与中华国民拒毒会等民间组织合作的主要原因。
中华国民拒毒会在极力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厉行禁毒的同时,还密切关注国联关于禁毒事务的动态,并通过当时的报刊及该会出版物进行宣传,以营造禁毒舆论。《拒毒月刊》每期皆设有国际禁毒消息栏目,对国际禁毒尤其是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的动态进行报道。除了定期利用出版物报道外,该会还在例行的拒毒周运动中对包括国联禁毒事务在内的国际禁毒动态予以关注和宣传。中华国民拒毒会的拒毒周运动在总部上海开展得尤为热烈,每个拒毒周运动的最后一天是国际日,意在促使民众和政府关注国际禁毒事务动态,培育拒毒运动的民众基础。
中华国民拒毒会在密切关注和及时报道国联禁毒动态的同时,还积极尝试与之联络。1927年10月2—8日,中华国民拒毒会在上海开展拒毒,国际日当天,该会不仅向民众宣传了国际禁毒形势,还拟就一份向国联禁烟委员会请愿的提案。主要内容是请国联责成各国政府限期肃清烟毒,取消鸦片专卖政策,禁止医药和科学用途之外的麻醉品生产;请国联设立毒物化验所,化验各国销售之毒物;将各国私贩麻醉药品的事实全部公开。该会后电国联禁烟委员会,告知其开展拒毒运动的情况,并呼吁国联“限制各国麻醉毒药之产量,至科学及医药用度,以竟敝国民众拒毒之全功”。该会自认是中国民间禁毒的代表,代表民众拒毒声音,与国联联络禁毒事务亦是其职责所在。1927年初国联承认其为可与之沟通禁毒事务的中国组织后,该会更受鼓舞。它希望国联能够秉持正义,对英国等殖民列强以毒祸华的行为加以谴责,同时调整国际禁毒政策。
然而中华国民拒毒会的不满和批评,并不能对国联产生明显影响。20世纪20年代,国联禁毒政策的走向由英法等殖民帝国主导。中国政府在国联禁毒政策形成过程中尚且人微言轻,遑论一个民间禁毒组织。此外,虽然国联承认中华国民拒毒会为可与之沟通禁毒事务的中国组织,但当时另一个民间禁毒组织万国拒土会也在向国联提供关于中国烟毒情形的信息。和中华国民拒毒会不同的是,万国拒土会虽然主要在华活动,但其主要成员是外国人,且以国际组织自居,对中国政府的禁政多有尖锐批评。万国拒土会提供给国联的信息也常常与中国官方和中华国民拒毒会提供的信息相抵牾。这种抵牾也降低了中华国民拒毒会对国联禁毒政策的影响。中华国民拒毒会之于国联禁毒政策的影响微弱这一事实,在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所谓远东鸦片调查团事件,缘起于1928年9月国联第九届大会上,英国代表建议国联派出一个调查团,前往亚洲调查鸦片问题,为下一届国际鸦片会议做准备。该提议不仅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让中华国民拒毒会对国联的恶感复生。中华国民拒毒会致函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称国联的用意“无非为寻求我国烟禁废弛之证据,以为干涉我国内政之张本,且为暴露我国劣状于世界,使明年之国际禁烟大会中我们再成为众矢之的”。中华国民拒毒会吁请南京国民政府反对国联此举,其调查需将区域扩展至世界各国,不可专限于远东;调查的范围要包括麻醉毒品,不可专限于鸦片;调查团应有中国代表。王正廷复函中华国民拒毒会,告知后者此事尚未议决,外交部已电中国代表王景岐,要其在行政院和大会据理力争,并称国联已经决定把其他毒品也纳入调查范围。
中华国民拒毒会还利用当时的报刊,包括该会的中英文出版物,刊文对国联决议派遣远东鸦片调查团表示抗议。其反对的理由是,“该团之目的,仅查鸦片,不查麻醉毒品。仅查远东,不及其他各国。仅有他国代表,而无我国代表”。而且,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是在浪费国联经费。该会《拒毒季刊》主笔戴秉衡还撰写英文小册子《远东殖民地之鸦片毒祸》和《远东调查团与鸦片专卖》,“对于列强在远东各殖民地公开吸烟的问题加以严正的讨论,尤其注重远东鸦片调查团组织的不合理之点。并叙述各殖民地华侨受毒之状况及中国人之公意”。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命中国代表极力争取,国联大会最终还是决定,远东鸦片调查团不含中国代表。该团三位调查人员分别是瑞典驻阿根廷公使埃里克 · 埃克斯特兰德(Eric Einar Ekstrand)、比利时政治经济委员会会长马克思——里奥 · 杰拉德(Max-Leo Gerard)和捷克斯洛伐克驻巴西前公使珍 · 哈弗拉萨(Jean Havlasa)。国联鸦片股还派出任博格(B. A. Renborg)担任该调查团秘书。远东鸦片调查团拟于1929年9月自欧洲出发,前往亚洲进行为期约八个月的调查。不过,在此之前,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就禁毒事务已有一次在华直接接触。1929年1—2月,国联副秘书长约瑟夫 · 爱文诺(Joseph Avenol)在秘书吴秀峰和彭莱(Henri Bonnet)的陪同下来华访问,主要目的是安抚南京国民政府因未能继任国联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途经上海时,中华国民拒毒会会长罗运炎和代理总干事黄嘉惠等人与爱文诺会晤,感谢国联承认中华国民拒毒会,并介绍了中国烟毒大致情形和开展禁毒的困境。该会有意隆重宴请爱文诺一行,但爱氏认为“需待南京之行完毕,重来上海再作杯酒联欢之举”。爱文诺完成南京之行后,中华国民拒毒会受全国禁烟委员会之请,于2月14日晚设宴款待,沪上多位政商名人参加宴会。宴会期间,罗运炎和爱文诺等人分别致辞。爱文诺在答词中有意回避了罗运炎提出的“远东殖民地内鸦片应该完全禁绝”和“租界是中国禁政的一大障碍”等问题,只是强调了中国有“强大的民意”协助政府开展禁政,以及远东鸦片调查团并非针对中国,欢迎中国派遣熟悉禁烟问题的代表前往日内瓦。
中华国民拒毒会在爱文诺的建议下,将诉求写成一份说帖,托其带回国联。尔后,该会在《拒毒月刊》刊发了说帖全文,主要内容为:一,强调吗啡等麻醉毒品在中国的泛滥,是当前中国禁政的最大障碍;二,既然麻醉毒品害处如此巨大,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只调查鸦片,令人难以理解;三,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的范围也应该扩大至所有受毒品之害之国家和地区;四,希望国联和其他国家能将麻醉毒品之生产限制至医学和科学用量。随后,中华国民拒毒会于3月14日给国联鸦片股邮寄了一份该会对当时中国烟毒情形看法的声明。国联鸦片股收到后,复函中华国民拒毒会,告知后者其将把声明分发给鸦片咨询委员会成员。虽然此时中华国民拒毒会已与国联有了更多联络,但是严禁烟毒的诉求难以在国联得到回响。
关于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一事,有些地方民间禁毒组织和中华国民拒毒会持不同意见。辽宁拒毒联合会就呼吁国联鸦片调查团去东北调查“日本关东洲及各地日租界纵毒祸华之事实”。这有悖于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南京国民政府当时对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一事的态度。这也表明,虽然中华国民拒毒会以中国民间拒毒代表自居,亦在多地设有分会,事实上难以做到完全统领全国民间禁毒力量。1929年的中国,中央政权尚有鞭长莫及之处,何况民间组织中华国民拒毒会。此外,辽宁拒毒联合会这一主张,也是当时部分国人对国联抱有美好期待的表现。这种期待,可谓数年之后国联李顿调查事件中国人心态的前兆。
在中华国民拒毒会竭力反对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之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已指示中国在鸦片咨询委员会的代表王景岐竭力反对此事。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出席国联的代表为施肇基、王景岐和齐致。王景岐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指示,要争取代表团中包含中国代表,并调查鸦片之外的其他毒品,且调查范围扩大至世界其他地区。1929年1—2月,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召开第十二届会议,王景岐曾做长篇发言,指责治外法权等问题对中国禁政的阻碍,并建议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将范围扩大至所有出产鸦片和制造毒品的区域。王景岐的提议并未获得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同意,后者只是同意在此届会议的议事录中加入他的发言。之后王景岐又专门致函鸦片顾问委员会主任,对此届会议的决议表示抗议,除了得到鸦片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一番解释外,于事实未有改变。
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强烈反对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有多重原因。其一,当时中国烟毒泛滥,如果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前往中国调查,势必将更多的烟毒实况暴露于国际社会,这也是为何南京国民政府提议国联将调查团的调查范围从远东扩展至世界其他地区,将调查内容从鸦片扩大至包含其他毒品的原因。强调吗啡等当时主要来自外国的精制毒品对中国的毒害,是中国在国联禁毒外交中长期持有的策略。其二,前述英国建议国联成立远东鸦片调查团,是为下一届国际鸦片会议的召开做准备。该调查团所形成的报告,将对之后的国际禁毒会议有所影响。由于国联拒绝中国派代表加入该调查团,中国驻国联代表声明该团最终的报告中不得有中国禁政相关的内容。中国对调查团最终报告内容的担心,也是其反对国联开展此项调查的重要原因。
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出发后,中华国民拒毒会除了发起舆论反对这一旧有策略外,还对该会的组织架构进行改革,增设国际科,以做专门应付。1929年9月4日,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从日内瓦出发,抵达马赛后乘船前往印度孟买。虽然该团调查远东之事已成定局,中华国民拒毒会依然坚持不懈地加以反对,并密切关注该调查团的动态,以及远东地区国家对此事的反应。1929年9月11日,远东鸦片调查团到达新加坡之前(10月22日抵达新加坡),当地《新民国日报》刊文呼吁当地禁毒组织对烟毒情况做进一步调查,为行将抵达的远东鸦片调查团的询问做准备,同时进一步展开宣传。中华国民拒毒会在《拒毒月刊》转载了此文。该文呼吁民间禁毒组织发挥作用,这与中华国民拒毒会的宗旨颇为契合。1929年12月15—29日,中华国民拒毒会召开第五届年会。此时,按照预定计划,远东鸦片调查团已经到达越南。在第五届年会上,中华国民拒毒会国际科提议讨论“应付远东鸦片调查团来华案”。次月,中华国民拒毒会在《拒毒月刊》再次刊文,谴责国联组织远东鸦片调查团拒绝中国代表加入,且调查范围仅限于远东,“于法理大欠公道”。中华国民拒毒会还呼吁全国民众:“一方面督促政府厉行烟禁,免为外人借口,一方面反抗外来毒品,暴露彼辈祸华政策,而求世界之公论。该调查团之来华,更绝对不予以承认云。”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国民拒毒会强烈反对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该调查团不仅按照既有计划完成在南亚、东南亚和东亚诸国和地区的调查,而且在1930年5月完成调查返回日内瓦后形成的报告中,对中国烟毒情形多有指责。虽然国联大会曾决定该团的调查范围不包括中国,但事实上该调查团除了曾前往当时为西方列强占领的港澳和大连旅顺等地外,甚至还曾前往京津沪等处,与国联宣称的计划有出入。这份报告还在1931年1月国联第62届理事会之前被分发给理事会成员国。中国驻国联代表处处长吴凯声致函国联秘书长表示抗议,并要求理事会讨论该报告时,需有中国代表参加。后来吴凯声在第62届理事会讨论时抗议,要求删除有关中国烟毒情况的内容,理事会并未同意,只是同意将吴凯声的意见一并分送各国。中华国民拒毒会对国联无视中国政府的反对,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完成考察,颇为失望,认为“英帝国之势焰已张,国际鸦片毒物之肃清,亦将永无达到的希望了”。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的报告发布前夕,中华国民拒毒会总干事黄嘉惠在报端刊文,批评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团的调查及其即将发布的报告,并非如英国等列强所言,是为了在其殖民地落实分期禁绝政策,实则“在掩蔽殖民政府征收鸦片税款之策略上,固有相当功能也”。
然而,此时中华国民拒毒会、南京国民政府和国联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较之20世纪20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关系日益密切(例如科技和医疗援华)的同时,其与中华国民拒毒会的关系逐渐紧张。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国民拒毒会在受到南京国民政府打压的同时,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该会成立之初的主要领导人物黄嘉惠和伍连德因禁毒主张有歧而渐生罅隙。概言之,医学出身加之供职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伍联德并不主张严禁政策,伍氏这一禁毒理念在30年代表现得愈益明显。1931年2月,伍连德在报刊发文,主张由中央政府组织各方切实调查,统制管理,施以重税,渐进地解决鸦片问题。伍氏此文被当时各报争相转载,一时议论纷纭。中华国民拒毒会等批评者认为伍氏之论实为变相之专卖。除了黄嘉惠本人卷入争端外,其夫人白芝英还一度被诬从事贩毒,加之报刊的渲染,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凡此种种,让中华国民拒毒会声誉有损。
即便如此,中华国民拒毒会仍追逐其最初宗旨,推动中国禁政和国际禁毒事业,主要表现是搜集烟毒情况报告国联,继续其国际参与。中华国民拒毒会希望国联能够主持正义,将日本占领下东北的烟毒弥漫情况公之于众。而同时期的厦门,亦受日人毒害严重,中华国民拒毒会将搜集所得情况,亦提交国联。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国联对日本的指责日增。中华国民拒毒会也进一步收集日本以毒祸华之举,报告国联。
然而,虽然中华国民拒毒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继续其国际参与,但民间禁毒组织之于国联的价值已经今非昔比。20世纪20年代末期,国联在禁毒领域的制度建设已趋完备,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公约》已经生效,国联新机构中央鸦片局(Central Opium Board)也已开始运作。在此背景下,国联可以从成员国获得前所未有的信息。与此同时,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迅速恶化。大致始于1930年前后,中华国民拒毒会在报刊,尤其是在其刊物《拒毒月刊》上对上海等地方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连篇累牍的批评,使之与政府关系更趋紧张。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六年禁烟计划”,又称“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意即从1934年开始,两年内解决烈性毒品问题,六年内解决鸦片问题,实质是实行专卖。国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一计划赞赏有加。六年禁烟计划在实现经济收益的同时,把禁毒运动、打击革命根据地红军和打击地方军阀势力相结合,强化蒋介石及其控制的军事委员会的权力。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分道扬镳,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逐渐走向瓦解,于1937年彻底结束了活动,其与国联的交流也因此终结。
结语
揆诸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国联交流的历史,显见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动,受到北京政府及其后继者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关系的影响。在1927年初国联承认中华国民拒毒会之前,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的交流主要经由中国官方代表完成。虽然亦有例外情形,例如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期间,中华国民拒毒会所派代表顾子仁曾与国联鸦片股股长瑞秋 · 克劳迪通信并面谈。从1924至1927年,虚弱的北京政府因国内烟毒日炽而招致国内国际批评,它需要中华国民拒毒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提供一些支持,不仅是在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时站出来为国人做一些辩解,而且包括向国联提供关于中国烟毒情况的报告和数据。中华国民拒毒会所动员的民间力量,为禁政无力的北京政府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之后逐渐加强集权,其与国联的关系虽有张力但是渐趋密切。这一情况,部分因为较之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更为民族主义化和集权化,尤其是在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部分因为国联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走下坡路,因此更为需要中国政府的支持。
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的交流所呈现的形态,尤其是其中持续存在的张力,并非仅仅因为当时中国国内糟糕的烟毒情形和中华国民拒毒会是一个“中国”民间组织,更因为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国联关于禁毒的主张存在明显不同。英法等殖民列强主张采取专卖的政策,而且它们左右了国联主导下国际禁毒政策的走向。而中华国民拒毒会自成立之初即主张采取严禁的政策。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交流的过程中存在持续张力,也源于它在国民政府和国联之间展开活动的两难处境。中华国民拒毒会强调自己是中国民间组织,代表中国民间拒毒之声,呼吁国民政府和当时的国联实行严禁的政策。这种诉求不仅使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张,也影响了其与国联的交流。随着中华国民拒毒会之于南京国民政府和国联的价值日减,它的消亡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国联的交流,折射了20世纪上半叶国际毒品问题治理过程中民间组织、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多维互动。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夏季号,作者黄运,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后。
|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刘玥莹
责编:刘梓熙
编审:张勇安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