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初日本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至今仍有着巨大影响。不过这是向前看,跟中唐以前的历史形态相比较得出的认识,并不涉及宋代以后的社会转型。王瑞来先生的宋元变革论,则是向后看得出的结论。经南宋历元,由明入清,追寻中国走入今天的轨迹,宋元变革论会给出回答。
宋元变革论的形成经纬
2005年,受邀参加科举废除百年学术研讨会。在考虑提交论文时,我决定写元代对科举的停废,给人们对20世纪的最终科举废除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在查找资料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接触到的史实与头脑中学术积淀,互相撞击,产生了思想火花,形成宋元变革论这一命题的雏形。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我的学术方向转型,目光从上向下,从长期以研究皇权为主的中央政治研究转向对地方社会的研究。
以《科举取消的历史》为起点,继续进行资料搜集与深入思考。当时,我在与东洋文库的同行们正在进行内容相关的宋人笔记《朝野类要》的译注作业。笔记中关于选人改官难的条目,让我对进士登第后的命运开始关注,并且与元代科举停废士人的职业取向贯穿起来,结合以往研究中积蓄的个案,写出数篇论文,初步阐述了我主张的宋元变革论。

《朝野类要》书影
宋元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
宋元变革论,看上去是与唐宋变革论针锋相对的命题。其实,两者并非二元对立,都是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历史走向的观察。
在诸多的命题中,20世纪初由日本内藤湖南首倡、宫崎市定等充实的唐宋变革论无疑影响最大。进入21世纪的重新关注,更使这一命题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唐宋变革是指中唐至北宋的变革,并非仅指唐宋之际,北宋作为这一变革期的终点,把唐代的因素发展到极致。因此说唐宋变革论作为古代以及古典主义终结的归纳,精辟而到位。不过,唐宋变革论并不涉及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是向前看而得出的认识。并且,在我看来,始初建立在部分推论基础之上的唐宋变革论,对两宋不加区分的捆绑论述具有一定的缺陷。而我则是向后看,从南宋历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来观察得出的认识。
靖康之变,北宋遽然灭亡。政治场的位移,开启了下一个变革。靖康之变是一个促因,许多变革的因素已酝酿于北宋时期。这些因素伴随着时空的变革而发酵,偶然与必然汇合,从而造成宋元变革。这一变革,由南宋开始,贯穿有元一代。开启了中国历史走向近代的滥觞。探寻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会给出回答。
叫“宋元变革论”,实在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提法,让人误以为是指在宋元之际发生的变革。其实,与绵亘200多年的唐宋变革一样,我是指一个并不短暂的时段,也长达200多年,准确定义说应当是南宋至元变革论,变革期包括整个南宋和元代。出于简洁,就称作跟唐宋变革论相类的宋元变革论。
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
宋元变革论,并非我的首倡。前面提及,欧美学者有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还有由中唐至明变革论等。我必须承认是受到这些说法的启示。
那么,欧美学者的这些认识又从何而来呢?追溯学术史背景,大概还要回到首创唐宋变革论的日本。战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领先于世,并且出于冷战等原因,欧美的几代学人大多通过日本学者的论著来认识中国史。
从内藤湖南首倡到宫崎市定完成,日本学者不仅提出了为学界瞩目的唐宋变革论,还从世界史的视野出发,全面确立了不大为日本以外学者提及的近世社会的学说体系。近世这一时段是介于古代与近代之间的过渡阶段。这样的中国历史分期,无疑比迄至鸦片战争的漫长数千年都视为古代的时代划分要精密得多。
不过,时代的推移呈渐进性。在我看来,北宋处于消化唐宋变革成果、蓄积下一个变革因素的时期,而南宋才开始走向近世。
同唐宋变革论一样,宋代近世说不区分两宋,是其有欠详密的一面。
历史的演进交织于遗传与变异之中。不截然分开而又区别观察,才是正确的研究姿态。北宋具有较多的唐代因素,而南宋又具有较多的北宋因素,都是必须加以留意的。由于同一帝系的两宋在制度设置和统治方式上的覆盖,纠结在一起的因素很多。应当从遗传的外衣之下,通过缜密的研究,揭示出时代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宋应当加以剥离区分。
唐宋变革论与宋元近世说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时代观察。我明确提出的宋元变革论,既有欧美学者的启示,更有日本学者潜移默化的影响。

宋徽宗题画、落款的《文会图》
从南朝到南宋:时空在江南重合
历史在时空中运行。以时间观之,根据时代变化的特征,必须把历来视为一体的北南宋加以切割。以空间观之,也必须将地域进行切割,将南北分开。广袤的中国大陆,地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研究者不可能将这一大陆板块的空间演化笼统地纳入到统一的时间演进中进行观察,否则的话,研究结论的精确度便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Skinner)的宏区划分理论范式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为什么我将宋元变革的开启期确定在南宋?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让时空在江南重合,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一轮变革。地域发展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既不平衡又渐进趋平。一池湖水,尽管水深水温有不同,毕竟同为一池,交互影响。变革从南宋江南的时空发端,如水流从高就低,藉由元明统一的时势,政治、经济、文化的推手便将变革向整个大陆各个地域辐射扩展。
让我们从明清向上回溯。以明清为主的近代以前江南研究,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积累。台湾学者刘石吉认为,“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已萌芽发展。19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势力冲击到中国沿海、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现之前,江南地区的‘近代化’(不是‘西化’)的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那么,明清江南高度的商品经济与早期工业化是从天而降的异军突起吗?
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最近最直接的基础是南宋和元代。江南商业市镇发展的最初高潮出现在南宋,商业经济的兴起引发传统经济结构性产生变化,江南农村经济在宋代、特别在南宋已演变成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在内的有机体系。南宋政府的多次发行的纸币会子已成为社会主要支付手段,在“钱楮并用”的基础上,贵金属称量货币白银也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特殊的国际政治格局之下,依托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历来的“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在南宋终于彻底转向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蒙古人的江南征服,除了少量威慑性屠城之外,多数以不流血的形式完成。蒙古的不流血征服,对于江南来说,意义极为重要。这使自南宋以来的经济结构未遭重创,改朝换代并未中断经济发展的进程,反而更为开阔疆域的形成与多种贸易方式的导入,更为刺激江南经济由内向转为外向。这就是宋元留给明清的铺垫。
明清的宋元因素不可忽视。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敏锐地观察到,宋元时代的中国“以华北为重心的状况开始向江南和南方移动”。杉山进一步由南宋俯视了元代:“这个南北逆转的现象被元代直接继承下来(严格地说来到了元代才真正开始展开),与明代的状况直接相连。这可以说是和现在有关的中国史上的大现象。”杉山的这段话,可以佐证我主张的宋元变革完成于元代,并且也意识到了宋元变革之于近代中国的意义。
在南宋历元的积淀之上,政治中心再度北移的明代光大了江南。持续繁荣而富庶的江南,在清代成为全国歆羡而向往之地。江南,不仅一直保持经济重心的优势,而且成为文化重心。近世乃至近代,最具中国元素之地,舍江南而无他。我讲的江南,是广义的南方。宋元变革的大剧,在江南的特定舞台上上演。

杉山正明
从侧面切入的尝试
(一)科举的盛世
论述中国历史如何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命题。我首先尝试从南宋科举及第后选人入官这一个侧面一点切入,从而揭橥社会转型之渐。
如所周知,从北宋太宗朝开始,伴随着宋朝统一事业的基本完成,亟需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以及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等多种因素,让宋朝政府全速启动了科举这架机器,开始了大规模的官僚再生产。
从此,两宋三百余年间,每科取士几乎都达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000人,南宋约为51000人。这些数字的总和数倍于宋朝以前和以后的历朝科举登科人数,折射出科举制度和由此造就的士大夫政治的时代辉煌。
(二)辉煌后的阴影:科举难、改官难
然而辉煌有阴影。科举造就了不少高官显宦,他们显现出耀眼的光芒。但科举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范进式的潦倒士人。即使在科举盛行的宋代,以解试百人取一,省试十人取一约计,也只能有千分之一的幸运者可以获得金榜题名的殊荣,而多数士人则与之无缘。就是说,五万人的金榜题名的光芒,完全遮蔽了五千万人次举子以及更多的支持着他们的家人的悲辛。
更为值得注目的是,这五、六万幸运儿在金榜题名后的命运,也并非个个都是风光无限。这是为迄今为止的研究漠视的一隅。北宋真宗朝开始确立选人改官制度,多数选人需要包括顶头上司在内的五名举主推荐,方能有资格升迁京朝官。制度性的规定,加上举主和胥吏人为因素,使得普通选人改官分外困难。这在北宋中后期已见端倪,降至南宋,员多阙少日渐严峻。在政界缺乏背景的普通及第者,尽管可以成为低级官僚的选人,由于制度上和人际关系上的因素,却几乎无法挣脱出通向成为中高级官僚的瓶颈。
大量通过千分之一高倍率激烈竞争科举及第者的选人,在此后的仕途上遭遇到更为激烈的新一轮升迁竞争。只有少数幸运者由于各种因缘际会,得以顺利改官,升迁到中级以上的官僚地位。大多数选人摧眉折腰,被呵责役使,忍受地位低下、俸禄微薄,小心翼翼地熬过十几年,甚至耗尽毕生的心血,到死也难以脱出“选海”。“金榜题名时”,在过去曾被形容为人生得意的几个境遇之一,但金榜题名后,却让多数金榜题名的时代宠儿得意不再,失望至极。
科举难,改官难,严酷的现实最终让对仕途绝望的士人“绝意荣路”,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使多数士人潜沉下层,滞留乡里,导致士人流向多元化。胥吏、幕士、讼师、商贩、术士、乡先生都成为士人的谋生选择。社会流动由纵向更多地趋于横向。纵向的推移带来横向的变化。下层士人和官僚无法进入主流的结果,最终必然是漫溢的支流淹没了主流,社会发生转型。

《吏学指南》书影
(三)疏离主流,士人走向地方
在经济发达、地方势力强盛的背景下,不少士人以各种形式流入地方社会。士人的参入,在客观上提升了地方社会的知识层次,强化了地方社会的力量。士人流向地方,既有因科举难而形成的水往低处流的主动选择,也有被动接受。南宋愈加严酷的“员多阙少”的状况,让有出身的士人长时间待阙于乡里。由于僧多粥少,不少低中级官员在一期差遣任满之后,也要回乡待阙。甚至即使是获得了差遣任命,也还要等到那个差遣的位置空出来之后方能赴任。同样也要滞留乡里。士人、士大夫滞留乡里,为地方所倚重,被邀请或主动参与到地方事务之中。除了待阙,丁忧守丧的三年,也给了士大夫在一定时期回归乡里和参与地域活动的机会,在地域留下他们的印记。南宋的宰相史浩就说过“贤大夫从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闲之日多”。因各种原因“被地方化”,在乡里的长期滞留,既让士大夫重新贴近乡里,也让乡里亲近了士大夫。
南宋的这种变化,与此后长期停废科举的元代社会变化紧密相关,也与明清时代乡绅势力的历史渊源割舍不断。元朝的停废科举,基本堵塞了旧有的士人向上流动的通路。彻底绝望的士人只好一心一意谋求在地方的横向发展。
流向地方的士人的知识资源与发达的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实力,两者合流,促进了地域势力的发展。而元代科举在几代人几十年间的停废以及儒户的建立,又将士人彻底推向了地方。除了利用知识优势为吏,从事教育也是士人的众多选择之一。传道授业,士人将政治理想倾注于社会。
将精力倾注于地方的士人,首先从齐家做起,经营一个家族,扩充一个家族的经济基础、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齐家是同地方建设同步进行,密不可分。近代中国社会的宗族,最可靠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南宋,从南宋延续而来。从此,宗族势力一直在地方社会作为末端血缘集团发挥着重要作用。
精英引领社会转型
士大夫政治格局,让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改变了既往的形态。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中国思想文化都是在王朝失去深入控制社会能力之时,开出了绚烂之花。而北宋则在士大夫的主宰之下,中国文化走上自然发展的正常之路,伴随着经济繁荣而繁荣,政治之手不再成为文化发展的强力钳制。
靖康之变,中断的只是北宋王朝的进程,并未改变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格局。不死鸟在江南重生,包括士大夫政治在内的北宋因素,由于传统、惯性以及百年积淀都被南宋全面接受。并且在南宋的特殊背景下走向地方社会。如同随风潜入夜,士大夫政治浸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任何时代的地域社会都存在着支配势力与领导层。在南宋,就是士大夫、士人引领着地域社会。
作为一个阶层,士人的身份逐渐明确并得到认同。并且,时空的变化,让士人与士大夫的面向也有了改变,由致君转向化俗,更为着重在地域的发展。在北宋,士人循蹈的还是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从南宋开始,士人则逐渐面向地域,行走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
政治精英体现在入朝为官,是对地域的脱离,而士大夫家族的根却根植于地域。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壮大,根植于地域的新士族也同时在壮大,北宋的苏州范氏,南宋的四明史氏,都是宋代新士族兴起的一个缩影。北宋时代开始建设经营的新士族,到了南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业已在各个地域盘根错节,相当强盛,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影响力,成为不可忽视的地域社会的主导性势力。
出官入绅,士大夫政治精英出于各种原因回到乡里之后,又变身为地方领袖,在长期经营的家族基盘至上,权势余威、富甲乡里、精神力量等综合因素,都足以使他们指麾一方。这些回到地方的士大夫精英,也成为仕途失意或对仕途望而却步的士人所依附的靠山。
在北宋,这个士人层向士大夫政治的金字塔尖聚集。到了南宋,攀塔路难行,这个士人层在地方弥散。不过分布于地方的士人并非一盘散沙。
以诗词书画等文化和道学等学术为媒介,各个地域的士人形成庞大而广泛的社会网络。这种士人网络,既编织于本地域,又由于人际交流,横向扩展于其他地域,并且向上延伸于各级官府。入仕与否并不重要,共同的文化背景,构成了士人间彼此沟通的身份认同。
由于拥有文化知识,并且拥有广泛的人脉,又有各种社团组织依托,更有宗族的根基,士人属于地方上具有整合能力的阶层。动乱时代崇尚武力,军人活跃。和平时期则是士人的天下。“士农工商”,传统的职业划分,士居于首。爱字惜纸,普通庶民对拥有文化知识的歆羡,让士人在社会上一直受到尊重。对地方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则更加扩大了士人的威望与影响力。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赈灾救荒,建学兴教,凡属公益事业,都能看到士人活跃的身影。知识人社会角色的转变,推动了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转型。向通俗而世俗方向发展的社会文化,精英意识淡薄,疏离政治,贴近民众。元代杂剧的兴盛,明代市民文化的繁荣,似乎都可以从南宋中后期的文化形态中窥见到形影。
士人和士大夫,在乡为民,入仕为官,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居中成为连接官与民的纽带。国家公权力贯彻乡役制度,地方乡绅推行义役制度,两者之间既有紧张的纠结,又有主动的配合。利益指向尽管有不同,但在客观意义上都是对乡村秩序的整合与建设。地方上的士大夫精英、大量普通士人,加之以献纳等方式买来出身夸耀乡里的富民,作为乡绅阶层,从事地方建设,调解地方纠纷,分派役职,动员民众,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成为与国家权力既依附又抗衡的强大地方势力。
从南宋后期的士籍产生,到元代的儒户确立,不凭血缘,不靠门第,文化贵族的世袭,终于在元代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不以拥有财富为标志,不以职业为区别,而以文化为身份,无恒产的士跻身于以职业划分的众多户种之中,成为编户齐民的一类,拥有不纳税,不服役的特权,从自贵到他贵,比较社会的其他阶层,儒户的确可以称得上称为客观存在的一个精神贵族群体。江南的这个群体,据估计拥有10万户之多。这为明清强势的乡绅社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原本作为士大夫政治的理论基础而形成的理学,在南宋特殊的背景下逐渐光大为道学,成为弱势国家所赖以撑住的精神支柱。失去了中原的王朝需要以“道”来申说正统,这是催生道学的一个客观的背景因素。而士大夫则以道统的承载者身份来充当了全社会的精神领袖。《大学》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发掘阐释,成为连接个人、家族、地方、国家的精神纽带,从而达成地方社会主导的国家与地方的互补。于是,南宋光大的道学,经由元代,在明清一统天下。
道学弘扬的道统,不仅超越了王朝,还在汉字文化的覆盖下超越了族群。而道学通过教育、教化向民众的普及,又成为建设地方的士人层连接与领导民众的方式之一。南宋以降兴盛的书院所彰显的私学理想与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北宋以来士大夫政治唤醒和培植的独立意识在士人社会的广泛渗透。不仅是书院,包括社仓、乡约、乡贤祠等机构与公约的设置,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形成一个互为作用的社会权威场,充分显示了士人在道学理想牵引下对地方的关怀与主导。道学在地方社会成为新兴士绅的道德标榜与精神指导。在弘扬道学的旗帜下,加上科举和为吏等“学而优则仕”的魅力驱动,商业活动等实用需要,教育从南宋开始获得了空前的普及。
南宋以降,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让着意于谋求在地方发展的士人逐渐强化了地方意识。对于发掘和树立的乡贤或先贤的祭祀,便显示了士人精英强化地方认同的努力。乡贤是地方的先贤,但又是超越地方的楷模。道学覆盖地方,乡贤回归地方。这样的乡贤树立,灌注了士人的普世理想。而乡贤的祭祀,无疑也成士人掌控精神指导权,并由此间接显示领导地位的方式之一。
除了从事教育之外,没有了科举的时代,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流向更为分散而多元,犹如水漫平川,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多数士人或许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与道义担当,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为稻粱之谋。我曾考察过由宋入元的黄公望的生平。这个以画出《富春山居图》而闻名于后世的画家,曾经长期为吏,除了为吏,黄公望还教书、算卦、入教,从事过多种职业。作画只是晚年的一种兼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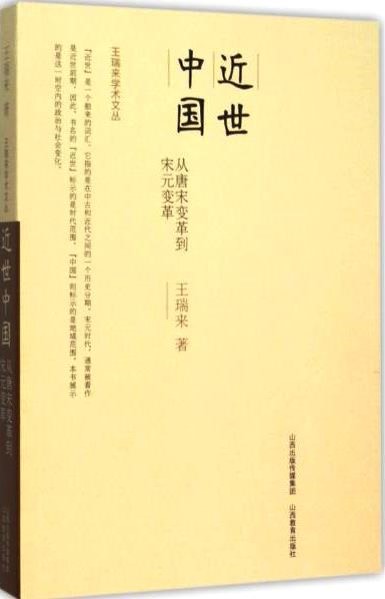
《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书影
从近世走向近代
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低级官僚的层面,至死无法升迁至中级官僚。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士人流向形成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提高了地方社会的知识层次,引领了社会转型。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
俯观明清,虽然科举得到了完全的恢复和发展,但以乡绅为主流的多元而强势的地方社会业已形成,呈现出任何政治力量也无法改变的势态。究其始,溯其源,发端于南宋,壮大于蒙元。
地方社会的崛起是宋元时代变革的一个标尺。南宋士人在科举和改官时遭遇的境况,并且由此所形成的士人流向多元化,实在是催化宋元社会转型之一因。
南宋又仿佛回到了南朝,政治、经济中心再度合一,经济重心的作用发挥得尤为显着。元朝取代南宋,科举的停废,以吏为官,则加速了自南宋以来的社会变化。社会变化的基础是经济结构。而蒙古人对江南基本上实行的不流血征服,则保全了经济结构的完整。
从南宋开始盛行的以职业划分户种的做法,全面实行于元代,到明代依然被保留下来,文献中明代负担劳役的军户、灶户(制盐)、乐户、果户、菜户、渔户、打捕户等,随处可见,大量手工业户种从农业分离出来,改变了社会结构,近代社会职业划分的基础渐次奠定。
宫崎市定在评论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时认同吉川的说法:“宋人们的生活环境,与过去中国的状况相比,具有划时代的变化,靠近了现代的我们。”这是相当敏锐的观察。
“靠近了现代的我们”的“具有划时代的变化”,酝酿于北宋,开始于南宋,完成于元代。像一杯混沌的鸡尾酒,经过南宋至元转型的动荡,降至明清,中国社会又变得层次分明,无论是乡绅阶层还是地方社会,都大致定型,走向近代。时(南宋、元)、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造成宋元大变革,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回望历史,尽管有不少迂回曲折,然而大河奔流已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挡。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河南大学的讲演,原载《文汇学人》2016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