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尽管从广义上说,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关的史料也极多,一辈子都无法读完;但若从沿革的政治意义上去分析,戊戌变法大体上就是“百日维新”,是一次时间非常短暂的政治事件。其主要活动着北京、在政治上层,且只有少数人参与其间,绝大多数人置身事外,闻其声面不知其详。又由于政变很快发生,相关的人士为了避嫌,当时没有保留下完整的记录,事后也没有详细的回忆。一些原始史料也可能因此被毁。也就是说,今天能看到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核心史料仍是不充分的。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台北中研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陈凤鸣先生分别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国第―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了大量档案或当时的抄本,主要是康有为等人当时的奏折,揭示出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奏稿》中的作伪,对戊戌变法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当此项史料搜寻工作大体完成后,还有没有新的材料——特别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可用来研究戊戌变法?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张之洞档案”中关于戊戌变法的大批史料,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寻多年的目标突然出现时那种心动加速、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改变研究计划,专门来阅读与研究这一批材料。
我在阅读“张之洞档案”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感受是,这批史料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
其一,张之洞,陈宝箴集团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他们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对变法的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戊戌变法是体制内的改革,须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参加或支持,方有可能得以成功。当人们从“张之洞档案”中看到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似可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
其二,以往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经常以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为中心;而“张之洞档案”中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让研究者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次改革运动。兼听者明。由此,易于察看到康、梁一派在戊戌变法中所犯的错误。
其三,由于这批材料数量较多,准确度较高,许多属当时的高层秘密,可以细化以往模糊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历史关键时刻的一些关键内容。这有助于我们重建戊戌变法的史实,在准确的史实上展开分析,以能较为客观地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也就是说,原先的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并进行了多次辨伪识真建立起当今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正面”——尽管这个正面还有许多瑕疵和缺损;那么,通过“张之洞档案”的阅读,又可以看到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另面”——尽管这个另面也不那么完整和清晰。任何事物都是立体的,多维观察的重要意义,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于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够阅读到历史的“正面”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另面”的机会并不多。这是我的一种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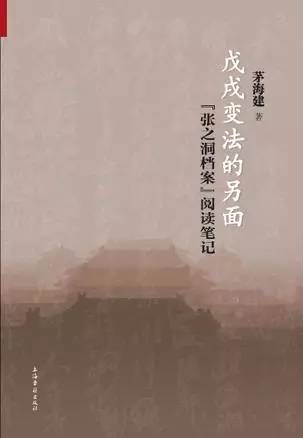
导论
张之洞是那个时代官场上的特例。他有着极高的天分,使之在极为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才密集的翰林院中大显才华。他深受传统经典的浸润,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他尊崇当时的大儒、曾任同治帝师傅的清流领袖李鸿藻(亦是同乡,直隶高阳人),而李鸿藻则历任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高官,又使之身为疆吏而“朝中有人”。曾国藩、李鸿章虽同为词臣出身,然以军功卓著而封疆;张之洞的奏章锋芒毕露,博得大名,竟然以发文章发达而封疆,实为异数。此种最为关键者,是他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从殿试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员的出任,以及在其人生数次关键的时刻,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或显或隐的“慈恩”。
“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十日之饮”、“申旦高谈”,表明两人(编者按:张之洞、康有为)有着很长而且很热烈的谈话。而张于此时花大量时间与康交谈,实则另有隐情。两人在马关议和期间皆主张废约再战,在换约之后借助张变法自强,在此性情志向大体相投之下,双方的相谈也很成功,张当时对康的评价很高。由此,张决定开办上海、广东两处强学会。其中上海一处,张之洞派其幕僚汪康年办理,广东一处交由康有为办理;而汪康年此时尚在湖北武昌,在其未到上海前,上海一会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等人先办。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浙江瑞安人,张之洞的门生,侄女婿,时任翰林院侍讲,恰在张之洞幕中。他当时不可能亲往上海。梁鼎芬是张的重要幕僚,此时亦准备临时回湖北。黄、梁皆是远程操控,上海强学会实际由康有为一人主持。
康有为用孔子纪年,乃效仿基督教用基督诞生纪年,这是“康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康于此也表现出有立孔教的政治企图。张之洞与康有为之间最重要的学术分歧乃在于此,然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正朔用纪年当属政治表态,立教会更有谋反之嫌,康此时虽绝无于清朝决裂之意,但此举必引来许多不利议论。此在康似尚属理念,在张则是政治。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初五日,康有为与张之洞之间有着两个多月的交往。在此期间,南京的十多天大约是他们的蜜月期,康到上海后,平静的日子还维持了一段。梁鼎芬、黄绍箕奉张之洞之命还在劝康;大约从十一月起,裂缝越来越大,以致最后破裂。从此两人再无合作。
从事情本身来探讨,两人破裂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两人性格,康有为、张之洞皆是自我意识坚强的人,康不愿屈从权贵,而自认为是后台老板的张决不允许康如此自行其事;其二是“孔子改制”,即所谓“康学”,这本是学术之争,然到了此时,已成了政治斗争,张也不允许将《强学报》变为宣扬“康学”的阵地。
张之洞精心筹办的《正学报》,最后未能刊行,其原因未详。以我个人的揣度,其未刊原因大体有二:其一,《正学报》的班底皆有较深的学术功力,似此可办一学园式书院(或近代书院),各自讲学研究,千妍万艳;而若要同心协力共办一份政论性的报刊,未必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康们弟子那般真能力行果效。作为总负责的梁鼎芬,其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可能会过于雅致而细碎,这作为学者当属及其自然与正当;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处处计较,将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写作。作为后台老板张之洞,对报刊文论时有苛求,往往揪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切手头事务极多,呈上稿件经常不能及时返回,这一作派明显不利于刊物的定期发刊。其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百日维新”开始之后,京师的政治局势变动极快,这本是各类报刊充分成长的最好时机,可随时发布评论或消息,且有众多读者而市场扩大;而《正学报》作为代表张之洞政治观念与立场的政论性刊物,企图对全国的思想和学术进行正确的指导,很难在纷乱的政局中,找到并坚持那种恰如其分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态度。从前引陈庆年日记中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幕中人物虽在武昌,但关注的是京师,任何景象与气温的变幻,都会在他们心中激起重重涟漪。政治家与政治评论家不同。政治家需要那种平静的态度和适度的言论,以能在政治风波中保持其稳固的地位,而不能像政治评论家那样,在政治动荡中指引人们的前进方向。而到了秋天,政变发生了,变法中止了,此类刊物也顿然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原有的意义。
如果张之洞入京辅政,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很可能成为此期朝政的纲领;而他对康有为及其学说的敌视,将会全力阻止康有为一派的政治企图。他对“迂谬”理念的反感,也将会全力阻止极端保守派的政治反动。若是如此,清朝的历史之中是否就会没有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没有义和团和庚子事变,而提前进行清末新政?
历史没有“如果”,也容不下太多的假设。于是,治史者与读史人又有了百般的思绪、万般的感叹和那种不由自主的暗自神伤……
第一章 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
在数量极其庞大的“张之洞档案”之中,有数以百计的文件涉及戊戌变法,而能让我眼前一亮、怦然心动者,是其中一件精心制作的折册,木板夹封,封面的签条写“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石芝所藏”(以下称《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其中的一些信件透露了戊戌变法中的重要内幕。
正当我为“石芝”其人感到极为困惑时,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茹静女士向我提供了情况:“石芝”很可能是李景铭,该馆另藏有“李景铭档案”8册,装订样式大体相同,也有3册亦署名“石芝”;其中一册题名已脱落、封套题为《李景铭存清室信札》者,页内有红色铅笔所写字样:“信札共9册。56、4、27萃文斋,共价60。00,总59号”。由此看来,《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原是李景铭所收藏,于1956年4月27日由近史所图书馆购自于北京琉璃厂旧书店“萃文斋”;又由于该册题签为《张文襄公家藏手札》而从“李景铭档案”中抽出,羼入“张之洞档案”。
李景铭,字石芝,福建闽侯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清末任度支部员外郎;北洋政府时期任财政部赋税司司长、印花税处总办等职。他对清朝历史较为熟悉,著有《三海见闻录》、《闽中会馆志》等书。然他又是从何处搜得这些信札,情况不详。台湾大学历史系李宗侗教授的经历,可能对此会有所帮助。李宗侗曾著文称:
昔在北平,颇喜购名人信札,所积至万余件,带至台者不过数百札耳。此劫余之一也。吾所注意与收藏家不同,收藏家偏重人与字,而吾则重内容,若内容重要,即片简断篇亦所不计。文襄遗物多经后门外估人之手,以其故宅在白米斜街,去诸肆甚近。忆曾购得两木箱,杂有诸人致文襄信札及文襄所批文件与亲笔电稿若干件,现回忆之,皆可谓为至宝矣。
李宗侗为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孙,他从地安门外旧物店收购了两木箱的张之洞遗物,李景铭是否亦是如此?而李宗侗于1935年因故宫盗宝案离开过北京,他的收藏是否另有出让?
《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贴有李景铭所写的五张签条:一、“张权,字君立,直隶南皮人,文襄公长子。戊戌进士。户部主事,礼部郎中,四品京堂”。二、“此三纸系杨锐号叔峤所写。”三、“张检,字玉叔,直隶南皮人,文襄公胞侄。庚寅进士,吏部文选司郎中,外放江西饶州府知府,升巡警道,署按察使。”四、“张瑞荫,字兰浦,直隶南皮人。文达公子,官□□道监察御史。”五、“石镇,字叔冶,直隶沧州人。为文襄公内侄,官安徽候道。”由此看来,李景铭对张家的情况亦有初步的了解。
《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共粘贴张之洞家属书信计24件,另有其门生杨锐来信1件。我之所以对其感兴趣,是因为其中的7件,即张之洞之子张权来信4件(1件为全,1件缺一页,2件为残)、侄张检来信1件、侄张彬来信2件(1件稍全,1件为残)。这些密信写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彬的一残件写于光绪二十一年),皆是向张之洞报告京中的政治情况,涉及戊戌变法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心机密!
以下逐件介绍张之洞收到的这批密信,并结合“张之洞档案,中亲电报,加似背景的说明。
《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所贴第22件,是张权的来信。张权,张之洞长子,字君立,生于同治元年(1862),光绪五年(1879)中举。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人在京发起强学会。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他进京参加会试。张之洞对此十分关心,亲笔写了大量的电报;亦曾于四月十八日发电指示其殿试之策略。张权此次会试,中三甲第63名进士,五月十三日光绪帝旨命“分部学习”,任户部学习主事。
张权到京后,除了应试外,张之洞也命其报告京中密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1898年4月2日),张之洞发电:
京。化石桥。张玉叔转张君立:四数已汇,到否?场作速钞,即日交邮政局寄。勿延。近事可详告。壶。卅。
“张玉叔”,张检,后将详说。“壶”为引之洞发电给亲属及密友的自称。四月初七日(5月26日)又发电:
京。化石桥。吏部张玉叔转交张君立::榜后何以总无信来,奇极。即日写―函,交邮政局寄鄂。行书即可,不必作楷。壶。阳。
“近事可详告”、“即日写一函”等语,说明了张之洞交待的任务。五月二十六日(7月14日)即会试、引见各项结束后,张之洞发电张检、张权:
京。张玉叔、张君立:急。分何司?即电告。前交邮政局寄《劝学篇》一本,当早接到。有何人见过?议论如何?康、梁近日情形如何?仲韬、叔峤与之异乎?同乎?众论有攻击之者否?即复。壶。宥。
“仲韬”,黄绍箕。时任翰林院侍讲。“叔峤”,杨锐,时任内阁候补侍读。两人皆是张之洞在京最亲信的人,这封电报中开列出张之洞所需了解的情报内容。除了私人性质的张权分户部后又掣何清吏司外,主要有三项:《劝学篇》在京的反应;二、康有为、梁启超在京的活动;三、黄绍箕、杨锐与康。梁的关系。至于第三项,很可能是张听说黄、杨等人参加了康有为等人组织的保国会的部分活动。六月初三日(7月21日),张之洞再电张检、张权:
京。化石桥,张玉叔、张君立:急。折差寄《劝学篇》三百本,以百本交仲韬、百本交叔乔,百本自留,亲友愿看者送之。康气焰如何?黄、乔、杨与康有异同否?户部难当,只可徐作改图。堂官已见否?前电久未复,闷极。速复。壶。
由此可知,张之洞为《劝学篇》在京发动了巨大的宣传攻势。“黄”指黄绍箕,“乔”指乔树枏,“杨”指杨锐。张之洞再问此事,仍是保国会的传闻,他还没有收到张权的回电。
张权的这封密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的。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