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16 岸本美绪 NJU学衡研究院
场、常识与秩序
文/岸本美绪 译/罗冬阳
小引:在《场、常识与秩序》中强调历史研究者用自己的感觉直接接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由此而获得的知识,对我来说只要是有效的就足矣”。作者以温文尔雅的方式批评了各种理论化和结构化的中国历史认识,倡导要从日常经验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社会。“地域社会论”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一个研究趋向,关心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形成的地方空间,理解历史的行动者是怎样和为何采取行动的。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要认真界定“地域社会论”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发现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性”,很难给其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地域社会被置于历史叙述的中心时,地域社会论必须回答不同或类似地域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地域社会与国家权力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复杂关系内部是否具有整合性等问题。
文本原载于黄东兰:《身体·心性·权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岸本美绪(1952—),东京都人,中国史学者。1975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卒业,1979年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中退,历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手、御茶之水女子大学文教育学部専任讲师、助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助教授、教授等,现为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大学院人间文化创成科学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変動》(1997)、《東アジアの「近世」》(1998)、《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1999)、《中国社会の歴史的展開》(2007)、《風俗と時代観》(1912)、《地域社会論再考》(2012),编有《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3巻·東洋学の磁場》(2006)、《中国歴史研究入門》(2006)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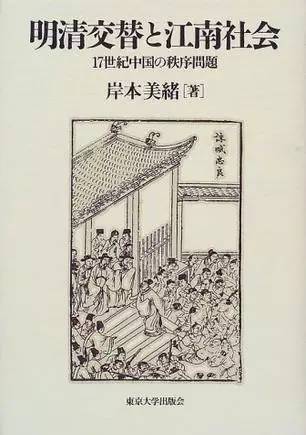
本文译自岸本美绪教授著《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一书序言。
本书以江南(长江三角洲)的地方社会为中心,就1644年前后明清交替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变动作探讨。除了部分为新写作外,主要部分由1986年以来已发表的论文构成。如果说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研文出版,1997)属于经济史部类的话,本书或许可以说属于社会史的领域。这表明了十数年间我所关心问题的变化,但经济史也好,社会史也好,我基本感兴趣的问题实质上几乎没有改变。前书收录的1987年的论文中,我陈述了这样的旨趣:不企图“将当时社会经济中的种种变化,诸如土地集中、商品生产、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等现象,直接与高度抽象化的发展阶段论、经济构造论联系起来”,而是试图探讨“对当时各个土地所有者、生产者而言,使得这样的变化成为可能、有利或者不可避免的具体的经济背景”。这也是贯穿前书整体的我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在本书,我所企图探究的,不是要在发展阶段论的大框架中,将阳明学的流行、乡绅支配、民众暴动等赋予明末社会特色的各种事象定位、论述其近代性、局限性等等,而是要具体地理解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采取那样的行动、什么样的状况将人们驱使到那一方向。
但是,在前书中,为了从当时日本明清史学界几乎尚未加研究的物价方面接近这一课题,劳动的大部分都倾注在物价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借以弄清事实。与此不同,明末清初江南社会的急剧变动是日本明清史研究一贯关注的焦点之一,阳明学、乡绅势力、民众运动,任何一个都有相当的研究积累。所以,本书工作的中心,与其说在个别的事实发现——当然,本书也希望多少包含有价值的事实发现——,不如说在于就明末清初的江南社会,将向来受到注目的事实加以重新解释,以解开研究史上的僵局,整合地说明各种事象,勾描出整体性的图画。特别是第一、第二、第三章,稍稍带有所谓研究史再检讨的论争色彩,正好也与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日本明清史研究的一股潮流受到瞩目的所谓“地域社会论”纠葛在一起,发表之初就受到各种方法上的批判和评论。
从这些批评获得教益从而产生的新见解,会在以下各章加以适当展示,这里想借本书全体序文的空间,再次回顾这样的问题:我的基本的方向性在研究史上具有怎样的特质?此种方向性来此何处?碰巧,1999年初,在东京学艺大学得到与学生们谈论“地域社会论”的机会,当时我试着以尽可能朴素直率的方法,把个人的情况也不加隐瞒地说出,表达我的思考方式。请允许将当时谈论的内容作若干的补充修订,重录于下,以为序。
在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中,“地域社会论”一语作为表示一种方法论立场的词汇来使用,已经是十余年前的事情。就像屡屡提到的那样,其成立的直接契机,可以说是1981年由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主办的题为“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与指导者”的学术研讨会。我也参加了那次研讨会,得到某种触及核心的问题被提出的印象。但是,朦胧感到问题并未轻松解决,而是留下了自己必须加以思考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后,含有回答这一有待解决问题的意思,在提到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意义时,我多次使用“地域社会论”一词来表述我的看法。结果,不料被视为“地域社会论”的“代表性论者”。然而,反躬自问不禁有些危惧,我的行为可能限制或者歪曲了八一年学术研讨会具有的丰富可能性。
关于被视为所谓“地域社会论”的各项研究及其内容,因已经有了很多的议论,也包括对此语的使用持疑义的论者,这里不再陈述我的看法,以免重床叠架。有兴趣的读者,请去阅读有关文献——可能的话,不仅是介绍性的、评论性的文章,也包括相关的实证论文——,做出自己的思考。在这里,我想以自我反省的心情思考:我为何又如何对“地域社会论”式的方法持有关心。想起来,某研究者为某一方法所吸引的过程,也许并非自一开始就有证明该方法“正确”的确实证据和道理,而是无意中暂时感到对于自己来说合适的感觉占据了优先的地位。就我来说,不仅是“地域社会论”,其他方面也确实如此。读别人的论文觉得有意思,然后读史料整理出论文,自己的偏好和倾向就自然流露于其中,然而并非最初就对其为何物有清醒的意识。遭到别人的指摘与批评,意识到自己的偏颇,在反省与辩白的蹒跚步履中,才逐渐将具有自身特色的“方法”自觉地对象化。
现在的我,或许会被看作抽象“方法论”的类型,然而学生时代的我,则是不掩饰对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扉页题词“个别难尽乎笔舌”抱有同感的“个别实证派”,对抽象化的“方法论”毋宁感到抵触和疏远。成为研究者以后,方认识到“方法论”并非外在的束缚自己的框框,而不过是将自己为什么如此思考及思考方式的基础公开的事情。即使现在,我对在前台夸示“方法论”以折服对手执学界之牛耳的事情毫无兴趣,我所感兴趣的不过是“我为什么如此思考”、“自何种前提的不同出发导致了自己与他人主张的差异”诸问题。偶尔确实也欣喜于其他研究者也感到了同样的走向,从而以“最近的学界动向”的形式轻率地加以一般化,还有一当遭到其他学者的强烈批评,遂坚持强调自己方法的正当性。反省这种态度,我并不主张下面叙述的内容“是新的(正确的)方法,所以各位都应该采用”。这里与其说是要说明我对“地域社会论”的关注基于我对“地域社会论”一般正确性的确信,不如说是要将出于我素来的习惯和偏好之情率直地揭示,至于妥当与否,则仰赖于读者的判断。
一、“地域社会论”的不定型性
“地域社会”一词是具有多种含义的含混的词汇,在所谓“地域社会论”出现以前,明清史学界着眼于“地域”的各种研究也已经很活跃。第一,自幅员辽阔的中国不能一概而论的见解出发,有将各个不同的地域,如江南、华北、福建等面积不同,产业、文化诸方面亦具有各自固有特色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第二,不注重各地域的不同的特色而是着眼于作为系统的统合性、自立性划分区域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实例之一是施坚雅著名的大地域(macro-region)理论。这一理论从以河川为中心的交通运输系统的角度,将中国划分为八大或九大地域。不仅可将中国划分为几大区域,还可以可像“朝贡贸易系统”那样,构想超越中国范围的广域系统。这第一和第二的地域,与人文地理学上“同质地域”、“功能地域”概念各相重合。第三,有一种动向,不是关注地理的、空间的大小,而是着眼于作为社会层级水平的当地社会。在战后日本的中国史学中,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不是宫廷-中央政府水平的政治史,而是处理作为社会基本构造的生产关系、阶级对立的社会经济史。而在英语圈中,通过把握充满纷争的地方社会(local society)的实态发现动态历史的主张,在1970年代以来变得日益显著,与静态的、概念化的国家秩序图像形成对照。

美国学者施坚雅
鉴于上述的情况,很明显,对“地域社会”的关注决不能说是“新的”视角。我也无意标榜“地域社会论”的“新颖”。尽管如此,从1980年代以降明清“地域社会”研究的一部分,还是可以看到与此前不同的共同特色。着眼于这一点,是我数次提到“地域社会论”的动机。
那么,那种共同的特色是什么呢?山田贤在拒绝“恣意”归纳的同时,将总称为“地域社会论”研究的底流中存在的思潮作了整理,请允许引用如下。
(1)“地域社会”、“地方社会”、“在地社会”等,是个人与个人相会,结成社会关系,在相互间反复接触的同时形成社会关系网的场所。这里有一种导向统合的磁力(或者作为对抗动机对反统合的抵抗)——不论用权力、支配、秩序等如何的名称来称呼这一磁力——发生作用,来使社会作为一体的社会凝聚起来。“地域社会论”所注目的是,这种磁力发生作用的“场”之性质。
(2)打个比方,“地域社会论”所注目的“场”好像使用共同语言的社会:在这里,各式各样的人(=单词)通过共同的行为习惯(=文法、统辞法)被结合起来。“地域社会论”并不认为这个“场”的范围一定重合于预先特定的空间范围(国家、县,等等),而认为是柔软可变的、自然而然形成的构造。以人和人随时随事结成的关系网及他们共有的社会观为基础而成立的认知体系才是支撑这个构造的根基。
由这一总结想象出的社会图像,或许会让人感到没有明确的轮廓,甚为模糊。但正是这种不定型性,将我吸引到了“地域社会论”。说起来,是因为我自孩童时代起,对社会这一事物的难以把握就感到不可思议和不安,一旦接触像有明确框架的构造物一样的“社会”图像时,与其说感到安心,不如说反而感到困惑。这样说有些费解,再稍加说明。
如果考察一下此时此地的“我”,我会如何感知自身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呢?实际上我不可能对这个社会作鸟瞰式的观察。我能够说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个社会的,仅限于家庭、工作单位或交际圈等极为微观的人际关系。譬如考察一下现在工作所在的大学,对其整体的印象,只是看了机构图有个观念上的了解,实际上是否如此,并未经亲眼确认。但感觉到这所大学是不用求证就“存在”的事物,则受此信赖感的支配,每天上班、授课、领受薪金。没有出现特别不便的情况,过着每日的生活。对工作所在的大学尚且有种不确实感,那么对大于此的社会,就更停留于含混的想象。幸运的是,我的常识和行为方式与他人似乎并没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即使有偶然的失灵,时下还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未来的什么时候或许会到这种程度)。说到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是怎样的事情,也就是与他人共有同类的常识、将指向适当目标的行为方式通过经验习得于身。试想,与我大同小异只拥有有限知识的无数的人们,各自行动的同时,创出具有某种程度秩序的社会,对其安定性并不抱太多的怀疑而生活着。这是令人惊异的事情,但创造出社会这一事物的却正是这些人们各自的常识和实践。
我们对社会首先能实感地确认的事实是,生活于社会中的每个人的知识极为有限和不完整。我们于日常中能以视觉、触觉所接触到的,只不过是我们相信存在的“社会”中的很小一部分。尽管如此,我们想象“社会”这一事物具有某种真实性,据此而可以作各种选择。如考大学、纳税、买卖股票等等。在这里有一种常识性的行为方式,几乎所有的人都已习得,所以大规模社会才能保持某种程度的秩序而存续下去。
二、方法上的个人主义
私见以为,“地域社会论”的暧昧性、不定型性出自研究者企图站在这一社会偏僻角落的行为者的视角来观察问题。“地域社会论”屡遭批评的一个特色是,不以像封建制、奴隶制那样的结构性的关注为前提,而是从每个人在宗族形成之类的事件中如何行动的微观事例出发来研究社会。初看起来,似乎处理的是与大局无关的细微琐事。但是,其关注的并不限于个别的微观事件。从这些事例抽象出当时人们的行为模式、选择的逻辑、社会图像等,将其作为整合性的概念性的模型加以把握,然后在更一般性的联系中加以理解。从被视为“地域社会论”式的多数研究中,都能感到这一方法论方向的存在。微观抑或宏观之类的问题,不是绝对的大小问题,而是方向性的问题。不是像神那样高高在上以超然的观察来把握社会,而是从社会各个角落里每个人的选择行动的集合构成社会的视点出发,去理解人们为何如此行动,此时,此方法论的方向无论如何只能是从人们的行为与动机出发,成为一种微观的、由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屡屡有“地方社会论”缺少国家论的批评之声,然而“地方社会论”自一开始就没有将国家作为屹立于社会之外的巨大实体来理解,而是从考察人们如何看待官吏、何故服从官吏的视角去解读“国家权力”。这正是要点之所在。
从个别人的动向去考察社会变动的方法论方向,我在修士论文中开始思考物价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强烈感知到了,我用“方法上的个人主义”一语——虽然论文中未使用此术语——来称呼它。我这种关心方式,连同对发展阶段论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对抗意识,在我有关物价问题的论文中作了相当明确的表达。当时我用“方法上的个人主义”一语考虑到的方法论的方向性,是与人类行为的相当合理主义的解释结合起来的。有感于“封建制”、“共同体”之类的术语,暗默之中将“当时人们为何采取那样的行为”之类的问题封杀,用从外面看的视点将当时各种各样的现象在过去的时段中定位,因此,我试图揭示,与此相反,当时农民和地主的经济行为,是基于与具体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细致利害算计的结果。那时,我读了经济学者原洋之介运用数理经济学方法解释华北农村共同习惯的论文,颇感震动。他认为:“仅从制度存在形态的外在观察构建起的发展阶段理论,在理解人类的行为方面存在不足”,“从关于人类的行为动机的现实而妥当的假设出发,解释历史上某一具体制度的形成、发展的方法,正是现代经济史学所最须要的。”对原氏的这一见解,我深有同感。稍后,我读到俄国(苏联)经济学者蔡雅诺夫的《小农经济原理》一书,已是七九年到八〇年间做助手的时候。
“经常‘从经济经营者的观点’出发……去理解subjective(主观的=主体的)的经济算计的意义,由此弄清必要的范畴。”我认为蔡雅诺夫的这一态度完全正确、得当,这种看法,现在也没有改变。但此后随着我的兴趣从经济史扩展到社会史方面,我关注的问题转到如何解释难说必定“合理的”人们的行为上面。通过对诸如明末阳明学、民变的考察,现时感到的是,个人的所谓合理的利害算计和超越的集体意识、伦理,是深深纠缠在一起、不能分割开来单独讨论的。例如像我对阳明学所作的论述那样,如果说人并不感到自我被局限在个人的肉体,实际上可能在扩大的血缘集团、甚至在人类的水平上感觉到——没有人会认为此种感觉是“错误的”吧——,那么利己和利他的区别就失去了意义。如此,如果考虑到在极端的情况下,正是为无私奉献所强固支撑的团结,才能够获得最好地保护其成员的实际效果,那么,作为一种经验性的感知而习得“放弃个人私利而获得自身保护的策略”,就决非不可思议。我被明末清初时期所深深吸引的,就是这个社会动荡的时期使得孕育着个性与共性之间此种紧张的相即性完全地显在化。但是,这种关注并不是全新的方向,也有我过去的关注、兴趣复兴的一面。
三、不安的历史学
当我们思考“社会角落的行为者”构造社会秩序的过程时,“以不安为媒介的聚集”和“经由常识的交流”两条路径就浮现出来。这两者并非互相排斥,也不清楚是否一切都能为两者涵盖。不过,对我而言,“不安”和“常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词,故首先就这两者加以思考。
自己生活的社会不是确定的实体,而是人们深信不疑的产物,稍加挤压,就会哗啦啦地崩塌。这种不安感,自孩童的时候即隐然于心。例如关于战争,我所关心的不是直接有关战争造成的灾难和罪恶,而是倾向于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将战争视为理所当然而毫不置疑,而今几乎所有的人又都理所当然地加以非难?”“能够说今天就正确吗?”我对“群众心理”(当时觉得是非常高级的专门术语)一词抱有兴趣,曾经考虑如何才能不为其裹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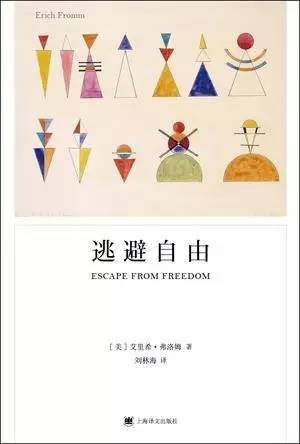
《逃避自由》中译本
刚进大学的时候,偶然中几乎同时读到了社会心理学家伊里奇·弗洛姆的《逃离自由》和增渊龙夫的《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深为铭感。弗洛姆的著作论述了从都市析出的下层中产阶级为无根之草的不安感所驱使,逃离自由,集结到纳粹主义的旗下。增渊的著作是处理以战国动乱为背景的“任侠式结合”形成的众所周知的名著。两者处理的时期和地域完全不同,但都描绘了旧秩序崩溃、从人与人相互争斗的不安中产生的对共同性的痛切要求反而束缚着人们的动态过程,我在感动之余,也深深感到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共同性。在处理以社会流动为背景的明末清初社会集团形成的潮流和阳明学的共同性理论等问题的本书各章中,读者会感受到这些著作的直接影响。

增渊龙夫的《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对“社会不安时期”明末清初的关心是贯穿本书的一个特色。因此书名中也特意用了“明清交替”一词,以凸显对伴随国家权力真空而来的秩序崩溃的不安感。第一章用到的“流动化”一词,也许会令人想起英语圈明清史研究中一直使用的social mobility。但是,英语圈的社会流动理论是为了以近代性的能力主义社会模型为基准测度社会阶层的流动水平。与此相对照,本书的“流动化”理论,毋宁是有关笼罩着明末清初社会的秩序崩溃的不安和混乱的。由不安驱使的人们生出的各种社会现象,如以权势人物为中心形成隶属性社会关系、拟制血缘性的集结、社会集团相互间的激烈抗争等等,毋宁呈现出与社会流动水平高而安定的社会系统的对极状态。本书所说的“流动性”,不是在宏观社会发展图像要素中表征“近代性”的指标,而是秩序动荡时期反复出现的社会性不安感的背景。因这一“流动性”概念而遭到“超历史的”批评,并非没有缘故。在这种社会不安中,人们要根本性地直面秩序问题,而我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迫切将我们的时代与当时联结起来的关心。
“地域社会论”的研究方法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根本上以“秩序的希缺性”的感知为前提,试图追问“秩序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对“地域社会论”和前此谷川道雄提出的通称为“谷川共同体论”的理论的常见误解,是将它们看作忽视了权力、统治诸问题的牧歌式的乐观的社会秩序论。不直接讨论阶级斗争、反权力斗争,而是探寻“领导权”之类社会整合的契机,“地域社会论”的这种态度,或许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吧。但是,私见以为,正是因为“地域社会论”者和谷川道雄作为其前提的社会观是“万人对万人的抗争”,所以他们必须问“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
阶级斗争史观虽可以说是一种动态斗争模型,但对我来说,令人不满的是阶级斗争史观对秩序的存在自身及其必然的、继续的发展持先验的信赖。构成阶级斗争史观基础的如建筑物一般被实体化了的社会构造的图像,与其说回答了我上述的问题,不如说让人觉得自一开始就封杀了这一问题。我感到阶级斗争论的某种乐观性,就在于不考虑霍布斯视为“人类之业”的秩序问题。当然,我不否认,正是这种乐观性在社会改革的实践中,鼓励着人们追求理想。并非简单批评实体化的社会像的虚妄就可了事,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会改革的实践中,正是这种实体的社会像,支撑了人们的行为。对此必须带着尊重的意识加以正视——,这也是我另一面的实感。
四、日常生活的意义构造
记得从初中到高中,我曾一度对“常识”一语非常感兴趣。热衷于英国评论家、小说作家切斯特顿,也是那个时候。他因写作以布朗神父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而出名,但正如西部迈所强调,他不仅仅是个幽默作家,更是个不容轻视的保守主义评论家。当然,我当时的理解力有限,但《星期四的男人》等小说中到处可见的警句,显示着切斯特顿对“秩序的希缺性”的敏锐感觉,与他机智而充满讽刺的对“常识”、“健全的秩序”的救护一起,吸引着我的心智。我不太清楚自己是否保守主义者,但至少有种模糊的感觉——对这个世界能恰如其分地运行的惊奇感、理所当然的日常性的共识中有着某种贵重东西的感觉、不喜欢无视让这个世界正常运行的重要性而盛气凌人地批评现状,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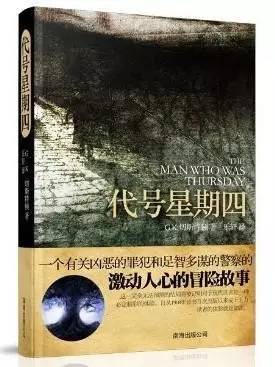
切斯特顿作品:《代号星期四》
1981年学术研讨会上森正夫基调报告的特色之一,是强调“意识”的重要性。意识的问题历来在意识形态论的形式下加以处理。而在意识形态论的情况下,有一种“意识形态=虚伪意识”的含义,亦即认为意识形态是遮蔽真实的面纱,只要将这层面纱揭去,作为实体的客观的社会构造就会显现出来。与此相对照,本文对“意识”的着眼点并非如此,而可以说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方式:为当时的人们所共有的社会意识本身创造了社会——在束缚我们的同时支持着我们的社会秩序,正是此种共同主观的产物。这次学术研讨会围绕民众对地方社会的领导权的赞同,简单地说,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将此看成统治阶级强制灌输意识形态的结果,另一种则看作真实的共同性的纽带。对于这一点,我没有特别深入的考虑,在研讨会上作了这样的发言:“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赞同,还是被蒙骗后的服从,问题不是决定哪个看法正确,不是哪个都行吗?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人们在地方社会见到各种各样的行为,作出那个正当、这个异常之类的常识性的判断,在这种判断的方式中,难道不是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可以说是固有的社会性的问题吗?”关于这样的问题,在社会学学科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注意到这一点,是这次学术研讨会数年后的事情。
现象社会学术语“日常生活的意义构造”,将我曾经模糊地爱用的“常识”一词,赋予了更加明确的表现形式,同时也觉得证明了将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正当性。对于无限多样的混沌的这个世界的诸现象,只有自赋予意义开始,人们方才构成社会这一有意义的事物,相互间的交流方才可能。这里建构起来的“日常生活的意义构造”,在人们赋予意义工作的产物这一点上是“主观的”事物,但并不是因人而异的,而是不论立场、信条的差异,只要是具有社会常识的成员,就会共有的“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构造。它也可以置换为规范、秩序等词语,但不应当作将人们的行为强制地齐一化的框架来理解,而应当被看成为将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人们的行为赋予意义予以解释的坐标轴。所以,即便是社会的激烈对抗,只要作为有意义的事件加以理解,那么就被包摄于一定的认知世界中。
本书的第四、第五章等部分,处理的是明末清初动摇了江南社会的诸事件,但关注的焦点不在那些事件的“事实”本身,而在于那样的事件作为什么样的情报传递给了地域社会的人们,然后人们赋予它们什么意义。着眼于“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之类主观观点的方法,作为“地域社会论”共通的偏重主观的态度,被当作像“无足幽灵”那样的观念论,屡屡遭到批评。这里要辨明的有二点。第一,私见以为,此种“主观的研究方法”,至少与这样的态度几乎没有关系。这种态度否定历史学中客观论证程序的可能性,将历史学上的主张归结为终究不可能对话的论者的主观。我觉得这样的原则是正确的:“(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必须处理社会实在中的人类行为及其常识性的解释。……这样的分析必然地不得不涉及从行为者的观点去解释行为及其背景的主观的视角。”(许茨)这是因为,与苹果落地之类的自然现象不同,人类的行为是经过人类的主观而进行的。明末江南社会为什么会发生民变,如果不通过追问当时的人们如何看世界的动向、将什么视为正当等问题,则无法解释。只要关涉人类的行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主观的解释”,方能采用假说与证实(证伪)的科学的程序。
包括我的论文在内,被视为“地域社会论”的诸研究,在这样的程序方面是否十分严密,当然还有讨论的余地。但我相信,“地域社会论”的目标,并非像屡遭批评的那样逃避社会科学,而毋宁是要摆脱教条化的社会实体化和不能证明的必然论,以开放的形式,将由人类行为织成的社会的动力学理论化。在这个意义上,我——在“后现代”流行的现在——或许可以说是相当旧式的“社会科学”的信者。
第二,着眼于人们意识的上述研究潮流,与对历史的物质性诸侧面的自然科学式研究决非对立。1979年在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举行的“江南三角洲学术研讨会”,是组织农学专家和中国史研究者对话的划时代事件,成为此后对中国史上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等展开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契机。这次学术研讨会作为八〇年代以降明清史研究新潮流出现的契机,屡屡与八一年名古屋大学的“地域社会论”学术研讨会并提,也有说法将两者对立起来,怀疑重视意识问题的地域社会论不得当地轻视历史的物质侧面。但私见以为,社会科学中重视主观的视角,批评的是不经意地将自然科学的类推应用于社会性的现象,丝毫没有轻视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之类问题的重要性,也没有否定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这些问题的有效性。莫如说,八〇年代以来的两股新潮流,是作为对过去拟似自然科学的社会经济史的批评同时出生的双生子。
那么,描述根据人们的主观认知形成的社会秩序时,作为方法性的难题模糊萦绕于我脑海中的,是这种“说明”的方法,最终果真能否说明人们主观的根据——人们为什么如此思考——的问题。例如,考察乡绅为何被认作为有势力者的问题,其根据可列举拥有大量土地、官僚经验等。但是为什么乡绅能急速集中土地、官僚经验为何成为威信的源泉之类的问题,就必须作进一步的说明。不先验地假定乡绅、官僚的势力,或者国家权力,那样的说明可能吗?此种说明的尝试能进行到什么地步而不会陷入逻辑上的循环论证?
在本书第二章的论文中写道:“假设人们选择乡绅作保护者,那么其基准不是拥有土地、与国家权力的联系本身,而是在地方社会具有的实际保护能力。然而这种保护能力也来自众多人们在乡绅下面的集结。这是明显的循环论证。”当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的想法是稍作停顿,将问题摆出。而另一方面,也怀着这样的想法:某种程度上觉察到了乡绅势力的根源只有以这样的循环论证才能作出说明。此后,虽有些晚但意识到了,在社会学领域,以“自组织性(aoto-organization)”、“循环回归性(reflexiveness)”、“自再生性(autopoiesis)”等术语讨论的问题与我未完全解决的疑问有关系。也就是,作为“基于成员对系统自我认识的自组织”的社会形成,或多或少不得不包含我提到的悖论。这一“发现”并没有解消我数十年来对社会抱有的不可思议的感觉,但至少这不仅仅是我的异常感觉,而且暗示着或许所谓社会本来就是因这种循环论的机制而成立的。
以上就“地域社会论”方法的若干侧面,夹杂着个人的事情,陈述了我的见解。社会的脆弱、不安定、狂奔时的苛烈,还有不可思议的精妙,一直以来我对些的关心,换句话说,就是这样一种惊奇:如此不完全的人集合起来,为何社会能够恰如其分地运行?因此,在观察明清社会之际,不是从高远处着眼,而是从观察和我一样对社会的整体抱有不透明感的人们如何摸索着构建社会的角度着眼。然后想在同样的平台进行对话。被视为属于“地域社会论”流派的研究者不一定全都抱着同样的感觉从事研究,但这里或许仍然存在作为一种时代思潮的对所谓“社会”的实在性和发展的必然性等的怀疑和不安。
以上所述,从今天社会科学理论的前沿来看,确实是幼稚而朴素的感想吧。但是,我认为如此足矣。作为历史研究者,首先使出独自的全部感觉能力直接接触对象,这是首先要解决的。由此而获得的知识,对于我来说只要是有效的,如此足矣。就这一方法,笔者只是尽可能给读者亮底,至于是否妥当,则有赖于读者的判断。
编辑:王瀚浩
微信:njuxueheng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交叉、理论创新的重要平台和研究基地,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为宗旨,致力于概念史、历史记忆等跨学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