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社会变革,至迟在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已基本成为我国学界的共识。多年来围绕这一论题争议颇多,涉及变革的属性、程度以及起始、路标等诸多问题,因而形成各不相同或不尽相同的多种唐宋变革论。但从总体上否定唐宋变革论的研究者极少。近期唐宋变革论似乎遇到颠覆性质疑。有鉴于此,草成本文,谈些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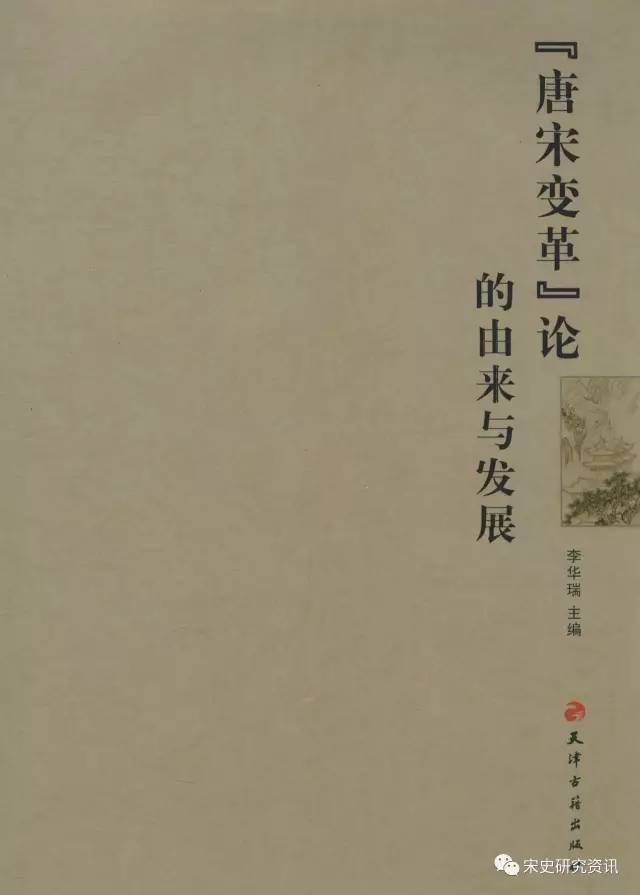
一、从是对还是错说起
唐宋变革是个较为复杂的论题,唐宋变革论又各式各样,只怕很难以是“对”还是“错”,一字以蔽之。前些日子有篇访谈录在网上盛传:《唐宋变革论错在哪》。标题相当吸引眼球,加之受访者是一位当今在中古史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于是访谈录收到奇效,点击率甚高。因访谈录谈及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刘子健、张广达等大家,在习惯于浅阅读的某些网友中又流传:“陈寅恪等大家都是唐宋变革论的反对者。”访谈录公布稍前,已有一篇书评在网上热传:《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吗——读包伟民教授〈宋代城市研究〉》,据说同样对唐宋变革论持否定态度。学友推荐,立即阅读。一读便发现:访谈录、书评与受访者、书作者的原意不尽相符。
受访者并未一概否定唐宋变革论,访谈录居然题为《错在哪》。一查方知,此标题系某网络编者所为。访谈录原载2016年5月29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题为《陆扬谈唐宋变革论》。《澎湃新闻》发布这篇访谈录,标题是《唐宋变革论究竟是怎么回事》,与受访者的原意吻合。日前有幸偶遇陆扬教授,虽未暇深谈,但他证实:《错在哪》,此标题和他无关,与其原意不符。不仅标题被误改,访谈录中的个别文字只怕也有记录之误。下面两句话就比较明显,一句话是:“陈寅恪从来没有关心过中唐。”众所周知,陈老有关中唐的论著颇多,其中最著名者当推《元白诗笺证稿》。另一句话是:陈寅恪“好像没有‘中唐(变革)论’这个说法”。习唐宋史者都记得,陈老《论韩愈》一文所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也记得,张泽咸曾引经据典,以此作为重要依据的之一,认为唐宋之际变革论“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上面两句话似乎不应出于受访者之口。

至于“陈寅恪等大家都是唐宋变革论的反对者”,更是出自某些网友的误会。据我所知,唐长孺、田余庆因其研究重点不在宋代,并未对唐宋变革论公开发表否定或肯定的意见。而张广达则是唐宋变革论的阐释者,且颇有深度。对于将陈寅恪的中唐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对立起来,柳立言已指出:“这恐怕是误解,因为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大多主张‘唐宋变革’的起点是中唐。”中唐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其实是一回事,前者是就其起点而言。刘子健固然是两宋之交变革论的倡导者,但他同时又是唐宋变革论的赞成者。刘氏曾说:“从宋代开始,中国已经步入近代时期,阶级区分远不及唐代以前那样严格、硬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世族没落,平民式的家族抬头,都和近代社会相像或相近。”在我看来,其中“近代”一类的词句未免欠妥。但刘子健并不反对唐宋变革论,应无疑问。此事并不奇怪,如王瑞来便既主张宋元变革论,又认同唐宋变革论。他说:“唐宋变革论与宋元变革论并不矛盾对立。”
至于前面提到的书评,恕我直言,只怕有将书作者包伟民塑造为唐宋变革论的反对者之嫌。书评反复说,唐宋变革论者如何认为,书作者又如何另有主张,将两者置于绝对对立的境地。在我的印象中,包伟民是一位相当标准的唐宋变革论者。他在《宋代财政史研究述评》一文中说:“中外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唐宋之际构成了中国传统历史发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期。”并从财政史角度梳理出“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三个重要表现。近年,他又是李华瑞主编的《“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一书的参与者之一,著有《唐宋转折视野下的赋役制度研究》一文。“转折”只怕不是“变革”的反义词,应当是其近义词。包伟民新近又说:“如何理解、对待‘唐宋变革’这个概念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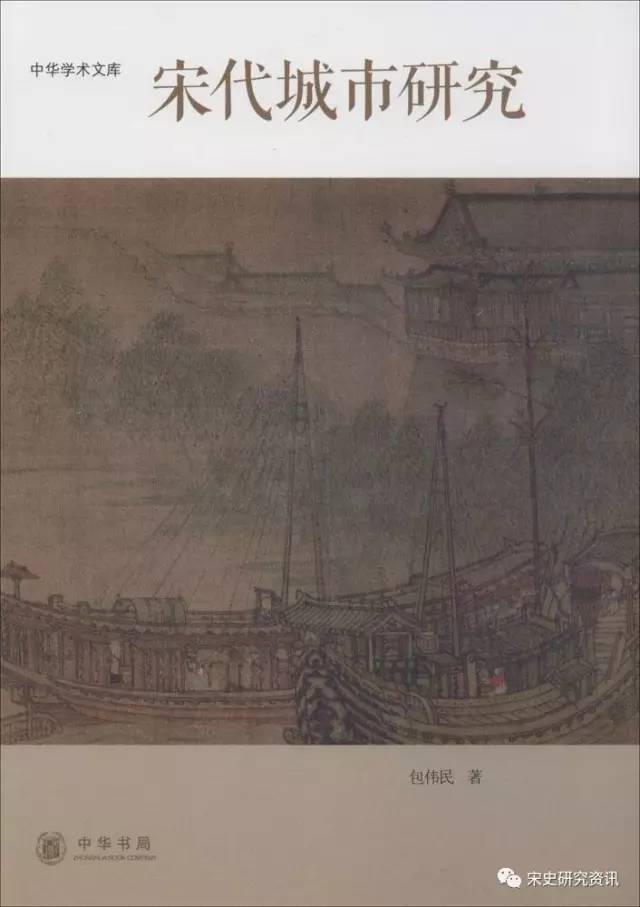
《宋代城市研究》一书创见颇多,但并非颠覆旧说之作。书作者说:“发展范式(除加藤的坊市制度崩溃论而外,还包括伊懋可的宋代城市革命说)有着充分的依据,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归纳。本书遵循前贤的这一思路,试图有所推进。”他所反对的是“范式过度强化”,但仍对唐宋之际城市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持肯定态度。此书的最后一段话是:“总之,经过自中唐以来长达两三百年的历史演进,大致到南宋时期,中国的传统城市终于进入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并由此建构了此后近千年的基本格局。”而书评则说:《宋代城市研究》一书“从城市史研究切入,揭示了宋史研究范式转向的路径——从片面的唐宋变革论转向更为客观的唐宋会通论,并提供了精彩的研究范例。”唐宋会通论与变革论究竟是什么关系?是“转向”还是“正向”?留待后文再议。矫枉难免过正,但从此极端跳向彼极端,终究不宜。
二、谁将内藤奉为圭臬
我个人认为,而今对唐宋变革论的最大误解莫过于:每提及唐宋变革,言必称内藤湖南,将一切唐宋变革论均视为“内藤假说”影响所致,把所有唐宋变革论者都看作“内藤假说”的信徒。访问者与书评作者便具有这种倾向。前者称:“内藤湖南提倡的唐宋变革论影响极大。”后者更是说:内藤的唐宋变革论“直至今天,依然被宋史研究界奉为圭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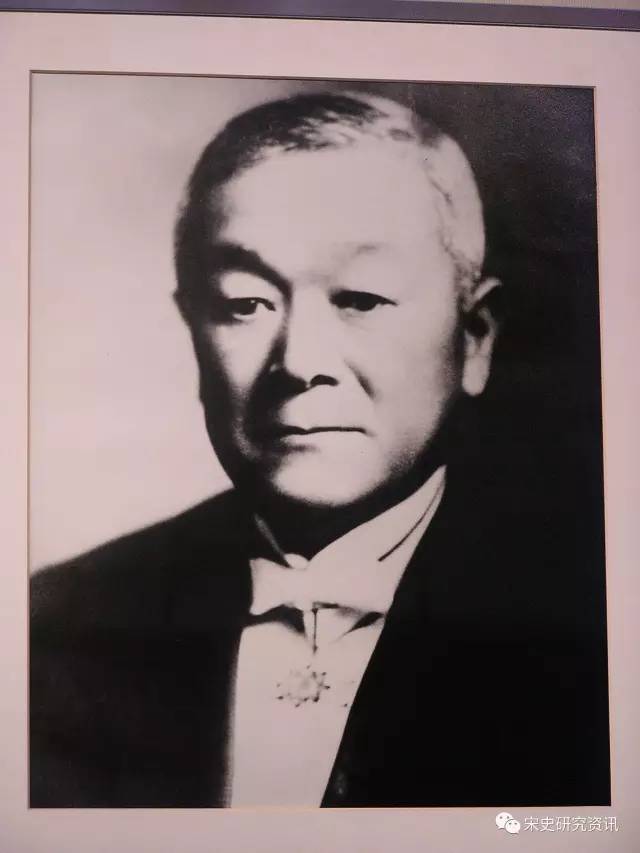
“影响极大”、“奉为圭臬”之说只怕不妥。仅就日本学界而言,就不是“内藤假说”的一统天下,绝非独此一家,别无它店。我们应当知道,日本学界曾有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和以前田直典、周藤吉之为代表的东京学派之争。他们虽然都主张唐宋变革,但并不相同。前田的“宋代中世说”与内藤的“宋代近世说”针锋相对,周藤的“宋代农奴说”与宫崎的“宋代自由佃农说”互不相让。加藤繁是东京学派开山白鸟库吉的弟子,与内藤不是一回事。书评作者只怕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有将加藤与内藤混为一谈之嫌。2006年6月19日,加藤的弟子斯波义信曾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座谈唐宋变革。在回答提问时,斯波直言不讳:“这一点我和日本京都学派(内藤虎次郎)的看法很不同。”这不免让人怀疑某些言必称内藤者,对于日本学界乃至“内藤假说”究竟知道多少。曾到日本大学做访问学者、对日本学界了解较深的虞云国指出:“支持其唐宋变革说或宋代近世说的整个内藤中国史观,却脱不开他的时代与立场的烙印。”这句话“你懂的”。如果对其“烙印”略有所知,相信更不会将其奉为圭臬。
尤其应当正视,唐宋变革论在我国学界源远流长,不是舶来品,并非纯粹属于所谓“东洋教条”。以下四点即是其证。
其一,“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不是日本学者,而是南宋史家郑樵。”几年前,我曾如是说。我们不应当忘记,郑樵有句名言:“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不是简单的史料,而是精辟的史论。岂止郑樵一人而已,在他之前有沈括,在他之后如王明清、胡应麟、顾炎武等人,他们对唐宋变革均有所洞察。沈括侧重婚姻习俗的变化:隋唐“重族望”,士庶不通婚,“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王明清着眼高门士族的衰败:“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胡应麟披露门阀制度的崩溃:“五代以还,不崇门阀。谱牒之学,遂绝不传。”顾炎武揭示土地私有的演进:土地占有者在汉朝、唐朝被贬称为“豪民”、“兼并之徒”,“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诸如此类的论述均表明:唐宋在中国,唐宋变革论的根不在外国,也在中国。我们岂有数典忘祖之理。
其二,上世纪前半期,近代学科体系建立以后,我国主张唐宋变革论的史家甚多,或可以夏曾佑、吕思勉、钱穆等人为代表。夏曾佑与内藤系并世之人,主张有相似之处。夏氏认为:“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两人相识且相交,内藤对夏氏“多有褒赞”,“从其书中,获得某些启发,引起思想共鸣”。照此看来,即便不是内藤受夏氏启发,至少也是相互影响。据虞云国研究,吕思勉“对唐宋之际中国历史有一个重大变化的基本观点,从未改变和动摇过。” 虞云国对吕老与“内藤假说”的关系持审慎态度。他说:“不能断定是否受到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影响。”钱穆当年对唐宋变革论述最多。研究者称,钱穆的“近代”说与内藤的“近世”论系“不谋而合”,“并没有发现钱穆直接或间接受到过内藤湖南的影响”。如果定要追根溯源,钱穆的唐宋变革论很可能来源于其崇敬的前辈学者夏曾佑和恩师吕思勉。吕思勉是其《国史大纲》初版的审订者。钱穆称,吕老对他有“特加赏识之恩”。可见,即使就这一阶段的情形而言,所谓“内藤假说”“影响极大”一说也难以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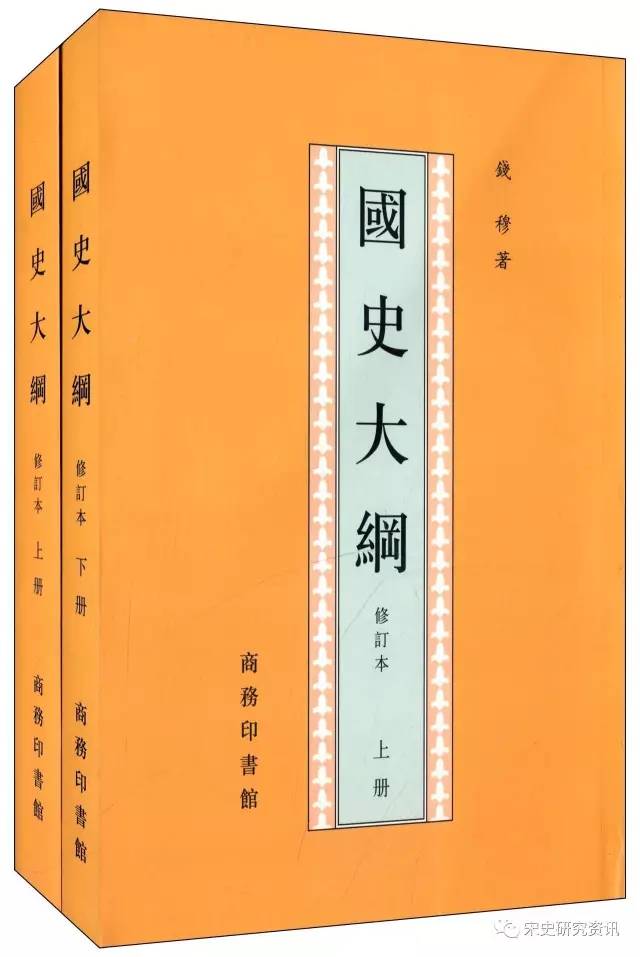
其三,上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历史学大体处于独立自主、锁闭发展时期。这个阶段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我国学者有自己的唐宋变革论,与日本学者明显不同。50、60年代之交,中国古代史学界开展了一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参与者甚多,讨论很热烈,涌现出不少唐宋变革论。其中以侯外庐的论述最具代表性。1959年,侯老接连发表《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两篇论文,每篇均达数万字之多。侯老是当年我国历史学界的“五老”之一,其威望之高、权威性之强、影响力之大,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于是,唐宋变革几成定论。1960年,胡如雷《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一文问世。他后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第五编《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中对其唐宋变革论有更充分的阐释和进一步的拓展。侯老以及胡氏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注重经济基础,突出阶级斗争,与内藤、宫崎等人并无因袭关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以侯老等为代表的唐宋变革论,或可称为我国学界的学术基因。二是对“内藤假说”持批判态度,且火力相当猛烈。1963年,中科院历史所编译室所编《宫崎市定论文选集》,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读物,供批判用。编者《前言》批判宫崎“故意歪曲中国历史的发展”,“建立起一套荒谬的中国历史分期说”。其主要论据之一是内藤、宫崎“断言中国自‘唐宋以来,资本主义成份即日益发展’,至宋代‘资本主义’已很发达”。由于《选集》系内部读物,在学界流布不广。所收论文有限,宫崎的代表作《东洋的近世》《从部曲走向佃户》未收入。
其四,“内藤假说”正式传入我国为时甚晚,传入后赞同者极少。1981年,夏应元发表《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一文以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在我国学界才渐渐广为人知。国内学者读到日本学者的代表作如内藤《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之类,则迟至刘俊文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于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之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传入我国后,学界的反映不是一致叫好,而是很难认同。有学者说:“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期学说是企图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范围这一努力的产物。大致而言,其所谓‘古代’相当于奴隶社会,所谓‘中世’相当于‘封建时代’,‘近世’是指资本主义。无论是将晚唐视作‘古代’(即奴隶社会),还是将宋代视为‘近世’,都是我们无法认同的。”还有学者如实指出:“大多数中国学者既不赞成(宫崎的宋代)自由佃农说,也不认同(周藤的宋代)农奴论。”并以我的《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为例证。此外,如内藤将六朝至唐中叶称为“贵族时代”、把当时的政治称为“贵族政治”之类, 晚周之后何来贵族,我国学者均感到不可思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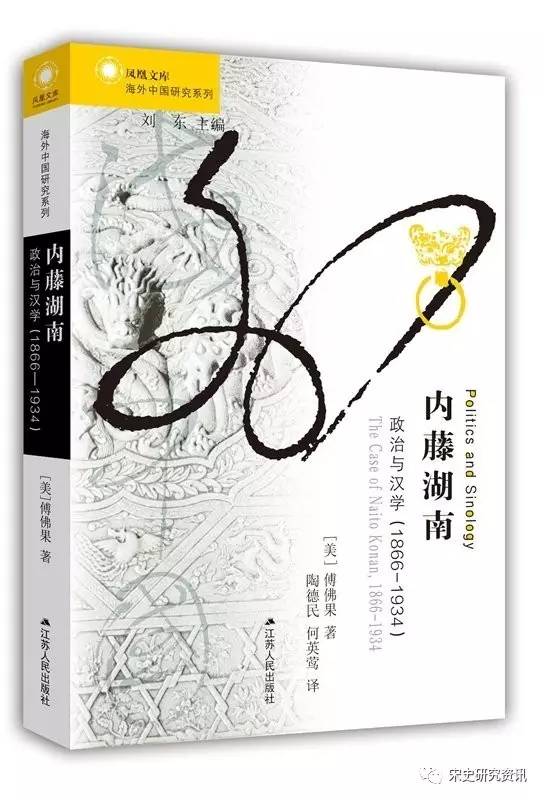
事情原本很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言必称内藤的情形呢?或许与接受过程有关。而今活跃在第一线的宋史学者大多是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研习历史的,他们对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知之不多,首先听说的是“内藤假说”,于是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积久成习,很难扭转。50、60年代开始研习历史者,其情况则大不相同。以本人为例,高中生时代就知道唐宋变革论。当年所读历史教材系前辈史家陈乐素、汪篯、王永兴等所编,侯外庐、邓广铭等撰文给予积极评价,称赞这套教材“严肃而审慎”。按照教材和老师所讲,唐代中叶均田制瓦解,随后府兵制崩溃,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宋代不再恢复均田制,这就叫做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论并不玄妙,原本如此朴实,也如此实在,只怕是很难被颠覆。上大学后得以加深,读研究生时刻骨铭心。1962年,我在金宝祥老师指导下写成并发表了第一篇宋史习作《论宋代的官田》。此文第一句话就是:“中唐前后,土地所有制形式发生重大变革。宋代是沿着中唐以后的路线发展的。”因而本人自称“较为固执的唐宋变革论者”,一再声言:我的唐宋变革论的形成与“内藤假说”没有半分钱的关系。话虽然说得较粗俗,但道出的是实情。1963年以后,开始陆续接触并阅读宫崎乃至内藤等日本学者的论著。我的态度不是视而不见,全然拒绝,而是有鉴别地加以吸取,有批判地予以利用。如我赞成宫崎宋代是“看不见篡夺”的时代一说,认为此说与史实大体相符。至于引用宫崎《从部曲走向佃户》一文,其实是为我所用,抽象认同,具体否定。在我的概念里,部曲不是农奴,而是荫附农民,佃户不是自由佃农,而是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并未完全获得人身自由的租佃农民,与宫崎有实质性的区别。此后,我从婚姻关系、学校制度等方面论述唐宋变革,与“内藤假说”并无多少干系,前者直接继承沈括、郑樵之说,后者则源于吕思勉。他说:“国子学与太学,初本是二,后乃合而为一。”吕老此言对我启发很大。至于在课堂上,我主要介绍的是改进版的胡如雷之说,同时对日本学者的两种唐宋变革论也略作简介,强调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中国学者的“口径”与日本学者是不同的。这些,相信学生们会记得。忆及这些往事,我不免要问:究竟谁将“内藤假说”奉为圭臬?
三、纠偏补弊的若干正解
学术需要潜沉,而非起哄。凡事一“热”,往往就出问题。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唐宋变革论又“热”起来,随之出现了一些应当反思的偏向和弊端。其主要表现是对唐宋变革论作夸大化引申和断裂化处理。继柳立言等学者之后,书作者包伟民与受访者陆扬相继站出来纠偏补弊。他们对唐宋变革论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正解,本人深受教益。

“唐宋变革是个筐,一切变化往里装。”将唐宋变革的范围无限放大,这种偏向较为常见。陆扬反对胡乱贴标签。他说:“唐宋变革论如今时常沦为一种分析古代社会变迁的‘方便法门’,对唐宋这段时期很多复杂的现象,学者在提供解释时往往贴上一个‘唐宋变革’的标签。”并指明其后果:“这就逐渐形成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惰性,从而使唐宋变革论这一概念失去解释的力度,甚至对未来的研究产生误导。”这一偏向被研究者们称为泛化。它之所以产生,只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唐宋变革视为解释唐宋历史的唯一模式所致。邓小南、荣新江正确地指出:“就唐宋时期长达六七个世纪的历史进程而言,‘唐宋变革’显然不是唯一的认识角度。”“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唐宋变革固然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如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的崩溃,三者在时间上虽然并不同步,但紧密相联,都是唐宋变革的重要内容。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方面,唐宋时期所发生的变化甚多,如南食和北食两大饮食系统的形成、起坐方式的改变(从席地而坐到垂脚而坐)之类,虽然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重大变化,但与社会变革并无多少关联,不应将其纳入唐宋变革的范围之内。
唐宋变革不是突变,而是渐变。它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并非翻天覆地、天崩地裂的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渐进过程,很难一刀两断。探究唐宋变革,宜用过程论。陆扬在访谈录中说得对:“以前往往认为宋代是反五代的,其实宋代对五代也有很大的继承性。”并举例以证明之:“五代为后来施行文治奠定了一个基础。”的确,五代重武轻文,只是概而言之。五代某些统治者有重文的一面。如梁太祖朱温号称“优待文士”,后周枢密副使翟光邺“好聚书,重儒者”,北汉主刘承钧“益重儒者”。再如书院兴于唐、盛于宋,宋代书院的开创者窦禹钧、戚同文,严格说来是两位五代人。
唐宋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因革。邓小南、荣新江认为唐宋两代既“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又具有“连续性”。他们将唐宋时代称为“延续与更革”的时代是相当准确的。从前研究者们探讨唐宋变革,往往采用唐宋对比法。本人即是一例。我早年所著《婚姻与社会·宋代》,开篇就说:“本书将采取把宋代同以唐代为主的前代相对比的方法。”而今反思,对比法的长处或许在于凸现更革,而弊端则在于忽略延续,局限性大,不甚可取。我要感谢书评作者,是她的评介引起了我对唐宋会通论的重视。包伟民在《宋代城市研究》一书中所倡导的唐宋会通论,可谓纠正唐宋断裂化偏向的一剂良方妙药,很值得传扬和推广。我的理解稍有不同的是,唐宋会通论对唐宋变革论不是简单的否定、颠覆,而是正面的充实、提升,不是唐宋变革论的转向,而是其正向。正如包伟民本人所说,他的思路是“因袭与变革并重”。唐宋变革论与会通即因袭论并无抵牾之处,两者相辅相成、兼容互补、相得益彰。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书作者与受访者对理论预设或前提预设均颇有微词。尤以书作者为甚,他较为明确地反对“强烈的理论预设”和“明显的目的论取向”。何谓理论预设,我理解不透,似乎主要是指欧洲历史的概念和框架,以致不惜削中国历史实际之足,适欧洲历史框架之履。无可否认,宫崎对此有所警觉。他说:“欧洲是世界全体中的一个特殊地域,不言自明。把特殊地域的历史发展模型,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其他地域,自然有很大的危险。”然而在其论著中用欧洲模型解释中国历史之处并不少见。中华文化从未中断,中国既无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又无后来伟大的文艺复兴。宫崎有意无意地把魏晋隋唐类比欧洲的中世纪,认为其时“文化停滞,欠缺灿烂光辉”,十分明确地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更有甚者,把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与欧洲历史上的蛮族入侵相提并论。宫崎说:“东洋的文艺复兴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他笔下的宋代不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影子,如宋代皇帝代表民众,犹如欧洲近世国王与第三等级的关系之类。包括本人在内的我国某些学人似乎也或多或少沾染这一倾向,如按照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情形来理解乃至解释宋代的城市、城市居民和市民文艺。这可能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其优势或许在于旁观者清,敏感性强。其劣势可能在于隔靴搔痒,偏离实情。就学术水准而论,内藤、宫崎可谓外国学者中难得的佼佼者,他们有不少精妙的假说乃至论断,但依然难以完全避免其劣势。与欧洲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兴起甚早,往往是政治中心、军事城堡、工商业都会的三位一体。其政治性大于经济性,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这一特性在宋代并无根本性的改变。而宫崎则认为:“宋代都市几乎变为完全的商业都市”,无疑与史实不符。宋代皇帝是士大夫阶层利益的肩负者,士大夫一方面对皇帝具有依附性,另方面又不时表现出“从道不从君”、“以道驭君”的铁骨和傲气,绝非百依百顺。而宫崎则宣称:宋代“士大夫阶层有如羊一样顺从天子”,显然片面性极大。某些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唐宋社会变革之巨超越春秋战国时期,断言:“宋朝是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读者只能怀疑是否译文有误。我国学者研究我国历史,身处其境,知悉国情,优势很明显。我等理当学人所长、避人所短,发扬自身固有的天然优势。
(学友陈鹤对本文有所贡献,2016年10月于成都外东青苔山村)
全文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5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感谢张邦炜先生赐稿!
【编辑】仝相卿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