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无论官方、学界还是舆论,都对“一带一路”与边疆民族等议题有着密切而持续的关注,传统汉文化中心史观的历史知识与叙述更是受到了普遍质疑。在此背景下,蒙元史自然而然成为焦点。蒙古帝国的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其历史与众多截然不同的族群、宗教与文化都有关联,晚近相关出版物往往着重世界史与全球史的视野,由蒙古军事史权威学者梅天穆教授撰写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讲座现场,左起:马晓林,张帆,主持人刘玉海
2017年10月2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与该书译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马晓林在北京彼岸书店就此书与相关焦点议题进行了题为“全球史视野中的蒙古帝国史”的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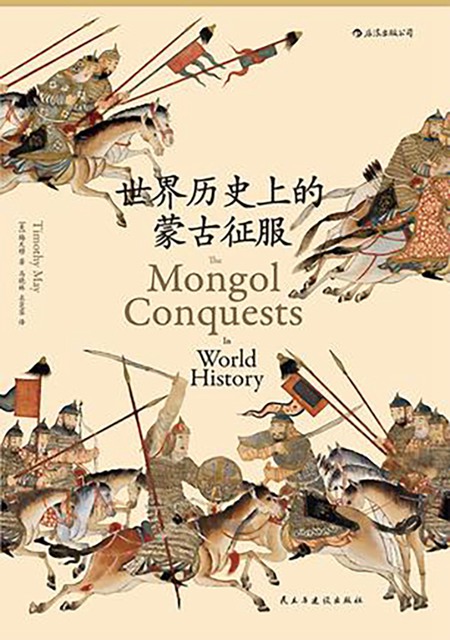
《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书影
为什么说世界史从蒙元开始?
《忽必烈的挑战》、《游牧民的世界史》、《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8卷)均为日本蒙古史学者杉山正明饱受关注的著作。杉山正明试图破除汉族中心论,力主元朝并非中国王朝,汉语史料对于蒙元以及游牧民族的记载有许多出于偏见的不正确指控,并提倡使用多种语言的史料,在全球史的视野中认识“蒙元时代史”(梅天穆称之为“蒙古治世”)。
杉山正明的书在日本就相当畅销,所以他在中日两国都有极高的知名度。这些著作的汉译出版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元朝的讨论,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与罗新《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等等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日本蒙古史学者代表人物:冈田英弘(左)与杉山正明
在马晓林看来,经过了最初新鲜的刺激后,如今汉语学界和中国读者已经对杉山正明产生了新的看法。他的观点承接自早期日本学界发展下来的学术脉络,所以有很多矫枉过正的地方,步子可以说迈得太大,现在的中国学者普遍已经不太想在细处做评论。但杉山正明的过人之处不在于具体观点与考证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他有着更崭新的视角与更宏大的视野,他谈论的主题实质上更是已经远远超出蒙古时代的范围。
实际上,自20世纪初始,国内学者就已经在思考同样性质的问题了,并且迄今尚无定论,马晓林认为这些问题的核心可以归结为:
1、如果宋代代表了华夏文明巅峰的话,蒙元是否只是起到了打断与破坏的作用?
2、蒙元统治者的身份应该如何定位?是皇帝,还是大汗?
3、各大汗国之间是平等国家,还是应该被理解为藩属国?
国内除了中国史学者中专治元史的,许多世界史学者也在进行着蒙元史的研究。但是在国内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划分中,中国史与世界史相对,世界史在原则上是又以国别为分野。张帆认为这样壁垒分明的学科划分弊大于利。在他看来,国内世界史学者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历史研究成绩尚可,但区域史,尤其是古代区域史相关研究则不甚理想。
蒙元史涉及的族群与地域繁多,尤其是学者对自己擅长领域以外的史事已颇感陌生,一手史料又涉及多种语言。如果不具备识读原始文献的能力,多语言的专名转写将是一个难点。仅以忽必烈为例,见诸文献的就有“Qubilai”、“Khubilai”、“Kublai”、“Kubla”等多种拼写方法,但国内世界史学者往往只能引用二手材料,所以研究成果普遍乏善可陈,基本都无法引用。
西方学术界则认为蒙元史首先应该在帝国史的视阈下加以考察。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前,从早期的罗马帝国到近代的帝国主义国家均具有多民族、多文化、没有固定疆域等特点,蒙古帝国也不例外。马晓林提醒道,“帝国(empire)”,尤其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t)”在西方是一个中性词,在中文语境中却长期是一个贬义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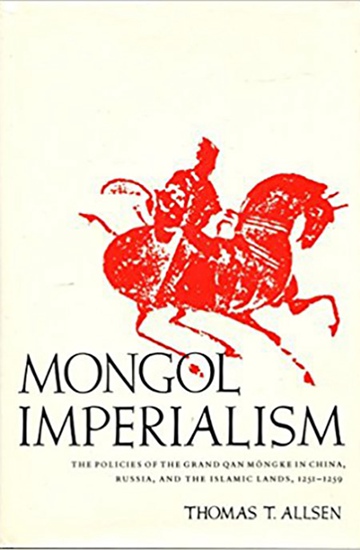
蒙古帝国主义由传奇式的学者爱尔森在其同名著述中提出。
正因如此,国内学界对蒙古的分期是从元朝角度着眼,普遍认为忽必烈即位的1260年以前为“前四汗时期”;1260年至1368年为“元朝时期”;自1368年明军攻陷大都以后则属“北元时期”,1368年之后200余年间蒙古人不同政权的历史都是蒙古史,属于民族史而非断代史的范畴,故与蒙元史再无干系。但西方的划分则普遍以1260年以前为“蒙古帝国初期”,“元朝时期”为“蒙古帝国解体时期”,1368年后为“后蒙古帝国时期”。
西方蒙古帝国史还有哪些重要著作没译过来?
《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为马晓林与其夫人求芝蓉博士合译。马晓林师从荣新江,求芝蓉则是张帆的学生,他们与梅天穆均是旧识。除了此书之外,梅天穆还著有《蒙古的文化与习俗》(Culture and Customs of Mongolia)、《蒙古战争艺术》(The Mongol Art of War)等作品。
梅天穆的主要研究方向与用功最勤的领域都是蒙古军事史,《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中个人见解最多,含金量也最高的自然是与军事有关的相关章节。《蒙古战争艺术》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却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代表了相关著述的最高水准。
在马晓林看来,梅天穆的著作既能反映学术界前沿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诸多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更重要的是,学者著述不同于一般的畅销书,作品含金量更高,也往往容易枯燥晦涩。但梅天穆非常注重学术的普及意义,他的作品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除了梅天穆以外,西方的蒙古帝国史研究还有很多重要的入门书。大卫·摩根(David Morgan)的《蒙古人》(The Mongols)虽然比较老,但是相当经典,此书已经有大陆的出版机构准备出版。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本田实信、John Andrew Boyle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爱尔森(Thomas Allsen)的《蒙古帝国主义》(Mongol Imperialism)则详尽讨论了蒙哥汗以及蒙古的行政制度是如何使整个蒙古帝国联结成一个整体的,。爱尔森是传奇式的学者,他是最早从全球史的角度研究蒙古帝国时代的人,“蒙古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正是由他提出的,他几乎所有著述都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准,在视野与问题意识上都会给人很多启发。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的《蒙古人与全球史》(The Mongols and Global History)则是同一主题更新的专著。
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的《蒙古人与西方》(The Mongols and the West)、《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The Mongols and the Islamic World)是晚近相当值得重视的著述。前书有很多篇幅讲述了后蒙古时代,甚至利用了许多梵蒂冈图书馆珍藏的档案材料。
《剑桥蒙古帝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Mongol Empire)也正在编写中,剑桥伊朗史和内亚史早已经编撰完毕,其中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蒙古,却都不连贯与完整。主编彭晓燕(Michal Biran)和金浩东(Kim Hodong)分别来自以色列和韩国,他们都具有国际视野。
改变世界史的不是蒙古,而是花剌子模人!
冈田英弘用“世界史的诞生”的口号宣告了自己的立场,无论欧美还是日本的蒙古学家都对蒙古征服中残酷的屠杀、惨烈的破坏等有所淡化。
张帆认为研究者很容易对蒙古征服产生代入感,所以可能会不自觉地拔高蒙古征服的意义。他提醒道,在当时蒙古的君主是不可能清楚自己做的事情背后会有什么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他们只是有着最简单与常见的掠夺征服欲望而已,被欧美史学家定位为世界史开端的第一次成吉思汗西征也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

元时期全图(部分),花剌子模位于地图最左边边缘处
中国历史上,在北方草原逐渐强大起来的游牧民族(尤其是草原东部)正常的发展模式都是向南发展,因为他们和中原政权的交流、联系与矛盾都更突出和紧密,他们有充足的理由首先征服中原,无论匈奴还是突厥都是这样的,但是蒙古不同,他们是在初期就向西发展,这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
而造成这一反常的原因,是花剌子模人的贪婪。1215年,成吉思汗试图与花剌子模缔结通商协议的使节和商队被见财起意的花剌子模人屠杀,他们侵吞了蒙古人的商品与骆驼。彼时蒙金战事胶着,一心进攻金朝的成吉思汗再次派出使臣,希望和平解决,竟又被屠杀。史载成吉思汗一个人在行宫旁边痛苦地和神对话,呆了三日三夜,最后才下定了西征决心。然后整个历史竟因为花剌子模的贪婪彻底改变了,如果没有他们,蒙古西征的时间至少会晚上很多。
但自此以后,蒙古的征服就和正常游牧民族的劫掠全然不同了。一般游牧民族的杀伐或是为了财富,或是和对方有宿怨,但蒙古似乎有一种见谁打谁的“使命感”,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要去征服。
马晓林补充道,杉山正明认为蒙古帝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即有一个自始至终的大一统计划,他们想要营建一个海洋帝国。但这或许是一种过于拔高的解释,蒙古人可能只是单纯地想要进行征服,当最后他们把自己战争的野心控制住的时候,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来了。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