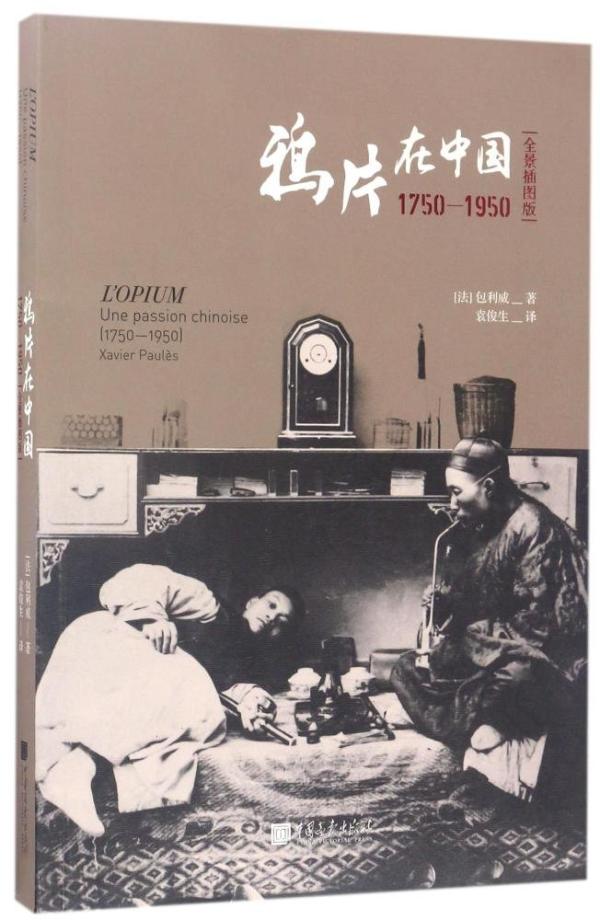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医疗社会史中心 黄运
2018-01-01 16:39 来源:澎湃新闻
包利威1998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广州中山大学做了一段时间法语教师之后,又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克强攻读博士,以晚清民国广州地区的鸦片问题入手研究。除了《鸦片在中国:1750-1950》,另著有《一种垂危的毒品史:1906-1936年间广州的鸦片》《从鸦片战争至当下的中国》,以及诸多相关论文。
稍为熟稔中国毒品史的读者初见此书,心中难免疑惑,关于近现代中国毒品史的书写已经颇为丰富,何以再添新著?不管是国内史家如朱庆葆、苏智良、邵雍、王宏斌、王金香等先生,还是西方学界的研究者如周永明、郑扬文和冯客(Frank Dikotter)等,都已陆续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在《鸦片在中国》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利威广泛吸收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力图补苴罅隙,对中国毒品史研究有所增益,同时,也挑战了一些既存的观点,总之,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观察、分析鸦片对两百年来的中国所产生的作用。那么,具体他是如何去做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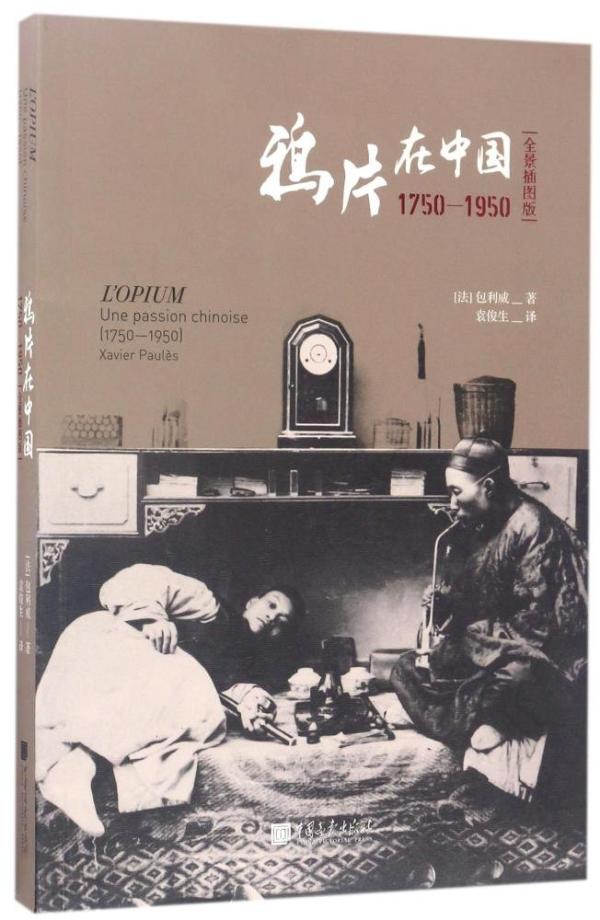
[法]包利威 著,袁俊生 译,《鸦片在中国:1750-1950》,中国画报出版社,2017-7-1
除去序言和结论,该书共计六章,第一章是对鸦片的生产、吸食及性能的概述。这一章既为不熟悉近现代中国毒品史这一主题的读者们铺陈了背景,同时,也论述了鸦片在这两百年中的作用之一——吸食功用。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作者探讨了鸦片在“外交关系漩涡”和“宏观经济”中的角色。此处的“外交关系漩涡”,具体而言,指的是中印鸦片贸易、中英鸦片战争、1907年中英禁烟条约及1911年中英禁烟条件、二十世纪初的数次国际禁烟会议、以及日本侵华战争。包利威对鸦片在上述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而后,他又探讨了鸦片对中国农村经济、易货交易网络、以及税收的影响。在第四章,包利威按照时间序列,逐次评析了自1729年雍正颁布禁烟诏令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各个历史时期内的禁烟政策。在该书的最后两章,包利威聚焦到鸦片的消费者,他首先在第五章阐述了烟民群体的变化过程和特征,而后分析了不同的鸦片消费场所,试图厘清谁在消费鸦片,以及他们在何处、如何消费。
在该书的结语,包利威对自己在序言中提出的问题做了回答。这个问题是:为什么鸦片会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令人吃惊地成为红极一时的毒品,又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短短几十年内便被彻底根除?
在包利威看来,鸦片流行于十九世纪的中国,首先因为“从中国购买茶叶的英国需要平衡双边的贸易额”(第268页)。其次,当1729年雍正颁布第一个禁烟诏令时,清政府打击毒品走私的举措很不得力。再次,当时存在一个有支付能力的精英阶层对这一洋货趋之若鹜,刺激了消费。最后,“鸦片消费可以缓解人的失落感”。“只有在社会里看不到前途,或感觉升迁无望的人才会萌生出这种感觉”(第270页)。
至于二十世纪鸦片消费被迅速消灭,作者认为原因在于十九世纪末中国日益崛起的民族主义再次挑起了关于鸦片消费的论战,鸦片被看作民族耻辱,是当时中国国力渐衰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掀起三场禁烟运动(自1906年的十年禁烟计划;1934-1940年的六年禁烟计划;以及新中国的禁烟运动)。最后,民众对鸦片消费的抗议也起了重要作用。
回答了自己提出的研究问题后,作者并未止笔于此,而是继而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吸食鸦片者越来越多是当时中国衰落的主要原因吗?在他看来,“早在18世纪末,帝国官僚机器就已经运转不灵了,鸦片并不应该被认作是唯一的元凶”(第272页)。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鸦片渗透到各个领域,带来不良影响,这是国力衰落的症状,而非国力衰竭的原因。同时,作者认为在经济层面,鸦片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他看来,鸦片“一度扮演着增强国力的角色”(第272页)。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鸦片被用来增加税收,成为国家用来整合经济的一个工具。此外,他还认为鸦片问题催生了一个平民社会阶层,显著的例子便是自清末渐次出现的民间禁毒组织。至于鸦片的社会影响,作者认为,人们在抨击鸦片的危害时,聚焦于那些遭受烟毒的重灾区。而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烟民都是禁烟宣传所描绘的那种穷困潦倒的人。所有能控制鸦片消费的烟民,虽然把钱花出去了,但却没有遭受任何严重的损害。在不损害身体健康,不危害家庭物质条件的前提下,鸦片给烟民增加了多重感受,让他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惬意”(第275页)。由此可见,贯穿《鸦片在中国》全书的主线是,鸦片在1750年至1950年这两百年的中国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对中国外交、经济、政治和社会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鸦片史的书写已有种种,那么包利威这本书的贡献在哪里呢?卜正民先生在序言中的概括中肯而且准确: “若从这一角度来讲述,鸦片的历史就会孕育出一系列其他的说法:一方面,国家的能力日渐强盛,让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意愿,同时也让本国人民去接纳这一意愿;另一方面,社会精英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也在提升,他们已初步学会如何向国家施加压力,但又置身于其体系之外。这两种说法是真实可信的,但却有许多漏洞。而包利威的论著恰好补了这些漏洞,并为这些说法起了有益的改进作用。”(序言,第4页)
此处的“这些漏洞”指的是什么呢?首先,包利威在承认鸦片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着意强调鸦片在两百年中也曾扮演了积极角色。例如,它曾是“易货交易的催化剂”(第108页),“为财富的集中提供了便利条件”(第124页),“加强税收的有力工具”(第125页);“它曾给烟民带来乐趣,有时甚至带来慰藉”(第276页)。其次,包利威更多地关照到鸦片吸食者的“历史”。如卜正民先生概述的那样,“包利威的论著并非仅仅依照国家的论点去作评述,或以供求关系为切入点去展开自己的论述,他向读者揭示出毒品对于每一个使用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还给我们描述出鸦片消费方方面面的差异,这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序言,第4页)。最后,包利威细致梳理了鸦片在外贸盈余、农村经济、易货交易以及税收等经济方面的影响。此外,他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了两百年鸦片史中的种种差异性,例如当时罂粟种植与粮食作物减少的关系,各地区地理环境不同,情况也各各有别。除此,还有各路军阀不同的鸦片政策,不同历史时期烟民群体的不同构成以及民众对鸦片吸食的不同态度,如此等等。包利威还指出了既有的中国毒品史研究中的一些史料利用问题,例如《申报》上的某些不实数字被反复引用以及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禁毒组织夸大的数据作为证据。
包氏“补了这些漏洞”,显见是其本人的一种学术关照,呼应了近些年西方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毒品史研究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向,是多重维度的。有新的研究取径,如周永明以人类学取径的《20世纪中国禁毒史》(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1999; 中文,2016),重点探讨了二十世中国的禁毒运动与国家建构的关系,又如郑扬文以社会文化史视角对中国鸦片史的研究(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2005)。也有新的观点,如对冯客等人对鸦片是近代中国的灾难的质疑。这种质疑,似可称之为“修正主义的”中国毒品史研究。冯客、周逊、拉斯•拉曼(Lars Laamann)于2004年出版的《麻醉品文化:中国毒品史》一书(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2016年该书再版)意在“系统地质疑” “中国曾是鸦片的奴隶”这一观点(2016版序言),强调了消费端对毒品市场形成的推动作用。关注毒品吸食者的维度有益于丰富既有的中国毒品史研究,而质疑鸦片给近现代中国带来的灾难则难以自圆其说。在《鸦片在中国》一书中,包利威提出“日本人‘毒化’过中国人吗”的问题,对此,王宏斌先生2005年在《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已做了颇为详实的论述(该书2016年再版),而李理女士的近著《近代日本在东亚的国家贩毒研究——以台湾日据时期鸦片问题为中心》(2015年)更是提供了确凿证据。
无疑,包利威《鸦片在中国》一书所做的修正,有些是于学界有所补益的,而有些则值得商榷。强调毒品消费维度的毒品史研究有其意义,撰述较为全面的中国毒品史无疑也不能忽略这一方面。提醒史家警惕使用晚清民国禁毒宣传中产生的那些史料(如中华国民拒毒会的相关资料)也有其必要性。可是,过于强调消费维度的毒品史研究则可能“矫枉过正”——弱化了供应端以及那些“中间人”所扮演的角色。西方列强昔日以鸦片强行叩开中国的国门,以及随后危害更甚的吗啡、海洛因等麻醉品倾销,日本侵华时期的毒化政策,对中国都为祸甚巨。更为客观地以鸦片为视角来看待两百年的中国历史,既需要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对西方修正主义的中国毒品史研究做出更多回应,也需要更多的基于原始资料的扎实可靠的研究。例如,近期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册《民国时期禁烟禁毒资料汇编》,就对学界研究大有裨益。不过,更详尽的史料占有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解决中国毒品史研究中的一些争议,因为史料的解读本是见仁见智。西方修正主义的中国毒品史研究的出现,也并非完全因为占据了不同的史料。有鉴于此,中西学界的对话与辩驳也就尤为必要了。
(感谢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勇安教授对本文修改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