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美]包弼德著、刘宁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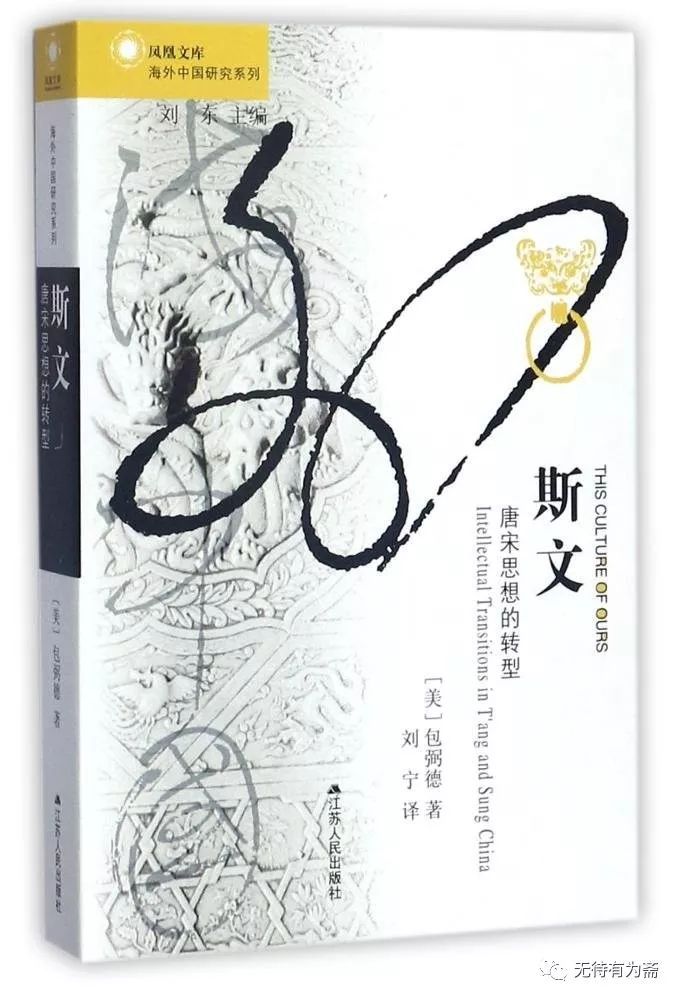
【感谢刘宁教授提供再版序与中译本再版后记】
再版序
包弼德

某些学问始终是国际性的,科学即是如此,在人文领域也有类似的例子。我写作《斯文》,主要是面对英文学术读者,但在中国有更多的人对它感兴趣。何以如此?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学者更喜欢不受哲学、文学、社会和政治等学科的束缚,而当今的美国学者则更愿意在学科之间严其畛域。
写作《斯文》时,我集中研究三个问题:一,中国的精英(我指“士”)如何转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二,“士”的价值结构以及世界观如何转变,这是一个思想问题;三,社会之变与价值结构之变,其间的关系如何。这本书的方法论,在英语里被称为“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心智史和(汉语中所说)“思想史”的区别在于,心智史更加关注“观念”(ideas)与社会的关系。要分析这种关系,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路径。

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是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他的心智史研究,是这类研究中最好的成果之一,体现了法国20世纪所兴起的一种学术兴趣,那就是将观念研究与社会研究相联系。夏蒂埃认为,“社会文化(sociolcultural)史”,比心智史的内容更加丰富,它以“观念”研究为核心,但如果译为中文“社会文化史”,就很难呈现这种核心特点。
心智史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它必然是多种研究方式的综合。单纯的社会史研究,会观察指导社会实践和人们心态结构的潜藏假设与价值构成,这些心态结构人们已经习焉不察,或者简单地认为是自然天生的。这就是所谓的“心态”(mentalities)研究。尽管我这本书是关注知识分子(literati),但有些内容是通过心态研究来揭示大众的心态结构。纯粹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则是就观念论观念。这方面最伟大的代表作是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的《存在巨链》,此书提出有一些基本观念(即“观念元”unit ideas),在历史上成为构造心智生活的基本元素。这些基本观念尽管以不同的语言来呈现,并不断适应新的思想形态,但其内涵相沿不断。它们可以最先出现在一个领域(例如哲学),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再度出现,并适应新的形态,进入其他领域(例如文学)。

“心态史”和“观念史”的研究方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心态史研究认为人们的生活并非随机,人们共同拥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会影响其如何看待并回应自己周围的世界。观念史认为,观念(什么是“观念”?这其实是个问题。我接下来会讨论,)是变动的。对观念的研究必须关注思想生活的所有领域;“观念”在文学中的表现,与在哲学中一样多。
但是,两条道路都有问题。心态史的研究可以揭示深藏的世界观,却不能解释那个世界观为什么发生转变。观念史将观念看作永恒不变和超时间的,忽视了同一个观念何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含义。而且,观念史忽视了思想文化如何通过多种“专门史”的交汇而成型。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lebaum)使用了“专门史”(special history)的说法,我这里就采用这个说法,他指出哲学史,就像艺术史、科学史和文学史一样,是“专门史”。“专门史”是在后人不断回应前人的问题,并对前人的著作不断推进深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诗学实践就建构了一个专门史,新儒家的哲学话语(philosophical discourse)也是。专门史之于其所存在的社会,有相对的自主性,其发展并不由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所决定。如果要说被后者决定,那就意味着社会是一个封闭、完整的体系,而事实并非如此,社会是由错综的利益所组成,在延续不断的社会演进中,这些利益相互交织,形成各种动静起伏。
我在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式,与两个潮流有关,一者出自英语世界,一者出自德语世界。两者在心智史领域都很受关注。前者是“剑桥学派”的语言环境学说。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于1969年发表了一篇今天看来仍非常重要的文章,在文中他提出了这一学说。他认为我们今天写心智史就是为了理解文本,而为了解释他所说的“理解”文本是什么意思,斯金纳批评了另外两种理解文本的方式。第一种是借助外在于文本的社会因素来解释文本,这样做隐含的前提是认为文本的真实意义是由社会、经济、政治因素所决定。“在语境中理解文本,这样做的基本前提,是认为一个特定的文本一定要放在其社会环境中来理解,但这个前提是错误的。”斯金纳承认了解环境是有用的,但是环境并不是行动的必然原因。如果是必然原因,那么为什么有着相同背景、年龄以及近似经验的人,却对环境做出了不同反应?即使有外在于行动者的行动原因,这也不必然意味着理解了这个原因,就可以理解行动者的行动意义。
心智史有一个更核心的观点,即认为文本自身是独立的,文本自身就是理解文本意义的关键,对此,斯金纳做了尤为详细的批评。他认为心智史的史家,为文本赋予了两种“神话”,两者都来自今人让历史文本从吾所好的阅读方法:第一种神话假定作品可以被归约成原理,而且经常是我们期望它们表达,或假设它们所表现的那些原理。第二种则假定一个人的作品都是内在一致的,因此心智史的工作就是去发现思想的一致体系,无视那些矛盾与反常。斯金纳认为,我们受制于观念上的狭隘,把后人关于作品历史意义的认识与作者自身的用意牵合一处。我们批评某人没能说出什么话,也不问问当时他是否有讲这番话的心思;而且我们还基于文本和那些假想原理的相似性来寻找“影响”。
的确,当我们说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是“儒家”或受佛教“影响”,我们就是假定他执守某些原则,他的想法内在一致,而并不真正去细致地调查他实际说了些什么。但是历史人物有时也宣称自己的道理内在贯通。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或者当朱熹说天理就是一贯之理时,他们宣称自己道在一贯,这既是说自己的思想内在一致,也是说自己对种种质疑的回应,条理一致。斯金纳认为,说自己道在一贯,或许不过是要表达期望如此,而非真的在描述自己的成就。他这个说法很对。但他质疑心智史以“观念”为研究主题是否恰当,说“有人认为‘观念’固定不变,这个想法似是而非……这样的历史……从来不正确……如果只关注某些‘观念’,认为以之为基石来探索历史才是恰当的,这是一种概念混乱的想法。”他质疑到这个程度,就多走了一步,过犹不及了。
在斯金纳和剑桥学派这里,观念本身消失了。消失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如果我们要根据一个人说过什么话,来把某些观念归于他,就需要区分这些话是指称一个观念,还是表达了这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的特定想法。因此斯金纳就可以做结论说:“书写一个观念的历史,其实就是书写一个句子的历史。”“只有关于一个特定表达的不同说法的历史,才是唯一能写的历史。”
这样一来,对斯金纳来讲,心智史需要研究各种说法所产生的语言环境。这个“语言学转向”为心智史带来很大改变。斯金纳接续约翰·奥斯汀(J.L.Austin),区分了说什么(言语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statement)和与说相伴随的行为(言语的力量the force of the statement)。要理解心智史,就要既掌握言语的语义(言内意义the locutionary force),又掌握言语的意图(施为力量the illocutionary force)。心智史的研究方法就是要确定“文本的意图是什么,以及这些意图被期望怎样实现”;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文本,而不是撰写观念的演变史或一个人的思想传记。
由此可以说,研究观念史,恰当的方法一定首先是描述一个特定的说法,在它被言说的特定场合,一般都会引起哪些交流,要全面描述这些内容;其次,寻绎这个特定的说法与其丰富的语言环境之间的联系,以此来破解这位特定作者的真实意图。
因此,心智史的研究首先是将表达置于其所产生的语境中来分析。这就是为心智史带来巨大改变的“语言学转向”。在更哲学式的研究中,观念以及拥有传记的社会行为者个体会消失,历史研究则关注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关注有针对性地回应其他文本的特定文本,以及历史上的行动者所要回应的特定经验。
我想学者都会同意,一个人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心意和价值观,任何观念都要以语言来言说。尽管文人有时说,做文是因为不能行其道,但在我这本书所讨论的时段里,韩愈和许多人希望文行兼备,并经常从做文,或者像程颐那样,从言说开始。严格地说,历史只留下纸上的文字,我们要弄清楚——当然也只是试着去弄清楚:首先,那些语言表达在哪一点上和当时其他语言表达的环境相适应;第二,它与其他人所说的有何不同。我们再也不能把“观念”当作脱离语言环境的有条有理的原则。有些人认为观念虽产生在过去,却能裨益当今,即使这些人,他们也承认“观念”不能外在于语言环境。
第二个潮流是德国学者瑞恩哈特·柯赛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y)。在我看来,它与前面讲的第一个潮流是一致的,也是试图理解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语言结构”)和社会实践如何相关。它所运用的方法,历史学者会感到很投缘,因为它询问历史上人们据以理解其环境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可以是一个词,比如“理”,但要理解它的含义,就要研究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人们如何理解它,以及为什么对于讨论它的人来讲,它是如此重要。“理”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对于它的使用,我们可以做历时的研究,但共时性的研究呈现出朱熹和程颐为之赋予了重要的新含义。柯赛勒克注意到有些概念(例如天地),其含义在历史上没有多少变化,有些概念则随时变化,必须做考察(比如“理”或“性”),有些则是为了回应时代而新创造出来的(例如“古文”、“道学”)。概念的形成是社会史的一部分,正因为概念的发展,带来新概念、新实践的普及;当然,概念是社会变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被社会变迁所决定)。柯赛勒克对德语中一个关于现代性的概念的发展特别感兴趣,在研究中他提出历史有一个“鞍型期”(saddle period),概念在这个时期加速转变,尽管他的讨论针对具体概念,但他关注一个时代所使用的概念,关注这些概念如何转变,这个研究方法构成了一种研究框架,可以适用于对其他时代和地域的研究。
思考中国问题时,想想概念如何在某一特定时期形成以及形成的意义何在,这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在755年安禄山叛乱之后,“文”被提升为支配一切的概念,为文士提供了新的世界组织形式,这一直延续到宋代。文治与武治(或者我们可以用科勒赛克的术语说,就是文、武这对概念,变得不平衡了,文胜过了武),文意味着恰当的形式与优雅得宜,意味着文化的、被书写的文学传统,意味着个人的文学写作。科举考试作为选官手段日趋重要,以文学才华取士的进士科名声提高,以至于1069年甚至要废除其他科目,这都特别反映了跟随概念转变而来的社会转变。8世纪晚期事实上是一个概念的加速期,此时“古”作为一种理想被复兴了(这个复兴意义上的“复古”,与恢复“古”的“复古”含义不同);编年体通史兴盛,在这种史书形态中,朝代从属于历史事件的编年记述;因门第而非才华所得到的特权受到挑战;税收制度改变了,国家允许私人市场从事土地的再分配,并不坚持土地分配要依律而行。
三百年后,也就是11世纪中期,又一个加速转变期开始了。这时学者官员开始为儒家经典做新的注释,全面改变政治制度,向商品经济而非农业征税,重新调整选官的考试标准,消解唐王朝的信条(帝国渊源于先王将天地模式转化为社会政治制度),并且为道德寻求普遍基础。这个时期人们激烈地争论,写作了大量被后人铭记的作品,通过政府和私人刊刻,这些作品被广泛阅读。12世纪晚期,新儒学道德哲学(或者说“道学”)在南方大部分地区传播,在13世纪进入科举考试,得到朝廷的认可;1315年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官方科举中被确立为权威解释,并一直持续到帝制时代的终结,这些都标志着那个加速转变期的终结。

我开始从事研究时,想探明士之地位的变化,与士这个理念(ideology)的变化之间,存在什么关系,道学的出现,使这个士的理念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着手这一研究多年之后,我完成了《斯文》一书。我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学”的理解发生很大变化,从“学”被理解为掌握“文”,并通过文章写作来展示,到“学”意味着努力从普遍、通贯的意义上去理解道,并通过个人的德行来体现;理解了这一变化,就可以认识价值观结构所发生的转变。简言之,“士”这个理念(ideology)的转变,可以概括为在思想生活中,从以文学为中心,转向以道学为中心。
对于那些将心智史只是当成哲学史的人来说,这毫无意义。在唐代,有哲学观念的人是佛教的僧人,他们探索理解和践行佛教教义的正道;在宋代,新的哲学观念出自那些自称为纯儒的思想家。然而,如果我们把社会与语言环境中概念的转变看作是心智的转变,那么就很容易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支配唐代士人的价值观结构的是“文”这个概念,以及作为社会行为的文章写作。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科举是相对于门荫越来越热门的选士方式,为什么希望寻求历史突破的韩愈,是用“文”这个概念来标举他的历史位置,以及为什么程颐在把自己和当时的士人之学区别开来的时候,要强调“文害道”。
这本书有不少缺点,我尤其想提醒读者注意书中两个方法论上的问题,以及一个有问题的看法。第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是,我本能地对心智史中的不连续与断裂感兴趣。然而唐宋时期的士人显然努力建立连续性(至少是以“古”作为一个理想世界)。因此王安石和朱熹都在声称自己得孟子之真义的时候,我没有问谁是正确的,而是认为他们对孟子都有自己的理解,并且与孟子的原始意义不同。但是,当思想家们严肃地对待历史文本,他们的确与历史有着连续性与关联性,而不同人的连续性与关联性是需要研究的,不能简单地说他们都是一回事,这一工作我没有做。
第二个方法论上的问题是,我更喜欢揭示思想家思想立场的差异,而不是去发现某一时期不同思想家所具有的基本共性。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我谈到过初唐的思想“信条”,但总的来讲,这本书关注差异,胜过共性。比如,我认为给“宋学”下定义是无用的。像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和程颐这些真正重要的人物周围,聚集着一群群学者,需要对这些学者的共性和差异做更多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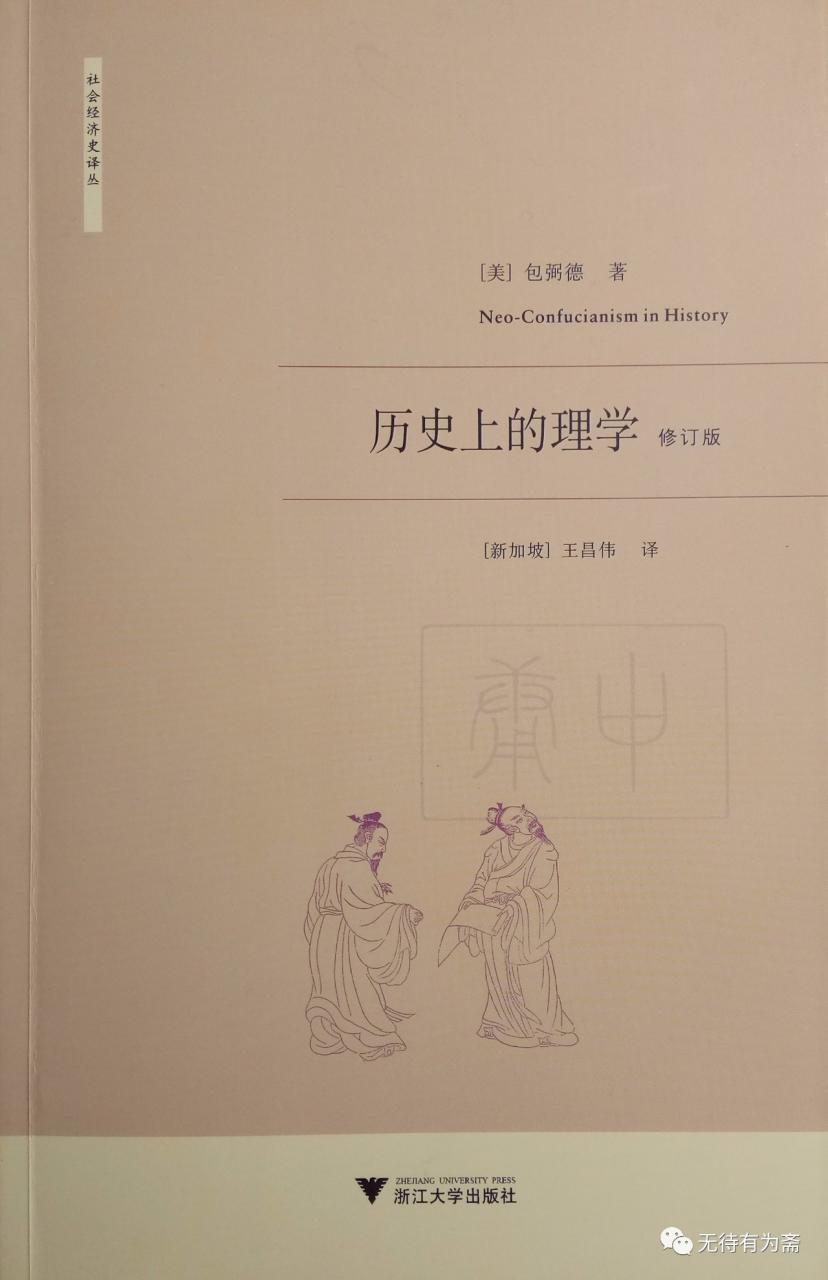
最后,我认为自己有一个历史判断上的失误,没有将王安石、新法与新学,放在更中心的位置。王安石和他的学派拥有一个完整的、包罗一切的蓝图,这个蓝图追求内在一致,即使这种一致性未能实现。王安石提供了新的信条,这个信条基于一种新的理性。即使他那个学派的大部分文献都散失了,我还是认为理解这个蓝图在政治与社会实践中如何体现,仍有很多工作可做。
我再一次感谢刘宁教授对全书和这篇新序的翻译。我还要说明的是,在《斯文》成书以后的这些年,我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对我有重要影响,其中一些影响,就体现在《历史上的理学》一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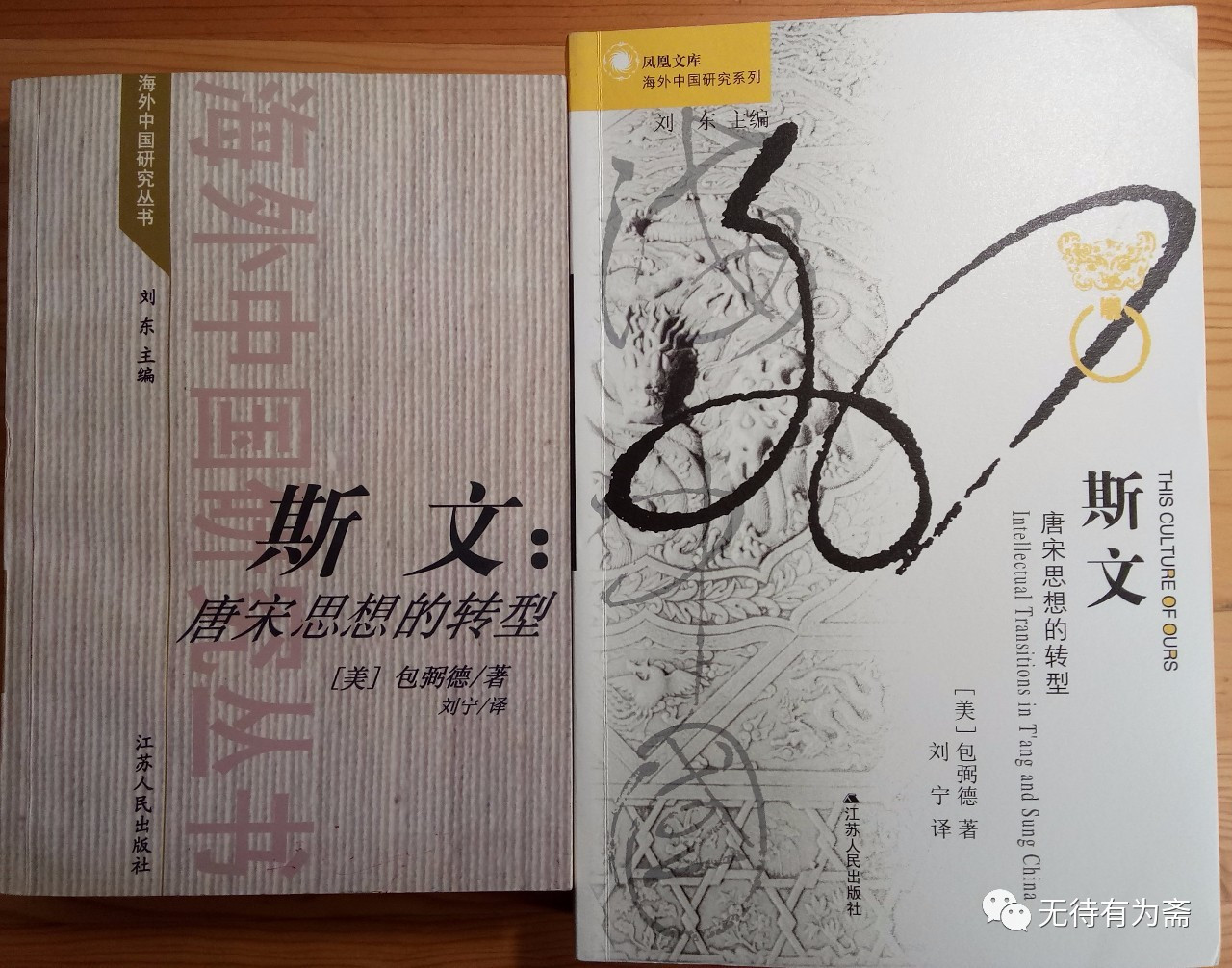
中译再版后记
刘宁
《斯文》的中译本问世已经十五年,汉语人文学界对此书的兴趣,并未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新世纪大陆学人对“唐宋变革”问题日见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也与《斯文》的影响密切相关。
作为一部唐宋思想史,《斯文》的问题意识、理论路径与研究方法,都颇为独特;它虽然有深广的影响,但似乎很难形成某种套路供人摹仿。全书引发最多关注和讨论的,是第二章“士之转型”。这一章对唐宋士人身份从门阀士族向地方精英的转型,做了细致的梳理,其研究视角接续了美国宋史研究对“士人”的关注,而对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基本依循了自郝若贝(Robert Hartwell)以来美国宋史研究的新轨辙。对于作者的结论,人们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比较容易从美国宋史研究的传统出发来理解其背后的方法与理路。然而这一章作为全书的九分之一,是为理解唐宋思想转型的社会背景奠定基础,全书最为浓墨重彩的,是对唐宋思想转型轨迹的深入揭示,其间所呈现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方法,都充满新的探索。
思想文化的转型,是唐宋转型极为重要的内容。“唐宋变革说”从内藤湖南首倡至今,已逾百年,人们已经对这一社会转型的内涵,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多种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比较而言,在有关“唐宋变革”诸多领域的讨论中,对思想转型的讨论最为薄弱。事实上,内藤湖南对历史分期的思考,以“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支那上古史》)为核心,其对“唐宋变革”的思考,虽然并不囿于思想文化而及于政治、经济诸多领域,但唐宋思想形态的变化作为“文化发展波动大势”最核心的体现,对其“唐宋变革”说的形成,显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内藤湖南之后有关“唐宋变革”的讨论中,人们的兴趣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而对思想转型的的讨论,则颇有裹足难行的迟滞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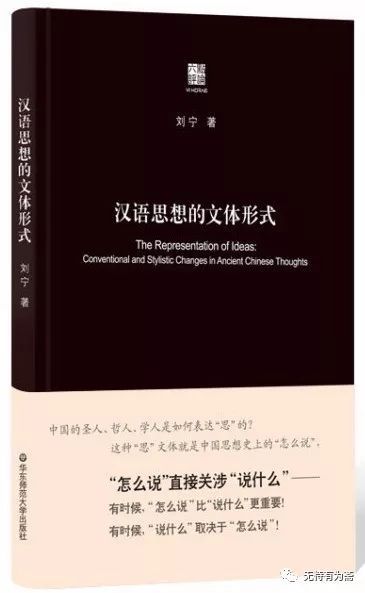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虽然复杂,但内藤假说本身对此的制约,颇可注意。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是近世的开端。唐宋变革是从中世文化形态向近世文化形态的转变。而内藤湖南对近世文化形态的理解,又显著地受到西欧近世文化的影响,认为近世文化的创造主体是有别于中世贵族的平民,因此其文化也以自由、平易、通俗为基本特征。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强调宋诗平易化、日常化的趋向,就是运用内藤近世文化观来观察宋诗的所见。但是,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对于如此复杂精微的宋代思想文化形态,运用内藤以自由平易为核心的近世文化观来加以认识,无疑有着相当明显的局限。而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对“宋学”的研究源远流长,而“理学”又是“宋学”的核心。直到今天,这个传统仍然在理解宋代思想方面发挥重要影响。然而,“宋学”、“理学”的传统视野,虽然可以更尽精微,却难以在社会转型的大视野下观察唐宋文化形态的区别与联系,自“唐宋变革说”问世以来,学界在对“宋学”与“理学”的研究中,也积极吸收“唐宋变革”说的影响,但两者之间仍然有着不易协调的矛盾。
美国宋史研究对于内藤假说的一大调整,就是不再以“平民”来看待作为宋代文化创造主体的宋代士人,而是从精英的社会流动、身份转变等角度来观察宋代士人的新特征。这就为突破内藤假说以自由平易为核心的近世文化观,深入理解宋型文化的复杂内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从基础的奠定,到形成对唐宋思想的新探索,其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很多在宋代士人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也往往专注于这一历史的讨论,而不再涉足思想的剖析。《斯文》对士之转型的梳理,直接继承和发扬了美国宋史学界关注“士人”的学术创变,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在此基础上,积极地探索了深入理解唐宋思想转型的新方法与新道路,它不依循理学的惯常叙述思路,而是从唐宋思想史的内部出发,揭示其起伏转折的轨迹。唐宋思想许多为人忽视的重要内涵,得到丰满的呈现,而理学的兴起这一前人论之甚多的问题,也因从唐宋士人转型和思想转型的大背景来观察,有了别开生面的阐发。在细致梳理唐宋思想流变的过程中,《斯文》所呈现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方法,都不主故常,创获颇多,习惯了哲学史、思想史传统研究方式的读者,阅读这部分讨论,会有陌生难解之感,而包弼德教授此次为再版所写的序言,细致地交代了自己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渊源与研究理路,其中对“心态史”、“观念史”的反思,对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与柯赛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理论贡献的剖析,都可以对读者有极好的启发。

如果说在百年前,内藤湖南首倡“唐宋变革论”是深深有感于唐宋思想文化形态的差异,那么《斯文》就是以其对唐宋思想史研究的卓越创获,对内藤湖南最为关切的问题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学界在未来的研究中,当然还会不断有新的答卷,但《斯文》的影响,应该是后来者所难以忽视的。
《斯文》对思想史的研究,综合了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史等诸多领域的观察,其中从“文”的视角切入思想史,将文学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观察,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深有所见。这样的研究格局,无疑要求学者有综合的学养和融通的视野,有沟通文史哲的学力与魄力。包弼德教授早年求学台湾时,曾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经典,奠定了经史根底,有得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汇通之道。在专业化、技术化日益增强的当今学界,《斯文》会越来越多地展现学术融通的魅力。
在《斯文》中译问世的十五年间,许多朋友对译文中存在问题给予指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雷闻研究员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陈雯怡研究员指教尤多,特此深表感谢!此次再版对译文做了全面的修订,感谢包教授惠赐再版序言,包教授发表在《中国学术》第1卷(2000),第3辑上的《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对于理解美国学界的唐宋转型研究有重要意义,此次经包教授同意,作为附录收入。译文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继续期待学界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