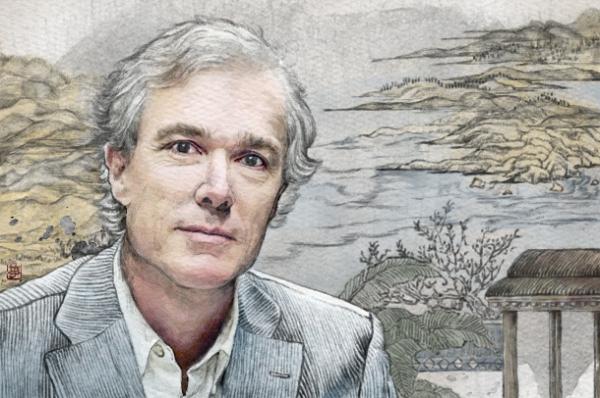
澎湃新闻:在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里,作者包括贺凯、黄仁宇等,您也是其中之一。而您主编的《哈佛中国史》每个断代都由一位学者负责,与《剑桥中国史》多位学者合作的写法很不同,这种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
卜正民:《剑桥中国史》让这么多学者共同参与撰写,好处在于可以利用他们的专业优势,如果是写纯粹学术性的著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这套《哈佛中国史》是面向大众读者的,如果让很多学者一起来写的话,很难统一,好像变得没有立场,没有自己的声音了。所以,我觉得每个断代让一位学者来写是比较合适的。
我个人是无法从秦汉写到清朝的,这样太难了。我决定把整个时段分成几部分,邀请不同的专业学者来完成不同的部分。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写了头三卷。他的学问很好,我邀请他写秦汉,这是他的研究领域。他觉得秦汉和南北朝必须合在一起写,分开就没意思了。我找不到特别合适的作者来写唐朝,我问他应该找谁,最后他说:好,我来写吧。他的研究专长不是唐朝,所以他自己觉得,这三卷当中,唐朝那一卷是写得最不成功的。但我觉得他写得很不错。对我个人而言,我有个优势:因为忙于各种事务,其他五卷都写好了之后,我才开始写自己那一卷。因此我可以从其他作者的写法中学习如何组织我这一卷。通史有其价值,《剑桥中国史》也有其价值,《哈佛中国史》则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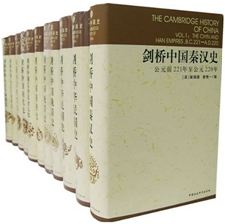
《剑桥中国史》
澎湃新闻:您在“《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总序”中提到,您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是什么原因呢?
卜正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花了不少时间在研究明末的情况上。越花时间深入下去,越觉得环境在那个时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观点目前也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同。另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大家越来越关心历史上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所以,我做了一个对照研究:从元代开始到明末,环境是怎样变化的,而在此期间,政治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我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联系。于是我尝试用一个框架将这两者整合起来。我不是说环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如果研究这段时期,却对环境变化的情况没有了解,就很难找到一个全面、完整的解释。我本人想要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来看历史,同时也想把这个角度介绍给中国读者。
澎湃新闻:您将十三至十七世纪的中国历史看成是一体连贯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能否请您谈谈,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视角?
卜正民:我原本计划《哈佛中国史》第五本只写明朝,不包括元朝,希望迪特·库恩(Dieter Kuhn)把宋朝和元朝合在一起写,但他认为宋与元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朝代。国外有学者认为存在一个“宋元明过程”,我不太赞成这个看法,这里面是有断裂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般人认为,蒙古人离开中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我越研究明朝的历史,越觉得不是这样。朱元璋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他如果要想象一个国家、一个朝廷是怎么回事,元朝就是他的样板。虽然他口头上说要回到宋朝,但实际上他对宋朝一无所知,他知道的只是蒙古人是怎样做的。蒙古人的统治方式和宋朝皇帝很不一样,却和明朝皇帝很接近。对我本人而言,我之所以想要将元明合起来写,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小冰河期正好从元代开始,到明末到达气温最低点。可以这么说,我是从环境史的角度来决定合写这两个朝代的。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谈到,明政府于隆庆元年(1567)解除海禁之后,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在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来到南洋之时,他们发现中国人早已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繁荣的商贸网络,将南洋、印度洋与大西洋等地联结起来。您的这一观点是不是受到全球史研究当中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卜正民:明朝政府固然可以禁止商人进行贸易,但是明朝商人却可以不理政府的禁令而偷偷地做生意,中国商人在十六世纪已经和东南亚有一些贸易往来。西班牙人把美洲的白银大量输入中国,靠着这些白银,欧洲商人才能顺利地在东南亚地区开展贸易。可以说,我的观点接近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是相当接近。我希望我的学生清楚,真实的历史并不是欧洲人像英雄一般跑到世界各地建立起各个商业网络,实际上在他们没去之前,这些网络也早已存在了。中国对南洋的商贸网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就像沃勒斯坦在他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南洋的商贸网络,欧洲人是不可能进入亚洲地区来进行贸易活动的。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澎湃新闻:在史料运用方面,您很注重对地图、画卷等视觉艺术材料的分析,试图由细节变化来印证历史变动。但是通过视觉艺术材料来分析历史变化,很容易堕入“以图证史”的陷阱,将画家自己的艺术创造解读为时代变化带来的影响。葛兆光老师就对您在《挣扎的帝国》里用明代雪景画的数量来证明“小冰河期”的天气变化委婉地提出过批评。对此您怎么看?
卜正民:我完全同意葛兆光先生的批评,国外也有人对我提出这样的批评。我对艺术的确是感兴趣的,但是没有足够深入的研究。我也清楚,一个画家为什么要画雪景图,有好多内在的、特殊的原因。但对我来说,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尝试从环境这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明朝历史,雪景画的数量恰好可以和我的小冰河期理论对应起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可以给外国读者留下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印象,让他们明白,中国画家也是很贴近现实世界的,而不是让他们觉得中国的艺术品都很离奇。当然,我知道中国读者对此大概会不满意。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在全书的论述中,地理空间上偏重江南。有关元明时期经济发展、海外贸易等叙述的着重点都在江南,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着墨较少。而且,您的《纵乐的困惑》也好,《秩序的沦陷》也好,都关注江南地区。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卜正民: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就是,江南地区的史料是最多的。参与政权的官员最多,经济上最重要,文化上也发达,留下了许多笔记和地方志。如果将明朝比作一列火车的话,江南就有点像这列火车的火车头,明朝的变化可以说是由江南引领着的,当然,广东、福建这些地方也都很重要,但是江南地区是最为特殊的。可能有些读者会发现,在我的书里面,对山西、陕西和山东这些地区都没有论及,但是提到了湖广地区,也提到了河南——河南的地方志很有意思。我在书的第二章尝试着对江南地区作了说明,当然,这也是面对外国读者的。

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澎湃新闻:梁启超曾经批评中国传统史书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很少关注普通民众。但是《哈佛中国史》却很少涉及各个朝代的政治史,对宫廷事件关注得比较少,更多着眼于某个朝代的普通民众的生活。能请您谈谈其中的原因吗?
卜正民:在邀请《哈佛中国史》的作者时,我就明确提出了,我们不要写中国各个朝代的政治史。因为对外国读者来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晋朝,什么是元朝,对宫廷生活也不感兴趣,他们可能更想知道,普通中国人在古代是怎么过日子的,当时的思想和艺术是什么情况。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不涉及政治史,而是淡化这方面的色彩。一些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常识的东西,外国读者可能一无所知。我们这套书,主要是面对外国读者的。
为了把我的读者引到我的故事里面,我故意用了一些五行志里怪力乱神的东西,比如关于龙的材料。我有个中国同学曾经问我:“你真的相信龙的存在吗?”我说:“不是我相信龙的存在的问题,而是我知道明朝人相信龙的存在,我想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相信。”当然,政治史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政治对社会的确会产生很大影响,可是大多数时候都是天高皇帝远,我感兴趣的是一般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知道,不少读者都对皇帝的生活很感兴趣,对皇帝做过哪些事情非常好奇,但描述这些是小说该做的事情,对史学来说意义不大。相比较而言,我们这几位作者当中,罗威廉对政治史的兴趣是最大的。
澎湃新闻:您1974年就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您认为和那时候相比,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您在《哈佛中国史》的序言里提到与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的交往,能谈下您对朱教授的印象吗?
卜正民:对中国的历史研究现状,我想我没有发言权,最近十年我并不在中国,虽然读过一些中国学生的论文,但是对整体情况并不熟悉。在我看来,朱先生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历史分析者。他的批评性很强,在他看来,没有批评就无法产生新的思想。他有时候很厉害,特别是对他不赞成的人。因为他觉得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不清楚历史,就不理解现在。他对我非常友好,可能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着复旦的联系。1975-1976年我在复旦的时候没有碰到他,可能是1978年才见到他的。我觉得他对西方的态度也非常开放,我特别尊重他。
澎湃新闻:在《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里,您提到自己1980年代在东京参加过山根幸夫教授组织的明史读书班,当时这个读书班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明史研究者,包括台湾的于志嘉。您能回忆下当时的情况吗?据我所知,读书班有段时间读的是叶春及的《惠安政书》,您后来在书中经常提到这位明朝官员。请问包括山根幸夫在内的日本学者,对您的明史研究有哪些影响?

卜正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
卜正民:我跟山根先生没那么亲近,但是他的读书班我参加了,一周一次(当时明史读书班确实在读《惠安政书》,我后来在很多书中都提到这部著作)。我很喜欢他的读书方法,他很严肃,非常下力气地研究中国史的问题,而且很博学,好像什么都知道。岸本美绪也参与了这个读书班,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系,她和山根先生不同,山根先生很严肃,她比较随和。我在东京待了两年,我在哈佛受到的汉学教育很不错,但是日本的汉学教育更加宏大深邃,有很多优秀的学者参与其中。我受到两个影响,一个是严肃的研究态度,一个是从下往上看的研究视野,这也体现在了后来我本人的书里面——日本搞社会史的学者都有点左,他们都是从二战时期过来的,战争期间都坚定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我们之所以去日本还有另一个原因: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不那么开放,美国学者是不能进去的,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可以到中国来。当时要研究中国史,都要去日本学习。我的朋友,像濮德培、王国斌等,都在日本待过一年,我是待了两年。我们都受到日本学者的研究的影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学者更多地前往中国,不再去日本,我觉得有点可惜。

叶春及:《惠安政书》
郑诗亮 尹敏志,2017-01-15 09:33 来源: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丁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