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田澍,原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7年第3期。转载时有删节
陆路丝绸之路发展到明朝, 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明朝统治者能够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大力变革传统制度,使国家治理能力得以大大提升。与此相适应,明朝对丝绸之路的管控能力自然也就明显强化。特别是面对北方元朝残余势力因不甘心失败而造成的长期压力,明朝必须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来有效控制陆路丝绸之路,以分化蒙古与西域诸政治体的关系,使其难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明朝。毋庸置疑,明朝陆路丝绸之路凸显着国防安全的首要特性。同时,由于明朝是14世纪至l7世纪陆路丝绸之路上长期稳定而繁荣的强大之国,有责任来规范和管理丝绸之路,维护其安全和稳定,使其继续发挥已有商道的功能,确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序交往。在明代,陆路丝绸之路将经贸文化交流和政治互动高度结合起来,使陆路丝绸之路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凸显着新的时代特点。
长期以来,学界谈论丝绸之路,大多仅仅围绕经济和文化的主线来展开研究,这种状况其实是不利于正确认知丝绸之路的。事实上,以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视角来看,自张骞“凿空” 以来,丝绸之路就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能离开中原王朝的国家安全和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支持而独立运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大国,中国古代各主要王朝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处于优势地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没有中国古代各朝的积极参与和强力支持,丝绸之路不可能顺利运行。其中明朝在丝绸之路交流史上自始至终地扮演着重要角色,对稳定和发展丝绸之路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当时世界的大国和领导者,“中国在明代享受着繁荣和发达。与前代相比,其经济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其掌控陆路丝绸之路长达两百多年,远超汉、唐、元诸朝。对明朝在陆路丝绸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予以专门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丝绸之路的特性和全面认识丝绸之路的走向。
总体而言,古代中国奉行积极的对外交往政策,注重与各政治体的友好往来。明朝与汉、唐、元诸朝一样,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积极的对外交流,将丝绸之路的精神发扬光大。在对外方针上,“明朝统治者既用不着靠掠夺别国来增加财富,又不必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人们的视线。相反的,海内升平日久, 国运昌隆,使明朝统治者更有心于追溯历代盛世中帝王的治绩,向往在海外树立威望,享有盛名。基于此,明朝统治者在国际事务中只能施‘仁政’,对海外诸国采取了以和平外交手段广为联络,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和平相处局势的方针”。建国伊始,明朝就对外奉行“一视同仁” 的政策,对遵礼守法的西域各政治体予以优厚待遇,确保友好往来。朱元璋向西域别失八里王公开表示:
只有承认大小之别,按照“天道”规范各自的行为,才能保境安民。作为具有古老文明的世界大国,明朝的这一做法“并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做法,而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防卫性施;外国君主如果想与中华帝国保持联系,他们就必须接受后者的条件并承认中国天子的普世权威”。

明朝对丝绸之路的主导地位是当时的客观要求。在蒙元帝国崩溃的过程中,只有明朝才能担负起维护陆路丝绸之路秩序的重任。有明一代,朱元璋的子孙都能以“受命于天”的思想认真践行着对西域的这一承诺,使这一思想和相关政策得以延续。如成祖所言:“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又言: “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天道恒与善人为君,体天而行,故为善者必赐之。”英宗对亦力把里使臣说: “朕恭膺天命,主宰华夷,一体祖宗抚绥之心,无问远迩。”后来又言: “自古帝王受天命,主宰万方,凡海内海外大小人民,皆在统御之中。而万方之人必知天命所在,尊敬朝廷,一心无二,然后可以保全长久。”在明朝诸帝看来,“尊天命” 与“顺人心”是统一的,只有将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丝绸之路才能正常运行;也只有如此,丝绸之路才能长久运行,各自才能从中受益获利。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明朝以充分的自信管控着丝绸之路。在这一历史时期,明朝将传统的“华夷” 秩序发挥到极致。对中国古代王朝而言,“统治者在乎的是自己管辖范围之内的统一,对臣服领土的管理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延伸。同时,在周边还存在不同族别形成的国家或者政权,这就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但这种认同的边界是主要承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就可以了”。明朝看重的不是穷兵黩武式的开疆拓土,而是中国“礼义” 文化认同的不断延伸。终明之世,明朝统治者对自己文化充满信心,将以“和”为贵与“德服远人” 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丝绸之路的交往之中。对此,朱元璋说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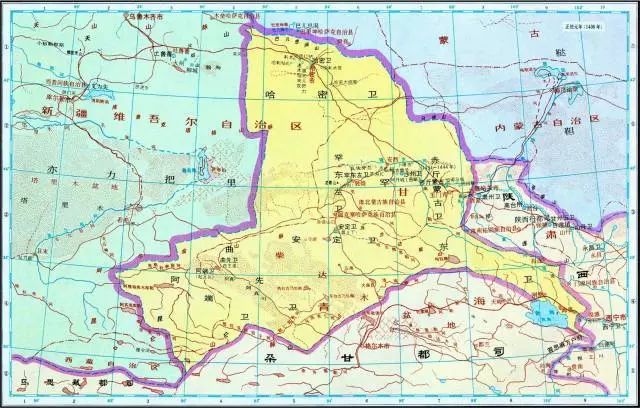
对于“厚往薄来” 的策略,明朝诸帝认真践行,不遗余力。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蛮夷在前代多负险阻不受朝命,今无问远迩,皆入朝奉贡,顾朕德薄,其何以当之!古之王者待远人,厚往而薄来,其各加赐文绮袭衣以答之。”
朱棣明言: “盖厚往薄来,柔远人之道。”宣宗即位后明确指出: “远国朝贡,固有常兮,然我祖宗以来待下素厚。今朕即位之初,凡事必循旧典,勿失远人之心。”景帝在“土木之变”后仍然重申:“夫厚往薄来,致治之常经。”对明朝来说,“厚往薄来” 是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做后盾的,对外交往的负担必须与自身的承受能力相一致。否则,只能使自己疲于应付,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而对西域诸政治体而言因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明朝,自然要设法从明朝获得更多的回赐,从而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在这一矛盾中,明朝必须制定符合双方利益的贸易规则,既能使自身的负担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又能使西域诸政治体获得预期的收益,以维持明朝在陆路丝绸之路上的良好形象和持续的吸引力。明朝统治者明白经济利益是维系丝绸之路顺畅的原动力,自己宣扬的“天道”、“人心”其实是以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后盾的。换言之,在明朝,丝路贸易必须要在既不劳民伤财和又不让“远人”无利可图之间寻求相对平衡。正如成化年间朝臣所言:“边防之险,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忧,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国以事边境,重手足而轻腹心,非惟不能保边,而适足以扰边;非特不能安民,而适足以困民。”
《明史·西域传》论道: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自是,殊方异域乌言侏倩之使,辐辏阙廷。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而四方奇珍异宝、名禽殊兽进献上方者,亦日增月益。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余威及于后嗣,宣德、正统朝犹多重译而至。然仁宗不务远略,践阼之初,即撤西洋取宝之船,停松花江造舟之役,召西域使臣还京,敕之归国,不欲疲中土以奉远人。宣德继之,虽间一遣使,寻亦停止,以故边隅获休息焉。
这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如何妥善解决对外交往的程度与国内经济承受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明成祖时期超负荷的下西洋活动很快被叫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明代的封建经济不可能持久地维持如此声势浩大的对外活动。所以,停止下西洋活动是符合当时的经济承受力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但刹车过快,并因此对外过于保守,则必然闭目塞听,日渐落伍于世界。当然,这一落伍的过程是缓慢的,需要漫长的时间。特别是要让当时的人真正认识这个过程更是困难的。美国学者就此论道:在明朝这个“真正的世界中心”,欧洲人还是“元足轻重”尽管“他们摧毁了阿兹特克人,用武力打进了东方市场,但是要给东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却没有那么容易。东方的社会发展仍然大大领先于西方,并且尽管欧洲有文艺复兴、船员以及火炮,1521年时,并没有多少证据显示西方将大大缩小差距。在我们看清楚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烧光特诺奇蒂特兰究竟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前,还需要3个世纪的时间”。
正是基于双方利益的周全考量,明朝依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可能,制定了相对完备的朝贡贸易的管控办法,以便持续有效地维护朝贡贸易。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朝贡期限。规定期限是有效控制贸易规模最有效的手段。明朝根据亲疏远近,对西域各政治体规定不同的朝贡期限,从一年一次、三年一次、五年一次不等,极远者不定期限。
2、贡使人数。由于朝贡赏赐与使团人数挂钩,故与贡期相适应,根据亲疏远近限定人数从三百人到几十人不等。控制朝贡人数是仅次于朝贡期限的又一重要举措。
3、进京人数。由于嘉峪关离京师较远,沿途驿站接待能力有限,故将合法进入嘉峪关的贡使分为起送和存留两部分,只有极少数的使臣被允许前往京师从事觐见皇帝等外交礼仪活动。起送使臣的比例一般为10%左右。或规定上线人数,从十人、 三十人、五十人不等,控制较为严格。只有如此严格控制起送人数,才能降低明朝境内5500里陆路丝绸之路朝贡贸易线上的运营成本和在京师的招待费用。
4、存留人数。大多数人关使臣被安置在肃州或甘州,在固定的专门场所居住,由明朝提供生活保障。明朝对存留使臣的赏赐由起送使臣带回。同时,人关后未被选中送往京师的贡物可在当地出售。当同团的起送贡使返回后再一道出关,离开明朝。
5、进贡路线。由于进入嘉峪关后贡使沿途所有开支由明朝提供,并由专人负责和接待,故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行走,不得变道游览,不得随意与一般民众接近,更不得刺探军情。
6、贡物。由于是按物赏值,故要求所携贡物为货真价实的“方物”,如马、玉石、水晶碗、羚羊角、铁角皮等常见之物,不得以贡“珍玩”而求厚赏。其中,马、驼、玉石是有明一代朝贡贸易中的主要“土物”,特别是撒马尔罕等处所贡“西马”尤为珍贵。
7、在京逗留时间。起送使臣到京后享受优厚待遇,在完成觐见皇帝、出席宴飨、领敕、领赏、出售剩余贡物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离京按原路返回,与在河西走廊的存留贡使一同放行出关,完成朝贡任务。不难看出,以上诸多规则中,核心的问题是加强对朝贡贸易规模的控制,较好地调节西域各政治体的朝贡频率,切实减轻沿途驿站和民众的负担,使明朝能够根据自身的承受能力构建与丝绸之路相适应的贸易体系和贸易规模,对保障丝绸之路的健康运行是十分必要的。从整个实施过程来看,明朝制定的这些规则是符合实际的,达到了政治预期。
当然,在实际交往中,出于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冲动,西域各政治体有时突破规则的约束违规从事朝贡贸易。纵观有明一代,明朝对西域贡使的违规行为采取了较为宽大的处理办法,以体现厚待“远人” 的基本国策。正如费正清所言:“在中国方面,尽管有游牧民族的归化来朝,同时却也不得不忍受他们在沿途时的胡作非为以及在京期间的酗酒闹事。”
当然,明朝也并非对违规之事坐视不管,而是通过适度的惩处来达到相对守规的目的,以确保朝贡贸易秩序的严肃性,使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这种驾驭之道就是朱元璋所谓的“威惠并行”之法。他说: “夫中国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怀德畏威为强,政以此耳。”
不难理解,在当时情况下,从事陆路丝绸之路贸易是极为艰辛的,存在着诸多风险。从贡使所在地出发到嘉峪关,大多数在万里左右,路途遥远,道路崎岖,小国林立,盗贼出没,秩序杂乱。贡使长途跋涉,既要付出异乎寻常的体力,又要支付昂贵的成本,有时还要付出生命代价。如万历年间,耶稣会士、葡萄牙人鄂本笃从印度出发,装扮成亚美尼亚商人,改名为阿布杜拉·以赛,经阿富汗、土耳其等地计划取道嘉峪关进入明朝。为了寻求安全,鄂本笃“跟随着四百名或更多的穆斯林商人或朝圣者一同出发。当时的海路既漫长又十分危险,天主教徒们的船只经常在途中遭受新教徒的洗劫抢掠。鄂本笃之所以作这趟旅行,部分目的就是想开辟一条欧洲与中国之间更短的通道,但更重要的目的则是想探明该地区是否存在着一个不同于中国的‘契丹国(Cathay)”’。翻越帕米尔去叶尔羌的路上“充满危险,鄂本笃五百人的商队雇了四百名保镖同行”。但不幸的是,鄂本笃“整个旅途运气不佳,他的钱财招来了其他商人的贪欲和敌意。他在甘肃边界肃州城逗留了一年半,由于不懂中文,要么试图通过书信同北京的神父联络,要么试图征得当局同意他们跟随一个骆驼商队旅行。很快,他被骗得身无分文,除了同伴艾萨克还留在身边。1607年3月,北京的一位神父终于找到了他,出钱陪他一同回到北京,但十一天后,他就死了。”在进入嘉峪关前,“部分行程中道路极为艰难,以致鄂本笃修士有六匹马都累死了”。鄂本笃的这一经历是14世纪至l7世纪陆路丝绸之路贡使历经千难万险而前来中国的集中写照。由于进入嘉峪关前沿途缺少大国的有效保护,贡使的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对此,明朝是十分清楚的,这也是为何明朝尽量宽待西域贡使的重要原因。《明史·西域传》就此论道:“盖番人善贾,贪中华互市,既入境,则一切饮食、道途之资,皆取之有司,虽定五年一贡,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难也。
为了获得更多的赏赐和回赐,西域各政治体时时突破朝贡贸易规则,或不按贡期而频频来朝,或不按规模限制而随意扩大朝贡人数,或贡品以次充好而要求高价赏赐,或献珍禽异兽而漫天要价,或滥充王使而冒领赏赐,或延长期限而靡费牟利。对于西域贡使的种种违规行为,明朝一方面不断予以告诫,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纠正;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予以宽大处理。如景泰七年(1456),撒马尔罕使团“所贡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块,六十八斤,余五千九百余斤不适于用”,按照规定由使臣自行出售,但他们“坚欲进献,请每五斤赐绢一匹”,景帝从之。成化五年(1469),哈密、亦力把力等地使臣前来朝贡,但哈密人数超额,亦力把力不到贡期,宪宗听从礼部的建议,“今违例来朝,不当给赐,然既到京,宜量为处置,以慰其心,请敕赐其国王并行陕西镇守等官一体禁约”。但这批还未归,另一批又到。哈密王母与土鲁番速宣阿力王联合瓦刺拜亦撒哈,共遣使二百余人人贡,明显违制,进人嘉峪关后等待处理。礼部和吏部会商后认为:“今哈密、土鲁番等使臣在京未回,而各夷又邀结瓦刺遣使来贡,既违奏定额数,又非常贡时月。若听其来京,以后冒滥难拒;若驱使空还,又恐招怨启衅。且瓦剌乃强悍丑虏,今却依托残破小夷,混杂来贡,若非哈密挟其势以求利,必是瓦刺假其事以窥边。中间事机,颇难测度,宜令兵部详度,庶不堕其奸计。”此议得到宪宗的支持,于是诏令镇守太监颜义等人: “各夷朝贡,俱有年限。今非其时,尔等其谕以朝廷恩威,就彼宴赉遣回,所进马驼却还之,听其自鬻,以为己资。其果有边情,不得已起送三五人来京。”但使臣马黑麻满刺秃力等拒不听命,决意面见皇帝,并以死相威胁。为了安抚“远人之心”,明朝最后做出妥协,按照10% 的比例确定进京人数,化解了矛盾。弘治三年(1490),撒马尔罕偕同土鲁番进贡狮子、哈刺、虎刺诸兽,甘肃镇守中官傅德、总兵官周玉等人奏闻,未经许可,便起送入京。而巡按御史陈瑶认为狮子诸兽“糜费烦扰”,不应接受,礼部赞同此议,提议“量给犒赏”,并言:“圣明在御,屡却贡献,(周)德等不能奉行德意,请罪之。” 但孝宗还是宽大处理,并未追究傅德等人宽纵之罪,认为:“贡使既至,不必却回,可但遣一二诣京。狮子诸物,每兽日给一羊,不得妄费。(周)德等贷勿治。”
但对于明显违规的行为,明朝给予及时的处置。如成化年间,撒马尔罕使臣怕六湾从嘉峪关人贡,在北京久待时,广结官宦,在市舶中官韦洛的支持下试图从海道返回,广东布政使陈选以贡道非法, “恐遗笑外番,轻中国”,极言不可,孝宗从之。弘治年问,土鲁番不按照规定的线路从嘉峪关入贡,而是从海上经广东人贡,且又贡献孝宗喜欢的“奇兽”狮子。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严,孝宗听从礼部的建议, “治沿途有司罪,仍却其使”,使土鲁番“稍知中国有人”。嘉靖年间,礼部官员上奏:撒马儿罕等使臣“在途者迁延隔岁,在京者等候同赏,驿递供应不赀,乞行禁约限制。比夷使到馆,已经译审者,给与钦赐下程,待给赏后住支。其见到待译与赏后延住者,与常例下程,应给赏赐,本部题准即行该库给发,无得稽迟。仍行该抚按官查照成化间事例,于各夷回还。但有与沿途军民交市延口一日之上者,该驿住支廪给军民枷号问罪,再行甘肃巡抚查复伴送人员有在途通同作弊,不行钤束催债者,从重治罪”。世宗从之。而对于有违国家安全的行为,明朝则拒收贡品。“由于哈密曾于1469—1470年间支持卫拉特人反对中国,明朝人遂拒绝接受其贡品。土鲁番人特别是苏丹阿黑麻的贡品曾被明朝政府多次拒绝,因为他曾入侵过哈密。”对破坏陆路丝绸之路秩序和安全的行为采取必要的“拒贡” 措施是明朝的正当行为,对维护丝路朝贡贸易活动和西域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纵观陆路丝绸之路的运行过程,可以看出明朝能够较好地掌控陆路丝绸之路的朝贡贸易,使交往活动能够按照相关规则在和平友好中平稳进行,秩序总体良好,明朝借此达到了以德服人、“怀柔远人”的政治目的,既确保了西域的相对稳定,也大大降低了明朝的北部边疆的战争风险,使相对和平的局面得以长久保持。
陆路丝绸之路既是明朝的外交之路,又是贸易之路;既是明朝西北边疆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明朝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内容;既是明代文明交汇的重要区域,又是民族交融的重要舞台。作为当时具有悠久传统和富庶文明的世界大国,明朝敢于担当,主动而叉积极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经济角色和文化角色,全力支撑着陆路丝绸之路的良性运行,使其具有稳定性和安全性,使l4世纪至l7世纪陆路丝绸之路继续发挥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连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