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黄朴民,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来源| 《历史学家茶座》2014年第2期,28-37页
本人不才,但正规的高等教育还是完整接受过的,自1978年混进大学,一口气在宁静的校园里泡了整整十年,本科、硕士生、博士生三个阶段,一个也不曾落下,是名副其实的“老运动员”。
读书,尤其是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其成败的衡量标志,就是几年寒窗用功下来,最后能否写出像样的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其他的都是扯淡。道理很简单,学位论文的写作,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学科知识的积累、问题意识的培养、研究能力的展示、写作水平的呈现之最综合的体现,而论文的答辩则反映了归纳问题的逻辑、口头表达的能力以及随机应变的水准,两者综合,对一个人的学术水平与能力的了解,大致也能够做到八九不离十了,所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正是因为论文的写作与答辩在研究生培养整个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性意义,导师和学生都予以高度的重视。导师生杀予夺、大义凛然,学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的就是最后的答辩那半天。
我硕士学位论文题目选得不理想,做“孟子政治思想研究”,可谓“题无剩义”,加上答辩过程中口才拙笨,发挥不佳,结果给时任论文答辩主席的沈善洪教授留下不太美好的印象,以致三年后我博士毕业求职时为浙江省社科院所婉拒。沈先生当时担任着浙江省社科院院长,进人最终由他把关。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学位论文撰写、答辩与一个人前程的关系。
一句话,在我读书那个年代,学位论文答辩绝对不是玩儿虚的,是真枪实弹的较量,论文答辩未能被通过,完全不是新闻,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完全不像今天,绝大多数情况下,学位论文的答辩只是一个形式,虚应故事,走个过场而已。当然,我们那时每个人所遇上的状况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导师宽容一点,走“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路子,有的导师严格一点,不但“批判从严”,而且“处理也从严”,那学生也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宋史研究权威邓广铭先生的把关之严在学界是出了名的,他的博士生中真的有人答辩数次未过,而被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学位论文答辩方面也流传过不少的趣闻逸事,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则是这样的:有一位硕士生专门研究南宋时期的圩田问题,论文提交给导师后,被毫不留情地打回,他百思不得其解,跑去请教导师,询问问题出在哪里。导师告诉他,论文写得很扎实,富有创见,但政治上有欠缺,即论文数万字中居然没有征引经典作家的语录,若能补上,便可通过。这位学生唯唯而退,但回寝室后却完全犯难了,经典作家可没有专门对圩田有评论的,那该怎么征引?他坐拥愁城一整天,临睡时突然来了灵感,茅塞顿开,原来他想到了毛泽东的名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于是赶紧抄到论文开头处。次日再将论文文稿呈交导师,果然顺利过关,得以允准参加答辩,并一帆风顺通过答辩,拿到学位。这也算是时代政治氛围制约规范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典型缩影了。
我1988年春夏之际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完成博士生三年的学习计划,接下来的事就是提交论文并参加答辩。那年春节前夕,我在将自己的论文初稿提交给导师杨向奎拱辰先生、田昌五先生之后,就返回老家浙江绍兴,去与家人团聚了。当时我孩子还未满周岁,正需要我帮着照料,于是我乐不思蜀,在家里一待就是好几个月,直至4月初同门Y兄打来电话,惊破我的春梦。
Y兄在电话中告诉我:“你赶快回学校,你的论文遇上麻烦了,田先生认为现在的稿子有缺陷,是不适宜提交答辩的。具体情况,电话里我不能细述,你自己回学校后再了解吧。”我一下子被打懵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赶紧购了火车票,昼夜兼程,返回学校。到了学校,取来杨先生与田先生两位导师的论文初评意见,我才弄清楚自己的论文症结所在。杨先生只对我论文提了些技术性处理方面的建议,没有更多的意见,而田先生则是对我论文的论述范围过于宽泛,期期以为不可。
原来,我们当时的论文选题是很随意很自由的,可做一本正经的论文,也可做有考据性质的古籍整理,如我同门齐涛兄,直接跟随王仲荦先生治学,最早的选题就是晚唐诗人韩偓的《香匧集》整理与研究,王先生逝世后田先生接手指导,才改选题为《唐代盐政研究》。又如,山东大学中文系杜甫研究权威萧涤非先生指导的博士生林继中君,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赵次公注杜诗先后解辑校》的整理与研究。此外,可以做非常宏观的大题目,也可以做非常微观的小考据,像萧涤非教授指导的另一位博士生、后来当上新华通讯社社长的李从军,其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唐代文学论纲》。我开始时的论文选题走的是类似于当年李从军的那条路,定为《两汉儒学思潮的嬗变及其特征》,现在看来的确是有些大而无当、天马行空了。田先生认为这类面面俱到式的东西,不应该成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就不容分说给打回来了。
今天细忖田先生的初衷,是完全合理的,这才是真正对学生负责。问题是当时已是4月份了,距离论文答辩只有两个月了,这中间还要留出论文送审的时间,而我又不想因此而延迟毕业。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推翻重来、另起炉灶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以原稿为基础,突出与强化重点,使论文命题更为集中,重点更为突出,讨论更为深入,形式更为合理。
于是在田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并报请拱辰师允准,决定重点地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两汉儒学的最大代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上延至战国末年、西汉初期的社会思潮趋势,往下涉及至《白虎通义》、汉末儒学演变,主次相从,详略相宜,从而对以董仲舒为中心的两汉儒学基本内涵、发展逻辑、主要特色、相关影响做出自己有一定新意的解读与揭示。与此相应,论文的题目也由原先泛泛的《两汉儒学思潮的嬗变及其特征》,改为《董仲舒与新儒学》了。
时不待人,确定了新题目后,我即全力以赴投入改写论文的工作。那段时间,可真是拼了小命,完全豁出去了,称之为废寝忘食也没有任何夸张,即兵法所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
那些天,我基本的作息规律是这样的:上午11点起床,下午搜集资料、酝酿思路,晚饭后伏案写作,一口气干到凌晨4、5点,成稿8000字左右,5点上床休息,直到中午。每隔两天,到田先生寓所,将两天来写成的稿子呈田先生阅示,田先生也跟着忙碌,我的文稿是随到随审,提出修改指示。我取回后也是按其要求加以改定。这样的奋斗持续了整整半个月,我终于完成了13万字左右的论文。接下来就是交付打印和装订,然后,便是将论文提交相关专家审阅评议。谢天谢地,至此,我终于赶上了与同门W君、Y君旅进旅退的答辩期限。
当时给我的博士论文书写评议意见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孔繁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葛懋春教授(他也是我博士生学习期间的副导师)、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蔚华研究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所所长赵宗正研究员、山东省社科院哲学所于首奎研究员、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主编李启谦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安作璋教授、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张岂之教授。他们对我的论文予以基本的肯定,如张岂之教授的评语就指出我论文将董仲舒思想体系概括为一大支柱、三重层次是颇为恰当的,认为我论文中强调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源自墨家的“天志”说是很有新意的观点,等等。送审的结果,意味着我的论文又过了一关,可以进入答辩的最后阶段了。
这里,要补上一笔的是,由于我论文完成拖沓的缘故,距离答辩的时间已所余无几,所以留给专家评审的时间十分有限,而这些专家拿到论文后都能及时审读并出具意见,确保了我能按时参加答辩,这是莫大的恩德,每念及此,我内心始终充满了感激之情。另外,我的母系山东大学历史系,也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当时没有快递这一说,论文用平信邮寄,有寄丢的担心,用挂号信邮寄,又费时多多,为了确保我能按时参加答辩,系里慷慨出经费,让我随身携带思想史专业三人的论文专程赴西安,呈送给张岂之教授审阅。

张岂之(1927-)
张先生当时正在校长任上,公务缠身,就让其助手任大援先生代收下论文,次日,任先生即来电话,通知我可前往西北大学取回张先生的评议书。原来,张先生收到三本论文后,用一个整夜的时间审读完毕,并用毛笔写出了三份详尽的评议书。山大历史系对自己学生的关爱,张先生的全身心投入,也都让人铭感五内,难以忘怀。
终于迎来了答辩的时候。当时博士生还是比较稀罕的动物,不像今天这样,博士满街走,教授贱如狗。那一年,整个山东大学也就11个博士毕业,其中,历史系就占了其中的六位,另外五人,分别是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的博士。缘是之故,学校很重视,在经费很有限的情况下,予以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们历史系的答辩搞得很隆重,从各地请来多位权威级学者主持或参加我们的答辩。
我记得当时到场的学者专家有下列几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张政烺先生、何兆武先生、张泽咸先生、李鸿彬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先生、河北大学的漆侠先生,西北大学的张岂之先生,山东师大的安作璋先生,我的导师杨向奎先生、田昌五先生和副导师葛懋春先生自然也参加了答辩。可谓阵容严整,名师云集。
那天我的论文答辩会,有以下七位教授参加:拱辰师、昌五师、张岂之先生、张政烺先生、漆侠先生、何兆武先生、安作璋先生,由张岂之先生担任主席。
这些先生中,当时我心里最发怵的是漆侠先生,漆侠先生是邓广铭先生早年的高足,是宋史学界除邓先生之外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的要求严格,在史学界是遐迩闻名的。更要命的,是他与昌五师私交最好,这使得他提任何问题,都不必顾忌导师的情面。——大家都知道,学生的论文答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检验导师的水平,如果学生的论文被挑出一大堆问题与缺失,客观上也多少是暗示导师指导上有所不足,没有将地雷提前排除掉,会让导师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其实,对我们来说,漆侠先生的严厉,已不是耳闻的印象,更是目见的事实。我上一届师兄答辩时,漆侠先生亦到场,有一位师兄在回答漆侠先生的提问时,表现得过于自信,结果让漆侠先生连珠炮似的追着问,直到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为止,搞得颇为狼狈,时间也大大延长,一场上午的答辩居然忙乎到近下午一时。
这次漆侠先生也在其他师兄的答辩中尽展学术风采,经常问得答辩的同学前言不搭后语,好在我已比较乖巧了,遇到答不上来的,就老老实实地缴械树白旗投降,表示自己读书有限、思考不周,日后当努力补课,迎头赶上,云云。这时,漆侠先生反而释然了,就给出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既能虚心地认识到自己之不足,那就表明还有希望,下去后继续用功吧!”大家如蒙大赦,赶紧诚惶诚恐地表示:敬受教诲。
由此可见,漆侠先生的“严”,并不是要和同学们过不去,而是希望通过此种途径,让同学们明白“学无止境”的道理,认识到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仅是一个读书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日后的路长着呢,只有虚怀若谷、谦逊谨慎,才能有所进步,逐渐成材。
冥冥之中有一种鬼使神差的宿命,即你越是害怕什么,那么,这害怕就越是会纠缠你。我的那场答辩,在进入答辩专家提问这个环节时,第一个发言提问的,就是漆侠先生。当时的答辩是现问现答,不像今天的学位论文答辩,是所有答辩专家问完问题后,给学生一段时间,让其下去针对专家所提的问题专门做准备。所以当时的答辩形式更要求学生具有敏捷的思维、随机应变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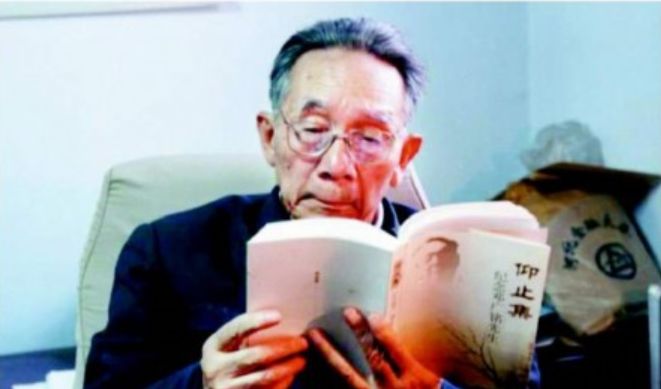
漆侠(1923-2001)
按常理说,漆侠先生是专治宋史的,我的论文是写汉代思想,研究方向隔得很遥远,可那个时代的学者又是何等人物,历史上的那点东西,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所以,一出招就是见血封喉,直击要害:“董仲舒讲天人合一,司马迁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他们所言的天人,含义是否一样,若不一致,差异又在哪里?”初闻之下,我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因为这之前我真的未曾考虑到董氏与司马迁的“天人关系”之异同,但时到如今,退路是没有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搜索枯肠,见招拆招,勉勉强强地陈述一番。大意是,两者形式相似,作为西汉思想界、学术界的顶尖人物,都一定会关注到“天人关系”这个两汉思想史上的最重大命题。但是,其“天人”所指代的内涵却有明显的不同,司马迁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抽象之天,也含有孟子阐述的命运之天的意义,是事物自由运行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的另类表述,而董仲舒所指称的“天”,则被赋予了人格神的涵义,具有了神祕主义、宗教化的色彩,从而造成了董仲舒整个学说走向神秘化的不归之路。
这样的回答,当然显得很肤浅,也不十分到位。但漆侠先生觉得我的态度尚端正,且也感到再提问,我也无法有更高明的表现了,所以,就点到为止,放我一马。不过尽管漆侠先生是高抬贵手了,但我这边却已是汗流浃背,近乎崩溃了。
所幸的,是接下来提问的张政烺先生非常温和,给了我以喘息的时间。张政烺先生是山东荣成人,与业师拱辰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前后届同学,其读书之广、学问之大,在整个史学界是得到公认的。他的论著数量不算多,但字字珠玑、篇篇精粹,堪称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典范之作,如《宋江考》、《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等等,皆为其例。

张政烺(1912-2005)
之前,我在杭州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曾有幸在学校听过他的讲座,题目是“甲骨卜辞中的劦田考”。张先生口才不是十分出色,但仔细体味,你能发现他的学术卓识的确是非同凡响,胜义迭呈,出神入化。如劦田问题,当时通行的说法是奴隶制下奴隶的集体耕作农田,张政烺先生认为这样的观点难以成立,遂从天文、历法、气象、宗教、古文字、民俗以及日本学者研究甲骨文的成果等多个方面,进行十分深入而精湛的综合性考释,发隐烛微,提玄钩要,论证了劦田的本义当为一种祭祀“田主”的盛大仪式。千古之谜,遂得以涣然冰释。我当时虽不能完全听懂和理解,但张先生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则让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推崇备至了。
但是,在人们面前,张政烺先生恂恂如也,非常低调谦和,这也反映在他在论文答辩的提问方式中。记得他当时对我提出的问题是让我对一块汉代碑刻的内容作简单的解释。我于汉碑所知甚少,当然答不上来,面红耳赤,惭愧无已。张政烺先生微微一笑,只说了四个字:没有关系。就此打住。但潜台词我还是懂的:年轻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似平原走马,宜放难收。人生有涯而学也无涯,还得静心苦身,继续学习啊。
接下来,是何兆武先生提问。何兆武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晚年调入清华大学思想史研究所任教。何先生才气横溢,学术水平之高姑且不多说,他的外语之好,也是让人钦佩不已的,曾译有英国思想史学派代表人物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著作。前些年曾以自传体著作《上学记》而广为人知。

何兆武(1921-)
当时的何兆武先生,五十开外的年龄,待人接物非常随和,一看就是有学问、有涵养的纯真学者。他当时提的问题,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具体的题目已无法回忆起来了,似乎与我论文本身的内容并无直接关系,我记得自己还是很勉强地做了答复。好长时间里,我在想何先生为何会提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呢?到后来,总算自以为猜测出何兆武先生的用意所在:正确的历史哲学的指导,是分析、揭示历史活动本质与规律的重要前提,否则难免会不得要领,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可见,“君子授人以渔”,何兆武先生实际上是在婉转地提醒我:要加强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学习与掌握,从而从新的视野、用新的方式来指导汉代思想史的考察分析,研究历史表象背后的本质内涵及其规律。这真是“良苦用心”的提醒了。
何兆武先生提问后,由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安作璋先生向我发问。安作璋先生是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更是山师大历史系的一面旗帜。他成名很早,“文革”前就有专著《汉史初探》面世,那时才三十来岁。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件容易的事。与今天只要买书号就可出书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时出版学术著作非大牌教授不可,而安先生能享此殊荣,足以证明在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颇具影响了。他日后与熊铁基先生合著的《秦汉官制史稿》,更是习秦汉史者所必备的案头之书。此外,他还著有《学步集》、《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评传》、《秦汉官吏法研究》(合著)等一系列重要著述,主编有《中国运河文化史》、《齐鲁文化通史》、《济南通史》、《山东通史》等。他与业师昌五先生私交甚笃,合著有《秦汉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流布。安作璋先生为人亲切随和,对后进的奖掖,可谓不遗余力。我后来被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聘任为专职研究员、学术委员,就是承蒙他的青睐,鼎力推荐的结果。
他在向我提问之前,先对我的论文作了评点,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这在整场答辩中,是独一无二的。人总是需要鼓励的,安先生的一番表扬,使我当时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宛如服了一粒定心丸。安先生的问题也相对比较容易,让我阐释一下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之所以为汉武帝采纳的时代背景,我做了较为全面的回答。安作璋先生颔首表示认可。
业师拱辰先生、昌五师先生因为是导师身份,就没有对我提太具体的问题,记得拱辰师只是在其他专家提问时插了一句,问我西汉中期为何特别尊奉“公羊学”,而不是“诗学”或其他“经学”载体。拱辰师的《绎史斋学术文集》、《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等著作,我是反复研读,稔熟于心的,因此较为轻松地作了解析。而昌五师则插话批评我对董仲舒以“天意”监督天子、限制皇权的意义评估太高,认为这仅仅是董仲舒本人的一厢情愿而已。他强调,在实际的皇朝政治运作中,其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即便是董仲舒本人,其遭遇政治风浪之时,也只能作出唯一的抉择——“遂不敢复议灾异”。换言之,在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的皇帝面前,作为读书人,千万不能自以为是,而只有借力打力,顺其自然。公孙弘是这样,董仲舒同样无法例外。
张岂之教授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整场答辩。所以,他是最后一位才发言的。他先是对我的论文作了较为全面的点评,既肯定了论文中的亮点,也毫不留情针砭了存在的不足。接着他话锋一转,向我发问:你的论文中有关于谶纬问题的讨论,征引了不少的纬书资料,那么请你回答你在写作论文时,阅读并参考了哪些载录纬书资料的文献?
应该说,张岂之先生的问题堪称一针见血,一下子抓到了论文的软肋,刺中了我的痛处。由于时间仓促,加上运用原始文献的意识不强,我论文中所征引的纬书材料,基本上都是第二手的文献,如陈登原先生的《国史旧闻》等等。本想打个马虎眼,蒙混过去,但在张先生的火眼金睛里,实在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尴尬之余,我只好老老实实和盘托出。
张岂之先生自然相当不满意,向我严肃地指出:治学的基础是不能偷懒,二手材料只是给你提供线索,最后还是得由原始文献来为你文章的论点作支撑。陈登原先生的《国史旧闻》一书,本身是很有价值的,但陈先生在抄录史料时,多有删节减省,是不宜直接拿来当史料用的。一番话讲得入情合理,道出了治学上应有的学风和态度。我无话可说,只有虚心接受,并在日后的研究中,时时刻刻用张先生的批评来提醒自己别再犯类似的错误。
经过整整一个上午灵与肉的“煎熬”,这场答辩会终于进入了尾声。答辩委员会对我的论文与答辩进行投票,来决定通过与否。所幸的是,尽管我的论文尚存在着大量的不足之处,我在答辩过程中的表现亦不尽如人意。但专家们秉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本着与人为善、奖掖后进的立场,还是给予了一致通过的判决。至此,一场称得上是近似“残酷”的学术“拷问”终于降下了帷幕。
答辩会结束,始终在场边观战的系副主任李老师对我说:看着你答辩时的窘况,我都替你感到紧张,现在的结果总算可让大家松口气了,要知道,这也是一次警告,你可是要重视啊!李老师说的是大实话。我也明白,自己论文的过关,有一定的侥幸成分。自己没有任何庆幸的理由,没有半点自满的资本。只有更努力以不辜负师长们的宽容与提携。
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忆及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场景,我浮躁的心就会沉静下来,知道学术的道路是那样的漫长,自己所取得的任何点滴成绩,永远是那样的卑微和渺小。
微信制作|曹 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