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冯立君主编《中国与域外》第二号(2017年12月),日文原载《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16),第18-23页,2014年。作者金子修一先生系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著有《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隋唐の国際秩序と東アジア》《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等。张鸿翻译。

一
中国宋代思想史研究家、对宋以后东亚交流史领域研究亦做出杰出贡献的东京大学小岛毅教授曾在《朝日新闻》(《历史认识的根源 中国的领土意识》,东京版2014年2月17日晚刊)有如下陈述:
19世纪后半叶,相对于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的军事劣势促使中国的国界意识觉醒,在接受近代西方主权国家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开始主张保全领土。然而,其原本的传统思想中,并未有直接管辖大海以及海中岛屿这样的意识。中华文明的摇篮乃黄河中游地区,汉字、儒教均孕育于此,而大海仅存在于观念中,缺乏对海洋的统辖意识。汉字的“山”、“川”均为象形字,而“海”却是复合的形声字,显示其乃一新概念。虽然经常称曰“固有领土”,但从历史上看,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地存在什么“固有领土”。以东亚为例,日本·韩国·中国三国,千百年来延续至今,似乎是个例外,但视之为历史的偶然而非固有的东西似亦无不可。如每个国家只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事态便无从解决,因而,是否我们应还原历史,依照当时人们的想法去重新看待并对今日这一状况进行反思呢?
以上报道可能对小岛氏的主张并未做出充分介绍,不过其中以当时思维重新审视历史并反思今日现状这一观点笔者完全赞同。2010年,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巡航船相撞事件爆发时,笔者恰好在中国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留学。亦不无紧随小岛氏其后发表些许个人看法这种心情,故在此拟就还原历史原貌这一见解做一阐述。
二
过去,通行的看法是日本乃岛国,因而认为日本历史基本脱离东亚国际局势独自运行。我是1968年上的大学,直至当时,学界普遍认为世界史是人类社会在外界刺激下由古代发展进入中世期,但日本存在其独特性,即日本由古代进入中世是在无外界刺激下发生的。然而以上世纪70年代为界,重视古代以来日本与中国、朝鲜关系这一观点日渐为学界接受。
1996年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开始出版发行,其第四卷《东亚世界的形成》(1970年)总论中,西嶋定生氏提出要从“东亚世界”这一视角理解日本历史发展的必要性。“东亚世界”一词日本历史学界1960年左右一直在用,当时西嶋氏在考察汉代皇帝统治特点中,发现爵位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于1962年发表题为《六—八世纪的东亚》一文,指出爵位制度不仅适用于唐代以前的中国国内,亦通行于中国王朝与日本、朝鲜诸国以及渤海之间,并将这种适用于中国王朝与外国间的爵位秩序命名为册封体制,指出册封体制即规定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国际秩序。包括对其的批判性观点在内,时至今日,册封体制依然是深受重视的一个历史概念,以下就此稍加详述。
如新罗每逢新王登基,唐王朝必派使册封。既为新罗的王,那么以新罗王称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西嶋氏注意到新罗王的“王”为爵位。封爵乃始自中国周代的一种制度,周王将土地分封于诸侯,同时授予冠以封地名称的爵位。如秦公、晋公等,秦、晋等分别为地名。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也开始纷纷以王自称,如秦王、楚王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始创皇帝称号后,王便成为高于公的一种爵位。新罗王的“王”号即为爵位,而“新罗”是其固有的国名,一旦获中国王朝册封,便成为领有中国王朝封地王爵的臣子,唐代新罗王成为唐朝皇帝名义上的臣子,爵位的授予通过册书(策书)完成。册书一词源自纸张未普及时期的木简以及竹简等短册状简木,今天韩国的博物馆依然保存有短册状竹简的册书。
成为中国王朝的臣子,则要受到身为臣子的某种程度的制约,同时在遭受他国侵略时,亦可得到中国王朝的援助。《魏志·倭人传》载,公元247年卑弥呼向魏带方郡诉说南部狗奴国与其相攻情况,于是带方郡派遣使者前去调停。239年卑弥呼遣使朝魏,魏皇帝授予其“亲魏倭王”的称号,即上述册封,魏从中调停可视为倭王成为魏臣子后从魏得到的帮助。唐代7世纪40年代东亚动乱时期,唐、新罗与高句丽、百济、倭逐渐形成两大对立联盟。新罗向唐王朝举讼高句丽入侵,于是唐派援军联合新罗于660年共灭百济,后百济复兴军向倭国求援,倭国援军663年白江口之战大败于唐军,百济最终灭国。之后,新罗与高句丽对抗进一步升级,唐与新罗联军668年再灭高句丽。
可以认为唐对新罗的援助是以对新罗建立册封关系为前提的,新罗与百济、高句丽对抗升级时,唐王朝曾表示因其国主为女王,故屡屡受邻国侵凌,建议以唐一宗支暂代为新罗国主。这在今日,无疑是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但在当时却可视为唐王朝为修正臣国秩序的一种考虑。此外,新罗此前一直使用自己的年号(私年号),后在唐王朝的要求下废止。在中国王朝看来,君临天下的皇帝乃天之子,是唯一受上天之命统治人间的人,因此观测天体运行、制定历法,甚至施行年号乃是天子的特权,新罗被要求停用本国年号即为此故。
爵位是一种身份制度,服饰的装饰纹样及颜色等均依爵位高低相应有别。包括其它诉诸视觉区别的身份秩序皆可归结为礼制一词。同今日人人平等观念不同,在古代,明确身份之别十分重要,故格外强调严守礼制。众所周知,日本及朝鲜延续至今的诸多习惯乃受中国影响而形成,且据西嶋氏研究,这些习惯是在遵守礼制中传入的。
综上,历史上古代东亚国家与中国王朝间多存在册封体制下的君臣关系,政治上受到直接影响,中国的种种文化以及制度也是在册封体制存在的前提条件下得以传入的。文化绝非流水般由高向低自然传播,文化的传播存在其相应的历史条件。古代东亚各国间的历史条件乃册封体制,即西嶋定生氏所提出的册封体制论。他还认为,册封体制大致自汉代起就已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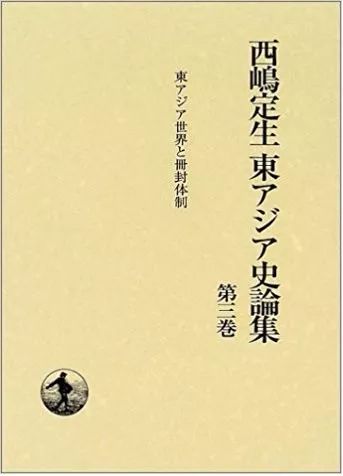
西嶋定生关于东亚世界与日本的论著
三
西嶋氏进一步发展上述册封体制理论,于1970年再提出东亚世界论。根据该理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世界一体化的19世纪上半叶以前,地球上存在若干个小世界,如地中海世界等,东亚世界亦属其一。东亚世界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北部以及连接中国与西域的河西走廊地区,当然历史上它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之所以将越南北部划入其中,可能是由于该地区汉代起直至唐代乃中国领土之故吧,不过西嶋氏的论著中对西面范围的划分稍显模糊。
西嶋氏列举出东亚世界的共同指标有汉字、律令、儒教和佛教,存在于东亚世界的佛教指汉译佛教。律令制及其后三项指标,均以汉字为媒介进行传播。汉字本身并非单纯作为文字表达的手段向无文字地区传播,日本便是一个明证。日语和汉语语法、音韵体系不同,日语中的汉字有的以训读法来读,而最初的万叶假名是作为表音文字来书写日语的,后来一部分草书汉字演变为平假名,此外又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片假名。而汉字并非因便于书写日语传入日本的。
西嶋氏认为汉字传入与东亚政治世界的存在密切相关。日本最早传入汉字的实物证据乃公元57年后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到了唐代,册书取代印章赐做王的身份证明。汉时纸张尚未普及,印章便亦用作身份证明。“汉委奴国王”金印当亦用于此后的外交中。邪马台国派往魏的使臣中有一位两度入洛阳者叫掖邪狗,首度时被授予“率善中郎将”银印,二度时《魏志·倭人传》载其为“倭大夫率善中郎将”,大夫是倭使臣的自称,“率善中郎将”是魏所赐官职。掖邪狗第二次派遣时是以率善中郎将这一官职并携带所赐银印入魏的,可以想见有了这些进入洛阳当十分顺利。
西嶋氏认为汉字是周边国家在与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必须使用的文字,随着对汉字的日渐掌握,以汉字记载的律令制、儒教、佛教逐渐为东亚国家吸收,并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随后,西嶋氏从东亚世界这一观点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不断加以描述,这里虽不能一一介绍,但笔者还是希望就须注意的几点展开论述。首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施行了郡县制,主要地方官员由中央派出,这种郡县制缺乏使中国王朝向外发展的内在机制,而西汉时推行的郡国制兼有郡县制和封建制,包含将外国纳入中国王朝的内在要素,它使得国内由中央直接实施管辖的郡县制与由爵位高低决定的分封制得以并存。国内施行的爵位制度推及外国便是册封体制。
汉代将外国纳入中国国内统治秩序理论逐渐形成,栗原朋信氏通过深入研究汉代印章制度,发现汉代有国内的“内臣”与外国的“外臣”之分,他指出外臣印章的规格要比内臣低一个等级。西嶋氏援用栗原氏这一内臣·外臣理论,推定册封体制始自汉代。魏晋南北朝至唐间,中国王朝赐予其他民族首长王·君王等封号的事例十分多见。关于此,其《六—八世纪的东亚》一书中有详细论述,指出汉代至唐代间的东亚国际秩序是由册封体制加以规定的。
然而10世纪初,唐王朝灭亡,东亚地区的新罗等国也相继灭亡,朝鲜半岛上高丽王朝建立,东北亚地区契丹势力抬头,据有渤海,甚至自称皇帝,定国号为辽。而在此之前,皇帝一直是中国王朝君主的专有称号,这一专有称号至此被周边国家开始堂而皇之地使用。
辽据有包括现在北京在内的长城以南地区,继唐代重新统一中国的宋代(北宋)力图重新夺回北到长城的地区却终未能如愿,之后试图与辽北部地区兴起的金结盟共同灭辽,未料金灭辽后很快自己也遭到进攻,不得已退据长江以南,史称南宋。南宋时期无奈之下甚至给予金高于对等国的待遇。
那么东亚世界至宋代是否就此终结了呢?西嶋氏认为虽然政治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在东亚地区终结,但东亚世界以其它形式继续存在。北宋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唐中期,西亚伊斯兰帝国兴起,唐后半期时伊斯兰商人航海来到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南海贸易不断发展,相当于今日海关的市舶司唐代仅在广州一地设置,到了宋代,从广州到长江的沿海一带设置市舶司的又增加了福州、明州等地。虽然从长安出发经由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商队依然继续往来不断,但从中国运往外国的主要商品不再是又轻又薄的丝织物而是又重体积又大的陶瓷。这是因为,一则毫无疑问海上贸易更有利于陶瓷运输,二则宋代以后轻巧结实的瓷器开始在江南地区大量生产。除此以外,到了宋代,随着铜的冶炼技术提高,品质优良的铜钱流通于市,大量铸造的铜钱更进一步激活了商品流通。这样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大贸易圈形成,即使以中国为政治中心的册封体制体系不断弱化,但以经济联系为主的东亚世界依然继续存在。
西嶋氏还指出,中国之后出现的元、明、清三朝版图较唐帝国或相当或超越,形式虽不相同,但一个政治上紧密联系的东亚世界再次复活。具体表述恕不赘言,在此仅从西嶋氏的论点出发,就相关国号问题指出一点。秦汉以后中国王朝的国号均取自其王朝开创者或者祖先受封于前朝的封号,如唐这一国号取自高祖李渊祖父李虎死后北周追封的唐国公,汉则因为项羽曾封高祖刘邦为汉王。然而,宋代以后无一国号是取自前朝的封号,这一点虽与册封体制的讨论并不直接相关,但笔者以为这可能与宋代以后爵位的社会性权威下降有关。
四
以上西嶋定生氏以册封体制为枢轴的东亚世界论对东亚地区研究者影响巨大,为古代日本史研究者考察日本历史发展中,即就并非遣隋使以及遣唐使那样与中国直接开展国交时期的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645年的大化革新虽发生在遣唐使未派出时期,但当年年初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可以认为这一东亚地区大变动对当时的倭国政权一定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朝鲜历史深受中国影响,在朝鲜史研究者间,很多人认为国际关系方面重视与中国王朝间形式上君臣关系的这一册封体制理论忽视了中国周边国家政治外交上的主观努力。不过随着研究人员对历史上册封存在模式多维度研究的积累,可以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册封关系的历史性意义。
有人评价西嶋定生氏的东亚世界论和册封体制理论以中国王朝为中心,我想这并非他的本意。《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一书试图立足东亚世界去讲述直至近代的日本历史发展过程。战后日本政坛对明治以后近代日本带给中国、朝鲜的巨大灾难毫无反省,对此西嶋定生氏在该书最后一章提出深刻警示。本稿伊始已有述及,西嶋氏首倡册封体制以及东亚世界论的20世纪6、70年代,学界通行的是日本历史独立发展观点,认为日本历史基本上与中国、朝鲜等近邻国家没有关系。针对这一看法,西嶋氏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前的整个日本历史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朝鲜密切相关,他从理论上指出,今日日本必须正确看待与过去中国、朝鲜间的关系,当然也包括其中不光彩的一面。
不过算来西嶋氏的这一主张也已过去了四五十年,事实上现在也有部分学者从学术角度对此提出了种种批判,这里恕难一一罗列,大致说来可分为对册封体制理解的批判与对东亚世界范围界定的批判。册封一词唐代以前的正史中几乎未见(有封册一词),因而其意思很难从史料中归纳总结。西嶋氏在解释唐代以前的册封体制时,强调中国周边国家获赐的王号为爵号。但是,汉王朝曾赐匈奴单于玺绶,唐封突厥、回纥(回鹘)可汗称号,封吐蕃赞普称号。这些单于、可汗、赞普均是匈奴、突厥、吐蕃等传统君主称号的音译,它们的授予可否亦视为册封,研究者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然而西嶋氏对这一质疑并未作答,可能在他看来,20世纪6、70年代,从理论角度彰显立足东亚世界理解日本历史的重要性才是当下最紧要的,而实证性研究探明中国与北亚、中亚各国关系对于勾画东亚世界框架并不重要。西嶋氏个人注重通过爵位秩序阐释国际关系,20世纪60年代其代表论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一书试图从同样赐予普通庶民的爵位功能去探究汉代皇帝的统治特点,随后他又发表若干论文,从爵位秩序探究日本古坟与东亚各国坟丘墓制,发人深思。不过,笔者以为如从爵位秩序解释册封体制以及东亚世界,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忽略了对匈奴、突厥、回纥等北亚、中亚各国与中国王朝关系的研究。
部分研究者对其东亚世界范围界定进行批判与此不无关系。西嶋氏将东亚世界的范围大致划定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北部,对于中国西面所达范围却并没有明确指出。近年来对北亚、中亚游牧民族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中国王朝中存在出身游牧民族者这一情况以及他们在中国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如上文所述,西嶋氏的东亚世界论重点在于阐明历史上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的关系,但是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非仅限于与东亚各国关系,故考察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时,仅凭西嶋氏的册封体制及东亚世界论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充分解释。因此,近来学界开始使用东部欧亚或者欧亚东部世界一词,研究者从更为广阔的区域去探讨日本与其它地区的关系,不断对西嶋氏的理论做出各种形式的批判或补充。
在此,笔者想以古代朝鲜史研究专家李成市氏的理论为例。其《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一书准确介绍西嶋氏东亚世界论的同时,亦指出其中今日看来所存在的不足,虽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其学术价值不容小觑。该书对西嶋氏的东亚世界论提出几点批评意见,其中最主要的当属在册封体制有效性方面缺乏实证研究之处。西嶋氏的东亚世界论没有探讨与“东边各国”以外地区国家的具体关系如何,中国文化如何在越南传播、扩散也毫无涉及。事实上,越南中国化不断加深、与中国王朝政治联系更加深入是进入10世纪以后的事情。5世纪倭五王时代以前日本虽受中国王朝册封,但真正吸收儒教、佛教、律令却是进入6世纪以后。关于册封体制的存在形态,西嶋氏仅在《六—八世纪的东亚》一书中做出论证,以后各时期均以册封体制存在为前提,不断进行扩展。对此,李氏在书中流露出极大的不满。
李氏史实分析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其有关汉字由高句丽向新罗的传播研究。高句丽与新罗边境地区遗存几方石刻碑文,新罗境内的碑文中也有被认为是高句丽语言书就的汉字。李氏认为此乃汉字由高句丽传入新罗之证据。古代日本门锁写做“镒”,但中国的“镒”字是表示黄金重量的单位,并非门锁的意思。然而近年来朝鲜半岛出土的新罗等国家的木简中发现,其中“镒”字也有用来表示门锁的例子。西嶋氏的东亚世界论将汉字的传入放在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间进行考察,但事实上,连同其本国用法一并从汉字先传入国再传入其它国家这种事例亦有存在,高句丽·新罗·日本三方关联的这种实例反而可能进一步丰富了东亚世界论中汉字存在方式的讨论。
此外,年轻的日本古代史研究者广濑宪雄氏从中国书仪入手,就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交往中往来的外交文书、即国书展开深入分析,针对与中国王朝存在国书往来的国家间关系接连发表新观点。书仪的实例不论公私,广泛存在,因此广濑氏的考查范围已然超越了西嶋氏的东亚世界。
五
如上所述,西嶋氏倡导的册封体制论和东亚世界论对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来各种批判声音不绝于耳。关于西嶋氏几乎未将游牧民族的存在纳入考察范围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考虑到上世纪6、70年代当时研究的积累现状。不过,如高句丽未经由中国王朝,与突厥等独立进行交往,故毋庸置疑,尽管是在讲述东亚世界,但对东亚以外地区漠不关心似乎亦是欠妥。
近来学界放眼更为广阔的欧亚东部世界,将日本历史的发展与东亚各国的历史发展时常关联起来进行解读,而西嶋氏的问题意识几乎不再被研究者们提及,这一点令我感到担忧。并非说只要问题意识是正确的,其论证程序恰当与否便无关紧要,但良好的问题意识会使我们挖掘出新的历史事实这一点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今日日中关系的恶化以上世纪70年代无法想象的一种形态表现出来,正如本稿伊始小岛毅氏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方面意识发生改变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同样西嶋氏瞄准19世纪中叶明治国家起点构想了东亚世界论。那么今天的我们在对该客观批判之处认真批判的同时,是否应亦不忘向前辈致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