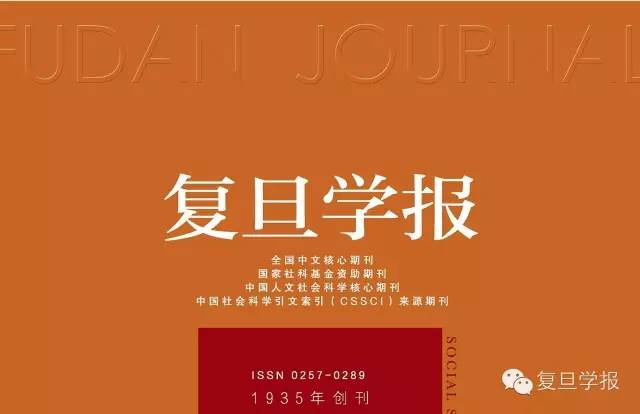
[摘要] 本文并非讨论艺术史,而是在讨论思想史。“职贡图”是古代中国描绘四方异邦前来朝贡的一种艺术形式。这种据信从6世纪上半叶梁元帝萧绎开始的绘制《职贡图》的传统,不仅在艺术史上影响久远,也呈现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史传统。即通过描绘异国朝贡使者,以表达天朝的骄傲和自信,在异国殊俗的对照之下,想象自己仿佛众星拱月的天下帝国。这种传统到了诸国并峙、疆域缩小、族群同一的宋朝仍然延续。本文以(传)宋代李公麟创作《万方职贡图》的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为例,考证当时北宋王朝与周边诸国的朝贡往来实况,并与《万方职贡图》中的朝贡十国进行比较,试图说明如果《万方职贡图》真是李公麟所绘,那它的叙述虽然有符合实际之处,但也有不少只是来自历史记忆和帝国想象。这说明宋代中国在当时国际环境中,尽管已经不复汉唐时代的盛况,但仍然在做俯瞰四夷的天下帝国之梦。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职贡图”的艺术传统还一直延续到清代,而类似“职贡图”想象天下的帝国意识,也同样延续到清代。这反映了传统中国对自我与世界的观念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影响至深。
[关键词] 天下帝国 朝贡体制 李公麟 《万方职贡图》
[作者]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上海200433

引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宋代的国际环境、历史记忆与自我想象
从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755)到11世纪初的“澶渊之盟”(1005),经历了整整两个半世纪,中国从混乱和分裂中逐渐又重建起一个相对稳定和统一的帝国。
不过,这个新建立的大宋帝国和两个半世纪前昌盛期的大唐帝国比起来,变化太大了。首先是疆域缩小了一大半,其次是帝国内部的族群与文化逐渐同质化,再次是政治与制度也形成单一的主流。特别是过去大唐帝国内部的“胡汉”问题,逐渐变成了大宋帝国外部的“华夷”问题。在北边的契丹(以及后来崛起的女真和蒙古)、东边的高丽、西边的党项(夏)、西南的吐蕃和大理、南边的安南等“强邻”环绕之下,缩小了的宋帝国就像宋人所说“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宋朝逐渐成为诸国中的一国。汉唐时代无远弗届的天下帝国已经是遥远的历史记忆。而承认天下必然“有阴(外)有阳(中)”之后,如何在现实中“严分华夷/内外”,倒成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心中焦虑。
可是值得深思的是,汉唐时代遗留下来“天下帝国”的历史记忆,在大宋王朝依然影响深远。这种历史记忆在疆域渐渐收窄的帝国中,逐渐转化成为一个想象,就是在有限的疆域之内,仍然做笼罩天下的帝国梦。在这个时代,中古中国形成的描绘帝国鼎盛时期万国来朝景象的“职贡图”传统,就承担了这种“想象天下帝国”的职责。
先从“职贡图”绘制的传统说起。
一、梁元帝以来:绘制“职贡图”的悠久传统
古话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和战争。其实,“征伐定邦”(戎)和“天授神权”(祀)都是古代皇(王)权合法性的来源。只是“戎”也就是真正的战争很残酷,得动员国家的全部力量,耗费成千上万的金银,死伤成千上万的兵卒,非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发动战争。倒是“祀”,也就是举行各种仪式比较容易,只要庄严而且隆重,歌舞奏乐祭天降神,场面越大越好。一般来说,古代中国帝王都特别重视三项仪礼,一是纪念节日,二是检阅军队,三是接见诸侯。按照古代经典记载,天子四时接见各方诸侯朝拜,春天叫“朝”、夏天叫“宗”、秋天叫“觐”、冬天叫“遇”。如果只取最重要的春秋两季,就叫作“朝觐”。如果中国周边各国按照制度来朝觐中国帝王,献上各国的土产和礼物,那么就叫做“朝贡”。有人说,古代中国从秦汉以来已经建立了“朝贡体系”,而“朝贡体系”就是当时以中国为中心,按中国礼仪制度构拟的国际秩序。
这个各国朝觐天朝帝王的传统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来历久远。关于这一方面,有三篇古文献很重要:第一篇是《尚书·禹贡》,根据它的记载,在中国之内有九州,在中国之外有岛夷、莱夷、淮夷、三苗等,周边以华夏为中心,他们都服从中国号令,都会给中国进贡土产;第二篇是《逸周书·王会篇》,它记载西周武王(一说成王)时,八方进贡的热闹场面,传说当时四方来朝贺的属国包括了东夷、南越、西戎、北狄各方;第三篇是《国语·周语上》,据它说周代天下已经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各种不同区域对天子有祭祀和进贡的责任,如果不依照自己的职责祭祀和进贡,就要受到惩罚,并且说这是“先王之制”。 这三篇文献半是传闻,半是想象,但它们都表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
关于朝贡制度的早期文献留下来不少,但有关朝贡的早期绘画却留存不多,最早的是梁元帝萧绎(508~555)《职贡图》。当然,梁元帝萧绎《职贡图》的原本现已不存,但现在存有三个后人摹本:一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王会图》,传为唐代阎立本摹本,有“鲁”等二十四国使者;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梁元帝番客入朝图》,传说是南唐顾德谦摹本,有“鲁”等三十三国使者形象;三是最有名的《职贡图》,传北宋摹本,原来收藏在南京博物院,现归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共剩下十二国使者图像、十三段说明文字。这就是人们最熟悉的一种《职贡图》,通常都认为这一种也许最接近梁元帝原作。
关于摹本的复杂源流问题暂且放在一边,不妨先来看这一《职贡图》的内容。现在留存的十三段文字涉及十三个国家,分别是滑(今新疆车师)、波斯(今伊朗)、百济(今朝鲜半岛)、龟兹(今新疆库车)、倭(今日本九州)、宕昌(今甘肃南部)、狼牙修(今马来半岛西岸)、邓至(今甘肃南、四川北)、周古柯(滑旁小国,在今新疆境内)、呵拔檀(西域小国,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胡蜜丹(滑旁小国,据说在今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交界)、白题(今阿富汗境内,接近波斯)、末(今土库曼斯坦)。
根据保存在《艺文类聚》卷五十五的梁元帝萧绎序文可以知道,这是萧绎在任荆州地方长官的时候,也就是526~539年之间,根据转述和亲见陆续画成的。据说,完整的《职贡图》还有若干其他国家使者的形象,根据学者考证有高句丽(今朝鲜半岛北部)、于阗(今新疆和田)、新罗(今韩国南部)、渴盘陀(今新疆塔什干)、武兴藩(陕西略阳一带)、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天门蛮(今湖南、湖北、贵州之间)、建平蛮(今湖北、四川之间)、临江蛮(今四川东部)。此外,还应该有中天竺(今印度)、北天竺(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一共是二十五国。这些国家大多不见于《宋书》和《南齐书》,但是有学者指出,它却与《梁书·诸夷传》的记载大体相合,说明梁元帝萧绎在绘制这个《职贡图》的时候,基本还算是“实录”。
这幅《职贡图》影响很大。据文献记载,阎立本、吴道子甚至中唐以降的李德裕,都曾模仿梁元帝临摹或创作这类夸耀天下帝国、表彰“圣明柔远之德,高于百王,绝域慕义之心,传于千古”的图画,并在后世逐渐形成图绘异国使节来天朝进贡的艺术史主题。这一艺术史主题从唐代历经宋元明一直延续到清代,无论在绘画作品还是在墓室壁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类作品。
下面书归正传,开始讨论(传)李公麟(约1049~1106)《万方职贡图》。
二、在宋代想象异邦:李公麟的《万方职贡图》
正如一开头所说,宋代由于周边强敌环伺,东亚形成了彼此制衡的国际秩序,因此宋王朝不再能像汉唐一样,作为天下帝国俯瞰四邻,反而是在四邻环绕之下,不得不缩小地盘以维持汉族王朝。尽管宋朝君臣以及很多士人始终有恢复“汉唐故地”的远大理想,也坚持中心对边缘居高临下的姿态,但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自欺欺人的夸张。其实在这个时代,所谓汉唐形成的朝贡体系已渐渐衰落,虽然富庶的大宋王朝凭借优渥的经济实力,还能维持一些邻邦的朝贡,但这种朝贡制度在当时只能约束或吸引更贫弱的邻邦。这些来“朝贡”的邻邦,通常也只是为了与中国进行贸易,获得丰厚的回报。因此,所谓的“万方朝贡”大半已是辉煌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记忆和满怀梦想。但就在这个时代,仍有不少图绘异邦朝贡的作品,宋代朝廷也建立了图绘朝贡国的制度。我们且看这幅最重要的作品,即传为北宋李公麟(1049~1106)的《万方职贡图》,或许它的绘制正与北宋官方那种“绘画其冠服,采录其风俗”的制度有关。
《万方职贡图》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关于它的流传与收藏经过有些曲折,这里姑且从略。众所周知,李公麟是宋代最杰出的画家,邓椿《画继》中说士大夫都认为他“鞍马愈于韩幹,佛像追吴道玄,山水似李思训,人物似韩滉”。据《宣和画谱》记载,他曾绘有两幅《职贡图》,其中另一幅《十国图》已经不存,只见于南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〇二的记载。而现存的这一卷《万方职贡图》描绘的十个国家,据曾纡(1073~1135)题词说,即占城国、浡泥国、朝鲜国、女直国、拂冧国、三佛齐国、女人国、罕东国、西域国、吐蕃国。曾纡题词在现存《万方职贡图》每一帧旁,一一说明李公麟所绘各个国家的情况与风俗。据题词末文字说,撰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图卷之末则有元代相当有名的文人白珽(1248~1328)、贡师泰(1298~1362)、赵良弼(1216~1286)、袁桷(1266~1327)等观画之后的题跋。
需要说明的是,曾纡字公卷,晚年自号空青老人,北宋南宋之间建昌军南丰(今江西南丰)人,是北宋晚期著名官员曾布之第四子。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他似乎对书画相当有知识,曾撰有《题怀素自叙帖》(绍兴二年三月)、《陈闳十八学士春宴图跋》、《跋李伯时天马图》(绍兴元年)、《题李伯时马图》(绍兴四年)等。根据其《题李伯时马图》中的“绍圣丙子(1096),伯时为予摹韩马,后为王彦舟取去,又在此马后七年也”一句,又可以知道他和李公麟曾有过直接交往。假如这些题记文字真的是曾纡所题,那么这幅《万方职贡图》当然可以确信是李公麟手笔。
下面把这一《职贡图》中涉及的十国之题记照录如下:
1.占城国:“占城国,秦为象郡、林邑,汉改属日南。唐弃林邑,徙占城,因号焉。其俗,出,人乘象马,粒食稻米,月食水兕、山羊之类。土无蚕丝,以白布缠胸至足,妇人衣服拜揖与男同。地不产茶,亦不知酝酿,止饮椰子酒、食槟郎。元日牵象周行,然后驱出,谓之逐邪。八月有游船之戏,十一月十五日为冬至,相贺腊月望日。城外缚木塔,王与民焚香祭天。刑禁设枷锁,小过鞭藤杖,死罪系乎树,梭枪舂其喉,若故杀劫杀,象踏之。”
2.渤泥国:“浡泥国,在西南大海中,所统十四州,以板为城,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王坐绳床,出,即大布单坐其上,众掩之,名曰阮囊。战斗用铜铸甲筒如穿以护腹。婚聘先送椰酒摈榔指环,再送吉贝布金银而娶之。腊月十日为岁首,宴会鸣鼓笛钹,歌舞为乐。以竹编贝多叶为器,盛饮食。习尚奢侈,王之服色略仿中国,最敬中国人,每见中国人醉者,则扶之以归。”
3.朝鲜国:“朝鲜国,周为箕子所封,秦为辽东外徼,因置八道,分统郡府州县,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色,无淫盗,柔谨成风。市多游女,夜则群聚为戏。婚无聘财,山多田少,故节饮食,居茅茨,文合楷隶,士娴威仪,以秔为酒,衣惟苎麻,三岁一试,有进士诸科,其器疏简,刑无惨酷,尚有中夏之遗风。”
4.女直国:“女直国,古肃慎地。东汉名挹娄,北史名勿吉。其俗极寒,穴居以深为贵,食肉衣皮,寒则厚涂豚膏御寒,好勇善射,婚姻男就女家,嚼米为酒,饮之亦醉,以溺沃面。父母死,立埋之。塚上作屋,令不雨湿。秋冬死,以尸饲貂狐,食其肉则多得之勇悍,啖生肉,酒醉杀人,不辨父母。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略知耕种,事弋猎,设官牧民,随俗而治。”
5.拂冧国:“拂冧国,前代不通贡,地土甚寒,无瓦,以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筚篥、扁鼓。其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掩之。贵臣如王服,或用色褐,缠头跨马,刑罚,罪轻者杖数十至二百,罪大者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斗战,小有争,但以文字相诘,铸金银为钱,无孔,面凿弥勒佛,背凿王名,禁私造。”
6.三佛齐国:“南蛮别种,在占城、真腊之间。所辖十五州,其地多热少寒,冬无霜雪,人用香油涂身,地无麦,有米及豆。贸易用金银。累甓为城,椰叶覆屋。民不输赋,有征伐则调发,自备其食。善战敢死,文字用梵书,男女椎结,喜洁穿净,居在海中,为诸蕃往来之咽喉。”
7.女人国:“在南海中,巫咸之北,轩辕之南,爪哇之东。仍有君臣上下。境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若生男则不育。”
8.罕东国:“古西戎部落,战国时月氏居之,秦末汉初,属于匈奴。其俗随水草畜牧,无屋居,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自君长以下,咸茹毛饮血,贵壮贱老,凡举事常随月盛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其父子男女相对蹲,髡头为轻便。妇人出嫁时乃卷发,病以艾灸,或烧石熨卧,或随病以刀决,俗贵其死,葬则歌舞相送,有棺椁而无封树,其征发兵马反科税,辄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之以为信。”
9.西域国:“天方,古筠冲之墬(地),旧名天堂,又名卤域。其俗风景融和,四时皆春,田沃稻饶,居民乐业,俗好善,男女辫发,衣细布衫,系细布带,有回回历,与中国历前后差贰日,人多以马乳拌饮,故人肥美。其产马高八尺许。”
10.吐蕃国:“即西番。其先本羌属,散处河湟江岷间,地薄气寒,风俗朴鲁,然法令严整,上下一心。其国君有城郭而不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君臣为友,岁立小盟,三岁一大盟。君死皆首杀以殉。无文字,刻木结绳,尊释信诅,其乐吹螺击鼓,四时以麦熟为岁首。其官之章饰,贵金,银次之,铜最下。俗重浮屠,政争必以桑门参决,贵壮贱弱,以累世战没者为甲门,不知医药,病唯祭鬼,喜啖生物,茹醢酱,犷好斗。”
三、实录的、想象的和记忆的:神宗朝所谓“朝贡国”之分析
以上署为“空青老人曾纡”所写涉及各国的说明虽然简略,但是情况颇为复杂,有的部分来源不明,有的部分则与《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四裔考》、《宋史·外国传》相当接近。有可能是后人伪造,但如果它真的是南宋初期的曾纡所题,那它们可能来自宋代官修五朝《国史》。出自五朝《国史》的这些异域描述,则应当与李公麟生活的时代士大夫对周边各国的知识大体吻合。李公麟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约二十二岁时中进士第,一直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五十二岁因病致仕。这三十年中,他处于政治舞台中心,其中最主要的时段就是北宋神宗、哲宗时代。如果这幅《万方职贡图》真的如同文献记载,创作于元丰二年(1079),那么我们不妨从各种历史文献中,看看李公麟可能目睹并据实图绘的熙宁、元丰时代北宋的外交情况如何,并且通过北宋真实的国际往来和画家想象的朝贡景象,看看宋人是如何延续汉唐盛世的历史记忆,想象自己仍然作为天下帝国的盛况的。
可是,当时北宋真正的国际环境与异邦往来究竟如何呢?其实,在李公麟创作这幅《万方职贡图》的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真正来北宋朝贡的外国并不是那么多。
我们不妨粗略地鸟瞰一下当时的情况。根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文献记载,从熙宁到元丰,在北宋历史上是很关键的时代。这时,北宋的国策开始从退守转为进取,不仅在西北开始用兵,声称要“复灵夏,平贺兰”,在西南也开始拓展,一方面让成都路“招诱西南夷”,另一方面联系林邑(占城)威胁交趾的后方。而对历来处于守势的北方,更是有人蠢蠢欲动,“上平燕之策”。宋神宗也确实跃跃欲试,试图拓展对外关系,重建朝贡体系。他根据李评的建议,设立“管勾客省官置局”,“总领取索诸处文字,类聚为法式”,也就是负责朝贡国的语言,并且在熙宁六年(1073),由宋敏求编撰了《蕃夷朝贡录》二十卷。可能这就是李公麟绘制《万方职贡图》的时代背景。
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对外拓展国际关系,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原本已经被契丹归为藩属国的高丽,通过南方的海上通道,重新与北宋建立了断绝四十三年的联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先是记载熙宁四年(1071)“高丽使民官侍郎金悌入贡至海门县”,接着卷二四七在熙宁六年(1073)又记载“高丽自国初,皆由登州来朝,近岁常取道明州,盖远于辽故也”。到了元丰年间(1078~1085),因为高丽国王王徽“比年遣使朝贡”,所以宋神宗也派出安焘等人作为信使出使高丽,并让张诚一特别修撰《高丽入贡仪式》,在高丽使团登岸的明州定海县,建造“乐宾”贡使馆和“航济”亭,还特意制造“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和“灵飞顺济神舟”,作为两国交往的船只。在元丰六年(1083)高丽国王王徽去世的消息传到汴京时,宋神宗还下诏令明州给他做水陆法会,并专门派遣杨景略作为使者赴高丽祭奠。显然,在李公麟作画的时候,高丽(朝鲜)确实是往来北宋汴京朝贡的,或者可以说《万方职贡图》中有“朝鲜”是有根据的实录。
但是,这里画的“女真国”却不同。在北宋熙宁、元丰时代,女真尚不够强大,当时的女真人一面依附契丹,一面依附高丽。据文献记载,11世纪中叶以前,它只是一个部族群,虽然完颜部逐渐统一各部族,但仍在契丹控制之下。据《松漠纪闻》、《契丹国志》等文献记载,那时女真苦于契丹的横征暴敛和无穷索求,只能忍声吞气。一直要到宋徽宗政和、重和年间(1111~1119),也就是李公麟绘制《万方职贡图》之后差不多三四十年的完颜阿骨打时代,女真才从“事大国不敢废礼”转向“问罪于辽”,正式建立大金国,并且在重和二年(1119)派了使者李善庆来汴梁与蔡京、童贯等见面,而北宋也才较为全面地了解了女真的情况。可是,在李公麟绘制《万方职贡图》的元丰二年(1079),女真并没有使团向北宋朝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五年(1082)宋神宗发现高丽虽然与北宋恢复通交,却把原来女真通过登州向北宋卖马的孔道隔绝了,就下令让臣下告谕高丽国王,“女真如愿以马与中国为市,宜许假道”,但“后女真卒不至”。这使得北宋对于女真情况几乎是一头雾水,所以元丰七年(1084)礼部官员听一个叫钱勰的人说,女真有四十余人在高丽,便派了一个叫郭敌的泉州商人“往招诱首领,令入贡及与中国贸易”,并下诏让明州知州从他们那里打听女真语言,但仍然“其后女真卒不至”显然,如果《万方职贡图》这幅作品真是李公麟元丰二年所作,那么关于女真来朝贡就只能是绘制者李公麟或题跋者曾纡的想象。
特别是西部、北部,作为北宋朝贡国的异邦更不多。正如熙宁年间宋神宗征询老臣意见时,著名的官员富弼所说的那样,当时契丹仍然很强大,“夏国、唃厮啰、高丽、黑水女真、鞑靼等诸蕃为之党援”,北宋只能容忍契丹辽对以上诸国的控制。其中,李公麟《万方职贡图》中所画的“吐蕃”进贡其实也颇不可靠。9世纪末,吐蕃王国已经分裂,在神宗时代其实已经不存在一个“吐蕃”,分裂的吐蕃各部,更不以吐蕃为名作为北宋王朝的敌国或属国。 被当时视作“吐蕃”的乃是北宋西北边疆的一些吐蕃遗族。深通边事的韩琦曾说,秦州以西古渭之地,当时有很多吐蕃人,“散居山野,不相君长,耕牧自足,未尝为边鄙之患”,倒是当时的北宋“杀其老小以数万计”,强取其地,建了熙河路。其中,居住在今青海一带,在宋仁宗明道年间(1032)曾经来朝贡的唃厮啰(997~1065)部,早在神宗时代之前已经分裂。至于在河州的其子董氊(?~1086),也并非北宋属国,却是“契丹之婿”,虽然也曾受北宋之封,于元丰元年(1078)曾来进贡,并且也曾与宋合作攻夏,但并没有使用“吐蕃”之名义。
那么,李公麟《万方职贡图》所绘的“西域”又如何呢?应该说,北宋时所谓“西域”并非一国,在北宋士大夫含糊笼统的“西域”概念中,有时候指传统所谓西域即今新疆与内亚,有时候指以大食等等更遥远的西亚各国。 当可是,自从雍熙元年(984)北宋使臣王延德从高昌经历千辛万苦返回之后,此后一百年间,北宋与西域的交往相当稀少。在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有可靠记载的大概只有于阗一国使者曾四次(元丰二年、四年、六年、八年)经“黄头回纥、草头鞑靼、董氊”来到北宋,也有零星的大食国各部经由海路到达广州等地。不过,那个时代的西域各国未必承认自己是来“朝贡”。比如元丰四年(1081)来到北宋的于阗使者阿辛所携国书,开头就是“于阗国偻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这类措辞,这就像隋朝日本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时让隋朝皇帝大为恼火的称谓一样。仅从国书措辞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至少在彼国看来,于阗与北宋之间并非所谓“朝贡关系”,而是“对等关系”。此外,当时来北宋的也有一些经由陆路来自西域龟兹等国人,也有一些经由海路到达广州的大食商人,他们或许以朝贡之名行通商之实,但他们是否真的是官方朝贡使团或使者,实在很令人怀疑。
不过,在李公麟绘制的各个朝贡国中有占城、三佛齐、勃泥等东南亚及海上诸国,这倒是可以相信的。如果说北宋的西北通道自中唐以后逐渐隔断,那么南方及海上诸国却与中国联系日多。这一趋势从宋初就渐渐发展,只是这一趋势并不是从神宗时代开始的。宋真宗时代(998~1022)就曾下令各地,“对交趾、占城、大食、闍婆、三佛齐、丹流眉、宾同胧、蒲端”等国来进贡的使者“邮传供亿,务从丰备”,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商人也好,官方也罢,都非常热衷来华。比如三佛齐,熙宁、元丰年间三佛齐人常常经由广东市舶司前来朝贡或者经商,也曾得到北宋王朝回赐的丰厚回礼。元丰二年(1079),也就是李公麟绘制《万方职贡图》这一年,有一个叫作“群陁毕罗”的三佛齐商人“来贡方物”,就得到“银水罐、交倚骨朵二对,银洗罗一面及赐僧紫衣二,师号度牒各一” ;而元丰五年(1082)更有人“持三佛齐、詹卑国主及管勾国事国主之女唐字书”来,元丰七年(1084)又有三佛齐来贡方物。 频繁前来的三佛齐使者,曾使得各地官员应接不暇,所以苏轼就说“今日观三佛齐朝贡者过泗州,官使妓乐,纷然郊外,而椎髻兽面,睢吁船中,遂记胡孙弄人语,良有理”。可以考见通过南海而来,或者经由南方陆路而来的朝贡者不少,包括交趾、占城,以及勃泥、注辇、詹卑,也包括可能泛海而来的,更远的层檀以及大食。
以上便是关于北宋神宗时代国际关系的概貌,也是李公麟绘制《万方职贡图》时可能接触的外国知识。这里还有三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在熙宁元丰年间,占城与北宋的关系相当密切,这也许是因为北宋对交趾即南越颇为头痛的缘故。北宋之初,南越的黎桓建立起前黎朝(980~1009),一面自称“明乾应运神武升平至仁广孝皇帝”,一面派遣使者到大宋来通好。忙于应付北边契丹的宋太宗,也只好承认南越独立、黎氏当国的事实。虽然这个黎氏王朝只有三十年,被李氏推翻,但是南越独立成为事实。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就有张方平建议联络更南方的林邑(占城),让占城作为威胁交趾后方的力量,因此占城这一时期与北宋关系热络,来朝贡的使团确实不少。第二,李公麟《万方职贡图》中没有日本,这是对的。虽然日本往来北宋多有记载,李公麟也可能目睹,但日本并非朝贡国,这一点北宋官方非常清楚。元丰元年(1078),日本国使者孙忠和通事僧仲迥前来进贡,以太宰府名义送上丝织品和水银等物,但明州官府就指出,他们实际上“非所遣使者,乃泛海商客”;元丰六年(1083),日本僧人快宗等十三人来华,虽然神宗也曾召见他们,但很清楚地说,他们是作为佛教徒来天台朝圣,而不是来入贡的。第三,在各个朝贡之国中有点儿奇怪的是,李公麟这一职贡图并没有画“大理国”。自从传说宋太祖玉斧划界,不再把大理算成大宋疆土之后,“宋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大渡河以南变成“外国”,因而大理国“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接受唐代教训的宋朝官方甚至颁布命令,约束边界上的军民不要越过大渡河去滋事。 但是,恰恰是在李公麟在朝廷任职的熙宁年间,神宗开始特别关注西南局势,熙宁七年(1074)甚至让成都府“招诱西南夷和买” ,第二年又下诏让大臣讨论西南大势,而熙宁九年(1076)五月,也就是李公麟还在朝廷任职之时,大理国来北宋汴京进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朝贡,这件事情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可是,李公麟却并没有把这次的朝贡画在他的《万方职贡图》中。
四、实录的、想象的和记忆的:《万方职贡图》中十国的分析
综上所述,在与北宋往来之关系上,传为李公麟绘、曾纡题记的《万方职贡图》中十个国家大体可以分成五类:
第一类是确实有使团或使臣来中国朝贡的国家(4国)。其中,包括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今印尼的苏门答腊)、渤泥国(今印尼的加里曼丹)、朝鲜(朝鲜虽是旧称,但当时国名并不是朝鲜而是高丽,而高丽也是同时向契丹辽进贡之国),这些国家虽然时有使团或使节来朝贡,不过也许更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与富庶的北宋中国通商。
第二类是并非制度意义上的朝贡国,而可能是一些商贾或人员,曾与北宋有过联系的“外国”(2国)。其一是女真(今中国东北),女真人虽然在崛起过程中逐渐与宋朝有人员往来,并且在神宗朝之后数十年,还约定联合夹攻契丹,但在熙宁、元丰年间仍处于契丹控制下,并非北宋的朝贡国;其二是吐蕃(今中国四川西部、青海及西藏),前面说到北宋时吐蕃王国已经瓦解,余部分裂,与宋朝时战时和,有时靠近宋朝边疆的部落内附,有时这些部落又成为边患,事实上恐怕并未有作为“吐蕃国”的朝贡使团,所以宋太宗才会说把它“置之度外,存而勿论”。显然,在神宗的熙宁、元丰年间它并不是北宋的朝贡国。
第三类是若干年中虽然偶尔有使者或商人前来中国,但也绝非北宋的朝贡国(1国)。拂冧国,据学者研究即首都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它并不是来朝贡的。《宋史》里都说拂冧“历代未尝朝贡”,一直要到元丰四年即1081年,也就是李公麟这幅《万方职贡图》创作之后的两年,才有一个叫作“你厮都令厮孟判”的人来,他虽然自称是国王派遣的朝贡使者,但恐怕只是一个到东方来的商贾。
第四类是原本并非北宋时代实有的朝贡国,而是绘制者或文字撰写者捕风捉影,或根据一些历史资料想象出来的异域(2国)。比如“罕东”(一说在今酒泉和敦煌附近,一说在西宁附近),以及“西域”(正如前面所说,宋代的西域并非一个国家)。整个神宗时代,西部除了于阗之外,由于路径被西夏、契丹和吐蕃余部阻隔,各国根本不可能成为北宋制度性的朝贡之国。
第五类则是想象的子虚乌有之国(1国),即“女人国”(有传说是在爪哇岛以东,一说是苏拉威西即Sulawesi岛)。从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并非与宋朝真正有官方或民间往来的国家。
我们推测,在李公麟生活的北宋神宗时代,这十国中真正来朝贡并且可以被李公麟亲眼目睹的,也就是高丽、三佛齐、占城和勃泥,而其他各国则或来自传闻,或来自史籍。显然,在西部、北部、西南都已经成为异国的情况下,宋朝已经没有多少汉唐时代天下帝国那种盛况,宋代所谓“朝贡”之国,主要在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此,10世纪中叶到13世纪之间(960~1279),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才开始转向海路、转向南方,这就是后来“南海贸易圈”形成的开端,也是当时大量在沿海建立市舶司的原因,更是后来有关异域新知识的著作,如《岭外代答》(1178年成书)、《诸蕃志》(1225年成书)等在南方产生的原因。
可是,中国历史上的帝国统治者和知识人,都喜欢看来朝拜的蛮夷,为什么?因为有中央天朝的心态。看到海外蛮夷一方面表现出低头臣服的恭敬,一方面显示奇形怪状的野蛮,心里会特好奇也特自豪。其实,正如与李公麟同时代的苏轼所说,包括高丽在内的各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很多人可能都看到了,“高丽之臣事中朝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中国之招来高丽也,盖欲柔远人以饰太平耳”。
但是,在一种需要表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传统天朝上国的心态中,他们觉得仍然可以用图画的方式、居高临下的眼光俯瞰四夷,一方面流露对野蛮人的怜悯和轻蔑,一方面满足唯我独尊的天下帝国意识,李公麟《万方职贡图》似乎就是这样的艺术作品。在已经不是天下帝国,也没有那么多朝贡国的时代,想象本朝仍然是天下帝国,依然有着万国来朝的盛况,这成为帝国的传统。即使到了北宋行将遭遇灭顶之灾的前夕,仍然有一个叫翁彦约的官员向宋徽宗建议绘制职贡图。他说,现在“天复万国,化行方外,梯航辐辏,史不绝书”,比三代汉唐都伟大,域外蛮夷“莫不向风驰义,重译来宾”,中国“声教所及,固已袭冠遣子弟,旷然大变其俗”,所以应当“观其贽币服饰之环奇,名称状貌之诡异”,“以见中国至仁,彰太平之高致,诚天下之伟观也”。。一百多年后,在疆域更加缩水的南宋,刘克庄(1187~1269)看了李公麟另一幅作品《十国图》之后,就说画上的十国中只有日本、日南和波斯三国“至今犹与中国相闻”,其他七国都已经只是历史记忆了。虽然李公麟所画并非全是“虚幻恍惚”,但大半朝贡国却只是李公麟的想象。刘克庄说,李公麟把异国人想象成野蛮人,“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发露骭,或髻丫跣行,或与群下接膝而饮,或暝目酣醉,曲尽鄙野乞索之态”。
“鄙野乞索之态”就是想象异邦时候的傲慢,这种傲慢则在心中产生自我满足感。其实,李公麟生活的北宋已经没有那么富饶和强大,周边各国也没有那么落后和恭敬。他们客观地看到了“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也真切地知道契丹、西夏等国,不仅“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称号,仿中国官职,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已经和中国不相上下,而且“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可是,在这样的积弱时代,自我安慰式的想象就更加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抚慰缺乏自信的心灵。所以,我说李公麟的《万方职贡图》象征着中国逐渐收缩的时代,却在想象自己的膨胀,这也导致了宋代中国(甚至以后中国)的一个传统,就是“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却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
对这种想象更加尖锐的批评来自明代知识人。在经历过蒙古时代笼罩欧亚,然后又再度收缩成为汉族国家的明代,很多人已经了解到宋代图绘异邦时,这种夸张只不过是自我安慰。明代学者韩洽写诗说,如果说唐代阎立本画《职贡图》还算是有道理,因为“有唐贞观万国宁,殊方异域皆来庭”。可是李公麟呢?他说,“龙眠居士生有宋,未必诸蕃真入贡”。所以,他怀疑李公麟是根据前人的旧作重新临摹,并不是真的实录。他特别敏锐地指出,宋神宗元丰时代,国家渐渐稳定和强盛,君臣享受了一阵子的和平,反而膨胀起来,争先恐后讲“强国术”,这使得君臣沉湎于崛起和称霸的幻想中,却“不知中国正凋残”。所以他说,李公麟画《职贡图》满足于无端的自大,还不如同时代的小官郑侠画《流民图》,让皇帝知道民众正在流离失所,应停止毫无意义折腾百姓的变法。
五、天下帝国意识的延续:以清代的《皇清职贡图》为例
可惜这种清醒的批评并不多,倒是通过《职贡图》想象天下帝国的这一艺术史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就连蒙古入主中国的蒙元时代,也同样延续了这个传统。随着疆域的扩张,各种各样的“职贡图”更是陆续出现,记载着那个时代膨胀的帝国与四裔的往来,夸耀着横跨欧亚的蒙元帝国之强盛,也满足着帝国之内君臣的虚荣。即使是在疆域大大收缩的明朝,也一样出现很多职贡图。这些图像一半是根据当时各种异域来朝的实际景象,一半则是沿袭历代各种职贡图的内容,把留存在历史中的知识、记忆和想象,掺入看似写实的绘画作品。像明代仇英的《诸夷职贡图》,不仅有“九溪十八洞主”,还有在历史中早已消失的契丹、渤海,甚至子虚乌有的女王国。
这种“想象天下帝国”的艺术传统到了清代,与帝国疆域一样,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值。18世纪中叶,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武力拓殖,大清帝国版图逐渐扩大,“圣武远扬,平定西域,拓地两万余里,增入各部落三百余种”,于是在乾隆年间终于出现了篇幅最大、描述异族与异国最多的《皇清职贡图》。乾隆十三年(1748),在平定大小金川后,乾隆皇帝就有心绘制各地的民族风俗图像,作为大清帝国统治亿万子民之证据。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则正式下令,由军机处统管此事,并且把现有的样本发到“近边各督抚”,让傅恒等主持其事,按照标准样式,绘制已经纳入帝国版图的各地民众风貌的图册。恰好,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太监胡世杰缴上一套《职方会览》,乾隆便下令让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瀚、程梁等人依照这种图册绘制“职贡图”。在绘制过程的若干年中,宫廷画家们根据军机处提供的资料,以及陆续看到的实际来朝使团情况,更依照当时不断征服的疆土情况,陆陆续续加上了爱乌罕回人、哈萨克、伊犁、土尔扈特台吉等。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这一图册不仅最终画完上呈,还由其他画家另外临摹了好几份,并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特别誊抄陆续增补过的九卷《皇清职贡图》若干份,作为《四库全书》之一。
在这个九卷本《皇清职贡图》中有三百多个不同国家与族群的图像,其中既包括了大清的朝贡国,如朝鲜、琉球、安南、暹罗、苏禄、南掌、缅甸等,也包括了远航而来进行贸易通商的法兰西、英吉利、日本、俄罗斯、荷兰等,还包括已经纳入版图的区域,如西部的西藏、伊犁、哈萨克,东部的鄂伦绰、赫哲、台湾,南部的琼州,以及西南的各种苗彝等。在当时大清君臣看来,似乎天下/世界都在大清的笼罩下,所以他们很蔑视梁元帝当年绘制的《职贡图》,只有三十余国,“既地限偏隅,无可称引”。就是对号称“盛世”的大唐,他们也颇为不屑,说阎立本在唐代绘制《职贡图》,但“一代时势转移于突厥、回鹘,不免委蛇求济,或结为兄弟,或重以和亲,且不足以语羁縻”,哪里比得上大清!“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这才是无远弗届的天下帝国。因此,在《皇清职贡图》的卷首,我们看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皇帝充满自豪的《题皇清职贡图诗》。他自负地说,大清已经笼罩天下,“书文车轨谁能外,方趾圆颅莫不亲”,四夷都来朝贡,“那许防风仍后至,早闻干吕已咸宾”。
可是,到了18世纪中叶,世界已经进入早期全球化和东西帝国共同竞争的时代。在中国,尽管一方面有关世界的知识越来越多,对于远近各种国家、民族、风俗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但另一方面却由于疆域扩大,仍然在想象自己作为天下帝国,作为天朝大皇帝,享受着“万国来朝”的满足感。或许应当说,《皇清职贡图》以及同时代的《万国来朝图》等绘画作品,正好反映了当时中国官方和知识人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念。自从梁元帝《职贡图》以来,到大清官方的《皇清职贡图》,历代的官方与士大夫都曾以异域来使朝觐为主题,画过这种叫作“职贡图”的图像。在很长时间里,这种表现天朝上国笼罩天下八方的图像,一直被当作“万国”、“异族”、“番鬼”甚至“洋人”图像的范本,无论是写实的,还是想象的,它都充当着对“中国”,以及对“世界”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也让中国始终像宋代李公麟《万方职贡图》表现的那样,虽然是“未必诸番真入贡”的时代,却总在“驰想海邦兼日出”。
Wanfang zhigongtu in the Song Dynasty
Ge Zhaoguan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f the article is not about artistic history, but ideological history. “Zhigongtu” is a special artistic depiction of the occasion as foreign countries presenting tribute to an emperor. The tradition, which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6th century, has its long standing influence on artistic history and also presents a characteristic ideological history. The pride and confidence of the empire was expressed through the contrast of exotic features and foreign envoys and arrived to an imaginative great empire that was prominent to the surround of tributaries. This tradition was handed down even to the Song dynasty in a time of territory decreasing and national assimilation. This article carries out a case study of Li Gonglin’s Wanfang zhigongtu that was created during the reign of Song Shenzong in Xining and Yuanfeng years, and examines into the tribute exchanges between the Northern Song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It compares the artistic work and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tries to explain not a small part of the work originated from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empire imagination though the other parts might have been in keeping with the truth. It proves that the Song dynasty still indulged itself in the dream of an overwhelming empire despite the fact it did not possess the thriving power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t points out in particular that this artistic tradition went on to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imaginative empire consciousness, which reflects the lasting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self conception and worldview.
Keywords: great empire; tribute system; Li Gonglin; Wanfang zhigongtu
[责任编辑 陈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