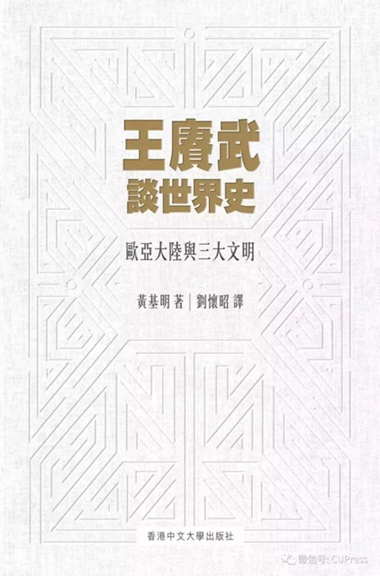
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
黄基明 著,刘怀昭 译
世界史研究绕不开欧亚大陆
王赓武
2018年书展新书
《王赓武谈世界史》中文序言
我对现代时期以前的世界史的理解是,一切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都发生在欧亚大陆,而它三面临海的土地始终关切于海面的波涛、牵动于洋上的风浪。但与陆路发生的事件相比,有关各大洋海事活动的记载显得凌乱而又支离破碎。数据的缺乏表明,海事在各大文明的早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那么起眼。
沿着欧亚大陆的边缘,三大延续而又显著的文明清晰可辨。西端是在西亚、北非和南欧这些相邻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地中海文明。欧亚大陆的南部边缘则目睹了印度文明的兴起,它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部分毗邻印度洋,并向东延伸到南中国海。欧亚核心以东,是中华文明(Sinic civilization);中华文明传播到了太平洋边的日本诸岛,但其影响力在东南亚则相对较弱。
欧亚大陆的腹地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从欧洲的莱茵河一路绵延向东,穿过俄罗斯及中亚的大草原,直抵印度河–恒河以及黄河、长江、湄公河的源头高地,从那里,这些大河向东向南奔流入海,汇入西太平洋。在三大文明中,地中海与另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中心有一片处于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大海。相比之下,印度平原紧贴浩瀚的印度洋,而中华大地则面朝东方和南方,朝向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数百个岛屿。
全球化的现代时期是海洋探索的产物,是1492年之后发轫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地中海扩张的一部分。那是一场真正的全球化进程,它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逐步将世界经济整合了起来。这一扩张是海洋性的,而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来地中海主要海军力量之间的控制权之争。一场场无情的争霸孕育出一种进犯性的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了要把陆地和海洋全都掌控在自己手上的帝国。当斗争最终蔓延到大西洋时,其势已锐不可当,很快就远播四海,蔓延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那种跨洋性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三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时出现了一个由美洲形成的新大陆,很快它就隶属于地中海的欧洲那半边。这给大西洋沿岸的探险船只提供了进入另两个大洋的通道。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而西班牙人等其他人则取道另一边,绕过南美洲进入太平洋。他们全都在东南亚殊途同归,并且在短短几十年间,全球就基本上归于海洋性了。这里一语道破的是近代史的前世今生:十八世纪崛起的新兴力量继续为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新的系统规范(systemic norms)。这些规范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支撑,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为后盾,以在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基础上创造出新型财富和权力的富于凝聚力的民族帝国(national empires)为靠山。

地中海规范
(The Mediterranean Norms)
这一转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地中海地区。自从五千年前文明的开端以来,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就与众不同。腓尼基人和希腊的海上殖民地为伟大的陆–海帝国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塑造出一个能够多方位扩张的权力系统,并如此这般地向北、向东、向南施展了拳脚。大约1500年前,那里发生了一场剧变,当时地中海周边国家因对一神论的解读存在激烈分歧而形成割据局面,地中海文明从此或多或少地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这与上一个千禧年的情形有很大不同——想当年,地中海就如一个内湖,万邦及帝国在湖上自由地竞逐商机、争享荣耀。
1500年后,地方冲突还在持续,而地中海文明仍处于分裂状态。地中海欧洲一侧的南半部分落入到穆斯林的阿拉伯势力手中,这一势力从七世纪一直幸存到现在。那长达1500年的分裂对西欧人形成阻滞,致使他们无法直接接触到欧亚大陆另一边土地上的灿烂文明。他们的商人既无法直接取道进入印度市场,也无法抵达那些更遥远、而且可能更富庶的中国城市。
他们知道遥远的东方物华天宝,他们想去那里通商,但四分五裂的地中海使他们寸步难行。他们于是转向大西洋。葡萄牙人领先其他欧洲人,最早到达印度、继而东南亚、中国和日本。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紧随其后。他们都偏爱垄断性的贸易手段,并以他们无可匹敌的海军实力来对付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商人。于是,在三个大洋皆被他们闯入之后,这些后来者就彻底改变了历史话语。尤为令人瞠目的是,他们发挥了地中海内部的海上冲突传统,使他们得以将一种全球性权力结构施加在原本并没有持续性海战传统的地区。
历史记载了马来人和占婆人(Chams)在华南及爪哇海域的较量,室利佛逝王国(SriVijayan)称霸马六甲海峡两岸的年代亦有史料可循。我们还知道,南印度的朱罗王朝(Chola)统治者曾有能力派遣海军穿过孟加拉湾来挑战室利佛逝王国的霸主地位。此后,满者伯夷(Majapahit)和泰国的海军也曾有数次短兵相接。但他们在十六世纪之前的这些所作所为,无一能与地中海地区展开的持续而致命的海战相提并论。加之,美洲新大陆为西欧带去了新的资源,促进了那里的科技繁荣、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于是,新的海军帝国如虎添翼,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旧的封建帝国不得不让步于那些在欧洲内部争夺权力的商业帝国。相互的交战持续了几十年,他们其间的一系列会谈为主权及重商主义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最终达致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的签订。他们随后逐步演进为荷兰、法国和英国等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帝国主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这些帝国为各国逐步(特别是在二战之后,随着帝国的解体)开始接受的一套新的系统规范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只有民族国家才有资格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许多亚洲国家都试图从各种后殖民地形态中跳脱出来、来建构各自的民族。如今它们仍在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努力着。与此同时,一些替代性结构出现了。这一情况的出现始于冷战时期,当时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力图将世界在他们中间分裂开来。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满足于仅做个民族国家或国家帝国便罢。对此,一些存在共同利益的民族国家就以发展各种区域性组织作为回应。
1990年代当冷战结束时,全球性超级大国只剩下了孤零零一个,这种情况也是前所未有。过去的一个世纪,世界的系统规范是由两个超级大国操纵强大的民族帝国来决定的。四十年后,举世仅剩一个超级大国。这种变化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卓越的海军有实力一手打造如今的全球化,令全球经济得到了增长。
深层结构
鉴于这一全球性框架,我们不禁要问,在研究未来的发展时,讨论过去那段大陆和海上力量相对均衡、相互关系较为稳定的历史还有意义吗?这时,「深层结构」这个词就为思考「过去会如何影响当下」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途径。弗朗索瓦.吉普鲁(Francois Gipouloux)在《亚洲的地中海》(The Asian Mediterranean)一书中提到了这种潜在结构。例如,早在地中海列强抵达之前,印度洋和太平洋就已经存在一种结构。那就是集中于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岛屿(即东南亚群岛)的那种半地中海(semi-Mediterranean)条件下的网络关系。
那里的深层结构是什么呢?很明显存在那么一种结构,它将欧亚大陆的各不同部分联系在一起,其踪迹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随处可见,可以一直下溯到十六世纪。《亚洲的地中海》揭示了这种网络的存在。其结构与地中海结构非常不同,因其并不受制于帝国海军之间持续的海上冲突。此外,该网络中从未有两股不相上下的势力僵持对峙1500年这样的超乎寻常的经历。相较于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罗马帝国和希腊帝国之间、十字军和突厥–阿拉伯人之间在地中海的海战,波斯湾和东海之间发生的任何冲突都要逊色得多。
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统治者立足大陆的权力运作方式,无论在印度文明还是中华文明中都是如此。几千年来,它们一直没有海上对手与之抗衡。这个框架中唯一的异数是远在东北一隅的日本。在那里,日本人确实积聚了相当可观的军事实力,但他们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选择超然于大陆事务之外,直到十六世纪晚期,即当欧洲海军已经真切地出现在日本的海岸上时,日本才开始崭露头角。
简而言之,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没有任何可与地中海地区相提并论的权力割据局面。两洋沿岸的贸易活动大体上是和平进行的,而商业、文化及宗教的迁移都是在没有重大冲突的情况下展开的。没有任何事情靠诉诸海战来解决。各种争端在口岸城市和流域王国(riverine kingdoms)之间就摆平了,统治者时常亲自参与贸易谈判,偶尔也会以暴力收场。这些活动将中国、日本、朝鲜的沿海地区联系在一起,并越过马来群岛一直绵延到印度和波斯湾。
的确,在十五世纪初,明永乐皇帝曾派郑和率领大规模的远洋舰队七下西洋。这是成功横跨两个大洋的第一支强大海军。这表明中国人有能力支持海军作战,然而这几次远航终以历史性的跑偏而收场。一俟郑和断定远洋上没有敌手,明朝统治者就把海军遣散了,对中国的海岸线之外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官方兴趣。此后,中国在外海的活动大体上就剩下福建和广东这两个南方省份的商人了。
这种官方兴趣的缺乏将我们带回到以大陆为基础的中国历史的深层结构中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立足于大陆,因此,东海及南海的半地中海特征从来不曾受到任何强烈或持久的关注。当然,在十世纪之后,当中国的人口向东南部迁移时,当中国出现割据、朝廷被逼南迁时,人们肯定对把握商机愈来愈有兴趣。但最终,历朝历代仍继续建立在大陆性的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其北部也不得不终年面对欧亚部落的袭击和进犯的威胁。
南亚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印度文明并不依赖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系,其沿海王国和口岸是独立于中央控制的。印度沿海的众多政体相互自行开展海上贸易,也与飘洋过海而来的外国商人洽谈生意。那些外商主要来自红海和波斯湾,也有少数来自东方。但印度与中国的共同之处是要面对来自中亚的陆路威胁。敌人总是一成不变地来自西北内陆,而印度次大陆又相对比较开敞,易受草原骑兵的攻击。因此,千年以来,印度统治者花了很大精力重兵把守陆路边界以确保不失。
在岛屿众多而又陆地辽阔的东南亚,情况又一次不尽相同。在这里,大陆与岛屿之间的利益划分造就了一段独特的历史。我前面提到,那里没有发展出任何能与中国或印度抗衡的力量。该地区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该地区自身内部,存在于依赖海上贸易的各方(尤其是在马来群岛)与面对内陆敌人威胁的大陆之间。本土的孟–高棉王国(Mon-Khmer kingdoms)与来自北方的泰国和缅甸军队之间的对抗,使他们长期将重心放在土地上。无论如何,大多数情况下,该地区的陆地国家与海洋性国家都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
总体而言,决定着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权力系统的关键性历史因素出自欧亚腹地,即马背上的势力,类似于冲击过中国、印度和地中海的那些骑兵。那些通过中亚陆路将三个文明连接起来的进攻性力量始终难以遏制。沿着所谓「丝绸之路」而展开的陆路贸易,靠的是众多不同的部落国家和绿洲古镇的共享利益,并且总是受制于局部冲突(若非全面战争)。相比之下,海上的联系就甚少涉及政治角力,因此很少有人费心去记录海上联系给从事商业活动的各方带来哪些好处。海事的记载主要就是关于船舶在港口之间进行的往来,每年随季节和季风的变化而动,并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大起大落。
深远影响
十六世纪后,随着全球性的海洋开发,通过欧亚大陆而进行的商业活动出现锐减,该地区也因此在过去三百年的发展中退居次要角色。那么,欧亚核心是否因此而无关痛痒了呢?如果我们审视一下那里的深层结构,就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欧亚大陆腹地的各国政体仍一如既往,目光向外,朝东、西、南三个方向全方位向外审视。他们当中包括那些从改变世界经济的全球力量中成长繁荣起来的国家。欧亚核心实际上从来都不是无关痛痒的,因为欧洲西部的现代化进程使俄国人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得以东进,而大陆上的其他发展则导致满清反向西迁。到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俄、中这两股势力在欧亚大陆中间相遇,那一幕远没有当时的海洋全球化那么富于戏剧性。但他们的相逢仍意义重大,并且这两个帝国最终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在1945年以后,当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展开了冷战时,中俄的相逢这使得大陆性势力有机会对海洋性主导势力发起反击。
尽管如此,大陆性国家仍然处于劣势。在冷战时期,最精锐的海军主要在自由民主国家或曰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边。海上优势使得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约束了苏联集团的发展。后者仅在中国沿海有些开阔的海岸,而中国人在整个二十世纪里都无海军可言。所以说,西方的胜利就是海洋霸权的胜利。
中国人这边则因为疏于海军建设,数百年来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确曾试图重振旗鼓,适时打造一支新的海军,但在十九世纪末兵败于日本人。1911 年后,中华民国陷入割据,继而遭到日本的侵略,无从着手建立过硬的海军。因此,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的胜利,完全是赢在陆战上。他们连一艘军舰都没有。解放军第一次提到海军是1948年要横渡长江的时候。即使在胜利后,他们也只是与大陆性强国结盟。没有任何海洋国家来帮他们培训海军,因为海洋国家正是隔海相望的敌人。因此,即使1990年代以来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也仍是面对一个完全主宰沉浮的海洋性超级大国,其实力甚至超过当年的英国。
在历史长河中,还有一个启示也值得记取。说到全球性海军大国,荷兰和英国的示范颇具指导性。其中,荷兰地处欧洲大陆,而英国则由岛屿组成。前者因此一直被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大陆性大国所遮蔽,其海军也无助于它在陆地上强大起来。而英国则在外海上不受约束,因而成长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但最终,英国人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因为他们没有大陆来帮助维持其实力。此外,作为一个如此贴近欧洲大陆的岛国,每当有欧陆国家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力量,它就会显得不堪一击。因此,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都需要美国这样本身拥有大陆基础的海军来打救它。
在地球的另一边,日本也有类似的问题。那就是从长远来看,仅做个岛国是不够的。一个没有大陆基础的海军力量是不够的。英国曾几近成为超级大国,但其实力得不到保障,因为它没有大陆可以依靠。可美国人就有。这正是如今这个系统规范的关键所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这么一个雄踞大陆、同时又凌驾于海上的强国。正是这样的优势使美国的海军力量于1945年以来主导了世界。美国在陆地疆界上没有敌人,因此它是驰骋三个大洋所向无敌的海洋性国家。他们从英国海军那里汲取了教训,极大地加强了陆上的保安。
相形之下,像德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陆性国家就成了跛足。他们根本就别想轻易地闯到外海上去。因此,他们的大陆力量无法支持做为全球大国所需要具备的那种海军。至于日本,它与英国是同样的命运。它没有大陆性根基,拼命想登陆朝鲜、东三省以及进入中国。最后,这一切使他们鞭长莫及,他们的宏伟计划终告破灭。
这让我们的讨论回到中国上来,来说说正在中国崭露头角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它对于美国人及其他人来说如此举足轻重。中国素有大陆性实力,现在又有了发展海军的能力。中国人在500年前曾拥有过海军,但复又失去。他们如今正试图再造一套必要的心理定势,以确保他们的新海军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若果成事的话,中国将成为拥有强大陆地支持的海军力量的另一个大国。在目前阶段,中国海军还无法与美国海军媲美。但他们现在已经非常重视海上事务。这仍是一项相对较新的发展,且中国的政治核心之中还谈不上形成了什么海军传统。现在敲响所谓「中国邻国正面临其海军威胁」的警钟,显然是另有心事,比如说,可能出于担心美国在中国沿海的霸权可能会面临挑战。
中国人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多层面的。有两个迫切的问题。中国在经济上与全球海洋性经济联系在一起,其未来的发展有赖于此。他们显然需要海上局势安全可靠。与此同时,它的边境有三分之二是陆路边界,而且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在陆路确实有潜在的敌人。这绝不是胡思乱想。中国人有数千年抵御陆路敌人的历史,他们绝不会以为将来就不会有这样的敌人。他们的邻国多达十几个,并非总是睦邻。因此他们永远无法免于大陆性威胁。
在此,我们回到文明的深层结构上来。欧亚大陆对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历史产生过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继续扎根于他们的文明中。中国尤其对海洋有强烈的意识,因为它看到自己的文明曾险些被来自海上的敌人所毁灭。如今中国文明进行了一番现代化,它想要确保那段失败的历史永远不会重演。因此,只要强国的海军坚持在中国沿海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中国的领导人就必须密切关注海军,与此同时又绝不能忘记,中国三分之二的边境在大陆上。即使在他们为应对未来的威胁而进行海上军备及其他复杂的备战时,强大的欧亚大陆传承仍会告诫他们,他们必须继续培养一种新的、均衡的全球史观。

王赓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海外华人、华人移民等问题。1986 至1995年间曾担任香港大学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新加坡东亚研究所(ISEAS)所长,澳洲国立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着包括:《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2013)、《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2014)、《天下华人》(2016)、《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2016)、《1800年以来的中英碰撞:战争、贸易、科学及治理》(2016)、《香港史新编》(增订版)(2017),等。详情请参本书〈王赓武著述一览(2008–2018)〉。
黄基明博士,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槟城月刊》(Penang Monthly)创报主编。出版著作多种,与Ding Choo Ming合编之Continent, Coast, Ocean: Dynamics of Regionalism in Eastern Asia (2007) 获东盟图书出版商协会2008年度「顶尖学术作品」殊荣,The Reluctant Politician: Tun Dr Ismail and His Time (2006) 获2008年亚洲出版大会奖。
学者推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进行,「全球史」应运而生,并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史学潮流之一。全球史的目标是向社会提供能够真正重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历史,然而要写出这样的历史却非常困难,不仅需要历史学家有深厚的学术功力,而且需要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本书就是一部完美地达到了这个目标的成功之作。它以广博的知识视野和新颖的问题意识,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前所未见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而且提供了对世界和历史认识的新视角。我本人从这部杰作中受惠良多。
——李伯重(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
这真是一本好书,出自思想深邃的资深学者,却又易读易懂,引人兴致、启人思考。我自己曾在新加坡、香港和北京与王教授倾谈历史,他的丰富阅历使他在观察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欧西文明时都有独到的见解。为此我十分羡慕并且感谢黄基明先生,通过和王赓武教授的对谈,从地缘、人文和经济等方面把王教授对世界文明演化和当今世界大势的看法展现给读者。王教授结合了海权论和欧亚大陆「心脏」论,说明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顺带也解释了中国近来所揭橥的「一带一路」的构思,富有现实意义。
——张信刚(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及教授,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