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彬村教授是 1976 年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碩士,1983 年取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同年 8 月,進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原名為三民主義研究所,1987 年改名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4 年 7 月改為現名)擔任副研究員,1990 年 7 月升任研究員迄今。曾於臺灣大學經濟系和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經濟史課程。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與臺灣海洋史以及明清經濟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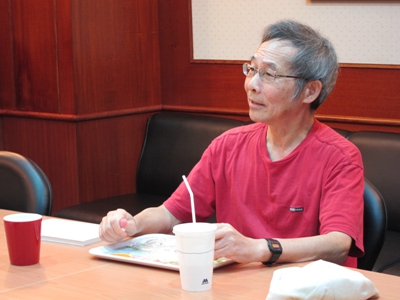
求學過程
張彬村教授在求學時,原先大學念的是臺大外文系,後來改念中文系研究所,出國後才轉而從事經濟史研究。張教授回憶起大二時,因覺得外文系的課程索然無味,於是就開始到中文系旁聽一些課,覺得內容很有深度,引發他的興趣。大學畢業之後,張教授就決定報考中文研究所,並於屈萬里教授 [1] 門下受業。在中文研究所期間,他曾經接觸古文字學、宋明理學、經學等不同領域,幾經考慮之後,決定以《易經》、《莊子》的比較為題,撰寫碩士論文。[2]
中文研究所畢業之後,張教授被分發到東港的空軍幼校服兵役。在當兵的同時,也思考未來的生涯規劃,並決定在退伍後申請出國留學。1978 年,張教授順利申請上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隨即赴美深造。美國的生活方式與學術資源,讓張教授大開眼界。
張教授回憶道,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有個東方圖書館 (Princeton Gest Oriental Library),藏書規模與多樣性,是他過去在臺灣無法想像與接觸的。特別是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那時候在臺灣都是禁書,只有史語所能看到一點點,但是要取得、借閱都並不容易。張教授在那裡,除了上課之外,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圖書館,讀書讀得津津有味。
張教授說起他在中國書籍中讀到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史觀,那樣的觀點對當時的他來說,新鮮且有啟發性。書上說中國在 1949 年解放以後,歷史學界開了三朵金花:第一朵金花是關於歷史分期,改變了過去按朝代分期的觀念,而是按生產力的關係來分;第二朵金花是農民起義的研究,過去我們認為是流寇、盜匪的歷史,他們定義為農民起義;第三朵則是有關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他當時覺得這樣的觀點很有趣,也能從結構主義的角度掌握到某些中國歷史的真實。[3]
張教授提到,過去在臺灣受的歷史教育,講 24 個王朝,一代一代的,就像魯迅說的「帝王的家譜」,寫的都是皇權更迭的歷史,還有一堆歌功頌德的話。在裡面看不到老百姓怎麽生活、怎麽掙扎。他那時候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沒有深刻認識,但覺得中國史學界這樣的觀點還不錯。
當時他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特別感興趣,1980 年夏天考完博士班資格考之後,開始與指導教授 Frederick W. Mote(牟復禮)[4] 討論博士論文撰寫方向。他在牟復禮的課堂上發表了〈十六、七世紀中國的一個地權問題:福建省漳州府的一田三主制〉這篇文章之後,[5] 初步將方向鎖定在社會經濟史。牟復禮教授相當肯定他的想法,並且建議他藉著修課,為撰寫博士論文做知識背景上的準備。因此他先後在東亞系以及社會學系、經濟系選修 Denis C. Twitchett[6]、William Baumol[7]、Arthur Lewis[8] 等學者的課程。在修課的過程中,他逐漸了解自己的興趣與極限,與指導教授再次討論之後,將範圍縮小至中國經濟史的研究。
張教授決定研究題目的另一個關鍵,則是與另一位明清經濟史學者傅衣凌 [9] 教授的結識有關。在 1980 年代初期,中國大陸跟美國建交之後,不少大陸學者來美訪問,傅教授當時曾經到普林斯頓訪問一個月。張教授當時受到牟復禮之託,代為招待傅衣凌教授。他赫然發現自己原來讀過傅衣凌教授的文章,也非常欣賞他的研究題材與研究方法。那段期間,他常常陪著傅衣凌教授在圖書館影印資料,並向教授請益,傅教授對於他的未來研究方向給予了很多建議。[10]
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與準備,最後張教授決定以 16 世紀明代中國對外貿易為主題撰寫博士論文。[11] 這個有關中國海洋史研究的重要主題,在那時還很少人接觸。開始撰寫之後,張教授相當樂在其中,他形容自己感覺像哥倫布在航海一樣地探索,覺得世界很廣大。在 1983 年時,他順利完成論文,並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而這個有關明代對外貿易史的博士論文研究,則開啟了張教授回臺參與推動臺灣海洋史研究的契機。
參與西洋經典著作的翻譯與經濟史課程的教學
不同於一般臺灣歷史學界出身的明清經濟史研究者之處是,張教授曾經翻譯西洋經濟史的名著,且有在臺灣大學經濟學系長期教授經濟史課程的經驗。這些學術經驗對張教授的研究生涯帶來不少有意思的影響。
張教授在 1983 年 6 月剛口試完時,在好友康樂教授 [12] 的引介下,開始參與新橋譯叢的西洋學術名著的翻譯工作。當時的翻譯團隊缺乏經濟史專長的譯者,他就在康樂的安排下,與夏伯嘉教授 [13]一同翻譯西洋經濟史論著。他當時被分配翻譯兩本著作,一本是有關西方工業革命的作品,另一本是 19、20 世紀近代歐洲經濟史的作品。[14] 在大學教學的經驗則始於 1987 年,那個時候臺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透過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陳昭南教授 [15] 引介,邀請張教授到臺大教授經濟史課程。他便從 1987 起前往開課,直到 2001 年為止。張教授表示,自己對西方經濟史的學習,很多是來自於翻譯與教學的經驗。他提到他自己一路走來,有些興趣是一以貫之,持續發展的,工業革命就是一個持續發展的興趣;有些興趣則是意外發現的。[16]
他提到翻譯新橋譯叢時,可說是吃盡了苦頭,覺得翻譯真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但也從中得到很多收穫。張教授也因此一直很關注工業革命,他認為工業革命不管對人類或對經濟史研究來說,都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張教授說,人類有歷史以來,最重要的兩個里程碑,一個是農業出現,另一個就是工業革命。在農業出現以前,人類是部落社會,大家靠採集與狩獵維生,即馬克思說的原始社會,那樣的社會不可能產生複雜的文明。但是大約一萬年前,農業出現之後,人類才開始演變出不同的文明。作為另一個里程碑的工業革命,比起農業革命則又更加複雜,到現在仍然眾說紛紜,沒有權威性的定論。在工業革命出現之前,大家通常用馬爾薩斯的理論去說明資源生產與需求的關係,主張人口的增長是等比級數,但農業社會糧食與資源的增加則是等差級數,因此人口與經濟成長到一定程度後就會遇到瓶頸,而陷入社會經濟危機。不過工業革命的出現,卻打破了馬爾薩斯的這一理論。
張教授也提到,自己受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觀點的影響很深。他舉了 economics 這個字為例說明,這個字起源於希臘,講的是主婦的家庭預算有限,但要滿足整個家庭最大的物質需求,這種運作的藝術,就是economics。推而廣之,人類的社會經濟生活永遠都是「資源有限,欲望無窮」,如何用有限的資源盡可能地滿足欲望,這就是經濟學。能夠滿足最大需求的選擇,就是最適選擇 (optimal choice),這就是理性選擇模型的基本精神。張教授認為這個理論觀點不只可以用來分析經濟現象與經濟史的議題,而且還可以用來分析其他的社會現象,將各種現象的運作原理分析得很清楚。
張教授更以自己的兩個研究為例,說明如何從史料的閱讀中發現意外的研究題目,以及如何把西洋經濟學的理論觀點運用在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上。[17] 張教授在中研院研究期間主要從事海洋史的研究,把主軸限定在移民與貿易。在蒐集研究材料時,時常查閱明清時期福建漳州、泉州地區的方志,看到很多寡婦守寡、殉死的紀錄。他回想起以前閱讀傅衣凌教授的研究時,當中也稍微提及這個現象。他後來又看了其他地區、時期的紀錄,發現宋代守寡的風氣並不盛,且如果理學家有親友喪夫,甚至會建議她們再嫁。經過一段時間詳細調查史料之後,張教授發現從宋代鼓勵再嫁轉變到明清鼓勵守節之間,其實是不同朝代間某種遊戲規則改變的問題,也就是說財產安排的方式改變了。
比如說從《名公書判清明集》裡面的幾個判例來看,宋代女性在夫死之後,可以分到男方一半的財產,再嫁時也可帶走財產。這個風氣的轉捩點其實與蒙古人的崛起有關。蒙古是搶婚制,女性被視作財產,他們的文化裡面沒有寡婦,丈夫死後,婦女由男方的兄弟繼承,稱為「叔接嫂」或「收繼婚」。當蒙古人開始統治華北時,曾經強力推行這個制度;但漢人不能接受,引起很多問題,例如自殺。忽必烈晚年時,有鑑於漢人強力反彈與各種悲劇的發生,於是採取折衷的方法,改變宋代的財產分配方式,使女性在改嫁的情況下,無法帶走夫家財產。寡婦在婚姻市場本來就處於劣勢,若不能帶走夫家財產,對寡婦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留在夫家守寡。張教授認為,道德上守節、延續香火當然是一種考量,但物質、經濟上的考量可能還是影響寡婦去留的關鍵因素。
這個制度到了明代,又被明太祖所繼承,清代也繼續沿用。寡婦在這樣的制度下,守節成為一個最合適的理性選擇。此外,中國的家族結構在明代嘉靖年間開始有所變化,寡婦在夫家家族中的地位被族長所認可,財產權也受到保障,凡此都間接鼓勵寡婦留在夫家守節。
張教授另一個意外發現的題材,則是有關唐代「陪門財」。有一陣子他持續閱讀《資治通鑑》,發現唐代有個成為陪門財的婚姻習慣。他注意到中國從魏晉南北朝起,開始有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門第觀念;到了唐代,這樣的風氣仍然相當盛行,但唐朝宗室出身的品第並不高,於是希望透過婚姻提高品第。與之聯姻的世家大族覺得有損聲望,便希望宗室能給予財物作為補償,也就是所謂的陪門財。說起來,這就是一種用經濟資本交換社會資本的行為。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專題研究中心
1983 年暑假張教授畢業回到臺灣之後,經由好朋友康樂的引介,來到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任職。進入中研院後,所長陳昭南教授召集他與吳劍雄教授 [18] 規劃中國海洋史的研究。當時這個領域在院內各所幾乎沒有人從事研究,陳昭南所長卻相當鼓勵他們去開創,是個了不起的所長,直到今天他還是很懷念陳所長。[19]
張教授說 1983 年 10 月海洋史研究計畫成立之初,參與的所內研究人員只有他與吳劍雄教授兩個人。一開始他們思索如何為計畫命名,究竟要怎麼翻譯 Maritime History?最後他們決定命名為「中國海洋發展史」,每兩年開一次會,並把討論焦點放在貿易跟移民這兩個主題上。到第十屆之後,張教授才退出,把這個活動傳承給年輕人,他們也開展了新的主題。2008 年時,張教授曾籌辦了一個總結性的活動——「中國海洋發展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工作坊」,邀請國內外學者,針對中國海洋史研究現有成果及未來趨勢,共同討論及交換研究心得,並作為中研院未來規劃及推動國內海洋史研究之參考。
接著,張教授特別提到曹永和老師來所裡擔任兼任研究員的聘任過程。[20] 海洋史研究中心剛成立的時候,曹老師尚在臺大圖書館任職,沒有專門學術研究人員的身分。張教授那時剛回國,對臺灣歷史學界還不是那麼熟,但讀過曹老師的海洋史研究,對他很佩服。曹老師來中研院這件事情,他的好朋友康樂是居中聯絡的關鍵。那時候海洋史研究中心需要找新的人力,他們第一個想到的目標就是曹永和老師。商量之後,就去找陳昭南所長談聘任之事。陳所長很爽快地答應,但有個難題就是曹老師只有高中學歷,按照當時的學術規章,要聘任為中研院的研究人員會有法規上的問題。
陳所長仍請張教授繼續邀請曹老師,他則向當時的中研院吳大猷院長報告,請其協助解決規章上的問題。很幸運地,吳大猷院長也大力支持陳昭南所長的提議,並在中研院評議會提案解決法規適用的問題,因此順利聘任曹永和老師擔任兼任研究員。這件事情成了一項創舉,這個條例後來也援用在王世慶教授身上。[21] 曹老師除了來中研院協助推動海洋史研究外,更因此受聘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開始開設臺灣史教學課程,培養了國內眾多的臺灣史與海洋史研究新秀。1986 年中研院成立臺史所籌備處,曹老師受邀擔任諮詢委員,協助創所籌設事宜。1998 年曹老師更以其在海洋史與臺灣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獲選中研院院士。由此可見,這個中研院聘任事件,是臺灣學術史上很重要的一頁。
曹老師來到中研院海洋史專題研究中心任職後,一直很投入中心事務,並協助推動歷屆的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張教授非常懷念曹先生,兩人在海洋史研究中心期間無所不談,常常一起論學。他指出,海洋史專題研究中心過去跟國外學界之間有很多合作關係,有些是曹老師拓展的,他在日本與荷蘭萊頓大學那邊都有很多朋友。除此之外,張教授自己也與美國、英國、法國學界友人有一些合作交流。而吳劍雄教授生前,也與澳洲學者一起進行華僑研究方面的合作交流。其後,朱德蘭、劉序楓、湯熙勇教授等日本九州大學與關西大學畢業的學者,回國後也陸續加入了海洋史專題研究中心,並一起推動與日本學界交流的海洋史研究。最近更有受到曹老師啟發的年輕學者鄭維中等人接棒,繼續推動臺灣的海洋史研究。
張教授也談到了他對於臺灣海洋史研究的看法。他注意到臺灣的海洋史研究是由曹永和老師所開創,而曹老師本身又受到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研究傳統的影響甚深。張教授說,小葉田淳 [22]、岩生成一 [23] 等日本學界重要的南洋史研究開創者,在臺灣大概待了八年左右,雖然時間不長,卻開創了日本學界的海洋史研究傳統。這個成就不但被日本新一代學者承繼下去,而且也影響了當年在帝大旁聽與戰後從學於岩生成一的曹永和老師。張教授認為那段時間的輝煌成就,日本國策是很重要的因素。當時那是由國家所主導的計畫,不像海洋史專題研究中心是起於張彬村教授與吳劍雄教授等個人的發想。不過,張教授也說,好的東西不一定砸錢就能製造出來,日本的國策雖然提供了資源與基地,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些學者畢生貢獻於學術研究,他們都有使命感。
張教授認為,如果要將臺灣的海洋史研究提升到那樣的層次,國家資源的挹注是必然的。再者就是學術研究不能炒短線,炒短線不會有結果。張教授提到過去求學期間,碩、博士指導教授屈萬里、牟復禮都曾經鼓勵他,除了一些工作上被要求處理的題目之外,應該再追求有深度且能夠長期討論的議題。開始工作以後,吳大猷、李遠哲院長也都很鼓勵院內的同仁做永續性的研究。但現在臺灣這樣的學術環境,很難不炒短線,為了生存,常常就是不停地申請計畫、填表格、發表文章,有時讓人覺得備受干擾。張彬村老師勉勵新進研究者在應付這些問題之餘,仍要不斷與自己對話,追尋自己所感興趣的議題,不然就很容易在這些繁瑣的事務中失去研究的樂趣。

經濟史生涯的回顧與展望
最後,我們也好奇地請問張教授,對於經濟學與經濟史的關聯與區別,他的看法如何。張教授說當初剛到中研院時,陳昭南所長一直強調跨學科研究 (interdiscipline research),這個想法讓他深受其惠。過去他有很多經濟學背景的同事,大家在遭遇問題時可以互相幫助,但他也承認現在沒有這個環境了。另一方面,他認為經濟學與經濟史兩者的定位不太一樣,經濟學首先關注的是經濟性的問題,像是供需、消費、生產、成長等,以及資源如何得到最有效率與最適的配置。其次,則是如何平均分配資源,使分配更加公平。而經濟學者在看待歷史的時候,是把歷史當作已經做完的實驗,因為有很多課題他們沒辦法實際做實驗,只好盡量重建過去的歷史事實,然後當作一個實驗來討論。他們著重的是歷史事件能不能支持他們提出的模式,因此不是真正在做「經濟史」的研究。
但經濟史的研究方法則不同。經濟史學者有兩個工作,一個是重建歷史上的經濟活動,第二個就是詮釋這些活動、事件。這兩個工作基本上是相輔相成的。從事這樣的研究時,如果沒有一些觀念基礎或理論框架,就會無法順利地、有效地組織這些事件,並加以詮釋。經濟史著重的是回到過去,且了解過去。經濟史學者要關注的並不是單一的事件,或者是個人。雖然這是構成經濟史研究的基礎,但是最終目的仍是了解長時期的趨勢或週期,從這個趨勢或週期中,找出一些交互作用的因素。
經濟學者與歷史學者所做的經濟史研究,是否有差別?對於這個問題,張彬村教授認為,如果是最上乘的作品,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一般的狀況下,兩者進行的經濟史研究,通常會顯露出各自不同的議題定位。經濟學家會依賴歷史學家重建歷史的功夫,他們要研究的東西不需要牽扯太多歷史因素,所需要的是其中的數據或事件,可以用來支持他所提出的模式或討論;而使用的數據、事件,會緊密地與經濟概念連結。歷史學者的經濟史研究呈現的則是回到歷史的具體情境,然後試著根據經濟學上的理論框架,重建、組織與解釋一些個別的經濟事件與現象。
關於訓練與養成這個部分,張彬村老師不認為歷史背景的經濟史學者一定要有完備的經濟學背景知識,頂多對總體經濟學或個體經濟學有基礎的認識即可。他根據自己的經驗給予的建議是,在研究的過程中面臨困難或問題時,自己可以找尋工具,特別是現在網路上很多資源容易取得,要自修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接著,我們請張教授比較臺灣與西方學界在東亞經濟史的研究有何特點?是否有一些必須克服的盲點?關於這個部分,張教授舉了美國與中國大陸為例,美國、中國大陸分別在 1960 年代與近期,因為國策而發展出一些大型研究,各自都有不錯的成果。但臺灣沒有這樣的資源,大家也都是由個人興趣出發,鮮少像美國、中國大陸、日本那樣由國家主導研究。再者,張教授覺得臺灣是個小國家,可能比較適合小而美的研究。張教授認為,有些璀璨的成果不是物質就可以製造出來的,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從來就不是什麽大型計畫的產物,而是他個人的發想。
最後,張教授也談到對未來明清史以及經濟史研究的期許。他指出近年年輕學者的求職日益困難,這是受到少子化、線上學習等趨勢的影響,大學院校師資的需求逐年減少。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主要集中於學術研究、生產知識,能夠來到這邊都是極幸運的,他希望大家可以真正樂於自己的研究。他勉勵年輕的學者除了基本的生存技能之外,能夠花些時間來探尋一些普世性的大問題,不要只鑽研零碎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大概很難有個確切的答案,但在探尋的過程中常常能夠有意外的發現。
張教授回顧學術研究的生涯,說自己其實是靠著好奇心跟一股傻勁走入這個行當。他認為學者沒有好奇心的話,大概很難持續從事學術研究。雖然像工廠一樣按件、逐件地做學術研究也能持續做一輩子,但這樣太可惜了。對他來說,學術研究的滿足感是在過程中體現的,當眼界不斷擴大,就更能體會追求知識的滿足。他覺得學者這一行是「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的比較,是一種自我比較的過程。因為自己的研究課題只有自己最了解、最在行,外在的評價、獎項什麽,那只是一種遊戲規則,有時也是從事研究時的雜音。唯有減少雜音,不斷深化、廣拓自己所追求、探索的課題,人生才會變得豐富。
[1]屈萬里教授 (1907-1979),研究專長為《詩經》、《尚書》等上古典籍,曾任中央圖書館臺灣辦事處主任、中央圖書館館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1972 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2]張教授的碩士論文為〈易傳與莊子的現實世界觀與理想世界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 年。
[3]不過,其後在西方經濟史與經濟學理論的研習對照下,對此種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史觀有所保留
[4]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1954 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畢業兩年後至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任教,1980 年起與 Denis C. Twitchett 等人合作編寫「劍橋中國史」系列。
[5]這篇文章後來發表於《食貨月刊》14 卷 2 期(1984 年 5 月),頁 95-107。
[6]Denis C. Twitchett (1925-2006),中國經濟史學者,「劍橋中國史」系列叢書的主編之一。
[7]William Baumol (1922-),美國知名經濟學家,歷任普林斯頓大學與紐約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8]Arthur Lewis (1915-1991),聖露西亞經濟學家,197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經提出經濟發展領域著名的「路易斯模型理論」。
[9]傅衣凌 (1911-1988),中國知名的明清經濟史學家,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10]張彬村教授的博士論文本來打算延續之前有關明清地權制度演變的研究,但傅衣凌教授告訴他,當時中國學界正在發掘與收集明清的土地契約文書等史料,由於無法實際使用這些新的史料,張教授在美國完成的博士論文可能很快就會被挑戰,因此放棄了這個主題的研究。
[11]Chinese Maritime Trade: The Case of 16th century Fu-chien, PhD The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3.
[12]康樂 (1950-2007),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1981 年開始主編「新橋譯叢」的西洋名著翻譯工作。1980 年臺灣的知識環境剛從封閉漸漸開放,該譯叢對於 1980 年代以來臺灣學界的學術新知移植與認識有很大的貢獻。
[13]夏伯嘉 (1955-),耶魯大學博士,西洋經濟史學者,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通信研究員。
[14]C. M. Cipolla 著,張彬村編譯,《歐洲經濟史:工業革命篇》(臺北:允晨,1984 年)。C. M. Cipolla 著,張彬村、林灑華譯,《歐洲經濟史:工業社會的興起(I、II)》(臺北:允晨,1985 年)。此翻譯計畫後來由允晨出版社轉移至遠流出版社再版,即新橋譯叢。
[15]陳昭南 (1936-2008),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國際金融與貨幣史學者,1976 年籌設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後改名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任籌備處主任及所長到 1987 年。 1990 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6]張教授有一篇文章,直接論及西方工業革命與明清經濟史的比較。張彬村,〈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鄭和下西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頁 24-29。
[17]張彬村,〈明清時期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 的問題〉,《新史學》10 卷 2 期(1999 年 6 月),頁 29-76;張彬村,〈唐代的陪門財〉,《燕京學報(新)》,2003 年第 14 輯,頁 19-40。
[18]吳健雄 (1940-1992),匹茲堡大學歷史學博士,著有《海外移民與華人社會》、《美國排華運動與排華法案之成立》等中國海洋史研究作品。
[19]張教授也提到他與陳所長曾經以英文發表有關明代紙幣崩潰問題的研究,見 Pin-Tsun Chang, Chau-nan Chen, Shikuan Chen,“The Sung and Ming Paper Monies:Currency Competition and Currency Bubble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Vol.17, No. 2(1995), pp. 273-288。此文是兩人合作研究十年的成果。陳所長生前曾經希望將其翻譯成中文以饗中文學界讀者,因此張教授最近特別以中文翻譯改寫,將於近期內發表。
[20]曹永和 (1920-2014),1939 年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畢業,1947-1985 年任職於臺灣大學圖書館,業餘從事海洋史與臺灣史研究,並和日本與西方學者密切交流。1984 年獲得正式研究員與教授身分,更密集地貢獻於臺灣史與海洋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學術生平參見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年)。
[21]王世慶 (1928-2011),長期在省文獻會等機構擔任文獻編纂工作,業餘從事臺灣歷史研究工作。1993 年獲聘為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1996 年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亦為臺灣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先驅與教學者。
[22]小葉田淳 (1905-2001),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博士,曾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講師、國立臺灣大學副教授、京都帝國大學名譽教授,研究專長為日本及東南亞貿易史、日本礦業史、貨幣史、交通史。
[23]岩生成一 (1900-1988),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學士,曾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講師、國立臺灣大學副教授、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專長為近代日本對外交涉史、日本荷蘭關係。
| 撰寫人: | 主訪人:林文凱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記錄:許雅玲(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