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强烈地感受到不同区域之间在自然环境、居住人口及其生产方式、居住方式、文化形态(特别是方言和习俗)等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且不说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较大距离的区域差异(如大区之间与省际的差异),即便是在乡村旅行,我们也会发现,每隔二三十公里,生活方式、自然条件、聚落类 型乃至田野形象和色彩全都会发生变化。每个村庄、每个乡镇、每个县都有属于自己的地域特征。这些地域特性早已渗透在平民百姓的心坎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 分。虽然随着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地区特性似乎正在逐渐消失,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个地区发生的变化,都有别于邻近的其他地区,或者变化 的方式各具特点,从而造成了界线分明的新差异。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 开始思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问题。首先,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是通过观察、感知而得以描述、展示并赋予其意义的,这种可以通过观察而认 知并加以描述、展示的区域差异,可以概括为“景观多样性”,它主要包括自然景观的多样性、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以及景观认知与意义的多样性。而不同区域在景观方面的差异(景观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这不仅是因为“今日的”景观乃是历史时期的遗存与积淀,更由于景观是人与环境的统一体,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本身就蕴含着对历史过程的记忆与解释。因 此,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乃至政治模式、文化形态诸方面也会有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是造就“今日的”景观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这些差异,可概括为“历史进程与道路的多样性”,它主要表现在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历史发展诸要素的区域差异三个方面;而其中 最为关键的是“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即: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条单一的轨迹,不同的区域都可能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不同区域在历史发展的出发点、走 向与所经历的主要阶段等方面,都可能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即其所走过的道路根本不同,而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曲折或分歧。而不同区域所走过的、有着根本性不同 的道路,则可称为“区域性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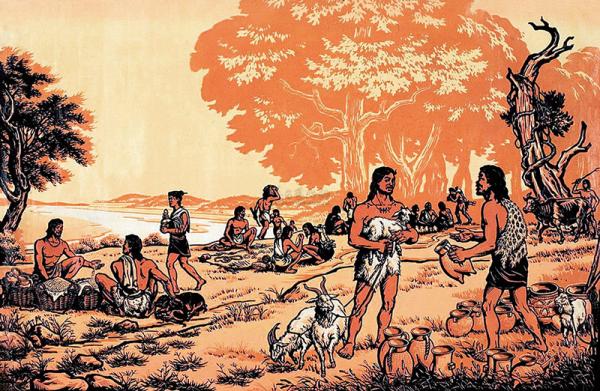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吗?
迄今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阐释,大抵都假定中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均基本遵循一个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走过一个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这主要有两种阐释路径:一是以社会形态演进为核心线索的阐释体系, 强调人类历史均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其初级阶段)的演化,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线索自亦如 此,中国各个地区亦概莫能外。这种思想方法假定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是统一的,并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作为“普遍规律”运用于中国及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分析中。 显然,这种阐释是建立在不完全归纳和未经证实的材料基础之上的,远远脱离了历史事实;其关于中国各地区历史发展走向的断言,更主要是出于先验的预设,主要 是靠预设和臆测构拟历史,先定下框框,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中。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一阐释体系已失去了其赖以成立的方法论基础,实际上已 被“束之高阁”。
认为中国各地区均走过相同或相似历史道路、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与文化一致性的第二种阐释体系,则以“朝代更替”为核心线索, 认为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变动,均与王朝的更替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假定各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与王朝的兴衰更替同步的,因而也 就是相对一致的。这样,有关各地区的历史发展,就主要被叙述为王朝武力向各地区的扩张与征服,人口迁移带来了各地区的经济开发,然后是王朝制度在各地区的 推行以及所谓“教化”的展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发展与中国文化的一致性或统一性得到贯彻与展开,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遂得以纳入中国历 史发展的总体轨道中。“王朝更替”的叙述与阐释模式,掩盖了不同区域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进程简单化了,因此已受到广泛的 质疑,在很多领域实际上已经被摈弃了。

草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跟山区的发展道路会是一样的吗?
区域多样性的视角引导我努力突破这种单线式的思考方式, 更着意于探究不同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纳入中华帝国体制内的根本性需求,分析这些区域自身的历史轨迹,理解其区域特性的形成及其与大一统 帝国的一致性之间的差别与关联。质言之,即探寻不同区域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考察这种区域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近年来 从事中古时期南方史地研究的基础上,我尝试摸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南方脉络”,试图将汉人群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区分为“中原道路”与“南方道路”;进而认识 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新疆(西域)地区、青藏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均有别于中原和南方地区,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当可视为与“中原道路”、“南方道路”并 存的区域性历史发展道路;使用中原王朝的更替以及中原王朝对这些民族地区的征服与控制,作为建构这些地区历史、文化阐释体系的基本框架,不过是“大中华主 义”(又以“大汉族主义”为其核心)观念下历史阐释体系的组成部分,反映的仍然是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这样,我即初步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中原道路、南方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与沙漠绿洲道路等五种区域性历史发展基本道路的看法。不仅如此。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有三个根源:一是自然的多样性,二是人群的多样性,三是人群对多样性自然的适应、应对与抉择的多样性。因此,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是绝对的,而一致性则是相对的。
区 域多样性的思想方法,不仅使我更着意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多元构成,强调中华帝国与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还促使我以一种更为宏大、包容的态度,去对待在宏 大的中国历史叙述中未能占据“一席之地”的各种区域性的历史与文化,尊重诸种形式的区域特性及其文化表现形态,承认并致力于揭示其在人类文明和中国历史发 展中的价值与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我将关注的目光从巍峨的殿堂转移到乡村的庙宇、集市,从“核心”转移到“边缘”,从“正统”转移到“异端”——但 这不是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改变,因为在“多样性”的思想方法中,朝廷的殿堂与乡村的庙宇、核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 同等意义的存在,是并列共存的关系,并无上、下或重要、次要之别。
核心与边缘: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与“内地的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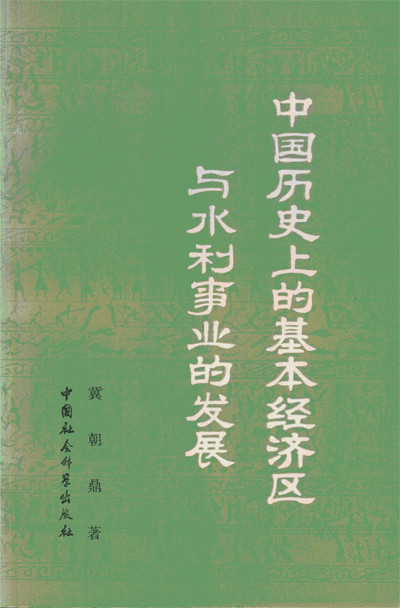
1935 年,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以高度的概括力,提出了“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 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他所界定的“基本经济区”有两层含义:第一,控制它就可以控制全国。第 二,在分裂、动乱时期,它是各政治集团奋力争夺的对象;而在统一时期,则是统治者特别重视的地区,统治者给予它许多优惠条件以确保其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 地位。冀朝鼎运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论证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
冀 朝鼎所说的“基本经济区”,主要是在农耕经济意义上,认为农耕经济发达之区即可成为基本经济区,并进而认为控制此种农耕经济发达之区,即可控制全国。事实 上,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达的农耕经济区不仅不“必然”成为据以控制全国的“基本经济区”,恰恰相反,在很多时候却“更可能”成为被侵掠、受控制的对 象。质言之,将农耕经济发达之区认定为据之即可控制全国的“基本经济区”,至少是不全面的。同时,“经济资源”与“统治资源”并不是一回事,农业经济之发 达只是提供了人力、粮食等经济资源,这些资源只有转化成可供国家支配的军兵、役夫与赋税之后,才能成为可以用来争夺天下、控制全国的“统治资源”;在农业 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国家政权是否可以有效地“动员”、调配某一地区的经济潜力,才是这一地区能否成为国家可以依赖的“基本经济区”的关 键。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模糊了“经济资源”与“统治资源”之间的差别,将经济较发达之区相对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直接等同于王朝国 家可以有效支配、利用的军事、财政资源;以此为基础,将“经济较发达”作为“基本经济区”的充分与必要条件。
那么,从王朝国家统治全国的角度看,怎样的地区是受到历代王朝特别重视、据之即足以统一天下控制全国的地区呢?换 言之,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可能成为这样的特殊地区呢?显然,受到历代王朝特别重视、据之即足以控制全国的特殊地区,并不一定就是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地 区,而主要是可以提供王朝统治所依靠的兵甲(军兵)、衣食(财赋)、人才(文武官员)以及合法性的地区,即兵甲所出、财赋所聚、人才所萃、正统所寄的地 区。这样的地区并不适宜单纯地使用经济区、政治区或文化区之类的概念来界定,姑且称之为王朝统治的“核心区”。换言之,核心区集中了王朝统治最重要的武力、财富、人才与文化资源,只有控制了这样的地区,才能控制并进而统一全国。在 核心区所应具备的四个要素中,兵甲与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只有拥有此二者,王朝才有可能建立起军队和官僚系统。由于财赋可以依靠武力和官僚征敛的手段获 致,所以财赋系统在帝国统治体系中,处于一种从属于武力和官僚系统的地位。因此,核心区作为“财赋所聚”之地,并不一定表现为此一核心区出产大量的财赋, 更重要的乃是全国各地的大量财赋集中于此。“正统之所寄”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权力”,决定着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在历代王朝更替过程中,“正统”乃是关乎 王朝命运的大问题,但在本质上,它主要是统治者对权力来源的阐释,是文化“建构”的结果。
重新界定了“核心区”的概念之后,我进而去思考,历代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在哪里?并对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核心区之所在及其转移形成了一个概括性认识:
(1)秦、西汉王朝的核心区,乃在关中及其西北边的北地等六郡,即今陕西中、西部地区;东汉帝国的核心区,则大致相当于今河南中部、山西与河北南部的黄河中下游两岸地,“三河”又是其最基本的核心区。
(2)十六国以迄隋、唐前期的核心区,当在长安、晋阳、洛阳为中心所组成的三角区域,只有兼跨关陇、河东与河洛的政权,才能统一北方,并进而统一全国。
(3)东晋南朝及南唐、南宋等立国东南的政权,核心区均在以广陵、合肥、寿春、淮阴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及以建康、京口、芜湖为中心的宁镇地区,即长江下游两岸地,而非在向以为经济发达之江南腹地。
(4) 晚唐五代时期,河北、河东、河南三大军事集团渐次合流,逐步形成以汴梁、洛阳、太原、广晋(大名)为中心的核心区;北宋时期,河东(太原)退出核心区范 畴,核心区在以开封、洛阳、应天、大名等四京为中心构成的区域,即今河南中部、北部及河北南部的黄河两岸地。
(5) 契丹(辽)帝国的核心区一直在其上京临潢府,即今大兴安岭中段以东的草原地带;金初的核心区在被称为“内地”的上京路(今黑龙江南境),海陵王迁都燕京之 后,即以燕地(今京津地区、河北北部)作为帝国之根本;蒙元帝国也经历了一个核心区由草原向汉地逐步转移的过程:大蒙古国时代的核心区当在斡难-怯绿涟地 区及鄂尔浑河流域,元朝建立后,以大都路、上都路为中心的腹里北部即今京津地区、河北、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地区乃是帝国最重要的核心区。
(6) 明初的核心区在以南京、中都为中心的畿内(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二省),永乐以后,逐步转移到以北京为中心的幽燕地区(北直隶,今京、津、河北地区);清 王朝则在明朝核心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扩大,包括了邻近草原地带的热河(今承德)与满洲发祥地的盛京(今沈阳)地区。
姑且不论立国东南的六朝、南唐、南宋政权以及主要表现为草原帝国的契丹(辽朝),综括上述历代王朝统治之核心区的转移,又可区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以迄于唐前期,各王朝的核心区虽历有变化,但基本稳定在关中、河洛与河东(太原)地区,长安、洛阳、晋阳乃是构成其核心区的三个基本点,不同朝代在此三个基本点之间有所变动;
第二阶段,自中晚唐五代至北宋,政治军事之重心渐次向东移动,后来逐步稳定在以开封、洛阳、大名、应天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两岸地区;
第三阶段,金元明清时期,虽然情势更为纷杂,但总的说来,四个王朝的核心区主要是在以今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北部地区。显然,中国历代王朝核心区的转移表现出由西北向东北、由关陇向幽燕移动的轨迹,蒙元、满清二代的核心区更是跨越长城,兼括草原与农耕地带,充分说明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并不取决于农耕经济的发达与否。至于是哪些因素影响或制约了历代王朝核心区的变动,以及这些变动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则尚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从 “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出发,可以进一步推衍“核心区”的内涵:在不同时期的中华帝国疆域内,均存在着不同层级的“核心区”,即不仅有统一帝国全国意义上的 “核心区”与南北分裂格局下南北政权各自的“核心区”,还有不同层级区域下的“核心区”,如施坚雅所划分的中华帝国晚期九大区域各自的核心区,各层级行政 区(州、道、路、省等高层政区,郡、府、州等中层政区,以及县级政区)内也都拥有自己的核心区。这就构成了不同层级的核心区,即全国意义上的核心区、南北 政权的核心区、大区的核心区、高层政区(州、道、路、省等)的核心区、中层政区(郡、府、州)的核心区以及县域范围内的核心区。在不同层级的区域范围内, 都会存在受到不同层级的政权(官府)特别重视的地区,它集中了其统辖区域范围内最重要的财赋、武力、人才等资源,并拥有来自王朝所授予的治理其统辖区域的 合法性(一般为军政中心所在);控制此种核心区,即足以控制其所得授权治理的全部区域。
与“核心区”对应的概念,是“边缘区”。“内地的边缘”这个概念的提出与思考,源自田野。2003 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我们在鄂西北郧西县作了一段时间的田野考察,这一地区在地理、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边缘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地处 鄂、陕、豫三省交界,地方偏僻,山高林密,因此自古以来官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就比较薄弱,民风亦强悍尚武。当地民户多为移民,来源纷杂,土著无几。民众生 计依赖种植农业,而生态环境恶劣,童山荒岭,崇山邃谷,可耕地资源十分有限;虽辛勤劳作,仍挣扎在温饱线上,民众生计颇为不易。境内风俗虽有千差万别,然 其共同特征则是“信鬼尚巫”,“事淫末,溺巫师”,原始巫术与民间秘密宗教较为盛行。考察结束后,经过多次研讨,我在调查报告中,初步提出了“内地的边 缘”概念,又进而结合许倬云先生有关中华帝国体系结构的论述,将“内地的边缘”界定为“处于中华帝国疆域内部、但却并未真正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或国家控 制相对薄弱的区域”,认为在“内地的边缘”区域,国家权力相对缺失,地方社会秩序之建立多有赖于各种地方势力,遂形成政治控制方式的多元化;其耕地资源相 对匮乏,山林、矿产资源丰富,民众生计多式多种多样;人口来源复杂多样,多为社会体系之外的“边缘人群”,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强烈的“边缘性”;在文化方 面,异端信仰、民间秘密宗教等非正统意识形态有较大影响。“内地的边缘”区域往往是传统中国诸种社会动乱的策源地,也可能孕育某些新生力量和新因素。

在“内地的边缘”区域,国家权力相对缺失,民众生计方式多样,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强烈的“边缘性”,非正统意识形态影响较大。
实 际上,对“边缘”(边缘区、边缘人群、边缘社会与边缘文化)的关注是我这些年从事田野与研究工作最主要的倾向之一,也可以说是具有个人特点的研究路径。除 了对于边缘人群、边缘社会与文化的“同情”之外,还因为我希望在“边缘”中能看到或“找到”新因素与新的社会群体的孕育与形成的迹象或可能。所以,在田野 工作中,我强调“倾听村落边缘的微弱声音”,用“心”去理解社会边缘人群的话语;在文献分析与运用中,则试图从官府、文人等主流人群留下来的文献中,去挖 掘弱势的边缘群体留下来的零星记录。比如白莲教的大部分教徒都是船夫、佣工、手艺人、货郎之类的边缘群体,这些人,在正常情况下,本来是没有机会发出并留 下声音的,幸运的是(对我们来说),他们起事被捕之后留下了口供。这些供单,前些年整理白莲教起义资料时,渐次公布出来。离开农民起义和白莲教研究的路 径,把这些材料放回到地方社会中,这些供单,就是非常好的边缘群体的声音。我们试图运用这些材料,去探究传统中国秘密社会(特别是秘密宗教)这一边缘性社 会中“核心集团”的凝聚与“核心区”的形成,认为秘密社会的“核心集团”,多由社会边缘群体中的“精英”构成;其“核心区”则多处于“合法性”政治社会经 济体系的“边缘”。秘密社会的空间扩散方式,往往是从一个“合法性”社会的边缘地带,跨越其核心地带,直接进入另一个边缘区域;其“核心集团”也往往采取 “裂变”的方式,即从一个“核心集团”分出成员,到另一个边缘区域传教授徒,营构另一个核心集团。这就是所谓“边缘的核心”。
“核 心区”、“内地的边缘”、“边缘的核心”三个概念及其研究理路,是我试图运用空间观念去分析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与结构的第二组概念,其理论根基是地理学的 “核心-边缘”理论,但我作了一些推衍或者说是“发展”,特别是边缘区边缘群体的“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的形成,我还没有能做出较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它实际 上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我还没有充分的能力把握。

2014-11-12 18:02 来自 私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