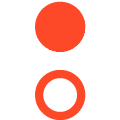作者:王若磊,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政法论坛》《法学》《环球法律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两部;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与国家治理理论。若您阅读后有所收获,欢迎关注公众号“雅理读书”(yalipub)
转眼21世纪就过了20年,第三个十年的第一场大雪都已经化了。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而言,这二十年是真正开始阅读思考的二十年,是“立人”的二十年。时至年末,偶见一两书单,远没有往年的景象,也许大家难有读书的心境和时间了。然而今年,或是因为研究的“深入-转型”,或是因为工作数年来第一次有了“相对”独立的办公空间,估计是近来读书最多的一年,自感受益颇大、进步不少。侧目看到旁边满桌杂乱堆砌的书,回味这一年印象颇深的一些,也算给自己一个纪念。有天脑中突然划过“小时代”这个电影,发现畅销作家真挺会选词与概括的。这个时代,可能没多少人再思考一些根本的大问题,我们看到几乎没人再关注“时代的精神状况”,很少再追问“大转型与大分流”的根源,好像一切都那么琐碎、具体、功利、技术化,无关痛痒。即便西方那些研究“社会平等”的哲学家们也是如此,学院派十足,几乎不直面时代的重大问题。或许我们没能力解决这些大问题,不过阅读和思考,却让我们有可能超越自己的局限,寻找些许意义。这几年支配我思考的,实际上是关于“大分流”的话题,当然,前后又有延伸:“历史上中国为何能早早在如此之大的疆域建立起一个相对有效治理的国家,两千年延绵不绝、高度文明且逻辑自成一体?”“但为什么后来中国落后了?为何传统中国长期停滞,未能自我超越?西方为什么能突然超过中国,出现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中西为何出现‘大分流’?”“近几十年中国又为什么能够迎头赶上?当代中国缘何兴起?”而这样的变迁背后,国家治理的模式与制度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两三年博士、硕士的课程,其实一直围绕“国家兴衰、社会平等与制度正义”这一主题进行讲授。当今年开始着手写作书稿时,更精细地读了一些论著,并不断延伸扩展。几年的阅读经历让我感到,当知识和视野从政治法律不断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从思想进入制度再到背后的深层历史社会结构,从当下回到过往,特别是西方回到中国,从一国、两国的简单对比,回到诸文明演进自身的逻辑脉络中时,似乎认识也逐渐成熟、不断深刻,以前的一些断论开始显得草率、单薄;每阅读一个新的学科、探索一个新的领域,就像打开一扇新的窗户。(美)彭慕兰:《大分流》,又名《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江苏出版社人民2004年版
“大分流”这一范式得名于彭慕兰《大分流》一书,他非常具有洞见地将加州学派关于国家间特别是中国与西欧近代经济变迁的比较研究提炼为“大分流”这一命题。不过不同于传统观点,一方面彭慕兰认为大分流出现的很晚,大约在1800年甚至1850年之后,而之前至少江南与西欧在经济领域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有斯密型增长,但也都未能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另一方面,在他看来是新大陆的发现和煤矿位置优越这类外在、偶然的因素造成了大分流,这些能源、资源物质因素使西欧突破了生态人口制约进而催生工业革命。这样的观点自然引发诸多争议。(荷兰)皮尔·弗里斯:《国家、经济与大分流》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在我看来王国斌2018年底出版的合著《大分流之外》(与罗森塔尔)或许更为客观持中。这部新书秉承了其更早作品《转变的中国》中的观点,进入了经济变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加州学派的一员,王国斌同样认为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内部也有变迁,经济有低速增长,但1800年的分流可往前追溯到1500年甚至更早,或许1100年左右开始的西欧国家间竞争就已为新体制的形成、海外资源的寻求和技术的变革埋下了种子,孕育了大分流。18年底翻译出版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尝试从另一角度冲击旧有观念,弗里斯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指出造成分流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传统中国政府太过强大,反而是相对于英国的现代政府,当时中国还是传统国家,羸弱的国家能力和低效的财政体制根本无力支持经济发展、有效组织市场。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
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
中华书局2010年版
当然,客观地分析“大分流”的话题,还需回到对传统中国真实的经济社会状况之上,也就自然要进入中国经济史特别是宋及明清经济史的研究。18年底万志英的新书《剑桥中国经济史》是近年难得一见的一本详尽铺陈与讨论中国古代经济的通史性作品,颇有价值,当然也延续了加州学派的乐观倾向。赵冈和陈钟毅的《中国经济制度史论》虽侧重于制度,但对经济状况和数据也有详尽展示,近路和观点也较为接近。李伯重先生多本关于阶段性、区域性经济史的作品,实际上更为细致、客观地展现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状况。比如《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详细考察了1800年前后松江地区的农业、商业、手工业、收入等状况,认为发展水平几乎与当时发达的荷兰相当,甚至更为健康。正如李先生所言,把握传统中国整体的经济状况,首先要扎实地做好一时一地的研究,才能连点成线、成面,形成整体判断。许新涤,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我觉得志在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加州学派,其实还有一个暗含的理论对手是老一辈的中国经济史学家,试图走出他们关于“传统中国停滞”或“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范式。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倒觉得老一辈学者的研究可能并不过时,反而更加扎实、更加客观、更加“中国”。最让我意外、受获颇多因而勾画满篇的著作是35年前吴承明先生和许涤新先生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系统、细致地描绘了传统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与内部变迁,同样也不回避问题,理性客观地分析了迟滞的原因。此外傅筑夫先生更早的著作《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核心也在回答这一问题。李伯重先生的导师傅衣凌先生(如《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和《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中的一些观点)远早于加州学派提出明清经济发达论,中国经济多元论和中国体制弹性论等判断,但也指出在“封建生产关系”包围下资本主义萌芽夭折了。可能如王家范先生调侃的,当代一些西方学者或许有些“饱汉不知饿汉饥”,把“萌芽”当做“大树”了。老一辈学者的严谨、扎实值得尊敬。
然而,仅仅把握经济本身并不够,如何形成如此的经济态势和状况,必须理解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要理解中国的历史模式。今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王家范先生再次印刷出版的老作《中国历史通论》,该书既有通史的气象与通透,又有细节的详尽考证,论述理性平和又不失风趣幽默,有时寥寥数语就颇有见地和启发。如今“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作品太少了。当然,回头再读一遍赵鼎新先生的小册子《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仍觉得是上乘之作,在有一定积累后理解更为深刻,历史脉络勾勒清晰,评论分析大气理性,期待《儒法国家》中文版早日问世;据说李伯重先生翻译的伊懋可的经典著作《过去中国的模式》也待出版。何怀宏老师的新版旧作《选举社会》是以“选举社会”提炼秦汉之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样态,侧重社会平等的面向。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阎步克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波峰与波谷》则是更为专业的历史作品,但也蕴含了历史哲学和政治制度的关怀、视野与洞见,分别以“士”与“制度和势力变迁”为主线探讨魏晋之前中国的历史常态。钱穆先生《国史新论》不同于《国史大纲》和《历代政治得失》的写法,跳出朝代探讨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模式演化的特征,以深厚的文化情怀和民族自尊反对诸多成见,以士人政府、平民政治、皇权相权划分、责任政治等维度呼唤对中国传统政治的重新理解和与再认识。不少观点虽不赞同,但却引人一读再读。苏力的《大国宪制》也是一本试图“回到中国历史本身”内在地理解其“建构逻辑”的著作。正如王人博先生在《业务者说》中所言,理解中国,先要“转身回去”,看中国历史是如何一路走来的。苏力较彻底地运用了这一视角与方法,一个法学家对于历史做出这般努力和研究令人敬佩,观点也一如既往的不同常见;不过开句玩笑话,文中感叹号太多啦,估计一些论证和推测历史学家们或会提出商榷。更为宏大的通史类著作这几年也出版多部,颇受追捧的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师生二人的《中国史》相继集结出版,有不少有价值的论述和洞见,但可能是由于关注点和兴趣点的原因,总觉论述显得有些疏松、不够集中,写法也相对传统。同辈青年学者施展的理论雄心令人钦佩,以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抽象能力撰写了《枢纽》这样一部佳作,试图展示中国历史的大逻辑,遗憾部分篇章有为理论而理论的嫌疑,有些地方看上去引申过多了。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在这里还要再进一步,即在理解中国历史模式的基础上,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转型”。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更新中国》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两种范式之外,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这样的历史社会学作品令我印象更为深刻,作者以社会结构的视角对法俄中三国革命背后的经济阶层因素和社会模式进行了深入比较,展示了不同结构下革命的不同走向,也重塑了对中国现代革命价值的理解。对于当代中国,周雪光和周黎安教授有不少佳作,突然翻到文一教授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但新见颇多、刀光剑影,事实上在以中国实践批判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
自己本专业的书籍就不多谈了,今年另一个巨大收获,是去了一趟印度,浏览了几本印度史和印度哲学的书,如世界历史文库中的《印度史》和汤用彤先生的《印度哲学史》,使我在中西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此次印度之行,不光在实践层面更真切地理解了“治理能力”这一概念,观念上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文明自身的演进逻辑及其复杂性。正如李普塞特所言,只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是不懂国家的人。其实,只懂两类国家同样如此,必须至少再多一个维度。否则简单的制度比较只会得出制度移植的结论,但制度作用如何发挥要面对深层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制约。如果简单移植管用的话,被英国殖民多年的印度早就成西方国家了。此处特别想引用福山关于印度的一段话,相比之前,《政治秩序的起源》里的福山已经意识到文明与历史复杂性了:“10世纪后,印度的政治历史不再是本土发展史,而是一连串外国人入侵史,先是穆斯林,后是英国人。从今以后,政治发展成为外国人如何将自己制度移植到印度土壤。他们仅取得部分成功。每个外国入侵者必须对付这同一的‘小王国’社会,四分五裂,却又紧密组织;它们不团结,所以很容易征服;它们屈服后,又很难统治。外国入侵者留下了一层层新制度和新价值,在某些方面是移风易俗的,但在另外很多方面,又没触碰内在社会秩序的一根毫毛。”当时,坐在破旧的大巴里感受拥堵颠簸的我,凝望着窗外与金碧辉煌的豪华酒店连成一片的破落贫民窟,脑海中不断闪现着看到的一张张或兴奋憧憬、或迷茫彷徨、或逆来顺受的面孔,琢磨着那几乎无解的由种姓、宗教、民族、语言、联邦制等带来的多元复杂局面,不禁感叹:其实每一个文明都有着自己的苦难,有着自己的历史包袱和复杂性,但也都坚韧的活着,在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艰难探索。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雅理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