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提出
明清时期都遇到了严重的海防问题,如明代前期和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清朝前期面对台湾郑氏政权的威胁以及晚期来自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在面对这些海防问题的时候,明清时期都绘制了一些“海防总图”,这些海防总图也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海防思想等的重要史料。以往虽然对明清海防总图有过一些研究,但基本集中于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和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这两个谱系上。由于除了这两个谱系之外,明清还存在其他众多的海防总图,因此这样的梳理并不全面,也无法反映明清海防总图的全貌,且以往对于这两个谱系的梳理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清海防总图的谱系和发展脉络进行全面梳理。现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些介绍。
较早对中国古代海防图进行梳理的是海外的研究者,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者是英国的米尔斯(J. V. Mills),主要的论文有1953年发表的《三幅中国地图》和1954年发表的《中国海岸地图》,主要对一些中国古代的海防和航海地图进行了介绍。
对海防图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则是国内学者,其中较早的就是曹婉如。其在《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郑若曾绘制的《万里海防图》有着三种版本。(1)72幅的《万里海防图》,也即嘉靖辛酉年(1561)年成书的《筹海图编》卷一中的“沿海沙山图”;《郑开阳杂著》卷一和卷二《万里海防图论》中的“万里海防图”与此图基本一致。(2)12幅的简本《万里海防图》,即《郑开阳杂著》卷八《海防一览》中的12幅地图,且认为72幅的《万里海防图》和12幅的地图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3)还有一种12幅的详本《万里海防图》,其原本已经散佚,但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徐必达识《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应是根据郑若曾的原本摹绘的,且这12幅的详本是12幅简本的底图。该文然后介绍了这三种《万里海防图》的绘制特征,如:图幅呈“一”字展开,不讲究方位的准确性,海居于地图上方而陆地在下方,且原图应当均有画方。该文最后谈及郑若曾图对明代后期海防图有着巨大的影响。
钟铁军的《明清传统沿海舆图初探》一文,虽然发表时间很晚,但成文于2009年前后,将明清海图的发展过程放置在明清海防及其政策演变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讨论,这是之前中国古代海图以及海防图研究所缺乏的。不仅如此,在曹婉如的基础上,该文列出了更多受到郑若曾《万里海防图》影响的地图。对于清代的海图,钟铁军提出,其较明代的海图主要出现了以下一些变化:表现的海域跨度更大,同时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海图;重视台湾和澎湖;受到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影响,形成了新的地图谱系,大致有《海疆洋界形势全图》系列、《七省沿海图》系列和《沿海全图》系列,约19种(幅)地图。在文后,钟铁军还分析了受到天启本《筹海图编》影响的《万里海防图》中存在的浙江台州部分地图错置的问题,且提出刻本地图也可以被转绘为绘本,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之前通常认为的是单向的,而应是双向的。
最近几年,李新贵通过4篇论文,即《明万里海防图初刻系研究》《明万里海防图之全海系探研》《明万里海防图之章潢系探研》和《明万里海防图筹海系研究》,基于地图的绘制内容以及背后所反映的海防思想将明代后期的海防总图分为四个谱系,即:
“万里海防图”初刻系,“初刻图是郑若曾、唐顺之绘制的12幅的沿海图。初刻系指包括此图在内及受其影响而摹绘的《海防一览》等。该图系有三个突出特征:突兀海中的半岛与控遏倭寇的岛;沿海、陆地的建置数量不等地标绘图上;每幅图都有不同的纵深。初刻系背后隐藏着绘图者军事协同与经济贸易相结合的海防思想”。
“明万里海防图”筹海系,“筹海图是郑若曾、胡宗宪绘制的《沿海山沙图》。筹海系包括此图及受其影响摹绘的《海不扬波》等。该图系有三个突出特征:近洋,绘制有停泊战舰的岛屿;沿海,绘制出支援海洋作战的建置与辅助作战的设施;因增添沿海设施与减少内地建置所形成较短图之纵幅,也是该图系的显著特征。筹海系背后隐藏着绘图者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协同的海防思想”,且李新贵等认为这一图系与初刻系存在巨大的差异。
“明万里海防图”全海系,“《全海图注》是山东巡抚宋应昌编绘的海防图。全海系包括此图注与受其影响而绘制的《筹海重编·万里海图》,及以后者为基础绘制的《虔台倭纂·万里海图》。该图系具有三个突出特征:营兵制的职官系统;港澳标注着停泊各种方位风向、数量不等的船只,或至周边的距离;沿海则保留着部分卫所。全海系背后隐藏着绘图者对当时海防思想的抉择”。但对于这一图系与明代其他图系之间的关系,李新贵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明万里海防图”章潢系,“章潢图是嘉靖四十一年左右章潢绘制的《万里海防图》。章潢系包括此图及受其影响所绘的崇祯元年《全边略记·海防图》、崇祯六年《地图综要·万里海防全图》、崇祯九年《皇明职方地图·万里海防图》、康熙年间《万里海防图》。该图系具有三个突出特征:图上绘制了简要的七条图注;沿海区域间有明确的分界点;海上有防御倭寇的防线。地图绘制者的绘图特征表明其绘图的目的,就是要完善明代的卫所体系;卫所体系的首要防御对象是沿海不法之民,同时还要灵活处理来华的日本人”。李新贵虽然认为这一图系应当参考了初刻系,但在文中对两者的关系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李新贵的4篇文章虽然对前人研究有着一定的突破,且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其对地图谱系的划分以及某些地图谱系的归属都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见后文分析。
王耀在《清代〈海国闻见录〉海图图系初探》一文中对其所过目的16种受到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影响的地图的谱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基本可以认定《海国闻见录》系列海图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发生了明显分化,形成了在绘画内容、文字注记等方面各具特征的三个子图系。一般而言,《四海总图》图系在亚洲大陆东部标注‘中华一统’,并在朝鲜半岛标注‘高丽’。《环海全图》图系则在清朝统治区域内增注了大量的区划名称、边疆地名,并标注‘朝鲜’;同时在卷首增加了大段的总括性文字,在《台湾图》的题记中提到‘乾隆甲午年丈量得实’。《天下总图》图系则在亚洲大陆东部示意性地绘制了几字形的黄河及长江与洞庭湖、鄱阳湖等,在朝鲜半岛标注‘高丽’;同时在卷末附注了‘东洋记’‘东南洋记’等大段文字”。
孙靖国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沿海地图研究》(12CZS075)的结项报告在尽可能全面搜集和整理明清时期各类海图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海防图、航海图、海塘图、盐场图以及江防图的发展脉络和谱系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清代晚期沿海图的转型进行了讨论,并且深入讨论了明清沿海地图上岛屿的呈现方式。由于该报告为未刊稿,因此在此对其中涉及海防图的部分进行简要介绍。报告的第一章在明代海防形势和政策的背景下对明代的海防图进行了讨论,且以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郑若曾系列地图为中心进行了研究,“考证出民国陶风楼影印的《郑开阳杂著》是清光绪、宣统时期的摹绘本,系根据康熙三十年(1691)郑若曾的五世孙郑起泓及其子郑定远刊刻之《郑开阳杂著》抄录或转抄,除少数缺失内容外,基本能反映康熙刻本原貌,而文渊阁四库本则有多处窜改”。报告的第六章则重点讨论了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系统的地图,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搜集到43种陈伦炯系统的地图,“指出‘环海全图’当为摹绘《海国闻见录》时参照了别的东半球投影地图所致”。此外,还对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的版本进行了分析,“认为此书在乾隆年间有两个刻本:乾隆九年和五十八年本,之后有四库抄本、艺海珠尘和昭代丛书本”,并对不同版本的差异进行了对比。
除了上述这些系统性的研究之外,多年来还存在一些对单幅海防总图的研究,代表性的如姜勇和孙靖国的《〈福建海防图〉初探》,提出“《福建海防图》绘制于万历二十五至三十二年之间,以描绘明廷在消弭倭患之后在福建沿海地区的山川形势和军事布防态势为主……从绘制风格与部分地物的绘制手法来看,《福建海防图》虽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中《沿海山沙图》颇有渊源,但因其系纸本彩绘而非刻版,较好地反映出作者最初所编绘舆图的原貌,可作为明代末期在海防军事战守中所使用的绘本舆图的样本”。
二、明代晚期“海防总图”的谱系
关于郑若曾的生平,尤其是其与绘制海防图和撰写《筹海图编》有关的经历,孙靖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筹海图编》是一部关于抗倭和海防的著作,内容涉及与抗倭有关的方方面面,在海防思想上强调“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全书共有地图114幅,一般采用文随图后的方式,分为《舆地全图》《沿海山沙图》《日本国图》《日本岛夷入寇之图》和《沿海郡县图》等部分,卷一即包括《舆地全图》与《沿海山沙图》,后者也就是72幅的《万里海防图》。明代后期受其影响绘制的航海总图数量众多,可以参见表1,而这一谱系,李新贵将其命名为“明万里海防图”筹海系,但命名为“郑若曾72幅《万里海防图》谱系”似乎更为明确。
可以肯定的是收录在《郑开阳杂著》卷八《海防一览》中的12幅的《万里海防图》与72幅的《万里海防图》确实存在较大的不同,大致而言:一是12幅的《万里海防图》在海域中绘制有大量岛屿,而72幅的《万里海防图》在海域中绘制的岛屿要少了很多;二是12幅的《万里海防图》在图面上绘制了更为广大的内陆地区,标绘了一些内陆地区的州县,而72幅的《万里海防图》对于陆地的描绘基本只局限于沿海地区;三是12幅的《万里海防图》在图面上方存在大量的文字注记,记述了岛屿港湾的形势以及军事价值,而72幅的《万里海防图》图面上的文字注记极少。因此,12幅的“万里海防图”谱系虽成立,但李新贵将其命名为“初刻系”,有些含义不清,“郑若曾12幅《万里海防图》谱系”这样的命名似乎更为明确一些。
李新贵认为“明万里海防图”章潢系受到12幅系统的影响,这点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其认为这一系统的起始者或者最初地图的绘制者为章潢,但章潢是《图书编》的作者,而《图书编》中大部分地图(甚至文字)都来源于之前已经出版的材料,也就是说《图书编》实际上是一部摘抄已有作品的著作,也即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是编,取左图右书之意,凡诸书有图可考者,皆汇辑而为之说……亦不及潢书之引据古今,详赅本末,虽儒生之见,持论或涉迂拘,然采摭繁富,条里分明,浩博之中,取其精粹,于博物之资、经世之用,亦未尝无百一之裨焉”。因此不能不加考订地就将章潢认为是《图书编》中“万里海防图”的作者,也不能直接将地图和相关文字所反映的海防思想认为就是章潢始创的思想。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对比图面内容,《图书编》中的22图幅的“万里海防图”显然与72幅的《万里海防图》在绘制内容上更为近似。以“杭州”附近地区为例,并没有像12幅《万里海防图》那样绘制到内陆地区的昌化、于潜等地,而与72幅的《万里海防图》近似,基本只是局限于沿海州县,较大的差异在于在杭州以南标绘了“西湖”;12幅的《万里海防图》中标注了杭州府所辖的仁和钱塘2县,但未绘制杭州城的轮廓,而在72幅的《万里海防图》中除此之外还标注了前右二卫且绘制了杭州城的轮廓,这点《图书编》“万里海防图”与72幅的《万里海防图》是一致的;《图书编》“万里海防图”未绘制出12幅《万里海防图》中杭州以东海域中的大量岛屿,而只是像72幅《万里海防图》那样标绘了少量地名和岛屿,且这些地理要素都存在于72幅的《万里海防图》上,如“鳖子门”“茶圃门”“栲门”和“火焰头”等;图中缺乏12幅《万里海防图》上的大量文字注记。因此,整体而言,该图是根据72幅《万里海防图》缩绘的。当然由于地图的图幅从72减少为22,因此随着图幅的大量减少,图面内容也进行了相应的简化,如减少了海中岛屿的标绘,陆地上的建制则主要保留了72幅《万里海防图》上的府州县和卫所,而省略了更为细致的烽堠、巡司和山隘等“不太重要”的、在军事层级上较低的地理要素。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其所绘内容并不能证明李新贵所阐述的章潢的海防思想,即“要完善明代的卫所体系”。因此,“章潢《图书编》‘万里海防图’谱系”确实存在,但其应当是72幅《万里海防图》的子类。
《虔台倭纂》“万里海图”比较特殊,由38幅图图构成,就图面内容看应当更接近于72幅的《万里海防图》,而不是像李新贵认为的是受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全海图注》的影响。如其图面上对于杭州府城的描绘近似于72幅《万里海防图》,且缺乏《全海图注》上极为有特点的江防的部分。不过,由于是缩绘,因此绘制者省略了72幅《万里海防图》上的一些内容,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少量内容,如广东的“防城营”等军事要素等,此外在图面上还增加了一些文字注记。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全海图注》,原图无图名,根据李化龙为其所作《全海图注序》中相关内容,定名为“全海图注”。序文中李华龙提到此系“大中丞宋公所辑”,曹婉如据此分析认为:“大中丞宋公”即宋应昌。该图纸本雕版墨印,1幅,纵30.6厘米,横1309.3厘米,摺叠成册,每摺宽11.4厘米。该图绘制时并无严格的固定方位,按照海洋在上,陆地在下的体例,由右向左作“一”字式展开,方向随海岸线的变化而转换。图中描绘了自广东防城营至长江口的海洋、岛屿、海岸、港湾、山川、城邑以及军事驻防情况,且还描绘了长江口至南京附近长江两岸的情况,并附有“日本岛夷入寇之图”。因此该图实际上属于“江防海防”图,但其中江防的部分要比其他江防图少很多,只是截止于南京附近的太平府,而不是九江。从绘制内容来看,与12幅和72幅的《万里海防图》谱系相比,该图更偏重于对海洋的描绘,但海中并没有绘制太多的岛屿,只是在某些岛屿附近标注有可以泊船的数量,如“常熟县”:“外浅内深”“泊南北风船三十只”等。陆地上主要标注州县、港口、巡司、把总、参将、卫所、沿岸的墩以及一些寺、亭、坡等地理要素,其中对于卫所的描绘似乎要少于“万里海防图”系统。总体而言,该图与12幅和72幅的《万里海防图》都存在较大差异,但目前尚未找到明确受其影响的其他海防总图,因此是否能构成一个谱系尚需要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大致而言,存世的明代晚期的海防总图有两个具有影响力的谱系,即郑若曾12幅《万里海防图》谱系和郑若曾72幅《万里海防图》谱系,而郑若曾72幅《万里海防图》谱系中还存在以章潢《图书编》“万里海防图”为代表的子类。
还要提及的是,明代后期的一些与海防有关的书籍中还有一些分省沿海海图,如《筹海图编》中的“广东沿海总图”“福建沿海总图”“浙江沿海总图”“南直隶沿海总图”“山东沿海总图”和“辽东沿海总图”,由此似乎也构成了一套海防总图。与这一时期其他海防总图不同,这套“沿海总图”并不呈一字型展开,每幅地图都有着大致的正方向,即除了“辽东沿海总图”为上西下东之外,其他沿海总体基本为上北下南。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各省“沿海总图”在绘制的地理要素上存在差异,如在“浙江沿海总图”“南直隶沿海总图”和“广东沿海总图”上主要绘制的是府州县的行政建筑;“福建沿海总图”除了标绘府州县外,还偏重于对卫所的描绘;“山东沿海总图”上,没有绘制山东半岛的东部,且海域所占范围有限;“辽东沿海总图”则是详细标绘了长城沿线的一些军事建置。因此,这套“沿海总图”有可能是用不同主题的政区图拼凑而成的。目前能见到的属于这一谱系的地图还有《武备志》《武备地利》和《三才图会》中的各省“沿海总图”。
明代晚期还存在一系列以“防倭”为目的的“海防总图”,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就是“日本岛夷入寇之图”。该图上东下西,日本居于地图上方,而中国大陆、朝鲜居于地图下方。从地图上方的“日本”“五岛”延伸出三条通往朝鲜和中国大陆的“总路”,即“倭寇至朝鲜辽东总路”“倭寇至直浙山东总路”和“倭寇至闽广总路”,然后从各“总路”再延伸出多条“侵扰”路线,并在地图上标明了这些路线最终“侵扰”的具体地点,如“从此入朝鲜”“从此入登莱”“从此入台州”以及“从此入琼州”。地图左上角的文字注记则说明了沿海的航程,即“沿海从南而北,自广至辽纡萦八千五百余程,径直七千二百余里,自安南至朝鲜一万二千余里”。此外,该图在明朝境内“计里画方”,按照地图左上角的图记“界内每方二百里”。
这一专门描述倭寇入侵的专题性海防简图出现在大量明代后期的书籍中,如《筹海图编》“日本岛夷入寇之图”、《万历三大征考》“日本岛夷入寇之图”、《地图综要》“日本岛夷入寇之图”、《师律》“日本岛夷入寇之图”、《海防纂要》“日本岛夷入寇之图”、《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倭夷寇道图”、《武备志》“日本入犯图”、《武备地利》“日本入犯图”、《图书编》“沿海界倭要害之地图”、《筹海重编》“日本入寇图”、《郑开阳杂著》“日本入寇图”以及《舆地图考》“海防总图”。这些书籍中的这一地图基本相同,只是除《筹海图编》《海防纂要》《武备志》之外,基本删掉了地图上的方格网,此外还有一些地图删除了左上角的图说。
此外,在《存古类函》和《武备要略》中还有“沿海防倭图”,该图海在下方,陆地在上方,绘制范围右起朝鲜,左至福州,标绘了沿岸地区的一些州县和卫所,在海中标注了少量岛屿,在地图下方标注了“倭奴”。总体而言,与《筹海图编》“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类似,这幅地图应当是一幅“防倭”的示意图。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将这幅地图与后文提及的程百二《方舆胜略》中的“海防图”进行对比的话,可以发现两者存在众多类似之处,如河流和海岸的走向,因此大致可以认为这两类地图应当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即都与《广舆图》“海运图”存在联系。当然两者也存在一些差异,如在“沿海防倭图”中,山东半岛上的登州被描绘为一个单独的岛屿,且没有使用计里画方等等。
这类“防倭”的海防总图进入清代之后就不再出现,这应当与倭寇威胁的消除有关。
三、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谱系
《海国闻见录》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八篇,即“天下沿海形势”“东洋记”“东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记”和“南澳气记”。下卷主要包括6幅地图,即“四海全图”“沿海形势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和“琼州图”。其中“沿海形势图”是一幅“海防全图”,该图与明代晚期的海防图相似,由右向左作“一”字式展开,方向随海岸线的变化而转换,绘制范围东起辽东半岛,西至防城以西的交趾界,但与明代晚期的海防总图不同,该图海在下陆在上。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地图被清代中后期大量地图所采用,有完全直接摹绘、刻印的,有对其在进行简单修订后摹绘或刻印的,也有按照需求对其进行节选或者增补后摹绘或刻印的。王耀在其研究中列出了其所过目的属于这一谱系的16种地图,并将它们分为《四海总图》图系、《环海全图》图系,以及《天下总图》图系;而孙靖国则列出了多达43种。下面即以这两者的研究为基础,结合本人的认知对这些地图进行介绍和分析。
清代中后期,尤其是后期摹绘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的绘本以及刻本地图数量众多,可将这些地图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几乎是对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地图的忠实复制,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第一幅地图“四海总图”是否被替换为“环海全图”或“天下总图”,而这也是王耀划分图系的主要依据;“琼州图”“澎湖图”“台湾图”和“台湾后山图”这4幅地图的排列顺序;以及摹绘者或者改绘者是否在地图之前、之后或者图面上增加了文字,而这些文字或来源于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或来源于其他文献。下面逐一举例说明: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四海总图”实际上是一幅东半球图,在亚洲大陆东部标注有“大清国”,将“清朝”称为“大清国”是传教士的习惯,不符合清代晚期之前中国地图的传统,因此这幅图显然应当来源于当时传教士绘制的地图。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华”一词出现很晚,因此后续的一些摹本或者改绘本,在地图上将“大清国”替换为“中华一统”,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沿海全图”,可以证明这些地图的摹绘时代应该是较晚的。此外,除了绘本之外,一些刻本书籍中也收录了这幅“四海总图”,如清杜堮(1764—1859)《石画龛论述》中收录的一幅“东半球图”、成书于道光年间的姚莹的《康輶纪行》中的“陈伦炯四海总图”等。
“环海全图”同样是一幅东半球图,就图面内容而言,与“四海总图”相比,两者在对“大清国”的描绘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四海总图”中只是简单的在“清朝”控制区域中标注了“大清国”,在西北方向上绘制了类似于《广舆图》“舆地总图”上的“沙漠”。“环海全图”上则标绘了清朝的各省。不仅如此,两者对于东亚海域中日本、琉球、台湾以及吕宋等位置的标绘也存在差异;且“环海全图”中出现了南极大陆。但需要注意的是,除此之外的欧亚非大陆,以及南亚海域中海岛的位置和名称以及文字注释,两者几乎完全一致。因此这两图之间存在明确的承袭关系。且除了单幅的绘本和刻本地图之外,一些刻本书籍中也采用了这幅地图,如上表中的《国朝柔远记》,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同治九年刻本,以及马征麟《历代地理沿革图》中的“地球上面图”。
难以准确地判断“环海全图”的改绘时间,但图面中几个重要的地理要素值得注意:第一,陈伦炯虽然长期在台湾任职,但在其《海国闻见录》的“四海总图”中,台湾依然只是被示意性的绘制,而在“环海全图”中,对台湾的描绘似乎是基于测绘的结果;第二,“清朝”范围内,除了各省之外,重点标注的区域集中在今天新疆范围内,且还有“尼布楚”“黑龙江”“推河”“毛明安”以及“翁机河”等北方地名,似乎说明改绘者重视的或者其所使用的底图应当偏重于边疆地区,因此似乎可以认为其改绘至少应当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也即清朝边疆地区受到的威胁日益严重的时期。
收录“天下总图”的地图目前只见到两幅,另一幅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沿海疆域图》,另一幅是中科院藏蔡鹤摹绘《中国沿海七省八千五百余海哩地图》。第一幅地图本人没有看到原图,但据过目者王耀的描述,这两幅地图中收录的“天下总图”基本一致。与“环海全图”类似,“天下总图”应当也是依据“四海总图”改绘的。两者除了“清朝”之外,图面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天下总图”没有绘制南极,也没有对东亚海域进行改绘,只是在“四海总图”的清朝范围内绘制了黄河、长江,并标注了一些省份名称。从《中国沿海七省八千五百余海哩地图》的图名中使用了很晚才大量用于地名图名的“中国”一词来看,该图的改绘年代应该也是较晚的。
因此,可以大致认为,几乎所有的这些摹绘本和改绘本的时间应该都是较晚的,应当至少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对于后四幅地图顺序变动的原因,目前缺乏资料无法进行深入的讨论,也许摹绘者和改绘者有着自己的出发点和认知,但也许是不经意造成的。总体来看,很多后来的摹绘本都调整了地图的顺序,将澎湖和琼州图放置在了两幅台湾图之前。
就增加的文字而言,很多摹绘本和改绘本在地图之前都增加了一段强调这幅地图海防价值的序言,在地图图面上增加了大量文字注记,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的“中华沿海总图”、周北堂绘和邵廷烈主持刻印的《七省沿海全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七省沿海全图》,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嘉庆三年(1798)的《盛朝七省沿海图》等等。就地图图面上文字注记而言,大部分与军事防御有关,其中“沿海全图”上的文字基本来自于《海国闻见录》;而“琼州图”“台湾图”“澎湖图”上的图注,其中少量抄自《海国闻见录》,大部分来源于如黄叔璥《台海使槎录》等其他材料。
第二类,则是按照需要截取了《海国闻见录》所附的6幅地图中的一部分从而形成的“新”地图,典型的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福建广东台湾沿海全图》和《浙江至奉天沿海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福建广东台湾沿海全图》,图前有一段文字,叙述了各地的水程以及海上的一些艰险。该图绘制范围右起福清县,西至与交趾的交界处,此后附有琼州图、澎湖图、台湾图以及台湾后山图。该图图面内容与《海国闻见录》“沿海全图”中相应的部分几乎完全一致。在地图的图面上以及所附“琼州图”“澎湖图”旁附有大量图记,而这些图记在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地图的大量摹本和改绘本中也都存在。
总体来看,清代中晚期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谱系地图虽然数量众多,地图之间也确实存在一些差异,但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此进一步划分谱系的意义并不太大。
四、明清时期的其他“海防总图”
明代王在晋《海防纂要》中有两幅海防图,即“广福浙直山东总图”和“山东沿海之图”。从图名来看,“广福浙直山东总图”的绘制范围应从山东直至两广,但该图绘制范围实际上从辽东的广宁至南京往南一些;而“山东沿海之图”,其绘制范围则从辽东直至广东。两图的共同特点就是,上南下北,右西左东,且虽然涵盖地域广大,但全图不成比例的突出绘制了山东半岛及其以北的部分。其中“广福浙直山东总图”只是简要绘制了沿海的府州,而“山东沿海之图”还标绘了内地的府州、辽东的府州县,以及山东半岛附近以及渤海湾中的一些岛屿。
明程百二《方舆胜略》中收录了一些地图,其中大部分抄自《广舆图》。这些地图中有一幅“海防图”,但《广舆图》中只有“海运图”而没有“海防图”,不过经过比对可以发现,这幅“海防图”实际上是《广舆图》“海运图”从兴化至朝鲜的部分,其虽然去掉了原图中绘制的海上的海运路线,但并没有完全消除“海运”的痕迹,在图面上留下了一些与海运有关的文字注记,如山东半岛东侧的“海运至此转嘴”,山东半岛南侧的“白蓬头急浪如雪,见,可避”,以及“西那”北侧的“北去海运道”等。而且作者画蛇添足地在地图右上角标注“每方百里”,可能由此希望与书中各分省图的“画方”相一致,但由于该图绘制范围要超出单一省份,因此显然这幅地图不可能是“每方百里”的。此外,明代潘光祖等辑《汇辑舆图备考》清顺治刻本中有一幅“海防图”,该图绘制范围和所标地图与《广舆图》的“海运图”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将原来的4图幅改为了5图幅,主要是将原图的后2图幅改为3图幅;且在后3图幅的海域中增加了斜向的不同于周围的海波纹的波纹线,但不知其用意为何。
清前期陈良壁《水师辑要》中的7幅分省海图,即“京东海图”“江南海图”“浙江海图”“福建海图”“粤东海图”“台湾海图”和“澎湖海图”,基本构成了从广东至北直隶的完整的海防图,图中标绘了海岸附近的府州县和卫所以及近岸的岛屿,比较特殊的就是还描绘了一些沿岸的沙洲。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套海图的绘制方式并不一致,“京东海图”的正方向大致为上西下东,“粤东海图”为海在下陆在上,而“江南海图”“浙江海图”“福建海图”为海在上陆在下,“台湾海图”标绘了海岸附近的陆上交通线以及港口的位置等,而“澎湖海图”则还在澎湖与大陆之间突出绘制了一条航海路线。
清道光二十年(1840)黄爵滋的《海防图》,该图集共3册,其中图二册,表一册,该图绘制方向为上南下北,绘有经纬线,没有采用传统海洋图不论方位一字展开的画法,其中第一册自左至右依次绘有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沿海的防御情况,而第二册则着重绘制广东沿海的自然、人文、军事布防的情况。第三册则将所绘地域范围、经纬度并图中表现府、州、县的图式符号及沿海口岸、山隘、水道、驻兵额数等一一作了说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前期黄叔璥(1680—1756)所绘“沿海岸长图”(又名“海洋图”),纸本彩绘,图幅555×1648.5厘米,图上未发现题名,收藏单位将其定名为“沿海岸长图”。该图呈“一”字型展开,陆在下海在上,描绘了中国大部分海岸线与濒临的海洋,还描绘了台湾、澎湖等沿海岛屿。图中只有极少数文字注记,如“鸡笼山”左侧“后山放洋北风至牛血坑十更”。学者根据地图前后的序文和跋文将地图的绘制者确定为黄叔璥,其为清代首任巡台御史,曾撰写过《台海使槎录》一书。
清代后期还出现了一些显示沿海形势的“要害图”,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年间卫杰编《中国海口图说》。图说分为3册,彩绘本,其中第一册为文字部分,首先是“中国海口形势总论”,然后是对从关东直至山东的北洋海口,以及从江苏至台澎的南洋海口形势的介绍,在“台澎海口形势论”之后还附有“台海土番形势论”和“台湾方言”。该册的后半部分则是“海口炮台说”,介绍了各种炮台的营建方式以及利弊。第二和第三册则是各海口的地图,在所有海口地图之前有一幅描绘了清朝控制范围的“总图”,其绘制重点集中在沿海地区,标绘了海中一些重要的岛屿和海口,且在右侧绘制了日本以及琉球。此后各图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制,对于陆地的描绘较为简单,主要标绘了海口附近的岛屿并用文字记述了海潮、沿岸的险阻、浅滩等情况。类似的还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藏清后期纸本彩绘的《海口图》、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沿海海口地舆图说》,以及大连市图书馆藏康熙年间彩绘《海口要隘水陆远近形胜全图》等。
值得注意的还有同治三年(1864)湖北官书局刻印的《南北洋合图》《南洋分图》和《北洋分图》,其中《南北洋合图》覆盖面从堪察加半岛南至印度支那半岛的整个亚洲东海岸线,包括日本及中国内地;描绘中国南、北洋海疆形势,绘制出重要的河流、国界与省界、城市、长城与柳条边墙。中国沿海标注详细,余则从略。《南洋分图》覆盖范围从江苏省北部淤黄河口南至广东省与广西分界处,由南洋大臣分管的沿海地区。除海岸、岛屿外,还包括长江中下游流域,描绘中国南洋海疆形势。《北洋分图》的覆盖范围从江苏省北部淤黄河口以北至俄罗斯希鲁河(锡林河)河口,由北洋大臣分管的沿海疆域。除海岸、岛屿外,还详细绘出东北地区各条河流与朝鲜半岛。《南洋分图》和《北洋分图》用三角山型符号表现地形,着重画出沿海及通航河流沿岸的各级政区建制城市、场、所关隘。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幅海防图虽然使用的是计里画方的方式绘制的,“每方一百里”,但从地图的形式来看,该图显然是测绘的结果,可能是受到康雍乾地图测绘的影响。这类用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海防总图在清代后期日益增多,如前文提及卫杰编《中国海口图说》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光绪年间的《大清一统海道总图》。
结语
海防总图时间上的这种分布应当与明清时期的海防状况存在密切的关系。关于明清时期的海防以及海防思想,前人研究众多,如基本可以参见《中国海防思想史》《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以及《明代海防述略》等论著。基于以往的研究,明代初年虽然也存在倭寇的袭扰,但一方面当时明朝的军事力量处于鼎盛时期,另一方面明朝在沿海建立了严密的卫所制度,倭寇的袭扰没有带来严重问题,虽然可能也绘制有一些海防总图,但没有广为流传,因此这些海防总图也就没有流传下来。而到了嘉靖时期,一方面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使得倭寇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另一方面明朝的海防系统已经衰败,无法对如此数量且大范围的倭寇袭扰进行有效的应对,造成了严重的问题,由此不仅产生了一些海防图,且还广为流传。
到了清代初期,海防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占据台湾的郑氏,但平定台湾之后,在很长时期内清朝没有面对严重的海防问题,因此这一时期虽然绘制了一些海防地图,但数量极少,而在后来具有影响力的《海国闻见录》,其作者陈伦炯与康雍时期收复和稳定台湾存在密切的联系。此后,一段时期内,并没有产生太多新的海防总图。
随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清代长期松弛的海防再次得到了重视,由此开始了各类海防总图的绘制。并且由于来自海上的威胁长期存在,因此各类海防总图的绘制也就一直延续了下来。而且,由于战争方式和武器的革命性变化,传统的海防总图逐渐不适用于新时代的需要,随之也就出现了用新的绘图方式绘制的海防总图,虽然这类地图数量有限,但这一时期可以被看成是海防总图绘制的转折时期。
需要提及的是,这一时期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谱系的地图依然被大量摹绘,甚至在清末的海防总图中占据着主导,但无论是地图上的行政建制、军事布防,还是其所蕴含海防思想都已经过时,且以战舰为代表的武器的巨大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形势的彻底变革,也使得这类地图在海防中已经失去了实际价值。那么其被大量摹绘应当有着其他目的,当然这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主题,不再赘述,但这是今后研究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2期
责编|于凌
网编|陈家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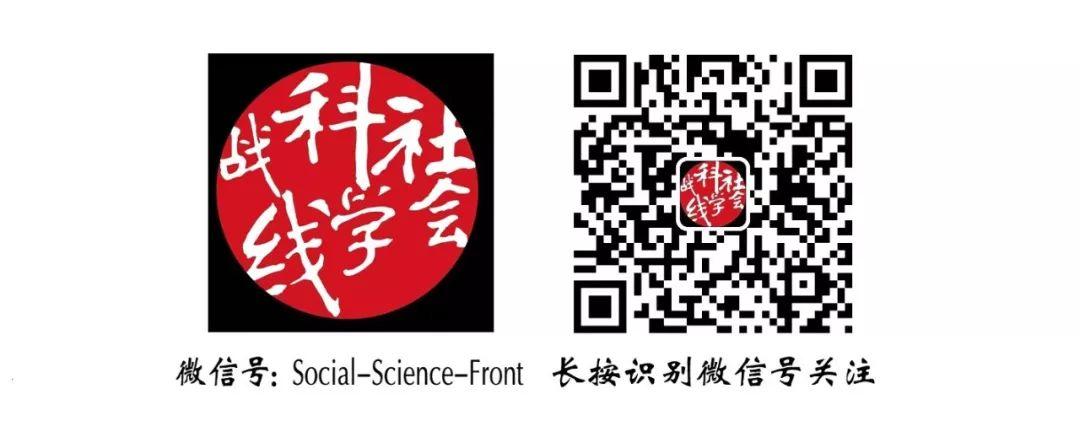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社会科学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