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宋史、西夏史。
一、宋史研究新格局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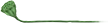
其一,2001年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学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成立。这是21世纪以来宋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家对漆侠先生的宋史研究的高度肯定。目前,该研究中心已经发展成为宋史研究最重要的资料中心,也是研究人员最多的机构。挂靠在河北大学的中国宋史研究会,编辑会刊《宋史研究通讯》,迄今刊印73期,编辑《宋史研究论丛》,已出版24辑。漆侠先生主编,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组织,国内70余位宋史专家共同撰写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由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弥补了宋史综合性研究成果缺失的遗憾。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中国宋史研究年鉴2015年》(姜锡东、王青松主编,2018年),以后还将定期出版宋史研究年鉴。
其二,宋史研究的传统重镇,河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以及杭州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进入21世纪以来依然保持了学科发展的优势。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成为宋史研究新的增长点。
其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的辽宋西夏金史研究曾在国内占有重要一席,进入21世纪以来则出现较大的起伏。
其四,在北京的高校中,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成为宋史研究重镇。
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新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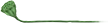
1.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出版
1999年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原文及全文检索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500巨册相比,电子版更便于文史工作者阅读和利用。
《四库全书》对于宋史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对此笔者曾撰文详述:“邓广铭先生说四库全书最有利于宋史研究。四库全书主要收录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备。汉唐典籍因多种原因到清初时流传有限,大大影响了四库的收录,明代文献因清人有偏见收录不多,如明人文集流传比宋多数倍或十数倍,而实际收录就没有宋人的多,清代只收录至乾隆以前。四库收录宋代文献约占现存宋代主要文献的六七成。现存宋人文集约800余种,四库收400余种;笔记小说今存五六百种,四库收集近400种;基本史料《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玉海》《三朝北盟汇编》、重要方志、野史、别史以及子部所收宋代类书更是遗漏不多。重要的文献只差《宋会要》。”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出版,对宋史研究来说产生了三个重要后果:其一,学者特别是“70后”青年学者利用电子版和数据库检索进行专题研究,论著数量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21世纪的宋史研究。其二,研究者依赖电子版和数据库检索,阅读文本史料的能力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由于检索材料主要服务于“问题”预设,故研究者对国史的认识已与西方汉学研究者趋同。其三,史学家以占有史料多为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通读二十四史已成为传奇神话。
2.新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宋史学界主要围绕传世文献进行研究。在考古新材料方面,“一是没有出现如先秦、秦汉、魏晋隋唐、西夏那样引起史学研究变革的新材料,如甲骨文、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也没有有待开发整理的明清档案那样一类资料”,“二是已有的考古新材料尚不足以推翻传世文献的记载”,并且“即使有新材料发现,也缺少应有的敏感度,而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1)《天圣令》的发现与价值
戴建国先生发表《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指出该藏本为佚失已久的北宋《天圣令》残本。该令典的发现,为研究唐宋社会变迁及唐制向宋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天圣令的史料价值主要有三:其一,提供宋令研究素材,有助于复原、研究唐令;其二,为研究“令”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提供可靠依据;其三,为唐宋制度史研究提供新资料。北宋《天圣令》的发现受到中日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唐宋史家的正面对话。
(2)《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整理与出版
“徐谓礼文书”是我国近代以来首次从墓葬中发现的宋代文书。文书现存15卷,约4万字。内容分为3类,即告身、敕黄与印纸,完整记录了南宋中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的历官全过程及其政务细节,是研究南宋中后期政治史及相关问题的第一手资料。2012年包伟民、郑嘉励编《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3)《宋人佚简》的出版和整理
《宋人佚简》是根据宋代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整理而成的原始文献。此书原有100卷,现存72卷,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文书内容涉及南宋初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尤以舒州酒务文书居多,是研究宋代财政史和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孙继民先生及其学生利用《宋人佚简》资料,对南宋舒州酒务公文作了专门研究,2011年出版《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4)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整理和出版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发现黑水城文献,内容涉及宋、西夏、金、元等,尤以西夏文献为著,为研究西夏历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俄藏黑水城文献共有8000多个编号,1996年以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按汉文文献、西夏文世俗文献、西夏文佛教文献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分编陆续出版。据孙继民等《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西夏刻本《文海》和《文海宝韵》背面为宋代西北边境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档案文书,共有190页,现藏俄国圣彼得堡博物馆东方学分所,其影印件收录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文书主要是宋代西北边境鄜延路(今延安地区)军政活动的原始记录和公文档案,反映了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初年西北地方军政活动情况。
3.《宋会要辑稿》的整理、点校、复原
《宋会要》是宋朝史官收集当时诏书奏章原文,先后修纂10次,成书2200卷余。它是宋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官方文献之一。《宋会要》明初已有散失,后收入永乐大典,清嘉庆年间由徐松辑出。1936年北平图书馆整理出版《宋会要辑稿》(上海大东书局,影印本),约800万字,共366卷,200册。20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机构合作,初步整理出一部电子版《宋会要辑稿》点校本。
21世纪以来,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学人经过八年的整理、校点,并经由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专家审稿、编纂,于2014年出版《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共16册。这是迄今最为完善的整理点校本。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先生领衔的“《宋会要》的复原、校勘与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组将从“新辑《宋会要》”“《宋会要》文本研究”“《宋会要》与中国古史研究”等方面开展专题研究。
4.《全宋笔记》出版及其史料价值
《全宋笔记》与《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被宋史研究学界统称为“四大全”。以戴建国教授为首的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整理出版的《全宋笔记》(10编,1998年策划,大象出版社2018年出齐,共102册),是继《全宋诗》(72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全宋词》(5册,唐圭璋编,中华书局,简体竖排本1999年,繁体竖排本2009年)、《全宋文》(360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85年策划,巴蜀书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齐)之后,宋代文献整理出版“四大全”的最后一种。2010年“《全宋笔记》的整理与研究”被列为首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都是由研究宋代文学的机构和人员进行整理与研究,而《全宋笔记》则是由以研究宋史为主的学者进行整理。在《全宋笔记》新书发布暨座谈会上,袁行霈先生为《全宋笔记》题词:“取笔记之精华,补正史之缺失。”据澎湃新闻报道:“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华瑞则认为,如果仅从补正史‘之缺’的角度衡量《全宋笔记》,未免低估了这套书的价值和意义。李教授指出,正史大体反映的是国家的、官方的立场,笔记虽然同样出自士大夫之手,但基本上可以算作半官方、反官方的书写,假如从社会角度观察宋代历史,今人对两宋会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而这正是《全宋笔记》对学界的一大贡献。”与之同理,《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对于研究宋代文学固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是不能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宋代文献“四大全”的史料价值,而是应当开阔眼界,另辟新径,从中发现和挖掘宋史研究的“新材料”。
三、宋史研究新生代培养的新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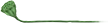
读书班、读书会之外,宋史研究生(以博士生为主)的讲习班也成为宋史研究会倡导的一种人才培育方式。讲习班始于2003年12月14日至20日,由包伟民教授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举办。其主题为“发现问题: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意义”,学员共计40余名,除浙江大学的学生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以及厦门大学等高校的近20名宋史专业研究生。此后,宋史研究会定期举办讲习班,迄今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已举办11次。每期讲习班都设有一个主题,由承办单位围绕主题邀请若干知名专家讲座,组织学生讨论。由于学生不满足于被动的听讲,因而其形式渐次改为老师讲座与学生提交论文互动相结合。讲习班的规模一般为三四十人,以博士生为主,并有少量硕士生参与。据听课研究生反馈,“与台湾、日本的宋史研究同行相比,我们的这种研习班还仅仅处在起步阶段,将来的道路还是很长的”。
四、问题研究的新突破与新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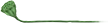
宋朝“积贫积弱”说由来已久。从南宋后期出现“民穷”“财匮”“兵弱”之说,到元明清时宋“武备不振”和“积弱”成为共识,中华民国时钱穆先生概括之为“积贫”和“积弱”,再由漆侠先生将“积贫积弱”连用以总结王安石变法的社会主因,至邓广铭先生将其写入《中国史纲要》,“积贫积弱”成为宋代历史特点的著名论断。20世纪后半叶,随着《国史大纲》《中国史纲要》作为教材被广为传习,遂使“积贫积弱”成为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确立了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的范式,宋代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落期,言其落后就是不言而喻的。
改革开放以后,“积贫”说被质疑,但是“积弱”说仍被沿用。进入21世纪,李裕民先生先后发文对“积贫积弱”说进行商榷,并得到宋史界著名学者的认同。但是这个问题仍需从对立统一的视角去看待。关于“积贫”,尽管宋朝社会生产者的依附关系较前代有较大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有较大提高、社会救济制度也难以被后世超过,但是除北宋中后期因王安石变法使得“财匮”有所舒缓外,南北宋大多数时期的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则是宋代财政史研究者的共识,所以从“财匮”之说来看宋朝的“积贫”是有充分根据的。关于“积弱”,曾有“国势弱”与“军事能力弱”二说。前者不被大多数研究者认同,是因为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超辽、西夏、金、蒙古、元。关于“军事能力弱”,宋朝战败主要发生在主动进攻战上,而防御战“宋军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因而应当改变宋人不能打仗的偏见”。尽管如此,政治腐败和战略决策的失误,“和平”对峙时(特别是南宋)常常扮演乞求、赔款、苟且、退让等屈辱的角色,防御战都是对侵略者深入国境之内的顽强抵抗,这三点既是宋代“积弱”的表现,也是宋代“积弱”成说的原因。
2.唐宋变革论的重新兴起
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09—1922年提出唐宋变革论,至今已近百年,日本、美欧学界对此已有充分讨论和基本定论。21世纪前后,国内学者关注“唐宋变革论”并引起热烈回应。国内唐宋史学界多借用“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等结论展开研究,只有少数学者从日美学界讨论的定义、范畴、范围讨论宋代问题。
这种现象为何出现?笔者曾撰文分析其原因:“民族历史地位的评价或者说对文明盛衰的评断,往往与国家的现实强盛与否分不开……20世纪早期国内学界对宋代历史的评价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国地位评判的缩影”,对于宋代文治的忽略以及特别强调“武备不振”“积弱”,这样与传统决裂的主张与认识,正是时代反思在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折射。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成为国内宋史研究热点话题的重要背景”。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将内藤湖南的这一假说视为“公理”,甚至泛化,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变革论”。面对这种现象和态势,笔者认为唐宋变革论对推动国际宋史研究确曾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继续炒冷饭、吃别人剩下的旧馍,无助于推动国内宋史研究的进步,反而“弊大于利”。
3.南宋史研究受到重视
进入21世纪以来,南宋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经统计,以何忠礼教授为首的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组织各地学者撰写、出版“南宋史研究丛书”,迄今已达80余种,加上“南宋史专辑”3期,总量在90种以上;海内外陆续出版研究著作,超过200种以上;近十余年间,学术专著出版近300种。笔者认为:“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大致与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完成的观点普遍被接受、朱熹及程朱理学的地位重新得到认可并形成研究热点等新的研究进展分不开;而刘子健先生《略论南宋地位的重要性》则直接推动了这一转变。”
4.宋代政治史研究再出发
这一提法出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其撰文指出:其一,“政治史研究的生机,来自具有活力的议题。问题意识与专题研究往往成为引领学术持续进展的生长点”;其二,“总体上讲,目前宋代政治史研究处于一个‘再出发’的阶段。其表现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即:对于‘传统领域’中一些基本问题的再认识,聚焦式议题的牵动,‘再出发’的力量积蓄”;其三,“经由对学术传统的反思、观念与方法的检讨琢磨,希望激发出具备发展潜力的话题;在辩驳切磋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富有牵动力的研究课题乃至学术方向。在此过程中,催生出聚焦面向不同、研究方式多样、组合层次不一的对话群体,形成国际性的政治史学术网络”。
在具体研究中,中国古代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中央与地方之间搜集、传递、处理信息的方式,对于政令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当代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5.经济史研究新动向与富民社会论、农商社会论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经济史研究呈现下滑趋势。尽管如此,借助当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与学术范式,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
关于宋代的土地制度、租佃制与地租形态等问题,“近一二十年来,这些议题明显受到经济学等学术范式的影响,效益、产权、风险控制与交易成本等核心概念与分析方法开始在讨论中扮演重要角色”。
宋代城市研究方面,包伟民在总结唐宋城市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宋代的城市规模、类型和特征,城市管理制度、市场、税制、市政建设、人口和文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多有新见。
“富民社会”“农商社会”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热点议题。李治安先生对此有较为深入的评价:“‘富民’‘农商’、赋役等牧民理政方式、南北整合等探索,既积极吸收‘唐宋变革’说的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该说的思维定式或理论窠臼,在诸多重要问题上做出了独特建树,有力推动了对中国古代史的科学与理性认识……可以说此举是继‘唐宋变革’说及‘宋元明过渡’说之后,中国学者争取到的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的学术话语权。”从2014年至2019年已先后在昆明、长春、北京、厦门、武汉、天津等地召开6次学术论坛,宋史学者围绕宋代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展开研讨,并与元明清史学者共同讨论其在宋以后的发展演变。
6.王安石、朱熹研究的新突破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20世纪宋史研究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对此,朱瑞熙、葛金芳、李华瑞等人都做了充分的总结。
进入21世纪以来,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在两个方面有新的突破。一是重新探讨王安石经学与新法的内在联系。过去一般认为王安石用周礼变法是托古改制,“法先王”只是变法的旗号,更有观点认为王安石经学是致乱祸国的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从宋代经学发展的路径重新审视王安石的经学,提出新法体现了北宋经学的新发展,北宋新旧党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宋学诸派学术斗争的反映。俞菁慧的《〈周礼〉“比闾什伍”与王安石保甲经制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俞菁慧、雷博的《北宋熙宁青苗借贷及其经义论辩——以王安石〈周礼〉学为线索》(《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以及刘力耘的《王安石〈尚书〉学与熙宁变法之关系考察》(《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都颇具代表性。对《三经新义》的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一个热点。二是如邓小南教授所言,真正突破的契机,可能来自于对王安石著述及其行实的重新整理。关于王安石研究,先后有王水照先生主编《王安石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教授考辨详悉的《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年)面世。
另外,关于朱熹的研究,在行实的重新整理上也有新的进展。朱熹的2000余通书信,直接反映出他毕生的政治、学术以及人际交往情况,而以往的编纂者对原始文本取舍改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初始的面貌”。通过目前一些具有“再开拓”意义的材料辑佚与研究,“可能让我们得以对于南宋中期政治文化史及朱陆关系等生发出不同的理解”。
7.专题式研究在各个领域全面推开
除了以上几个较大问题外,21世纪以来,宋代灾荒史、社会救济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政治文化(士大夫、礼仪、思想与社会)、基层社会(皇权不下县、胥吏、基层组织、基层行政区划、士绅、民间信仰)等问题受到中青年学者的关注,区域社会、地方精英、国家祭祀、婚姻家族、社会性别、疾疫灾害、理念认同、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依然持续受到关注,“更重要的是,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特有的视角及研究方式,也愈益发挥出引领与渗透的作用”。
设置于1999年的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迄2018年共评出10届获奖作品,代表了21世纪以来国内中青年研究宋史的最高水平。获奖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的修改稿,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逐渐成为研究主力和骨干,代之而起的专题式研究在各个领域全面推开。典章制度史、财政问题与部门经济史、城市史、人口史、交通史、货币史、区域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家族史、妇女婚姻、文化思想等领域都有颇见功力的专著问世。
由于专题式研究选题一般比较适中,资料收集和积累相对容易,又易于把握学术史的梳理,加之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博士的学位论文都采取专题形式,故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专题式的研究仍然是宋史研究的主要路径。
五、“大宋史”研究的新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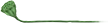
一是专题式研究固然深入细致,但是问题也非常突出,即研究细碎化、缺乏宏观贯通的把握。前辈师长大多能贯通古代史,同辈研究者大致可以贯通断代史,而1970年后出生的大多数学者则只能照应断代史中的某一专门史,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其研究方法和选题与西方汉学研究者有趋同的隐忧。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过分强调“问题意识”不无关系。“问题意识”,即为了证明预设问题的正确和模式的成立,许多学习者甚至研究者已经不再去大量阅读宋史的基本史料,而是根据自己所确定的研究问题去选择必要的史料进行阅读,这直接造成了当前宋史学习者与部分研究者在文献积累与分析能力方面远不如前辈宋史学家,间接地造成了当前的宋史学习者与部分研究者缺乏宏观视野,无法对宋代历史进行全局式的把握。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二是长期以来我们跟在西方汉学(西方社会科学和历史理论)之后亦步亦趋,选题往往是跟在美日学界后面,甚至以日美的研究范式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如前述唐宋变革论。为了证明“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脉络,11—14世纪中国历史的空间被一步步人为缩减,从北宋260万平方公里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再转向元明江南更狭小的地区,并且在日趋狭小的疆域空间内,又侧重于君主、士大夫和科举制等“精英”文化、地域重心及其相关议题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大量翻译、引进西方汉学论著,其负面效应就是“一味追求和模仿”西方汉学风格的“汉学心态”。造成汉学心态的原因比较复杂,走出汉学心态、重建学术自信,需要学者“在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重新解释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自觉可能也就在其中了”。
近些年有学者提出国史研究应当注重传统史学对人、事的书写,借以补充百年来国人遵奉西方历史“以事为本位”“以问题为本位”书写方式的不足。更有学者呼吁恢复历史学的人文性,亦即历史学的本源和主体,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在历史学的四个基本要素即时间、空间、事情和人当中,人是连接其他要素的关键。这些意见值得学界重视。
三是10—13世纪的历史,被人为划分为宋史、辽史、西夏史、金史,各立畛域,断代研究。老一辈学者大致能兼顾辽宋西夏金史,从同辈到学生辈乃至再传弟子,能够兼顾辽宋西夏金史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应多提倡和回应“大宋史”的研究理念。
所谓“大宋史”,是著名宋史学者邓广铭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一种研究理念,旨在强调前后并存的辽、宋、夏、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不是局限于赵宋王朝。2012年11月25日四川大学举办“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代表在闭幕式上呼吁打通断代史纵向、横向的界限,继承邓广铭先生倡导的“大宋史”理念,笔者在做学术总结时对“大宋史”的两层含义作了解释:“其一,学科间、专门史间、断代史间的整合研究,形成大的视野,全面完整地认识10—13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二,研究者应具备纵向兼通唐史和元史,横向宋辽西夏金史要互通的治史素养,眼界才能开阔,问题讨论才能深入,见识才能高远。”
2017年10月召开“宋史前沿论坛”,学界同仁围绕“大宋史”展开深入的对话与交流。澎湃新闻网站“私家历史”报道此次会议,标题就是“走出‘唐宋变革论’迈向‘大宋史’研究”。邓广铭先生在40年前就提出的“大宋史”理念,在学界内部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也出现了不少致力于“大宋史”的研究成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概念似尚未超出“大宋史”研究领域,影响力还比较有限。正如华东师范大学陈江注意到的,百度百科收入了众多与会学者的人名条目,却没有收录“大宋史”这一词条。这也说明不仅要继续提倡“大宋史”研究,而且要有一批学者来实践这一理念,才可能改变各自为政的断代史研究。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
责编|于凌
网编|陈家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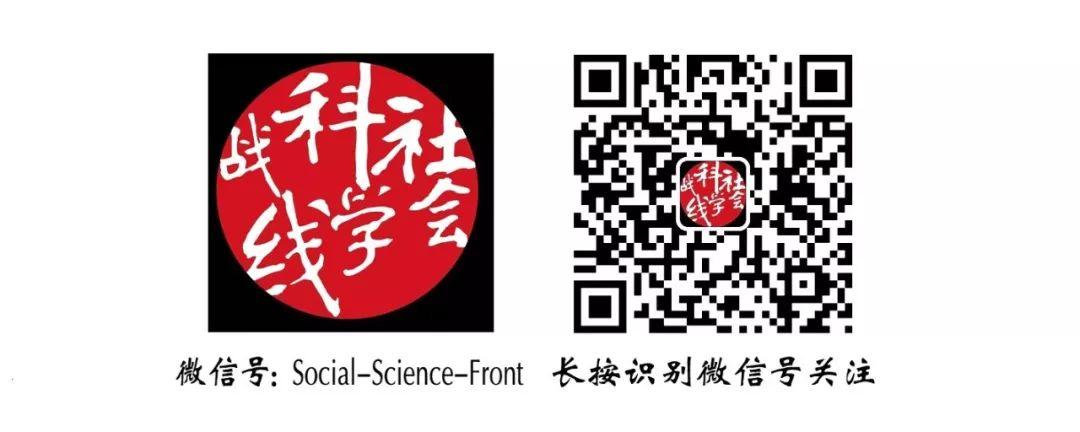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社会科学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