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表现出“纵的停滞”与“横的拓展”的特征,传统以“政治集团”或“党派分野”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领域陷入瓶颈,通过社会网络这一概念的引入,认识政治活动中的“政见—庇护”复合结构,有助于完善传统的政治集团分析范式。“政治过程”与“政治文化”这两个观察维度的引入,拓展了政治史研究的范畴。受新史学的影响,作为政治史研究基本单位的“事件”曾饱受批评,反思传统历史学编纂与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构拟,发现与提取“决定性的瞬间”,才能重新赋予“事件史”研究以合法性。
关键词:政治史;社会网络;事件
作 者: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
目录
一、社会网络与政治集团:一对概念的分梳
二、“政见—庇护”复合结构与政治集团
三、过程与文化:政治史范畴的扩展
四、抓住“决定性的瞬间”:重新赋予事件以意义
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
——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

众所周知,政治史长期占据历史编纂与研究中的主流,不过自20世纪以来,随着学术潮流的变化,日益变得边缘化。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概观而言先后受到两波冲击。首先是在现代史学肇建之初,以梁启超批评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倡导新史学为代表,不但破除了既往以政治精英人物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及叙事方式,同时也抛弃了传统史学所注重的“鉴诫论”“正统论”这类现实功用。第二次则是在二战之后,随着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及影响扩张,强调长时段的观察及对结构的揭示,使得以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被视为“海面上的浪花”,失去了历史研究中的皇冠地位。这一学术风潮在当时封闭的环境中,自不可能立刻对中国史学产生冲击。至1980年代国门重开之后,从西方不断接引而来的新方法与议题,成为中国史学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不可否认,这些新的方法与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间接造成了政治史研究的边缘化,这一变化也与国际潮流同步。
仍需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边缘化,并不是指政治史论著数量的减少,相反随着出版的繁荣与便利,相关研究在数量上一直保持着可观的增长。其主要表现有二,政治史不再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可以说近四十年来具有超越断代史影响的方法、议题或论争,绝少与政治史有关,更不要说由政治史研究者来发起或推动。其次,由于缺少新方法与新议题的冲击,政治史研究内卷化的倾向较为明显,至今仍多承袭陈寅恪等学者开创的政治集团分析范式,多少显得自外于新史学的潮流。这种孤立的状况,不但使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这些活跃且不断变换研究范式的领域少有互动,与国际学界也缺乏对话的对象。最近十余年来,这一现象尽管有了一定的改观,但不少问题依然如故,笔者在文中将其概括为“纵的停滞”与“横的拓展”,并以此切入谈一谈当下中古政治史研究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一、社会网络与政治集团:一对概念的分梳
所谓“纵的停滞”主要体现在传统以“政治集团”或“党派分野”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领域。直到现在,政治集团分析方法仍在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在内中国古代史各断代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这一分析范式的形成与接受,当然与陈寅恪等前辈史家借助经典研究的垂范有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集团范式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史学中“党争说”的发展,政治集团分析的一些基本维度,如血缘、乡里及同僚间的庇护与援引,皆不难在史籍中攻讦政敌结党的文字中读到。总括而言,较之于传统史学,陈寅恪的贡献大凡有二,一是综合考虑家世背景、社会阶层、文化风习、人事关系等各种因素,使“政治集团”这一概念统摄了政治、社会、文化三个互相关联、互为支撑的层面,使之初步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解释力的分析工具。其次,不再将政治集团的进退与治政得失乃至王朝兴衰联系起来,而是将其置于中古社会、文化变动的背景下加以讨论,不但超越了传统“党争说”汲汲于君子与小人之辨的道德训诫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将“党争”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权力与利益的争夺。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勾勒的一系列政治集团及其消长,如关陇集团、牛李党争,谈的是政治权力的转移,但他真正的着眼点是社会阶层的升降。某种程度而言,社会阶层以及因阶层差异产生的文化区隔是陈寅恪改造“党争说”过程中引入最重要的现代史学分析要素。
这一研究范式在接榫传统知识人读史趣味的同时,赋予其现代史学的分析功能,逐渐成为政治史研究中支配性的方法。同时也要承认,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世文献中的海量记载,尤其是在史料相对匮乏的古代史上段,关于政治人物言行的记录构成了留存文献的大宗,也为学者提供了施展的余地。某种意义上而言,史料的偏向间接造就了研究的偏好。长期以来,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先行研究,弊端也日渐显露。目前通行的政治集团分析,以“事件”为中心,辅翼以对政治人物家世、地域与阶层等要素的分类,不可避免地集矢于权力争夺的具体过程,旁及背后的政治组成,大多数情况下反倒忽略了陈寅恪研究中注重观察社会阶层变迁的一面。另一方面,这一研究方法往往试图在一系列“事件”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恰好落入布罗代尔批评的彀中,“一个事件在必要时可以表现为一系列的意义和关联。它有时表明非常深远的运动。而且,借助于昔日历史学家所珍视的‘原因’和‘结果’的游戏(无论这种游戏是否牵强附会),它可以占有比它自身的时段长得多的时间。因为它具有无限的延伸性,所以它可以不受限制地与所有的事件、所有的基本事实结为伉俪”。更需要指出是,大多数研究者似乎都不太注意区分“因果性”与“相关性”之间的不同,而是汲汲于建立事件与事件之间单一的因果链条,勾勒出看似环环相扣的连续线索,不免有陈寅恪所谓“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嫌。
不得不承认,政治史在各专门史中或许最受惠于同时也是最受困于历史的辉格解释,由于史料记载的晦暗,高层政治活动又距离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较远,难以避免较多地运用推测与假设。在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浪潮中,因为缺乏“科学性”,渐成弃儿。在此背景下,如何适当地运用“后见之明”,而不是为已经发生的政治结果寻求合理化的解释或成为决定研究高下的关键。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如何来有效地界定一个政治集团,作为传统政治史研究展开的基本前提,虽然一直聚讼不已,仍值得抉出做进一步的讨论,既往讨论较多的是概念与边界的分歧,不过笔者看来,首先需要分梳的是社会网络与政治集团这一对不同的概念。

在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中,尽管很早就建立了一套相当发达的以“任贤”与“绩效”为中心的选举与考课制度,但无可否认,依赖庇护关系而形成的人际网络构成了官僚个人及群体在体制中展开日常活动或争夺权力的基本形式。理论上而言,官员升迁主要依据治绩的优劣,不过庇护网络在更多地时候发挥了持续且相当重要的影响。这一网络不但寄生在官僚体制的各层级中,而且大多数时候隐居幕后,难以准确地量度其作用。一方面,我们确实能从史料中留存的大量党争攻讦文字中识别出这类网络,这也成为学者勾勒政治集团的重要依据,但被发现的无疑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将庇护关系视为官僚体制中的结构性存在,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基层的人际网络并不为史料所存录。同时需要警惕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这冰山一角,只是高级官僚政治关系的一隅,不但具有片面性,更是即时的,很难想象古人的政治立场不会随时势而改易,但史籍中记录或强调的往往只是他在某一时刻的政治倾向。除此之外,留存的相关史料,不少出自政敌之手,难免又有扭曲夸大的成分。
另一方面,这类在政治活动中发挥着或隐或显作用的社会网络是否就等同于政治集团,既往的研究对此尚缺乏明确的辨析与界定。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士人个体在进入或准备进入官僚体制内时,通过血缘、地缘等天然的纽带寻求奥援,进而借助婚姻、交游、同僚等手段拓展网络,这类行为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某种意义上也是官僚阶层自利取向的表现。而有效地运用自身的社会网络,成为官员获得荐举、升迁等各种政治机遇的重要手段,因此建立关系本身才是目的所在,连接网络“节点”反而是次要的、工具性的。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成为拓展庇护网络的因缘与媒介,这类要素在官僚体制中的延续性甚至不会随着制度设计的变化而被削弱。例如,从察举到科举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变,但孝廉同岁与科举同年作为重要的身份标识,在官员社会网络形成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则是类似的。这种自利性的社会网络及托庇于这类网络利益交换的普遍存在,确实成为官僚从个体走向“结党”的重要基础,但更多时候,这种自利性的社会网络作为维护官僚阶层既得利益的手段,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同时也不具有排他性,即官僚个体可以借助不同的“节点”,游走于多个不同层次、大小有别、疏密不一的社会网络中。
政治集团一词尽管经常被学者所使用,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其实相当模糊。若要将其与普遍存在的社会网络作一区隔,政治集团形成的基本要素需有一较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如果说社会网络或亲或疏、不具有排他性,政治集团则紧密结合兼具排他性。笔者在研究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时曾指出,司马懿与王淩、司马师兄弟与夏侯玄,虽然后来互为敌手,早年却曾活跃于同一社会网络中,关系密切,只是因政治目标的不同,才导致日后的分途。如果没有亡魏成晋的政治目标,司马懿虽然在曹魏政权中故吏旧属众多,拥有相当的潜势力,这些要素的存在并不会天然地导致政治集团形成。同样一个政治集团,因为目标的变动,也会发生分合,甚至化友为敌,如高平陵之变时,因反对曹爽专权,蒋济、高柔等曹魏老臣选择站在司马懿一边,但随着司马氏家族代魏自取野心的显露而与之分道扬镳。

借助对魏晋之际政治过程的复原,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观察到社会网络与政治集团之间的分合。社会网络有时确实可以成为政治集团的基础,但在转化的过程中,也蕴含着因政见不同,导致原有社会网络分裂,分化为两个甚至多个对立政治集团的可能。这种常伴着政变乃至血腥屠戮的剧烈转换,虽然作为“事件”常在史书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不过是王朝政治中的“变态”。从王朝政治的日常而言,因庇护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网络虽然也会因人事关系的变化,发生分化重组,总体而言仍是一种广泛寄生于官僚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存在,而政治集团则是暂时的、非连续性的。如果说庇护关系宛如庸碌而平淡的日常,政治集团则象征着短暂而剧烈的变化。同时,由于传统政治史研究关注“事件”,往往借助官僚在“事件”中的言行来勾勒政治集团,在方法上不免有“倒放电影”的嫌疑。事实上,人际关系的形成具有偶合成分,学者重视的地缘、血缘、同僚等关系某种意义上只是为“政治集团”的构拟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建立在“后见之明”的基础上,并不能真正说明政治集团的缘起。学者在研究中枚举的形形色色的政治集团,哪些带有主观建构的成分,哪些是真正根据史料识别而出的,恐怕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二、“政见—庇护”复合结构与政治集团
中国古代的政治行为中大约有两类可以被称为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一类是如上文所讨论的以独揽朝政乃至建立新朝为目的的政治活动,另一类则多可归入史籍中常言的“党争”范畴。前一类型中权臣借助政治或军事力量侵夺乃至颠覆皇权,反映的是君臣之间的矛盾,属于纯粹的权力争夺,常见于汉唐时期。此类政治集团往往脱胎于权臣个人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强的依附性,一旦鼎革完成,摇身一变,成为新王朝统治的核心。后一类则是官僚内部因政见或利益不同,产生的分野,并不挑战皇权,经常掩饰于“君子与小人”“得君行道”之类话语背后,中唐以后比比皆是,以中唐牛李党争、北宋新党旧党之争、明末党争最为典型。

关于后一类,内藤湖南曾有一概观性的评述,所揭示的两种类型及其变迁似尚未引起中文世界学者的足够注意。内藤湖南指出“唐的朋党,不过是以贵族为中心,专以权力斗争为事。到宋代,则以政治上的主张,或由学问上出身的不同而结为朋党。这说明,政权自从离开贵族之手以后,由婚姻或亲戚关系而结成的朋党渐衰,而由政治上的见解,或由共同利害的原因,结为党派”。他所勾勒的唐代党争是贵族间的权力之争至宋以后渐变为士大夫的政见之争的演变线索,无疑将其作为唐宋变革中的一环来加以理解,因政见分歧形成的党派也具有近世特征,这一断语的得失姑且不论,治宋史的学者亦有不同的看法。值得抉出讨论的是,所谓党争的核心究竟为何,到底是政见之争还是权力之争,对此学者的认识颇存分歧。以中唐的永贞革新为例,黄永年便曾批评王叔文集团代表庶族地主阶级的新兴力量与推行反藩镇、反宦官政策这两种成说,认为王叔文集团的聚合与成败,只是唐代统治阶级各个集团之间内部斗争的体现。如果进一步检视黄永年对陈寅恪的一系列批评,不难注意到借助对具体史实的辨析,强调传统中国政治的斗争与阶层或理念无关,其本质不过是围绕一个或多个政治人物为中心人事关系的结集、分化与冲突,这一思路贯穿在黄先生的大多数政治史研究中。如果说陈寅恪尝试引入社会阶层等量度手段,将传统“党争说”锻造为“政治集团”分析范式,而黄先生思路则倾向于回到“党争说”,着眼于对具体政治行为的分析,否认阶层、地域、文化等因素潜在而持续的影响。客观而言,黄永年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事件过程的考订,在研究方法上则有后退的嫌疑,所论对政治集团说的滥用有重要纠偏的作用,并未真正突破陈寅恪范式,开辟新路。
政治确实是由各色人等争夺权力的行为构成,但政治超越了权力争夺行为的总和。将人的政治行为归因于对权力的欲望与认为这些行为受阶级、文化决定一样,不但抽掉行动者的主体性,同样也是“贫困”的历史决定论的产物。如果我们将“党争”仅仅视为权力之争的话,那么与前一类挑战皇权的政治行为不同,党争中各方所争夺的不过是皇权委托治理的衍生权力,即执政权。理论上,基于利益的权力之争并不存在边界,最终会导向对皇权的挑战。而中唐以后的党争,在话语乃至行为上都是以强化皇权为旨归的,尽管效果上或有南辕北辙的可能。因此,理念与政见的分歧也是党争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旦有了“得君行道”的机会,需要把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政治行动中去,这需要由人来执行推动,不可能不涉及人事安排与权力分配。任何改革都需要权力作为保障,而权力的获得与保持,不可能真正远离政治攻讦与利益交换。随着这一系列要素的传导与作用,政见分歧最终会以争夺权力的形式表现出来。随着权力争夺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中,例如某一官员的选任,理念变得暗淡,利益浮出水面,庇护关系开始发挥作用,导致政治行为的“劣质化”。
如果借用上文“社会网络”与“政治集团”这一组概念做进一步分梳,则可观察到“政见—庇护”复合结构的存在。以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为例,新旧之争的核心当然是政治理念之争,政见的分歧导致了双方重要人物的对立,但正如之前学者指出的,新旧党争的面貌并非如此纯粹,尤其是随着政争的激化与持续,每一项政治决策与官员任免,都可以成为双方角力的舞台,顶层的政见分歧传导到中下层,转而受制于原有庇护网络中的各项人事纠葛。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呈现出“政见—庇护”的混合形态。传统所谓新党多小人、旧党多君子之说,也可以得到另一种索解。旧党作为政治上的保守派,社会网络业已形成且较为稳定,不利于新进,躁进之士通过支持新法的政治姿态,有机会跻身一个正在形成且快速扩张的庇护网络,无疑是有利可图的政治投机。庇护关系本来是官僚体制中隐而不彰的结构性存在,而政见之争及因分歧产生的政治机遇与利益再分配,作为新出现的变量,刺激了原本稳定有序庇护网络的分化与重组,作为结构(structure)的社会网络与作为能动(agency)的政治斗争两者互相作用,在平静的水面上掀起巨浪,冲破堤岸,改变了原有的权力格局与运作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党争的持续,庇护关系往往会重新取得优势,政见分歧上升至君子小人之辨的道德攻讦,进而沦为排斥异己的手段,乃至出现“党禁”,于是理念褪色,关系浮现,政治生态恶化,是学者熟悉的党争后期常见的图景,而“政见—庇护”模型或许可以较好解释两者之间的转化与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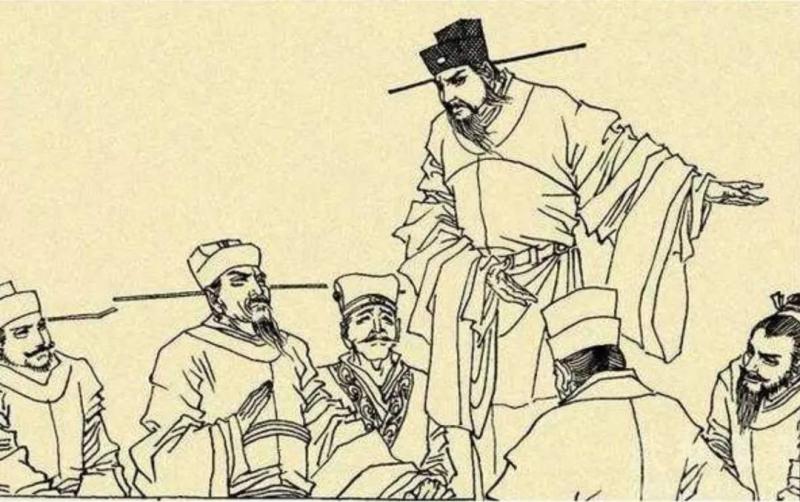
内藤湖南在唐宋变革论视野下勾勒出的朋党性质变化,这一假说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在于政见分歧是否成为朋党政治的重要诱因,而在于宋以后的朋党对立是否越来越以政见为基础,政见成为超越血缘、地域、同僚等其他人际关系结合的存在,广义庇护制的衰落一直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而在这点上,恐怕尚难以观察到变迁的趋势。
三、过程与文化:政治史范畴的扩展
较之于传统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停滞,近年来政治史研究依然发生了可观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政治过程”与“政治文化”这两个观察维度的引入,拓展了政治史研究的范畴,此即笔者所谓“横的拓展”。最早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引入“政治过程”这一概念,大约出自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一书,寺地遵的研究与以往政治史多用力于形态、结构、静态方面的做法不同,而是观察其运动、冲突、动态的方面,通过对过程的细致把握,展现政治活动的复杂性。在当时的语境下,寺地遵挑战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是在时代分期论争的背景下,无论是将宋代归为中世还是近世,都预先将宋代设定为一种与唐进行比较的静态类型,忽视了其前后期的变化与联系,其次则是在传统治乱兴亡或民族斗争的框架下简化地理解宋代政治史。寺地遵主张的“政治过程”研究,通过对南宋初期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人物、决策的分析,在时间轴上清晰地呈现了秦桧主导的绍兴十二年体制的成立过程与维系机制,摆脱了原来大而化之的论述,注意观察人事关系与政治形势的动态演变,但在方法上并没有溢出传统政治集团的分析范式,包括作者本人将吕颐浩、秦桧归入北宋权门的余绪,将李光视为江南地主阶层的代表等,皆是如此。由于作者分析细腻,虽也运用党派对立的分析框架,但不显得生硬。因此,此书某种意义上呈现的是在“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审慎地运用政治集团分析方法所能达到的高度。不过值得思考的是,陈寅恪将社会阶层与政治集团相结合的研究,固然有不少弊端,究其要旨则是尝试揭示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政治过程研究强调复杂性的同时,却回避了结构,永远呈现变动与未完成的状态,描述代替了解释。
“过程”这一概念后来在邓小南提倡的“活”的制度史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除了对制度变迁的关注外,还强调人对制度的能动作用,从而将制度与政治相勾连。在传统制度史关注文书行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至政治信息的传递、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与互动等面向。另一个取向则是对“政治空间”的重视,政治活动必须依托具体的场所,通过对都城尤其是宫城布局变迁的研究,或探讨政务空间变化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或从官僚机构与宫廷相对空间位置的移动,考察权力结构的变迁。这些研究虽然依傍之前两个重要的学术传统,一是依据考古与文献资料对都城空间的复原,二是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所总结“内朝的外朝化”这一官僚制度演变的规律,但较为成功地将权力构造与政治行为置于特定的空间中予以呈现,更为准确地把握了制度变迁与政治过程的律动,十余年来汉、唐、宋各断代史中都产生颇有分量的作品。平田茂树近年又进一步借用“场”这一概念,来统合物理性的政治空间与具有功能性的抽象政治空间,指出“人类活动的空间不仅是指物理空间,当然它还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空间,并经由人与人互相之间的各种沟通结构,由其空间中产生的政治性秩序、社会性秩序等社会结构”,是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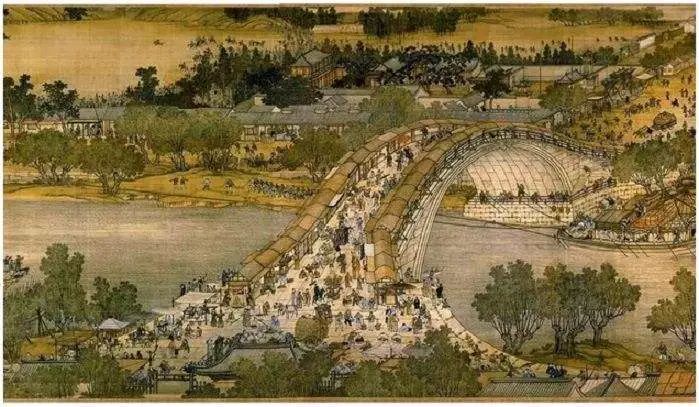
政治文化一词在国内学界产生巨大影响,或要归功于内外两股潮流,一是脱胎于士大夫政治研究,较早标举这一概念的是阎步克,他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政治形态,自汉代以后,也可以说特别地表现为一种‘士大夫政治’,这种政治—文化形态有其独特的运作机制,并构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接下来他参考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定义,进一步界定了何为政治文化,“经常用于指涉处于政治和文化交界面上、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那些有关事项和问题”。陈苏镇等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也有系统的思考,并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提炼与扩展。其次则是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标举的研究取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早先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在议题上接榫了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界生发出巨大影响的两个学术热点:士大夫政治与思想史、学术史。聚焦经学、道学、道统这类思想资源与皇权的关系与互动,关注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思想如何作用于现实,而实际的政治需求又如何反噬学术,这些研究或隐或现地安置了学者的现实关怀。近年来,随着政治文化这个名词被广泛接受、乃至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议题后,反倒激发了学者对风谣、谶纬、祥瑞、灾异等这类传世文献中大量留存而且与政治行为关系密切史料的讨论,产生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论著。这些研究关注广义的“天人关系”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作用,力求与古人站在同一情境,阐发这类以往多因被视为“迷信”而遭摈弃不论的“事件”在古人世界中的意义,大大拓展了政治文化研究范畴的同时,关注点与之前也发生了偏移。研究范围的膨胀及边界的模糊,使得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显得无所不包,甚至可以说除了具体政治斗争与人事关系之外的政治史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范畴。不过概念的精确与范畴的扩展往往是一对矛盾,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研究门类,已得到学者的公认,但在“横的拓展”的同时,似乎并没有真正成为有效的分析工具。
如果说传统哲学史以思想家为中心,思想史研究则重视观念的流变,而政治文化研究则尝试将观念与具体的政治行为相勾连,其不证自明的前提是认可观念与行为之间是相互影响甚至有因果关联的。问题是这种联系就一定存在吗?即使存在,是否就那么直接。或者说之前学者关心的是普遍思想与具体行为之间的联系,即使我们承认“观念”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对于古人的选择与行动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结构”如何作用到具体的事件中,而每一个“事件”都被“结构”所统治吗,其间的“缝隙”与“断裂”才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如我们熟悉的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将当时清谈家对才性离合的不同持论与他们的政治立场、社会阶层相勾连,读来固有发隐抉微之妙,但这种联系是否就那么简化而直接实在颇让人怀疑。

陈寅恪立足于社会阶层的观察无疑深具卓见,但社会阶层的变迁与政治集团未必同步,尤其是难以建立起因果联系,社会阶层与政治集团的关系如此,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亦如之。注意把握历史演变的不同节奏,传统史学的一大缺陷在于运用单一的时间尺度去衡量“一些既无同样延续性、又无同样发展方向的运动”,并在此基础上构拟出因果联系。而年鉴学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破除编年史的神话,通过对时间的分类,使之从先后顺序的标识转变为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因此在发现“联系”的同时,亦需注意“断裂”的存在,既往研究对此似尚缺少足够的自觉。
四、抓住“决定性的瞬间”:重新赋予事件以意义
至少在笔者看来近年来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更多地渊源于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自身演进的脉络,但在议题与方法上,与西方史学新文化史转向后兴起的“新政治史”研究有不少暗合之处。目前西方学界流行的新政治史主要集中于记忆、符号、仪式、话语、观念、心态与集体行动等议题,实际是新文化史浪潮中的一个分支。如学者谈及新政治史将法语“政治”一词的阴性概念(la politique)扩展到阳性的“政治”(le politique)。阴性的“政治”指的就是权力和政治活动本身,而阳性的“政治”指的是与政治有关的一切东西,包括和政治有关的所有对象,如货币、住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活动、新闻媒体以及新兴的网络世界等,关注重点从精英人物转向普罗大众,从重大的历史事件转向日常的政治生活,无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运用的史料较之于传统政治史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倡导要重回政治史,也意在响应这一潮流,而非简单地重返传统以精英人物为中心的政治事件史中去。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新政治史关注一般人的政治意识与行为,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史料丰富的近代以后,在法国与新政治史兴起相伴随的是对“现时史”的研究,将战后法国乃至第五共和国的历史都纳入其中,这种“政治的文化史”由两根支柱构成:表象体系和传播过程。其中涉及的很多议题虽然饶有趣味,但对于古代史而言,恐怕难逃“无米之炊”的困窘,大众政治意识的形成与塑造某种意义上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古代缺乏明确的匹配对象。例如传播在现代政治中十分关键,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中尚不足以断言其意义大打折扣的话,至少因传播手段、效率及覆盖对象的不同,对其作用机制需重新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理论的驱动,时至今日,与国际接轨的任务可以说已大致完成,国际学界流行的方法与议题,很快都有学者在中国史领域中予以引介尝试。在此背景下,我们或稍可反思对“理论进步主义”的崇拜,并非新的理论与方法就一定能带来研究的突破,重新检视史料的特征,并承认其边界与局限,在此基础上,再思考新方法运用的可能,或许是更务实的做法。对政治史这样传统的研究门类而言,方法改良的重要性或许超过议题的改换。
无可否认,年鉴学派对传统政治史的批评深刻而有力,编年、事件与精英人物恰恰构成了既往政治史研究的三根支柱。在新史学的浪潮中,以事件、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一方面缺乏给历史变迁提供“结构化”解释的能力,同时也面临着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可能被重现的质疑,内外夹攻之下,从中心滑落至边缘。某种意义上而言,直到今日,作为专门史一员的政治史,其学科的合法性仍需“保卫”,其中的关键恐怕在于如何重新给“事件”研究赋予意义。
关于“事件”的局限,布罗代尔曾做如此譬喻,“一个事件是一次爆炸,如16世纪人们所说的‘瞬间的事情’,它的迷人烟雾填满了当代人的心灵,但是它不可能持久,人们刚刚勉强看到它的光亮”,认为“短时段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不过他也同样谈到“因为比根深蒂固的生活结构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的断裂点”,而结构本身并不可见,隐藏在林林总总的事件背后,“事件”或许仅仅是一次爆炸,如果爆炸能够照亮“结构”,便不仅仅是一种扰动。借助“事件”的扰动,我们可以观察到何者为常态,何者为突变,而新增的突变哪些是转瞬即逝的,哪些又被结构所吸纳,成为常态的一部分。过去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权力争夺的过程,现在有学者提出要关注政治运作中的日常,但两者不是永不交叉的平行线,存在互相的作用与转换。
政治史研究的核心是权力的生成与运作,这或可被视为对一个相对稳定结构的揭示,属于政治的日常,但结构往往会遭到事件的挑战与破坏,事件也会反馈结构,大多数事件或许仅是扰动,但有些事件可能成为重塑结构的契机,这便是结构中的断裂点。我们需要尝试抓住“决定性的瞬间”,重新赋予事件以意义。因此需要被抛弃的不是事件史,而是解读事件的方法。可以说举两个具体的研究略作说明。如果说陈寅恪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司马氏代魏是儒家大族取代了法家寒族的曹魏政权的观察,意在揭示东汉至西晋统治阶层的构造,那么笔者通过高平陵之变过程的分析,指出政变的成功有侥幸成分,司马懿本人当时并无控制政权的把握,实际上是借助“事件”挑战了结构,并尝试在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对结构进行反馈和修正。事实上,没有对事件的研究,我们很难发现表面上连续的结构内部的缝隙,容易陷入停滞论的泥潭。
另一个则是更微观的研究,近年来有三篇论文先后讨论了北朝隋唐的“二王三恪”制度,较早孙正军、吕博两文虽持论各有异同,但都尝试在北朝至中唐,勾勒这一制度流变的连续线索,乃至尝试与“关陇集团”等既存的分析框架相呼应,而夏婧仅考索柳怀素这一小人物的生平与命运,并无理论关怀。如果进一步思考的话,或可察觉其内在的紧张,如果按孙正军、吕博所勾勒的线索,“二王三恪”是一项随着政治环境变化被不断随之调整的制度,属于权力结构变迁中的一环,尽管是相对边缘的环节,甚至可以说这一缘饰性的制度所以突然被学者关注,或许也反映了中古史“题无剩意”的研究现状。只要我们认为“二王三恪”的改易处于当时政治博弈的风口,需要解释的便是为何柳怀素这样一位非姬姓的小人物也有机会充任此位,选人的轻忽与制度的庄重形成了悖论。这或可被视为“事件”对“结构”的反问,也提醒我们思考学者所习惯勾勒政治、制度变迁这类连续性线索的有效性,并对任何统摄性的框架保持警惕。

要重新赋予“事件史”研究以合法性,关键在于如何发现与提取“决定性的瞬间”,而非简单地依照时间上或空间上连续与相关将其排列组合。什么才是重要的、值得研究的“事件”,并非天然形成,往往需要经过“历史”与“史家”的赋义。一方面我们需要承认,作为史实的事件本身就有轻重之别。一般而言,一场战争当然比一次普通的官员任免来得重要,也更有可能被记录下来,更容易被后世史家纳入历史解释的因果链条中。另一方面,历史并不是过去发生所有事件的集合,史家基于“后见之名”对事件的拣选与解说,已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而赋义的轻重,往往又随着史家对历史认知的变化而摇摆。例如,在既往的认识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毫无疑问是历史上的大事件,被定义为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之一。近年来学者倾向于认为无论是甲午的失败,还是1905年废除科举,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期影响均要大于辛亥革命。或许辛亥革命确实属于布罗代尔所言的那类事件,“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除了改旗易帜外,并未触动中国社会的实质。另一方面,如“叫魂”这样的小事件,虽然发生的时候多平淡无奇,经过学者的发掘,成为观察帝制中国统治方式的切片。因此,何为历史事件,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它发生的时候,只有当它被史家纳入某种包含因果关系的叙事时,事件才成其为事件。
事件作为史学研究的单位,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也不是天然的不具有合法性,需要经由史家的赋义。如果说对“政治过程”的强调,否定的是既往研究中建立在后见之明基础上的简单化的因果解释,尝试恢复历史本身混沌的形状,但仍不免以事件为中心,本质上不脱实证主义史学的色彩,而对于决定性瞬间的观察与选择,则反映出史家对于事件背后社会结构的理解。当下我们亟需走出的是充溢着猜测、阴谋的政治史,或许这些作品深受非专业读者的欢迎,但史家不可能真正重返甚至接近的历史现场,对动机的种种揣度,或许有猜对之处(当然也没有办法证实),但并无意义。既往政治史对事件、人物孤立的讨论(包括对事件意义、人物评价等方面),其弊端不言而喻。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从既往以人物为中心,转向以政治行为为中心,政治行为包含了人物、制度、关系、决策、观念等多个面向,从事件走向整体,在整体中观察事件,借此重新赋予“事件史”研究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