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刁书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史、中朝关系史。崇德元年(仁祖十四年,1636),皇太极第二次征朝鲜,朝鲜战败,签订“城下之盟”,被迫接受清廷册封,履行朝贡义务。顺治元年(1644),清朝迁都北京,李朝为尽“事大”之礼,每年都派朝贡使赴京朝贡,清朝作为朝贡的答礼赐给物品的同时,允许使节团与清朝商人在北京会同馆贸易。在会同馆贸易中,有诸多清商与李朝贡使进行贸易,尤其是活跃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京师巨商郑世泰最为闻名。有关郑世泰的研究,仅见日本学者1篇论文,在研究清与朝鲜贸易的论著中也有所涉及。笔者以为前近代东亚地区存在着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封贡体制,这种体制下的东亚地区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有共同性,而且在经贸上也有着密切关联性。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在清朝日三国形成的东亚贸易网络中,北京会同馆中朝贸易和东莱倭馆日朝贸易互为前提,相互关联。而先前的研究中,缺少将前近代东亚三国贸易视为贸易整体,较少关注日朝贸易与中朝贸易间内在的关联机理与互动。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以李朝使臣所撰写的燕行日记为基本史料,参考其他文献,梳理京商郑世泰与李朝贡使在京城会同馆贸易盛衰实态,进而透视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贸易及其变迁。
刁书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史、中朝关系史。崇德元年(仁祖十四年,1636),皇太极第二次征朝鲜,朝鲜战败,签订“城下之盟”,被迫接受清廷册封,履行朝贡义务。顺治元年(1644),清朝迁都北京,李朝为尽“事大”之礼,每年都派朝贡使赴京朝贡,清朝作为朝贡的答礼赐给物品的同时,允许使节团与清朝商人在北京会同馆贸易。在会同馆贸易中,有诸多清商与李朝贡使进行贸易,尤其是活跃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京师巨商郑世泰最为闻名。有关郑世泰的研究,仅见日本学者1篇论文,在研究清与朝鲜贸易的论著中也有所涉及。笔者以为前近代东亚地区存在着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封贡体制,这种体制下的东亚地区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有共同性,而且在经贸上也有着密切关联性。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在清朝日三国形成的东亚贸易网络中,北京会同馆中朝贸易和东莱倭馆日朝贸易互为前提,相互关联。而先前的研究中,缺少将前近代东亚三国贸易视为贸易整体,较少关注日朝贸易与中朝贸易间内在的关联机理与互动。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以李朝使臣所撰写的燕行日记为基本史料,参考其他文献,梳理京商郑世泰与李朝贡使在京城会同馆贸易盛衰实态,进而透视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贸易及其变迁。
一、李朝赴京贡使团与会同馆贸易
李朝赴京贡使的名称,有节行、别行以及赍咨行、历行等。节行,定期使行。李朝初期对明朝贡为冬至、圣节、正朝、千秋四行分别派送。顺治二年(1645)始合并为一,即每年阴历十一月出发,前往北京,翌年四月归国的三节兼年贡使,称“冬至使”。直至清末,李朝每年都不间断地派遣。别行,临时使行。如清廷有庆吊事,或李朝发生特别事件,急需解决才派遣,有谢恩、陈奏、陈贺、进香及辩诬、告讣、问安、参覈使等。赍咨行,也称赍奏行,通常指事情不甚紧要,如派遣护送漂海清漂流民。赍咨行,属略使,未必三使具全,多从堂上或堂下译官中选派一人为赍咨官前往。历行,也称皇历赍咨行,每年十月初前往北京,领受清廷时宪历的定例使行。节行和别行有定例使行与临时使行的不同,且使行目的也有区别,从而决定朝鲜向清进贡的岁币、方物种类、数量也有诸多差异。
李朝贡使团依使行种类不同,使团人员构成也不尽相同。大体上,使团包括正使、副使、书状官各1人,大通官3人(堂上译官1人、上通事2人),押物官24人,共计30人,称为正官。这是中朝两国公认的定员数。清廷允许上述正官在例行朝谒清帝仪式上着公服出席,可受到礼部的接待,并享有清廷回赐礼品。这些正官在赴清使行中均有各自承担的职掌。以冬至使行为例。正使、副使、书状官称为三使。正使与副使一般由正三品以上宗室及官员中选拔,书状官由五品官员中挑选。正使代表朝鲜国家出席清朝举行的各种礼仪活动,如递交国书、领受赏赐等。副使除随同正使参加各种礼仪活动外,总掌使团中的各项事务。书状官负责详细记录每日行程、沿途见闻,归国后向国王禀报,并兼有纠察使团人员是否携带违禁物品,对携带者予以惩罚之责。而赴清使团中,作为“大通官”之一的堂上译官,才是使行中“总察行中,主管公干”的总负责人。两名“上通事”,是堂上译官的副手,参与管理使行中诸务。押物官24员中,有押物、押币、押米等官,是负责使行中数百驮方物、岁币、岁米等管理及掌管负责运送这些物资的数百号人马的译官。另有医员、写字官、画员及分属正使、副使、书状官的军官等人。
朝贡使团每次赴清使行需时近半年,往返路程约4000余里。这期间率领数百驮货物和大量人马往还的译官作用最大,李朝官府为他们配给从人与马匹,或允许其自带,赴京使行中的正官以及配给的马夫、奴子等总人数就达220余人,马200余匹。此外,李朝从事贸易的商人也作为使团成员同行。如前所述,依据清礼部规定:朝鲜贡使团清廷予以赏赐者为30名正官,其余人员都不予赏赐。乾隆四十五年(1780)随同使团赴京朝贡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了该使团的人数:正使、副使、书状官3人,大通官3人,押物官24人,即得赏者30人,无赏者221人,总计251人。
对李朝贡使而言,携带白银和特产人参,借朝贡滞留北京期间,同清商贸易,购买清朝的物产也是使行的重要任务。因此,使团的正官,即正副使、书状官、译官等依其官品由政府支给米、木棉、麻布等作为盘缠外,政府还支给银两或人参作为人情费或贸易费等公用经费。清入关前,李朝贡使往来沈阳期间,政府以盘缠为名,最初支给正官每人南草50斤。清迁都北京后,南草价每斤换银1两,等于说,每位正官携银50两。这仅是使臣作为盘缠的支出。作为“八包贸易”资金则远不止于此。有关“八包贸易”沿革,《通文馆志》载:“宣德年间,遣使请免岁贡金银。敕书有曰:‘金银本非本国所产,自今但以土物效诚’。自是赴京买卖,禁银货,领带人参,而厥数浸多,至于每人许赍八十斤,此所谓八包也。其后,又代以银子带去,而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计银二千两为一人八包。”可见,朝鲜因银矿缺乏,曾多次请求明免金银之贡,以他物代之,至宣德四年(1429)得到明廷允准。嗣后,赴京使团禁用银两,允人持人参10斤于会同馆贸易,所贸人参10斤分为八包,此为八包之始。后所带人参数渐多,以致泛滥。至崇祯初年,李朝规定每人赍80斤,每10斤为一包,亦称八包,继而,又允准带银,以人参“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共银二千两,为一人八包”。清代明后,仍申行此法,“康熙初,始定以银子,堂上及上通事三千两,堂下二千两”。此八包法,并非赋予所有赴京使团员役的特权,如前所述,只有使团中三使(正使、副使、书状官)及堂上官、上通事、押物官等正官30人有此特权。如赴清的朴趾源所言:“使行时,例给正官八包,正官者裨译三十员。”这30员正官,用于贸易的八包定额银,计达6万至7万两。而使团中其他随从人员,如奴子、马夫、厨子、军牢、引路、书者、牵马等杂役都无此特权。这种八包额定物品,最初由官府支给,后改由译官等自筹,即“八包者,旧时官给正官人参几斤谓之八包,今不官给,令自备银”。换言之,使行正官赴清前要自筹八包定额银。此外,正官除额定八包贸易外,还兼管尚衣院、内医院等衙署的贸易,为与正官的八包区分,称为“别包”贸易。我们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祖元年),赴清使李坤《燕行记事》中所载是年使团一行人员携带八包银为例,加以说明:“八包都数:堂上四员,御医一员,上通事二员,放料军官一员,湾上军官一员,合九员,八包各天银三千两,式合二万七千两;从事十五员,医员一员,写字官一员,画员一员,偶语别差一员,裨将八员,药房书员一人,合二十八员,八包各天银二千两,式合五万六千两;内局药材贸易,包银五千二百七十两,尚方匹缎贸易,包银四千七百两,内农圃菜种贸易,包银三十两,合一万两。以上都合八包天银九万三千两。”由此可见,到李朝正祖朝,虽正官人数达37员,但仍遵守规定的八包银额。上述规定的所谓八包银额,意味着李朝政府容许使行员役在北京进行贸易的上限额度。朝贡使团在北京的贸易,有公贸与私贸两种。公贸,包括为补充贡使团费用的使节贸易,有由上通事负责的尚衣院为王室购买衣服、宝石以及生活用品的尚方贸易,有由次上通事负责的内医院为内医院购入药材的内局贸易,还有以别将身份为各地方衙署购置所需军需品的别将贸易。关于私贸,朝贡使除公贸易外还从事私贸易,另有京商、湾商等冒充随员、马夫等身份混入使团中从事的私贸活动。
李朝贡使团到达北京住在会同馆,贸易以会同馆贸易为主。清廷对在会同馆贸易的外国使节虽有诸多规定,但对朝鲜贡使团还是网开一面。如规定:“凡外国贡使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由部移文户部,先拨库使收买,咨覆到部,方出示差官监视,令公平交易。”可见,清廷唯独对朝鲜、琉球的贸易不拘时间限制,要求贸易前由礼部移文户部,由户部派员优先贸易李朝贡使所带货物后,方准在户部差官的监视下于会同馆内贸易。与此同时,清廷对前来贸易的清商也有诸多约束。如规定:清商须由会同馆监督取保,发给腰牌,方可入馆交易;在交易中,清商“如有赊卖及故意迟延欺诈,至外国人久候,并私相交易者”,或“有代外国人收买违禁货物及将一应兵器、铜铁违禁等物,卖与外国人图利者各问罪”。贸易结束后,李朝使团需呈贸易清单于礼部,由该部出具公文,以便出山海关、凤凰城栅门等关免税验放。当然李朝使团回国途中也“不许将违禁货物,私相买卖”。
李朝贡使团在会同馆贸易,一般使用银或以物兑换清朝通用货币。白银当时已经作为东亚地区贸易时共同支付的货币,朝贡使团如携带白银以外物品,则需兑换为清朝国内通用货币。如使臣李宜显所言:“我国之钱,不可用于燕中,故自入北京境,以白金、纸、扇等物,换贸燕中钱文,以去随物买取。其钱如我国所谓小钱,而三百三十三个为一两。”这种以银或物品兑换清通行的货币机构就是典当铺。据乾隆年间赴清的使臣洪大容所见,这种典当铺,“关内外大小村堡,凡有列肆,必有当铺,亦必雕牕峻宇,绝异于他肆……沿路换银换钱者,多归当铺”。可见,所谓典当铺,就是给朝贡使团以银换钱,以钱换银的场所。这种交易,是“现银售卖,不得赊欠、拖延”。
李朝贡使团在会同馆贸易,一般是在归国前十日,最为活跃。朝贡使留下的燕行文献记载了会同馆开市的景况。据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往来总录》癸巳二月十一日条载:“是日,胡人持各色物货入来,馆中纷沓如市。盖告示榜揭,后门无禁,人皆任意入来故也。”韩德厚的日记也载:“始揭开市榜,而物货之价,比前倍踊。盖彼中商贾输转南京锦彩,待我国使行,方做大买卖,其初则平其直相贸,少无欺负,商译辈亦得其利矣。”从事贸易的清商,以京商为主,有乌商、刘商、于商、陈商、项商、黄商。此外,还有晋商、鲁商,更有南方徽商、广商、浙商、苏商等。正如洪大容《湛轩书》所载:“此外诸商,不可尽记,岁杪入京,诸商遍馆……正月初,衙门禁诸商,不得入馆。十六日,提督挂榜告示,始拦入,诸译亦不胜其苦。至十数岁儿,持小小器物,遍行馆中,呼卖甚苦,可想其尚利成习也。”
二、京商郑世泰与李朝贡使团的贸易
清朝商人在会同馆与李朝贡使贸易,从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以京商为主,尤其是郑世泰执中朝贸易牛耳。郑商生卒年,文献阙如,语焉不详。康熙五十一年(1712)赴清的金昌业,于翌年正月曾见郑世泰,给他的印象是“年可四十”,据此推断,郑氏约生于康熙十年(1671)。郑商去世与英祖二十二年(乾隆十一年,1746)颁布“纹缎禁令”(禁朝贡使输入清纹缎等高级绢织物)有密切关联。据《英祖实录》是年十二月丙子条载:“燕商郑世泰闻有新禁,大惊,即报江南止其织纹,谓我人曰:‘在汝国王,诚盛德事,吾属自此无以聊生矣。’”郑商是专与朝鲜作纹缎生意的,为赚钱,他多先期从南方购买十多万银两的货物。李朝发布“纹缎禁令”,意味着朝鲜将断绝与他做纹缎生意,这样他先期从江南购入的纹缎就会滞销,招致破产。所以,时年已过七旬的世泰,“闻有新禁,大惊”,“吾属自此无以聊生矣”,是其遭受巨大打击的真实写照。由此推断,其卒年应为乾隆十三年(1748)左右。就是说,郑世泰生于康熙十年,卒于乾隆十三年,享年77岁,所生活的时代为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
郑商全盛时,称“北京大贾”“北京买头”等。如是称谓与其出身经商家族有关,“自其父时,以此起家,至世泰益富”。世泰是子承父业。其父应在清定鼎北京后,就从事会同馆的中朝贸易而发家致富。不仅如此,郑商家族还颇有权势,其祖母曾得到康熙帝的旌表,金昌业的日记载:“世泰家在玉河桥路傍,尝见其门立棹楔,书曰:‘钦奉圣旨,旌贞节女某氏之闾。’余问:‘贞女,于君何人?’世泰曰:‘祖母也。’”为此,郑家“作庙堂于玉河馆门傍,昼夜焚香,其香若盘绳,燃其一端,则烧至一昼夜云”。朝鲜使臣对世泰的最初印象“形瘦黑甚,没风采,不似万金财主”。看似其貌不扬,却凭借家族势力,“婚娶多仕宦家,以此颇有权势”。其父去世,竟用价值千金的孔雀板作棺衾。对此,与金昌业同年赴清的崔德中在《燕行录日记》中曾大发感慨:“闻富贵之家婚丧之节,婚时宴亲友之需,髻餙钗钏之资,动费千金;丧之棺衾葬需,饭僧诵经之费,亦计千金。若用孔雀板,则价直千金,板纹如孔雀尾,虽盛生鲜,盛夏不腐,千年不朽,而产出南京。故即今天下富大贾头郑世泰父丧,用此板云矣。”郑世泰成为富甲京师的巨商是在17世纪中叶,在会同馆经营与朝鲜的贸易。据金昌业日记载:“郑世泰,即北京买头,我国所买锦缎,皆出于郑,其价银多出十万两外……锦缎外,凡干难得之货,言于郑,则无不得者。”康熙五十九年(1720)赴清正使李宜显在日记中,对郑商的兴盛也有详载:“郑世泰,即北京大贾也,其富罕俪,我国所买锦段,皆出其家。至于世所称难得之货,求之此家,无不得者。下至花果、竹石、名香、宝器,亦皆种种具备。家在玉河桥大路之南,制作甚宏杰,拟于宫阙。为我国买卖之主,故译辈凡有大小买卖,奔走其家,昼夜如市。此人通南货,而今番货到稍迟,译辈以此故延行期,使行淹速,此人实执其权矣。”乾隆三十年(1765),作为三节年贡兼谢恩使行的洪大容对全盛时期的郑商如下追忆:“数十岁以前,使行入燕,凡公私买卖,惟有郑、黄两姓当之,皆致巨万。郑商尤豪富,交通王公连姻,又多一时清显。每我国有事,多藉其力。”由此可见郑世泰在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会同馆中朝贸易中的兴盛面相。
如前所述,郑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北京巨商,与其交结王公贵族,与名门高官联姻有密切关系。朝鲜使臣对此感同颇深:“至世泰益富,而婚娶多仕宦家,以此颇有权势。”
郑商凭借其权势与李朝使团的堂译(也称首译)、商译相互结托,掌控会同馆的中朝贸易。堂译,为贡使团的堂上译官。文献记载:朝贡使行,配堂上译官2员,堂下译官21员。堂上译官在赴清使行中担负“总察行中,主管公干”的使命,换言之,堂译统辖使行诸员役,管理使行诸事务,至于掌控使行贸易是不言而喻的。如金昌业所云:“行中大小事,首译执权,毋论我国人,虽彼人通官以下,于首译之言,无不从者……凡馆中买卖折价高下与行中聚敛多少、驿奴黜陟,皆在首译之手。自我国商贾、驿卒,至彼人中馆夫辈,待首译若待其主。”商译,顾名思义,从事“商贾买卖间”“专恃译舌”的通事。基于堂译与商译在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清商极力向堂译与商译示好。乾隆三十年(1765)赴清的洪大容亲眼所见:清商项氏不辞劳苦到山海关和家乡邦均店(今河北三河县)专程迎接堂译与诸商译,不惜破费数十两银宴请招待,目的无外乎欲多交易其货。
既便执会同馆贸易牛耳的郑世泰也极力交结堂译与诸译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赴清的谢恩副使闵镇远亲见郑商“逐日来往于译辈所在处”。同年赴清的金昌业也注意到郑商每隔三五日就到堂译、译官下塌处,每次都带鲜花、水果等。兹摘录《老稼斋燕行日记》癸巳(1713)正月的记载:“(初四日)是日,郑世泰入送水仙花,一盆种十余茎,花盛开,花大如单瓣桃花,色白有雅韵。此花曾屡次买来,而终不开,今日见之,特奇。”“(十六日)首译朴东和入海棠、梅花各一盆,谓得于郑世泰,花方盛开。海棠,即我国所谓山茶也,曾知山茶为海棠,见此益验其然。”“(十七日)崔寿昌得生荔枝五个进,伯氏、副使、书状适来,各分一个,亦送一个于余……问其出处,即郑世泰所送来。”乾隆三十年(1765),三节年贡兼谢恩使洪大容对郑商与诸译的交往也有段追忆:“且十数年前,一行入馆,郑家所以待诸译、诸商者,酒食声乐之费已不赀,寝具铺盖供给惟谨,此世泰之旧规,今已不能也。”不仅如此,郑世泰为能在会同馆中朝贸易中击败其他对手,独获贸易之利,不惜贿赂使团译官。使臣崔德中在日记中载,因郑商与使团贸易的“物货之未及来”,开市时,郑商唯恐其他清商“先其利”,遂“从中弄奸”贿赂译官金士杰银300两,私嘱金士杰,“号令甲军,牢闭中门,使商胡不得任意出入”。
郑商在全盛时,操纵会同馆中朝贸易,使朝鲜使团对其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会同馆中朝贸易中,朝鲜“所买锦缎,皆出于郑,其价银多出十万两外”。郑商囤积居奇,在贸易中,凡是奇缺难得之货,他都有储备,“凡干难得之货,言于郑,则无不得者”。使臣李宜显所言更为具体:“至于世所称难得之货,求之此家,无不得者。下至花果、竹石、名香、宝器,亦皆种种具备。”所以,“我国买卖之主,故译辈凡有大小买卖,奔走其家,昼夜如市”。因郑商所贸货物奇缺、珍奇,所以他得以操控贸易价格,“郑世泰物货高,其价不肯下,译辈落莫之状可矜”,“译官辈与郑世泰争价,犹未决”。而崔德中《燕行日记》载录更为详细:“第买卖之规,我国之人,书给物货之名,预给价银,而临行论价,故郑胡随其多买之物,增其价直,寡买之物减价,以增比减,增多减少,每致见欺,诚可痛也。”文中所云“每致见欺,诚可痛也”,是使团对郑商囤积居奇,操纵会同馆贸易价格那种无奈心情的真实流露。不仅如此,郑商因控制交易品的货源,致使朝鲜使团常因等待郑商的货物,延误使团的归期。
郑世泰掌控中朝贸易,尤其是绢织品贸易。17世纪中叶以降,会同馆贸易,朝鲜主要以白银购买清朝的生丝及丝织品。这些商品,为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即长江三角洲地区所生产。在中朝贸易中,丝织品是输往朝鲜的大宗商品。生丝在顺治年间就已输往朝鲜半岛。康熙时,输往朝鲜的清朝生丝,多由东莱倭馆转输日本。康熙十六年(1677),李朝使团在会同馆购得生丝及丝织品,归国时,“商贾车辆,倍蓰于前,弥亘数十里”。郑商深谙绢织品利益所在,控制中朝贸易中的丝织品向朝鲜的输出,形成独家代理的局面:“我国所买锦缎,皆出于郑,其价银多出十万两外。”对此,洪大容记载更为翔实:
“盖缎货皆出南方,又我国所需,皆取价贱,好尚与中国异,郑家习知之。先期贸取于南市,容入七八万两银,每年为常。织匠亦知我国好尚,缎品渐变,与中国所尚不同。”郑商为垄断会同馆丝织品对朝鲜的输出,深谙朝鲜人喜尚花色品种,甚至在每年贸易使团未到京之前,先期从江南丝绸产地预定7—8万银两丝织品,运回京师,经会同馆贸易,获得暴利。雍正十年(1732)七月,书状官韩德厚详细记载了会同馆贸易中,郑世泰等清商垄断绢织品价格的情形:“盖彼中商贾输转南京锦彩,待我国使行,方做大买卖。其初则平其直相贸,少无欺负,商译辈亦得其利矣。輓近以来,人心渐黠,巧伪日滋,谓商译辈,既远路驮载银货而来,势不可空还,遂稍稍增价而要之,迁延日时。及至行期已迫,则我人亦没,奈何只得顺其意而交易,以故其直逐年倍蓰,其弊靡有纪极。”可见,以郑世泰为首的清商抓住使团归国行期迫近,不想空持银而归,急于购物的心理,从而导致绢织品价格逐年攀升。
综上所述,全盛时期的郑世泰交结达官显贵,与名门高官联姻,以此作为资本,凭着雄厚的财力,与李朝首译、译商相勾结,采取投机性的手段,掌控会同馆对朝贸易。应当指出的是,这种贸易行为,在获得巨额利益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最终导致郑商衰亡。
三、郑商家族衰亡的原因
如前所述,笔者推断郑世泰死于乾隆十三年(1748)左右。乾隆三十年(英祖四十一年,1765),赴清的洪大容《湛轩书》载:“世泰既死,子孙世主之。”说明世泰去世后,家业已由子孙继承。乾隆四十五年(1780),赴清的朴趾源对郑商有段追忆:“郑世泰之富,甲于皇城,及世泰死,一败涂地。”是说世泰去世不久,家业很快衰败。郑商衰败的原因值得探究。
首先,郑商的衰败与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贸易发生变化有密切关联。如上所述,17世纪始活跃的东亚三国贸易,至该世纪末达到极盛,进入18世纪中叶后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东莱倭馆日朝贸易中日本银的输出减少,由此带来北京会同馆贸易中清朝生丝输入朝鲜逐渐中断。由于德川幕府采纳新井白石提出的限制银、铜等贵金属出口的政策,致使倭馆白银输出减少,这就使以中介贸易获利的朝鲜,用银作为结算手段从会同馆贸易生丝的管道断绝,从而导致会同馆的中朝贸易衰败。可见,上述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贸易发生的变化是郑商衰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郑商的衰败与李朝1746年颁布的“纹缎之禁”有直接关系。李朝贡使主要通过会同馆贸易清绢织物,郑氏全盛时,李朝使团每年从郑氏贸易的绢织品,所需银两达10万余两。郑商为获得巨额利益,在贡使团未到之前,先期从南方购入价值高达7—8万两银的绢织品。这种商业行为具有极大的投机性与冒险性。这种贸易投资是完全依赖李朝对绢织品的所需为前提,一旦李朝需求有变故,其贸易的风险性即刻显露。天有不测风云,英祖二十二年(1746),李朝颁布纹缎禁令,“自今年使行为始,上而衮服,下而朝衣,军用外,绫罗贸来者,一切严禁”,即严禁贡使团从清朝购买纹缎等高级绢织品。同年四月,进一步严肃禁令,除没有奇纹、异色的华美花样的王宫用衮服、朝服、军服外,“纹缎绫奇纹、异色纱缎、有纹花紬之类”都在禁止之列。
纹缎禁令颁布后,直接导致郑商先前从江南购买的绢织物成为滞销之货,给其以致命的打击。《李朝实录》载录了郑商得知李朝纹缎禁令的反应:“燕商郑世泰闻有新禁大惊,即报江南,止其织纹。谓我人曰:‘在汝国王,诚盛德事,吾属自此无以聊生矣。’”英祖二十六年(1750)四月十三日,英祖在欢庆殿接见从清归国的冬至三使臣,君臣对话中,言及禁纹缎令给郑商的致命打击:“上曰:‘纹缎严禁耶?’(副使黄)晸曰:‘纹缎今则不必虑矣。非但出来时,搜检之甚严,来此之后,京乡无用处矣。’上曰:‘郑世泰谓:以我国禁纹段,故大失利,其家产大不如前云,然否?’晸曰:‘……概闻失利则多云矣。’”从上述君臣对话可知,李朝纹缎禁令颁布后,确有效果。不仅在会同馆中朝贸易时,搜检之严,严禁纹缎输入朝鲜国内,即便流入国内,无论是城乡,都无人敢用,致使郑商“大失利,其家产大不如前”。对此,洪大容所言更为具体:“及我国禁纹缎,郑家所先贸者,既不见售,又中国所不用,因此而大窘,渐以消败。”可见,纹缎之禁应是郑商衰败的直接原因。
最后,郑氏子孙沉湎酒色赌戏,败其家业也是郑商家族衰败的重要因素。郑商死后,家业由其子孙承继。然而,其子孙多为纨绔子弟,热衷于吃喝嫖赌,“诸郑之年少者,又以酒色、赌戏,益败其业”。更有甚者,其子孙中,有将分得的家业败光,沦落到卖身戏场。朴趾源日记载录了郑商之孙卖身戏场,被当年世泰的伙计偶见,以千金赎回。据日记玉匣夜话条载:“有言,朝鲜商贾熟主顾郑世泰之富,甲于皇城。及世泰死,一败涂地。世泰只有一孙,男中绝色,幼卖场戏。世泰时,伙计林哥,今巨富,见场戏中一美男子呈戏,心慕之。闻其为郑家儿郞,相持泣,遂以千金赎之。与俱归家,戒家人曰:‘善视之,此吾家旧主人,勿以戏子贱之。’及长,中分其财而业之。世泰孙身肥白美丽,无所事,惟飞纸鹞,游戏皇城中。”这位“今巨富”的林哥曾是郑商的伙计,对主子有情有义,以千金将郑商之孙赎回,养育之,及其孙成人,分其财产一半与之,希望他重振郑氏家业。然而,世泰孙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惟飞纸鹞,游戏皇城中”。
郑商子孙沉湎酒色赌戏,到头来竟沦落到拍卖家产抵使团货款的地步。会同馆中朝贸易有明确规定,使团交易前,要向清商“书给物货之名,预给价银,而临行论价”。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三节年贡兼谢恩使团赴清贸易,事先郑商子孙依惯例,根据使团所列购物清单,预收价银8000余两,却未如期购到使团所需物品,却将预收使团的价银挥霍殆尽。按规定,在使团归国前,郑家必须还清货款。无奈之下,郑家子孙只好拍卖家产抵价,结果犹不足,由此引起债务纠纷。为此,郑家束手无策,日夜涕泣。首译徐宗孟见其可怜之状,出面斡旋,才使所欠之银得以减免。亲历此事的洪大容日记有详细记载:“是行,郑商受行中银,犹为八千余两,并见夺于债主,及一行将归,郑家尽卖家产,以充货物之价,犹不足,家人辈日夜涕泣。徐宗孟招诸译及下辈,凡与郑商银者,语其状,令各减三十两,以救其急。”可见,郑商的衰败与诸子孙酒色赌戏,败其家业不无关系。如赴清书状官李宜老所言:“前有郑世泰者,能主张物货,有悖子,家产今荡败矣。”
四、从郑商的兴衰透视东亚三国贸易变迁的轨迹
郑商会同馆贸易的兴衰与东亚三国贸易的变迁息息相关。东亚三国间的贸易自17世纪始活跃,至该世纪末达到极盛,18世纪中叶以降始发生变化。
17世纪以降,在会同馆中朝贸易中,李朝贡使团贸易大宗商品为清朝生丝等。这类商品,除朝鲜国内少量需求外,多通过东莱倭馆日朝贸易输往日本。如使臣闵鼎重言:“我人之贸白丝于清国者,皆入倭馆,则辄得大利。白丝百斤,贸以六十金,而往市倭馆,则价至一百六十金,此大利,故白丝虽累万斤,皆能售之矣。”可见,倭馆日朝贸易中,朝鲜交易白丝不仅数量大,而且从中可获近2倍利润。郑商全盛时,就以与李朝贡使贸易丝绸闻名于世。他深谙朝鲜人喜尚丝绸的花色品种,于每年贡使团未到京之前,先期从江南预定7—8万两银子的丝绸品运至京师,以应会同馆贸易之需。李朝贡使购入的丝绸皆以白银结算。使臣韩德厚曾感叹:“一使之行,八包之银,多则十数万两,小不下七八万两。”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副使李坤一行所带八包银9.3万两。不仅如此,就连“皇历赍咨之行入去之银,几至十五万两”。就是说,李朝贡使团每次在会同馆贸易,所需银两少则7—8万两,多则达15万两之多。这些银两,并不包括栅门后市等国境地带的走私贸易中交易的银两。史载:“沈阳、栅门开市,创设于数十年来,多赍银货,极为滥杂。”朝鲜私商携带多额之银,参与栅门后市贸易,“一年至为四五次,而每次银或至十余万,合每起使行应带八包计之,则一岁渡江之银,几至五六十万”。可见,对朝鲜而言,赴清贡使团每年要消耗银子五六十万两。对如此众多的银子外流,李朝廷臣颇多微词。雍正五年(1727),副使郑亨益归国复命,曾向国王奏言“近来矿银之流入彼中(清朝—引者),太无限节……以我有用之货,贸彼无益之物,尽归消瀜,以启奢侈,此甚可闷”,他建言:“请自今勿令入送于彼中。”朝鲜矿产资源不丰,本国自产银有限,国内流通银多来自倭馆日朝贸易,这些以清朝丝织品与本国人参等贸来的日本银,至18世纪中叶,由于德川幕府采取限制白银外流的政策,致使倭馆日朝贸易中“倭银之出来我国者甚少”。对此,《李朝实录》有如下揭示:“英庙丁卯(1747)以前,清人不与倭人互市,故倭人之贸唐产者,必求之东莱,以此莱府银甲于他处,行于国中者,多倭银,国中诸矿产亦丰,而不许赴燕交易。其后清人与倭通市,倭人直至长崎岛交易,而不复向东莱。于是遂专用矿银,产亦渐减于昔,自此国中银大绌。”这里将日朝贸易中,日本银向朝鲜输出减少,归于中日长崎直接通商,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但至少说明18世纪中叶以降,日本银输入朝鲜明显减少则是实情。
日朝贸易,因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而中断。战后,经依存朝鲜贸易的对马藩从中斡旋,李朝遂与德川幕府于1607年复交,并于庆长十四年(1609)与对马藩签订《己酉约条》,由此倭馆日朝贸易再开。倭馆贸易中,日本输入品主要为朝鲜产人参、清朝产生丝等,其中生丝中上等品的白丝,为输入大宗。换言之,李朝贡使团从会同馆贸得生丝等“燕货”,大多(至少至18世纪中叶为止)经倭馆日朝贸易输出日本。上述生丝与人参,两者约占倭馆对日贸易输出额90%。朝鲜输入品:主要是日本银(丁银)、铜、锡等矿产品,占输入品总额80%。其中,日本银输入占55%左右。可见,日本银为朝鲜输入主要商品。
然而,日本自宽文(1661—1672)以来,国内的银、铜产量逐渐减少,德川幕府为限制本国金、银、铜外流,采纳新井白石提出的限制银、铜等贵金属出口建议,下达了“贞享令”(贞享三年,1686)。此限制令不仅对中日长崎贸易有重大影响,对倭馆日朝贸易也产生严重影响。不仅如此,日本货币改铸,对三国贸易造成极恶劣的影响。17世纪末以降,日本对输出白银几度改铸,严重影响白银输出。改铸前,对马藩输出白银,为德川幕府铸造纯度达80%(银80%,铜20%)庆长银,朝鲜称丁银。但元禄八年(1695),德川幕府为降低货币成色,增加货币流通量,采纳勘定奉行荻原重秀改铸货币的建议,竟然将纯度80%庆长银,改铸为纯度64%元禄银,导致银质量迅速下降,随之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宝永四年(1707),日本又铸造更加恶劣的“宝银”(宝永三年改铸银,纯银度50%)。李朝政府对日人的欺瞒极为不满,正德元年(1711),日本只好又铸造纯银度80%的“特铸银”。但特铸银因京都银座(特铸银铸造所)对马藩的供给不畅而有所减少,1710—1714年间,年平均1028贯,之后的1738—1747年间,年均只有383贯,至1755年其铸造被停废。与此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清生丝输入增加,致使东亚三国贸易中生丝的输入受到严重的冲击。东印度公司于17世纪末始在广东输入生丝等,与葡萄牙、荷兰争夺贸易主导权,后英船从事非法贸易,生丝输出日渐激增,从而导致清朝国内生丝价也随之腾贵。为此,清廷一度禁止生丝对东印度公司输出。由于英商请求,清廷才允许输出。有学者统计,在清朝生丝总输出量中,东印度公司所占比率最高。乾隆十五年(1750)为59%,乾隆四十八年(1783)为70%,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83%,以这样的增长率,最终东印度公司独占了广东贸易。这样一来,朝鲜通过会同馆中朝贸易输入的生丝日益减少,转运至倭馆日朝贸易的生丝也随之中断,东亚三国贸易衰退之势已成定局。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
责编|于凌
网编|陈家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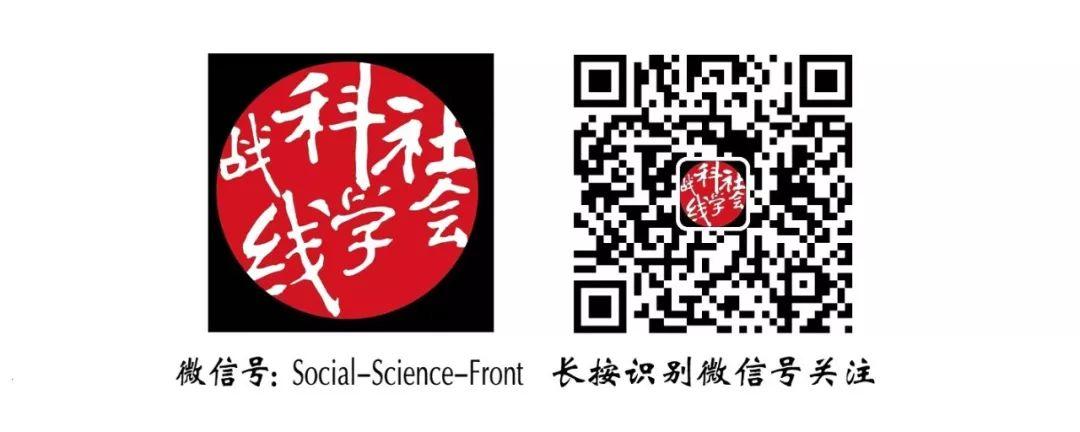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社会科学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