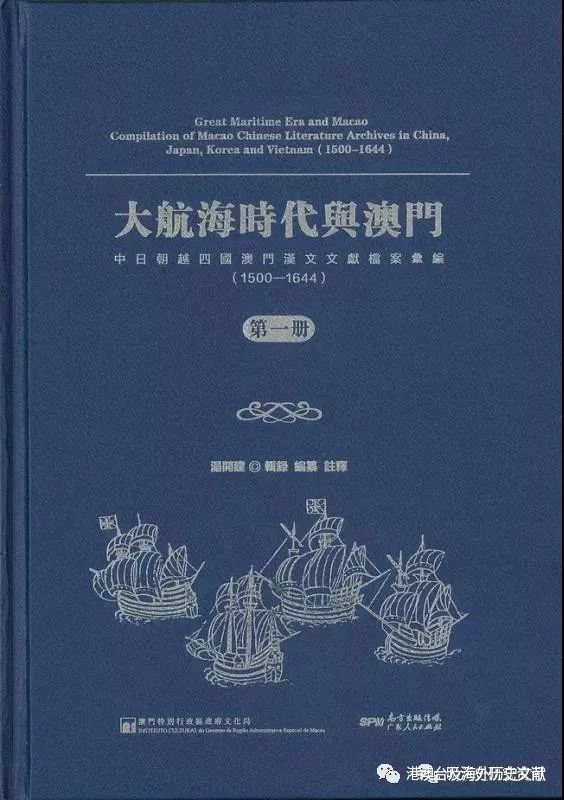
作者:汤开建
出版社: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
该文经作授权在本公众号刊出。
本书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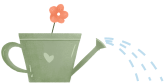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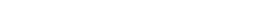
(一)
從東方而言,中國和日本是參與大航海活動的最主要代表。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並不是海洋國家,但從宋元以來,由於海外貿易的發展促使了中國航海業的興起,而明永樂至宣德時期的鄭和下西洋,毫無疑問為中國後來的大航海打通了通往西方世界的新航線。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大航海”應始於明成化、弘治以後,據有關統計,明朝從建國開始,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門之前,一共頒布過15次“禁海令”。明朝中央政府頒布的禁海政策,從洪武時“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到嘉靖時“片板不許下海”,嚴格禁止人民對外通商貿易,限制外國人到中國進行貿易。這導致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以海洋為生的民人經濟上的嚴重困境,出於謀生的需要,他們私自下海,遠帆通番。剛開始下海通番者人數並不太多,但由於當時下海的通番船隻已經遠達印度的古里地區,據巴羅斯(João de Barros)的《亞洲旬年史之四》稱:“當時華人航行印度海岸,因為香料貿易的緣故,他們在那裡有自己多處商站(rias)。” 1510年葡萄牙人攻佔滿剌加後,華人下海通番船隻也來到了滿剌加,“去年有四艘中國式帆船從中國來到這裡,所帶貨物不多,他們接踵前來窺探本地。”這些私自下海通商的商人們,在印度和滿剌加與葡萄牙人通商後獲得了較好的利潤,並將這些資訊帶到中國沿海各地,明人周玄瑋稱:“閩廣奸商,慣習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爲主,中載重貨,餘各以己資市物,往牟利恆百餘倍。”明人洪朝選言:“嘉靖甲辰,忽有漳通西洋番舶,爲風飄至彼島,迴易得利歸,轉相傳告。”說明漳州海商在嘉靖前就與西洋通商,而且獲得很高的利潤。故到明朝成化、弘治以後,下海通番者就越來越多,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如“成化二十年(1484)十二月辛未,有通番巨舟三十七艘泊廣東潮州府界”。一次通番的巨舟就達37艘之多,可以反映當時通番人數之眾。又如“正德九年六月丁酉,近許官府抽分,公爲貿易,遂使奸民數千駕造巨舶,私置兵器,縱橫海上,勾引諸夷,爲地方害。”奸民數千駕造巨舶,在海上通番,可以反映當時通番規模之大。到嘉靖時,下海通番的規模與數量更是令人吃驚,以致當時的寧波知府曹誥捶心頓足地大喊:“今日也説通番,明日也説通番,通得血流滿地方止。”在明代成化、弘治以後的中文文獻中,“泛海通番”、“私通番舶”、“私通番貨”、“下海通夷”等詞比比皆是,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民間海商集團遠洋航海事業的繁盛。
這些所謂的通番下海者,在明政府的眼中均視為“奸民”,更多地被視之為海盜。但實際上,這些下海通番的人最初都應該是海商,當明政府禁止他們通商時,他們就轉為海盜,而互市貿易開通之時,這些人亦都變成了海商。正如萬曆時期福建巡撫許孚遠所稱:“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市禁則商轉而爲寇。”稍後的徐光啟亦稱:“於是多有先期入貢人船踰數者,我又禁止之,則有私通市舶者。私通者,商也。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又從而嚴禁之,則商轉而為盜,盜而後得為商矣。”這些海商們駕駛着自己製造的巨舶大艦揚帆遠洋,北上日本,南下南洋,甚至遠至印度半島的西洋古里、西洋瑣里(即葡屬印度)一帶,展開了他們為利甚巨的海上貿易。於是,導致了嘉靖“大倭寇時代”的出現,最早的徽商海上貿易集團出現了,如許棟兄弟集團、王直、徐海集團;最早的閩商海上貿易集團出現了,如李光頭(李七)集團、洪迪珍集團;最早的浙商海上貿易集團出現了,如毛海峰集團;最早的粵商海上貿易集團出現了,如何亞八集團、吳平、曾一本集團。這些屬於民間的中國海商集團規模都很大,如朱紈《甓餘雜集》所載,據“浙海瞭報,賊船外洋往來一千二百九十餘艘”。而王直集團更是這批海商集團中規模最大者,明萬表《海㓂議》稱王直:
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歩,容二千人,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僣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兵十餘道流劫濵海郡縣。
郭棐《廣東通志》稱,曾一本集團“率眾數千,乘船二百餘艘,突至廣州。”中國東南沿海的私人海商集團在隆、萬之際,雖然遭到了明朝政府的嚴厲鎮壓,但私人海商集團的海外勢力並沒有被明王朝的鎮壓而遏止,反而他們的勢力更向海外拓展,如林道乾集團在柬埔寨、暹羅,林鳳集團在臺灣、呂宋。至於天啟後崛起的鄭芝龍集團,到天啟七年(1627)時,在海上已經擁有約400條帆船,60000至70000人;到崇禎時,“海盜一官在中國沿海擁有1000條帆船,稱霸於中國海;方圓20荷里內,人皆避之。”。鄭芝龍不僅稱霸海上,而且大規模地同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以及東南亞商人展開通商貿易。據荷蘭東印度公司報告:
鄭芝龍每年往大員向荷蘭東印度公司提供1400擔生絲、5000擔糖、1000擔蜜薑、4000擔白色吉朗綢、1000件紅色吉朗綢,價值總計300000里耳,而鄭芝龍將得到3000擔胡椒的供應。
在崇禎四年(1631)到崇禎十三年(1640)鄭芝龍集團的“黃金時期”,就有不少於325艘的中國帆船駛抵馬尼拉貿易。明人鄒漪《明季遺聞》記載:
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列入二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可敵國。
鄭芝龍集團成為中國東南沿海最大的海商集團,其通商範圍廣及東洋、南洋各地:大泥、浡泥、占城、呂宋、魍港、北港、大員、平戶、長崎、孟買、萬丹、巴達維亞、馬六甲、柬埔寨、暹羅。
中國海商集團這種亦商亦盜的海上活動,成為了東方大航海的主流,而且這些海商集團大多又與西方的貿易船隊聯䑸合流,共同推動這一時期的海上貿易的發展。嘉靖時,“許一、許二、許三、許四勾引佛郎機國夷人絡繹浙海,亦市雙嶼、大茅等港”。嘉靖時,“海寇何亞八、鄭宗興潛從佛大坭國引番舶與陳老、沈老、王明、王直、徐銓、方武等合䑸入寇”。天啟時,“紅夷一小醜,狡焉挾市,封豕長蛇,薦食閩疆,且勾寇首劉香,薩倭渠魁李大舍,合䑸橫掠於海上。” 可以說,從嘉靖時被稱為“海上之王”的王直,到崇禎時建立龐大海洋帝國的鄭芝龍,這一批又一批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成長和發展起來的極為龐大的民間海商集團,他們跨海過洋、縱橫萬里,成為中國“大航海時代”之俵俵者。
東方的大航海活動除了中國海商的大規模下海通番外,還應包括琉球、日本、暹羅、滿剌加及越南等國的海上貿易活動。琉球應是除中國以外最早參與到東亞海域大航海活動中的重要國家。琉球本身就是一個由眾多島嶼組成的海洋之國,從14世紀後期一直到16世紀初期是琉球王國最繁盛的歷史時期,該國國民穿越東亞和東南亞海域,積極發展對海域周邊國家的集散貿易,他們不僅與中國、日本保持着密切的貿易關係,而且還開展了維持朝鮮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頻繁的貿易活動。以滿剌加而言,琉球早在明天順七年(1463)開展了對滿剌加的貿易活動,並留下了國王諮文;成化九年(1473)琉球國再次派船到滿剌加貿易,因遇風浪漂到廣東香山港;正德五年(1510)琉球又派一艘有水梢兩百人的船隻裝載瓷器等物前往滿剌加購買胡椒、蘇木等物。據《歷代寶案》的資料顯示,琉球從15世紀晚期就有船隻從那霸前往北大年貿易,在1514到1530年間,這種航海貿易活動進行得極為頻繁,而這些貿易都發生在葡萄牙人到達這一地區之前或剛剛到達這一地區之時,反映了琉球商人在東亞海域航海活動中的前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所謂琉球商人大多是早期移居琉球的福建人。
日本也是一個海洋之國,海岸線長,沿岸航路發達,因此遠距離的物資輸送量相當可觀。但日本早期的航海業大多還僅局限在近海航行,雖然有大量的倭寇船隻進入中國海,甚至抵達東南亞海域。但到15世紀為止,日本人的渡航目的地基本限制在中國寧波、朝鮮三浦、琉球那霸這三個地方。日本海上活動的大規模南下,應始於歐洲人東來以後,就在17世紀前30年間,總計有超過356艘以上朱印船從日本列島往東南亞方向航行。這些朱印船前往交趾有71艘;暹羅有56艘;呂宋有54艘。1592年,豐臣秀吉創立朱印船制度,是日本海外貿易史上一大創新。它表明日本政府開始重視海外貿易,並支持日本商人向海外發展。統治者專門給前往海外貿易的船隻頒發“朱印狀”。所謂的“朱印狀”,是指交給商船標有航行目的地等的證明文件,這種文件證明持有它的船隻是普通的船隻,不是海盜船。在某種程度上,它是日本商船的“護身符”。此外,英國人威廉·亞當斯(三浦按針, William Adams)在1600年適時漂流到日本,後來成為德川家康的外事顧問,也提陞了日本的造船與航海技術,並打開了日本人的眼界。西洋的船隻結構部分應用到日本的遠洋船隻上,先進的航海儀器引進了日本,葡萄牙人的領航員被朱印船大量使用,這些都加強了日本對外延伸的能力。加上進入十七世紀以後,中國和西洋商船的不斷到來日本,都刺激了德川家康尋求日本對外擴大視野的興趣。據西川如見《增補華夷通商考》,當時與日本通商貿易的國家除中國外,主要有朝鮮、琉球、大冤、阿媽港(澳門)、東京、交趾、占城、柬埔寨、大泥、六坤、暹羅、滿剌加、莫臥爾(臥亞)、咬留吧(巴達維亞)、爪哇、番旦、阿蘭陀等國。在這一時期,日本方面也出現了一批專為經營跨國遠洋貿易的著名商人集團,如開闢新西班牙航線的田中勝介,專門從事安南貿易的京都商人集團角倉了以,長期從事臺灣、安南、暹羅等地貿易的長崎商人集團末次平藏,以及專門從事菲律賓群島和印度支那地區的大阪商人集團末吉孫左衛門等。日本商人的朱印船在政府的支持下大規模地進入了東海、南海及印度洋區域,正如1597年進行全球航行的義大利商人卡萊蒂(Francesco Carletti)所言,日本人會利用一切手段,冒著極大的危險,到各式各樣的地方闖蕩。當然,這一時期活躍在西太平洋海域中展開東西方貿易活動的還有朝鮮、安南、暹羅、柬埔寨等國的海商。
16世紀中葉以後,南海首先進入東亞海域大航海活動的巔峰期,其貿易熱潮也順勢擴大到東海,甚至北進日本海域,南下東南亞海域。在這些區域內,華人(包括華裔琉球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海商聯結起來,結合為一體,構成了東亞海域內龐大的貿易網絡。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華人海商成為了這一貿易網絡中最為重要的主體,人數眾多的華人海商駕駛著大小中國“戎克船”(Junk)馳騁在上述海域,南來北往,東西鉤連。初是下海通番、通夷,繼而壓冬留寓,一批一批的華人隨著“大航海”活動移民海外。最早應是1500年前後出現於滿剌加的“中國村”(Kampung Cina),該區包括有一兩條街道,其首領稱蔡喇噠(Cheilata)。16世紀中葉在日本的平戶、博多、長崎,則先後出現了“大唐街”,“皆中國人所居也”;在馬尼拉,則出現“澗內”、“八連”及“大明街”等華人聚居區,“中國人賈以數萬”;16世紀末在爪哇島的萬丹也出現了“唐人街”;而在巴達維亞,則出現“班芝蘭”(Pantjiolen)的華人聚居區,據道光初年完成的《咬留吧總論》記載,“唐人約有十萬三”。而當時往葡萄人居住地澳門的華商則更多,“閩粵商人,趨之若鶩”。到崇禎時,僅聚居澳門的福建商人就達數萬人之多,“閩之奸徒,聚食於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其他如越南會安,暹羅大城、六坤、大泥,馬來西亞滿剌加,印度尼西亞的三寶壟,在明中葉後的大航海活動中,都有大量的華商及其家人移居該地,而形成了後來的南洋華僑社會。不僅華人大規模移民海外,日本人也出現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在很多東南亞各地的港口和城市出現了日本人居住的街區或日本城,在最鼎盛之時,移居呂宋的日本人有3000人之多,移居暹羅的有1500人之多。當時也有很多日本人移居澳門,據中國文獻記載稱:澳門葡人“收買健鬥倭夷以爲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隨着這一時期大航海活動的發展,亞洲各國之間的大規模移民亦同時出現。
從西方而言,位處於大西洋岬角的葡萄牙是最先衝破驚濤之險奔赴東方的歐洲國家。15世紀末16世紀初即進入印度,佔據印度半島東南部馬拉巴爾海岸一線,1509年,葡萄牙人首次從海上抵達南洋群島,海軍將領狄奧戈·薛奎羅(Diogo Lopes de Sequeira)率領船隊來到蘇門答臘大島的北部,訪問了陂堤港(Pedir)和巴西(Pasei)。1510年,葡萄牙軍攻佔印度果阿(Goa),遂在此建立要塞,並以此為葡人東進之根據地。1511年,首任葡印總督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Afonso de Albuquerque)率由19艘戰船組成的葡萄牙艦隊攻佔滿剌加,控扼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馬六甲海峽。同年,又派遣安東尼奧·阿佈雷烏(António de Abréu)率3艘船去馬魯古(Molucas, 即摩鹿加群島)、班達島(Banda Island)、索洛群島(Solor Islands)及帝汶島(Timor Island)。1512年,又派船往德那地(Ternate)進行丁香貿易。根據葡印總督阿豐索·阿爾布科爾科發回情報稱:
中國是瓷器和絲綢的巨大出口國,同時也出口麝香、大黃、珍珠、樟腦和明礬。中國市場定期大量吸收的是胡椒。在此資訊的基礎上,葡萄牙王室很快便制訂了一個全面進入東亞的計劃,尤其是進軍中華帝國,他們已把中國視作最有潛力和最突出的商業夥伴。
於是,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制定了一個在中國海岸進行領土定居的雄偉計劃:
主要是建立堡壘和海上軍事力量,並採用當時在波斯灣某些地區、印度西海岸和馬來亞半島的模式。國王準備將此作為商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運作,使中國南海岸與東南亞的主要港口城市連接起來,再將其中一些商業活動引至歐洲。該計劃的第一步即組織一個龐大艦隊前往中國。
明正德八年(1513)1月,滿剌加要塞司令路易·布裡托(Jorge Rui de Brito)船長委派歐維士(Jorge Álvares)搭乘一艘中國帆船滿載胡椒前往中國。儘管歐維士未能進入廣州港,但卻做了一筆利潤豐厚的生意,滿載中國貨物返回滿剌加。正德十一年(1516),葡印總督羅博·阿爾伯加瑞亞第三次派遣使節杜阿爾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出使暹羅,並與暹羅簽訂了第一個葡暹條約,即允許葡萄牙人在暹羅居住,並可在阿瑜陀耶京、那撒琳(Tenasserim)、墨規(Morqui)、北大年及六坤(Nakon Sri Tammarat)等地經商。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派遣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出使中國,這一使團歷經坎坷,雖然大使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已經到了北京,但與中國政府建立自由通商貿易的要求卻遭到了失敗。明嘉靖二年(1523),葡萄牙人西蒙·阿不留(Siãmo de Abréu)率領船隊航行至西裡伯斯島(Celebes,即蘇拉威西),目的是要探清海路和貿易路線,從而將滿剌加與婆羅洲連接起來。明嘉靖三年(1524),葡印總督瓦斯科·伽瑪(Vasco da Gama)派遣葡萄牙船長杜阿爾特·科埃略由海路來到交趾支那的海濱城市會安。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葡萄牙正式進入日本,隨即開闢了當時世界上最長的一條貿易航線——葡日貿易航線,展開了極為頻繁的葡萄牙與中國、日本之間的貿易。據葡萄牙學者羅理路(Rui Manuel Loureiro)的研究稱:
從1544年開始,葡萄牙人航行日本的次數劇增,很快形成了一個十分盈利的三角貿易,連接滿剌加與中國港口,然後再與日本港口連接起來。當時貿易的主要貨物是馬來群島的胡椒,用以交換中國的絲綢,再以中國的絲綢交換日本的白銀,繼而再用白銀交換絲綢,用絲綢交換胡椒。當時貿易的貨物還包括硫磺、硝石、水銀、麝香、武器、扇子及其他產品,這一三角貿易則最占數量。當時在最東方的航線上經商的多數是葡萄牙私商,也有葡萄牙王室的船隻。他們是葡萄牙人在亞洲的重要部分。
從1546年到1617年間葡萄牙每年均有船隻從印度果阿前往日本進行貿易,多則4艘,少則1艘。這一時期日葡貿易航海主要使用的是葡萄牙東印度大船,這種船隻一般都在800噸以上,有的甚至達到1200到1600噸。1618到1640年間的日葡貿易的方式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笨重的大黑船改為200到300噸的中等平底帆船進行運輸,所以每年往日本貿易的船隻數量增多,多則8艘,少則3艘,而且貿易量也大增,據學者統計,16世紀後期葡人每年從日本運回的白銀只有50到60萬兩,而到17世紀20年代前後葡萄牙人從日本運回的白銀則高達350到430萬兩。
西班牙獲得了西半球的保教權以後,以新開闢的美洲大陸中部的墨西哥城為據點,橫渡太平洋,也開始了對東方世界的侵佔和掠奪。到16世紀70年代時,西班牙人的勢力不僅控制了當時的美洲大陸的大部分地方和島嶼,而且將其殖民統治橫跨太平洋進入菲律賓群島,並建成了以馬尼拉城為中心的亞洲據點。從此,西班牙人開闢了墨西哥至馬尼拉的跨太平洋航線,同時北進臺灣、琉球、日本,南向馬魯古群島及東南亞諸地,且與葡萄牙展開激烈的競爭,力圖打開中國的大門,搶佔中國市場。至此,馬尼拉城與中國福建、與中國廣東和澳門,甚至日本與新西班牙(日本稱濃毘須般),一條又一條的新航線被開闢,當然其中最重要的還是馬尼拉與中國福建地區的貿易。福建地區的華人與馬尼拉的貿易在很早以前雖已出現,但華人貿易大規模地進入呂宋貿易則是隆慶海澄開港“準販東西二洋”及西班牙人控制馬尼拉以後,1572年福建華船到馬尼拉貿易的衹有3艘船隻,到1583、1584年時就增加到30艘左右。1588年後每年至馬尼拉的中國船多時為40餘艘到50餘艘,少時則為10餘艘到20餘艘不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中國福建與菲律賓貿易全部由華人船隻來承擔,並沒有馬尼拉的西班牙船前往中國福建。華人滿載着西班牙人需要的絲綢、瓷器、糧食及其他生活用品前往馬尼拉,而西班牙人則將從新墨西哥運來的白銀與其交換。這樣華商與西班牙商人的貿易一方面成為了解決馬尼拉西班牙人全部生活品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馬尼拉又成了中國與新西班牙貿易的中轉站,並將中國的絲綢等貨運往新西班牙。1580年葡萄牙被併入腓力普二世統治的西班牙帝國時,他們在東亞海域又開闢了馬尼拉到澳門的航線。從1583年,葡萄牙船長囉嗚衝·呚呧呶(Bartoloméu Vaz Landeiro)的代理人若爾熱·莫沙(Sebastião Jorge Moxar)從澳門開始了首航馬尼拉的貿易,帶去了大量的棉織品、絲織品、橄欖油、葡萄酒及中國點心等貨物,以交換白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因此而大獲其利。1584年,囉嗚衝·呚呧呶又帶了兩艘船航行馬尼拉,並載有大量貨物。但是這條航線的開通,多次遭到了各方的阻擾,並非每年都有船隻航行,直到17世紀後澳門與馬尼拉的航行纔開始逐漸增多,據學者統計,17世紀前42年,澳門與馬尼拉的航船總數為82艘,平均每年近2艘(其中有多年是沒有船隻航行記錄)。澳門的商船將中國的絲綢、錦緞、瓷器及印度的紡織品運到馬尼拉,再轉運到新西班牙,而從馬尼拉運回的主要是西屬美洲的白銀。1602年一位南美的主教稱:“菲律賓每年輸入二百萬西元的銀子都轉入中國人之手。”這裡面應該是包括了由福建華人帶回中國和澳門葡萄牙人轉入中國的白銀總數。此時的太平洋上,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大黑船(日本人稱之為南蠻船)東來西往,絡繹不絕,呈現出無比的繁榮。
新興崛起的低地尼德蘭國家荷蘭也迅速地加入到這一搶奪東方市場的競爭中,從16世紀90年代起,荷蘭商人們即開始了準備遠航亞洲諸港口的計劃,中國和香料群島是最重要的目的地。1594年,荷蘭第一家公司“遠方公司”(Compagnie van Verrre)成立,為建立與東方的貿易,翌年便派遣船隊遠航東方。荷蘭人第一次遠征東方的船隊由4艘船隻組成,司令官是曾在里斯本經商的霍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荷蘭艦隊進入遠東第一個據點就是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上的萬丹,然後將目標指向中國,希望在中國東南沿海地方找到一個據點,但這一企圖卻沒有成功。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後,首先在爪哇島上的巴達維亞城建立了該公司的東方根據地,他們駕駛着船身更為高大、幡帆更為眾多、速度更為快捷的艦船乘風破浪闖入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海域,到1621年時荷蘭在亞洲管治領土及勢力範圍含括有印度半島、印支半島、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他們或在這些地方設有商棧,或建有要塞,或在這些地方進行貿易活動。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荷蘭人企圖搶奪葡萄牙人控制下的澳門,攻佔澳門的計劃失敗後,又佔領了中國的澎湖。最後在中國軍隊的圍逼下,於1624年8月26日,荷蘭艦隊司令官宋克(Martinus Sonck)命令拆毀澎湖城堡,並率領所有船隻和人員攜帶各種物品正式撤離澎湖,退守大員,佔據臺灣。荷蘭人佔據臺灣後,不斷派出船隊在福建沿海地區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其中與鄭芝龍集團貿易規模巨大,雖然遭到福建當局的拒絕與干預,但從1635年直到1644年明朝的滅亡,福建地方的中國人與臺灣及巴達維亞的貿易一直順利地進行。據1636年1月4日和12月28日的巴達維亞城報告稱:“近來,自由暢通地從中國到大員的貨物運輸日益頻繁,所有運去的現金幾乎全部令人滿意地用掉。”曹永和先生根據《大員商館日記》統計,在1636年11月至1638年12月的兩年零兩個月時間里,共有334艘中國商船前往臺灣貿易。它們運載大量的生絲、砂糖、瓷器、絲綢、布匹、大米、黃金以及磚石木柱往臺,運回的是胡椒、銅、鉛、鹿肉以及各種壓艙物。1644年,抵達巴達維亞的中國商船一共8艘,輸入貨物3200噸,但這些商船自巴達維亞運返中國的貨物,由1637年至1644年,每年衹有800-1200噸。
荷蘭人不僅開通了臺灣至福建沿海和福建至巴達維亞城的貿易航線,而且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隊還以阿蘭陀的名義遠航日本,並開闢巴達維亞至臺灣、琉球再至日本長崎的貿易航線。1607年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司令彼得·韋爾霍夫(Pieter Verhoeff)率領一隻由13艘艦船組成的船隊離開歐洲前往東方,其中有2艘船滿載絲綢、胡椒和鉛從巴達維亞航抵日本,要求通商,但遭到拒絕。“慶長十四年(1609)八月甲戌,南蠻阿蘭陀國貢獻駿府,賜書於彼國主,許其每歲到肥前平戶而商舶交易。”同年荷蘭在平戶設立商館,後於寬永十八年(1641)又將平戶的荷蘭商館遷往長崎出島。荷蘭每年派商船到日本進行貿易,運往日本的貨品主要是絲綢和鉛、錫,而運回巴達維亞則以白銀居多。當時福建人李光縉《景壁集》則稱:
和蘭人富,少耕種,善賈,喜中國繒絮財物,往往人挾銀錢船以出,多者數百萬,少者千餘,浮大海外之旁屬國,與華人市,市漢物以歸。
荷蘭人挾銀錢數百萬進行貿易,可以反映荷蘭輸入中國的主要的還是白銀。據西方學者統計1622-164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日本輸入亞洲的白銀總值26,498,753荷蘭盾,平均每年1,892,768荷蘭盾。這些荷蘭人從日本帶入亞洲的白銀又是通過與華人的貿易而進入中國市場。這一時期荷蘭人駕駛着“荷蘭舶”、“紅毛船”,還攜帶着威力強大可以洞石穿城的“紅夷大礮”,欲與西、葡一比高下。
英國東印度公司來到東方,稍晚於上述歐洲海上強國。當葡萄牙商人在遠東貿易中獲得巨額利潤時,引起了英國人的注意。1600年在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支持下成立東印度公司,目的就是要展開對東方的大規模航海及其貿易活動,以打破葡萄牙人對遠東貿易的壟斷局面。1602年與爪哇島上的萬丹土王簽約並在此建立商站;160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到達印度半島西岸的蘇拉特(Surat);1611年在印度南部的馬蘇裡帕塔姆建立商站;1612年在蘇拉特、阿瑜陀耶、北大年及印度尼西亞東部的望加錫建立商站。慶長十四年(1609)七月,獲日本德川幕府頒賜朱印,允許航海來日本貿易,慶長十八年(1613)八月,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隊攜帶國王文書,向德川幕府進獻猩猩絨、弩砲、望遠鏡等方物,九月德川家康復書稱:“伊袛利須(英吉利)舩到日本,不問何港,愛護無他,賜邸江戶,地基任其所請。”故英國在平戶設立商館,展開對日貿易。但英國在日本的貿易並不成功,平戶商館設立不足十年,至元和七年(1621),即“以無利潤故止通商”而關閉商館。英國人對中國的最初影響應是萬曆四十八年(1620),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獨角獸號”(Unicorn)追擊澳門葡萄牙船而遭遇颱風,該船沉沒於廣東陽江海面,廣東地方政府組織人力從該船上打撈了數千匹西洋絨布和36門紅夷大礮,這一事件在中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而英國第一次正式航行中國,則是在崇禎八年(1635)。該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倫敦號”(London)在果阿與葡印總督簽訂協議,去中國不直接參與對華人的貿易,並要求從澳門帶回葡屬印度所需要的銅和澳門博卡羅鑄礮廠生產的火礮。這一次航行從英國來說主要目的就是要讓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中國建立直接的貿易關係,但在葡萄牙人的干預和監管下,加上廣東政府拒外國人於國門之外的態度,這一計劃並未獲得成功。崇禎十年(1637),當時的中國官員還將英國人誤認為是“紅毛荷蘭”的時候,東印度公司4艘船隻在威德爾(John Weddell)上校的率領下來到澳門,並不顧一切地闖進廣州,委託華人通事、牙行展開貿易,但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和驅逐。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遠東航海和貿易比較而言,英國東印度公司早期階段在東亞海域的航海和貿易都處在不利的地位,其在各地的貿易所獲得的利益遠遠不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
歐洲列強們在東亞海域爭雄鬥勝、叱吒風雲,西人、西力、西風滾滾而來,勢不可擋。而在這一系列西力東漸的大航海活動中,無論哪一個國家,最後都無不以打開中國廣袤市場,開展同中國的自由貿易為其主要目標。然而,要打開中國市場開通與中國的貿易必須要在中國的周邊尋找一個根據地。葡萄牙人從16世紀第一個10年開始就在尋找這一據點,先是廣東的上川、浪白,然後福建的月港、浙江的雙嶼,他們與中國東南沿海的私商集團及日本、東南亞等地的海商勢力聯合起來,在這些地方建起了一個又一個的貿易據點,但最後均被明朝官方禁海派給摧毀。經過了長達40餘年在中國東南沿海海上航行的周折,最後於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在廣東珠江西岸香山縣的“濠鏡澳”地方獲得了“僑寓”的權利,葡萄牙人稱之為Amaquam ,華人稱之為“亞媽港”,同時期的日本人稱為“阿媽港”。澳門就在東亞海商勢力發展的鼎盛之時即所謂“嘉靖大倭寇時期”而誕生。
澳門開埠以後,葡萄牙人“舉國而來,負老擕幼,更相接踵,夷衆殆萬人矣”;“夷人戀居射利,居者、行者往來相錯,漸成都市。廣袤二舍,聚居近萬人,傭販賈客倍之。”很快就在中國的南海之濱建成了一座“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高居大廈,不減城市”的地中海式歐洲城市;甚至有人稱:“今聚澳中者,聞可萬家,已十餘萬衆矣;”更有人稱澳門:“邇來不下數十萬人矣。”從“殆萬人”到“近萬人”到“已十餘萬衆”再到“不下數十萬人”,反映了澳門這個“海濱彈丸地”在葡萄牙人開埠後城市發展變化之迅速。
不僅澳門城市人口發展迅速,而且通過葡萄牙人海上貿易,澳門人財富積累之快亦令人咋舌。一艘艘飛揚跋扈的葡萄牙大黑船“十二帆飛看溜還”,一個個富可敵國的葡萄牙商人“珴珂衣錦下雲檣”。明人周玄瑋稱:“廣屬香山爲海舶出入襟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並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明人羅大紘稱澳門“商與夷為市數千人,金錢不下數十萬”。甚至澳門的耶穌會士也因為參與對日本貿易而發財,“香山濠鏡澳,有三巴和尚者巨富。”萬曆十九年(1591)時,明人王臨亨親眼所見:
西洋古里,其國乃西洋諸番之會。三四月間入中國市雜物,轉市日本諸國以覓利,滿載皆阿堵物也。余駐省時,見有三舟至,舟各齎白金三十萬投稅司納稅,聽其入城與百姓交易。……然夷人金錢甚夥,一往而利數十倍。
三艘葡萄牙船一次載來的貨物,其價值就高達白金九十萬,反映了澳門貿易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利潤之豐,以致通過海上貿易而使澳門很快地富裕起來。1582年完成的《市堡书》即稱:“可以预计,不久之后,澳門将成为这一带最富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到1635年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完成《要塞圖冊》時則稱:“澳門市是東方最繁華的城市之一,與各地來往貿易興隆,有大量的各種財物和珍貴物品。……他們比那個印度州的任何地方的人都富有。”
澳門,在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還是一座沒有任何行政村落無人居住的荒島,為什麼這一“滿地都是突出巌石”的荒島,在16世紀中葉後很短的時間內就發展成為一座人口眾多、極為繁華富庶的城市呢?其根本原因就是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在東亞海域極為發達的大航海活動,推動了葡萄牙人的澳門這一國際貿易港口的發展與繁榮。15世紀末葡萄牙人東來以後,一直將發展中國貿易為其主要商業目標,而最終選擇澳門為其遠東貿易的根據地,是有着極為重要的原因的。首先,澳門位處於當時世界上最為漫長和繁榮的葡日貿易航線的中間段上;同時又是澳門至馬尼拉至墨西哥之太平洋航線的起點;17世紀後,葡萄牙人還開闢了澳門至中南半島上的安南、交趾、暹羅、柬埔寨及印度尼西亞群島上的萬丹、望加錫、巴達維亞、帝汶等短途航線;而這些航線的開通則使澳門成為了葡日貿易、西葡貿易和澳門與東南亞貿易中最為重要的中轉站、始發站和商品集散地。其次,由於澳門地處珠江出海口的西岸,背靠廣州,而廣州不僅“金银遍地”,還被西方人稱之為“世上再无此富裕之地。”它是中國內地十幾個省貿易貨物的集散地,可以說廣州是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市場。荷蘭人努易茲關於中國貿易報告稱:
中國物產是這麼豐富,它可以充足地供應全世界某些貨物。漢人將全國各地的貨物送到易於脫售的城市或港口。……然後又送到澳門和廣東的市集,但是商品這麼多,葡萄牙人根本買不完。
特別是明中葉以後,在明朝與西洋的貿易中,廣州是唯一合法對外開放的港口。克路士(Gaspar da Cruz)《中國志》載:
因為自1554年以來,萊昂尼·德·索劄任少校,和中國人訂立條約說我們要向他們納稅,他們則讓我們在他們港口貿易。從此後我們便在中國第一港口廣州作貿易。中國人帶著絲綢和麝香上那兒去,這是葡人在中國購買的主要貨物。
明人霍与暇《勉齋集》言:
凡番夷市易皆趨廣州,番船到岸,非經抽分,不得發賣。……每番船一到,則通同濠畔街外富商搬瓷器、絲棉、私錢、火藥違禁等物,滿載而去,滿載而還。
而將澳門與廣州兩地貿易緊密相連的方法就是“上省”與“下澳”。“上省”就是指葡萄牙商人去廣州貿易,在廣州省城海防安全沒有遭受威脅的時候,一般都是由葡萄牙商人上省城貿易。成書於1582年之後的《中國諸島簡訊》稱:
從澳門取海道前往廣州,可走兩條路:一條叫內線,即沿著澳門所在島嶼的西側,途經香山鎮,沿著順德島的左側,前往廣州。另外一條叫外線,即沿著澳門港所在島嶼的東側,穿過一個小海灣,途經許多小島,沿著順德島的左側,前往廣州。
“下澳”是指廣州的商人前往澳門貿易,在廣州省城海防安全遭受威脅之時,則多改為由廣州商人到澳門去貿易。明人霍與暇《勉齋集》稱:
大約番船每歲乘南風而來,七八月到澳,此其常也。當道誠能於五月間,先委定廣州廉能官員,遇夷船一到,即刻赴澳抽分,不許時刻違限,務使番船到港。……於六月間,先責令廣州府出告示,召告給澳票商人,一一先行給與,候抽分官下澳,各商親身同往,毋得留難。……抽分早則利多入官,澳票先則人皆官貨,私通接濟之弊不禁而自止矣。
正是由於明朝政府實行的這一套機動靈活的“上省”、“下澳”制度,這樣就將澳門這一孤懸海島的港口與廣州這一中國南方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緊密地鉤連在一起。不管海上風雲變幻,中國南大門海域的對外貿易始終能保持一種穩定的開放狀態,澳門因此也就成為了廣州港的外港。
正因為澳門具有上述極為特殊且極具優勢的地理位置,所以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以後就很快將澳門建成了一個極具規模的國際貿易港口。萬曆初期的劉承範《利瑪傳》稱:
夫香山澳距廣州三百里而遙,舊為占城、暹羅、貞臘、諸番朝貢艤舟之所,海濱彈丸地耳。 第明珠、大貝、犀象、齒角之類,航海而來,自朝獻抽分外,襟與牙人互市。
明人王臨亨《粵劍編》亦稱:
西洋之人往來中國者,向以香山澳中爲艤舟之所,入市畢,則驅之以去。日久法弛,其人漸蟻聚蜂結,巢穴澳中矣。
誠如上言,澳門的港口貿易能產生“一往而利數十倍”極為高額的利潤,故吸引了無數中外商人來澳門經商。國內則“中國豪商大賈,亦挾奇貨以徃”,“閩粵商人,趨之若鶩”,外國商人進入澳門則“列廛市販,不下十餘國”。由於葡萄牙人從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一直控制着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葡日貿易航線,並壟斷了這條航線上對中國和日本的貿易,所以有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東亞海域中的各國都要附隨葡萄牙人纔能參與對中國的貿易,所以在澳門出現了“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的經濟現象,據明人蔡汝賢的《東夷圖說》,在萬曆中期“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有回回、錫蘭山、浡泥、彭亨、百花、呂宋、咭呤、甘坡寨、順嗒等9個國家。而這些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的國家,都參與到廣州貿易之中,而形成了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匯聚東西方各國商人貿易著名的“廣州交易會”(又稱廣州市集)。故1582年抵達澳門的利瑪竇(Matteo Ricci)稱澳門:“不僅有葡萄牙人居住,而且還有來自附近海岸的各種人聚居,都忙於跟歐洲、印度和摩鹿加群島運來的各色商品進行交易,……不久那塊滿是巌石的地點就發展成一個可觀的港口和著名的市場。”
正是由於澳門這一國際貿易港口的創建,一場規模極為龐大、影響極為廣泛的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運動在東亞海域出現。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及中國、日本、東南亞商人們將他們從歐洲、印度、東南亞及日本販來的貨物轉賣到廣州,而又從廣州購買中國的生絲、綢緞、磁器、茶葉及藥材轉販到東西方各國。正如葡萄牙學者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所言:
一個連續數月的集市首次在廣州舉行後,以後一年兩次,一月份澳門商人開始購買發往馬尼拉、印度和歐洲的商品,六月份則購買發往日本的商品,以便及時備好貨物,使商船能在東南和東北季風開始時按時啟航。遠東與歐洲的貿易為葡萄牙王室壟斷。一支王家船隊每年從里斯本起航,通常滿載着羊毛織品、大紅布料、水晶和玻璃製品、英國製造的時鐘、佛蘭得造的產品,還有葡萄牙出產的酒。船隊用這些產品在各個停靠的港口換取其他的產品,船隊由果阿去柯欽,以便購買香料和寶石,再從那裡駛向滿剌加,購買其他品種的香料,再從其他群島購買檀香木。然後,船隊在澳門將貨物賣掉,買進絲綢,再將這些連同剩餘的貨物一起在日本賣掉。換取金銀錠。這是一種能使所投資本成2倍或3倍增長的投機買賣。船隊在澳門逗留數月後,從澳門帶着金、絲綢、麝香、珍珠、象牙和木雕藝術品、漆器、瓷器回國。葡萄牙國王為自己保留了東方貿易中最大的特權。他給予有功的大臣的最大實惠就是允許他們用一兩艘大帆船運來東方商品,賣給里斯本商人,以獲巨大利潤。
當然從澳門出口的轉販的商品最大宗為中國絲綢,據西班牙罗耀拉(Martin Lgnácio de Loyola)修士《自西班牙至中華帝國的旅程及風物簡志》稱:
帝國全境有大量的絲綢,多從廣州城運往葡屬印度,每年多達3000多公擔(每公擔59公斤),另外,運往日本的許多公擔沒算在內,還有通常開往呂宋群島的15艘船所載和暹羅及其他國家的人拿去的大量絲綢都未計算在內。
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則這樣記錄:
《葡屬亞洲》一書斷言,他們每年的出口達5300箱精緻絲綢,每箱包括100匹絲綢、錦緞和150匹較輕的織物。
而從澳門運進廣州輸入中國內地最大宗的商品則是白銀,據1590年《日本天正遣歐使節團》一書載:
葡萄牙人為了採購貨物,每年運到那個叫做廣州的城市的白銀,就至少有四百個塞斯特爾休(Sestércio,古羅馬銀幣,合兩個半阿斯asse),但一點兒白銀也都沒有從中國流出境外。
而據葡萄牙學者索薩的統計,1546-1638 年,葡人從日本帶到中國的白銀數量達到 3660-4110 萬兩。除了從日本運入澳門的白銀外,還有從馬尼拉將美洲的白銀也大規模地運回澳門,1635年菲律賓檢查總長孟法爾坤(Juan Grau y Monfalcon)稱:
因澳門葡人到中國廣州市上購買貨物,運往馬尼拉出售。……葡人現在自馬尼拉運走的銀幣,有過去中國商人運走的三倍那麼多。
而李慶博士則認為,從1582年到1642年從馬尼拉流入澳門的白銀不會少於2000萬比索(約1600萬兩),可能會超過3000萬比索(約2400萬兩)。兩者相加,在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東亞海域大航海活動最興盛時期,葡萄牙人運進澳門再輸入中國內地的白銀達6000-7000萬兩之多。而中國絲綢大規模地流入歐洲、美洲及印度、日本、東南亞地區和美洲、日本白銀大規模地進入中國內地成為了這一時期大航海活動所推動的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表征。
在16-17世紀的東亞海域中,先後出現了多條國際貿易航線,而這些航線又構成了這一時期東西方經濟交往的貿易網絡,在這一網絡中,由廣州、澳門這兩個港口而構築的華南貿易中心,毫無疑問成為了東亞及東南亞內部貿易網絡的最為重要的總樞紐;以此為外延而形成了平戶、長崎、那霸、大員、馬尼拉、巴達維亞、萬丹、帝汶、阿瑜陀耶、北大年及會安等港口為中心的廣袤的東亞-東南亞貿易商圈,而廣州——澳門則是這一廣袤貿易商圈中最為重要的支柱。通過這些貿易商圈和貿易網絡中的大航海活動,又推動了這一時期第一次全球性的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碰撞。
因此研究澳門歷史,我們的著眼點決不能僅盯住澳門一地,一定要將其置身於“大航海時代”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才能夠準確地把握澳門歷史之真諦。包括澳門的起源、澳門的興衰及澳門經濟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等最為重大的問題,無不與“大航海”這一偉大時代密切相關。這就是我將本書命名為《大航海時代與澳門:中日朝越四國澳門漢文檔案文獻彙編(1500-1840)》之緣起。
(二)
澳門歷史研究發展至今日,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查閱以往為量甚巨的各種研究論文和著作,不痛不癢的文章,“海納百川”拼湊的著作;毫無新意,不斷重復;甚至出現普及性知識讀物遠遠繁榮過深入系統的學術研究;很多學者研究澳門歷史完全罔顧這一領域裡面還有極為龐大的葡、西、荷、法、義等國所保存的各種西語材料,一味採用單一的中文材料自話自說,從不考慮中西互證。這一切,帶來的就是令人厭倦的學術“審美疲勞”,致使澳門歷史研究落入進退維谷的學術“瓶頸”。毫不誇張地說,現今的澳門歷史研究已經陷入極度嚴重的困頓之狀。原因何在?我認為,其根源就在於歷史資料的單一性與斷裂性。大面積、長時段的歷史時期,並無第一手歷史資料的支撐,故形成眾多澳門歷史時期的斷層和空白。即使是研究“香火”十分鼎盛的早期澳門史,其間缺漏仍然不少,甚至還留下許多至今仍未解開的“歷史之謎”。因此,繼續全面系統竭澤而漁地搜尋整理有關澳門歷史的中西檔案文獻,仍是今日深入展開澳門歷史研究不可或缺而且應該更加重視的基礎工作。
自上世紀90年初我投身到澳門學研究中始,至今已近卅載。一直以來,秉承着竭澤而漁地收集中西澳門史料為宗旨而展開澳門歷史研究。前些年,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去做基礎的史料整理工作,也編纂和出版了多種澳門歷史研究資料集。原以為澳門歷史研究的中文史料整理工作應該做得差不多了,至少可以說在中文史料整理工作方面已大致完備。然而,這一思維很快就被本世紀初“大數據時代”的出现而打破,各種新的歷史資訊鋪天蓋地而來,各種數據庫、資料庫、各大機構編纂的數以千計的檔案文獻古籍影印叢刊及海內外各大圖書館、檔案館開放的館藏圖書在線閱讀等等,構成了一片橫無際涯的史料的大海汪洋,而將每一位研究者所需要的新史料推置於波峰浪谷之中,考驗着每一位史學研究者對史料追求的勇氣與毅力。面對這一切,我曾彷徨於自己對電腦的生疏及技駑,但很快意識到,如不趕上這一時代的潮流,亦必將成為時代的棄兒。針對目前澳門學研究領域出現的隱憂與危機,針對澳門歷史研究目前已經陷入學術研究“瓶頸”的困境,我們要想有所突破,要想繼續地深入發展,就仍然需要繼續大規模地挖掘原典中文史料、編譯西文資料,真真正正全面系統地完成澳門歷史研究的基礎史料工作,這應當成為下一個階段工作的重中之重,而這一工作的完成則必須依靠新時代的新方法,即“E考據加乾嘉”。1999年,我們和澳門基金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作編纂出版了《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時至今日已經走過了20餘年。在大數據時代出現之前,我們整理的這一套頗具規模的檔案文獻確實推動了中國學者早期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然而,由於大數據時代史無前例的信息的開放和文獻資料的公佈,這些公佈和開放的信息與資料如同排山倒海的潮汐將我們史學研究工作者固有的認識堡壘,毫不留情地摧毀。如果我們還仍然沉浸在20餘年前憑著手工勞動、個人記憶和爬梳所得出來的有限資料來研究澳門歷史,這種研究的片面性和準確性是令人懷疑的,我們永遠也衹能停留在歷史的碎片化和真相的表層。
鑒於此,我製定了一個極為宏大的工作遠景,即在原有文獻調查的基礎上,在全球範圍內對有關澳門史的檔案文獻資料進行一個全方位的搜集與整理,最終將散落在各處的檔案文獻進行徹底的“清底”。同時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搜集中文文獻的同時,也要注重西文文獻的整理編譯工作,二者決不偏廢。從2012年開始,我承擔澳門大學重大項目“全球澳門學文獻調查”,組織了近二十名國內外學者,對海內外各個檔案館圖書館有關澳門文獻進行了全面調查和編目整理,還利用澳門大學的先天優勢,組建了一支來自葡語系及我的博士生共有十餘人的翻譯團隊,開展對澳門有史以來內容最為豐富的一套葡文檔案集——《澳門檔案》(Arquivos de Macau) 及葡文原始文獻包括聖保祿學院年度報告(Cartas Ânuas Do Colégio De Macau)、耶穌會中國副省年信(Cartas Ânuas Da China)、遠方亞洲(Asia Extrema)的翻譯工作,至今已完成了兩百多萬字的翻譯稿,這一翻譯工作至今仍在進行。實事求是地講,要“竭澤而漁”地搜集編譯有關澳門學的外文檔案文獻這一任務,肯定不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要想將我們這一領域相關的外文檔案文獻“竭澤而漁”並且翻譯成中文,在目前來說還衹能是美好願景而已。僅葡文檔案文獻資料一項,就有里斯本國家圖書館、海外歷史檔案館、阿儒達圖書館、外交部歷史檔案館、埃武拉公共圖書館、印度果阿檔案館及澳門歷史檔案館等十餘家圖書館、檔案館,藏有超過數十萬份有關澳門的公文、報告、日記、書信等葡文文獻檔案,其中多數還是漫漶不清的手稿。即便是經費充足,當今國內學界也很難找到一批精通葡文的歷史學家從事這一工作,史學界的葡語人才的培養成為我們研究領域當務之急。當然還包括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雖然,在我們的前途橫亙着無數難以逾越的障礙與鴻溝,但我們必須要沿着這個方向矢志不渝地走下去。
如果說“竭澤而漁”地翻譯整理澳門歷史研究外文史料還不是我们现阶段所能完成的任务,那麼,藉助現代高度發達的網絡技術手段,就我們這一代學者而言,對澳門學漢文檔案文獻的清底工作,卻是可以歷九轉而可告功成的。最近20餘年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數據庫方法的運用,學術研究的路徑、手段以至研究形態,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人們已經真切地感受到學術研究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各種資料庫和數據庫所公佈的海量的中文古籍,包括中國基本古籍、中國方志、中國譜牒、中國金石、中國類書、歷代別集、明清檔案、明清實錄、諸子經典、佛教經典、全四庫、叢書總匯、家譜集成、中國近代報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朝鮮實錄、韓國燕行錄、韓國記憶數據庫等等,這些數以兆億字計算並可供全文檢索的中文古籍的出現,為我們全面搜尋澳門歷史研究的新資料提供了無以倫比的方便和快捷,也為我們竭澤而漁地全面掌握澳門歷史研究資料提供了可能。特別是海內外各大圖書館、檔案館所開放的在線閱讀網絡資源,更是為我們直接提供了長期以來我們知道或並不完全知道的稀見原典中文古籍的查閱。瞬息之間,我們就可以遨遊於世界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之間,直接翻閱我們需要查找的原典古籍,如中國國家圖書館、廣州大典在線數據庫、澳門歷史檔案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室、臺灣故宮博物院檔案館、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葡萄牙里斯本阿茹達宮圖書館、葡萄牙埃博拉公共圖書館、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西班牙國家圖書館、西班牙塞維利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西班牙皇家歷史學院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美國猶他州族譜研究中心、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詹姆斯·福特·貝爾圖書館、美國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美國康涅狄格州歷史學會、美國羅德島州歷史學會、美國迪美博物館菲利普斯圖書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德國國立圖書館、德國巴伐利亞州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外交部檔案館、英國國家檔案館、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梵蒂岡羅馬教廷傳信部檔案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瑞典斯德哥爾摩北歐博物館檔案館、瑞典哥德堡大學圖書館、丹麥哥本哈根國家檔案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日本內閣文庫和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等等。因此,自2012年起,我決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開新一輪的明清時期澳門歷史研究資料的全面搜集與整理,包括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地區漢字文化圈中的漢文檔案文獻。這次整理出來的明清澳門漢文文獻與二十餘年前相比,已經大大地超越;特別重要的是我們搜尋了很多並不為以往澳門學術界所關注的珍貴澳門史料,包括第一次將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越南300餘種漢文文獻中相關的澳門史料收入其中,這裡面有很多文獻均為第一次向學術界公佈,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總之,這一次對明清時期澳門漢文史料的全面搜集和整理,應該說大大地擴展了自大航海時代以來,以澳門為中心的東西方經濟文化交往歷史資料的記錄,這一記錄至少從漢文文獻層面較為全面地反映了這一偉大時代,也為我們準確認識這一偉大時代提供了來自漢文文字所記錄的資料保證。從這一角度而言,我相信,本資料集的完成,將為未來澳門學研究的系統深入發展奠定堅實的史料基礎。
(三)
下面,我想分為五個方面,來談一談我們編纂的《大航海時代與澳門:中日朝越四國澳門漢文檔案文獻彙編(1500-1840)》一書的重要性和主要特色。
首先,我們將明代澳門歷史資料的搜集置於大航海時代東亞地區漢字文化圈這一新的歷史視角而進行。我們將本資料集命名為《大航海時代與澳門:中日朝越四國澳門漢文檔案文獻彙編(1500-1840)》,更是基於對明清澳門歷史全新的把握與認識。第一,我們認為,澳門的起源與明成化、弘治以後中國東南沿海出現的海上私人貿易集團有關。這些海商集團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他們遠赴南洋諸國,甚至進入印度洋,與葡萄牙人展開商業貿易,並且與葡萄牙人聯合經營,引領葡萄牙人在中國東南沿海展開大規模的走私貿易,澳門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產生和出現的。所以,研究澳門的起源,必須要了解明成化、弘治以後這些私人海商集團與葡萄牙商人的關係。第二,明清澳門歷史與葡萄牙和西班牙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一、在明代的中文文獻中,將葡萄牙和西班牙都稱為佛郎機,所以明代所出現的“佛郎機”一詞有時候讓人們很難分清哪是指葡萄牙,哪是指西班牙;二、明代的澳門與西班牙所佔據的馬尼拉甚至與西班牙所佔領的拉丁美洲有著密切的貿易關係。澳門與馬尼拉是大航海時代伊比利亞民族在東亞海域出現的關係最為密切的“雙城”;三、明代從萬曆八年(1580)開始,葡萄牙曾併入西班牙王國,直到崇禎十三年(1640)葡萄牙才從西班牙獨立,所以澳門從1580至1640年整整六十年是屬於西班牙統治,西班牙人給明代的澳門歷史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甚至可以說,澳門開埠以後,明代的澳門歷史絕大部分時間都是由西班牙人來統治,不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面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天主教,當時西班牙天主教士幾乎佔領了天主教對遠東傳播的最為主要的澳門陣地。而這一段西班牙人統治澳門的歷史,在我們以往的澳門歷史研究中並未獲得清楚的認識和充分的表現。因此,本資料在編纂上有意識的突出了西班牙在明清澳門歷史中間所起的作用和影響。這應是本資料編纂新的歷史視角之一。第三,除了西班牙以外,荷蘭、英國、法國、美國等歐美國家的東印度公司和商人們在明清時期也與澳門發生著密切的關係。荷蘭初抵中國時,就開始覬覦葡萄牙人所佔據的澳門寶地,甚至多次與葡萄牙發生搶奪澳門的戰爭。入清以後,荷、葡之間的競爭亦甚劇烈,為了在對華貿易中獲得更大的利益,雙方的詆毀、攻擊,直到乾隆中期才中止。在整個大航海時代,雙方互為仇讐的競爭關係貫穿始終。英國人來華之初,與澳門葡萄牙人的關係亦與荷蘭人大體相同。但是,由於在大航海時代的全球貿易網絡中,澳門、廣州由於其自身特點而構成的互為依存的貿易關係,所以在大航海時代的後期,不管是朋友還是競爭者,上述歐美國家的船隊、商人及傳教士與這兩個港口城市都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廣州貿易,澳門住冬。在清政府一系列條約制度的約束下,澳門並不心甘情願地敞開了懷抱,迎來了他的朋友和敵人。在大航海時代的後期,澳門真正成為了一個繁華的匯聚著世界各國人口的國際化都市,並形成了澳門歷史上的“第二次開埠”。正因為如此,廣州十三行的行商與夷商也就成了“廣州-澳門”貿易體系中可圈可點的明星。這也就是我將這部資料集命名為“大航海時代與澳門”之深刻寓意。
其次,本資料集仍然是按照二十年前我們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的方法,根據文獻的分類對明清時期中國、日本、朝鮮、越南四國所藏的有關澳門問題漢文檔案文獻進行全球性的搜尋和全面系統地發掘整理,這次整理出來的明清漢文檔案文獻與二十年前相比已經大大的超越,當時收錄的明代及清中前期中國文獻為250餘種,而今天我們收錄的明清漢文文獻則超過1600種,也就是說,這次重新收集的明代澳門史料從文獻種類而言是過去的6倍。除了搜集整理的文獻遠遠多於二十年前編纂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外,特別重要的是,我們搜尋了很多都是為以往學術界並不為人所知的珍貴澳門史料。下面擇其最為重要的數種文獻予以簡單介紹:
一,我們在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找到的明代韓霖《守圉全書》,其中卷二之《設險篇》、卷三之《製器篇》、卷四之《豫計篇》、卷五之《協力篇》、卷末之《贈策篇》,共保存有明代澳門史料及中西文化交流史料達兩萬字之多,其中收錄的《公沙效忠紀》、《西洋城堡制》、《購募西銃源流》《望遠鏡》《恭進收貯大砲疏》《催護西洋火器揭》《西儒陸先生若漢來書》《唩嚟哆報效始末疏》《西洋大銃來歷略說》《戰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議》《仁會廣放生說》《仁會約引》《南居易平夷疏》《南居益與趙明宇本兵書》《韓霖論紅夷、呂宋、澳夷》等十餘篇獨家記錄的極為珍貴的寶貴文獻,為我們增加了對澳門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很多新的認識,其中還有很多關於澳門開埠初期的歷史資料成為了我們打開澳門開埠史之謎的鑰匙。
二,我們在日本內閣文庫找到的沈㴶《南宫署牘》、曹學佺的《曹能始先生石倉全集》、何喬遠的《鏡山全集》、許孚遠的《敬和堂集》等十幾種日本內閣文庫收藏的明人著作文獻,不僅是日本獨家收藏的明代刊本,而且其中蘊含的極為豐富的明代澳門史料,很多均未被人使用。如《敬和堂集》中收錄的《請諭處番酋疏》,該疏章中保存了極為詳細的所謂“潘和五起義”的全過程,不僅記錄了西班牙菲律賓總督郎雷氏·敝裏系朥是·貓吝爺氏對華人統治的殘暴,也反映了當時華人往呂宋貿易通商的繁盛,以及華人與西班牙人的關係。內中的材料,很多細節都是獨家所有,不見於他書。《敬和堂集》雖有《明經世文編》本和《明別集叢刊》本,但都未收錄《請諭處番酋疏》,所以日本內閣文庫本的明人文集尤顯珍貴。
三,我們在南京圖書館找到的孤本書劉堯誨《督撫疏議》,該書所蘊含的明代澳門史料及中西文化交流史料極為豐富,其中很多史料均為該書獨有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特別是林鳳逃遁於西班牙人佔領的馬尼拉和西班牙使臣馬力陳率團首次訪問中國的記載,更是中文史料對這一事件的獨特記載。
四,中國國家圖書館找到了善本書張本《五湖漫闻》、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張本《五湖漫闻》中記錄了歷史上極為重要的第一次葡萄牙使團中的通事傅永紀的詳細材料,為我們解開“火者亞三”的歷史之謎提供了新的證據;而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則是全面記錄英國第一次來廣州貿易及與澳門葡萄牙人關係最為詳細的材料,其中兩廣總督張鏡心對葡萄牙人和英國人的認知,又使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明代中國士大夫對西方列強進入中國的態度。此二書應為研究明朝澳門歷史不可或缺的中文文獻,其中關於澳門的材料均為獨家記錄而為學界不知,這兩種文獻的發現有助於解決澳門早期歷史研究之謎。
五,浙江省圖書館首次發現的利瑪竇、徐光啟合著的《開成紀要》稿本不僅是研究明末中西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資料,包括很多西方化學工業物品和西方器物的傳華,其中特別是對望遠鏡製造的全過程的介紹,不僅可以說明利瑪竇是最早將望遠鏡帶進中國的西方傳教士,而且還向中國民眾介紹了望遠鏡的製作方法,而導致中國人自己開始學習製造望遠鏡。這在西方科學技術傳入中國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六,我們還從現在已經影印刊行的多種四庫類叢書中找到畢自嚴的《度支奏議》、洪朝選的《芳洲先生文集》、郭應聘的《郭襄靖公遺集》、羅大紘的《紫原文集》、鄧士亮的《心月軒稿》、許弘綱的《群玉山房疏草》、喻安性《喻氏疏議詩文稿》、范景文的《戰守全書》,這些文獻中都包含著極為重要的、也是以往學者未曾利用的澳門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珍貴材料。如《郭襄靖公遺集》中的《總督條約》,不僅記錄了萬曆時期中國內地商民與澳門葡萄牙商人走私通商的繁盛狀況,而且記錄了進入澳門的華商充當葡萄牙人的經紀人設立牙行的史實,為我們研究廣州行商的明代形式提供了證據。又如《戰守全書》中,記錄了在馬尼拉長期生活的華人伍繼彩掌握了西班牙人鑄造西洋大砲之技術,後來投奔明朝的詳細過程,對於了解17世紀初,西洋大砲技術傳華的路徑和過程,提供了新的渠道。其中特別是喻安性的《喻氏疏議詩文稿》,該書不僅記錄了萬曆四十一年喻安性到澳門驅逐日本人而給澳門葡萄牙人訂立《海道五約》的詳細情況,而且還記錄了當時葡萄牙人與喻安性反復商討雙方條件的詳細細節。其中,《澳門立石五禁》、《香山澳散倭紀事》這兩篇文獻,應該是澳門開埠後,明朝政府為保衛國家安全,對居住澳門之葡萄牙人進行有效管理最為重要的文獻記錄,亦為獨家所載。
七,我們還從多種地方志中找到了為學界未曾關注的澳門歷史重要文獻,如僅見於《康熙上杭縣志》中的丘道隆《請却佛郎機貢獻䟽》全文;《萬曆鉛書》中的《費方伯上書止暹羅兵》一文;《嘉慶海州直隷州志》中的胡璉指揮屯門海戰殲滅佛郎機三船的記錄;《康熙上海縣志》所收錄的《敬一堂志》中收錄了大量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貴史料;《康熙平和縣志》中《風土志》收錄了平和人郭奏、吳渭從咖喇吧經商回國曾停留澳門,後向家鄉當地官府匯報了澳門詳細情況的資料;《康熙金華府志》記錄了劉仔於康熙十五年代表清政府出使巴達維亞的珍貴資料;《雍正浙江通志》收錄了繆燧《番舶貿易增課始末》,其中關於英吉利在浙江寧波早期貿易的情況,記錄極為詳細。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發現了《道光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這是一部全面記錄澳門地理、氣候、行政、宗教、城市、商業、物產、風俗,以及中葡關係的地方調查報告。其中除部分資料見於《道光新修香山縣志》之外,絕大部分內容都是為《香山縣志》所無,很多史料可以糾正現行澳門史研究中的錯誤。
八,在明清詩文集中,還找到了很多為前人所未見過的澳門詩歌,如葉權《沙南遺草》中,留下了澳門歷史上第一首關於澳門的詩歌——《夜泊濠鏡澳》。葉權是澳門開埠後,第一個來澳門旅遊的布衣文士,他留下的《嶺南紀遊》,成為了我們研究澳門歷史最早的漢文文獻。而他的第一首遊澳門詩的發現,為我們研究明清澳門文學史,提供了新的資料;繆艮《塗說》中收錄了乾隆時期遊澳門時所見到金采香的《戊午秋觀夷婦禮拜詩八絕句》,此八首詩在《橡坪詩話》中曾經簡單公佈。而繆艮所見金采香詩不僅有詩文,而且每首詩都有很詳細的說明文字,都是研究澳門社會生活、風俗習慣的極好材料;姚啟聖的《憂畏軒遺稿》也保存了他任香山知縣時撰寫的有關澳門的詩歌,這些都是研究清代初期的澳門歷史的好資料;康熙時期的錢光夔《粵吟》收錄《墺門》五言長詩是以往未被人關注的極為重要的澳門詩歌,此詩應在澳門文學史上擁有一定的位置。這一次明清澳門詩歌的大量挖掘,很多均是以往研究者未曾提到和未曾使用過的珍貴史料。
九,我們在《清代稿鈔本》中找到了一份鴉片戰爭前關於澳門全面報道的新資料《洋事雜錄》,其中《史濟泰口述澳門情形》詳細報道了澳門的地理、經濟、砲臺、人口、樓房、教堂、政府機構以及社會風俗等,並稱澳門“巨富十七八家,小康三四十家,餘為窮乏。”《胡、馬密查澳門情形》則記載了澳門的稅收和英商、葡商的情況。《史濟泰述良歹夷人》則記錄了澳門富裕葡人的資產以及販鴉片與不販鴉片的商人,並明確報道了十六位澳門葡人擁有的資產,五、六十萬者為兩人,二、三十萬者為兩人,十餘萬者為五人,三四萬者為七人。如此詳細的澳門社會內部的中文資料發現,不能不說是這一次深度挖掘的重要成就。
以上所述,僅是本資料集新發現的一小部分。毫無疑問,如此大規模的澳門新史料的發現與公佈,我想這對於澳門歷史研究而言,一定可以增加更多的新的內容及研究話題。特別是對明清澳門歷史研究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向學術的縱深推進一定大有裨益。
第三,本資料集不僅全面搜集各種明清漢文文獻中的有關大航海時代澳門問題史料,而且第一次將明清日本、朝鮮和越南漢文文獻中的與上述相關的史料亦收入其中,這是從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等歐洲國家在遠東活動的角度來重新考量澳門在遠東地區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取的作用和地位。同屬於漢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鮮和越南留下了數以萬計的漢文文獻,這裡面也包含了為量甚巨的關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與澳門在這一地區的活動之史實。本集此次收錄的日本漢文文獻共160餘種,朝鮮漢文文獻80餘種,越南漢文文獻20餘種。從已經搜尋到的這260餘種日、朝、越海外漢文文獻來看,其中保存的明清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歐洲國家及澳門在東亞及東南亞海域活動的資料亦有相當豐富的記錄,特別是反映這一時期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內容則更為充裕。絕大部分資料均為中國漢文文獻所不載,即可補中國漢文文獻所載之不足,又可與中國漢文文獻所載相互補證。
如日文文獻《異國往復書翰集》、《異國所所御書之草案》、《異國日記》、《外番通書》、《外番通表》及《羅山先生文集》中多處保存了葡萄牙果阿(日本人稱之為“五和”)和澳門(日本人又稱之為“阿媽港”和“天川港”)與日本政府相互往來的通信和文件,這些文件構成了澳門與日本關係最為重要的內容,此為明清文獻所缺,其中既有葡日貿易的大量數據,以及天主教在日本傳播的大量事實。又如1608年在澳門發生的日本朱印船騷亂事件和1610年在長崎發生的葡萄牙黑船遭圍剿而焚毀事件,致使葡日雙方五六百人在這兩次事件中喪亡,這是澳門歷史上極為重大的事件,衹有透過日本文獻和葡文文獻才能準確獲知這一事件的過程。西班牙人早期同日本的交往,我們在明清文獻中找不到記錄,日本漢文文獻《續皇朝史略》明確記錄:“天正九年(1581)春二月,信長入朝。時呂宋貢崑崙奴,信長召見之,伴天連率崑崙奴而至。”這就是說,西班牙人在1571年攻佔馬尼拉以後,不到10年就開通了對日本的貿易航線。而西班牙與日本的正式官方交往則見於慶長六年(1601),日本漢文文獻《異國所所御書之草案》還保存了一封日本德川幕府將軍源家康回復呂宋國行政長官“郎·巴難至昔高·提腰”(Don Francisco Tello de Guzman)的國書。1590年,葡萄牙人若奧·伽瑪(João Miguel da Gama)駕駛一艘600噸的大帆船橫渡太平洋,第一次開通了澳門與拉丁美洲的貿易航線,這些資料都衹能見於葡萄牙檔案文獻。而日本漢文文獻中則保存了很多關於新西班牙(即墨西哥,日本漢文文獻稱之為“濃毘數般”)與東方交往的珍貴材料,在慶長七年(1602)時就出現了“年年濃毘數般往返之舟八艘也”的記載。而在慶長十六年(1611)之前亦出現了日本商人田中勝助航行新西班牙的記錄,並且帶回了當地的土產五色羅紗、蒲桃酒等。而在第二年,新西班牙又派船航行日本,日本漢文文獻《外蕃通略》稱:“慶長十七年六月,前大將軍源家康、大將軍秀忠並賜復書於濃毘數般國主,謂唯許物貨貿易,而切禁傳異教。”還有大量的日本與荷蘭(阿蘭陀)、英吉利(伊袛利須、伊伽羅諦羅)貿易交往和文書往來的記錄。這些寶貴的日本漢文記錄,為我們瞭解大航海時代形成的歐亞非美全球貿易網絡提供了明清文獻所不具錄的確切證據。
日本漢文文獻還提供了大航海時代歐洲各國與日本文化交流方面的珍貴史料,如新井白石的《采覽異言》中關於歐洲國家的介紹十分詳細,也是最早將西學向日本介紹的日本學者,其中有一部分資料來源於中文古籍,但大部分都是從西人口中、書中訪問和翻譯而來。又如《和漢三才圖會》所記錄的當時的各種南蠻和阿蘭陀傳入日本的物種和器具,其中特別是關於望遠鏡、自鳴鐘、番椒、番薯、煙草傳入日本的記錄,有的比中國早,有的與中國同時,有的還互相交叉傳播,反映了明清之際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多途徑與多渠道。大槻茂質的《蔫録》一書中,還收錄了兩篇譯自荷蘭文的關於煙草傳播的原始記錄,其所載傳播途徑和傳播過程極為詳細,是一份東西方文化交流極為珍貴的原始史料。關於西洋醫學在日本早期傳播的記載甚多,如日本華人盧驥的《長崎先民傳》、淺田宗伯的《皇國名醫傳》、河口信任的《解屍編》、久我克明的《種痘龜鑑》,記載了很多日本人前往阿媽港、馬尼拉和果阿等地學習醫學,又回到日本擔任醫生,甚至後來成為了幕府和皇宮的御醫。再如明代徽商王直,中國文獻僅載其在日本通商貿易中獲得成功,但通過日本漢文文獻《南浦文集》之《鐵砲記》,我們卻可以獲知最早將葡萄牙人帶到種子島並將葡萄牙人的鳥銃這一新式火器傳入日本的也是王直。《佐佐木家譜》還記載當時有“唐人長子口”(考證應是擅長於製造火砲的海盜毛海峰)在嘉靖時也到日本種子島教授鐵砲術。可見雖然鐵砲是葡萄牙人傳進日本,但實際上的傳播者卻是華人。然而後來鳥銃又通過日本人傳入中國,這成為了中日葡三國之間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佳話。
朝鮮漢文文獻的數量雖然比不上日本,但其中保存的葡萄牙、西班牙及澳門的漢文史料亦為不少。朝鮮人稱澳門為“香島”,又稱澳門為“甘河”,稱葡萄牙為“寶東家流”。當明武宗正德年間第一次葡萄牙使團來華時,中文史料記載都十分稀罕,而在朝鮮王朝實錄中就有大段的資料表現此事,增補了我們對葡華首次外交史的認識。崇禎時期,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第一次將大量的西方書籍、地圖、器物贈送給朝鮮使臣,這一事件在朝鮮漢文文獻中成為了大書特書的重大事件,反映在朝鮮文人的眾多詩集和文集之中,也證明了這一西學東漸事件對明代的朝鮮王朝所產生的重大影響。萬曆壬辰之役,明朝政府為了幫助朝鮮抗擊日本的侵略,明軍在澳門徵集了一批黑人部隊入朝抗日,“黑面蠻奴”這一形象在朝鮮文獻中大量的反映,甚至被神化,這也是朝鮮漢文文獻表現的特色。
越南漢文文獻中關於明代葡萄牙、西班牙及澳門的記錄相對較少,但從少量的記錄中也可以反映澳門與越南的貿易及經濟文化交流。越南人稱澳門為“瑪糕”,在越南黃高啟《越史要》中,記錄了17世紀初葡萄牙人茶那低孥(João da Cruz)在順化城南建立鑄砲廠的記錄,還將葡萄牙的造船技術傳入越南。最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看出當時澳門的教會如何向越南傳播天主教以及越南政府的應對策略。
可以說,我們從漢字文化圈的角度來搜羅整理大航海時代澳門歷史資料,這應該是一次全新的嘗試,亦有利於我們全面準確把握和認識大航海時代以來葡萄牙、西班牙及澳門在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中所取的作用和地位。這也應是本資料編纂新的歷史視角之一。
第四,本資料集這次搜尋整理的130餘種從海外及中國各地圖書館、檔案館及民間收集到的族譜資料,也是其重要特色之一。以往學界對族譜與澳門的關係關注不夠,或者是因為中國族譜存量過於龐大,且內容龐雜,不易搜尋翻檢,再加上族譜中所載資料往往有為自己祖先歌功頌德、粉飾添彩的現象,所以在澳門歷史研究中很少人使用族譜中的資料。我們這次對中國所存族譜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調查,除了利用中國譜牒庫網絡檢索資料外,還先後查詢了澳門歷史檔案館、猶他州族譜中心、北京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暨南大學圖書館、珠海市圖書館、晉江市圖書館以及目前已經出版的《臺灣文獻匯刊》、《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中華族譜集成》、《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泉州譜牒華僑史料與研究》、《晉江族譜類鈔》等,從中輯出了近30萬字有關華人在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西班牙管治下的馬尼拉及荷蘭管治下的巴達維亞的社會生活史料。其中重點反映了澳門開埠以後閩粵地區華人對澳門最初的移民群,特別是明代鄭芝龍編纂的《崇禎鄭氏族譜》,該譜記載了福建安平鄭芝龍家族對澳門的早期移民,該家族竟然有五代人因來粵貿易而死於澳門。族譜中出現了大量的明代澳門地名,均為其他文獻所不載,為澳門早期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資料。《晉江英岱二房石門份洪氏族譜》則記錄了嘉靖三十三年(1554)海道副使汪柏與葡萄牙船長索薩簽訂協議後,廣東按察使黃光昇“開澳與夷貿易”,而晉江人洪廷秀即進入澳門貿易,後來其二弟成為澳門巨商,這是一份佐證澳門早期開埠史的重要史料。而劉後清《湖北監利存澤堂劉氏族譜》中保存的明韶州同知劉承範《利瑪傳》不僅記錄了利瑪竇早期在肇慶、韶州的活動,而且還記載了萬曆十七年(1589)兩廣總督劉繼文準備進攻澳門而派劉承範前往澳門打探消息,而劉承範返回將澳門真實情況向劉繼文匯報後,明軍取消了這一次軍事行動,而導致數萬澳門葡人免遭屠戮之重大歷史事實。這一記載不見於各類正史實錄及文集,而得以在族譜中保存,彌足珍貴。明代馬尼拉西班牙當局曾對前往馬尼拉貿易的華商和定居在馬尼拉的華僑進行過多次屠殺,在福建族譜中有大量的記錄證明福建各地商人死於這幾次屠殺。毫無疑問,本資料搜尋和整理的族譜中的有關葡萄牙、西班牙及澳門的資料也成為了新的視角之一。我們在顏敘鋙的《重修颜氏遷粤家譜》中,還發現了晉江商人顏亮洲在清康熙創立十三行的原始記錄:“會奉榷部檄募充十三家與蕃漢通市,公乃投筆廁身其間,時則有若陳監州、葉比部,皆公同事,然尤推公為領袖云。”與《勤餘文牘》記錄的“自康熙間,吾鄕吳留村督粤,立官行十三家,互市澳門”相合,可以證明十三行確實於康熙二十三年後,由兩廣總督吳興祚和粵海關監督成克大創建。在這次族譜收集中,我們還收集到了民國高仲泮編纂的《高氏宗祖貴顯徙居捷錄》,這份族譜陳垣先生曾經使用過但未公佈收藏處,很多學者輾轉使用,但都未見原件,這份族譜記載了第一位向歐洲人學習西醫而又成為清宮御醫的新會人高竹,該人也是從澳門被征召進京的。這份族譜的發現,使我們第一次看到了記載這一中西文化交流大事的原典材料。
第五,我們這一次花功夫最大的還應是在對舊檔案的整理和新檔案的公佈。眾所周知,清宮收藏的清代檔案至今仍是一個講不清楚的問題,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就將故宮的檔案整理出版,先後有《文獻叢編》、《明清史料》、《掌故叢編》、《史料旬刊》等檔案資料出版,近些年來臺灣故宮博物院、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先後整理了不少檔案專輯面世,而中國大陸第一歷史檔案館則整理出版了更多的檔案專輯,其中與澳門相關的在海峽兩岸分別出版的檔案專輯多達數十種,每種少則一二十冊,多則七八十甚至百餘冊,是一個極為龐大浩瀚的檔案資料的海洋。1999年,我們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作出版了《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其中檔案卷一共四冊,明代及清中前期共為兩冊,到道光二十年止,共公佈明清有關澳門問題的檔案738件,應該說公佈的量不為少,但如果詳細地核對其他幾十部檔案集,我們就發現這一時期有關澳門問題的檔案還有大量地保存在其他的檔案集中。於是,為了保證這一時期有關澳門問題檔案不成為“漏網之魚”,我們重新對海峽兩岸以前出版與澳門相關的各種檔案集進行了重新的輯錄,發現新增的檔案大大地超過了1999年《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中所公佈的檔案數量,很多新增檔案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充實了很多澳門史的新內容。僅舉一例說明,關於康熙六年(1667)爆發的“盧興祖澳門詐賄案”,在以往的《明清史料》檔案中衹公佈了“刑部殘題本”三件檔案,而在也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撰的《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中則找到了有關這一案件的一份內閣雜冊的檔案,標題為《盧興祖所呈香山縣知縣姚啟圣貨單賄單審答過情節》。全檔共15000餘字,極其詳細地記錄了康熙六年香山知縣姚啟聖打破清朝海禁,率船下澳通商貿易的各種細節。衹有讀了這份檔案,才能使我們了解這一事件在清初澳門歷史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像這種遺漏於1999年出版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清宮澳門檔案,在其他的檔案集中還有大量的存在,在此不再贅言。但可以說明,如果我們衹採用二十年前出版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中的澳門檔案,那就必然會造成大量的澳門檔案流失,也致使我們無法了解清宮澳門檔案所反映的澳門史實。
我們除了對海峽兩岸過去出版的幾十種有關澳門問題的舊檔案集進行重新整理外,還將海外檔案館有關澳門問題的中文檔案也進行了全面搜集與整理。如許地山編《達衷集:鴉片戰爭中英交涉史料》、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普塔克編《葡中文獻》、劉芳編《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史料》、吳旻、韓琦編《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等,還對部分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英國、義大利、梵蒂岡、德國、荷蘭、瑞典、丹麥、美國等國的圖書館和檔案館收藏的零星澳門漢文檔案進行了全面的搜羅,找到了很多極為重要的歐美各國在廣州、澳門貿易的收據、貨單、船牌及商館名錄等資料,為我們研究清代歐美各國在廣州、澳門的貿易提供了大量的證據。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四)
總而言之,我們這一次對明清時期(1500-1840)漢文檔案文獻有關澳門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歷史資料全面搜集和整理,應該說大大地擴展了大航海時代以澳門為中心的這一東西方交往的歷史記錄,這一記錄至少從漢文文獻層面較為全面地反映了這一偉大時代,也為我們準確認識這一偉大時代提供了來自漢文文字所記錄的資料保證。史學即史料學,這一道出歷史學真諦的名言告訴我們,沒有全面徹底竭澤而漁的歷史資料保障,要完成真實反映一個時代歷史的“信史”是絕不可能的。從這一角度而言,我相信,本資料集的完成,不僅可以大大地豐富以往學術界對澳門歷史認識的學術知識,更可以說,它將為撰寫澳門歷史的“信史”奠定更為堅實的史料基礎。但是,我們決不能忘記,這個基礎還僅僅衹提供了東亞地區漢字文化圈中漢文歷史資料部分,還有一個更為廣闊的領域,即大航海時代以來各種西語(包括日語)中關於澳門歷史資料的記錄,這是一項更為艱難複雜的工作,而這一基礎的構築,恐怕還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更大的財力和人力方能完成。祗有當上述兩個基礎均被中國學者牢牢掌握之時,澳門歷史研究方可稱真正深入了學術之堂奧,真正進入了國際學術之前沿。
湯開建
辛丑年二月於氹仔澳門科技大學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港澳台及海外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