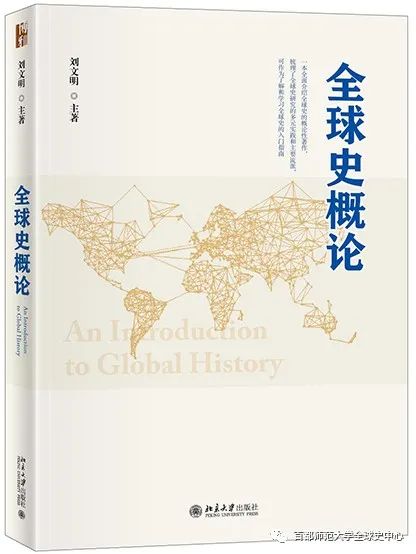
刘文明主著:《全球史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导言
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擅长对历史人物的传记式书写,她的《马丁·盖尔归来》(1983)便是这种研究的代表作。2006年,她又出版了一本得到史学界高度评价的著作――《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书中的主人公是16世纪一个被西班牙海盗俘虏的穆斯林,故事便围绕他在两个世界的跨文化生活而展开。他在被俘前的伊斯兰世界里名叫哈桑·瓦桑(al-Hasan al-Wazzan),在被俘后的基督教世界中则称为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瓦桑出生于穆斯林统治时期西班牙的格拉纳达,随着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他们一家逃往菲斯(属今天的摩洛哥)。瓦桑在菲斯长大并成为一名外交官,代表菲斯出使过非洲许多国家,与一些穆斯林统治者有交往。然而,他在1518年的一次出访归程中被西班牙海盗俘虏,并被当作礼物送给了教皇利奥十世。此后他生活在基督教世界,改名为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学习并掌握了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并且融入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圈子。他把有关非洲的地理、文化和风俗介绍给基督教世界,留下了包括《非洲志》在内的几部手稿。1527年,当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攻陷并洗劫罗马之时,阿非利加努斯逃回北非,其身份又变回为一名穆斯林。在这本书中,戴维斯在书写方法上仍然保持了从原始资料出发来“深描”个人命运的特点。不过,与《马丁·盖尔归来》相比,该书中的主人公被放在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来审视,16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及其关系成为理解瓦桑(阿非利加努斯)个人命运的结构性因素。显然,戴维斯的微观史出现了“全球转向”,全球史领域两份权威刊物《世界历史杂志》和《全球史杂志》都有书评给予了高度评价。
英国历史学家琳达·科莉(Linda Colley)在从全球视角探讨英帝国史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她的《不列颠人:1707-1837年的民族塑造》(2003)就从英国对外战争的角度讨论了不列颠民族观念的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宏大叙事。然而,她于2007年出版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世界历史中的一位妇女》,则以18世纪中后期生活于英帝国的中产阶级妇女伊丽莎白·马什(Elizabeth Marsh)的艰辛经历为中心,以个人传记的方式编织和讲述了一个全球史的故事。伊丽莎白的父母相识于牙买加并在回到英国后生下了伊丽莎白。1755年他们移居地中海的梅诺卡岛(Menorca)。1756年英法七年战争爆发,法军进攻该岛,他们一家前往直布罗陀,而伊丽莎白则准备回英国与一位海军军官完婚。然而,就在回国途中,船只被摩洛哥海盗劫持,她差一点成了摩洛哥苏丹的性奴。由于此次摩洛哥人的劫持是国家行为,目的在于要求与英国谈判和开展贸易,因此两个月之后人质被释放。但伊丽莎白的命运由此被改变,最后与一个曾同她一起在船上被俘的英国商人结婚。然而,伊丽莎白的丈夫因七年战争的影响而破产,于是前往印度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伊丽莎白也到了印度。但她在印度的生活并不平静,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冲击了东印度公司,伊丽莎白的丈夫被公司裁员,由此全家丧失了经济来源。1779年伊丽莎白的丈夫去世,她和孩子在加尔各答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时光。科莉把伊丽莎白的经历置于大英帝国全球扩张这一大框架下来叙述,把她的个人命运与当时的大英帝国及全球化联系起来,使个人传记的书写转化成了一种深入理解全球史的途径。
如果说戴维斯从微观走向了宏观,那么科莉则从宏观走向了微观,她们最终在“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这里实现了会师。“全球微观史”这一概念首先由欧阳泰(Tonio Andrade)提出,他在2010年一篇论文中讲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过程中一个卷入其中的农民的悲惨故事,试图以此来彰显跨文化联系和全球性转变中的“人”的悲欢离合,并就此提出:“我们应该采用微观和人物传记的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将真实的人填充到‘模式’和‘理论’中去,书写一种或者可以称为‘全球微观史’的历史。”[①]可以说,欧阳泰提出这一概念是对近年来全球史研究微观化趋势及相关研究实践的一种恰当概括。
那么,什么是全球史?这个问题很难用一个简约的定义予以概括。因为全球史从出现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学术背景的许多学者参与到了对全球史的讨论和研究,这些不同维度的探讨造成了对全球史理解的多元化。
一、什么是全球史
全球史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之时,几乎等同于一种宏大的全球历史的书写,威廉·H. 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早期的全球史开拓者也正是这样设想和付诸实践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当时美国大学中普遍实行的“西方文明史”通识教学的缺陷,认为有必要以一种“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史取而代之,于是开始了全球史的教学和教材编纂实践,此为全球史在美国的发端。因此,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1963)和《世界史》(1967),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人类全球史》(1962)和《全球通史》(1966)等早期全球史著作,均为世界通史著作。随后,菲利普·柯丁、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等学者也加入到全球史探索的行列,但他们的思路并不是大而全的世界通史,而是某一方面的专题史,例如柯丁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1984),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972)和《生态帝国主义》(1986)。当然,此时的麦克尼尔也出版了几本专题性的全球史著作,如《瘟疫与人》(1976)和《竞逐权力》(1982)等。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史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一方面,宏观全球史著作继续得到发展,如理查德·布利特等人编写的《大地与人:一部全球史》(199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1998),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编写的《传统与相遇:全球视角的历史》(2000)(中译名《新全球史》)等。另一方面,全球史作为一个培养研究生的学科在美国确立,促使了全球史研究走向实证化。于是出现了像本特利这样致力于界定全球史研究范畴的学者。他提出,全球史主要是对世界历史上跨文化互动现象的研究,包括移民与流散社群、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扩张与殖民等研究主题。这种探索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史从宏观叙事向微观实证研究的发展,出现了唐纳德·怀特的《世界与非洲的弹丸之地:冈比亚纽米地区的全球化史》(1997)这种微观个案取向的全球史著作。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史研究在宏观世界史、中观专题史和微观个案史方面都发展起来,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中观专题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如彭慕兰的《大分流》(2000),C.A.贝利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2004),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2009)等。微观个案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如大卫·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2007),斯温·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2014),以及《行者诡道》和《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等等。
从全球史书写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全球史的研究从最初探讨西方的兴起等宏大命题,逐渐走向了对全球化进程中流动和互动的人或事物的多样化研究,微观化、实证化和多元化的探索成为全球史研究一种重要趋势。
实际上,不同学者对全球史的不同书写,也反映了他们对“全球史”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有什么样的全球史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全球史著作。如果认为全球史应该书写全球,结果就会写出一部宏观世界史。如果认为全球史只是一种“全球性”视角的历史,也可以从一种广阔视野来考察微观的人、物或者事件,那么这种研究的结果就会写出一部在特定空间内进行关联性分析和叙事的全球史。
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全球史学者甚至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述“全球史”。在西方学术界,全球史的变体概念就有世界史、新世界史、新全球史、跨国史、跨文化史、交结史(entangled history)、连接史(connected history)等不同术语。这些术语的差异无论从字面上看有多大,但其内核是一致的,那就是:这些历史都是从关联、互动和整体的视角来审视跨国家、跨文化或跨地区的历史现象,并声称以此弥补民族国家史研究中的不足。
由此,什么是全球史?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首先,全球史作为对民族国家史的补充,就是要弥补民族国家史的不足,要在历史研究中突破“民族国家”这个框架的束缚,将问题置于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更广阔的情境中来理解。因此,如果一种历史现象可以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得到很好的解释,那么这种历史现象就不应成为全球史的研究对象,这项研究也不能说是全球史研究。相反,如果一种历史现象在其发生的民族国家框架里难以得到合理解释,必须要跨越国家边界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需要涉及区域甚至全球范围的相关因素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那么这个问题就应该是全球史问题,这种研究也就是全球史研究。其次,全球史具有不同于民族国家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当一个历史问题需要用全球史的方法来解决时,也就意味着这种历史是一种跨国家、跨文化、跨区域的历史,更加注重关联和互动,更加强调宏观的整体视野,在这种理念和方法下研究和书写的历史,也就是全球史。因此,笔者认为,全球史没有一种统一和固定的模式,可以由不同学者书写出不同的全球史,因此全球史是一种复数的历史,用英文表达即是global histories。
在西方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世界史”学科的存在,因此许多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全球史进行学科化时,使用了“world history”作为这个新兴学科的名称,这样使得world history和global history在西方国家几乎同义,在西方语境中经常通用。然而,在中国,由于世界史作为一个学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体系和特色,世界史是外国历史的集合,这决定了中国语境中的“全球史”与“世界史”是两个不同概念,并且都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全球史”,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全球史学科建设不同于西方。因此在中国,全球史不仅要弥补民族国家史的不足,还要弥补中国已有世界史的不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中国纳入世界之中。中国是世界之中国,世界是包含中国之世界。这种全球史可以发展成为中国史和(中国的)世界史之外的一个历史分支领域,因而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正如首都师范大学设立的全球史专业。当然,全球史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民族国家史研究的“全球转向”。作为研究方法的全球史,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是融为一体的。
关于什么是全球史及相关理论和方法,西方和中国学者都有过讨论。在西方,帕特里克·曼宁的《世界史导航》(2003),柯娇燕的《什么是全球史》(2008),入江昭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2013),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的《全球史导论》(2013)和《全球史是什么》(2016),都从理论和方法上探讨了全球史。这些作品对全球史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界对全球史的一个认识过程。曼宁的著作基本上是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刚刚确立的全球史学科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一种总结,目的在于为人们学习和研究全球史提供一些指南性帮助。柯娇燕的著作则是对以往西方宏观世界史的一种学术史概括,并由此提出全球史更多地是一些宏观历史分析和叙事的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归纳在分流、合流、传染、体系4个范畴之下。现在看来,这两本书都因为成书较早而只是反映了全球史初兴之时的状况,以及作者基于当时已有相关成果的思考。入江昭对全球史的思考同样也是从学术史入手的。他积极提倡跨国史,但也许由于他发现不可能讲述一种脱离全球史而存在的跨国史,因此将全球史与跨国史一并作了简要介绍。康拉德的著作出版时间相对较晚,因此也比较好地反映了近年来全球史的发展状况,以及作者在此基础上的有益思考。
康拉德倾向于认为全球史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视角,其研究对象并非要囊括全球,而是将历史现象置于一种全球情境中来分析。因此“全球”的含义不是指地理空间上的全球范围,而是指一种思考问题的全球视野。他对全球史这一定位无疑是合理的,也充分考虑到了已有的大多数全球史研究实践。不过,笔者并不赞同他将跨国史置于全球史之外,这种区分实际上也有悖于他对全球史的解释。如果说全球史是从“全球”视角对各种历史现象的探讨,是复数的历史,那么跨国史也是其中的一种。从跨国史兴起的背景及相关研究来看,它更是全球史多元实践中的一元。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研究美国史及美国外交史的学者为了打破美国例外论,提出将美国置于全球情境中来理解,由此产生了跨国史。因此,对民族国家的一些历史现象进行跨国化理解,实际上是在全球史兴起和历史学“全球转向”的大背景下,从“全球”视角来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及相关跨国历史现象。这种历史与全球史没有本质区别,将它看作是全球史多元实践中的一个流派是合适的,而在考察跨国历史现象之时仍然保留民族国家作为思考单元,正是这一流派区别于其他全球史流派的重要特点。
康拉德在提出自己对全球史的理解之时,特别讨论了全球史书写中的反欧洲中心论问题,认为“将全球史从以欧洲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难题”[②]。不过,笔者认为,反欧洲中心论是全球史学者应该牢记的初衷,但不能成为全球史研究中的负担。因为,在全球史兴起之时,从事全球通史编纂的学者力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将此作为全球史书写的一个重要目标。这种理念在其后全球史的发展中一直得到坚持,尤其是在涉及西方兴起、欧洲扩张及东西方关系的历史叙述时,反欧洲中心论成为全球史研究和书写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全球史发展过程中的多元实践,尤其是全球微观史的兴起,一些个案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警惕欧洲中心论叙事,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考察非西方世界中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移民,就不像编纂宏观世界史那样必然会涉及欧洲中心论。因此,对于全球微观史研究,是否应该避免欧洲中心论叙事,应该根据研究主题来酌情处理,“反欧洲中心论”不应成为这种研究的理论负担。
实际上,关于如何书写全球史、为谁书写全球史的问题,自全球史产生以来,就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之中。这一张力来自于全球史书写应该具有怎样的目标,是建构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意识、服务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还是从特定民族视角出发、服务于特定民族或民族国家的历史。具有理想主义或世界主义色彩的全球史学者认为,全球史应该是从“世界公民”视角、在摆脱民族国家立场和反对各种中心论叙事的情况下书写的一种各地各民族都能接受的历史。这种学者的早期代表如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全球史应该是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而形成的叙事,他的初版《全球通史》就标榜如此,倡导书写一种“世界公民”视角的全球史。后来,马兹利什在其《文明及其内涵》(2004)、《新全球史》(2006)、《全球时代的人道观念》(2009)等著作中,也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最终会走向一种共同的“全球文明”。入江昭在其《全球共同体》(2004)、《我们生活的时代》(2014)等著作中,也乐观地相信全球化的发展正在弱化民族国家而走向一种全球共同体。因此他们都主张历史学家应该顺应全球化潮流,研究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历史。然而,许多全球史学者承认自身仍处于民族国家时代这一现实,认为在此条件下的任何一种历史书写都具有主观的位置性,即历史书写具有自己的视角和出发点。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生活组织形态的情况下,历史学不可能实现去民族国家化,生活于民族国家之中的历史学者也不可能不打上民族国家的烙印。因此,他们不太关注“理想”而倾向于探讨“问题”,全球史的微观化和实证化研究由此蓬勃发展起来。可以说,至今已有的全部全球史成果,都处于理想的全球史与现实的全球史这个连续统一体两端之间的某一点。大致可以说,从理论层面思考全球史的学者,较多地谈论理想的全球史,而从历史个案出发的实证研究者,其成果则更多地是现实的全球史。《白银资本》、《大分流》,《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棉花帝国》等全球史经典之作,都是其中偏于现实的研究成果。
中国学者也有对全球史的各种讨论,例如,何为“全球史观”、全球史是否应该书写全球、全球史研究是否使用原始资料等等。这些问题到今天已无需讨论,因为全球史的各种研究实践(尤其是实证的全球微观史)已经对此做出了回答。不过,也有极少数学者没有看到各种全球史的实证研究及相关成果,而是强调理想主义学者倡导的那种全球史,由此批评“全球史”是一种“民主化”史学。这种脱离当今全球史整体学术状况来抽象地谈论全球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历史学的思考。实际上,从现实来看,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惠者,因此中国政府也竭力倡导经济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今天,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全球史从历史视角来理解全球化,因而成为一个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学分支领域。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全球史,更多地是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而不是一种站在全球立场的历史。
二、全球史的思考视角和研究路径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全球史相对于以往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现了历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历时性的内源性解释是历史分析的主要方法,即对一个人、物或事件的理解,建立在对其前因后果和内在因素的分析之上。然而,对于全球化时代发生的一些历史现象,由于它与外部有着密切联系,着眼于从一个更大的空间来看待并进行分析,就有可能弥补内源性解释的不足,甚至颠覆以往的看法。因此,历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就是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更大的空间来考察,拓宽观察的视角,从历时性分析转向共时性空间维度的思考,强调历史现象之间的横向关联和互动,从而更好地解释历史。
“社会空间”这个概念在全球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全球史学者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或地方框架,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突破了各种政治或地理边界的流动空间。这种空间可以是有形的区域性空间,例如海洋、帝国、贸易圈等,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由交流网络构成的空间。但全球史的叙事空间更多地是没有固定形态的流动空间,例如,移民或旅行者的流动轨迹,物品或思想观念的流动范围,由中心与边缘构成的关系结构,各种跨国组织等等。这种空间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是它因不同的研究对象而不同,另一方面是它因同一研究对象的流动而变化。例如中国瓷器传播到欧洲与英国人移民北美,就涉及到不同的空间,而瓷器从东到西流动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变化的空间。因此,在全球史研究中,并不像民族国家史研究那样事先有一个给定的空间――民族国家范围,而是全球史学者在确定研究对象之后,根据研究需要来构建空间。这种空间随着人或物的流动而流动,研究者应该根据史料和论题,确定一个分析和叙事的空间来服务于主题阐发。为何“社会空间”构建在全球史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要因为全球史的实证研究,并非全然要探讨一个确定的全球范围的历史,“全球”只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意识或视角,因此对于研究的空间范围应该有多大,要由研究者根据研究主题来确定。
那么,在全球史研究中,究竟选择多大的空间范围才是合适的?这完全由全球史学者的研究旨趣和主题需要来确定。不过,从已有的全球史成果来看,根据研究的切入视角和路径,全球史研究的空间范围从大到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大历史。如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弗雷德•斯皮尔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等,将人类史纳入宇宙自然史的范围来考察。(二)宏观世界史。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等,无论通史还是某一时期的历史,涉及的范围都是全球。(三)全球视角下的区域史。此类研究强调区域体系以及区域间的互动关系,或者对不同区域进行比较。例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等。(四)专题性全球史。即对同一主题或同类现象进行全球史的专题研究,包括政治事件、制度、性别、移民、贸易、技术、思想观念、生态环境、疾病等,因此这类研究空间是随着主题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菲利普·柯丁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帕特里克·曼宁的《世界历史上的移民》等。(五)流动个案研究。最常见的包括对移民、旅行、商品流通、观念传播等方面的个案研究,如罗斯·邓恩的《伊本·巴图塔的冒险经历:一个14世纪的穆斯林旅行家》,大卫·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斯温·贝克特的《棉花帝国》,科莉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等,这里涉及的空间随着研究对象的流动而变化。(六)关联和互动视角下的小地方研究,即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个案研究。这种研究就是把卷入全球化之中的某个小地方置于广阔的关系情境中来理解,通过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关系,从大世界来理解小地方,从小地方来窥视大世界。例如唐纳德·怀特的《世界与非洲的弹丸之地:冈比亚纽米地区的全球化史》,卜正民的《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等。
在全球史研究中,“互动”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工具。从威廉·麦克尼尔的文明互动到杰里·本特利的跨文化互动,全球史学者关于“互动”的阐述得到发展,它也由此成为全球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不过,“互动”作为全球史研究中的一个术语,应该与中文日常生活语境中的“互动”区别开来。在全球史兴起之前,“互动”一词在中文中已经存在,通常指日常生活中个体间一种相对平等及和平的关系,即日常所说的人际互动。然而,全球史中的“互动”一词由英文interact(名词interaction)翻译而来,这个词在以往的英汉词典中都解释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没有“互动”这一表述。全球史将其译为“互动”,本质含义仍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存在于两个主体之间,无论二者是否平等,也不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涉及暴力,因此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广义的“互动”,威廉·麦克尼尔、杰里·本特利、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等许多全球史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不是指个体间的关系,而是指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和平和平等的,也可以是权力不平等条件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甚至暴力冲突也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因此,他们将“互动”一词用于欧洲扩张过程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就不足为奇了。在中国,“互动”一词在全球史语境与生活语境中的这种差异,犹如“批判”、“反动”等概念在哲学语境与生活语境中的差异一样,应该区别开来。
以互动为基础形成的“网络”,也是全球史学者构建其研究主题所需的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概念。借助于这个概念,全球史学者得以将研究个体结构化,进而将微观个体与宏观结构联系起来,从而做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例如对国际移民的研究,考察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如何实现迁徙、怎样融入新的社会,可以借助于移民过程中和进入新社会环境中的人际关系网络来理解,而这个关系网正是把微观个体与国际背景联系起来的中层结构。由此,借助于网络这一概念,研究者得以书写出一种考察国际移民个案的全球微观史。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史中的流动、联系、互动、网络等概念,只是全球史研究中思考问题的视角和解释工具,是实现研究目标所借用的手段。如果,把这些借以理解世界历史中各种问题的概念工具,当成了全球史的研究对象,即以考察世界历史上的流动、联系、互动和网络为目标,如果说这也算得上全球史研究的话,充其量只是一种初级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放弃了对这些概念背后深层历史问题的思考和揭示。
三、本书的基本框架
自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在研究生中开设全球史专业以来,笔者一直担任“全球史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因此本书的构想也源于10年前教学的需要。没有预料到的是,本书的完成竟然花了10年时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全球史在这10年间的快速发展,新的成果不断涌现,这给概述全球史的各种实践带来了困难。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不断调整结构和增添新内容。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全球史作为一个历史学新兴领域和审视历史的新方法,尽管还会有发展变化,但总算基本成型了,这是我们得以完成这本概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当然,如前所述,全球史是一个复数概念,本书内容只是根据我们对全球史的理解而写成。作为概论性的入门书,我们力图对各种全球史研究实践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以期达到全面介绍全球史的目的。
本书第一至三章是对全球史兴起的学术史回顾。第一章考察了全球史兴起之前欧洲和中国的世界史传统。在欧洲,“普世史”一直是史学书写中的一种传统,虽然在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之后为民族国家史的大潮所淹没,但这一传统并没有中断,并为20世纪下半叶全球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中国的世界史是泊来品,在20世纪上半叶初步形成了以西洋史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史。从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史在中国开始成为一个学科,但它主要由外国国别史构成,即使有世界通史,也是主要是对中国之外各国历史的合编。第二章考察了全球史在美国的兴起。20世纪50-80年代,威廉·麦克尼尔、马歇尔·霍奇森、斯塔夫里阿诺斯、菲利普·柯丁等人的全球史探索标志着全球史在美国的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史在美国作为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确立起来,并在研究和教学方面获得了快速发展,还出现了相关研究的争鸣。到世纪之交,全球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思潮开始蔓延至世界上其他国家。因此,第三章介绍了全球史在欧洲和中国的兴起及研究状况。全球史的发展在世界各地并不均衡。那些积极参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在政治上比较稳定的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日本、中国等,接受了全球史并且发展较快。而在非洲、南美洲和东南欧的许多国家,由于经济欠发达和不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甚至有的还面临着国家构建的任务,因此民族国家史在其历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全球史没有得到发展。因此,本书在介绍美国之外的全球史发展状况时,主要集中于英国、德国、法国和中国。
介绍全球史的分支领域和研究方法是本书的主要目标。因此从第四章起,我们根据已有的各种全球史研究实践进行分类,考察了全球史的各个分支领域及相关研究方法。其中,第四至七章介绍了全球通史、跨文化互动、比较世界史、新全球史和跨国史等全球史的研究领域,但它们并不是全球史学者要考察的实体历史单位,而更多地是从研究方法来说的,因此这几章实际上是在探讨全球史研究和书写的主要方法。第八到十章则着重介绍了全球史研究中几个活跃的分支领域,包括帝国史、海洋史、生态环境全球史、大历史/小大历史,这些研究领域具有历史实体性,可以成为全球史学者的研究对象,但它们也涉及到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因此各章在介绍这些领域时也探讨了相关研究方法。
全球通史和各种形式的宏观世界史是全球史的一种书写形式,这种历史书写形式与大学历史教育密切相关,因此用于大学教育的世界通史成为最初形式的全球史。本书第四章通过介绍美国主要的全球通史著作,对全球通史编纂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世界历史上的大规模历史进程主要通过跨文化互动来实现,因而跨文化互动成为理解全球史的一个关键因素和核心概念。以杰里·本特利为代表的全球史学者从理论视角考察了跨文化互动,提出了移民与流散社群、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扩张与殖民等几种跨文化互动的主要形式。因此本书第五章就对“跨文化互动”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理论阐述,同时考察了移民与流散社群、跨文化贸易、相互认知和文化交流这三种跨文化互动形式,并探讨了其中所蕴含的研究方法。第六章探讨了全球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比较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早已有之,但全球史学者在探索全球史研究及书写方法之时,将这一方法发扬光大了。菲利普·柯丁实施了“比较世界史”的研究项目并取得了许多成果,彭慕兰等加州学派的学者则运用“交互比较”方法来考察中西“大分流”的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第七章探讨了“新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研究方法。马兹利什提出的“新全球史”和入江昭等人提出的“跨国史”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探讨的对象都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现象,因此关注跨国历史现象和憧憬一种“全球文明”或“全球共同体”,强调对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跨国组织的研究,使得这两个全球史流派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相似之处。本特利之所以强调跨文化互动,是因为他关注的前现代世界,民族国家尚未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形态,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重要的是文化差异。而入江昭之所以强调跨国,因为他关注的是现代世界,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形态,历史学家需要突破的是国界而不是本特利所面临的文化边界。因此,跨文化史和跨国史在研究理念上没有本质区别,是全球史研究中因关注不同时代而导致差异的两个不同流派。
第八章考察了全球史研究中两个非常活跃的新兴领域――新帝国史和新海洋史。帝国史和海洋史在全球史兴起之前已经存在,但全球史与新文化史等其他新兴分支学科的介入,赋予了这两个研究领域以新的活力,由此称为“新帝国史”和“新海洋史”。以前被忽视的种族、性别、移民和流散社群、身份认同、互动网络等研究主题,在新帝国史和新海洋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九章考察了环境史与全球史交叉的研究领域――全球视角下的生态环境问题。历史上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物种交流、疾病传播等现象都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而是具有跨国性、跨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因此这些问题也必然成为全球史的研究领域。这一章主要以克罗斯比、威廉·H.麦克尼尔和约翰·R.麦克尼尔的研究为例,探讨了生态环境全球史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主题。本书最后一章是对大历史的介绍。大历史探讨的是人类起源与进化、生命体和地球甚至整个宇宙的演化,是宇宙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综合,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它不属于全球史的范畴。然而,由于大历史学者与全球史学者有着共同的人文情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也由于大历史学者试图将大历史基本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人类历史研究,提出了“小大历史”,而这种大历史理念下的微观历史研究实践完全可以纳入全球史的范畴,因此本书专辟一章来阐述大历史。
从本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国内读者提供一本全面介绍全球史的概论性著作,而不是深究全球史应该是什么和对相关理论的抽象讨论。因此本书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力求系统地介绍全球史。由于全球史是在历史学“全球转向”这一大背景下开展的历史研究多元实践,流派纷呈,对这些流派进行系统梳理和介绍,有助于读者对全球史形成一个较为清晰全面的总体认识。其次,注重从方法论上对已有的全球史研究进行总结,对全球史主要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概括分类。全球史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不同学者的不同探索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径和方法,因此我们综合地根据研究对象、视角和方法,将已有研究成果分成不同的领域加以考察,每一个领域也可以说反映了一个全球史的流派。这样有利于读者在了解全球史时各取所需,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来阅读和参考。再次,我们希望为国内初学全球史的同学提供一本通俗易懂的入门教材。因此,本书在写作中也考虑到了教学的需要,尽量减少抽象的理论探讨,多从实用视角分析介绍经典的全球史成果及其研究方法,尤其注重那些选题适中、运用原始资料进行研究的全球史著作,让读者感到全球史研究的可操作性。
当然,由于全球史仍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新兴领域,每年都有大量新成果问世,本书的阐述不可能囊括全球史研究的全部成果,必然有所遗漏。另外,作为复数的全球史,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本书体现的只是我们的一种理解。因此,书中不足之处,还请同仁不吝指正。
[①]欧阳泰:《一个中国农民、两个非洲男孩和一个将军――全球微观史的研究取向》,《全球史评论》第七辑,2014年12月,第45页。
[②]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43页。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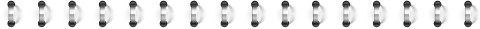

首师大全球史中心
公众号ID:gh-cnu
欢迎关注,谢谢大家~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